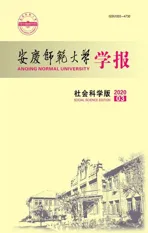隐没的史家:朱书的晚明史研究述论
2020-12-29江伟
江 伟
(安徽省宁国中学历史教研组,安徽宁国242300)
朱书(1654—1707),字字绿,一字紫麓,号恬斋,别号杜溪,安徽宿松人,清初杰出的学者,一生著述丰厚。据初步统计,有《杜溪文稿》《杜溪诗稿》《朱杜溪稿》《游历记》《癸壬录》《闽游诗》《评点东莱博义》《松麟堂偶钞》《古南岳考》《恬斋日记》《恬斋纪闻》《恬斋漫记》《寒潭琐录》《谋野录》《糊饦集》《仙田诗在》《朱氏家谱》等十余种,还参加过《宿松县志》的校阅和大型类书《佩文韵府》《渊鉴类函》的修纂。但是,由于受戴名世“《南山集》案”和乾隆朝禁书令的影响,朱书的著作沦毁几尽,存者十不足一。清中叶以后,学人开始收集朱书散佚的诗文,初步探讨朱书的学术成就。然而,时至今日,学界大多将朱书视为古文家,注重他在文学方面的成就,对于他的史学成就,则鲜有研究。据笔者所知,目前只有吴航《清代南明史撰述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一书对朱书的史学成就略有涉及。本文拟在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朱书在晚明史研究上的成就,以期抛砖引玉,进一步深化朱书史学研究。
一、朱书晚明史撰述考略
朱书是清初古文名家,然其学术追求却是史学。他的史学成就主要集中在明史领域,正如他的好友方苞所说:“(朱书)尤熟于有明遗事”[1]。在明史研究中,朱书对晚明史(包括南明史)又着力甚勤,成就最大,其史学撰述大多集中在这一领域。
(一)《癸壬录》
《癸壬录》是朱书的史学代表作。是书记事上起明万历元年癸酉(1573),下至清康熙元年壬寅(1662),历时90年,取“癸酉”“壬寅”两个纪年的首字,故名《癸壬录》。《癸壬录》内容涉及面很广,朱书在《自序》中介绍说:是书“上而朝廷之爵赏予夺、巡幸播迁,下而朋党之角争盛衰、往来报复,内而宫闱宦竖之显晦,外而督抚勋镇之战守,以至忠臣之捐躯湛族,义士之穷饿远遁,莫不见于是编”[2]20。
《癸壬录》今不存于世,故无法得知其篇目。查阅康熙《杜溪文稿》,发现该书卷二录有《癸壬录自序》一文,卷六又有《龙眠愚者方公家传》《金中丞传》二文,题下小注都说“入《癸壬录》”。朱书为友人张符骧文集《依归草》作序又说“属有《癸壬录》之编,乃作《艾御史传》寄良御(张符骧,字良御——引者注)”[3]。可见,《艾御史传》也是《癸壬录》中的一篇。有学者据此推断,《癸壬录》很可能是传记体史书,或至少存在为数不少的传记[4]。
《癸壬录》之所以不存世,是受到文字狱的影响而毁。由于受康熙朝戴名世“《南山集》案”和乾隆朝频繁文字狱的影响,朱书的著作大多沦毁不存,幸存下来的只有诗文集等数种而已。据此可以推断,《癸壬录》就是在这两次文字狱中被禁毁的。乾隆四十七年(1782),闽浙总督陈辉祖奏缴应毁书籍,将《杜溪文稿》列入应禁书籍清单:“《杜溪文稿》一部,刊本。……其稿内《癸壬录自序》一篇,语意更为狂谬。”[5]《自序》尚且“狂谬”,其书必定更是如此。《龙眠愚者方公家传》是《癸壬录》一书存世文章之一,系桐城方以智之传。崇祯帝自缢后,方以智辗转南下投奔南明弘光政权,后又任职于隆武政权和永历政权。清军大举南下之后,方以智秘密组织反清复明,被捕之后又拒绝投降清朝。而且,该文还多次提到南明诸帝的庙号、年号。这样的文章在书中一定还有很多,这是清政府不能容忍的。可见,《癸壬录》一书是因为触及了清政府的忌讳,以致被禁毁。
(二)《皖江先贤(耆旧)传》与《皖江文献》
朱书鉴于国史、方志对乡邦(安庆六邑)人物记述的不足,决定撰写乡邦史书《皖江先贤(耆旧)传》。他说:
伏惟鉴汉唐宋皖人之寡传,乐元明至今之独盛,依小史、外史之义,以成先贤耆旧之纪载,而不为史志之所遗略,则六邑君子必有毅然任之者。书得从其后,以观成焉,不亦美乎?元以前皖人入史志者,不复具,惟蒐明至今止,凡显仕、隐晦、独行概为立传。有著作可传者,别为一书,名曰《皖江文献》[6]11。
由此可见,《皖江先贤(耆旧)传》是一部乡邦传记体史书,记事上起明初,下至清康熙年间。因此,晚明之后的人物也必然在记述之列。文中所谓“隐晦”“独行”,应该就是指那些抗清义士和不仕清廷的遗民。《皖江文献》则是一部资料汇编,必然包括明末清初人物的著作。然而,今未见《皖江先贤(耆旧)传》和《皖江文献》二书,故二书应该毁于文字狱,也可能没有完稿。
(三)其他撰述
除了上述著作之外,朱书还有不少撰述涉及到晚明史。乾隆四十年(1775),安徽巡抚裴宗锡上奏称,缴获《游历记》《闽游诗》等24种“违碍”书籍,这些书“非系及宏光、隆武等伪号,即有悖逆诋毁触碍语句,种种缪妄,殊堪痛恨,应请销毁”[7]。可见,朱书《游历记》《闽游诗》二书,应该记述了很多南明史实,故而遭到查禁。
据朱书在《游历记自序》一文中说:“予生平好游,今天下疆域凡十五区,予足迹所到已三之二。于是仿桑钦、郦道元以道里为经,以见闻为注,作《游历记》若干卷,曰两畿、曰燕秦、曰燕梁、曰秦楚、曰闽豫章入燕、曰闽浙入扬州、曰江行。”[8]《游历记》是一部历史地理学著作,今有《燕秦之道》一卷存世,文中并没有清廷忌讳的文字。可见,该书涉及南明史的内容都在沦毁部分。《闽游诗》是朱书客居福建时所作诗歌,原有150 余首,今只有十来首存世。雍正末年,朱书长子朱晓重刻《杜溪诗稿》,回忆说:“《闽游诗》百五十余首,刻过五十首,板亦不存,今从王年伯方若所订刻之。”[9]《闽游诗》在乾隆禁书之前便已毁板,可见是受到了戴名世《南山集》案的影响。可以推知,《闽游诗》是一部以诗写史的著作,可能涉及到南明鲁监国、隆武两个政权的相关人物及台湾郑成功的事迹。
此外,朱书还有不少单篇文章也涉及到晚明史,这些文章散见于他自己的文集或者附录在他人的诗文集中。
二、对明亡断限及明朝败亡原因的探讨
朱书的晚明史撰述大多湮没不存,故不可窥览其内容。然而,根据朱书现存诗文,可以初步认识朱书晚明史撰述的内核。他对明亡断限的看法,对明朝败亡原因的分析,都具有重要价值。
(一)明亡断限和清朝正统问题
明亡断限,即明朝终结于何年,是清初史学界探讨的核心问题。据研究,清初史学家对明亡断限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亡于崇祯朝,二是亡于弘光朝,三是亡于永历朝[10]。朱书主张明亡于永历朝,他甚至公开提出“明祀绝于壬寅”[2]20,也就是说,明亡于永历十六年,即清康熙元年(1662)。
清初,明亡断限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更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因为明亡断限与清朝正统起始密切关联。确定明朝亡于何年,也就确定了清朝何时开始成为中原的正统王朝。朱书将明朝终结的时间定在永历十六年,意味着他将清朝正统起始时间定在康熙元年。也就是说,朱书不承认清顺治一朝的正统地位,而是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各政权为正朔。在清初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下,朱书敢于明言明朝亡于永历十六年,这种无所畏惧的史学精神无疑值得后人敬佩。法国学者戴廷杰推崇说:“当其时,如是之言,罕闻极甚,盖人意中有,笔墨间无矣。”[11]
(二)明朝败亡原因的分析
朱书晚明史撰述的学术宗旨,主要在探讨明朝灭亡的原因,总结历史教训。在朱书看来,明朝灭亡不仅在于“天命”,更是因为“人事”,具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帝王失德。朱书对崇祯帝及南明诸帝痛加贬斥,认为诸帝用人失误,导致明朝灭亡。他说:
嗟乎!明之亡也,固若斯之易乎?得天下有二道,曰英明,曰宽厚;失天下亦有二道,曰刚愎,曰愚柔。崇祯英明,而弘光亦不失为宽厚,宜可以守天下而无失,而究与刚愎、愚柔同尽。悲夫!卫灵公无道,以圉、贾、鮀三人而不丧。今即使尧舜在上,而所用者温体仁、马士英,亦必不能治,况其他乎?[12]
他进一步批评道:
北都沦丧之后,一建南都,再建闽海,三建肇庆,由是迁武冈,迁南宁,迁安隆,迁云南,寄命缅甸,以终焉。方其始也,地大于昭烈、宋端,亲近于晋元,统正于李昪、刘崇,而所仗以立国者,则昏贪之马士英,海贼之郑芝龙,叛降之刘承胤、陈邦傅,流贼之孙可望。人主既无股肱心膂之托,而清流又或从而激之,夫安得而不败?[2]21
不仅如此,南明诸帝每当面临清军进攻之时,往往弃城而逃,以致不可收拾。朱书说:“即以明论,景泰不迁而存,弘光、隆武、永历皆奔迁而亡。崇祯时,京师戒严者四,不迁亦不亡。”至于后来崇祯帝不迁亦亡,朱书则归结为“天命”,非人力所为[13]。
第二,党争误国。朱书对明朝败亡原因的考察,并不限于就事论事,而是注重历史溯源,推原祸始。他认为,朋党之争是明朝败亡的重要原因,但党争之祸却始于万历年间,“要其祸自万历初基之,而万历末即受之,所以基祸者不一端,而党为大”。因此,朱书指出:“明祀绝于壬寅,而其端伏于癸酉(万历元年——引者注)”。[2]22
朱书对明末党争之害的认识非常深刻。他评论道:“门户分,则其事也不急于疆场、重于国是,争者未息喙而国已亡矣。”[14]8又说:
而争门户者,不急国家之急,止急其党。是其党者,虽跖、蹻奉之登天,死犹有余美焉;非其党者,虽管、葛挤之入渊,死犹有余疾焉。收罗党人,智于朝廷之求策,力防异党之攻己而思去之,勇于将帅之除盗寇,卒至卑者泥首事仇,高者殒身膏斧,国与家俱尽,而向所争为党者,亦已烟消影灭,而不知何有,徒委君父于草莽而不能顾[2]21。
这样的论述,使我们看到明末朋党斗争所带来的影响。正是群臣朋比为奸,党同伐异,置国家安危存亡于不顾,这才错失了抗清的良机,以致败亡。
朱书还进一步探讨了明末朋党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官员讲学是结党的重要祸根,“夫讲学之名立,则附会者多。苟不得附,则忌之者众。内部必皆君子,外不能使人安于为小人,则门户分。”[14]8而掌握监察、弹劾之权的言官,为当权者利用,随意行使弹劾权,加剧了党争之祸。朱书叹息道:
然国之败亡,言官实与有责焉。自两党角立之后,内阁、六部不能自主一事,听之言官,言官又自相溃讧。其后,孙传庭宁出关以死,不肯复对狱吏。陈永福辈甘弃守汴之功,投身逆闯。不亦悲夫![15]
可见,朱书身处明亡清兴之际,对明末党争之祸有更深的认识,他的反思更为沉痛深刻,绝非泛泛而论。
第三,外攘失策。有明一代,北方的蒙古始终是明王朝的巨大威胁。朱书认为,明朝的败亡与明朝后期对蒙古政策的失败有着莫大的关系。他说:
夫秦据天下之首,河环东北,山塞西南,重险之固,号称天府。而屡忧不固、震及疆场者,何哉?其患不在无险,患在有险而无备也。王者苟能奋扬威武,则当收燉煌,守河外三城,复故疆土;不则闭关谢西域,毋疲中以事外。此二者,百世不易之道也。若明之季,既不能张挞伐之威,又不能划疆自守,矜受贡虚名,边备渐驰,使三百年之金瓯,始坏于西陲之彝,终纶于西陲之寇,外攘失策,内乃不安,故至此极也。[16]
朱书的这段评论相当精彩,他是透过历史现象去挖掘明朝统治衰微的深层原因。明朝隆庆年间,朝廷迫于蒙古右翼的军事压力,允许其“封贡”、互市,使宣府、大同以西获得了较长时期的安定。但是,明朝由此放松了对蒙古右翼的警惕,以致西北边境军备松弛,这给李自成农民军提供了机会。而且,蒙古右翼也没有真正臣服明王朝,此后又战争不断,根本没有达到朝廷所期望的目标,故朱书指出明朝政府是贪图“受贡虚名”、“疲中事外”。在抵御后金的战争中,明朝屡屡受到蒙古方面的牵制,进而逐步丧失抵御后金进攻的主动权。后世有学者指出,明朝后期对蒙古政策的失败是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17]。这一观点与朱书的论断不无相通之处。
第四,财力枯竭。明季,财政紧绌,以致对农民军、后金的战事不可为。朱书对此有深刻的认识,他说:
呼呼!有国家而亟言聚财,未有不至于败亡者也。盖尝观于有明之季,崇祯十余年间,天子恶衣菲食,不敢妄自靡费,然展转叹息,恒若窭子寒生,皇皇无策以支吾朝夕用,卒底于灭亡[18]1。
对于明末财政紧绌的原因,朱书认为在政治腐败。他进一步论述道:
延及穆、神,天下无虑,一切皆变而征银。于是奄竖群小之伦,皆得饱其私囊,天子之自供又日益溢。其大患,则屯盐废而边士无所得食。至其末年,边饷之增逾数百万,殚竭天下之膏血以输边,而士之守塞者,曾不得颗粒焉,往往去而为盗。水旱之备日驰,饥馑荐臻,追呼交迫,民亦以盗为薮。不得已,大出向年之所积,求其一救,顾适以藉寇赍盗,而举国以殉之,良可哀也[18]2。
换言之,万历之后,皇帝、宦官化公帑入私囊,严重削减了朝廷的财政收入。更严重的危害是,屯田不兴,水利不修,军民沦为盗匪者日多,从而减少了赋税来源。同时,为了镇压日益汹涌的农民起义军,朝廷又增加了一笔财政开支。也就是说,政治腐败使得明王朝的财政系统失去了再生功能,最终财力枯竭,以致无力支付巨额的军费。
三、朱书晚明史撰述的特点
通过对朱书诗文的解读,可知朱书的晚明史撰述特别重视史料的收集,对弃明贰臣的批判不遗余力。因此,朱书是一位史识绝伦的历史学家。
(一)注重史料收集
史料是历史学的基础。朱书为撰著晚明史,非常重视史料的收集。由于晚明去时不远,朱书特别注意从民间探访遗民故老、抗清志士子弟,以掌握各种传闻轶事,正如朱书自己所言:“书家世力农,三百年无一人通籍于朝,未睹金匮石室之藏,徒以中年好游,因合闻见为此书(即《癸壬录》一书——引者注)。”[2]2可以说,《癸壬录》一书的史料来源,很大一部分是通过调查走访得来的。云南是南明政权最后活动的区域,朱书未能亲往,但友人茹仪凤前往云南景东任职时,朱书还请他代为蒐罗史料,“西南轶事,尚望于政事之暇,为我蒐而示之”[19]。
朱书在探访传闻轶事时,更加注意搜集明人诗文、奏疏等一手史料和墓志、行状、事略、传记等重要的二手史料。他为了撰写《皖江先贤(耆旧)传》,撰文向安庆六邑征集文献,“敢告六邑同志之士,共为揽缀,或行状、事略、事略、传记、谱牒、碑铭之文,乞赐邮寄;有先贤奏疏、文集,并望借览,抄录纳还原本,不敢敝污。”[6]11《癸壬录》的撰著也是如此。朱书客居福州时,友人张岩为他提供了很多资料,“(张岩)家多藏书,喜借客钞,……予方编《癸壬录》,常常往其家借书”[20]。李嶟瑞则“以先曾外大父蒙修王公事迹寄之”[21],以助朱书。
朱书在搜集晚明史料的同时,还参阅了当时人所著晚明史的论著。如李清《南渡录》就是一例,朱书还撰有《书〈南渡录〉后》一文辩驳其观点。冯甦《见闻随笔》《劫灰录》二书是重要的晚明史著作,朱书“每以未抄为恨”,后从其子冯永年处见到二书,“辄大喜过望”[22]。
(二)痛斥弃明贰臣
出于儒家伦理观念,朱书在撰述晚明史时,对忠臣义士的表彰着墨甚多,《癸壬录》中就有不少忠节人物的传记。朱书在表彰忠节的同时,对投降李闯、满清的明臣又口诛笔伐,痛加贬斥。他讥讽这些贰臣对明王朝的忠贞程度尚不如南京灵谷寺中的银杏树:
其苗裔,即靖难后腰玉者,亦不乏也,受国家三百年爵禄之贵,而两都沦陷,其视腰玉不啻粪土而弃之如遗焉。树犹区区守先朝之赐玉,树殆不知时势之已改矣!庙社既墟,而后天地之间,惟海上一隅以赐玉终奉故朔,垂三十七年,今亦已矣。树又何贵于先朝之赐,而用以见奇若斯哉![23]
他甚至主张对贰臣以六等定罪,“宋企郊、牛金星等十人可磔,若得而即戮于市,不待议也,余则纵欲罪之,亦必俟北都既复,否则擒之贼中而后可也”[24]9-10。这样一褒一贬的评价标准,凸显了朱书关于忠节的价值取向。
值得一提的是,朱书特别注重明臣的晚节。如弘光时期的马士英、阮大钺,虽有结党误国之大罪,“而其不降犹可原”[24]10。
四、余 论
据前文所述,朱书将明亡时间定在永历十六年,意味着他不承认清顺治一朝的正统地位,而是奉南明为正朔。因此,对于清朝立国以后的史实记载,朱书均不书清朝年号,而是在明崇祯之后,续书弘光、隆武、永历之年号,将南明各政权视为明朝的延续。在朱书的撰述中,还称崇祯帝为“烈皇帝”,称弘光帝为“安宗”。烈皇帝是南明弘光帝为崇祯帝所上谥号,安宗是南明永历帝为弘光帝所上庙号,而清廷给崇祯帝所定谥号是“愍皇帝”,弘光帝则被指斥为僭越帝号。可见,朱书的晚明史研究,是在站在明朝立场进行书写,这缘于朱书强烈的遗民情结。
朱书出生于顺治十一年(1654),严格来说,他并不是真正的明遗民。然而,朱书却将明亡定在永历十六年(1662),则朱书自视为遗民。在故国已亡,空怀抱负的情况下,他只好将自己的亡国亡君之恨诉之笔端,撰史总结先朝败亡的教训,寄寓亡国之痛,抒发故国之思。不过,需要说明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之朱书又入仕清朝,他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这种遗民情结也在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