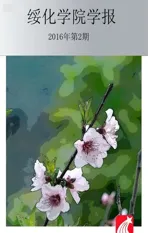诏令范畴下的“策”体辨析——以汉代诏令为例
2016-04-13魏昕北华大学文学院吉林吉林132013
魏昕(北华大学文学院 吉林吉林 132013)
诏令范畴下的“策”体辨析——以汉代诏令为例
魏昕
(北华大学文学院吉林吉林132013)
摘要:“策”体在汉诏中大抵可分为三类,即策书、策告和策问。策书通常用于人事的升降任免;策告是以简册相告于天地、宗庙、神明;策问则用于选拔贤良文学、博士弟子等人才。关于诏令类“策”体的辨析,在诸家评述中多有涉及,其主要从考竟源流和分类辨析纵横两方面对“策”体加以梳理,既反映了“策”体功能的多样化,亦说明绝大多数功能早在汉代已经存在的事实。可以说,“策”体的细化,既是文体自身规范化的结果,而很大程度上更有赖于评述者的归纳和总结。
关键词:现诏令;汉代;策书;策告;策问;辨体
据《汉官解诂》记载:“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惟此为异也。”[1](P23)这是说,在汉制规定中,皇帝的命令被分为四种,而策书即为其中之一,其功能在于册封诸侯王或罢免三公。《文心雕龙·诏策》亦曰:“汉初定仪则,则命有四品: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敕。……策封王侯。策者,简也。”[2](P358)可见,“策”体在汉制规定的诏令范畴下,指的即是用于人事升降任免的策书。然这一制度性界定,与“策”体在汉诏中的实际使用情况颇有出入,如武帝时颁布的“策贤良文学诏”,实是对贤良文学的命题考试;平帝选后之际,太后则下诏“策告宗庙”;王莽在位期间,“作告天策,自陈功劳”……这些“策”体虽属诏令范畴,然与策书的功能迥然有别。这也使得后世的文体评论者在辨析和总结“策”体功能时意见不尽相同。本文即试图在梳理汉诏“策”体使用情况的基础上,对诸家评述作以分类剖析,以期对诏令范畴下的“策”体功能有进一步明确、深入的认识。
一、汉诏规定中的策体:策书
关于策书,蔡邕《独断》在《汉官解诂》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具体介绍:“策者,简也。礼曰:不满百文,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长一短,两编,下附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曰。以命诸侯王三公。其诸侯王三公之薨于位者,亦以策书诔谥其行而赐之如诸侯之策。三公以罪免,亦赐册,文体如上策而隶书,以一尺木两行。唯此为异者也。”[3](P子部850-78)从中可知,汉制下的策书可分为三类:其一,册封诸侯王和三公;其二,悼念并追封去世的诸侯王和三公;其三,罢免三公。具体来看,三类策书体式分别如下:
(一)册封体式。关于诸侯王的册封,在体式上颇具典型意义的,当属汉武帝元狩六年册封三王的策书。据《史记·三王世家》载:“孝武帝之时,同日而俱拜三子为王:封一子于齐,一子于广陵,一子于燕。各因子才力智能,及土地之刚柔,人民之轻重,为作策以申戒之。”[4](P2114)这三则策书的行文如出一辙,内容大抵一致。以《齐王策》为例:
维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汤庙立子闳为齐王,曰:于戏!小子闳,受兹青社!朕承祖考,惟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于戏!念哉!恭朕之诏,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显光。义之不图,俾君子怠。悉尔心,允执其中,天禄永终。厥有愆不臧,乃凶于乃国,而害于尔躬。于戏,保国艾民,可不敬与,王其戒之。[4](P2111)
策文首先交代了举行册命的时间和空间,以及颁布册命的执行者等几个要素。接下来,册命的主体被分为两部分:一是宣告册封之命,阐明册封的神圣意义:继承祖考之命,在封土之上建立国家,以达成“世为汉藩辅”的长远目标。二是向受命者施以告诫之言,强调务修德行,方可使其国祚长久;并申明“保国艾民”的神圣使命。整体来看,策书呈现出古奥典雅的语言风格;而诸如“朕承祖考,惟稽古,建尔国家,封于东土,世为汉藩辅”这样的语句,则成为模式化套语,在三则策书中被反复使用。三则策书如出一辙,说明在册封诸侯王方面,策书体式在武帝时期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规制。
册封三公的策书,在《汉官旧仪》和《汉仪》中皆有所收录,说明其此类策书体式亦具备了一定的规制。以宣帝策丙吉丞相一职为例:
惟神爵三年十月甲子,丞相受诏之官,皇帝延登,亲诏之曰:“君其进,虚受朕言。朕郁于大道,获保宗庙,兢兢师师,夙夜思过失,不遑康宁,昼思百官未能绥。于戏丞相,其帅意无怠,以补朕阙。于戏群卿大夫,百官慎哉,不勖于职,厥有常刑,往悉乃心,和裕开贤,俾之反本乂民,广风一俗,靡讳朕躬。天下之众,受制于朕,丞相可不慎欤?于戏!君其诫之。”[1](P39)
从策书格式来看,其与册封诸侯王的区别并不大。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册命过程中,突出了“皇帝延登,亲诏之”,意即皇帝将受命者引入登殿,亲自册封授命。据《北堂疏钞·设官部》载:“诸王在长安,位次三公。”可见,三公的位置要高于诸侯王,故皇帝“亲诏之”,正显示了三公身份的尊贵。这一点也从称呼上体现出来:与直接称诸侯王为“小子”相比,对三公的称呼则要庄重、委婉得多:“君其进”,“御史大夫其进”,以尊称或官职来称呼受命者,并示之“其进”,表现出尊敬和亲切的态度。在述及册封意义时,皇帝还往往宣称自身处于高位的谨慎和戒惧,从而向三公表明其辅佐朝政的重要使命。册封三公也形成了一些固定的套语,如“朕郁于大道,获保宗庙,兢兢师师,夙夜思过失,不遑康宁,昼思百官未能绥”这样的表述,也同样出现在宣帝任命杜延年为御史大夫的策书中。
(二)吊唁体式。吊唁策书乃是针对去世的诸侯王和三公而言,前者如章帝时的《东平宪王哀册》;后者如顺帝时的《策祠杨震》《会葬宋汉策》,灵帝时的《追赠杨赐册》,它们都是体式完整的吊唁策书。
从行文来看,吊唁策书普遍以四言句式为主,语言风格颇为庄重、肃穆。策书大抵包含几方面内容:追述逝者的德行、功绩;表达朝廷的哀悼之情;向逝者进行追赐。但每则策书的具体表述各有千秋,并未形成固定的格式和套语,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逝者个人的际遇有关,不同的哀悼对象有着彼此各异的德行、经历和功绩,这便使得策书吊唁的语言不能一概而论。
如《策祠杨震》和《会葬宋汉策》虽同为顺帝所颁,然两则策书却因哀悼对象的不同境遇,各有偏重:由于太尉杨震乃为樊丰等人谗害而死,其死后天下屡遭灾异,故吊唁策书着重于对杨震平反昭雪,肯定其正直的品行;并且皇帝因灾异宣称“朕之不德,用彰厥咎,山崩栋折,我其危哉”,以示罪己。[5](P1767)而太中大夫宋汉,曾“四迁西河太守。永建元年,为东平相、度辽将军,立名节,以威恩著称。”故策书着重于对其军功的表彰:“前在方外,仍统军实,怀柔异类,莫匪嘉绩,戎车载戢,边人用宁。予录乃勋,引登九列。”其中更引《诗经·大雅·江汉》中的诗句,将宋汉比作平定淮夷的召公,褒美之辞溢于言表。[5](P905)
(三)策免体式。策免策书主要是就罢免三公而言,如宣帝策免御史大夫萧望之,哀帝策免大司空师丹等等。与册封策书相比,策免策书并未将颁行策书的时间、地点、以及执行策免之人作为构成策书体式的必然要素。策免体式的主体内容通常包括几个部分:其一,罗列策免对象在任职中的过失和罪状。萧望之在策免中即被责为“廉声不闻,敖慢不逊,亡以扶政,帅先百僚。”[6](P3281)而师丹任职大司空的种种过失与不当,在策书中更以相当长的篇幅进行了逐一列举。其二,在策免中,皇帝通常声称不忍治其罪,以示恩泽与抚慰。如哀帝在策书中向师丹称:“以君尝托傅位,未忍考于理,已诏有司赦君勿治”即属此类。[6](P3507-3508)其三,宣布策免结果,命策免对象上交三公印绶,归还三公的权力。可以说,策免体式在汉代虽然没有形成固定的规制,但其行文程序还是比较完整的。
策免体式与册封体式的差别表明,册封之事属吉礼,宣读册封策书时,往往伴随着隆重的册封仪式,过程极为庄重,故在策书中须交代具体的册封时间、册封地点、执行册命之人等等;也就是说,册封策书具有固定的规制,正是符合册封仪式必须庄重、严正的要求,适合在册封仪式上宣读。相较而言,策免策书则无此要求和限制,其不仅在形制上较册封策书简略,连书写文字也被规定仅能使用隶书而已。可以说,策免策书更加强调的是罢免三公的功能性和实效性。
二、汉诏规定外的策体:策问与策告
诏令范畴下的“策”体,除了汉制规定下的策书以外,在现实使用中还包括策问与策告两种类型。
(一)策问。策问乃是汉代用于选拔人才的一种考试方式,其肇兴于文帝与武帝时期。清王兆芳《文章释》:“策问者,……著词于策以咨问贤才也。主于询言咨事,制诏试学。源出汉文《策贤良文学诏》,流有武帝《策贤良制》。”[7](P6282)吴曾祺《涵芬楼文谈》:“汉文武二帝,均策问贤良文学,此后世以策试士之始。”[8](P25)
文帝十五年九月颁布的《策贤良文学诏》无异于命题考试,这次策问向参加对策的贤良文学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一要明于国家之大体;二须通于人事之始终;三能直言极谏。除此“三道之要”,还需围绕“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个方面直陈其志。行文方面则务求“周之密之,重之闭之”。“重闭”原有“重重关闭、防护严密”之义,在这里则与“周密”义近,指行文论事须严谨缜密,没有疏漏;尽量做到“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晁错即在此次对策的贤良文学之列,他根据策问提出的各项要求,每段行文皆以“诏策曰”领起,围绕“三道之要”展开了精彩论述。[6](2291-2299)如果将文帝策问与晁错对策两相比照,互相参阅,便更可见出此番问答相得益彰之妙。
武帝时,多次策问贤良。董仲舒即以贤良的身份受策察问,其闻名于世的“天人三策”便作于此时。“天人三策”正是针对武帝的三次策问而作。班固在《汉书·董仲舒传》中不仅收录了“天人三策”全文,武帝的三次策问亦全篇录入其中。这三篇策问,文采斐然,突出了擅于设问的特点。例如,在首次策问中,武帝一连抛出五个设问句向对策者发问,欲在以往的历史经验中寻求朝代兴废的必然规律。在措辞方面,武帝策问受儒家经典影响,颇尚典雅之风,而这也成为他向对策者提出的要求之一:“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虖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虖?‘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6](P2513-2514)针对此前的对策,武帝提出“文采未极”,“条贯靡竟,统纪未终”,以为对策之言尚未论述透彻,条贯始终,故命“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要求论述能够更加全面、深入、具体,达到“茂明之”。“茂”字即涵盖了武帝对行文措辞的整体要求和倾向。
明朱荃宰《文通》称:“对策存乎士子,而策问发于上人,尤必通达古今,善为疑难,不然,其不反为士子所笑者几希矣。”[7](P2749)可见,策问虽属于诏令范畴的应用文体,但也要求策问者具备“通达古今”的文化素养,方可擅于发问。成帝建始四年夏,“上尽召直言之士诣白虎殿对策,策曰:‘天地之道何贵?王者之法何如?六经之义何上?人之行何先?取人之术何以?当世之治何务?各以经对。’”[6](P2673)可以说,成帝的策问即呈现出“善为疑难”的特点。
射策则是策问的一种特殊形式。《汉书·儒林传》:“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6](P3620)这是说,武帝时期,始有射策。《汉书·萧望之传》:“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师古曰:“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6](P3272)《汉旧仪》:“太常博士弟子试射策,中甲科补郎,中乙科补掌故。”[1](P89)大体来看,射策相当于以抽签考试的方式,选拔博士弟子以补官员之缺。由于射策“列置案上”“不使彰显”,故其具体内容无由得见,史书中亦无明确记载。唯东汉徐防曾上疏对射策进行改革,故使射策内容方可窥见一斑:
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五经》各取上第六人,《论语》不宜射策。虽所失或久,差可矫革。[5](P1501)
从中可知,射策通常以五经作为考试内容,但博士弟子在策试时,往往脱离章句本义,主观穿凿附会,互相争论非议,故射策虽为诏令形式,却并未发挥诏令原本应起到的引导作用。正是有鉴于此,徐防提出:“《论语》不宜射策。”《东观汉记·徐防传》载:“防上疏曰:‘试《论语》本文章句,但通度,勿以射策。冀令学者务本,有所一心,专精师门,思核经意,事得其实,道得其真。于此弘广经术,尊重圣业,有益于化。虽从来久,大经衰微,学问浸浅,诚宜反本,改矫其失。’”[9](P708)力图通过改革,使射策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二)策告。所谓策告,即帝王出于天子名义,以简册相告于神明。《史记·周本纪》:“夏后氏之衰,有二龙止于夏廷,而言‘余,褒之二君也’。夏帝卜杀之,去之,止之,莫吉;卜请其漦而藏之,乃吉。于是布币策告之。龙亡而漦在,乃匵去之。”“布币策告”,师古注曰:“奠币为礼,读策辞而告之也。”[4](P147)夏帝以策告的方式,使二龙离开夏廷,可算是帝王策告之滥觞。
《汉旧仪》载:“有天地大变,天下大过,皇帝使侍中持节乘四白马,赐上尊酒十斛,养牛一头,策告殃咎。”[1](P40)根据汉制的规定,天地之间发生巨大变故,或遇天下大过之事,皇帝便须举行祭祀仪式,将灾祸罪过策告于神明。王莽在位期间,因无计平定邓晔、于匡的起兵,便用过以策告天的招数:随着邓晔、于匡进兵的深入,王莽在节节败退的局面下无计可施。其听信大司空崔发“呼嗟告天以求救”的办法,率领群臣进行郊祀,并效法儒家经典中的记载,仰天大哭,向上天祷告剿灭反贼;继而又作“告天策”千余言以自陈功劳。[6](P4187-4188)此番策告仪式举行得极为隆重,策告规模也声势浩大,擅长以悲哀之情诵读策文者,因此而得以提拔为郎的人数达至五千多人。凡此种种,不仅反映了王莽对以策告天的重视程度,更说明他对策告效果的深信不疑。
三、“策”体功能辨析与总结
由上可知,诏令范畴下的“策”,大体可分为策书,策告,策问三类。这是根据“策”在诏令实践中的功能进行的划分;这种划分显然与蔡邕《独断》、刘勰《文心雕龙·诏策》中的界定颇有出入。二者皆将诏令范畴下的“策”,视为汉制规定的“策书”;不过策告与策问的功能,并不会因未经明确界定而被否认。事实上,“策”作为一种记录工具,最初是以简册的方式而出现。随着简册用途的多样化,“策”必然发展出多重功能。就“策”体而言,其原无定体,只是因功能不同,遂逐渐分成不同的“策”体。随着各种“策”体彼此间的分野逐渐清晰,它们的功能亦进一步得以明确。蔡邕、刘勰的界定,即是对诏令范畴下的“策”体进行规范总结的一种方式;然这一方式并不是唯一答案,继之其后的诸多学者亦从不同角度对“策”体功能进行了辨析和总结。概而言之,其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侧重于“策”体的考竟源流;另一类则侧重于对“策”体分类辨析。
(一)考竟源流。此类评论通常对“策”之本源及“策”体发展过程进行细致的梳理与考察。如明代朱荃宰所撰的《文通》。此书设有“文体论”十六卷,收辑古代散文文体160种。《文通序》称:“文有体,体有要,有流有别。”故朱氏着重于对文体名称的解释,对文体源流和特点进行辑录考述:
“《集古韵》作‘笧’,通作‘策’。国史亦曰‘简册’。杜预曰:‘大事书之于策,小事简牍而已。’简札牒毕,同物异名。单执一札为简,连编诸简为册。郑玄《论语叙》云:‘书以八寸策,误为八十宗。’《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其制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称皇帝,以命诸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木两行,惟此异也。’《说文》云:‘册,符命也。’字本作‘策’。汉制命令,其一曰策书。汉武帝封三王策文,唯用木简,故其字作策。至唐人,逮下之制有六:其三曰‘册’,字始作‘册’,盖以金玉为之。《说文》所谓‘诸侯进受于玉’,‘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者是也。又按:古者册书施臣下而已,后世则郊祀、祭享、称尊、加谥、寓哀之属,亦皆用之,故其文渐繁。其目凡十有一:曰祝册,郊祀祭享用之;曰玉册,上尊号用之;曰立册,立帝立后立太子用之;曰封册,封诸王用之;曰哀策,迁梓宫及太子诸王大臣薨逝用之;曰赠册,赠号赠官用之;曰谥册,上谥、赐谥用之;曰赠谥册,赠官并赐谥用之;曰祭册,赐大臣祭用之;曰赐册,报赐臣下用之;曰免策,罢免大臣用之。今制:郊祀、立后、立储、封妃、亦皆用册,而玉、金、银、铜之制,各有等差。其文当以古为准。”[7](P2722-2723)
由这些辑录的材料来看,“策”原为“简册”。而具有命令性质的“册”,因书于简册之上,故作“策”。值得一提的是,“《说文》云”一段摘自《文体明辨序说》,关于“策”体,其着重强调了“策书”这一命令性体制,并梳理了策书自汉代至明代的发展过程。从梳理情况可以看出,策书的分类逐渐被细化;朱氏指出这是由于其用途更加广泛,而导致“其文渐繁”。然从所列的十一种“策”体来看,绝大多数实际上在汉代已经得以应用;也就是说“策”体的这些功能在汉代已经存在,只是当时尚未被明确地加以区分、命名而已。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策”的功能被有意识地进行细化,进而在形制上呈现出彼此清晰的界限和规定(如玉、金、银、铜之制,各有等差),故策体的划分也越来越清晰。
与之相比,清代王之绩《铁立文起》一书在介绍“册”时,则意识到“册”体自生成之时,便具备了多项功能,而并不是后世发展出来的衍生物:“王懋公曰:‘或谓册体始于《洛诰》’,非也。观《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则册书由来已久,其不自周始可知。《明辨》谓古者止施之臣下,亦非。观《顾命》:‘丁卯命作册度。’注云:‘命史为册书法度,传顾命于康王。’是且施于新主矣。《明辨》又谓后世祭享亦用之,则又非。观《洛诰·丞祭岁》:‘王命作册,逸祝册。’古人祭祀告神,何尝不用册书?又观汉唐宋册文,或用之玉立,或用之哀封,或用之谥赠与祝祭。近人有谓汉唐宋册,惟颁制臣下,谬亦犹之《明辨》矣。”[7](P3372)正是主张册书功能多样性具有原初特点,故其对《文体明辨》将册书的对象仅限制于臣下进行了反驳。这一思路对于理清册体的源流,颇具启示性。
清代王兆芳《文章释》在辑录各家关于“策”体评述的同时,更将能够体现“策”体源流的代表作逐一列出:
“册者,古作‘笧’,借作‘策’,或作‘筴’,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者也,天子之命编简作符册也。……源出《大始天元册文》(《素问·天元纪大论》《五行运大论》引。)流有《武王即位筴》(见《逸周书·克殷》《史·周本纪》《齐世家》。)周公《金縢册》,成王《命周公册》,襄王《策命晋文》,汉武《封三王策文》,《文选》《文粹》列‘册’。”[7](P6280)
“策问者,‘策’本字作‘册’。著词于策以咨问贤才也。主于询言咨事,制诏试学。源出汉文《策贤良文学诏》,流有武帝《策贤良制》,晋陆机《为武帝策秀才文》,《文选》列‘策秀才文’。”[7](P6282)
“哀册者,哀,闵也,伤也,以闵伤之词书于简册也。挚虞曰:‘今哀册,古诔之义。’主于叙功属思,爱闵悲伤。源出周穆哀盛姬,内史执策,流有周景《追命卫襄》。魏文为《武帝哀册》,明帝为《甄皇后哀册》、《赐汉献册文》,晋潘岳作《景献皇后哀册》,《文选》、《文粹》列‘哀册’。”[7](P6286)
如此一来,便为“策”体的考竟源流提供了颇为详实的文献材料。
(二)分类辨析。这一类评论往往依据功能、主体、对象等不同标准,对“策”体进行横向比较;通过辨析,对“策”体加以明确、细致的区分。
明代谭浚《言文》释“策(册)”曰:“策,谋也,符命也。汉帝下书四品,一曰策,策贤也,约敕封侯,使贤不犯。《音义》作‘简’。策问例置案上,试者封策射取而答之,曰射策。若錄政化得失显而问之,曰对策。射策者,探事而献说;对策者,应诏而陈政。蔡邕曰:‘不备百文,不书于策。’哀策问册同之。汉武帝《对贤王册》,董仲舒《贤良策》。”[7](P2391)其主要从功能角度,将“策”体主要分为策书、策问两类;而与策问相应的,又有射策、对策两种方式。其中,射策者“探事而献说”、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主体皆为应试者,故射策、对策在这里被界定为具有上行的奏疏性质,与诏令范畴下的“策”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来裕恂《汉文典·文章典》则将“策”分别列于诏令类与奏议类之下。在诏令范畴下,释“策”曰:“策者,书策也。古者,大事书于策。有赐封之策,如汉武帝《封齐王策》《封燕王策》《封广陵王策》是也。有试士之策,如汉《贤良策》,唐《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是也。汉世又以策免三公。”[10](P26)而在奏议范畴下,“策”则释为:“策者,谋也。策之体有三:曰制策,天子问而臣下对也;曰试策,有司策试士而令对之也;曰进策,士庶著策进上者也。然试策、制策,属诏令类,惟进策乃臣僚士庶,有策而进于上,奏议类也。王通《太平十二册》、王朴《平边策》是也。若对策,可谓之对,不得谓之策。”[10](P18)不难看出,两个范畴下的“策”体有重叠之处:作为诏令之属的“策”可分为赐封之策,试士之策;而列于奏议范畴的“策”体,除了进策之外,其他“策”体本质上仍被视作诏令之属:制策、试策,自不待言;具有奏议性质的对策,著者亦认为:“可谓之对,不得谓之策。”意即应试者所对之言,乃是对制策、试策的反馈。这一界定与《言文》的观点大相径庭。
张相《古今文综》将诏令“策”体划分为策问之属、册文之属、祭告之属:
1、策问之属:“《释名》:‘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临轩发策,选才取士。汉时曰诏曰制,六季曰策文,唐宋以还,通曰策问。”其下又细化为策诏、策制、策文、策问四种。
2、册文之属:“《说文》:‘册,符命也,诸侯进受于王者也。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释名》:‘汉制约敕封侯曰册。册,赜也,敕使整赜不犯之也。’《独断》:‘《礼》曰:不满百文,不书于策。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按古文作笧,假借为策。董仲舒《对策》,文中称‘明册’,或‘册曰’,斯知通用旧已。古者册书,施之臣下。逮至后世,其用甚繁,或施之于尊,或施之于卑,要之不离乎符命者近是。”其下又分成七小类,分别是:
(1)册尊:所谓玉册者也。
(2)册立:皇后太子,属国之主,凡其正位,均以册文。
(3)册封:《独断》所谓以命诸侯王、三公者也。
(4)册免:《独断》所谓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者也。
(5)哀册:任彦昇以汉乐安相李尤作《和帝哀册》,为哀帝册之始。《释名》:“哀,爱也,爱而思念之也。”
(6)谥册:谥,今本《说文》作作谥。《北堂书钞》九十四引《说文》:“谥,行之迹也。从言,益声。”《广韵》:“谥,《说文》作谥,汉唐碑版均作谥。致譌之时,当在五代。”……谥册云者,《独断》谓:“诸侯王、三公之薨,亦以策书诔谥其行。”特变其制,施之于尊,是其异尔。
(7)杂册。
3、祭告之属:“亦有以册文行之者。”其分为四小类:告天、告庙、祭陵、谕祭。
《古今文综》对“策”体划分得极为细致,并将“策”体所能发挥的功能皆囊括其中;可以说,它是对诏令范畴中的“策”体进行了一次集大成式的总结。
此外,还有一些关于“策”体的评述,在分类辨析的同时,亦对其源流进行了梳理。如吴曾祺《涵芬楼文谈》将“策”体分为策问、册文、谥册、哀册。关于策问,其曰:“汉文武二帝,均策问贤良文学,此后世以策试士之始,自南北朝下至唐宋元明,以及我朝,相沿不改。其非临轩亲试,而有司主之者,亦以类及焉。”将策问的使用情况作以历时性描述。同样,在界定册文、谥册时,亦对其源流、发展逐一进行了交代。
要之,评论者们对“策”体分类的细化,反映了“策”所具备功能的多样化;这并不完全是“策”体在后世发展的结果:从各种“策”体的源流梳理来看,其绝大多数功能均在汉代已经发挥作用。这些历时性线索表明,除了汉制规定的策书外,策告、策问等其他体制在汉代也同时存在;而形式上的细化,除了“策”体自身的规范化因素,更有赖于评述者的归纳和总结。
参考文献:
[1][清]孙星衍等辑,周天游点校.汉官六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0.
[2][南朝·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3][汉]蔡邕.独断[M].四库全书文渊阁影印本.
[4][汉]司马迁,[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南朝·宋]范晔,[唐]李贤等注.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6][汉]班固.颜师古注.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王水照.历代文话[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8]吴曾祺.涵芬楼文谈·附录[M].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辛亥年版.
[9][汉]刘珍等撰,吴树平校注.东观汉纪[M].北京:中华书局,2008.
[10]来裕恂.汉文典[乙].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丙午年版.
[责任编辑王占峰]
“Ce”Stylistic Analysis in the Category of Imperial Edicts——Taking Imperial Edicts in Han Dynasty as an Example
Wei Xi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hua University, Jilin 132013)
Abstract:There are generally three types of“Ce”in the Han Dynasty imperial edicts which are imperial edicts of nobility-conferring appointment, imperial edicts of Jane report, and imperial edicts of questions. Imperial edicts of nobility-conferring appointment are commonly used to appointment and removal of personnel. Imperial edicts of Jane report are used to pray to heaven and earth, the gods and temples by Jane. Imperial edicts of questions are used to select the talents of elite literatures and doctoral students. There are many comments about the“Ce”stylistic analysis in the category of imperial edicts, and they can be actually divided into two approaches which are carding the origin and classification analysis. The comments reflect a variety of features about“Ce”, and prove the fact that the most of the features has existed as early as the Han Dynasty. In a manner of speaking, the refinement of“Ce”is not only a result of literary style standardization, but also largely depends on the inductions and summaries of the reviewers.
Key words:imperial edict; Han Dynasty; imperial edicts of nobility-conferring appointment; imperial edicts of Jane report; imperial edicts of questions; stylistic analysis
作者简介:魏昕(1980-),女,吉林吉林人,北华大学文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文学与文化。
收稿日期:2015-10-22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0438(2016)2-008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