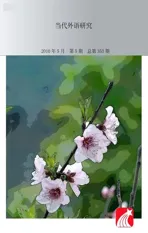庞德创译汉诗之“俄狄浦斯情结”
2010-04-05魏家海
魏家海
(湖北武汉理工大学,武汉,430070)
1. 引言
庞德对汉诗的翻译可分为“模仿”(copies)和“改编”(remakes)两类(见Tryphonopoulos等2005:60),统称为创译。在创译中国古诗过程中,他吸收了大量的中国文学传统,但这些创译没有、也不可能完全颠覆西方文学传统。庞德与西方文学传统的关系,是一种爱恨交织的“俄狄浦斯情结”,面对西方文学传统,他总有一种无法逾越的焦虑,他的译诗与西方文学传统构成了互文关系。庞德的创译在吸纳接受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时,并没有否定西方文学经典的价值,西方的诗学传统挥之不去,在其翻译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2. 西方文学拟古传统的无形操控
庞德精通多门西方古语,如古英语、拉丁语、希腊语、罗曼语、法语、意大利语等,翻译了大量的古英语、普罗旺斯语和托斯卡纳语古典诗歌。拟古传统在庞德的诗学中根深蒂固,这使他能“以古创新”,在古典文学中淘金,通过翻译使其在现代文学“复活”。庞德荟萃古典文学精华,既操纵它为建构世界主义普世意义的诗学规范服务,但同时又被它操纵,在翻译中国古诗并使之通向现代性的道路上,摆脱不了传统的纠缠,他甚至不能完全摆脱他所猛烈抨击的维多利亚诗歌风格。庞德在诗歌创新的过程中,始终处在传统和革新的纠葛之中。
庞德在翻译创新中不自觉地继承了西方的古典传统,在引进中国古诗的“新式”诗歌情绪和意象组合方式时,并没有丢掉西方的传统之根,正如T. S.艾略特所言:一个作家不能脱离其传统进行创作(引自黄杲炘1999:123)。有学者称“庞德从灵感到创作都深深侵浸在一种崇尚古韵的意识之中,而且这种意识与其现代主义诗学创新意识交织在一起,二者既冲突又融合;冲突是表面的,融合才是其实质”(王贵明、刘佳2006:79)。这道出了庞德受西方文学拟古传统无形操控的原委。具体说来,这种操控表现在诗歌的叙事性和逻辑性上。
2.1 西方文学传统中的叙事特征
和中国文学传统中以抒情文学为主流不同,西方文学传统以叙事文学为主流。源于古希腊的西方文学,如希腊神话故事和荷马史诗、戏剧和罗马史诗《埃涅阿斯纪》等,都是叙事文学。超级稳定的农耕文化造成了中国文学的内倾性和静态性,文学传统以抒情为主,而搏击自然的海洋文化则形成了西方文学的外倾性和动态性,叙事文学最能表现这种动态性,“叙事文学成为诗人和作家们在创作中模仿现实、复制现实的主要手段”(杨恒达2007)。
西方的长篇叙事诗重在事件线性发展的外在呈现,在语言上显然以动态性词语为主导,而中国诗重在情感碎片化和非连续性的内在抒发,在语言上静态描写性的词语往往占主导地位。由于叙事诗在西方文学传统上的影响力巨大,庞德的翻译也未完全摆脱这种传统的影子。例如《诗经·小雅·小明》的第二章: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
曷云其还?岁聿云莫。
念我独兮,我事孔庶。
心之忧矣,惮我不暇。
念彼共人,眷眷怀顾!
岂不怀归?畏此谴怒。
Long long ago we set out
thinking the sun and moon veering about
would see us home at the year’s turn,
heavy in mood to brood that I alone
work in mood to brood that I alone
work for that crowd—
no furlough allowed,
longing for home,
fearing the price.
这首诗描述了小官吏久役于外,欲归不能而牢骚满腹的情形。庞德在翻译该诗时,首先使用了西方叙事诗中典型的叙事风格,以“Long long ago”这一典型的故事讲述方式开头,彰显了译诗的故事性和叙事性,这种表述模式既体现了中国诗的情感,又带有西方诗歌叙事传统的明显印记。除了“we set out...would see...work”等主谓型句式具有自然的叙述特点外,现在分词非谓语结构thinking...longing...fearing也暗示了语言的动态性和叙事性,共同构筑了动词的联系性,隐含了“模仿现实”和“复制现实”的叙事传统。
2.2 西方文化中的逻辑思辨传统
西人重分析和逻辑推演,思维传统中理性主义思想浓厚。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所崇尚的理性思想传统经后世哲学家们的不断完善,早已植根于西方的思维传统之中,并深刻影响了西方语言的特征。英语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结构,重“形合”,语言的外在形式要素如主谓一致、曲折变化、形态变化和衔接、连贯尤为重要。
拼音文字的“逻各斯中心主义”被视为西方的传统。英语是理性主义思维传统的产物,受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逻辑思维模式的影响,英语的理性体现在“抽象性”、“客观性”、“确定性”等特征上(连淑能2006:38),注重形式的理性联结功能,而不仅仅是靠意义的感悟。庞德深受西方逻辑思辨传统浸淫,在翻译中无法规避这种传统思路。庞德的译诗语言大多符合标准语法规则,虽然有些诗句模仿汉语意象并置,生成并列短语形式,以至语法脱落,但这是对汉语形式的刻意模仿,不是主要的方面。译诗的主要形式仍是把碎片化的意象通过逻辑思维串联起来,建立有效的主谓结构和联结形式,构建英语诗行的句法化。例如,《诗经·国风·东方之日》:
东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
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东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闼兮。
在我闼兮,履我发兮。
Sun’s in the East,
her loveliness
Comes here
To undress.
Twixt door and screen
at moon-rise
I hear
Her departing sighs.
庞德的译诗把意象sun和east用句法化链接起来,意象door,screen和moon-rise用介词twixt和连词and及介词at粘合起来,是典型的英语“形足性”特征,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理性色彩。尽管庞德力图通过大量使用短语以摆脱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主义传统,但其译诗的整体语言框架却并未脱离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形式。
3. 创译中的拟古倾向与西方古典话语模式
庞德先后开创了“意象主义”和“漩涡主义”的诗歌运动,试图开辟诗歌历史的新纪元。他在费诺罗萨的遗稿里发现中国古诗的诗风同他的诗学有暗合之处后,便迫不及待地改造中国诗,通过创译为汉诗构建西方话语模式。他的创译大大淡化了中国古诗的“古代性”,特别是他翻译的《神州集》中的诗歌,是完全摆脱了古奥风格羁绊的新式自由诗,但后来庞德所译的《诗经》则显示出他的翻译风格有了明显改变——拟古倾向由淡而浓。一方面,由于他的古汉语水平大为提高,他通过直接阅读中国古诗领悟了其中的古风之玄妙,迫切希望传译出中国古诗中的古朴风格和诗学倾向;另一方面,也由于他在翻译《诗经》时,诗学本身和他的个人境遇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意象主义和漩涡主义影响已烟消云散,他自己则因叛国罪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此时他对西方文化的依恋情结更难以割舍,诗学的古典倾向逐渐回转。
首先,在译诗的词汇选择上,他的西方古典意识开始复苏。例如《诗经·周南·桃夭》: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
之子于归,宜其室家。
桃之夭夭,有蕡其实。
之子于归,宜其家室。
桃之夭夭,其叶蓁蓁。
之子于归,宜其家人。
O omen tree, that art so frail and young,
so glossy fair to shine with flaming flower;
that goes to wed
and make fair house and bower;
O omen peach, that art so frail and young,
going to man and house
to be true root;
O peach-tree that art fair
as leaf amid new boughs;
going to bride;
to build thy man his house.
上例中,译者选用了古体词art(are),thy(your),amid(among)和bower(boudoir),给人古香古色的印象。这些词把古典文学意识同现代性揉合在一起,古词和今词的汇通和穿插,诗意的古今共融和互补,谱写了一章协奏曲,意味着庞德的古风追求诗意化了,流露出他对欧洲古典文学依依不舍的感情。
其次,在译诗的韵律上,庞德翻译《诗经》比翻译《神州集》更注重韵律和节奏,自觉或不自觉地使用了维多利亚诗歌的韵式和格律,似乎挣脱不了传统诗歌的形式框架。国外有学者(Cheadle 2000:181)把“维多利亚的诗学格律”看作是除“主角的浪漫性”、“选词的现代性”之外使庞德的译诗比原诗更靠近英语读者群的三个因素之一,可见庞德受到传统西方韵律诗的影响之深。例如《诗经·郑风·羔裘》: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
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豹饰,孔武有力。
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
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Lamb-skin coat and a leopard cuff
Goes on living beneath my roof
There are others, I’ve been told
and this one is getting’ old.
Askin’ and askin’, now I hear
others are called and might appear
with a lambskin coat and leopard trim
although I am fond of him.
原诗的韵式是“abca,cccc,cccc”式,译诗的押韵基本上遵从古英语的英雄偶句(heroic couplet),呈“aabbccdd”式,第一行和第二行虽非严格的押韵,但cuff和roof末尾的辅音f相同,是押半韵。译诗中lambskin和leopard,skin;还有coat和cuff是押头韵,living beneath押的是半谐音/i/,askin’和askin’为叠词押阴韵。这些押韵手法均与西方传统韵格要求相符。又如《鱼藻》(TheCapitalinHao):
鱼在在藻?有颁其首。
王在在镐?岂乐饮酒。
鱼在在藻?有莘其尾。
王在在镐?饮酒乐岂。
鱼在在藻?依于其蒲。
王在在镐?有那其居。
Fine fish in weed, that is their place.
And the king’s good wine in his palace.
Fish in pond-weed wagging a tail
And the king in high Hao at his wassail.
While fish in pond-weed lie at ease
The kings of Hao may live as they please.
这首译诗不仅译得比较忠实于原诗,而且严格使用了英雄偶句“aabbcc”韵式,头韵也很清晰,如fine,fish,fish,fish,和weed,wine,wagging,while,weed,尽管有些是遥韵,但总体音韵效果很好。原诗每两行八个字译为一行,译诗每节第一句音节数也是八个,第二行是九个,只有第二节的第二行是十个音节。译诗的格律化趋势很明显。
庞德在开创自由诗的过程中并没有完全放弃格律诗的审美追求,这是传统诗的无形渗透力同他自己的诗学相互交织、相互补充的结果。有时为了凑足押韵和增强语音效果,庞德刻意采取分行处理的方式,把一句诗行分成若干小行,每小行只有一两个词,例如《螽斯》和《野有死麕》的译诗都是典型的例子。这些具有传统诗歌特色的译诗更具诗味,读起来更有节奏感和韵律感,是传统诗歌话语模式的活化和变形。
4. 译诗中的“化静为动”与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
在创译中国古诗的过程中,庞德特别注重以语言的流动性带动译诗的动态性,使中国古诗“动”起来,从而建立自己的动态诗学观。庞德用动态性来弥补中国古诗静态美有余而动态美不足的缺憾,实现改造中国诗的目的。庞德宣称,他的目的是“使死人复活,呈现活的图形(figure)”(Xie 2001:208),声称“艺术的精神在于动态性”,“译者的职责就是把‘动态内容’,即诗歌的生命力传送给读者”(Yip 1969:76)。“动态”是诗歌能量的喷发,“化静为动”,把中国古诗的静态画面在他的译诗里转化为流动画面,展示给西方读者,这就是庞德翻译诗学的精髓。
音乐就是这种动态性的最佳载体。庞德很有音乐功底,曾经出版过两部歌剧。他对音乐的感悟力也渗入进创译之中。他声称“诗歌是用词语谱写的音乐”(Nadel 2001:236),不论是诗歌创作,还是诗歌翻译,他都十分强调突出诗的节奏感。他擅长用“音乐短语”(musical phrase)即短语结构构筑诗歌的节奏,构建起一种“短语节奏”(赵毅衡2003:210),以自由诗的形式,表达诗歌的情绪。他的汉诗创译基本上抛弃了押韵和格律,以建构新诗的形式,使英译诗歌步入了现代性。从表面看,庞译似乎是“无序”的,但实质又是“有序”的,译文虽然无韵,但节奏清晰,抑扬顿挫,是一种“赋格”(fugue)形式,即用复合格发展主题,而不仅仅是单调的单个格律。
庞德还偏爱用带有“敲击音乐”(percussive music)式的、联想性的词语和带有清脆联想意义的词语创译中国古诗,以表现明快的节奏和动感,这是他追求动态美学的具体体现。这种意义的流动性和画面的动感性反映了西方叙事诗的基本特点,强调意义的流动性和直线延伸性,正好弥补了中国古诗画面的静态性有余而动态性不足的缺憾,从而使译诗的意境动起来,节奏加快,将中国诗的静态美改造成了译诗的动态美,以适应西方读者的审美情趣。如卢照邻的《长安古意》的前半部分:
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七香车。
玉辇纵横过主第,金鞭络绎向侯家。
龙衔宝盖承朝日,凤吐流苏带晚霞。
百尺游丝争绕树,一群娇鸟共啼花。
游蜂戏蝶千门侧,碧树银台万种色。
复道交窗作合欢,双阙连甍垂凤翼。
梁家画阁中天起,汉帝金茎云外直。
The narrow streets cut into the wide highway at Choan,
Dark oxen, white horses,
drag on the seven coaches with outriders
The coaches are perfumed wood,
The jewelled chair is held up at the crossway,
Before the royal lodge:
A glitter of golden saddles, awaiting the princes;
They eddy before the gate of the barons.
The canopy embroidered with dragons
Drinks in and casts back the sun.
Evening comes.
The trappings are bordered with mist.
The hundred cords of mist are spread through
and double the trees,
Night birds, and night women,
Spread out their sounds through the gardens.
Birds with flowery wing, hovering butterflies
crowd over the thousand gates.
Trees that glitter like jade,
Terraces tinged with silver,
The seed of a myriad hues,
A network of arbours and passages and covered ways.
Double towers, winged roofs,
border the network of ways;
a place of felicitous meeting.
Riu’s house stands out on the sky,
With glitter of colour
As Butei of Kan had made the high golden lotus to gather his dews.
原诗主要铺陈长安豪门贵族奢侈享乐的生活,是一幅颇具特色的以静态描写为主的诗歌画面,尽管原诗也使用了动词,但总体画面遮盖了诗歌的动感性,以展示长安的奢华场面为主。
庞德只译了原诗的前十六行,译诗使用了多个动态动词和动态介词,如动作性动词(词组):cut into,drag,eddy,drink in,cast back,come,spread through,spread out,hover,crowd,stands out,meet和gather等;发光性和发声性动词:glitter,ting和soundthrough等,展示了动作、视觉和听觉艺术的流动和融合。此外,译诗中还使用了不少引起“响亮”声音联想的词汇,如以[k]音为首的词:cut,coach,crossway,canopy,cast,come,cord,crowd,cover等,[]音为首的词:glitter,gold,gate,garden和gather等,[d]音为首的词:dark,drag,dragon,double和dew等,另外,还有很多含有[b]音的词语,从而刻画出一幅情景交融和声情并茂的流动画面,场面动了起来,实现了由“静”到“动”的转化,让原诗的画面描写具有了叙事性,彰显了西方叙事诗的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中国诗在英语中的“本土化”。又如李白的《送友人入蜀》(Leave-TakingNearShoku):
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
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芳树笼秦栈,春流绕蜀城。
升沉应已定,不必问君平。
They say the roads of Sanso are steep.
Sheer as the mountains.
The walls rise in a man’s face,
Clouds grow out of the hill
at his horse’s bridle.
Sweet trees are on the paved way of the Shin,
Their trunks burst through the paving,
And freshets are bursting their ice
in the midst of Shoku, a proud city.
Men’s fates are already set,
There is no need of asking diviners.
原诗描写蜀道山路之艰险,目的在于抒情,译诗也具这种特点,叙述和描写相互交织,但叙事特色更强烈。译诗中的动态词(语)有rise,grow out of,burst through,busting等,是对事件(动作)的“摹仿”。亚里士多德(1996:178)说过,诗人是个“摹仿者”,必须摹仿“(一)过去或当今的事,(二)传说或设想中的事,(三)应该是这样或那样的事”。亚氏强调事件的摹仿,庞德把“当今”或“设想”中的“事”(路途的艰险和遥远)“活化”了,生动形象,充满了对友人的关爱之情。正如莱辛对比画的“静态性”和诗的“动态性”时所言:“诗呈现的是一个渐次进展的动作(事件),其构成部分在时间里依次进行”(叶维廉2006:202),也就是说,诗有动态的叙事性特征。不过,叶维廉指出莱辛的“诗”只指“史诗或叙事诗”(204),可见史诗的显著特征。庞德译诗的这种叙事方法明显有亚氏史诗论的影子,叙事传统在力主诗歌改朝换代的庞德那里,并没有断香火。
5. 译诗中的“化破碎为连贯”与西方文化的理性逻辑传统
虽然庞德在翻译中“偏爱形式、碎片和具体细节”(Genztler 2004:23),有些意象的翻译就是碎片化的并置,但理性主义和形式逻辑的传统早已植根于庞德的思想里,无论他怎样反叛,都是“剪不断,理还乱”,理性逻辑情结挥之不去,因为这是他的思维惯性。庞德通过费诺罗萨的论文,并通过自学汉语,逐渐认识到汉语的象形会意和连贯特点,但由于深受西方主体文化的长久熏陶,他的译诗大多还是倾向于正统的语言逻辑形式,主谓结构明晰,介词、连词等的使用发挥了自然流畅的衔接作用。如李白的《玉阶怨》(TheJewelStairs’Grievance):
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
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
The jeweled steps are already quite white with dew,
It is so late that the dew soaks my gauze stockings,
And I let down the crystal curtain
And watch the moon through the clear autumn.
这首怨诗表面写玉阶之怨而实写宫女的不幸遭遇,原诗的意象铺陈,主题意义“妙在不明说怨”(沈德潜语),实际在说怨,意在言外,“此篇无一字言怨而隐然幽怨之意见于言外”(高棅语)。这一主题淹没在意象群中,诉说者(主语)受到压制,意义在理解上具有多元性,观物感应的美学姿势和层次具有多解性。庞德“具体明晰”的翻译使译诗语言更为具体,意义空间有所缩小,联接手段多样,语言呈现高度的理性逻辑色彩。如,“罗袜”是一种丝织的袜,译为“gauze stockings”(薄长袜),意义有所减损,“玲珑望秋月”可以理解为“望见明亮的秋月”,也可理解为“在明亮的秋天夜晚望月”,等等,译诗用了“through the clear autumn”(透过明亮的秋天),译诗语言地道、连贯、通顺,连接词如with,so...that,through,and等,增添了语言的逻辑性。
此外,原诗中压抑的诉说主体是不明确的,可以是“我”,也可以是“她”,叙述视点具有多解性,庞德增添了“I”和“my”,译诗语言符合英语的规范,具有理性化。又如《诗经·陈风·东门之杨》(Rendez-vousManque):
东门之杨,其叶牂牂。
昏以为期,明星煌煌。
东门之杨,其叶肺肺。
昏以为期,明星皙皙。
Neath East Gate willow
’tis good to lie.
She said:
“this evening.”
Dawn’s in the sky.
Neath thick willow boughs
’twas for last night.
Thick the close shade there.
The dawn is axe-bright.
原诗描写一位痴情女子等待自己的情郎,但对方违约不至,因而女子生出了徘徊、失望、焦虑不安的心情。庞德将诗的标题改译为RendezvousManque(失约),抓住了主旨。原诗中的树叶意象“牂牂”与“肺肺”和月光意象“煌煌”与“皙皙”,在语言上只是碎片,暗示天已放亮,但情人始终未曾露面,以烘托女子的失望心情。译诗把这些意象重复和词语重叠句法化了,除了“Thick the close shade there”之外,其他句子都加上了谓语系动词“is”、表示逻辑关系的介词“in,for”和连接性副词“there”等,体现出很强的逻辑性和连贯性。虽然诗行采用了语言变体如缩略词(’s/’twas)、简体词(neath)和生造复合词(axe-bright)等,但是译诗逻辑化的理性思维和原诗碎片化的意象叠加迥然不同。
尽管译诗的特殊叙事方法把原诗中的女子“化妆”得很开放大胆,显得有些滑稽,丢失了原诗的含蓄美,但这种贯穿于理性逻辑语言的叙事特点却显示了译者与西方文化传统间的亲密关系。
6. 结语
庞德创译中国古诗,字里行间都流露出西方文学叙事模式、逻辑思辨方式和古典话语模式的影响。他的西方文学的传统意识同中国情结交织在一起。总体而言,其西方文学的传统占据了上风。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庞德在翻译中国古诗时采用了创译手法,但他对西方文化仍然怀有深深的眷恋。这有利于把中国古诗改造成动态化、逻辑化和连贯化的英语诗,客观上便于中国古诗在西方的传播。
Cheadle, M. P. 2000.EzraPound’sConfucianTranslation[M].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Gentzler, E. 2004.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ies.Revised(2nded.) [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Nadel, I. B. 2001.TheCambridgecompaniontoEzraPound[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Tryphonopoulos, D. P. & Stephen J. A. 2005.TheEzraPoundEncyclopedia[C].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Xie M. 2001.Pound as a Translator [A]. In Nadel (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EzraPound[C].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Education Press.
Yip, W-l. 1969.EzraPound’sCatha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黄杲炘.1999.从柔巴依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叶维廉.2006.中国诗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亚里士多德.1996.诗学(陈中梅译注)[M].北京:商务印书馆.
连淑能.2006.中西思维方式:悟性与理性[J].外语与外语教学(7):35-38.
王贵明、刘佳.2006.今吟古风——论埃兹拉·庞德诗歌翻译和创作中的仿古倾向[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6):79-85.
杨恒达.2007.西方文艺学[OL].http:∥www.rwlh.com/html/fzhbg/index.asp?rootid=0_130&leaf_id=10_30_50.
赵毅衡.2003.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