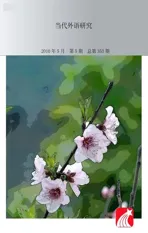作为文化译介单位的“字”与“词”:世界表达的中国化、中国表达的世界化
2010-04-05陈卫恒
陈卫恒
(北京语言大学,北京,100083)
1. 前言
“字”与“词”的话题是中国理论语言学中关于不同语言基本单位和编码类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字”这一概念使用广泛,既是书写单位,也是音节,同时也是意义单位。“词”在英语中是“word”,它是印欧语的基本单位,一个词往往对应于一个重音管辖下的数个音节。在汉语中,“词”却是不太容易确定的单位,正如印欧语中词素(morpheme)不太容易确定一样,但它却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与作为多音节语的印欧语言中音节与意义无强制性关联不同,汉语是单音节语,音节与意义有强制性关联,其基本编码规则是一个音节对应于“一个字、一个意义”。对此,赵元任先生(1980)认为,并非每一个语言都有跟英语的“word”一样的单位。在汉语里跟“word”相当的、一般大众都知道、谈到、天天用到、不分说跟写的概念单位就是“字”。由于汉语的“字”跟语言学上语素(即语言里有意义的最小单位)的概念最为相近,因此汉语有“单音节语”(每个音节都有意义的语言)之称。至于汉语的所谓“单音节神话(monosyllabic myth)”,“其实是有关中国的种种神话里最真实的一个”。
恰当地译介外来文化词,或者将中国文化词译入外语,需要规范地制约、引导和筛选不同的译法。良好译介的一个基本标准是:有利于而不是有害于中国与世界的交融。由此出发,本文认为,鼓励在译介规范中坚持“字”本位,是达到良好译介的一个重要前提。汉字作为汉语言的基本编码单位和汉语文资源的基本载体,是区别于其他国家语文资源的重要特色和标记,在帮助我们识解世界以及在中国文化外译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 字与外来文化词的汉译:字化
在与外来词相关的许多研究中,徐通锵(1994)从字本位理论角度对汉语引进外来词所作的研究最引人注目。他对“字化”或“音节字化”规律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他把借词定义为音与义都借自外语的词,并提出语言接触是借词产生的根本动因。如鸦片战争以来,西学东渐,大量新事物和新概念出现在我们国家的社会生活中,使得表达它们的外语词也渗入汉语,汉语与自己结构类型和编码原则有根本不同的语言(主要是印欧语言)产生了接触甚至碰撞。对待外来词的“入侵”,汉语主要采取“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方法。这主要体现在意译法的广泛采用:只借用其概念而非其语音构造和“语素组合成词的那种语法构词规则”,从而坚持“字”的“表义性”。即使有些词暂时采取了音译,后来大多更换为意译,如telephone从“德律风”到“电话”的译法;microphone从“麦克风”到“扩音器”的译法;bank从“版克”到“银行”的译法等。
对有些难以意译的外来词,徐先生发现,我们的常规做法是尽可能进行汉语化的表义性改造。印欧语的词大多是多音节的,汉译时,往往只取其第一个音节,再配以一个作为意符的汉字,使之汉语化。这种汉化改造办法由来已久。汉、魏、晋、南北朝以来佛教名词的翻译就反映了这一点。比如,“佛”源自梵语buddha,该词早期译法有“佛陀”、“佛驮”、“浮图”等,“佛”或“浮”对应的都是bud-这个音节,本来没有任何意义。但是,由于“佛陀”的音译不符合汉语“一个字,一个音节,一个意义”的编码习惯,“汉语社会就把buddha这个词的意思归入bud-这个音节,译为‘佛’,使之汉语化,再以此为基础造出‘佛土’、‘佛法’、‘佛像’、‘佛身’、‘佛经’、‘立地成佛’之类的字组,使之消除外来的痕迹”(徐通锵1994)。
这些汉语改造外来词的方法,目的很清楚,即“坚持‘字’的表义性,反对把它降格为一个纯粹音化的符号”。这是为使外语的结构适应汉语自身结构特点而进行的一种调整。印欧系各语言之间的借词由于语言结构类型的一致,因而借用很自由,基本上只需要进行字母的对应转写就可以借用另一种语言的词,不需要进行原则的调整。但是,徐先生指出,这种处理借词的方法与汉语的意译化方法有着“天壤之别”。对此,他后来又有进一步的说明。他曾对吕必松先生说(吕必松2005:52),“汉语借用外来辞也往往要用汉语的规律对其加以改造而使其汉化。汉语改造外来辞的基本办法就是从外来辞的音节中选取一个适当的音节并配以相应的汉字,使原本没有意义的音节具有表义的功能,或者实现‘字化’。”
徐先生曾认为,“‘专词’指人名、地名等,必须音译(1994)①”,但后来他明确认为,“美、英、法、意、西、葡②”和“奥林匹克”这些专有名词的音译实际上也是一种有意义的字化。这就是说,没有纯粹的音译,更没有绝对中性专用于记音的汉字;只要用汉字翻译,就将涉及意义,无意义的音节也会带上意义。在面对专名译名时,中国人不会把外来音译词当成纯粹的记音手段,因为汉字本身每个字都有其固定的意思。在“英吉利、法兰西、美利坚、德意志”或“英国、法国、美国、德国”等说法中,用字往往蕴含着美誉,它们虽然是音译词,但在潜意识中可能会引导积极的主观评价。再比如,“Cambridge”也是一个地名,徐志摩采取意译加音译译作“康桥”,无疑增加了国人对该地名的亲切感,即便是初闻③。如译作“坎布里奇”则会让国人初闻即感陌生④。汉字音义形一体,适于听、说、看。良好的译法应力求音义兼顾。
我们认为,字化手段在外来文化的译介中尤为有效。外来词如要在中国扎根,让中国人感到亲近,常常需要音义形兼顾的字化,这一点已为外国人所认识和利用。比如,可口可乐、丁克、万维网、维生素⑤等译名,都是成功的例子。有些译法,表面上看属于音译,但实际上其意义隐含其中。比如,“诺基亚”、“爱立信”所用的汉字就蕴含着积极的评价,至少没有消极的蕴含。“瑜珈”的好处就在于不让你一下子明白,保持神秘感。汉堡(包)、比萨、麦当劳、肯德基,作为品牌名称也有其并非消极的意义隐含。
字化的第一步是实现无意义的音节向有意义的字的转化,这里的“字”包括现成的汉字,也包括专门为了翻译而新造的字。前者,如“几何”对应于“geometry”中的“geo”,“基因”对应于“gene”;后者如“氢”(hydrogen),体现了汉语从“轻”的角度对于质量最小元素的理解。随着有关外来词在中国的扎根,字化还可以进一步发展。这主要表现为,多字词的单字化。如“马克思”、“列宁”中的“马”和“列”就属于这种情况。它们都可以单独使用。这些字成了多音节外来词中的一个音节,被“语素化”了。这方面的例子很多,“的士”里的“的”(如“面的”、“摩的”),“麦克”里的“麦”(如“耳麦”)等等均属此类。这是字化深入的表现。
在目前的字化现象中,也存在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其中,字化与外语字母的翻译的矛盾就是一例。不少外来词中或含有拉丁字母或干脆由英语字母组成,如:卡拉OK,UFO,WTO、维生素A、DNA、甲型H1N1流感、B超、U盘、T恤、CT、cc、XO等等⑥。这显然和字化是矛盾的,因为拉丁字母作为一种舶来品,是纯粹的记音单位,严格来说在汉语编码中不是一级意义单位。但是,目前由于外来文化特别是英语作为国际语言在逐渐影响和渗透着现代汉语,用英文字母直接表义在汉语中也有了一些表现。比如,“OK”就有很多人在说,甚至有人用“O了”来表示“OK了”;台球斯诺克的解说中,用“K球”表示“Kiss”(“轻触”之意)球;江西鹰潭“赵C”人名事件则说明拉丁字母甚至进入国人姓名的现象(张军2009)。严格来说,这实际上是临时的借用或语码转换,并非产生了在汉语中扎下根来的外来词。说话者或使用者这时是在直接讲外语,而不是在使用汉化后的外来词。有关字母的读音常常完全按照外文的发音,而不是汉语拼音方案的发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18条,“汉语拼音方案”可用于汉字不便或不能使用的领域,但是根据我们了解,在实际生活中,很少有人使用汉语拼音方案的字母音去折兑英文字母。去年2月26日,“赵C”人名事件最终以赵C选用规范汉字改名而结束(张军2009)。这进一步体现了把拼音字母或英文字母作为汉语的一级表义单位的不适合性。
对于字母外来词在汉语中的发展应如何规划,值得研究。我们认为,可有以下对策:1)坚持用汉字翻译。比如,一个办法是从意义出发,侧重意译,比如UFO译作“不明飞行物”;MRI译作“核磁共振造影”,简称“核磁共振”或“核磁”;加入WTO,也可以翻译成“入世”,WTO就是“世贸组织”。当然,也可以兼顾读音,“幽浮”也是较好的翻译。雷达、镭射⑦也是这方面的例子。从这个角度看,SARS称为“沙士”侧重音译,而“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s)则突出了意义,译成“非典”则突出了“以我为主”的表达方式。如字母涉及到序列意义,翻译时可以用汉语的序列字(如“甲乙丙丁午己庚辛壬癸”等)来翻译。2)通过缩略,掩盖或省略字母。如:“彩色B超”简称“彩超”,避免了字母B的出现;“甲型H1NI流感”简称为“甲流”,等于省却了有关字母。3)“滴滴涕”(DDT)、“敌敌畏”(DDVP)、“优盘”体现的是将字母汉字化,也应是一种有效的办法。4)承认字母在汉语编码体系中的地位,承认其也是一种主要表现为单音节的“字”,是字的特殊表现形式。它不同于阿拉伯或罗马数字符号的引进,它既包括字形的引进,同时也有字音的引进。
总之,“字化”作为外来词译介的总原则,无论是纯粹意译的字化还是兼顾音义的字化,都值得肯定。字化符合汉语编码的根本机制,有可能成为主流的译介方式。纯粹的音译和字母化的翻译由于不符合汉语的编码原则,只能作为支流或辅助性的译介方式存在。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虽然长期以来字化主要是一种国人相对被动地译介外来文化的原则,但是随着中国人越来越走向世界,世界越来越走进中国,这个译介原则正在成为一种中国人主动识解海外世界、构建海外家园的语言手段。在国际交流中,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外国地名在海外华人口中有了颇具特色的中国名字。比如,很多大学就被赋予了颇具中国特色的汉语译名,如Mount Holyoke College译作“曼荷莲学院”、“和丽山学院”,突出了该校作为贵族女子大学的特点;有些地名纯音译不够亲切,就改用音译加意译的方式,如“麻省”、“加州”、“费城”等,这种译法比完全音译更让中国人感到亲切。西密歇根大学所在地Kalamazoo由此类推,被译作“卡城”。受此启发,越来越多的外国人为方便交流,在其名片上印上与自己英文姓名字谐音、谐义的中文姓名,顺序也与中文的姓与名一致。这就说明了字化作为文化词译介的主要原则符合时代的发展方向,不但有助于外来文化的“请进来”,也有助于中国语言和文化的“走出去”。
3. 字与中国文化词的外译:词化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在向西方学习,中外文化译介主要以外来文化的汉译为主,但是,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地位的提高,一方面中国希望世界倾听自己的声音,另一方面世界也希望倾听到中国的声音,所以中国文化词的外译就日益显得重要。那么,如何在中国文化词的外译中更多地体现中国的特色呢?
我们认为,侧重意义的中式英语(Chinglish)直译法和强调语音外壳的音译法是两种主要的表现手段。前者如“paper tiger”(纸老虎”),“Long time no see.”(好久不见)等⑧,都是十分生动的例子,表面上搭配不够自然的英文表述里却反映了中文的表达特色;后者如“fengshui”(风水),“kongfu”(功夫),“toufu”(豆腐)、“weiqi”(围棋)、“leechi”(荔枝)、“longjing”(龙井)、“longan”(龙眼)、“ginseng”(人参)等,比比皆是。它们都是汉语作为外来词成功进入外语的例子。
类似的翻译,有些是中国人主译的,有些是外国人译的,但都让人在句法上、拼写和发音上能迅速感受到汉语的特色。其翻译原则与以上外来文化词的汉译有所不同。如果说外来文化词的汉译主要体现的是“字化”,在中国文化词的外译上体现的则主要是“词化”。中国文化词的外译主要是基于“词”(word)而非基于作为单音节语素的“字”。如果说“字化”是单音节语言类型的汉语音义结合的编码原则,那么“词化”则是多音节语的音义结合的编码原则,以符合多音节语的编码习惯。
在具体翻译过程中,本来在汉语中有独立意义的字,由于是语素而不是词,在转化为外来语时不必单独考虑,不是翻译时需要考虑的语言单位。比如,“纸老虎”中的“老”字在直译时不必作专门的对译,“好久”只需整体对译为“long time”。本来在汉语中有意义的音节,在转化为外来词后,常常会转变为看似无意义的音节,如fengshui、toufu、weiqi中的feng、shui、tou、fu、wei、qi都不能被认为具备自身独立的意义,单独来看它们只是表音的音节;在feng和shui,tou和fu,wei和qi结合为词后,才有了意义。如果说外来词汉译有关的“字化”体现了无意义音节的意义化,那么“词化”体现的则是有意义音节的无意义化。
这种无意义化表面上体现为放弃汉语编码原则,遵循外语编码原则,但深层依然体现了汉语的特色,外国人看到或听到来自汉语的词时,依然可以感受到其独特的外来性。其中原因就在于“词化”依然保持了汉语的特色。直译式的“中式英语”体现了汉语词汇没有形态变化,以合成词为主要构词方式的特点;“完全音译”则体现了单音节汉字的发音特色,这里无论是单音节本身的结构(如音位组合原则),还是按照汉语拼音形式的拼写法都突出了汉语的特色,让英美人无论是从听觉还是视觉上都能迅速感受到汉语的风采。直译式的“中式英语”和“完全音译”造出的外来词语明显打上了“中国制造”的标记。表面上是以“词”为单位,但深层依然蕴含着“字”在编码上的音义特点。
随着中国文化词越来越多地进入外语,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在中国词的外译中,应该怎样规范译法,才能满足汉语传播和文化外译的需要?
首先,与其他译法相比较,直译法和音译法在文化保真上有着自己的独特优势,理应进一步得到提倡。比如,在武术术语的翻译上,直译法有助于传达汉语原名的文化意义,“白鹤亮翅”(White Crane Spread its Wings)、“开门见山”(Open Doors and See Mountains)等拳法的翻译都是值得参考的译法。后者如译为“Come Straight to Point”则不但偏离了武术动作的技术内涵,而且也不利于在武术课中穿插中国传统文化的介绍。对于“武术”“太极”“丹田”、“气”等词在无法准确翻译的情况下,音译不失为一种明智的处理。直译和音译有助于武术术语在实现国际化的同时保持民族性。这一原则同样也适合中医、民乐、中餐菜单、中国建筑、旅游景点、中国名牌产品等领域文化特色词语的翻译。如果承认等价的翻译是不可能的,翻译一定意味着损耗,那么直译和音译有助于保持中国文化的原味,塑造中国品牌和中国形象,同时在客观上也有助于汉语的传播和中国的国际化。在各种平行的译法中,直译法和音译法有助体现“以我为主”的原则。比如,“神州”系列飞船较好的译法应是“Shenzhou Spaceship”,而非“god ship”或“divine vessel”。在中国首位航天员飞天之后,“Taikonaut”(太空人)就立即进入了主流英语词典。这样的音译,有些是我们自己翻译的,体现了以我为主的原则,向世界传达的信息是中国的创造性和国家实力的增强;有些是外国人翻译的,体现了对中国原创的尊重。
其次,面对各种平行音译法时,应给予汉语拼音方案以优先权甚至唯一通行权,努力使它获得最大的生存空间。随着中国文化自觉和自信意识的提高,以及世界对中国特色文化的关注,我们在音译上坚持拼音方案,体现以我为主的原则。比如,“珠穆朗玛峰”的译法“Zhumulangma”取代“Everest”。作为地名“北京”的音译,“Beijing”应该得到比“Peking”更多的支持。“jiayou”(加油)和“fuwa”(福娃)的名字(Beibei,Jingjing,Huanhuan,Yingying,Nini)传遍了世界。jiaozi(饺子),taiji(太极),mianzi(面子),guanxi(关系)等也都体现了拼音方案为基础的音译的流行。这些都不仅是汉文化的国际传播,而且也是汉语的国际传播。
最后,对于有些传统译法是否更改,也需认真讨论。如果要坚持拼音方案,那么Peking(University),Tsinghua(University)、Hongkong、Macao、Sun Yat-sen(孙逸仙)等是否也应按拼音方案更新,都值得权衡利弊、仔细研究。“豆腐、豆芽、粽子、汤圆、长衫、麻将”这些词倾向于音译,但汉语的“龙”有无必要直译为long、loong、lung,还是坚持dragon的译法?前者的好处是可避免误解,避免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因为在西方“dragon”是含贬义的,与我们的民族图腾龙象征吉祥这一文化内涵南辕北辙。但是应该看到,不同文化的人们在理解外语的时候,只有先与自己熟知的物象联系,才能尽快理解。东西方的“龙”和“dragon”是不同的,但是“dragon”是与“龙”最接近的形象。译为“dragon”,有助于西方文化采取包容的态度,承认其它文化体系里“龙”的内涵,促进不同文化或文明之间的相互认同和对话,而“long、loong、lung”的译法不利于求同存异。由此可见,“以我为主”的原则不宜简单把握,而应认真权衡利弊、灵活贯彻。
总之,中国文化词的译出与外来文化词的译入都应遵循外语的编码规则,以“词”为基本单位,并兼顾发音、文法和文化习惯。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努力保持中国语言的特色,减少语言所承载的文化价值在翻译中的损耗。具有本土特色的直译和完全的音译,表面上看都没有实现彻底目的语化,但这恰恰有助于保持语词的文化内涵。这样的译介策略,在更高的层次上,也有利于中国语言国际传播和文化国际传播的融通,实现中国“走出去”的战略。
4. 结语:字与中西文明对话、中国化和去中国化
“字化”现象进一步说明了“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⑩(赵元任1995:248),因而也是外来词进入汉语时必然使用的编码单位,起着过滤器和包装纸的作用。对于外来词,我们有时也会禁不住要问那是哪个字,生怕弄错了⑩,而英语、阿拉伯语等拼音文字语言对于外来词似并没有这样的担忧。它们似乎可以更方便地接受外来文化词,无论是在书面文字的转写还是实际口头发音的转换上。英语的computer和technology在阿拉伯语、乌尔都语中可以仅按语音的转写规则音译为本族语词,而在汉语中由于汉字鲜明的表义性,若将其音译为“康普特”和“特柯诺拉季”这样的意义不明的词语,则会引起汉语社团本能的抵触和反感,因而要求翻译者重新进行“有意义的表述”。我们接受“电脑”和“技术”的译法,说明在翻译外来文化词时,译名如果恰当地实现了“字化”,会更易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并流行开来。汉语不是没有音译词,关键是汉语不接受纯粹的音译词。虽然汉语的外来词曾经历过音译的现象和阶段,如“德谟克拉西”和“赛因斯”,但它们后来被“民主”和“科学”等有意义的表述所替代了。这是汉语的使用特色。
与“字化”相对的是“词化”。如果说,外来词的汉译主要体现了“字化”的要求,那么在中国文化词的对外译介上,“词化”的要求则十分明显,特别是与音译相关的词化。对中国文化词,我们当然可以坚持意译的原则,采用外语中的已有词汇来译介中国文化词,如可用“mascot”翻译“福娃”,用“dragon”翻译“龙”,但这样翻译的缺点是可能会牺牲文化特色和原创性,或者歪曲、误导中国文化词的实际内涵。对此,直译和音译作为有效的手段正可补其不足。特别是基于汉语拼音方案音译而来的中国文化词,由于包含异域特色又照顾了多音节语言接受外来词的习惯,承载汉语的声音且易于流传,因此可以作为中国文化词译介的主要形式,便于中国语言和文化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为世界所认识和了解。
附注:
① 朱一凡(2007)对音译字字化的机制和动因做了进一步的探索,值得参考。音译和意译常常不能截然分开,音译和意译中间往往存在着音译加意译的可能。cement从“水门汀”到“士敏土”再到“水泥”的译法变化,表明二者之间存在过渡区域。
② 雷立柏(2008)提到,“Africa本来是Afrigus(‘不冷’)或apricus(‘日照良好’)的意思,为什么称‘非洲’呢?我在2006年和一位来自Africa的留学生谈话,问他喜不喜欢‘非洲’这个名称,他直接说:‘这个名词将来一定要改。因此,我在自己的著作中尽量避免用‘非洲’,多用‘阿富利加’来代替它或直接用Africa。”他还提到“叙利亚、希腊、那不勒斯”等的汉译的不准确性。其基本观点是,外来词的含义,要么努力翻译出其命名理据,要么保持其外语形式不译,总比使用引人误解的汉字好。这实际上反映了“字”与和“义”的强制关联,没有只表音不表义的字,人们十分自然地会见字想义、望文生义。即使是面对纯粹音译而来的外来词,人们也避免不了对其用字意义的联想,所以翻译者在选字上依然需要十分考究。
③ 窃以为,“剑桥”的译法,也有如此效果,但似乎不如“康桥”温馨、柔和。
④ 严格来说,这样按只译音不译义做法译出来的词并非真正汉语化的外来词。我们在说这样的词时常常感觉是在说外语而非汉语。玄奘对佛经的翻译,如麽贺(“大”,maha)、底哩也(“三”,tri)、畔左(“五”,panca)、尾你也(“明”,vidya)等,严格来说都属此类。
⑤ 相比“维他命”的译法,“维生素”只是用“维”字保持着原词的语音。
⑥ 张普(2005)称之为字母词语,其定义是:“现代汉语中含有字母的词和含有字母的相对固定的短语。”刘永泉(2002)的定义是:“由拉丁字母(包括汉语拼音字母)或者希腊字母构成的以及它们分别与符号、数字或汉字混合构成的词。”
⑦ 与“镭射”相比,“激光”则是一种完全从意义出发的重新表述,摆脱了原词语音外壳的束缚。
⑧ Double Star(双星)、Double Happiness(红双喜)、Golden Rooster(金鸡)等商标应也属此类。见《汉字五千年》(国家汉办/孔子学院总部2009)封底。
⑨ 赵元任先生完整的原话是:In Chinese conceptions, tzu4is the central theme, tz’u in rather varying senses is a subsidiary theme, and rhythm gives the language style.译文:“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字’是中心主题,‘词’则在许多不同的意义上都是辅助性的副题,节奏给汉语裁定了这一样式”(赵元任1992:248)。
⑩ 其实,如果我们仅着眼于记音,则完全可以不在乎这一点。
孔子学院总部/国家汉办.2009.汉字五千年[M].北京:新星出版社.
雷立柏(Leo Leeb).2008.我学习汉语之路[J].国际汉语教学动态与研究(4):90-93
吕必松.汉语的特点与汉语教学路子[A].吕必松编.2005.语言教育与对外汉语教学[C].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48-62.
徐通锵.1994.“字”和汉语研究的方法论[J].世界汉语教学(3):1-14.
张军.2009.赵C人名事件[A].“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课题组主编.2009.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08)(上编)[C].北京:商务印书馆:278-288.
张普.2005.字母词语的考察与研究问题[J].语言文字应用(1):71-74.
赵启正.2006.向世界说明中国(续编)[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
赵元任.1980.中国话的文法(丁邦新译)[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赵元任.1992.汉语词的概念及其结构和节奏(王洪君译)[A].袁毓林主编.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拓与发展——赵元任语言学论文选[C].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31-248.
朱一凡.2007.音译字字化的机制和动因[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3):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