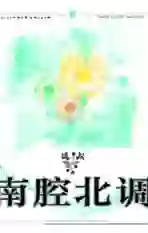乡土世界建构中的身份迷思与精神重造
2022-06-27仲恒
仲恒
摘要:沈从文的湘西题材作品,在时代洪流和个人经历的双重影响下,隐含着多重创作心态。从表面上来看,这些作品体现了沈从文对乡土世界的依恋和对现代文明的排斥;从深层次来说,其中蕴藏了情感与现实、城市与乡村间话语裂隙中沈从文矛盾彷徨的心理;再进一步剖析,可以挖掘出沈从文通过构建由美与爱构成的原初文明状态,以重塑国民精神的崇高理想,凸显现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关怀和时代担当。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书写 创作心态
20世纪80年代,文艺心理学的研究视角进入国内学界,学者们着眼于剖析文学家的精神世界、创作心理,乃至一个创作群体在时代背景下凝结的共同心态。但是,由于人心幽微绵邈,常常导致学者对文学家创作心态的研究,陷入模棱两可的“主观唯心主义陷阱”。为解决这样的弊端,“欧美的心态史研究者将书籍史和阅读史作为联系过去心态的一种手段,开始了书籍史/阅读史与心态史研究相结合的新探索”[1],将书籍、作品作为创作者心灵世界的重要外现载体进行研究。
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注重在文艺心理的研究中与创作主体进行互动。如杨守森的《生命存在与文学艺术》强调“从创作主体出发,注重对作家、艺术家创作过程中的心态分析”[2]。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家们承受了时代剧变带来的巨大灵魂震颤,激烈的内心冲突、跌宕的心路历程纷纷在其作品中呈现。沈从文作为京派重要作家,“立足于湘西世界而为现代文学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3],其作品具备极高的艺术价值。在传统社会的伦理体系被现代文化逐渐瓦解的时代,城与乡呈现出两幅全然不同的景观。沈从文踟蹰在二者之间,独特的人生经历构筑的微妙心理定位和复杂精神场域,每每流泻于对湘西故土的书写中,为现代文学研究留下了一个含金量甚高的富矿。

一、对商业文明的排斥与对乡土世界的依恋
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俨然是一个未被现代商业文明入侵、也未被传统礼教文化渗透、纯粹由爱与美构成、类似“桃花源”的乡土文明世界。那里山水清澈秀丽,人性质朴善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和谐,流淌着脉脉温情,与其他作家笔下的乡土世界呈现出不同的风貌。例如,在现代作家笔下,常常出现传统社会中的特殊群体“童养媳”。她们在宗法和礼教构成的人际结构中处于最底层,大多背负着悲惨的命运,在多方压迫下毫无喘息空间。萧红的《呼兰河传》中的团圆媳妇,出嫁不到一个月,便经历了诸多残酷折磨。冰心的《最后的安息》中的翠儿,被认为克死了公公而遭百般虐待。王西彦的《悲凉的乡土》也描绘了童养媳凤囡被婆婆揪着耳朵打骂的场景。沈从文笔下的童养媳萧萧,则与这些悲苦女性迥然不同,她“像一株长在园角落不为人注意的蓖麻,大枝大叶,日增茂盛”[4],在静谧如水的环境中恬然生活着,祖父还时常和她开玩笑,戏称她是“女学生”。甚至当她受人勾引,怀了孩子,按照传统应“沉塘”或“发卖”时,她的本族人心有不忍,竟默许她和小丈夫“仍然如月前情形,姊弟一般有说有笑地过日子”[5]。她生下孩子后,婆家人发现是个儿子,便“把母子俩照料得好好的,照规矩吃蒸鸡同江米酒补血,烧纸谢神”[6]。
通过沈从文与其他作家的对比,可以发现他笔下的湘西世界全然不见晦暗阴冷的色调,萧萧也不像其他作家塑造的童养媳那样心灵被绝望所填充。相反,她健康蓬勃地生长,被单纯而原始的善意浸泡着。沈从文其他小说中的湘西世界也大抵如此,通常被认为是负面的形象,或难以被传统道德伦理所接受的情节,在这里都被染上了暖色。如《边城》中的商人重义轻利,《丈夫》中的男人来看望作船妓的妻子时,自己却觉得羞愧不堪。
同时,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主色调是绿色的,充满了蓬勃的生机。其中,自然环境是饱含绿意的,如《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中的“山坡全发了绿”[7] ;《月下小景》中“松杉挺茂嘉树四合的山砦”[8]。人物的着装也是绿色的,如《三三》中女主人公飘忽的葱绿衣裳,《长河》中夭夭的葱绿布衣,而《边城》中的女主人公“翠翠”的名字本身便带有绿色的含义。人的色彩与自然的色彩水乳交融,不分彼此,在同一片文学空间中和谐地共存。人被打上了自然的烙印,与自然相契合的生命状态比比皆是,如翠翠像一头小鹿,性格如水般清澈;《虎雏》中的小兵像豹子一样野性难驯。自然也被赋予人性,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有自己的灵动,《边城》中老船夫屋后的白塔、《长河》中河岸的橘子园等,都是“人化”了的,具备自己的“灵性”。
從“绿色”本身也可以看出沈从文笔下湘西世界的和谐与清新。瓦西里·康定斯基认为,“绿色有着安宁和静止的特性,如果色调变淡,它便倾向于安宁;如果色调加深,它趋向于静止。”[9]自然和人物被渲染上的浓厚绿色,便使整个世界都显得静谧空灵。高爽的《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对此进行了精到深致的总结,即“绿色象征平静中沉淀着蓬勃的力”[10],道出沈从文的乡土世界在宁静祥和中蕴含的力量。
然而,沈从文作品中的城市与乡土截然相反。湘西山灵水秀、悠远静谧,城市则喧嚣纷杂、污浊不堪;湘西的人朴素单纯、劲健勇敢,城市的人则荒淫放纵、怯懦卑劣;湘西世界满是和谐纯粹,城市世界则满是尔虞我诈。如描写8个教授去青岛海边度假的《八骏图》,刻画城市高级知识分子的丑恶嘴脸:教授甲桌子上摆着全家福,却在蚊帐里挂上了半裸美女;教授丙白发苍苍,却对自己的侄女产生了欲望……他们声名显赫、受人尊敬,却心理变态、人格畸形,这凸显出城市生活对于人的压抑和扭曲。《绅士的太太》更侧重描写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叙述一对夫妇之间的逢场作戏,即俩人之间毫无感情,相互欺骗隐瞒,丈夫荒淫无耻,背着妻子和其他女人卿卿我我;妻子更是淫荡放纵,与西城大少爷通奸,展现了城市道貌岸然的人际关系背后伦理道德的败坏。
沈从文揭下了虚伪的道德面纱,展现出城市日常生活的物欲横流,正如他在《绅士的太太》的题记中所说:“我不是写几个可以用你们的石头打他的妇人,我是为你们高等人造一面镜子。”[11]也正是因为迫切地寻找“镜子”,沈从文笔下的城市与乡村二元对立,即他无意去展现城市氛围的全貌,仅仅构建了局部的、可以推动情节发展并有利于主旨表达的城市生活空间,他的城市小说“明显不具备‘湘西那样的迷人与异国情调’……在表现城市世界中人的心理扭曲与精神无能时,其氛围‘显得陈腐与公式化’”[12]。在沈从文的眼里,城市仅作为一种道德符号与乡村对立,“而非一套完整的城市语汇”[13]。也就是说,聚焦点之外的城市中发生了什么、城市整体是一番怎样的图景,他是不关心的。这既是其城市小说失之偏颇的根源,也与他深厚且理想化的“湘西情结”密切相关。
沈从文对故乡湘西世界有着深深的眷恋。那个被青山绿水环绕的世界美如梦幻泡影一般,让人觉得不应存在于兵荒马乱、遍地疮痍的20世纪早期中国。与之相反,他笔下的城市物欲横流、人性缺失,与乡土相比,存在鲜明的反差。这种强烈的对比不但凸显了他对乡土的亲近,更映射出他对城市的排斥。
这与沈从文的生活经历有着紧密联系。童年时期的沈从文身心沉浸在葱茏灵秀的自然山水中。1917年,15岁的沈从文离乡参军,1922年前往北京求学,但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均未录取他。纵使屡屡发表作品,但他在北京文坛依然被视作异类,使其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后来燕京大学聘请他任教时,他断然拒绝,背后也映射出他潜藏内心的复杂情绪。同时,沈从文在北京的生活十分困顿,如若不是郁达夫等人的资助,或许已经不能维系基本的吃穿用度。此外,沈从文曾沉痛地哀悼和自己同样离乡来京,在京生活郁悒悲苦的满叔远和刘梦苇,也可被人们管窥出“借他人酒杯,浇心中块垒”的意味。
所以,都市的惨淡生活更激起沈从文对于乡土的怀恋。他屡屡以“乡下人”自称,在晚年的自我评述中还总结道:“我人来到城市五六十年,始终还是个乡下人,不习惯城市生活,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沅水和水边的人们,我感情同他们不可分。”[14]同时,沈从文不无悲悯地指出:“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太杂乱,……这并非你们的过失,只是你们的不幸,造成你们不幸的是这一个现代社会。”[15]因此,他意图展现湘西乡土社会的“优美、健康与自然”[16]。这种体验和论调也明确体现了他对都市生活的反感和对现代商业文明的排斥。
二、迷茫的身份定位与话语裂隙中的矛盾彷徨
虽然沈从文极力构建一个美好恬静的乡土世界,但是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乡村世界不可能如沈从文所描绘的那样洁净无垢。一方面,伴随着西方文明的侵入,中国乡土的稳定架构逐渐被商业文明所渗透、瓦解;另一方面,纵使地处边陲,传统宗法的毒害未曾深入骨髓,但接近原始状态的生活所带来的蒙昧野蛮也不可避免。
沈从文的作品也体现了他对湘西世界的喟叹和反思。在《萧萧》中,萧萧在婆家未遭到虐待和不公,甚至生活得无忧无虑,但是深入其细节,可以发现这里并非完美无瑕的“极乐世界”。童养媳的身份对女性来说有很大的心理压力,但是萧萧对此毫无波澜:“到那一天,这女人还只是笑。她又不害羞,又不怕。她是什么事也不知道,就做了人家的媳妇了。”[17]因为她心中对此并无概念,如一株草木般无知地生长。她和花狗之间的媾和,也仅仅是一种动物本能意识驱使下的行为。花狗用最原始的唱歌方式去引起她的注意,而她所期望的“和花狗进城”也不是去追求自由,她甚至不知何为自由,这不过是在生物本能的影响下媾和后怀孕的一种蒙昧行为。此后,她因不想生下孩子,又喝冷水、吃香灰,足见这并非一种田园牧歌式的爱情。得知萧萧怀孕后,其他人对她的态度也很暧昧。“沉塘”“发卖”是处罚的规矩,但为什么有这样的规矩、谁定的规矩,大家都莫名其妙。萧萧生下了儿子,婆家竟将她的儿子一起抚养。这些既体现了湘西世界中人们的善良淳朴,但也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他们的麻木和无知,这一正一负两种特质奇妙地共存在他们身上。
可见,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书写存在两种话语体系。一方面,他意欲怀着脉脉温情去构建出美好的图景;另一方面,他深知自己的故乡亦有积弊沉疴,远没有想象中那样美好。这两种话语纠葛不清,时刻撕扯着沈从文的内心世界,构成了巨大的话语裂隙。这种话语裂隙,在他回到阔别11年的故乡后写下的《湘行散记》和《湘行书简》中体现得更为清晰。面对故乡中那些带有野蛮落后的精神状态的人,他说:“他们生活得单纯,使我永远有点忧郁。”[18]他笔下的那些水手们“全是在能够用力时把力气卖给人,到老了就死掉的”[19]。吊脚楼里的妓女们对于自身的健康和生命也漠不关心:“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病倒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20]
在《边城》中,舢板上的水手和吊脚楼中的妓女也存在真挚的感情和高尚的品德,他们“既重义轻利,又能守信自约”[21]。面对同样的群体,沈从文既对其寄予真情,又明顯地秉持一种悲悯和审视的态度:“他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这些小人物的哀乐,他们应付生存的方法和发泄情感的娱乐方式古今相同,感觉不到活着的惶恐……历史于他们毫无意义,他们似乎也与历史毫无关系,这令他感到哀戚。”[22]在哀戚惆怅的同时,沈从文又怀着一种改造的心态,想着“不过有什么方法,可以改造这些人狂热到一种新的竞争方面去?”[23]这是他以精英知识分子视角看待家乡的结果,正如美国学者伍梅芳所论:“作为京派作家,沈从文以城市或精英读者为书写对象,其叙事和审美视角不属于湘西原住民,而是反映城市精英的目光。”[24]
这种悲悯、审视乃至改造的心态其来有自。费孝通认为“近百年来更在东西方接触边缘上发生了一种很特殊的社会”[25]便是所谓的“乡土中国”,也即“乡土中国”的概念,是在西方文明侵入后才被发现的。因为西方所谓的“现代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来讲是异质的,在包容吸纳西方文明的过程中,城市吸纳得多,而乡村吸纳得少,形成了一种差异和断层,构筑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矛盾,也使有识之士用西方文明滤镜去检阅广泛存在于乡土中的中国传统文明。
沈从文从凤凰小城走出,离开乡土进入城市,对这种差异有着异乎常人的敏感。当他将目光投向城市时,可以跳出城市的圈层,揭示其丑恶,并描摹乡土的美好。但他在城市里生活多年,并凭借卓越的天赋和才能跻身文艺界。不管他自己是否愿意承认,他都已经成为一个精英知识分子,此时的他再将目光投回生养自己的乡土,便不由自主地带上了一层他者的审视目光。纵使他怀着对故乡的眷恋和对城市的排斥,想要讴歌乡土的美好,但京派作家、现代学者的身份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知识和视野,每每唤醒他的理智,压制他的情感,迫使他反思乡土世界的缺陷,对其赋魅的同时,又不得不进行祛魅。因此,沈从文在乡土世界的感性依恋和理性反思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碰撞,其文学作品中的话语便被撕扯开一条难以弥合的裂隙,其矛盾彷徨的心态也就由此生成。
进一步看,在沈从文的湘西书写中,体现出的矛盾心态还有更深的意蕴。据前文所述,在城市中,他一直以“乡下人”自居,纵使在城市生活十年,乃至大半生,也无法融入其中成为一名“城里人”。张同胜认为,这种以“乡下人”自居的心态,是沈从文对城市中带有敌意的他者凝视目光的内化或抵抗。他在都市中被冷落、蔑视,便自称“乡下人”,并有意将湘西世界中的正面因素和城市生活中的负面因素绝对化,其中蕴含的乡土情怀“是一种梦境、一种斗争策略、一种情感寄托”[26]。湘西世界不但是他魂牵梦绕的生命起始点,更是他被他者目光凝视后重构自尊的话语资源,这说明他一直略带激愤地冷眼观望城市,带着一份自我疏离。然而,“地方的一切虽没有什么变动,我或者变得太多了一点”[27]。当沈从文回到故乡后,又悲哀地发现自己已经再难融入这片土地了,面对他投以无限温情的湘西世界中人,他却说:“但同时我又与他们那么‘陌生’,永远无法同他们过日子,真古怪。”[28]
现代知识分子的身份,让沈从文与湘西世界之间产生了一层无法冲破的隔膜,他只能以他者的目光去看待这里,却永远无法属于这里。所以,他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使他可以跳出城市看城市,跳出乡土看乡土,但也让他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端。主观的情感使其排斥城市而亲近乡土,而客观的现实又使其被乡土挤压出去,这种身份认同的迷茫和情感依托的悬空,使其笔下的湘西世界在祥和下蕴藏着隐痛,其矛盾彷徨的心态也更加深刻。
三、歌颂人性美好的虔诚与重塑民族精神的担当
从个人内心世界来看,沈从文对于乡土的书写显现出其依恋而矛盾的心态。但如若沈从文囿于一己天地中难以自拔,那么他便不能被称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如果研究者在剖析沈从文的内心世界时,只局限于他对个人命运的思考和悲戚,也会忽略他更为珍贵的情操,导致研究有所缺失。
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书写和构建,体现着作者广阔的胸懷和崇高的理想。他意图塑造一个纯粹由美与爱组成的乌托邦。在其乡土小说中,有诸多想象、虚构的成分,这固然符合他经验世界中“身临其境”与“思想散步”这两种方式[29],但更是他“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地说明”[30]之文学理想的发扬。沈从文所追求的是在艺术中表达精神的光辉和圣洁,这背后是他独特的生命观和人性观,他认为“人性是生物性和神性的统一”[31],人在满足自己生物性的同时,要向往超越动物本能的崇高光芒,以期趋近本就存在于生命中的神性。为此,他“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32]。正因为对人性本真的崇尚,他最终与所审视、反思的那些湘西世界中的人达成了和解。在批判他们精神状态庸碌麻木,不知为何而生,亦不知为何而死的过程中,沈从文看到了他们的生活在最根本上是庄严而肃穆的。虽然他们并不自知,但他们自然而然地散播善意;无论他们生活得如何,但“却从不逃避为了活而应有的一切努力”[33]。通过对“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34]的描摹,沈从文在更高的层面上作出弥合话语裂隙、消解矛盾心态的努力。
他笔下的湘西世界,不但在现代商业文明的侵蚀下保持出尘姿态,也几乎不受中国传统礼教与宗法的桎梏。在《萧萧》中,面对“沉塘”“发卖”两种惩罚选择时,作者直接亲身下场,介入故事中,作出“沉塘多是读过‘子曰’的族长爱面子才做出的蠢事” [35]的批判,还表示这些规矩的制定者,“是周公还是周婆,也没有人说得清楚”[36],这便是对传统礼教的一种辛辣嘲讽。所以,沈从文的笔触直抵生命最原初的形态,其最根本意义在于构建了一片不受政治和文明沾染的,展现人性原始状态的世界,如教徒般对美与爱满怀虔诚,用理想化的审美视角及其背后的深情,取代了其他乡土文学作家的激切批判,在“‘神’之解体的时代,重新给神作一种光明赞颂。在充满古典庄雅的诗歌失去价值和意义时,来谨谨慎慎写最后一首抒情诗”[37] 。这种立足于审美现代性的乡土书写,对后世也产生了影响,从沈从文、汪曾祺,到王润滋、李杭育再到肖江虹,构成了一条乡土小说发展的承续脉络。
沈从文建立关乎爱与美的“宗教”,不仅为宣扬自己的文学理想,更是意欲为中华民族开出属于自己的药方。他的心态和五四文学革命传统具有传承关系,“希望个人作品成为推进历史的工具”[38],赋予文学以丰饶国民情感、重塑民族精神、提振文化自信、促进文明改良的重任。他认为人们需要“美和爱的新的宗教” [39],来激发对生命的追寻、对人类未来的探索,进而生成“崇高庄严”的感情,由此方能重造国家民族。从这个视角看,对湘西世界的书写,无疑就是沈从文针对古典德行消逝的难题所交出的独特答卷。在这份答卷中,充满自由主义的色彩,与政治保持一定的距离。
这绝不能说明沈从文将自己拘囚在湘西的世外桃源中。恰恰相反,他的视野从湘西小世界扩展到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命运和发展的大天地中,正如他自己所说:“虽然这只是湘西一隅的事情……必然包含若干人情的冲突与人和人的关系的重造。”[40]鲁迅用辛辣的笔法揭露中国乡土世界的丑恶,塑造了阿Q、华老栓、祥林嫂等一系列人物,以抨击传统社会对人性的摧残践踏,具备现实价值和普遍意义;沈从文用温柔的情感构建中国乡土世界的美好,塑造了夭夭、傩送等一系列形象,以激发人们心底的善念,这亦是一种启蒙精神的体现。所以,沈从文书写湘西世界,也是为通过一隅水土中的人事沉浮,求索关乎“中华民族赖以生存和向前发展的‘文化母体’”[41]。
总之,沈从文一生命运曲折,在时代洪流中漂泊沉浮,曾沉醉于沅水微波的他,在决然走向滚滚红尘后,用大量笔墨描摹自己的故乡,书写出独特的湘西世界。字里行间流淌着西南边陲的清新灵秀,也埋藏着他幽微曲折的心灵世界。剖开其中对故乡深厚感情和类似“流亡者”的孤寂悲戚,可以发现沈从文希望以泛神情感勾勒湘西世界纯粹的美与爱,建立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进而重造国家和民族。其中体现的是沈从文作为知识分子的社会担当感和历史使命感。正因如此,他对湘西世界的书写,才通向了对人类命运和发展的思考。
参考文献:
[1]于文.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社会史转向[J].国外社会科学,2008(04).
[2]杨守森.生命存在与文学艺术[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307.
[3][31]权绘锦.现代文学经典作家十八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222,227.
[4][5][6][17][35][36]沈从文.萧萧[M]//沈从文小说精选集.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9:66,80,80,64,79,79.
[7]沈从文.七个野人与最后一个迎春节[M]//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87.
[8]沈从文.月下小景[M]//沈从文全集:第九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17.
[9][法]瓦西里·康定斯基.论艺术的精神[M].查立,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0.
[10][22]高爽.沈从文创作心态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20.
[11]沈从文.绅士的太太[M]//沈从文全集:第六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13.
[12][13][24]刘竺岩,等.新世纪美国沈从文研究述评[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09).
[14]沈从文.从文自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122.
[15][16][30][32][34]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M]//沈从文全集:第九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4,5,5,2,5.
[18][28]沈从文.河街想象[M]//沈从文全集:第十一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32,132.
[19]沈从文.水手们[M]//沈从文全集:第十一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28-129.
[20]沈从文.桃源与沅州[M]//沈从文全集:第十一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35.
[21]沈从文.边城[M]//沈从文全集:第八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71.
[23]沈从文.箱子岩[M]//沈从文全集:第十一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81.
[2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1.
[26]张同胜.他者凝视的内化与抵抗:沈从文的“乡下人”问题新论[J].西部学刊,2019(13).
[27]沈从文.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M]//沈从文全集:第十一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53.
[29]沈从文.给一个读者[M]//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228.
[33]沈从文.历史是一条河[M]//沈从文全集:第十一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88.
[37]沈从文.水云[M]//沈从文全集:第十二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28.
[38]沈从文.沉默[M]//沈从文全集:第十四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108.
[39]沈从文.美与爱[M]//沈从文全集:第十七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362.
[40]沈从文.长河[M]//沈从文全集:第十卷.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9:7.
[41]吴翔宇.沈从文重构“乡土中国”的文化機制与话语实践[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06).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