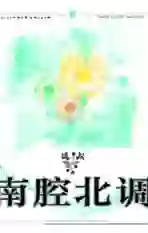纯诗境界再论
2022-06-27枣红马
枣红马

引论:纯诗境界,具有深厚而广阔的理论加持。
瓦雷里提出的纯诗和纯诗境界,不但具有可操作的应用性,又具有广阔前景的理论性。从世界性的研究状况来看,它确实显示了诗学的人文学科的科学性。在《纯诗境界论》中,我主要是在诗学实践的层面上探索纯诗的境界,而在这篇“再论”中,则主要在诗学理论的层面上探索纯诗的境界。
既然纯诗境界具有诗学理论的科学性,那么,它必定具有内在关系密切的心理学和哲学的理论加持,而且,随着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多学科的融合性和跨界性,更是扩展了心理学和哲学的研究思路,也为纯诗诗学的理论发展提供了更多的思想方法。比如,美国物理学家卡普拉博士从现代科学中寻找哲学寓意,他的在西方影响巨大的著作《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通过对印度教、佛教和道家的哲学思想研究,认为“东方神秘主义和西方神秘主义差别在于,神秘主义学派在西方始终只是配角,在东方的哲学和宗教思想中却构成主流”[1]。他所揭示出的东方神秘主义的直觉性,和超越日常生活三维世界体验的更高层次的多维存在,对于领悟纯诗的诗学义理具有较大的拓展意义。诗,是诗人通过想象创造意象,而想象则是诗人的心理活动和心灵所孕育的,所以,诗和一切有灵性的多维时空具有血肉的联系,而东方哲学的神秘意蕴就充溢着诗的灵性。再比如,美国超心理学家迪恩·雷丁博士以研究心灵现象为方向,写出成为亚马逊畅销书的《意识宇宙——心灵现象中的科学真相》,他认为人的心灵现象具有特异功能,这种特异功能是一种超自然现象,是一种神秘主义现象,具有超自然的存在和力量。据此,他提出“非眼视觉”超自然现象。关于这种现象,30多年前我在论诗的时候提出过“灵感视象”,但我那只是关于诗的构思的诗学体验,而雷丁博士则进行了心理学实验,更具有科学的可信性。
卡普拉博士和雷丁博士对于东方神秘主义的研究所得出的本质性的结论,一个是直觉性,一个是非眼视觉,都涉及深度的心理创造活动。所以,我认为,卡普拉的直觉说和雷丁的非眼视觉说与诗学幻象的潜意识创造,都应该是诗人的一种特殊功能。真正的诗人是必须具有诗的天资的,是一种诗学的特殊功能。如果不具备这种天资,很难成为优秀的诗人。有的诗人写了一辈子诗,出版了多部诗集,但由于缺少灵感视象的特殊创造心理,诗的形态则多是观念化乃至于概念化、口号化、说教化,没有什么诗学的价值。所以,我认为卡普拉和雷丁对于东方哲学思想的研究,有助于纯诗理论的深入探究。
那么,卡普拉博士是如何发现东方神秘主义的直觉性思想的呢?他对于中国的道家和禅宗进行深入研究之后说,“道家关心的首先是观察自然和发现自然之‘道。道家认为,当一个人遵从自然的规律,自然地行事,并且相信自己的直觉知识时,就能享受人类的快乐。”他认为《道德经》“不是表达一种理性的概念……而是一种有机的图像……它保持了字词形象的高度综合性的启发力”。他认为,“禅宗比任何东方神秘主义流派都更为深信言辞永远无法表达终极的真理。”因为,“禅宗的经验就是觉悟的经验”,而“禅宗所说的觉悟是指直接体验一切事物的佛性”。[2]这就是说,中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多是感悟型的,也可以说是诗性的感知。对此,中国现代哲学大师冯友兰先生的著述作了具体而深入地阐释。在西南联大期间,冯友兰一边紧张地钻防空洞,一边淡定地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汪洋大海中浸泡,写出了体系性的“贞元六书”。而其中的《新原人》《新原道》对于他所认为的宇宙至高境界“天地境界”作了深入探讨,这对于我们认识纯诗境界的理论性,具有哲学思维的启发。
愈是深入纯诗境界,愈是觉得那些诗学的境域里奥妙无穷。理论,人文的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和跨界的多学科融合的理论,犹如隧道里的光芒,指引着我们走出狭窄的思维空间,在纯诗境界的无边无际的宇宙空间遨游。
一、纯诗境界的神秘性指向:隐秘和无限。
西方人探讨的东方神秘主义,具有超强的隐秘性内涵,诸如上面提到的直觉性和非眼视觉。隐秘的意蕴,从诗学的意义上来说,它隐藏在哪里呢?它隐藏在诗人的潜意识里和前意识里,它催发诗人的灵感视象,它在灵魂的中心地带生长发育;它隐藏在大自然乃至宇宙本体里面,那是自然造就的神秘的力量;它隐藏在诗人创造的意象里面,这就是中国传统诗学的最美妙的意境。一般来说,这些地方只可用心灵意会,很难用语言准确描述,这是神秘性的一般性特征。就是因为意蕴的隐秘,古代人只能谈感悟的心得,现代人掌握了科学理论之后,才以心理学的科学实验而揭秘。对于这样的心理学隐秘,我们是看不到的,除非诗人具有特殊功能的非眼视觉,就是我们常说的超強的内视力。因为隐秘的意蕴所隐藏的地方,都是一种无限的所在。而这种无限的意蕴表现在诗学上,就必定有符号的显现,它就是幻象。幻象的意境是无限的,就如卡普拉博士说的用言辞永远无法表达的终极的真理。或可从另一个角度说,人的想象力有多高多大多强,那么幻想的意境就有多高多大多强。当然,人的想象力是无限的,而幻想的意境也就必然无限。这就是瓦雷里纯诗论中所涉及的感觉和幻象的两个本质性内容。也就是说,在纯诗的幻象里,隐秘和无限的境界不是分割的孤立存在,而是融为一体,成为诗人的深入探秘和永远追寻。
这样的纯诗境界并不是凭空捏造或者无端地想象出来的,它和人、宇宙的一些天性及运动、发展规律有着惊人的一致性。人的精神无限,宇宙的精神无限,而纯诗的境界也就无限。
冯友兰先生把人生和宇宙的境界分为四种: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和天地境界。功利境界和道德境界是放在社会的语境中考察的,它不是诗学的境界,因为诗无功利,甚至也不能用道德境界来衡量。对于此,河南著名诗人于赓虞在1929年就曾经论及。他认为,“论诗之价值当论其本身是否为完美的诗足矣,不能以其伦理效应而论其价值,此点虽甚重要,但往往被古今之批评家所忽略。”“诗人只要将其生命的灵影、和谐的韵节表现之于完美的诗篇,则其职务已完;至于道德的或伦理的影响,乃是诗的副产品,无关于诗人,无关于诗之本身。”[3]这就表明了,我国新诗领域对于纯诗理论的探讨早已经开始,可以说与国际诗坛基本同步,而且至今仍有诗学的价值。而冯友兰说的自然境界,并非自然界的自然,而是人原始的素朴的世俗的境界,譬如人的日常一般的愉悦情感,此亦非纯诗追寻的境界。鉴于此,我就具体分析冯友兰概括的天地境界。6F391035-CC3F-499D-A3D3-BDC9AF0B01DC
冯友兰认为,对于宇宙人生的参悟,都要“依照永恒底理”,就是规律。那么这个永恒的规律在哪里呢?“不仅是在人的‘性分以内,而且是在‘天理之中”,“不仅是人道而且亦是天道”。而且道体是“无头无尾的大事”,“是整个底太极”,就是上面说到的无限,是思悟之后的“究竟无得”。这就是人生和宇宙的天地境界。[4]他说的“天道”“无头无尾”“太极”“究竟无得”,其实就是某些西方现代哲学家的“虚无”说。虚无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没有,而是至高境界的没有,反过来或可以说是一种“大有”,是“无边无际的有”,是“无限的有”,就是冯友兰说的“永恒底理”。老子说的“大音希声”,应该说已经开始了探索“虚无”的境界,换个形象的说法,大音希声就是虚无的胚胎。而闻一多先生论诗时提出的“宇宙意识”,与冯友兰论哲学时提出的“天地境界”,都具有“无限的有”的基本内涵。我想,要能捕捉到“无限的有”和“虚无”所蕴含的意义,就应该彻悟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否则会让人感到很玄乎。“宇宙意识”和“天地境界”的意蕴,和中国传统的道家哲学属于同一个思想体系,而“虚无”在世界范围内与道家哲学应该是近似的思想体系。人们把道家和道家之后的同体系学说称为玄学是不无道理的,而这个“玄”,就我的理解它是一个褒义,内里蕴含着神秘的美、奥妙的美,这样的美和诗的意境美同为天籁之美。
由此可以看出,古今中外有识之士对于无限的理解的指向是相同的,而这一切都归于“道”,它的神秘、奥妙之美,给纯诗的境界带来了无限的意蕴。
西方人是这样认识道的。卡普拉认为,“带着中国特点的对应于神秘主义的方面,它要求哲学家们超越人间俗事和日常生活……达到神秘主义的天人合一的中国贤哲的理想。”“‘道就是无法定义的终极实在”,“道家对直觉的智慧要比对理想的知识更感兴趣”,“对于道家来说,与自然界相协调地行事,也就意味着自发地按照自己的直觉行事,也就是相信自己的直觉智慧”,道家“强调所有直觉、女性、神秘和柔顺”,而“禅宗的经验就是觉悟的经验”。[5]卡普拉这些论断抓住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而这个根本就是直觉和觉悟。对于卡普拉关于“道”和相关的“禅宗”的理解,联系诗学,我认为包含了这样几个方面的内涵:一是道的隐秘性通过直觉生发诗的意象,如果有概念化的介入,詩意就会遭到破坏;二是以悟的思维方式探求终极存在,超越于语言的表达,它终究会幻化为诗的幻象;三是天人合一的神秘主义,这与前二者有紧密的关联性,神秘性一定是隐秘的超语言的,它推动着诗人去探索和追寻更为广阔的意蕴。我想,这三个方面都是纯诗和纯诗境界的本质元素和纯诗创造的本质因素。
从卡普拉的研究可知,对于“道”,不在于探究它是什么内容,而在于探究它的表达形态和追寻的过程。按照冯友兰的说法,就是“觉解”。
觉解是一种认知方式,但它不是认知概念和论证概念,而是悟,心悟。觉解不是一般人们说的理解,它是一个过程,既是一个感觉的过程,也是一个思悟的过程。对于这种东方的习惯的认知方式,卡普拉博士把它与艺术结合起来考察,得出的是直觉意识状态的结论。“东方的艺术形式也是沉思的方式。与其说它们是艺术家们表达思想的方式,不如说是通过发展直觉的意识状态来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的一种方法。”[6]这种觉解的感觉和思悟的过程,继续创造着东方神秘主义的意识状态,正如上面所说,这种状态很玄秘,也很美妙,所以,我们中国古代自然主义诗人创造的意象,都有非常含蓄而美妙的意境。
虽然,这是东方的神秘思维方式,但却有着人类的适应性。哲学家康德把人的性格分为悟知性格和验知性格。叔本华进一步探讨,认为所谓悟知性格,就是人生来就具有的先天性格,是人的最内在的本质,是自在之物,意志自身。而验知性格则是悟知性格的表现,即意志的客体化。由此,叔本华通过探讨人的悟性,从而得出由悟性而产生的反省思维。悟性是人的天性,而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发挥这种天性,“吾日三省吾身”,形成了中国古代人的内省思维。而这种内省思维很适于诗的创作,当这种思维的内省达到极致时,也就是诗的意境达到无限境界的时候,中国便出现了唐诗宋词的诗学时代,并且成为世界文学的一座高峰。
悟性和内省思维,让西方人认识到了东方神秘主义,而东方神秘主义则蕴含着无穷的诗学奥妙,它凝聚了纯诗境界追寻的无穷魅力。对于这种诗学奥妙,很难用西方的科学方法论证,因为按照冯友兰的说法,“神秘经验是不可了解的,其不可了解是超过了解。”[7]我想,冯友兰先生不仅仅是在讲中国哲学,也是在讲诗学,在讲纯诗境界的追寻。在《纯诗境界论》中,我选取了自然、人性和生命三个方面来论述纯诗境界,而诗人对于这三个方面的认识也是神秘经验。这在于两个因素,一是这三个方面的自身本性,都隐藏着神秘感的意蕴,它本身蓄蕴丰富的诗意;二是诗人的本性,诗人神秘的直觉认知思维,就是诗性的感觉和思维。这两个方面的融合,就产生了诗的神秘经验。因此,诗是不可以用概念来解读的,因为这种解读是有限的。而用悟的方式觉解,就是冯友兰说的“不可了解”,而这种“不可了解”则超越了概念的解读,因为这样的“不可了解”的觉解是无限的。诗的构思和创作充溢着神秘的悟性,而这种神秘的悟从隐秘的奥妙开始,一直沿着隐秘的指向,向至高的奥妙境界浸透,抑或顿悟地绽放。所以,我认为隐秘和无限是融合在一体的诗学境界。
发现神秘的隐秘,是哲人和诗人的天性,而感悟隐秘,就会通向无限,就是纯诗境界的追寻。这里举一个人们熟知的例子。禅宗五世祖弘忍的大弟子神秀曾写过一个偈语,“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是在规劝和教导,而他并没有发现万事万物之中的隐秘,所以,境界只停留在具有一定哲理意义的规劝的层面上,是有限境界。而六世祖慧能虽然不识字,却悟性极高,他发现了隐藏在万事万物之中的就是后来冯友兰说的隐秘而无限的天地境界,也说出了四句偈语,“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或可以说,慧能具有纯诗的天资,而神秀则无,因为从他内心世界流出的是说教。说教,抑或类似于哲理诗,不可能达到隐秘和无限的纯诗境界。6F391035-CC3F-499D-A3D3-BDC9AF0B01DC
二、纯诗境界的灵魂表达:诗学力量的根源。
上面谈到的隐秘和无限的哲学、诗学义理是隐藏在“道”之中,而道无限,诗也无限。那么从人学的义理来看,它应该是隐藏在生命的最为隐秘且深邃的地方,就是灵魂的世界。现代主义诗学更加强调最为内在的自我、更为心理学意义的精神和更为哲学(注意,哲学不等于哲理)意义的境界,而最自我和最精神的人的本性则更加靠近灵魂世界。因为那里是最为隐秘和最为至大的诗学力量的根源。
灵魂,不论是医学意义、宗教意义还是人本意义上的考察,都是非常虚幻的存在。但是很多诗学家都认为,那里就是诗学力量的本源。可是,这种力量给人的感觉依然是一种虚幻的存在。所以,我认为,要把这种虚幻的力量变成可感知的力量,那就要首先弄清楚灵魂是怎样的存在。
医学意义和宗教意义的灵魂离诗学较远,姑且不论,而人本意义上的灵魂和哲学意义上的灵魂则直接与诗学关联,这里依据人类学家弗雷泽和心理学家荣格的考察而论之。
弗雷泽考察灵魂是因为要考察生命的动力。人为什么能够生存,人为什么会死亡,对于原始人来说,他们认为都有一个主宰生命的动力,那么这个动力是什么呢?弗雷泽通过考察各个原始部落人种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正如未开化的人在解释无生命的自然过程时,以为是活人在自然现象之中或背后操作一样,他们也这样理解生命现象本身。在他看来,一个动物活着并且行动,只是因为它身体里面有一个小动物在使它行动;如果人活着并且行动,也是因为人体里面有一个小人或小动物使得他行动。这个动物体内的小动物,人体内的小人,就是灵魂。”其实,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就认为,灵魂和身体是二元性的,灵魂是每个人的真正自我,是形而上的。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继续了灵魂的生命动力说的探讨,提出了三个灵魂即植物灵魂、动物灵魂、人的灵魂,人的灵魂是高级灵魂,其他灵魂则是低级灵魂。而不论是低级灵魂还是高级灵魂,都是主宰生命世界的动力。只不过,弗雷泽以人类学的大量文献资料结合广泛的田野调查,比哲学家们的论证更具体,更有可信度。为了进一步说明灵魂的生命动力说,弗雷泽这样考察道,“正如动物或人的活动被解释为灵魂存在于体内一样,睡眠和死亡则被解释为灵魂离开了身体。睡眠或睡眠状态是灵魂暂时地离开,死亡则是永恒的离开。如果死亡是灵魂永恒的离体,那么预防死亡的办法就是不让灵魂离体,如果离开了,就要想法保证让它回来。”[8]这就是说,原始人开始认识人的最高最本质的生命,认为就是灵魂。在他们的认知世界里,灵魂也是人,而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只可想象的人却高于那个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体的人。在那个时候,人就把人分为两个人,一个自然生命的人,一个精神生命的人,而灵魂就是人的精神生命。灵魂说很重要,他们认识到了人的本质。灵魂动力说也很重要,他们认识到了人的创造和创造的力量。
认识到人的灵魂动力说,不仅仅是哲学家和人类学家,心理学家荣格也作了深入地探讨,其结果具有基本的一致性。荣格认为,“在原始人中,灵魂是生命的神奇气息(因此有了‘阿尼玛一词),或者火焰。我们上帝的一句未曾被收入宗教经典的格言恰当地宣布:‘离我近之人离火不远。”他继续说,“有灵魂的存在是有生命的存在。灵魂是人身上的有生命之物,是独自生存并孕育生命的有生命之物。”最后,他得出了與弗雷泽一致的灵魂永生说,“阿尼玛意指灵魂,表示非常奇妙的不朽之物。”[9]
他们考察和论述的灵魂动力说和灵魂永生说,都是精神生命的创造性力量,是人的意识深处的生命力量所凝聚的至大的精神境界。对于弗雷泽说的那个灵魂“小人”,荣格这样解读,“灵魂‘要多小有多小、要多大有多大,他虽然只有‘拇指般大小,但是他‘团团围住地球、统治着十指空间。”[10]这样的至大的生命动力,无疑显示了精神生命的至高境界,所以,现代主义诗人们愈是深入认识人,认知诗,就愈是靠近灵魂,表达灵魂的生命动力。从而也可知,纯诗愈是表达这样的生命动力,愈是能够强化境界的追寻。
那么接下来,人们对于灵魂这样的生命动力、精神境界怎么去认知去表达就是一个关键所在。灵魂具体地存在于人的意识深处,对于它的认知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方法就是感知。这样就又给人们带来一个困扰,那应该怎样感知呢?感知,它是人的一种功能性,荣格在论述“精神”这个概念时,他说,“我们关心的是一种功能性情结,它最初在原始的层面上被感知为一种无形的、气息一样的‘在场……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圣灵降临节奇迹的风。原始心理认为,十分自然是把无形的在场具体化为鬼或者恶魔。”荣格这里说的“鬼”“恶魔”已经不是概念性的“精神”,而是被感知的意象性的“精神”,从概念到意象,就是人的感知功能的作用。对于这种感知功能,荣格在心理学意义上使用的是“投射”,“任何熟悉古人的自然科学与哲学的人都熟知多少‘灵魂被投射进了外部世界的未知部分。”而“经验表明,投射从来就不是有意识的”,因为“有着情感负荷的内容时刻潜伏在无意识之中,并在某一时刻迸发形成投射”。[11]
从潜意识里投射的能够被人感知的就是意象,而纯诗的构思和创作过程就是创造意象,尤其是现代主义诗学追求梦幻般的幻象创造。瓦雷里创作《海滨墓园》正是这样的投射,开始创作时诗人不是有意识有目的地要表达什么观念抑或理念,他只是拥有了强烈的感觉,对生命律动的原生态的感觉。在生命的感觉中,在对生命境界的追寻中,灵魂的中心地带完成了一种幻象的创造,就是“海滨墓园”,而在“海滨墓园”这个诗学幻象里,就蕴含了生命的至高境界。正如卞之琳先生对该诗的评价,“《海滨墓园》的主旨就是建立在‘绝对的静止和人生的变易这两个题旨的对立上……以求达到‘无我境界,回环往复。”[12]
上面所谈的弗雷泽说的灵魂即人里面的“小人”,荣格考察的灵魂就是“气息”,就是“火”,这里的“小人”和“火”不是哲学式的概念表达形态,而都是通过感知功能化为的意象。所以,我认为,可感知的灵魂的介质就是意象,或可以说,灵魂的力量就是意象的高级形式幻象的表达。幻象既是心理学意义的创造,又是哲学意义上的境界,具体到诗学意义,幻象的创造过程就是纯诗境界的追寻过程。6F391035-CC3F-499D-A3D3-BDC9AF0B01DC
意象的创造是一种心理活动,而幻象的萌发则是潜意识和前意识的心理活动。按照法国诗学家马利坦的研究,潜意识和前意识的意识领域是灵魂的中心地带,因此可以说,幻象就是在灵魂的中心地带产生。灵魂是诗学力量的根源,那么,幻象则是从灵魂的中心地带创造的诗学力量的投射状态。关于诗学的幻象,我在《“荒谬”的意义——张鲜明幻象诗学论》(《南腔北调》2021年第3期)和《幻象的生存——再论海子原始意象的现代主义演绎》(《南腔北调》2021年第10期)都联系诗人的作品进行了论述,这里不再赘谈。
正因为灵魂是诗学力量的根源,它的中心地带是潜意识和前意识,所以,从表面上看,它是隐藏很深的静默的土层,其实它是时时掀起波涛巨浪的汪洋大海。即使一时有平静的现象,但这现象的深处也一直搏动着生命的动力。因为这是由灵魂的本身特质所决定。荣格以歌德的《浮士德》为例,认为浮士德“本质上是一个象征”,是“灵魂深处的某种东西的表现”,“它是智者、辅助者和救世主的原型,也是术士、骗子、贪污者和魔鬼的原型。这种意象从人类历史萌芽时期开始就潜藏在无意识之中;当时局动荡,某一个重大的错误使社会偏离了正确的方向,它就被唤醒了。”[13]他这样描述潜藏在灵魂深处的原型被唤醒之后的情境:一条出动的猛蛇,宛如一道炫目的霹雳进入上帝的万物之中,似乎要把万物扯破和撕碎一般,内心的灵魂诞生时,兽性的肉身获得仅仅一瞥,俨然宛若发光一样。获胜的上帝诞生在我们人类中持续时间和闪电持续的时间一样长,而在上帝那里,闪光不断,因此终究是永恒的。这里的“闪电”是魔鬼的一种表现,经过搏斗,上帝获得了生命的永恒。大概欧洲人对于灵魂间的搏斗是一个通识,所以陀思妥耶夫斯基才说,美是上帝与魔鬼彼此争夺人心的战斗。当然,上帝的永恒也是一个象征,具体的意识和心理的搏斗却不是象征那样单纯化,而是复杂又惊心动魄,灵魂间活生生地演绎着惨烈。如果能够细细阅读海子的长诗,自会品味出那种灵魂搏斗的美学震撼。
所以,我想,纯诗一定会表达灵魂间的搏斗,纯诗的境界追寻也一定会表达灵魂搏斗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因此表现出生命的深邃,和生命动力的永恒。
三、纯诗境界的时空拓展:境域、新的复合体和在此意义上的境界追寻。
人类自从成为人类的时候,实用主义便与生俱来,饿了就要找吃的,渴了就要找喝的。不饿了,不渴了,就开启“实用主义”时间,分割它为我所用。最原始的认知就是把它分为白天和黑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实用。这样粗线条地划分“实用主义”时间,人们并不满意,便开始用文化进一步分割,把一天的时间分割为十二个块块,还起了一个个文化范儿的名字。老百姓说的“半夜”就是有文化的人说的“子时”。人们越来越聪明,开始用科技分割时间,发明了钟表,便把时间定死在一格一格的刻度中,残酷地把时间用秒来衡量,稍纵即逝。作家福克纳对于如此残忍地分割“实用主义”时间,再也看不下去了,忍不住便在他的伟大的小说作品《喧嚣与骚动》中,借人物之口向人们发出了振聋发聩的惊世之语:“钟表杀死时间。”钟表杀死时间?是的。“只要那些小齿轮是在咔嗒咔嗒地转,时间便是死的;只有钟表停下来时,时间才会活过来。”[14]
实用主义,真是对生命精神的一种限制或抑制。自从有了钟表,在很多人的眼里,时间不再是自由流動的风,它的自由生命和生命动力被捆绑,被世俗化。虽然人们发现了历史的书写,想把过去的时间留住,但它已经被书写者挑来拣去,揉来搓去,早已经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而且,其中谁又敢说没有实用主义的干预呢?
救救时间吧,人类如果不想固定在狭窄的时间里毫无生气地活着,那么就要救救时间。有思想的人,也早已经开始了行动。哲学家柏格森在钟表时间之外发现了绵延时间,即用直觉体验到的川流不息。哲学家海德格尔视野就更开阔了,他发现了时间性的存在状态,就是他说的“境域”。境域,复活了时间的生命活力。
境域内涵的实质是三元一体化的整体性。《存在与时间》的中文译者这样介绍,“存在本身只有在‘时间中才能展现出来。正因为此,‘时间被海德格尔称为存在本身得以展现的‘境域。”境域作为时间的存在状态,它包含着曾在、将来和当前。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将来、曾在状态与当前这些境域格式统一奠基在时间性的绽出统一性之中。整体时间性的境域规定着实际生存着的存在者本质上向何处展开。”[15]由此看出,境域的将来、曾在和当前的三种时间状态是一个统一性的空间世界,它既是“世内的存在者”,又是“世外的存在者”(这个概念是笔者根据海德格尔的“世界都要更在其外”的论断,又与他的“世内的存在者”相对应而创设的)。海德格尔认为,人作为存在者既以“世内的存在者”领会自己的世界,而又与境域也就是“世外的存在者”“照面”,二者的融合,就是超越了自我的时间性存在的空间世界。
现代主义文学大师艾略特在他的名作《传统与个人的才能》中认为,创作不仅仅有过去性,同时又有现在性,构成一个同时并存的秩序,他把这种构成称为“新的复合体”。“新的复合体”,就是立体的时间性空间。他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作《荒原》就是这种诗学理念的实践。“新的复合体”与“境域”这两个时空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诺贝尔文学奖诗人帕斯承续了哲学家海德格尔和诗人艾略特的时间理念,他认为原始人“时间观念的人领域是广大的”。时间的原型“用一个理想时间的统一性来对抗真实时间的多元性,用一个超越时间的时间的同一性来对抗时间的异质性”。[16]而“对现代性的寻求是一种返本归原。现代性将我引向自己的开端,将我引向远古”“于是我明白了诗人只是世世代代的长河中的一个涟漪”。他认为,过去、未来、现在为时间的“三元体”,“现时是这三种时间的会合点”,“对现代的寻求使我们发现古代,发现了我们民族掩藏着的面孔”[17]。他又认为, “未来将成为时间三元体的中心。”现时是三种时间的会合点,未来是三种时间的中心,这就说明,帕斯强调现时和未来的存在状态,并且不被过去的时间所淹没。而且,超越时间的时间,即具有统一性的理想时间,在对抗实用主义的时间。基于此,帕斯认为,“现代的时间是批判的时间”,因为“现代的本质恰恰是对永恒的批判”。而且这种批判“提供了一个双重意象:时间的尽头和它的重生,原型的过去的腐败及其复活”。[18]6F391035-CC3F-499D-A3D3-BDC9AF0B01DC
既看到时间的永恒,而又有对永恒的批判;既看到时间的尽头,而又想象到它的重生;既看到它的腐败,又听到它复活的声音。时间性的空间,依然充满了巨大的精神搏斗,跃动着生命创造的力量。正因为帕斯对时间的理解如此深邃阔远,他的灵魂时时在与宇宙对话,在超越时空中探寻人的本原,才写出了伟大诗篇《太阳石》。
“太阳石”是墨西哥城出土的石历,而在诗人的灵魂世界,它已经成为超越物的存在。它是一个象征,是一个超现实的时间幻象,是一种探寻宇宙奥秘的力量。在这个时间的幻象里,“太阳石”在诗人多维的时间性空间里,“将生与死、爱与恨、历史与现实、神话与梦幻、孤独与理解、拒绝与接受、追求与绝望融合在同一首诗的字里行间”。诗的多维的时间性的空间幻象,创造了神秘的宇宙幻境,造就了诗的美学魅力。因此,西班牙一位诗人发自内心深处地说:“我有三本《太阳石》,一本为了阅读,一本为了重读,一本将是我的随葬品。”一位墨西哥文学评论家这样评判这篇长詩,“只要西班牙语存在,它就是用这种语言创作的最伟大的诗篇之一。”[19]由于《太阳石》被世界文坛广泛关注,1990年帕斯也因此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如此赞扬帕斯的诗学理念和他获诺贝尔文学奖的长诗,并不是说诗人们都应该去如此创作,而是意在说明,时间的幻象的确在拓宽诗人的感觉和思维空间,意在说明时间性的空间是那样的丰富而深邃,它无所不包,它至大无边,它不仅丰富了诗人的精神世界,更是丰富了人类的精神生命的世界。我想,从这个视角理解闻一多先生说的诗学意义上的“宇宙意识”和冯友兰先生说的哲学意义上的“天地境界”,会更加丰富纯诗境界的理论和思想。
由此可知,纯诗的境界存在于两个世界里,一个是绵延性、弥漫性、渗透性的时间性空间。自从神话出现的时候,人类已经创立了时间性的空间,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它绵延着,丰富着,变幻着,创造着,让人类生存的世界不断扩展,让人类的精神生命的力量不断强化。但它随着人类的成熟和进步,逻辑思维也在不断地杀伤着形象思维,如果不是思想的勇士和幻象诗人们发现它保护它创造它,它几乎要被湮灭。他们以潜意识的感觉和思维保存在内心深处,这就是纯诗境界存在的另一个世界,即心灵空间。这两个空间世界的最佳存在状态,就是二者的无缝融合,即“太阳石”的时空结构存在状态。
这样融合的存在就是“场”的存在,不仅仅是物理学意义的场的存在,更是精神意蕴的场的存在。这个场,就是不断创新不断变幻不断生长的复合体的存在。按照雷丁博士的说法,是超越空间的存在,也是超越时间的存在,是超常现象的存在,是超自然现象的存在,也是神秘主义的存在。这样的存在是多维度的存在,我们日常看到的是一维线形、二维平面、三维立体的存在,而多维的存在则是更高的存在。可是,这种存在只是存在于物理学的计算中和人们的想象中,所以,现代物理学家爱因斯坦这样描述他对于所谓时间存在的认知:相信物理学的人都知道,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区别只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幻觉。根据现代物理学的义理而理解,这种幻觉的存在,有诸多能量的存在,这种能量就是活动的神秘力量。对于这种神秘的生命能量,现代物理学家能够感觉到,诗人也能感觉到,当然,诗人对这样的神秘力量的感觉,或者说对于这样的纯诗境界的感知和认知往往是直觉的,非算法的,甚至是梦幻的,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诗性的感觉。这种感觉表现在诗里,就是幻象的存在。这就再一次证明,诗学的幻象在心理学和哲学意义上是一种巨大的美学存在状态,它之所以成为纯诗的至高至大的境界,就是因为蕴含着诗人们追寻、发现和创造的神秘的诗学力量。
参考文献:
[1][2][5][6][美]卡普拉.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M].朱润生,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6:5;76,77,89,90;76,78,83,86,87,89;17.
[3]解志熙、王文金编校.于赓虞诗文辑存(下)[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581.
[4][7]冯友兰.新原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166,167;14.
[8][英]詹·乔·弗雷泽.金枝(上)[M].徐育新,汪培基,张泽石,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269.
[9][10][11][瑞士]荣格.荣格文集(第五卷)[M].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24,23;178;167,48,51,54.
[12]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一册(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23.
[13][瑞士]荣格.荣格文集(第七卷)[M].徐德林,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131.
[14]袁可嘉,董衡巽,郑克鲁,选编.外国现代派作品选.第二册(上)[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152.
[15][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7:523,430.
[16][18][墨西哥]帕斯.泥淖之子——现代诗歌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M].陈东飙,译.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8:24;42,35,18.
[17][墨西哥]帕斯.对现时的追寻——在诺贝尔奖授奖仪式上的演说[J].赵振江,译.北京:世界文学.1991(3).
[19]赵振江.燃烧的激情执着地求索——《太阳石》浅议.北京:世界文学[J].1991(3).6F391035-CC3F-499D-A3D3-BDC9AF0B01D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