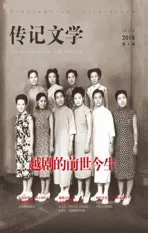茅盾致俞平伯的一封信:红学界关于曹雪芹卒年“大论战”的一个侧影
2018-04-20北塔
北 塔
中国现代文学馆

茅盾

俞平伯
1963年3月25日,茅盾给俞平伯写了一封信——
平伯先生:
廿三日手示敬悉。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年,例应标明某年至某年;因壬午、癸未两说相持不下,中央雅不要在此学术问题上遽作结论,故有于1763加(?)之拟议。兄谓应广征文教界同意,弟亦谓然。前日饭后谈及,不过透露有此一说,非正式也。至于影响国际观感,似亦未必;因世界各国颇有类似之事,大作家生年和卒年加(?),文学史上比比皆是。弟于曹氏身世,并无研究,壬午或癸未都无成见;但近日读双方驳难之文,私意谓壬午除夕之说固有明文,但既有异议,不妨倾听,求其深入,不宜遽作结论。癸未说之论据,“小诗代简”一证实不硬朗,倒是“四十年华付杳冥”之挽诗一证较为有力(因抄本此诗题下明注甲申)。鄙意亦正同尊论:原挽两首,此为改作;原两首写于初丧,此改作则在一年后,——假定为雪芹逝世周年之后数日。如此解释,本亦可通,但究属推想,如无旁证,不能杜反对者之口。且反对者亦可质问:既改作于周年祭,何以诗中完全看不出?如此循环质难,如无新材料,则仍为疑案。鄙见以为卒年问题非可多数取决了;因其为考证问题。强求一致,反伤团结。
大函论及近来研究《红楼梦》文章,颇伤繁琐支离。一部分文章确有此病。承嘱注意,甚为感佩。报告估计不过四千字左右,主要论点当在《红楼梦》之思想性与艺术成就,至于近年对曹氏身世考证,对《红楼梦》版本研究——此两方面之成绩,虽不能不提,然亦不打算多费笔墨。尊见以为如何?杂事甚多,一个月内恐尚无暇起草报告。初稿成后当印发广征意见。
匆复 顺颂
健康
雁冰三月廿五日上午
正如开头所说,此信是茅盾对俞平伯“廿三日手示的”回信,写于1963年。同年,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在北京举行,由文化部、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和故宫主办。作为文化部长兼作协主席,茅盾予以热情支持。在红学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俞平伯与茅盾曾为北京大学校友,两人之间有过较多交集与往来,两人在1963年3月的这番通信往来主要是讨论红学问题。
20世纪50年代,俞平伯因为《红楼梦》的相关研究而遭到毛泽东的点名批判。据相关文献所载,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亲自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其他有关同志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说:山东大学两个大学生李希凡和蓝翎写文批判俞平伯,那是30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的错误观点第一次认真的开火。
此后,全国各地随之闻风而动。俞平伯所在的单位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从1954年11月25日至12月27日,共召开了6次批判会。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从10月31日至次年2月8日,共召开8次批判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作协还召开联席会议,并组织了专题批判小组。这期间,俞平伯忙得晕头转向,哪里有批判,他就得到那里去接受批判!
这次批判风潮,不仅是针对如何评价和研究《红楼梦》的问题,而且要从各个方面对“五四”以后较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和批评。同年11月5日,《人民日报》登出了题为《肃清胡适的反动哲学遗毒——兼评俞平伯研究〈红楼梦〉错误观点和方法》一文,对俞平伯进行批判。
对此,俞平伯一开始持以抵触情绪。他虽然到处去配合参加对自己的批判活动,但始终不肯公开承认错误,使得批判一时难以为继,后来才逐渐转变态度。
1955年3月15日,《文艺报》半月刊第5期刊登了俞平伯的检讨:《坚决与反动的胡适思想划清界限——关于有关个人〈红楼梦〉研究的初步检讨》。检讨发表后,俞平伯也就从这场轰轰烈烈的大批判运动中淡出了。
有人说,俞平伯在遭受批判之后,就对红学讳莫如深,甚至不允许家人谈论《红楼梦》。如此看来,他主动给茅盾写信讨论红学,应是对这种误解的有力驳斥了。实际上,俞平伯对红学矢志不渝,哪怕是身处大批判的漩涡中心,他仍不放弃对《红楼梦》的研究,并出版了《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红楼梦》版本有两个系统,一是脂砚斋评本,80回;一是程伟元、高鹗续补本,120回。脂本评语非出自一人,其中以脂砚斋和畸笏叟的评语最为重要,它涉及作者曹雪芹生平身世、人物原型和写作修改等情况,向为研究者所重视。流传的脂评本不止一种,各本评语也参差互见。俞平伯将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本、乾隆己卯冬月脂砚斋四阅评本、乾隆庚辰秋脂砚斋四阅评本、乾隆甲辰本、有正书局石印本这5种评本的评语汇辑校订,于1954年出版《脂砚斋红楼梦辑评》。俞平伯辑评本中所据的甲戌本系过录本,庚辰本为照片。1959年他重订此书时,用已影印的庚辰本补正有关条文,修订后于1960年作为新一版印行。1962年又据当时影印的甲戌本订补讹漏,印行新二版。正是因为俞平伯始终没有停止对《红楼梦》的研究,所以哪怕是在书信中,他对红学的探讨都是深入细致的,从他与茅盾的这次通信中所探讨的问题便可窥一斑。

俞平伯辑《脂砚斋红楼梦辑评》
两人在通信中所讨论的主要是曹雪芹卒年的问题。1963年3月22日,两人见面时谈起纪念曹雪芹逝世二百年之事。从他们通信的语气中推测,大概是茅盾向俞平伯透露纪念展览会及配套宣传材料上,将在曹雪芹卒年1763年的后面加一问号,表示学术界对此年份尚存争议,而俞平伯对此举予以反对。
俞平伯反对的首要理由是:曹雪芹去世距今不过两百年,中国学术界就搞不清楚他的卒年了,这会影响中国学术的国际形象。他在给茅盾的信中说:“鄙意纪念近世(十八世纪后半)之艺术大师,而对他的卒年尚搞不清楚,留下疑问,于国际观感影响均不甚好。”茅盾对此的答复是:“至于影响国际观感,似亦未必;因世界各国颇有类似之事,大作家生年和卒年加(?),文学史上比比皆是。”
俞平伯予以反对的第二个理由是:曹雪芹卒年1763年是板上钉钉的,不必加问号。他在给茅盾的信中说:“壬午说、癸未说虽差了一年,却同为一七六三;因此即使并存误说,而一七六三已包含在内,自不须加问号。只有癸未除夕方为一七六四,而此说从《懋斋诗钞》(即使它正确编年)并看不出来,乃摘取甲戌本脂批‘壬午除夕’之‘除夕’二字与含问题颇多之《懋斋诗钞》与癸未说捏合而成者,以弟妄评,诚为穿凿附会……”
关于曹公卒年,红学界主要有三种说法:“甲申说”“壬午说”“癸未说”,尤其以后两者为最主要。“甲申说”与“壬午说”皆由胡适首倡。
胡适于1922年首揭“甲申说”,继之者有梅节、徐恭时、蔡义江等。其所根据的是《四松堂集》付刻底本中敦诚的《挽曹雪芹》一诗,诗云:“四十年华付杳冥,哀旌一片阿谁铭?孤儿渺漠魂应逐(前数月伊子殇,因感伤成疾),新妇飘零目岂瞑?”由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明确标为“甲申”(此二字就在诗作的下面,以白纸贴盖),所以胡适下判断说“曹雪芹死在乾隆二十九年甲申(年)”。

爱新觉罗敦诚撰《懋斋诗钞》《四松堂集》
“壬午说”认为曹公卒于乾隆二十七年即壬午年除夕,阳历为1763年2月12日,由胡适于1927年首倡。大多数红学家支持该说,代表人物有俞平伯、王佩璋、周绍良、陈毓罴、邓允建、冯其庸等。其中俞平伯为胡适弟子,王佩璋(即王惜时)为俞平伯的学生。弟子虽有为导师辩护的动机,但并不像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1976年的增订版中所指责的那样,王佩璋是在配合其师故意向他发难而持“壬午说”。
“癸未说”则认为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八年即癸未年除夕,即阳历1764年2月1日,由周汝昌于1947年首倡。主要代表人物有曾次亮、吴恩裕、吴世昌、郭沫若等。
关于曹雪芹卒年的问题,从1947年开始,学界断断续续地一直争论不休。到了1962年,随着二百周年纪念活动的临近,这种争论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自3月起,为确定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的具体纪念日期,红学界展开了一场关于曹雪芹卒年的“大会战”。茅盾与俞平伯的通信便是这场论争的一个侧影。

“曹雪芹逝世二百周年纪念展览会简要说明”
其实,俞平伯对“壬午说”也曾持以怀疑,这点跟胡适一样,有过自我怀疑和否定阶段,当然后来就肯定此说了。胡适曾于1927年购得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卷一正文开始时有一条脂砚斋批语:“壬午除夕,书未成,芹为泪尽而逝。”胡适在购书后第二年(1928)2月,据此写出了《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见《胡适文存》三集卷五),推断曹雪芹卒于乾隆二十七年(1763)。20年后,周汝昌写了一篇《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发表在1947年12月5日天津《民国日报》副刊“图书”上,周文认为“曹雪芹确是卒于癸未年的除夕,即公元1764年2月1日”。这篇文章被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看到,于1948年1月18日给周汝昌写信,简要表达了他个人的看法:“先生推测雪芹大概死在癸未除夕,我很同意。”俞平伯在1948年6月11日回复《民国日报》副刊“图书”编者的信中也曾承认,周汝昌“推定雪芹卒于乾隆癸未”,“甚为的确”。
不过,从1953年下半年开始,俞平伯在《〈红楼梦〉简论》《读〈红楼梦〉随笔》中否定了“癸未说”,转而支持“壬午说”。1954年3月1日,他在《光明日报》副刊“文学遗产”第1期刊出《曹雪芹的卒年》一文,写道:“我认为曹雪芹死于乾隆壬午除夕,即一七六三年的二月十二日。”自此始,俞平伯便坚持认为曹雪芹卒于“壬午说”。
那么,俞平伯为何在怀疑之后又重新肯定了“壬午说”呢?
从茅盾信中所说的“癸未说之论据,‘小诗代简’一证实不硬朗”一句话中,或可觅得一二答案。
“小诗代简”即《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作者是敦敏(敦诚之兄弟),诗见于后者所著的《懋斋诗钞》:“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巳前三日,相劳醉碧茵。”这是一首五律,内容是敦敏邀请曹雪芹于“上巳前三日”到住处观花饮酒,功类请帖。
周汝昌认为,这首诗作于癸未年(乾隆二十八年),因为“若雪芹真在二十七年除夕死了,敦敏如何还能在二十八年上巳(农历三月三日)前三天约他去赏花饮酒?再看这本诗集排到乾隆二十九年甲申春,敦敏才有《河干集饮题壁兼吊雪芹》一诗。再把这一点与敦诚《四松堂集》的《挽曹雪芹》诗,下面注明‘甲申’而且是甲申开年的第一首诗这个事实合起来看,则可推断,雪芹本系癸未除夕死去的,次年敦敏兄弟才挽吊他”。后又补充说,敦敏的这首“代简”诗是邀请曹雪芹来给敦诚过生日,因为“癸未年的‘上巳前三日’,正是敦诚的三十岁整寿。癸未除夕雪芹死。甲申年初敦诚作挽雪芹诗”。
周汝昌又是如何认定《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这首诗写于癸未年的呢?他在《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一文中并没有全面明确的交待。直到1953年9月,《红楼梦新证》出版时,周汝昌才在其中加以说明:“按此诗前三首题下注:‘癸未。’……故知为本年所作无疑。”对此,俞平伯在《曹雪芹的卒年》一文中驳道:“我认为曹雪芹死于乾隆壬午除夕,即一七六三年的二月十二日。”“周君所据前三首虽题癸未,但《小诗代简寄曹雪芹》这一首并未题癸未,安知不是壬午年的诗错编在这里呢?《懋斋诗钞》的编次虽大致依年份,但有时不很精确也是常事。与其把脂评明明白白的话认为误记一年,似不如将本无题署年月的诗认为误编在次年,较为合理。”俞平伯认为《懋斋诗钞》中的作品并非严格按照创作时间的先后编次,《古刹小憩》虽标注作于“癸未”,亦不能证明在它之后的第三首即《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也一定写于这一年。
1961年,胡适也回归“壬午说”,他在《跋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影印本》中写道:“我曾接受汝昌的修正。但近年那本《懋斋诗钞》影印出来了,我看那残本里的诗,不像是严格依年月编次的;况且那首“代简”止是约雪芹‘上巳前三日’(三月初一)来喝酒的诗,很可能那时敦敏兄弟都还不知道雪芹已死了近两个月了。所以我现在回到甲戌本的记载,主张雪芹死在‘壬午除夕’。”
以上便是茅盾复俞平伯的信中所说“‘小诗代简’一证实不硬朗”一句的背景资料,也由此可知,茅盾对曹雪芹卒于“壬午说”并没有俞平伯和胡适那般肯定。
而如上述,俞平伯、胡适与周汝昌争论的焦点在于《小诗代简寄曹雪芹》到底是否作于癸未年,就像王佩璋所说:“主要关键就在于《懋斋诗钞》上这首《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了。……要知道这诗是否作于癸未,就需要查明《懋斋诗钞》是否‘诗是按年编的,有条不紊’。”双方似乎都认可一个推论前提,即假如《懋斋诗钞》是严格依年月编次的,那么就能证明它作于癸未年。

周汝昌曾在《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一文中,“断定这些诗是以作成先后而编排的,并没有错乱。”而王佩璋上面的研究成果发表后,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中,又再度强调指出:“我初次得见的《懋斋诗钞》,是个清钞本,年月次序,清楚明白,诗是编年顺录的”,“迨后我又见到了原底稿本——圈选以备付刻的底本,事情更清楚了。底稿本是随作诗顺序陆续抄上去的,本来就是按年照月,连‘编’都用不着的。这更不会错。”言辞中不无自我辩护的意味。
显然,周汝昌对王佩璋等人的观点并不认同。他在《红楼梦新证》中反驳道:“这个底本因付刊前要删割有避忌的诗,遗有空白处,后来收藏者‘燕野顽民’得到此本,见有脱粘等处,怕有零落,因此略为粘缀修整,并为此写下识语。未想这却引起有些研究者的误会,说诗集的编序不可靠了,被他搞乱了。其实全非如此。一些研究者作了些论证,想证明此本并非编年的,但都难成立。”
的确,王佩璋的辩驳乍看言之凿凿,却也有为辩驳而辩驳的意味,仔细读来,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一)版本上的各说各话。周汝昌初次得见的《懋斋诗钞》是个清钞本,原藏燕京大学图书馆,现存哈佛大学;而王佩璋依据的是1954年夏吴恩裕先生在《八旗艺文编目》著者恩华家里发现的手稿本的影印本,与周汝昌所据的根本不是一个版本。
清钞本与手稿本差别如何?清钞本里面的诗到底是周汝昌所说的“编年顺录的”?还是像王佩璋所说的“时序颠倒紊乱”?两人各执一辞,并无定论。据说,20世纪70年代,赵冈与余英时均在美看到了哈佛藏的《懋斋诗钞》清抄本,赵冈比对国图本与哈佛本后,据此理出了《懋斋诗钞》流传的大致经过,认为“从这几个当事人的关系看来,后者是直接从前者过录而得”;余英时进行比对后,根据两本的异文则得出“清抄本的祖本比影印本要早”的看法。但遗憾的是,两人对诗抄的编次均没有予以关注(张胜利:《王佩璋对曹雪芹卒年的考证及影响》,见《红楼梦学刊》2014年第4辑)。关于清钞本的编次时序问题,迄今仍无定论。
(二)逻辑上的混乱。即便《懋斋诗钞》的编次真如俞平伯、王佩璋所言,是“颠倒紊乱”的,也并不能就此推断《小诗代简寄曹雪芹》一定不是作于癸未年,更不能断定它作于壬午年。对此,王佩璋倒不像乃师那样坚决肯定(不是癸未年,就是壬午年),她推测《小诗代简》的写作年代“虽不作于癸未,也不必一定作于壬午,可能作于壬午以前如己卯、庚辰、辛巳等年”。
另外,也有论者指出,《小诗代简》的写作年代与曹雪芹卒年其实没有必然的关系,“在《红楼梦》作者生卒年的研究史中,《懋斋诗钞》的编年问题只是考证卒年的重要依据之一,并非全部证据;即使确认了《小诗代简》的写作年代,也并不能据此确定曹雪芹的卒年时间”。
(三)先入之见的偏颇。王佩璋在她的研究文章中一方面说“这首诗虽不作于癸未,也不必一定作于壬午”,另一方面却又说“曹雪芹的卒年还是以卒于壬午之说较为可信”。这明显是矛盾的,许是受其师俞平伯的影响,而被先入之见框住了思维。
茅盾在给俞平伯的复信中说,于曹雪芹的卒年1763后加(?),是上层的考虑,因“壬午、癸未两说相持不下”,“中央雅不要在此学术问题上遽作结论”。对于俞平伯所提出的“应广征文教界同意”,茅盾又委婉周全地表明自己的意见:“卒年问题非可多数取决了;因其为考证问题。强求一致,反伤团结。”关于曹雪芹的卒年问题应持存疑的看法,茅盾虽对俞平伯解释说是官方的旨意,但从复信中明显可见也是他自己的态度,当然,茅盾的顾虑也不无道理。而从两人的这番通信往来中,可窥当年红学界关于曹雪芹卒年“大论战”之一斑。

茅盾(左一)、俞平伯(左三)在《红楼梦学刊》组织的红楼梦研究工作者座谈会上(1979年秋)
《红楼梦》中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描写比比皆是,甚至到了琐屑的程度,但这并非《红楼梦》的最伟大处,《红楼梦》之非凡在于对世事人生的形而上探索和概括。对于有的研究者沉迷于作家的生活小节或者作品个别章句的品咂赏味,皓首穷经进行研究考证,而忽视这部经典之作整体的文学性与哲学意义,俞平伯和茅盾都是反感的。
俞平伯在信中说:“近来报刊发表关于《红楼梦》的文章,颇伤繁琐,支离。”他说自己“近年考证《红楼梦》的改从作者的生平家世等等客观方面来研究,自比以前所谓‘红学’着实得多,无奈又犯了一点过于拘滞的毛病,我从前也犯过的”。俞平伯虽然精于考证但又不囿于考证,他认为小说与历史固然有关系,但小说绝对不等于历史。比如,在《大观园地点问题》一文中,他曾考证大观园的大小和位置,最后却感慨道:“反正大观园在当时事实上确有过一个影儿,我们可以这样说。作者把这一点点的影踪,扩大了多少倍,用笔墨渲染,幻出一个天上人间的蜃楼乐园来。这是文学上可有应有的手腕。它却不曾预备后人来做考证的呵。”
对于文学作品,当然可以从史学的视角去解读,但更应该从美学的角度去欣赏、哲学的高度去概括。俞平伯说:“我们应该用历史的观点还它的庐山真面,进一步用进步的文艺理论来分析批判它。”他看重从人生哲学和修辞美学的角度,去探讨《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比如,他用佛教的“色空”观总括《红楼梦》的思想主旨:“余以‘色空’之说为世人所诃旧矣。虽然,此十六字固未必综括全书,而在思想上仍是点睛之笔。”“此十六字”指的是《红楼梦》读者所熟悉的“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入色,自色悟空”。
相较而言,茅盾在《红楼梦》上没做过类似的考证工作,所以他在信中所说“弟于曹氏身世,并无研究”,并非谦辞。跟俞平伯一样,他最大的兴趣在于《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因此,他说他即将代表主办方,在这次纪念活动上所作的主题报告“估计不过四千字左右,主要论点当在《红楼梦》之思想性与艺术成就,至于近年对曹氏身世考证,对《红楼梦》版本研究——此两方面之成绩,虽不能不提,然亦不打算多费笔墨”。茅盾的这个报告题为《关于曹雪芹》,后载于《文艺报》1963年第12期,文中对曹雪芹的家世、生平、思想和创作,尤其是对《红楼梦》的思想和艺术成就均有精辟而丰富的分析和评价。
综上可见,茅盾与俞平伯在关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卒年这一细节问题上的观点虽存在分歧,但他们都认为,文学研究,包括《红楼梦》研究,其总目的应该是挖掘其思想,彰显其艺术;考证工作不是不可以做,但考证工作应该“配合着这总目的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