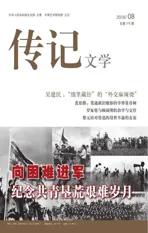张恨水传 选章二
2016-09-12解玺璋
文 解玺璋
张恨水传 选章二
文 解玺璋

漂泊
转过年来,就是民国元年。这一年,张恨水十七岁了。父亲便谋划着要送他到日本去留学,而他本人却希望到英国去,“我并没有考虑到我还没有念过两册英文哩”, 他说。但是,就在这年的秋天,家里发生了一场变故,从此改变了他的人生。父亲因一场急病突然故去,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就被切断了。那时,母亲只有三十六岁,带着他们六个孩子——他与三个弟弟、两个妹妹,最小的妹妹张其伟只有两岁,日子过得实在凄惶。父亲曾是全家的依靠,父亲不在了,生活也就没有着落了。于是,母亲只好带着孩子们离开南昌,回到潜山老家。她手上没有任何积蓄,就靠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度日。所得有限,自然没有能力供儿子在城里读书。于是,张恨水便离开了甲种农业学校,出国留学的希望自然就完全破灭了。
父亲之死已使他悲痛欲绝,中途辍学更让他惶恐不安,而乡下的生活又是单调乏味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这样在家中待了半年。烦闷之中,只能看看旧书,或是在乡野间各处走走。一个半大小子,整天无所事事,是让众乡邻耻笑的,但他除了读书的确找不到事做。他还记得,那时,家中有一间书房,窗外是一株桂花树,他常常在弥漫着桂花香气的窗前读书自娱。乡邻因此送了他一个外号,叫他“大书箱”,意思是笑他只知念书,不务生计。后来他曾夫子自道:“我那时真是终日吟诗,很少过问身外之事。” 如果他是个富家子弟,或生在官宦人家,也还罢了,偏偏他的家庭此时绝不能供养一个只懂得闲情逸致的才子。但他还是颇有些自负的。他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务农自然不在他的眼界之内,即使是乡间的那些秀才贡生,他也不怎么看得起,总觉得他们有点“迂”,而才子应该是旷达的。这就使得他在乡下的生活有了一点“孤寂”的意味,才子本是多愁善感的,这样的处境倒是让他体会到不少诗人的逸兴。
春天来了,张恨水不想总窝在家里,他要出去寻找机会。这时,他的堂兄张东野从上海写了信来,邀他到上海,答应为他想办法,找出路。张东野比张恨水大六岁,是祖父张开甲的长孙,早年曾随祖父在江西南昌读书,后考入江西讲武堂,与张恨水进入新闻界的引路人郝耕仁同窗,并一起加入同盟会。毕业后,他在上海警察局谋了个闸北区公所小队长的职位,辛亥年,参加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在攻打制造局的战斗中立了功,升任宪兵大队长。不久,当他听说堂弟张恨水因叔父病逝而困在老家时,马上向他伸出了援手。
于是,民国二年(1913)春天,张恨水就到上海来了。这是他第一次来到上海这个现代大都市。那时,他身无分文,食宿都没着落,就和张东野一起住在警察局内,埋头读书,准备考学。过了些日子,张东野打听到苏州有一家蒙藏垦殖学校正在招生,就建议他去报考。学校据说是孙中山办的,校长是陈其美,多年后张恨水还记得:“我因这学校与农业相近,就前去投考。考得很容易,除了一篇国文,只有两道代数,几个理化题目。榜发,我录取了。我对此事,高兴得不得了。因为我中学没毕业,我又跳进专门了。亲友们帮忙,凑些款,让我缴了学膳费,我就到苏州去读书。”
垦殖学校当时就设在苏州阊门外留园隔壁盛宣怀的家祠里。苏州是一座秀美的古城,与繁华喧闹的上海迥然不同,显得古朴、谧静、清幽、典雅,有一种古色古香的味道。学校所在的留园,更是一座巧夺天工的江南园林。张恨水打心里喜欢这里的读书环境,认为是“生平最好的待遇”,他说,“房子又大又好,我宿舍窗外,就是花木扶疏的花园。隔壁留园的竹林,在游廊的白粉墙上,伸出绿影子来看人”。1946年5月5日,时隔三十三年,他在《南京人报》副刊《南华经》发表《红楼一角旧书斋:二十年尘梦之三》一文,描述他心中的“圣地”尤为详尽:
予曾读书苏州学校,为盛氏之往宅,与留园盖一墙之隔。其理化讲堂,即留园之一角,划入校中者也,教室上为西式红楼,下为精室,小苑三面粉墙,一处掩以雕栏,两处护以垂柳。廊外首植绿乔四株;其次为寒梨碧桃,交互而生;其三为垂丝海棠六本,更杂以紫薇;最末则葡萄一架,梅花围于四周。雕栏下有古井一,夭桃两树覆于上,夭桃之上,则为翠竹一排,盖隔墙之竹林也。相传此处为杏卍寝室,故其外之花木,罗列至于四季。予住校时,即卜居于此,花晨月夕,小立闲吟,俱感清趣。湖海十年,豪气全消,而一念及此,犹犹然神往。数年前乘沪宁车经过苏州,每见桑林之上,红楼一阁,恍然如东坡老遇春梦婆。近来每走京沪路,犹注意及此。则沧桑再变,红楼一角,且不能见。真古人所谓“事如春梦了无痕”矣。
如果不是这个地方真的让他动心,很难想像隔了这么久,他还能记得这么清楚;同时也说明,他具有超强的观察能力,而这是一个好的作家、小说家必备的素养。那时,他是个家境贫寒的学生,囊中羞涩的窘迫一直困扰着他,有时连买纸笔的钱都没有。他常常想起亡故的父亲,又惦记着操持一家生计的母亲和几个年幼的弟妹。他是长子,父亲临终前曾将家庭这付担子转交给他,他也做过郑重的承诺。因此,他很想早一点为母亲分担养家的重负。但这时他几乎看不到任何出路,前途竟是那样的渺茫。至少,他“实在还没有幻想到吃小说饭”,而一心一意要做的“依然是个科学信徒”, 只是还不能确定,这个“科学信徒”能否让他很快赚到钱,以减轻年轻守寡的母亲的负担。
于是,课余之时,这个敏感而又内心丰富的青年,常常就拿了书本依靠在红楼的栏杆旁发呆——倚栏杆兮涕沾襟,这真是个绝妙的意象,在诗词小说中,穷愁落魄的才子很少不将情思寄托于这根“栏杆”的,“栏杆”激发了他们郁结在心中的思绪,这些无从发泄的愁苦,便借了诗句得以抒发,“有时也填一两阙小令,词句无非是泪呀血呀穷病呀而已”。还是在南昌的时候,那位曾教过他八股和试律诗的储先生,就夸他有诗才,鼓励他作诗。这些年,他自己也很钻研近体诗,读了《随园诗话》《白香词谱》《全唐诗合解》一类的书,为此还结交了两个诗友,楼下花园便是他们抒发诗情的地方,有了兴致,就题几句诗。
不过,吟诗填词毕竟不能当饭吃,穷困像一座大山,横在他的面前,逼得他不得不去想办法,找出路。因为从小喜欢读小说,十三岁那年,他还试着写过一篇小说,主人公是个十三四岁的男孩儿,力大无比,使两把铜锤,在庄前打死一只猛虎。他把这个故事讲给弟弟妹妹们听,没想到竟能博得他们的赞许,他也因此受到了鼓舞。如今既在困境之中,他便想到写小说,也许能给他一些机会。他从《小说月报》刊登的征稿启事中发现,小说的稿费是每千字三元。这个数字对一个穷困潦倒的学生来说,诱惑是很大的,很能刺激他的写作欲望。“我很大胆的,要由这里试一试。”当时,学校里正闹学潮,不用上课,他于是有了作小说的机会。学校的理化讲堂是一幢小洋楼,楼下是花圃,隔壁就是有名的留园,风景绝佳,他便躲在小楼里作起小说来。“我一个人坐在玻璃窗下,低头猛写。偶然抬头,看到窗外竹木依依,远远送来一阵花香,好像象征了我的前途乐观,我就更兴奋地写。”
三天时间,他试着写了两个短篇小说,一篇是文言的《旧新娘》,约莫有三千字;一篇是《桃花劫》,用了白话,大约有四千字。前者写一对青年男女的婚姻史,是喜剧;后者写一个孀妇的自杀,是悲剧。这是张恨水在小说创作道路上跨出的第一步,如今,小说已湮灭无闻,我们无从了解他都写了些什么,但就题材而言,他的趣味与风行一时的言情小说还是有关系的。小说写好后,他便悄悄寄给了商务印书馆的《小说月报》编辑部。原本是不抱有幻想的,可是,“事有出于意外,四五天后,一个商务印书馆的信封,放在我寝室的桌上。我料着是退稿,悄悄地将它拆开。奇怪,里面没有稿子,是编者恽铁樵先生的回信。信上说,稿子很好,意思尤可钦佩,容缓选载”。既然是“意思尤可钦佩”,我们猜想,张恨水的这两篇小说,或有不同于流行的“哀情”“艳情”之处,因而得到了恽铁樵的肯定。他那时已经看到了言情小说千篇一律的病根,认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进而提出了“社会言情小说”的概念,并指出:“社会大事,无过于婚嫁生死,而言情小说,实包此四者。”又说:“言情不能不言社会,是言情亦可谓为社会。”恽铁樵既有此认识,那么很显然,他从张恨水的小说发现的“尤可钦佩”的“意思”,很可能就是他所期待的言情小说的社会内容。既如此,我们是不是可以说,张恨水的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与“鸳鸯蝴蝶”不同而多了社会这个维度。
得到恽铁樵的回信,张恨水大喜过望,因为他看到,自己的能力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他“居然可以在大杂志上写稿”了,对他来说,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他终于忍不住发自内心的欢喜,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要好的同学。但是,他等了“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直等恽先生交出《小说月报》给沈雁冰先生的那一年,共是十个年头”, 那两篇小说也未能露面。尽管如此,张恨水仍然受到很大鼓舞,后来他“吃小说饭”,不能说和这封信一点关系没有。
这年夏天,民国以来不断积累的国民党与袁世凯的矛盾终于爆发,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发动二次革命。十八日,陈其美宣布上海独立,通电讨袁,但未满一月即宣告失败,二次革命也随着重庆讨袁军的战败而告终。由于垦殖学校是孙中山创办的,并以陈其美为校长,自然也就成了讨袁军的一支力量,学校把写了“讨袁军”字样的旗子也挂起来了。可是,没有几天,各地“讨袁”的势力就垮台了,领导“讨袁”的大人物纷纷逃亡海外,学校也就跟着解散了。这样一来,张恨水再次失学,当冬天到来的时候,他黯然回到了老家,再做打算。然而,还是一筹莫展,他讲到那时的情形:“找职业,我太年轻,也无援引。务农,我没有力气,这也不是中途可以插班的。那么,就在家里呆着吧。好在家里还有些旧书,老屋子空闲的又多。于是打扫了一间屋子,终日闷坐在那屋子里看线装书。”
这间屋子在张恨水成名之后成了张家后生晚辈们借以自励的“圣地”,人们将它命名为“老书房”,张恨水就是在这里自修自写,奠定了毕生的职业。他记忆中的“老书房”不过是一间黄土书屋:“这屋子四面是黄土砖墙,一部分糊过石灰,也多以剥落了。南面是个大直格子窗户。大部分将纸糊了,把祖父轿子上遗留下来的玻璃,正中嵌上一块,放进光亮。窗外是个小院子,满地青苔,墙上长些隐花植物瓦松,象征了屋子的年岁。而值得大书一笔的,就是这院子里,有一株老桂树。终年院子里绿阴阴的,颇足以点缀文思。这屋子里共有四五书箱书,除了经史子集各占若干卷,也有些科学书。我拥有一张赣州的广漆桌子,每日二十四小时,总有一半时间在窗下坐着。”
按照当时乡下人的价值观,衡量一个青年是否有出息,只有两条标准,或者做官,或者发财。用这样的眼光看张恨水,自然觉得他“一事无成”。也有乡邻用“仕途经济”一类的话劝导他,他当然听不进去,因为,他既“中了才子佳人的毒,而又自负是革命青年”, 正做着别一种梦。不过,他毕竟形单影只,抵挡不了众议的汹汹而起。逃避的唯一办法,就是躲在黄土屋中写作。“在我书桌上,有好几个稿本,一本是诗集,一本是词集,还有若干本,却是我新写的长篇小说《青衫泪》。”这是一部“苦闷的叙述和幻想的故事”, 书是用白话章回体写的,中间又夹杂了不少诗词小品,体裁则模仿《花月痕》的套路,至于小说的内容,主要“谈青年失学失业的苦闷,一托之于吟风弄月,并不谈冶游”。不过,这部小说并没有最后完成,只写了十七回,就被他自己放弃了。
当又一个春天来临的时候,不肯困居乡间的张心远,再次离开家乡,来到南昌。当时,他身上只有四五元钱,家里也很难给他太多的资助,于是,通过向亲友挪借,凑了些钱,进了一所补习英语、算术的学校,目的还是想考大学。父亲在世时,曾在南昌置了些房产,所收房租还够他支付补习学校接下来的学费。不久,家里的生活也无以为继,不得已,母亲就把南昌的这所房子卖了,得了八九百元钱,都由母亲收着,做家常度日之用,他也不忍去要。但借贷总不是长久之计,这样,大约半年之后,经济来源一断,他的学业也就终止了。到了这一年的秋天,听说有个本家叔祖张犀草在武汉的一家报馆里当编辑,他就带了一包读书笔记和小说,借了一笔川资,跑到汉口去投奔这位年龄并不比他大很多的叔祖,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条出路。
对于张恨水的到来,张犀草倒是很欢迎,他安排张恨水住在一家杂货店楼上。张恨水把自己的诗作拿给他看,得到了他的赞许。张恨水便根据他的建议,把诗稿投给几家报馆,居然有诗作发表了。每天也写些小稿在叔祖编辑的报纸上补白,虽然都不给稿费,但稿子有人看,诗也有人说好,“却也聊以快意”。“恨水”这个笔名就是这时问世的。自从有了“恨水”这个名字,原名“心远”倒慢慢地少有人提起了,人们只知有张恨水,不知有张心远。由于“恨水”这个名字曾引起人们的种种猜测,张恨水为此还作了特别的说明:
本来在垦殖学校作诗的时候,我用了个奇怪的笔名,叫“愁花恨水生”。后来我读李后主的词,有“自是人生常恨水常东”之句,我就断章取义,只用了“恨水”两个字。当年在汉口小报上写稿子,就是这样署名的。用惯了,人家要我写东西,一定就得署名“恨水”。我的本名,反而因此湮没了。名字本来是人一个记号,我也就听其自然。直到现在,许多人对我的笔名,有种种的猜测,尤其是根据《红楼梦》,女人是水做的一说,揣测的最多,其实满不是那回事。
在汉口一住几个月,除了给报纸补白,并没有其他事情可做,恰好他的族兄张东野随“文明进化团”到汉口演出,就介绍他进了文明进化团。张东野现在已经有了艺名叫张颠颠,团里还有两位主要演员,一位是演生角的李君磐,一位是演旦角的陈大悲。他们二位都是中国话剧早期历史的开创者,李君磐曾创办开明剧社,刘半农在他那里做过编剧,他还是鸳鸯蝴蝶派的圈内人;陈大悲早年加入春柳社,后加入进化团,他还是“爱美戏剧”最早的倡导者,曾写过一部《爱美的戏剧》,对当时的新剧运动影响很大。他们对于张恨水这个年轻人,多少有那么一点怜惜,“主持人李君磐先生,他倒不一定要我演戏,帮着弄点宣传品,写写说明书,也就让我在团里吃碗闲饭”。于是,他就跟随文明进化团到了湖南,先在常德,后来又到沣县,巡回演出。时间久了,浸润其中,他也跃跃欲试,完全没有料到,“我居然可以登台票几回小生,我还演过《卖油郎独占花魁》的主角”。在另一个场合,他提供了剧团生活的更多细节:“头一场演《落花梦》,派我一个生角,是个半重要的角色,大家认为我演的还不错,就是说话太快了一点,派戏人说,演演就好了,我听了也很高兴。初步定了我三十元的月薪,李君磐和陈大悲也不过百多元。不过薪金是有名无实的,我从没拿过三十元,十元也没拿过,但是伙食很好。”

民国时期的汉口
看上去,张恨水在剧团里过得还不错,一张说明书不过三五百字,对他来说简直轻而易举,“我的工作不忙,有时就约朋友出城去玩”。这期间,他还随团到津市、澧县跑码头演出,生意不错。民国四年(1915)六月,剧团要到上海参加演出,他又随着大家到了上海。“这时,有几个同乡的文字朋友,住在法租界,我就住在他们一处。”同住的朋友当中,有一位就是郝耕仁。他是安徽怀宁人氏,与恨水堂兄张东野为江西讲武堂同窗好友,毕业后都被派往上海警察局任职。当初,张恨水到上海投奔堂兄时,他们或许就已经见过。他比张恨水年长十岁,是前清一个秀才,写得一笔好字,能诗能文,尤以古文见长,曾经还是同盟会员。他看张恨水年纪轻轻,跟着张东野一路瞎跑瞎混,毕竟不是办法,就劝张恨水,凭着自己的这番笔墨,到内地去找个编辑的工作。但一时间却找不到机会,他也只能继续跟着李君磐的剧社四处演戏,但收入甚微,果腹之外,竟无钱置办冬装,他说:“那时的穷法,我不能形容,记得十月里,还没有穿夹袍子。其间我又害了一场病,脱了短夹袄,押点钱买中药吃。病好了,上海我就再也住不下去了。”于是,他就借了路费回了安徽老家。
跟着剧团跑码头演戏的经历,给了张恨水很深的刺激,返回乡下后,他下决心不再流浪。不过,在家里依然无事可做,只有拿写小说来解闷。两个月内,他写了两个中篇,一篇是《未婚妻》,另一篇是《紫玉成烟》,都是文言。这在当时恰恰是一种时髦,虽然梁启超在十几年前就主张用白话写小说,陈独秀、胡适等人也在大力提倡白话文,但民国最初几年,社会上流行的还是用文言写小说,一时竟成为风尚。有学者研究认为,林纾(琴南)译作的风行和影响,是其首要原因。包天笑在回忆录中就曾讲到林译对时风的影响:“这时候写小说,以文言为尚,尤其是译文,那个风气,可算是林琴翁开的。林翁深于史汉,出笔高古而又风华,大家以为很好,靡然从风的学他的笔调。” 作为文学青年的张恨水,对于文学时尚自然是很敏感的,而且,他对林译小说也并不陌生,读过不少,尤为喜欢其中的心理描写,认为是中国小说所缺少的,再加上他的古文修养,也许会以为,用文言写小说比用白话更便捷,更得心应手。对他来说,这固然是一种习惯,而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却是不易体会的。
民国五年(1916)五月,堂兄张东野、叔公张授书在上海吃了官司,族人因张恨水常在外面走动,有见识,便推举他到上海,设法营救。一到上海,张恨水马上去找郝耕仁帮忙。但这件事却有些棘手。关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我们所能看到的材料很有限。据1991年续修《张氏宗谱·东野公传》记载:“1915年与叔公张授书刺杀袁氏密使未遂,在上海被捕,关押五年,授书牢死。” 至于他们的行为纯属个人意愿,还是接受过哪个组织的指令,我们亦不得而知,所能知道的只有,张东野早年曾加入同盟会,参与了陈其美领导的上海起义,在攻打制造局时立过功,被委任为宪兵大队长。“二次革命”中,陈其美沪军都督一职被袁世凯解除,张东野亦离开上海,加入李君磐的文明剧团,化名“颠颠”,暗地里从事反袁活动。1915年,与叔公密谋暗杀袁密使,不幸所用炸弹意外爆炸失火,二人先后被英租界警察抓捕。袁政府曾对二人提出过引渡要求,但被英国政府拒绝了。他们被关押五年,此后,张东野被释放,张授书却因伤病,惨死狱中。张恨水说,张授书是他的患难之交。张授书的遭际给了他很大触动,经过很多年,他还常常想起这位小叔公。民国十五年(1926),张授书死难七周年,七月七日这天,他想起有一年的七夕之夜,他们同客金陵,乘兴在江边散步,“见银汉横江,繁星照水,各有所感。楚萍(授书之笔名)谓今夕不可无诗,尔先咏之”,于是,张恨水就先吟了一首:
一度经年已觉稀,参横月落想依依。
江头有个凭栏客,七度今宵尚未归。
七年之后,又逢七夕,张恨水怀念故人,便把这首诗发表在他主编的《世界晚报》副刊《夜光》上,并加了一段“跋语”:“楚萍因闺中无画眉之妇,故流落在外,且七年矣。读予诗,以为不谅而规戒之,凄惨不复能语。今吾友亦死七年矣,一忆此事,终日不欢也。婚姻不自由,诚杀人之道哉!”
在张恨水看来,张授书的不幸,根源于他的婚姻,由于对婚姻不满意,故漂流湖海,不常家居,而寓沪既久,与民党游,渐渐从事革命,最终走上这条不归路。张恨水的营救固然没有成功,就在此时,陈其美在上海法租界萨坡赛路十四号日本侨民山田纯三郎的寓所亦被袁世凯的刺客枪杀,张恨水跟随郝耕仁参加了收殓其尸的工作。他既在上海无事可做,便一个人去了苏州。在这里,他又一次遇到了李君磐,应李之邀,他二次加入文明剧团,在苏州一带演出。这时,剧团中人均为一时才俊,有黄秋士、徐卓呆、刘半农、郑逸梅等,张恨水负责撰写剧本和拟广告。不久,有人要去无锡演戏,有人要回上海,李君磐有意到南昌发展,就叫上张恨水和他先行去做宣传和推广,闹了几个月,一无所成,随着冬天的到来,他便辞别了李君磐,回老家去了。
转眼到了民国六年(1917)年的春天,张恨水二十二岁了。郝耕仁看他穷愁潦倒,在家乡也无事可做,便从故乡石牌专门写信来邀他一同出游。综合张恨水后来的几次回忆,我们对这次游历有了如下的印象:他们相约三月初在安庆会合,然后,沿长江顺流东下,先到上海,郝耕仁尽其所有,将身上全部盘缠都拿出来,又向朋友借了点钱,买了些家庭常备药(一说为他家有祖传的)。郝的计划是仿照老残所为,以卖药为借口,行走江湖。郝耕仁是老大哥,张恨水是小老弟,自然一切都依郝耕仁的主张。他们便收拾起两小提箱药品,由镇江一个叫仙女庙的地方坐船过江。原打算经江苏,沿淮河北上,进山东,达济南,再浪迹燕赵。“仙女庙是个小镇市,我们在一家小客店落脚,临近就是运河,有一道桥通到扬州,那晚月色很好,我们俩在桥上闲步,看到月华满地,人影皎然,两岸树木村庄,层次分明。有渔船三五,慢慢地往身边走,可是隐约中不见船身,只见渔灯,从这里顺流而下。郝耕仁说,这里很好。他要吟诗,于是就乱吟一阵。眼见月亮西斜,我们才回小客店。第二天我们到邵伯镇去,只有二三十里路程,当然是步行而去,这日天气很好,我们背了小提箱,且谈且走,村庄里树木葱茏,群鸟乱飞,田野里麦苗初长,黄花遍地,农民背着斗笠,在麦地里干活。”
游历的感觉看来不错。黄昏时分,他们来到邵伯镇,在一家旅馆歇下。“郝君还是三块豆腐干,四两白酒,陶陶自乐。醉饱之余,踏月到运河堤上去,我们还临流赋诗呢。”这邵伯镇自古就是个繁华之地,它的得名很有渊源,据说是为了纪念东晋时的谢安,如今隶属扬州市江都区。他们住的这家店,店主是个斯文人,门口两个长脚灯笼上写着“九门都统”,暗示他曾是个京官。他们自称是卖药的商人,但穿着打扮和风流倜傥的神态,分明是两个读书人,店主对他们的身份就有了疑问,于是对他们说,你们可以住在这里,但要找个保人才行。郝耕仁出去找了一个西药店的经理,把这番出来卖药的想法都和他谈了,他表示能够理解,也愿意作保。但他劝二人不要再往前走了,不安全,现在这一带驻了很多军队,前面也许会有战事发生,还是回去为妙。店主也担心他们住在这里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力劝他们返程。这种情形之下,西药店经理就把他们带来的药品打折收购了,算是有了回程的路费。
郝耕仁做新闻记者多年,又有些狂放不羁的文人性格,张恨水与他很有点惺惺相惜的意思。他们从刘鹗的小说《老残游记》中得到灵感,都向往浪迹江湖的生活,故郝一呼而张即应,但他没想到结局会是这样,行程刚刚开始,就宣告结束了。“次日傍晚,我们就搭了一只运鸭的木船前往湖口,以便天亮由那里搭小轮去上海。在这段旅程中,我毕生不能忘记,木船上鸡鸭屎腥臭难闻,蚊虫如雨。躲入船头里,又闷得透不出气,半夜到了一个小镇,投入草棚饭店,里面像船上统舱,全是睡铺。铺上的被子,在煤油灯下,看到其脏如抹布,那还罢了,被上竟有膏药。还没坐下呢,身上就来了好几个跳蚤。我实在受不了,和郝君站在店门外过夜。但是郝君毫不在乎,天亮了,他还在镇市上小茶馆里喝茶,要了四两白酒,一碗煮干丝,在会过酒账之后,我们身上,共总只有几十枚铜元了。红日高升,小轮来到,郝君竟唱着潭派的《当锏卖马》,提了一个小包袱,含笑拉我上船。”张恨水不禁感慨,出门真难啊。郝耕仁告诉他,“这不算什么,昨天我们在旅馆里的时候,茶房就轻轻对我说,镇上保安团里的人已经住到我们对过房间里来,只要他们说声‘捉’,我们就得跟了走。”张恨水听了说,好险呀!这样想来,昨晚的“鸡鸭齐叫,臭气熏人,蚊子乱咬,也就不在乎了”。
对张恨水来说,这次浪迹江湖的尝试虽说不像他想的那样浪漫,但他觉得长了不少见识,沿途所见所闻,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郝耕仁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深深打动了他,让他对这种仰之弥高、望之弥艰的人格境界有了更切实的了解和体会。张恨水在父亲去世之后,虽然失去了安逸的生活环境,断绝了求学之路,饱尝了生活的艰难与辛酸,但他毕竟是个“文人”,有一种本能的清高,对社会底层的生活所知不多。这一次,他才真正看到,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百姓过着怎样的日子,真切感受到这个社会的残酷与不公。日后,张恨水能用自己手中的笔,批判强权,同情弱小,揭露社会黑暗,这次浪游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是他人道主义情怀的肇始和开端。回到上海后,他曾“写了一篇很沉痛而又幽默的长篇游记,叫《半途记》”, 可惜后来丢失了。
在上海,他与郝耕仁住在法租界的渔阳里,“我是靠郝君接济,郝君是靠朋友接济”,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除了和朋友谈天,就是作诗。有时,我们也写点稿子,向报馆投了去”,稿费是没有的,但也由此知道了投稿入选,不是什么难事。除此之外,他利用这段时间读了不少书,早起“随耕仁至粥店,啜粥二三碗,然后往商务印书馆或中华书局及书业公会等处阅书,必待书局打烊始回法租界渔阳里。几至终日忍饥,归后卧地板上,犹高谈阅读所得”, 倒也是一件乐事。因为有了上次的教训,他很怕在上海过冬,所以,“在西风起,北雁南飞的日子,我就回故乡了”。
(待续)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