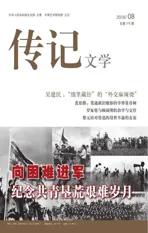马淑清:生长精神的黑土地
2016-09-12文|新伟
文|新 伟
马淑清:生长精神的黑土地
文|新 伟

垦荒队员马淑清、杨增亮夫妇
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出生在城市,却因一声号召,自愿选择了远行,用沸腾的热血染红了屯垦戍边的战旗;有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拥有美好的青春,却因一句誓言,坚定选择了开拓,用火热的激情打破了北大荒悠悠千载的沉寂;就是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把自己交给了亘古荒原,交给了北大荒碧朗的天空,交给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共青农场。
共青农场“五老”之一的马淑清动情地说:“我们把最好的年华献给了黑土地,但我们青春无悔,因为这段经历给我们留下了一辈子受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曾经有这样的文字赞美北大荒的历史变迁:它就是一部壮丽的史诗,每一寸土地上,都刻写着闪光的诗句,这部史诗的作者,正是那些千千万万的垦荒人。在老人眼里,共青农场已不仅仅是产粮的北大仓之一,而且更是一种精神的诞生地。
“告别了母亲,背起行装,踏上征途,远离故乡,穿过那无边的原野,越过那重重山岗,高举起垦荒的旗帜,奔向遥远的边疆,勇敢地向困难进军!……”采访结束时,马淑清夫妇主动向记者唱起那气势磅礴的歌曲《垦荒队之歌》。歌声中,我们仿佛看到一批批年轻人告别父老乡亲、跨过万水千山、来到偏远的北大荒的身影……
哭成一团的第一个春节
2013年3月初,到北大荒垦荒58年后的马淑清重返故乡哈尔滨。她说,自己有些不敢踏上哈尔滨的土地了。“火车驶进月台,心跳得厉害。”
“当年我是‘哈尔滨通’,如今却成了‘哈尔滨盲’。”少小离家老大回,走在中央大街的石头路上,马淑清“念叨”着当年中央大街的模样。走到马迭尔冷饮厅,马淑清兴奋地拍起了巴掌,“冰棍还有呢!我好几次在梦里吃过!”
重回哈尔滨,马淑清寻找一直尘封在心底的最深记忆。“我最想见见当年我的垦荒启蒙老师沙启彦。”马淑清一直有个遗憾,当年报名志愿垦荒,大部分是缘于沙启彦的影响。几十年过去了,马淑清再也没能与沙老师取得联系。
经过有关部门的努力,马淑清敲开了沙启彦家的门。开门的那一刹那,两位老人足足怔了一分钟,“小马,你可老了啊!”“沙老师我可找到您了!”两双手紧紧握在一起。两位老人半小时的谈话,始终没离开过“北大荒”的字眼……
1955年,祖国的边疆还有大片待垦的荒原,当共青团中央一声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时,燕京儿女从祖国的心脏,海河儿女从美丽的渤海湾,松花江儿女从天鹅项下,齐鲁儿女从胶南、临朐、惠民,冀中儿女从秦皇岛的机关里、从保定的学校里、从石家庄的工厂里陆续出发。他们来到了北大荒的萝北荒原上,把一生都献给了这片黑土地。
萝北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北部,土地面积1500平方公里,当时人口不足8000人,平均1.8平方公里只有1个人,故有“六十里地是邻居,三十里地南北炕”之说。马淑清等垦荒队员与凤鸣山下出没的野狼斗,与“三班倒”的蚊子、小咬、牛虻斗,与东北“吃人”的暴风雪斗,热血和忠诚感动着今天生活在这里的新农垦人。
当时,北大荒成为全国志愿垦荒青年向往的圣地。1937 年10月,马淑清出生于哈尔滨,上有一个哥哥,下有一个弟弟。当年,与马淑清一样先后来到这里垦荒的全国志愿垦荒队青年达2602名。据马淑清介绍,她所在的哈尔滨市南岗区报名赴萝北垦荒的青年超过700人,而被批准成行者不到十分之一。马淑清是1955年 12月由哈尔滨市来到共青农场开垦荒原的。马淑清来的理由很简单:“全国人民都来建设黑龙江,自己是黑龙江本地人,更不能落后,不能等闲视之。再说当时北大荒土地在睡大觉,而好多人家里很困难,粮食不够吃。”
为什么要参加志愿垦荒队?马淑清说,话要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说起,当时,我们国家的经济还很落后,农业生产的发展滞后,粮食短缺,饥荒不断,由此直接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安定。“几亿人口的国家缺粮食是全民的大事。党中央、毛主席提出要扩大耕地、增产粮食,在全国组织开垦荒地,组织拓荒者向荒地进军。毛主席曾指出,青年人可以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在北京市第三次青年团代表大会上讲话,号召青年人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为此,全国有志青年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到农村去,到边疆去。”
1955年8月30日,北京市首先组织青年志愿垦荒队开赴北大荒,“北京青年这个头带的好,全国各地青年积极响应。哈尔滨青年热血沸腾起来,积极响应号召,主动到哈市青年联合会报名,要求参加垦荒队,去开发边疆,建设边疆”。马淑清说,哈尔滨青年志愿垦荒队是1955 年9月开始组织的。“当时,由梅树生、孙永贵、王永坤、王英君、赵玉琢5人为发起人,开始组织哈尔滨青年志愿垦荒队。”

1958年,哈尔滨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合影
马淑清讲,当年团组织选拔垦荒队员的条件“苛刻”,“南岗区团区委对每个递交申请书的青年都讲明了北大荒的艰苦,本人同意还不行,还要家访,家里人同意了,还要排除是家里唯一劳动力的青年”。经过选拔的青年还要在大会小会上表决心,意志动摇的也不能去。马淑清说:“我被办事处的沙启彦老师看中,作为南岗区两个骨干之一,另一个是李兆麟将军的女儿李石——后来成了沙启彦老师的妻子,她大我几岁。当时很多身边的小姐妹都退缩了,十几个姐妹中,只有我和李石成行了。”
10月30日,哈尔滨青年志愿垦荒队先遣队派104名男女青年开赴萝北荒原。由原团市委干部吕希孟带领,有党员12名、团员60名,其中女队员12名。“第一批我就报名了,他们走了,我们正参加学习。第二批队员是当年12月,400人,分3天到达萝北,后成立三个大队。我是第二批来萝北的队员,于12月25日晚离开哈尔滨市,第二天到达萝北荒原,被分在第三大队工作。在动身之前,我们向家乡人表达了决心,一定要与困难做斗争,战天斗地决不向困难低头。”
经过一天一夜的路程到达萝北荒原,马淑清这些起先还很高兴的小青年一到目的地就傻眼了,真是一片大荒原,没有房子、没有路,什么都没有。“当晚,我们就住在先期来到北大荒的北京、天津垦荒队为我们挖好的地洞里。地洞上边搭了两片草帘子,后来才知道那叫地窨子,睡在用草铺成的大通炕上,地窨子门是一块大木板挡上的,晚上顺着木板往屋里灌风。外面刮大风,里面刮小风。吐一口唾沫到地上,一下子就成了冰渣了。”
马淑清说,初到北大荒的日子里,就住在这样的地窨子里。“生活上困难只要不怕辛苦便可以解决,可最让你恐惧的是,每到夜晚狼会在我们附近转圈叫,听的我们这群小青年毛骨悚然,有的女垦荒队员吓得用被子捂着脸直哭。可是就这样,我们这些队员当时愣是没有一个想要回家的。因为我们要相互比啊,谁说要走要回哈尔滨,那是要丢一辈子人的,以后在儿孙面前是抬不起头来的。”
马淑清所在的三大队后来住的房子都是萝北老乡上冻前给盖好的土房,“中间没有间壁墙,炕上铺上草就睡人了。有的没来得及搭炕,就在地上睡,外面用木头挡上。三大队四栋房子都是地铺,由于房子盖得晚,四面漏风,油灯点上就被风吹灭了,风刮得都点不着。屋里用大铁桶做炉子、烧木头。当炉子烧起来时屋里冻地都化了,屋地就变成海绵地,晚上睡觉把鞋脱了,穿着棉衣、棉裤,盖上被子睡觉,头上还戴着狗皮帽子。第二天早晨醒来,屋地上、被子上一层浮雪,眉毛、头发上挂满了白霜,盖了一宿的棉被冻成了梆梆硬的冰坨。我们来这里没有水井,吃饭、洗脸都是用雪水。由于缺水,有很多队员都是两天洗一次脸,这些事在当时都是习以为常的小事”。
做饭和喝的水都是用马爬犁到蜂蜜河里去提。北大荒的冬天,千里冰封,拉运饮用水非常艰难,拉一次水需要大半天,拉水人的手脚都冻坏了,但是大家没有一个叫苦的。马淑清说:“当时我们吃的粮食都是从各地调运过来的,有玉米面、高粱米,偶尔吃一顿白面或大米饭。当时没有菜,都是上冻后从外地拉来的冻萝卜、冻白菜。”
从1955年12月开始,为了来年建房子,“我们整天奔波忙碌上山伐木,全体队员都去”。白天,男队员伐木,女队员负责做饭、清雪、劈柴火。队员不到20岁的年纪,没有劈过大的木头,一斧头挥下去,木头纹丝不变,连续劈几次后大木头仍是没变化,把斧子一丢跑到一边哭,哭过后回来拎起斧子继续劈。马淑清看到这样的场景,自己也偷偷地抹泪。“因为没有运输力量,我们只能是人拉、人抬、人扛,同时为了取暖,每天还得扛运烧柴。我们来时北大荒比现在要冷得多,每天气温都是在零下四十左右,真是水滴成冰,而且由于荒原经常下大雪,刮西北风,人感到特别冷,在这种艰苦的环境下,我们每天照常上山伐木、拉烧柴。”
据马淑清讲,有一名叫朱荣正的垦荒队员,在上山伐木时冻掉了自己的10个脚趾盖,当时没有告诉任何人,直到第二年春耕时才被队友发现。朱荣正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不想被动员下山,我要和大家永远地战斗在一起。北京垦荒队员周俊是赶马车的老车板子,由于长时间在外作业,把脚趾头冻伤了,天天流黄水。一天脚冻木了,走路都很困难,他赶紧到窝棚里烤火取暖,脱鞋时连鞋带袜子一起脱下来了,一看吓了一跳,袜子上粘着3个指甲盖。那是脚冻木了,失去知觉,指甲盖黏在袜子上,脱鞋时连袜子一起带下来的。马淑清说,队员们手上、脸上、脚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夜里睡进被窝,冻伤的手脚像猫咬,让人难以忍受。”
很快,1956年的春节就在眼前。“我们垦荒队500多人到达萝北什么都没有,当时都是十七八岁的孩子,盼过年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在这时,哈市政府、团市委派来慰问团,我们都特别高兴,就像见到亲人一样。”
她还清晰地记得,慰问团鼓励他们要克服困难,并带来家乡人民的问候,同时带来的还有慰问品和慰问金:桔瓣糖、冻梨,还有每人5角钱。
大家一个劲跟慰问团打听家乡情况、国家情况,是不是还会有其他垦荒队员过来。慰问团代表一边回答着,一边说:“家乡人民很惦念你们啊,陆续还会有垦荒队员来跟大家汇合。你们要扎根在这里,更要有信心把这荒原变成粮仓,你们现在是在艰苦中炼钢,在炼钢中不能当逃兵。”
“当时甭提多高兴了,心里暖洋洋的。那5角钱放在我兜里,一放就是半年多。到了1956年的四五月份,我们几个小姐妹商量,将5角钱托人从嘟噜河小卖部买了些咸菜,大家一扫而光,别提吃得多美了。男同志买回来的蝶花香烟大家轮着抽,真美啊!”马淑清每每想起总觉得回味无穷,她说那时的“咸菜就大饼子”比现在的香肠还要香。
送走慰问团,大家迎来在萝北的第一个新年,500多个十七八岁的姑娘小伙聚在一起包饺子。“包饺子,连擀面杖也找不到一根,就用玻璃瓶子擀面。没有面板,就找一块铁板,再找一床干净的床单铺在上面,就在上面擀面。”于是,大家一手拿着“擀面杖”擀面皮,一手按着床单不滑动。原本擀面很熟练的马淑清一下子手生起来,毕竟此前没有如此操作过,动作不听指挥。擀的面皮儿自然不好看,又厚又长,像牛舌头,于是再加工,一擀又破了个洞。看到大家的“杰作”差不多,边笑边摇头。包的饺子像梨,不像家里包得像小船儿,肉馅调皮地从破裂处钻了出来,真是“露馅”。马淑清说:“包出啥形状的都有,最后煮出来的饺子都成馄饨了。即便这样大家伙也吃得精光,这顿饺子在往后这么多年中对我来说也是吃过最香的一顿。”
春节开联欢会,结果哭声一片。“有些队员想家就哭。领导说:‘不能哭,要哭别在人前哭,你在被窝里哭。’谁哭了也不准去劝,一劝都哭了起来。我也哭了,和大家哭成一团。我们当时给家里写信,报喜不报忧,不像现在的年轻人啃老,向家里要钱,我们在信里说在这里生活得很好,不用挂念。”
过完年,没多久她们便接到哈尔滨市委送来的发电机和收音机。马淑清说:“听到收音机里播出的新闻,我们这群姑娘小伙又沸腾了好一阵。电灯亮起的那一刻,我们的心也被照亮,眼前的一切都那么温暖清楚,不再害怕黑夜的降临,不再感到垦荒的艰难。”
不拿国家一分钱工资,唯一的福利就是过年时5角的“压岁钱”,自己吃糠皮、豆饼、野菜,把打下的粮食如数上交国库。到北大荒后的第一个中秋节,每人发了两块月饼作为奖励。“是白糖与花生馅的。男生站着吃完了,我咬了一口——特别香,没舍得一次性吃完,用纸包起来放在口袋里,干活最累的时候咬一口,不知不觉吃了一块半。半个月后想吃的时候,去打开包装纸,发现那半块月饼长毛了,我后悔死了,伤心地哭了。一个大姐说,哭什么,不及时吃,也怪不得长毛。”老人笑着讲起这段往事,“还记得第一次吃馒头,是刀切的,不是圆的,我一次就吃了8个。现在就是吃两天,我也吃不了8个”。
不当“钢渣子”的“飞刀手”
去北大荒之前,各地政府都对志愿者交代得清清楚楚:北大荒一穷二白,什么都没有,到那儿就得开荒种地,就得重新创业安家。马淑清说,来北大荒的人当时表示不当逃兵、不让人生有污点、不做拖后腿的人,大家你追我赶,都要求进步。“许多人都心里较着劲,北大荒再艰苦,就当在这里炼钢,要当好钢,不能当‘钢渣子’。”
垦荒开始了。大家憋着劲,赛着干。天不亮就起床,晚上天黑才回来。一米一米地填平泥浆,一寸一寸地铺平沼泽,一锄头一锄头地垦荒犁地,风餐露宿,爬冰卧雪。树根被一棵棵铲除了,手上的血泡也变成了老茧。一天下来,全身被疼痛折磨得觉都睡不踏实。
最可怕的是成群结队的蚊子、小咬、瞎蜢。“它们是‘三班倒’,尤其是北大荒的蚊子,叮人生疮、溃烂,小咬往头发里钻,咬得人心烦意乱。干活时只能戴着纱窗布制成的防蚊帽子,从上到下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只留张嘴在外边吃饭。”马淑清回忆着说,“有些队员,尤其是女队员,一开始确实想家啊。晚上,几个女队员偷偷抱头哭。但是,哭完了,第二天一早起来还是争着干活。”

1960年,马淑清(二排左一)出席萝北县二届一次妇代会时留影
1956年6月7日,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胡耀邦来到哈尔滨青年志愿垦荒队看望队员。“当时大家正忙着干活,一听说共青团的领导来了,都高兴地放下手中的活,跑来和首长握手。整个垦荒队轰动了。胡耀邦看到我们这样辛苦,便问我们当中一位15岁的青年:想妈妈么?小队员回答说,不想妈妈,只想在这里垦荒。胡耀邦怜惜地说,我40多岁了还想妈妈,何况你们呢。胡耀邦看到条件那样艰苦,对围过来的垦荒队员说:不要向困难低头,要坚决向困难冲锋。还嘱咐我们要经受考验,要热爱北大荒,建设边疆,在这里扎根,成家立业,开花结果。”
“胡耀邦来看望我们的时候提出要有‘孩子哭’,说随着年龄增长,该谈对象了。”马淑清说,搞对象,男生多女生少,后来许多山东女青年来报名参加垦荒,“来了不少山东女青年,我还去鹤岗接过她们。哈尔滨后来也来了两批女青年,逐步解决了扎根问题”。“这时,有人动摇了,来了好久,没收入,不挣钱,年龄大了,有一部分思想动荡起来,像炼钢出现‘钢渣子’,家里来电报多了,有的装病,找什么理由的都有。”
随着条件的好转,垦荒队盖起了“拉合辫房”,还成立了畜牧队,组织上安排马淑清在畜牧队当副队长。“当时畜牧队建在西山脚下(十四队西边),我开始了新的工作,养猪养牛。在草甸子里搭猪棚子,围起来就养猪,条件非常简陋和艰苦。那时养猪喂的是大锅糊猪食,糊好了用水桶往猪圈里挑。给猪喂食时,猪都来抢食儿,弄得我全身都是猪食和猪粪。这些活,在大城市里见都没见过,什么都得从头学起,学防疫、给猪打针、配种、接下崽。饲料没有了,还得赶着牛车去拉饲料。”
那时冬天雪大、夏天雨多,路特别难走,狼也特别多,晚间打更都要拿着枪。马淑清记得,有一天深夜,狼叼走了猪崽儿。“我们全队人员去追,在草甸子追了半个多小时,猪的叫声逐渐小了,这时一名老队员拦住了我们说:‘咱回吧,这猪怕是没了,再往前走就是狼窝了,咱这些队员可别再出事了。’我们一想老队员说的对便原路返回,回来后,姑娘们和小伙们心疼小猪都哭了。”
有一年冬天,垦荒队员们经历了一场特大暴风雪的考验。漫天的大雪一下就是好几天,平地上大雪足有一米多深,屋子门都推不开。“人们只好从窗户跳出去,跳出去也走不了,根本迈不开步,只好在雪地里连滚带爬地修雪道。当时人吃的口粮和喂马的饲料都要到县城去购买,用马车拉回来,取暖的烧柴要到西山去拉,可是大雪封道,车马走不了,大家一致说:‘我们在屋子里坐等,老天爷不会给我们送吃的送烧的,还得靠我们继续奋斗。’于是大家破窗而出,经过人清马踩最终修通了出去的雪路,经过大家的拼搏奋战,终于战胜了雪灾,度过了难关。”
这年冬天,马淑清从省城办事归来,当时鹤岗市没有通往萝北垦区的客车,“下车时已是下午,由于惦记畜牧队的工作,我们三人步行往回走。凌晨两点到畜牧队时,得知饲养的黄牛撞开栅栏跑了,我当时也忘记了疲劳,骑上马便去追赶,由于不知烈马的习性,当即被狠狠甩在地上,昏了过去”。
1958年,马淑清被调到蔬菜队任队长。“种菜是个技术活,哪个月份种什么菜,一切又要从头学起。喂猪时候要防狼,种菜时要防狍子、野猪、熊瞎子来祸害,狍子、野猪一来就成群,虽然对我们没有伤害,但种的菜却被毁掉一半,于是我们便拿着铁盆和瓶子轮流值班看菜地,只要野猪、狍子一来就敲。在农忙时我们要参加全庄的锄草工作,麦收、秋收、割小麦、割大豆,从不会到会,最后成了比男同志割的还快的‘假小子’‘飞刀手’。我一直按照团中央书记胡耀邦要求的那样,不向困难低头,凡是别人会的我都要学会,别人能坚持的,我一定要坚持到底,决不后退。”
在蔬菜队,马淑清不仅收获了新鲜的时蔬,得到了很好的历练,而且丰收了爱情果实。马淑清的老伴杨增亮说:“我也是哈尔滨人,道外区的,同一批来的,到了才认识她。她是蔬菜队队长,我是团支书。”马淑清笑着说:“老伴大我一点。有一次,他向我写信,向我求爱。两人志同道合,于是建立朋友关系。他很正义,支持我的工作,他在工作上比较突出,被推荐上农业大学,毕业后我们才结婚。”
由于表现突出,1959年1月马淑清从垦荒队调到预七师二大队任副队长。不久,共青农场的前身萝北农场成立,她又从二大队调到萝北四分场机关做妇女工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这时开始拿工资了,生活好了。”
马淑清先后担任过妇联主任、农场工会副主席、民政主任、信访办副主任等职。这么多年过去了,很多垦荒青年后来都返回故乡,但马淑清等一批老垦荒人却留在了这里,实践着当年来时许下的诺言——“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在工作中,她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多次受到表彰,曾被评为“共青农场优秀党员”“共青农场文明市民”、黑龙江省农垦总局“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标兵”,其家庭也被评为共青农场场直社区“十佳文明家庭”。“通过几十年的勤奋努力,我认清了一个道理,只有听党的话,跟党走,什么艰难险阻都能克服,什么样的惊涛骇浪都能越过。”
不褪色的多彩晚霞
作家丁玲是一位北大荒人,曾创作过散文《杜晚香》。文章深情抒发了对北大荒的热爱:“什么地方是最可爱的地方?是北大荒!什么事业是最崇高的事业?是开垦建设北大荒!什么人是最使人敬仰的人?是开天辟地、艰苦卓绝、坚韧不拔、从斗争中取得胜利、从斗争中享受乐趣的北大荒人。”
经过几代垦荒人的努力,昔日的北大荒已经从人烟罕至的蛮荒之地变为今日全国最著名的商品粮基地、名副其实的天下大粮仓。青春,是人一生最美好的岁月,是马淑清最难忘的记忆。她为自己的选择骄傲,为自己毕生的奉献而自豪。北大荒,是马淑清一生奉献的地方。北大荒精神,是马淑清和她的荒友们用青春和汗水铸造的。年轻时的一腔热血,让她为垦荒事业奉献了一生;年迈后的执着信念,让她为弘扬共青垦荒精神而继续发出光和热。

马淑清(中)与老垦荒队员在一起
“一晃60年过去了,我从当年的小姑娘成了别人嘴里的奶奶,萝北垦区也从当年的‘六十里地是邻居,三十里地南北炕’成为当今现代化的大型国有农场——共青农场。”马淑清说,当年和自己一起来垦荒的500多名哈尔滨青年志愿垦荒队员,如今活着的不到百人了。“虽然我们在逐渐老去离去,但我们每一位老队员都还是一名志愿者,我们要把这种精神传下去,虽然我们退休了,但是公益活动我和老队员们都积极参加,空闲时我会给青年人讲述当年的垦荒历程,让他们知道在这片土地上曾经有一群像他们一样的年轻人,把自己的青春、汗水、生命留在这里,把国家的需要当成自己的使命。”
旧貌换新颜,“大荒”变“大仓”。北大荒已非荒地,抬头可见湛蓝的天空,低头即是绿油油的稻田,优美的环境令人心旷神怡。一句当地最流行的话可以概括现在的北大荒——“耕作在广袤的原野上,居住在现代化城镇里”。共青农场的变化日新月异,这里已经慢慢走出了单一依靠农业生产的经济模式,大大小小的企业、商业都在蓬勃发展,变成了一座崭新的北方共青城。
“原来,这里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现在,马路宽了,路灯亮了,房子成群了,走到地里也几乎不沾泥,我们爱这里的一草一木,不羡慕城里人的生活。我们也回过哈尔滨,知道城市的变化也大、也好,但是哈尔滨有的,我们这里也有,这里什么也不缺,这里有真山真水,这是我们建设起来的,在这里我们很幸福。”马淑清说,我在“共青”生活了这么多年,对共青的感情可以浓缩在诗人艾青的那句诗“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里。“现在,共青场区面貌灿然一新:经济发展环境得到优化,公共秩序井然有序,生活小区清新雅致,场区花草遍地,街头绿树成荫。感受着这些变化,我常常热泪盈眶,我热爱共青!”
夕阳像一个红透的大火球,慢慢地向不远处的凤鸣山梁贴近,渐渐地沉到山的那边去了,西边的天空血一样红。落日熔金,颇为壮观。携手走在共青广场上的马淑清夫妇,回忆依稀的往事,品味多味的人生,望着这美丽壮观的晚霞,脸上褐色的寿斑也亮着紫红色的光,闪亮的瞳孔里也燃烧着憧憬和希望。
华灯初上,长龙般桔红色闪耀的路灯、绿树红花交相辉映的公路、道路两旁鳞次栉比的高楼,这些无一不让共青人在这里尽情享受宜居闲静的幸福。一个布局合理、功能齐全、独具特质的中国北方“红色共青城”正呼之欲出。
共青农场不单纯是生长庄稼的土地,更是共青垦荒精神的摇篮,这种特别的精神食粮哺育着这里的人,也滋养着来来往往的人,汇聚成一股力量。“……在那荒凉的土地上,将要起伏着金色麦浪,让那丰收的粮食,早日流进祖国的谷仓。在那辽阔的土地上,我们要建立起美好家乡,用我们的辛勤的双手,建设祖国富饶的边疆……”告别之时,老人唱起久违的歌曲,时隔60年,她依旧能一字不落地唱出来,那深情的歌唱让人动容……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