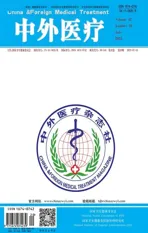对心脑血管疾病高风险人群进行干预的最新进展
2023-09-26彭仁聪林日琦潘华生伍崇信
彭仁聪,林日琦,潘华生,伍崇信
广西医科大学附属武鸣医院心血管内科,广西南宁 530199
心脑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and cerebrovascular diseases, CVD)是所有与血管病变有关的心脑疾病的总称,主要包括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 HF)、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coronary heart disease, CHD)、心律失常、高血压和脑卒中等。尽管近年来药物和器械有所改进,但CVD患者的病死率及发病率仍然高于癌症和传染病[1-2]。心血管疾病是造成全球生命危险的最大单一因素,占中国死亡人数的40%以上[3-4];而脑卒中预计到2030年仍是全球仅次于缺血性心脏病的第二大死因[5]。
1 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
2016年,中国CVD患病人数估计为9 380万,是1990年(4 060万)的两倍多[6]。1990—2016年,CVD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整体显著增加14.7%[6]。2016年,缺血性中风(ischemic stroke, IS)的年龄标准化患病率最高(1 534/10万),其次是缺血性心脏病(ischemic heart disease, IHD)(1 507/10万)和外周动脉疾病(peripheral arterial disease, PAD)(1 441/10万)[6]。1990—2016年,因CVD导致的年死亡人数从的251万增加到397万;其中,PAD相对增长率最高(268.7%),其次为心房颤动和扑动(184.9%)、IHD(184.1%)、IS(83.8%)、主动脉瘤(aortic aneurysm, AA)(72.4%)和心内膜炎(45.8%);只有风湿性心脏病的发病率显著下降,下降近一半(-47.9%)[6]。IHD、IS和出血性中风(hemorrhagic stroke, HS)是2016年心血管疾病死亡的前三大原因(年龄标准化病死率:分别为137.7/10万、56.9/10万和76.0/10万),占心血管疾病死亡总数的2/3[6]。在IHD、IS、HS、AA和心内膜炎中,男性的病死率远高于女性[6]。
CHD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发病率和病死率的主要原因[7-8],大多数年轻的(50岁以下)冠心病研究对象对危险因素的管理较差[9]。中国以研究对象为中心的心脏事件评估研究的最新报告发现,中国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myocardial infarct, MI)的发病率逐渐上升。国内的一项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中青年人群中CHD的患病率呈上升趋势[10],这被认为是吸烟、高血压、糖尿病和血脂异常的流行等因素所致。以上数据共同支持“控制危险因素将有助于减少中国冠心病的健康和经济负担”的观点[11]。另外,最近的一项回顾性研究表明,与过去几十年相比,中国年轻CHD研究对象的心脏死亡和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的总发生率有所增加[12]。
高血压是心血管疾病的主要可调整危险因素,是中国的头号死因[13]。随着人口老龄化现象的加重,高血压、冠心病、脑卒中等心脑血管疾病的卫生支出正逐年增加[14-15]。有调查发现,中国18~24、25~34、35~44、45~54、55~64岁人群高血压患病率已分别达到4.0%、6.1%、15.0%、29.6%、44.6%[16]。国内外研究均表明[17-18],从高血压前期到高血压期,心血管病的发病风险逐年增加,尤其是中青年人群。国内有研究发现,65%的基线血压为130~139/80~89 mmHg的35~59岁的受试者,在15年的随访中发现血压升高至>140/90 mmHg,与血压控制在<30/80 mmHg者相比,心血管病风险增加3倍[18];来自美国的一项研究中的青年受试者,在31年的随访中观察到受试者的心血管病死亡风险有增加趋势[19]。中国的高血压和高血压前期的患病率很高,但对高血压的认识率、治疗率和控制率均很低。
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IS的发病率上升,发病率和病死率高,以及中青年人群长期面临巨大的心理、生理和社会压力,中青年人群发生IS已成为日益严重的问题。尽管IS发病率会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但估计18~50岁的中青年人群IS发病率就已经占到了10%~20%;与老年人中风相比,中青年人群IS的发病率在全球范围内呈上升趋势[20]。在许多欧洲国家和地区的研究中,中青年人群IS的年发病率为5/10万~15/10万人次;在大多数北美洲,中青年人群IS的年发病率为20/10万人次;澳大利亚和亚洲的研究,以及在一些非洲国家和伊朗研究中,中青年人群IS的年发病率高达40/10万人次[21]。与老年人的中风相比,由于潜在危险因素和病因的多样性,中青年IS的异质性更大[22]。
HF的风险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是老年人住院的主要原因(≥65岁)。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美国中青年人(<65岁)的HF相关死亡人数增长最快[23]。相关学者对137 582例主要诊断为HF的住院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发现[24],因HF住院的成年人有27%年龄<65岁;其中,在非西班牙裔黑人男性和女性中,59%和43%因HF住院的患者年龄<65岁;在因HF住院的西班牙裔男性和女性中,分别有41%和25%的研究对象年龄<65岁;相比之下,21%和12%因HF住院的非西班牙裔白人男性和女性年龄<65岁。CVD的主要危险因素有:高血压、血脂异常、HF、糖尿病和吸烟等。国内外的多项随机临床试验和前瞻性队列研究均表明,控制这些危险因素有利于总体人群CVD的一级和二级预防。
2 国内外建立了多种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预测模型
目前,在多项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国内外己建立了多种预测CHD、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等发病风险的模型或简化方法,并且有些被纳入了CVD的防治指南,作为医护或疾控人员开展CVD各级预防的有效工具。目前国外应用较广泛的CVD风险评估方法主要有:Framingham风险评分(Framingham Risk Score, FRS)、集群队列风险方程(Pooled Cohort Risk Equations, PCRE)、系统性冠心病风险评估(Systemic Coronary Risk Evaluation,SCORE)、WHO/国际髙血压联盟(International High Blood Pressure Alliance, ISH)心血管病风险预测图等。以上几个国外的CVD风险评估模型比较适用于欧美成年人[25-26],但对中国个体或群体发生心血管病的综合危险预测存在高估的可能。而我国常用的心脑血管疾病风险评估方法有:国人缺血性心血管病10年发病危险度评估表、血脂指南危险分层方法、中国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风险预测研究(简称China-PAR)等。国内外这些风险评估模型主要纳入包括年龄、性别、高血压、高血脂、吸烟、糖尿病、肥胖等传统的心脑血管疾病危险因素,这些因素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密切相关。
3 除了传统的危险因素,非传统危险因素同样影响着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
除了主要传统危险因素,还有非传统危险因素与CVD发病风险相关[25];研究发现,MI和脑卒中的绝对风险随着心理困扰程度的增加而增高,心理困扰与急性CVD事件有强烈的剂量依赖性[26]。正念减压疗法、自助和积极目标干预、基于网络的认知行为疗法能够缓解患者的心理痛苦,促进心理健康[27-29]。医护人员可借鉴相关的心理干预方法降低中青年CVD高危人群的心理困扰水平,同时还要促进其健康生活行为方式的改变[30],这些生活行为方式应该包括认知行为、饮食行为、运动行为等。有研究证实,日常饮食中的高钠摄入与脑卒中危险性增高相关,钾及鱼类摄入量增多与脑卒中危险性降低相关[31-32]。研究还发现,缺乏运动的人,其发生脑卒中和死亡的风险均明显高于经常参加运动的人;2018年美国心脏协会/美国心脏病学会指出增加有氧运动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有益,防治作用优于药物[32-33]。有调查研究发现,家庭支持对保持更高的生活质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降低常见的慢性病的发生。
4 存在的问题与展望
在关于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研究中,对高危人群的危险因素进行评估、分层和干预,对心、脑疾病的管理至关重要。目前对CVD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判断、影像学检查和一些生化指标。理想的诊断标志物应具有高度特异性和敏感性、快速和无创性。多年来,临床医生一直试图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防治,建立更全面有效的干预模型显得尤为重要。寻找一些生物标志物和疾病危险因素来帮助识别、早期预防、干预和治疗,以预测、评估、预防不良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但临床上可常规应用的指标相对有限。相信随着越来越多研究的开展,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做到等精准的防治,改善其生存和生活质量,减少社会负担与家庭经济支出;同时也可为评估未来我国心脑血管疾病潜在疾病负担,制订防治策略提供基础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