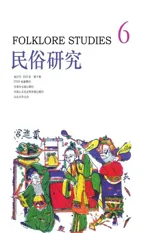民俗、俗道与礼俗:许地山与中国现代民俗学的“礼俗转向”
2023-01-21秦文硕
秦文硕
一、引 言
1928年,从国外留学归来不久的许地山,或许是欣喜于当时中国民俗学蓬勃发展的状况,在翻译戴伯诃利的《孟加拉民间故事》时,袒露自己对民俗学的热爱:“因为我对‘民俗学’(Folk-Lore)的研究很有兴趣,每觉得中国有许多民间故事是从印度辗转流入的,多译些印度的故事,对于研究中国民俗学必定很有帮助。”(1)许地山:《译序》,[印]戴伯诃利:《孟加拉民间故事》,许地山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3页。在这篇译序中,许地山竟然用了一大半篇幅来介绍英国民俗学家博尔尼《民俗学手册》中的第十六章“故事”部分。(2)参见[英]库路德编、[英]约瑟·雅科布斯修订:《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钟敬文、杨成志译,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英]伯恩:《民俗学问题格》,杨成志译,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1928年;陈锡襄:《一部民俗学著作的介绍The Handbook of Folklore, by Charlotte Sophia Burne》,《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11、12期合刊,1928年;王京:《中日民俗学的早期交流——何思敬与〈民俗学手册〉的引进中国》,《名作欣赏》2022年第21期。无独有偶,国内同期注意到这本《民俗学手册》的,还有何思敬、陈锡襄、钟敬文、杨成志等学者。(3)参见[英]查·索·博尔尼:《民俗学手册》,程德祺等译,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第211-219页。博尔尼的《民俗学手册》,偏重于对民俗知识的分类理解与研究方法的解说,此时一批中国学者不约而同地关注,或许意味着他们已不再满足于埋头搜集民俗材料,而产生了理解民俗、阐释社会的集体性学术冲动,尽管不乏对民俗学“能否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4)“民俗学——这是否能成为独立的一门学问,似乎本来就有点问题……民俗学的价值是无可疑的,但是之能否成为一种专门之学则颇有人怀疑,所以将来或真要降格,改称为民俗志,也未可知罢。”详见周作人:《周序》,[英]瑞爱德等:《现代英吉利谣俗及谣俗学》,江绍原编译,上海中华书局,1932年,第1-2页。的质疑。
在这一波民俗研究热潮中,杨成志、杨堃等人推动中国民俗学向西方的人类学、民族学转向(5)参见杨成志:《民俗学之内容与分类》,《民俗》季刊第2卷第4期,1942年;杨堃:《民人学与民族学(上篇)》,《民族学研究集刊》第2期,1940年。,另一些学者则立足于中国民俗学的本土化发展,将之导向“中国礼俗史”或“礼俗学”的研究。许地山便是主张民俗学本土化发展潮流中的一位代表性人物。然而迄今为止,许地山的民俗研究并未得到学界的重视,仅有个别学者予以简介。如曹小娟在《思想史视野中的许地山》中设有“许地山对民俗学的研究”一节,从“民间说唱、民间故事、民间信仰”三个方面梳理了其民俗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6)曹小娟:《思想史视野中的许地山》,厦门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刘锡诚所著《许地山的民间文学观》一文,则介绍了许地山与民俗学相关的部分履历与作品。(7)刘锡诚:《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卷)》,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328-331页。两篇文章都是对许地山民俗研究的简单介绍和对其学术成果的罗列,未能将其学术思想置于早期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学术脉络中予以理解,自然也就无从探索其民俗研究所蕴具的学术意涵与张力。
究其原因,诚如岳永逸所言,以往学术史的讨论都没能离开“民俗学”(Folklore)这一路径,往往满足于以“北大时期、中大时期、杭州时期”为主线的传统民俗学史书写模式,因而忽略了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多元位相。(8)参见岳永逸:《Folklore和Folkways:中国现代民俗学演进的两种路径——对岩本通弥教授〈东亚民俗学的再立论〉的两点回应》,《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7期。近年来,已有部分学者注意到“俗道论”(Folkways)(9)当时学者将“Folkways”翻译为“风俗论”“民风论”“民俗论”等,本文依据许地山的译法,统一译为“俗道论”。参见岳永逸:《孙末楠的Folkways与燕京大学民俗学研究》,《民俗研究》2018年第2期。、“风俗史”(10)参见岳永逸:《风俗与民俗:中国现代民俗学的史学根性和民族性》,《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22年第1期;王晓葵:《“风俗”概念的近代嬗变》,《文化遗产》2010年第3期。等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不同路径,拓展了既有民俗学史的书写模式。而许地山对于“俗道论”的阐发,及其以“礼俗学”为中心的民俗研究系列成果,理应得到重新评估与发掘。本文试图梳理许地山的学术生涯与早期中国现代民俗学的渊源,分析其《中国礼俗史》编纂的设想以及与燕京大学社会学派民俗学的关联,呈现他立足于中国民俗学本土化发展的诸多作为,并以此为基础,理解中国现代民俗学发生礼俗转向的学术表现与动力机制。
二、许地山与中国早期民俗学运动
许地山,字赞堃,笔名落花生,1893年生于台南市,为我国第一位牛津大学毕业的研究生。他曾积极参与并倡导“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我国著名作家、宗教史学家。许地山的学术生涯,是从1917年受基督教会资助入汇文大学文学院(燕京大学前身之一)读书开始的。1920年,许地山从燕京大学文学院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转入宗教学院继续求学。1922年,他获得燕京大学宗教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教,先后执教于燕京大学文学院与宗教学院。1935年,在胡适的推荐下出任香港大学文学院院长。许地山的文学造诣颇深,其小说《空山灵雨》《缀网劳珠》《危巢坠简》等深受大众喜爱,还曾出版中国第一部研究印度文学的专著《印度文学史》。在宗教史研究方面,他撰写了中国第一部道教专史《道教史》,并发表中国第一篇专论古因明史的论文《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11)参见曹小娟:《许地山的学术思想与方法研究》,《西安工业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
许地山对于中国礼俗文化的关注,则可追溯至1922年他为燕京大学文学院高年级同学开设的“中国宗教史”选修课。根据燕京大学毕业生叶启芳的回忆:“他从中国古代宗教引申到中国古代的礼教和风俗,见闻渊博,议论风生,全班十多个同学如沐春风之中,我对于中国民俗研究之兴趣,是这样给许先生诱导起来的。”(12)叶启芳:《追怀许地山先生》,《民俗》季刊第2卷第3、4期合刊,1943年。同年,他发表《粤讴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文,倡言“留到一所地方必要打听那里底歌谣或民众的文学”,同时还“盼望广东人能够把这种地方文学保存起来,发扬起来,使它能在文学上占更重要的位置”。(13)许地山:《粤讴在文学上底地位》,《民铎杂志》第3卷第3期,1922年。由此可见,当时的许地山已对礼俗与歌谣研究抱有浓厚情趣。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1922年《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中,首次在公开发表的刊物中使用了“民俗学”一词,并得到众多学人的拥护,而此时许地山恰巧担任周作人的助教,却并未因此投身于歌谣研究会的相关活动之中,而是热心中国礼俗文化研究,颇耐人寻味。
1923年,许地山进入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宗教研究院,专心研究宗教史与宗教比较学,获得文学硕士学位。一年后,他转入英国牛津大学曼斯菲尔学院研习宗教学。据人类学家罗致平回忆:“许先生在英国牛津大学深造时,曾跟马勒特教授研究过民俗学,也曾翻译过他的‘宗教学入门’,惜此书尚未出版,否则也可供给民俗学研究者以有益的参考。”(14)致平:《前言》,《民俗》季刊第2卷第3、4期,1943年。这里所说的马勒特,国内常译为马雷特(Robert Ranulph Marett),是人类学大师泰勒的高足,1914年至1918年担任英国民俗学会会长,曾因《心理学与民俗学》一书被中国民俗学者所了解。许地山的这段经历,鲜有资料记载,但可据此推测,师从英国民俗学巨擘的许地山应是最早接触英国民俗学发展状况的学者之一,而周作人等则是从日本学界间接了解到英国民俗学发展状况,在理解上难免会有差异。
1927年回国后,许地山就职于燕京大学文学院宗教学系,同时兼任文学系、历史学系、社会学系以及北京大学哲学系、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授课教师。1928年前后,许地山着重研究印度宗教史、民俗学(15)周俟松、杜汝淼编:《许地山研究集》,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482页。,还翻译了戴伯诃利所著《孟加拉民间故事》(16)[印]戴伯诃利:《孟加拉民间故事》,许地山译,商务印书馆,1929年,译序第3页。。他对印度文化钟爱有加,此后陆续翻译了《二十夜问》(17)许地山:《二十夜问》,作家出版社,1955年。《太阳底下降》(18)许地山:《太阳底下降》,作家出版社,1956年。等印度民间文学作品。当时钟敬文出于敬仰之情,曾多次委托赵景深引荐,希望当面向许地山请教,因种种原因未能如愿,但“许地山译介的印度故事成了钟敬文最早的专业食粮,许地山只翻译而未研究印度故事类型,后由钟敬文填补了空白”(19)董晓萍、王邦维:《钟敬文中日印故事类型比较研究(上)》,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编:《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11辑,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13页。。
在1929-1930学年,清华大学社会人类学系四年级开设必修科目“民俗学”(每学期3学分,每周3小时),讲授的内容是民俗学原理及采集民俗研究材料之方法。(20)李森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287页。尽管在当时的课表中并未列明谁为授课老师,但细看四位在岗教师许地山、许仕廉、吴文藻、倪逢吉(21)《国立清华大学一览》,清华大学,1930年,第68页。的经历,若以是否接受过民俗学教育、写过民俗研究文章、开设过民俗学课程等条件推断,授课教师应为许地山。就笔者目前所见资料而言,这应是中国高校第一次开设名为“民俗学”的课程。
1930年,许地山在燕京大学历史学院开设“民俗学与历史”这门课。“民俗学在当时是门新学科,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是作为分析或辨别历史资料的引导。在这门课程的授课形式上,许地山没有采用课本,也没有印发讲义,他上台讲课,学生们做笔记。学生们都十分钦佩他的博学通义。”这种授课风格,与当时顾颉刚倡导的“为了历史的民俗学”十分契合。(22)叶国庆:《许地山在燕京大学》,《民国趣读》编辑组编:《教会大学》,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第156页。巧合的是,顾颉刚当时也在燕京大学历史学系教学。顾、许二人还曾一同指导了硕士生叶国庆的毕业论文《平闽十八洞研究》。(23)参见叶国庆:《平闽十八洞研究》,燕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32年。
1933年,许地山打算利用燕京大学“工作五年休息一年”的制度,先回家探亲,再赴印度访学。为筹备访学费用,许地山在当年秋天赴中山大学文学院社会学系任职。据民族学家岑家梧回忆:“恰好不久许地山先生也来中山大学教书了,我听了他一个学期的民俗学。”(24)岑家梧:《人类学研究的自我批判》,《光明日报》1951年1月27日。据当时资料显示,中山大学文学院史学系的确于当年开设过“民俗学”课程,且为“一年级第二学期必修”,而在社会学系的选修科目中也有“民俗学”。(25)李森编:《民国时期高等教育史料汇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第287页。
1943年,中山大学《民俗》杂志发表了一组名为“纪念民间宗教史家许地山先生”(26)《纪念民间宗教史家许地山》,《民俗》季刊第2卷第3、4期合刊,1943年。的文章,对理解许地山的生平履历与民俗研究有极大帮助。罗致平在前言中提道:“许地山对于民俗学的主要贡献不在已发表的著述中,而在其他许许多多的原稿上(即道教史论,鬼神思想与祭礼,道教词典等)。”(27)致平:《前言》,《民俗》季刊第2卷第3、4期合刊,1943年。同期刊登的一篇《〈扶箕迷信底研究〉提要》文中则补充说:“该书刊行在抗战时期内,流传不能够普遍。”(28)于田:《〈扶箕谜信底研究〉提要》,《民俗》季刊第2卷第3、4期合刊,1943年。由此可知,当时许地山发表的民俗研究成果不算多,且流传度不广。
1935年,许地山赴任香港大学任文学院院长,与大陆学界的来往渐少。“当时的香港,与燕京大学相比,图书和专家都十分匮乏。在教学上,许地山在燕京大学教的多是专门的课程,而在香港,他只能教授生徒以启蒙的课程。”(29)连士生:《怀想许地山》,《南行集》,新加坡南洋报社有限公司,1955年,第11页。作为香港文化界的执牛耳者,许地山出席了大量社会活动,甚至参与调解各种社会纠纷,难以专务民俗研究。不过,许地山在当地风俗启蒙方面的贡献,仍然受到容肇祖的充分肯定:“香港的风俗文化教育的事业,还保持着一切五四运动以前的空气,故此他有《国粹与国学》一篇论文,在今年七月内陆续发表,希望激起革新的精神。”(30)容肇祖:《许地山先生传》,《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年。令人惋惜的是,许地山在1941年因突发心脏病而英年早逝,其民俗研究生涯戛然而止。时至今日,除了他的《扶箕迷信底研究》(31)许地山:《扶箕迷信底研究》,商务印书馆,1946年。一书偶被提及,其民俗教育事业、民俗研究成果均鲜为人知。
纵观许地山短暂的学术生涯,他对弗雷泽的“社会学人类学”、马雷特的“心理学与民俗学”、戈姆的“历史学与民俗学”以及博尔尼的《民俗学手册》等颇为推崇,说明他对英国民俗学有着广泛而深刻的理解。他在拼写“民俗学”的英文单词时,坚持使用比较传统的Folk-lore写法,这在某种程度上显示出他对于英国民俗学“文化遗留物”说的熟稔,倾向于将民俗视为无文字社会中“民众的知识”。大约正基于此,他才致力于将中国民俗学研究引向了一条有别于英式“民俗学(Folk-lore)”的道路——“中国礼俗”或“中国礼俗史”研究。
三、礼俗成为主流话语
1930年后,许地山在民俗研究中最常用的是“礼俗”一词。他主讲的“中国礼俗史”课程在燕京大学颇受欢迎,曾先后在历史学系、社会学系开课。他还系统地发表了《礼俗与民生》《礼俗调查与乡村建设》《三十年来我国礼俗变迁回观》等论文,并在广州协和学院做过题为《中国礼俗与宗教》的学术演讲。那么,许地山为何开始频繁使用“礼俗”这一概念而非“民俗”?
事实上,许地山在当时学界并非特例。当时北平的一批民俗学者的关注重点,与身处杭州、福建、上海等南方地区的学者大有不同,他们不再把民俗学的重心放在民间文学方面,而对与社会生活密切关联的“礼俗”一词情有独钟。比如,江绍原在北京大学开设“礼俗迷信研究”的课程,黄石称“民俗学”为“礼俗学”,杨堃认为“礼俗调查”就是“民俗学调查”。(32)参见黄华节:《礼俗改良与民族复兴》,《黄钟》第6卷第1期,1935年;杨堃:《中国现代社会学之派别与趋势(续)》,《鞭策周刊》第4期,1932年;江绍原:《中国礼俗迷信》,王文宝整理,渤海湾出版公司,1989年。1930年《民俗》周刊停刊,次年北平出现了另一本专门性的民俗刊物《礼俗》。(33)《礼俗》半月刊由国立北平师范大学研究所于1931年创办,共刊行了9期。对许地山而言,所谓“礼俗”即礼仪与风俗的合称:
礼俗是合礼仪与风俗而言。礼是属于宗教的及仪式的;俗是属于习惯的及经济的。风俗与礼仪乃国家民族底生活习惯所成,不过礼仪比较是强迫的,风俗比较是自由的。风俗底强迫不如道德律那么属于主观的命令;也不如法律那样有客观的威胁,人可以遵从它,也可以违背它。(34)《礼俗与民生》首刊于商务印书馆1947年刊印的《国粹与国学》。详见许地山:《国粹与国学》,《空山灵雨》,煤炭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117页。
斯时,中西、新旧等各类文化现象混杂在社会之中,使得民众无所适从。针对这种社会状况,南京国民政府认识到“制礼乃经国之大业,正俗之宏图……非创制革新礼俗,不足以重新建立社会之体系”(3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全宗号十二(6),案卷号18160。转引自阚玉香:《北泉议礼及其成果——〈中华民国礼制〉》,《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为此成立了一系列负责礼俗改造的机构,如1929年在内政部下设“礼俗司”,专门负责礼乐风俗的审订、宗教寺庙监督、古物古籍保护等事项,并在1930年实施“全国风俗调查计划”。随后,各地纷纷设立“礼俗讨论会”“礼俗研究会”“礼俗改进会”等学术组织。
北平得风气之先,早在1929年时即成立礼俗研究会,比中央礼俗研究会早成立了6年。北平礼俗研究会成立的原因,是“中央关于礼俗,既无明令规定,各地礼俗,又多卑陋腐化之处,而尤以北平为数百年旧都所在之地,关于婚丧庆祝,繁文俗节,极为琐碎,而其中尤含有封建思想,或迷信之处,当此革新时代,此种礼俗,若不加以改革,实足以束缚北平民众之思想,而碍社会之精华”(36)《北平改革礼俗 放弃繁文缛节 设礼俗研究会》,(上海)《时事新报》1929年9月2日。。至于北平礼俗研究会的成员,则“邀请北平新旧学者研究各种礼俗之起源,及改良之方法、并从新制定各种礼仪制度,以代替旧式礼俗,并将研究所得,呈请市政府公布,于中央未颁布此项法令前,即作为本市之法令,并拟建议中央,采纳公布云”(37)《北平改革礼俗 放弃繁文缛节 设礼俗研究会》,(上海)《时事新报》1929年9月2日。。由此可知,北平礼俗研究会成立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使北平成为全国礼俗改革的先行地区,这在官方层面为“礼俗”一词赋予了合法性。
正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下,身在北平的一批民俗学者以“礼俗”贴近官方话语,将关注点移向民众生活本身,为中国现代民俗学大大拓展了学术空间,而许地山即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1935年,许地山应商务印书馆之邀,领衔主编《中国礼俗史》一书。许地山力邀三位学者共同撰写该书:“江绍原是撰述迷信方面,陶希圣撰述社会经济方面,黄华节撰述各种气节方面。他所要着手的是中国的物质生活与礼仪习俗底历史,大约在年内可以完成。”(38)《落华生将完成中国礼俗史》,《每周评论》第157期,1935年。在这份简要的写作计划中,可以得知这部“中国礼俗史”至少包括迷信、岁时节气、礼仪习俗、物质生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内容。
受到许地山邀请参与撰写《中国礼俗史》一书的三位学者,均为当时著名的民俗学家,并各有术业专攻。其中江绍原、黄华节(黄石)均在北平高校任教,都是宗教学出身,还在国外留过学,与许地山颇多相似之处,因而旨趣相投。赵世瑜认为,“他们研究民俗,都具有宗教学的共同背景,这就决定了他们研究的对象较集中于礼俗、民间信仰的方面,他们的研究面更为宽阔,他们由于对国外学术发展较为了解,所以在掌握民俗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上更为熟稔,他们从宗教的角度出发,更直接地切入民俗的本质特征(这里的意思是说,大多数民俗事象均具有宗教的或巫术的根源),因此他们更接近专业的民俗学家”(39)赵世瑜:《黄石与中国早期现代民俗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6期。。这样一支志同道合的民俗学专业队伍,不仅规划了“中国礼俗史”的研究蓝图,而且每个人也都计划从自己最擅长的领域着手。令人遗憾的是,此书最终未能出版,这或许与核心编写人员许地山、黄石到香港后,与大陆出版界联系不易有很大关系。
许地山的编纂计划,没有按照传统的断代史编纂风格,而是划分为与当时社会改革运动密切相关的四大板块,体现出“经世致用”的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如岁时礼俗是黄石用力颇勤的研究领域,他擅长运用多种文献来追溯节俗的起源和流布,并用人类学的方法解释和探究春节、寒食、端午、七夕等节俗的原初性质、意义等。(40)吴丽平:《黄石与民俗社会学》,《民俗研究》2020年第6期。江绍原是礼俗迷信研究的专家,他的礼俗迷信研究涉及人生礼俗、姓名迷信、岁时节日、医药民俗等方面,主张“一切真实的学问都是涉及迷信研究和破除迷信的”(41)王文宝、江小惠编:《江绍原民俗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289页。。他认为,“只怕无论怎样古的礼,若不用我们的科学知识、道德标准和艺术兴趣,好好的提炼一番改造一番,决不能合我们今人的用”(42)王文宝、江小惠编:《古俗今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114页。。至于许地山本人,则打算借助“中国礼俗史”的课程内容来撰写书稿。早在1931年,许地山在历史学系开设“中国礼俗史”课程时,课程简介即为“研究中国历代(1)衣、食、住状态之变迁及其环境之影响;(2)礼教风俗之沿革。上学期上古至唐,下学期五代至近时”(43)《私立燕京大学历史学系课程一览》,燕京大学,1931年,第8页。。颇具匠心的是,许地山还在该书中专门设计了社会经济史部分,并特邀社会经济史专家陶希圣主笔。因为陶希圣擅长从社会组织的角度看风俗,同时大力推崇在礼俗改良前一定要先进行礼俗调查,“我们以为习惯风俗与社会组织是有密切关系的,社会组织一方面受过去历史的影响,一方面又受当时环境的影响。一种礼俗调查,必须明瞭它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才可了解,所以又必须明瞭社会组织的变迁”(44)陶希圣:《中国社会史经济史研究的方法》,《社会研究》第60期,1935年。。这与许地山的主张很是吻合,“要知道中国现在的境遇底真相和寻求解决中国目前的种种问题,归根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与其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底研究入手”(45)许地山:《国学与国粹》,《国粹与国学》,吉林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6年,第99页。。
四、从风俗到礼俗:“中国礼俗史”进化之路
近年来,岳永逸提出中国现代民俗学运动有着更为丰富多元的位相,不但有诸如传教士司礼义这样研究中国民俗的“土著之学”,还有明显有别于Folklore的Folkways这一支脉。(46)岳永逸:《Folklore和Folkways:中国现代民俗学演进的两种路径——对岩本通弥教授〈东亚民俗学的再立论〉的两点回应》,《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20年第7期。其中,Folkways这一支脉主要指燕京大学社会学派民俗学的研究:
在中国社会学创建时期,美国著名的民俗学家、社会学家孙末楠和他关于民俗的学说一同被介绍了进来。因为派克在始终重视民俗研究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孙末楠民俗学说的宣讲,孙末楠的民俗论对燕京大学的民俗学、社会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诸如对于民俗的理解发生了从风俗到礼俗的整体转型。(47)岳永逸:《孙末楠的Folkways与燕京大学民俗学研究》,《民俗研究》2018年第2期。
实际上,许地山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40年毕业生李荣贞,曾在其学士学位论文《中国民俗学的发展》中,这样追溯燕京大学社会学派民俗学的发轫:“1937年之前,社会学派先有许地山燕京大学讲授中国礼俗史,继之者则有吴文藻先生,黄石先生。”(48)李荣贞:《中国民俗学的发展》,燕京大学学士学位论文,1940年。由此可见,在燕京大学社会学派民俗学研究的学术脉络中,许地山的礼俗思想有开启之功。
许地山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渊源,要追溯到1917年他在汇文大学读书之时,当时他辅修了社会学等课程。此外,因其基督教徒身份的缘故,许地山经常前往由北京基督教青年会主导成立的北京社会实进会,在其图书室读书,学习了很多西方社会学知识。(49)朱睿:《许地山与文学研究会》,西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1年。1919年,许地山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并在上面发表了一系列与社会学相关的论文,旨在向大众传输关于社会的知识,以促进新文化运动下的社会改造。(50)参见许地山:《女子底服饰》,《新社会》第8期,1920年;许地山:《劳动底究竟》,《新社会》第17期,1920年;许地山:《强奸》,《新社会》第10期,1920年;许地山:《十九世纪两大社会学家底子女观》,《新社会》第17期,1920年;许地山:《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新社会》第14、15、16、18期,1920年。留学归国后,作为教师的许地山与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虽然教职在宗教学院,但他长期承担着社会学系的课程,还经常在社会学系举办讲座,同时还是燕京大学社会学会创办的《社会学界》编辑部的主要成员之一。
1929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发表《建设时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方针及步骤》一文,将“中国风俗”研究列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十大研究方针之首(51)许仕廉:《建设时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方针及步骤》,《社会学界》第3期,1929年。,足见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对中国风俗研究的重视程度。值得关注的是,许仕廉在介绍这一研究方针之前,特意强调燕京大学社会系在研究方针设置上的特色,即“研究范围,随时随地随教授兴趣而定”(52)许仕廉:《建设时期中教授社会学的方针及步骤》,《社会学界》第3期,1929年。。热衷“中国风俗”研究的许地山,则备受燕京大学学子欢迎:
许先生因为研究宗教及历史——尤其是社会史——所以对于社会上的风俗、习惯、迷信、信仰,特别注意。什么骂人的话,祈祷的话,咒念的话,他都知其来历。至于小孩子衣服上的花纹,鞋帽上的老虎头,怀中带着的一些玩艺,以及一个菩萨的一双鞋,一个庙宇的一尊神,他都无所不知其所以然。此外如什么宫,什么寺,哪天打鬼;什么庙,什么观,哪天会神仙,更是他的拿手戏。而且通透的程度,会使你惊奇,所以燕京学生们,关于这方面的参观游览,差不多都请他领导。只要有工夫,都是有求必应,因此,只雍和宫打鬼一事,虽然一年只有一度,他到那里却有过八次之多。(53)《文学象速写(四):“落华生”许地山:专门研究的都是东方文化风俗,家里摆满了砖瓦石块骨头贝壳》《沙漠画报》第3卷第1期,1940年。
事实上,许地山当时是在社会学系兼职:1928年至1929年,许地山受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许仕廉的邀请,义务为社会学系的学生授课,主要讲授人类学(54)傅愫冬:《燕京大学社会学三十年》,《社会》1982年第4期。;同年,许地山率领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赴福州调查“疍民生活状况”,由此形成的《福州疍民调查》和《福州市台江区小船户各种统计及其生活状况的调查》,是近代较早对“疍民生活”进行介绍的调查报告(55)吴高梓《福州疍民调查》,邹德珂、项孝挺《福州市台江区小船户各种统计及其生活状况的调查》,收录于李文海编:《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底边社会(卷下)》,福建教育出本社,2004年,第565-587页。。显然,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中国风俗”研究的学术取向,与许地山有着莫大关系。许地山曾强调说:“关于历史,我尤有相当认识,因为我是研究东方风俗文化史的人。”(56)《文学象速写(四):“落华生”许地山:专门研究的都是东方文化风俗,家里摆满了砖瓦石块骨头贝壳》,《沙漠画报》第3卷第1期,1940年。因此,曾亲身参与燕京大学民俗研究活动的杨堃,一直称江绍原为“民俗学家”,却称许地山为“中国风俗史学家”。(57)杨堃:《编纂野蛮生活史之商榷》,《鞭策周刊》1932年第1期。那么,许地山又是如何从早期的风俗研究过渡到礼俗研究的呢?
上文提到,孙末楠的“俗道论”(Folkways)在1930年代的燕京大学颇受欢迎。孙末楠的这一学说,是在斯宾塞进化论的基础上形成的,而许地山则是早期进化论的推广者,并曾效仿斯宾塞与孙末楠,发动燕京大学一众学者着手收集“野蛮社会”的材料。(58)“斯宾塞尔编社会学,所用的材料,差不多完全是从野蛮部落及原始社会中得来的。野蛮部落,组织简单,易于研究;而且与我们所谓的文明社会,相隔甚远,若风马牛之不相及,我们去研究他,也可不发生偏见。孙末楠看清楚这一点之后,便着手收集关于野蛮社会的材料。我们现在翻开《民俗论》及孙恺著的《社会学》一看,没有不惊讶书中事实之丰富,材料之充足的。”详见吴景超:《孙末楠传》,《社会学刊》第1卷第1期,1929年。1932年7月,许地山牵头,与吴文藻、江绍原、黄石、李安宅等一同在《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版,发起编纂“野蛮生活史”并“征求同工”的学术活动。(59)《编纂“野蛮生活史”缘起及征求同工》,《大公报》1932年7月30日。1930年,随着“俗道论”(Folkways)在中国的流行,许地山发表了《文化与民彝》一文,将Folkways翻译为“民彝”(后翻译为“俗道”)(60)许地山在《国粹与国学》一文中说:“一般人所谓国粹,充其量只能说是‘俗道’底一个形式(俗道是术语folk-ways的翻译,我从前译做“民彝”)。”详见许地山:《国粹与国学》,《空山灵雨》,煤炭工业出版社,2016年,第122页。。
正是在对“习惯”“民彝”“民望”“制度”“法律”一组概念进行本土化理解的过程中,许地山较为系统地呈现了孙末楠的民俗理论并有所发展。许地山认为,有关人类生活科学研究的困难在于,资料搜集很多,但是缺少研究的方法,所以文化研究很难像自然研究那样寻找规律;从文化史的角度来寻找规律,相对来说是个更合理也更容易的办法,而文化史书写的第一步就是理解人之习惯和思想的历史,即风俗史。此外,文化的衰败与进步,与风俗有很大的关系,谈保留中国文化也必先了解中国风俗史。(61)许地山:《文化与民彝》,(天津)《益世报》副刊1930年5月24、28日。孙末楠“俗道论”的特点,就在于他阐明了风俗发展的规律性。如果说博尔尼所界定的“民俗”(Folklore)概念,是指野蛮民族的或者野蛮民族遗留的风俗,那么孙末楠所使用的Folkways概念,则注意到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即使原始的族众也能从风俗中衍生出一种带有道德和福利观念的行为模式,这就是所谓“民望”(Mores)。正是基于对“Mores”和“礼”这两个概念的比较,燕京大学一批学者才开始转向礼俗研究。许地山曾将“俗、礼、法”的关系做了这样的说明:
在民望中有一大部分是禁忌(Taboo),而禁忌又可以分为保护的禁忌与破坏的禁忌,礼也含有大部分的禁忌在里头,所谓“祝”是属于保护的,“诅”是属于破坏的。礼及民望底其他部份既是伦理的及哲学的,故这两种于规定行止上有很大的力量。(62)许地山:《文化与民彝》,(天津)《益世报》副刊1930年5月28日。
法律底产生很后,在原始文化里,只有风俗与禁忌。在法律上所谓善恶,都以其时地之民彝为标准。由禁忌生礼仪,故在原始社会中,礼仪是共栖最重要的表示,婚礼,医乐,教育,行军等事,都与它有关系。(63)许地山:《文化与民彝》,(天津)《益世报》副刊1930年5月28日。
许地山的这一研究思路,在当时并非个例。1930年左右,受孙末楠学说、当时社会礼俗改良实践以及传统礼学研究等多重影响,多位得到过许地山指导的燕京大学师生也对俗、礼、法等概念进行了比较与辨析。如李安宅在1931年出版的《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中,认为“礼”包括民风(Folkways)、民仪(Mores)、制度(Institution)、仪式和政令等;广义的礼,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面向的文化;狭义的礼,则专指琐屑但也有着型式的“礼节”。(64)李安宅:《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31年,第4-5页。1933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本科生瞿同祖发表《俗、礼、法三者的关系》(65)瞿同祖:《俗礼法三者的关系》,《社会研究》(周刊)1933年第32-35期。一文,试图通过厘清俗、礼、法之间的关系来理解中国的法律系统。1934年,更关心民俗研究的黄石,出于对瞿同祖提出的“俗、礼、法”三分的异议,明确提出民俗社会学研究的四分法,即“风、俗、礼、制”四型。(66)黄华节:《民俗社会学的三分法与四分法——论风俗礼制四者的关系》,《社会研究》第52期,1934年。但仔细分辨,尽管上述学者对于“俗、礼、法三分”“俗、礼、法、制四型”的分类,以及对于“俗道”和“民望”的关联的理解有分歧,但在西方学术本土化上,大致都将Mores和Folkways与中国的“礼仪”和“风俗”分别等同起来。
许地山还注意到,与当时学术上所提倡的“民众为中心的历史”不同,现实生活中的民众在民俗话语上处于极其弱势的地位。“民彝”基于老百姓的生活实际需要而产生,但当它失去活力后仍然存在,“因为生活方式大半是前人做定的,其方法或者可以使人不费力而获益,并且不知其利益,但有时也能使人费力而不收实效”。即便在当时,有些民彝已经变得暴虐与强制,严重影响百姓的日常生活,但民众总以“我们的祖宗也是这么做”为理由得以延续。如果到了“民望”阶段,百姓将拥有选择权,“在历史里,群众是被一个选择的阶级所管理的。他们有他们底民望,他们可以规定他们要走底路程,使群众模仿他们”。显然,许地山认为民众并非照搬“民望”,而是倾向于将其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相结合,不断地形成新的“民望”。不过一旦进入制度化阶段,民众又失去了选择权,许地山强调国家必须意识到,失去选择权的下层民众容易沦为不负文化责任的芸芸众生,“众人以为是,他们也以为是”,因而国家必须知晓并尊重民众的主体意愿,因为“民众实在有自决底能力,凡民众有利底事情他们一经发觉或被人指导,就必照着奉行”。(67)许地山:《文化与民彝》,(天津)《益世报》副刊1930年5月28日。
针对民众与国家的关系,许地山提出“民众的中庸与保守”“民众的利好倾向”“国家对文化的责任感”等风俗发展的若干特征,更对中国“以礼化俗”的社会治理方式大为推崇:
我国古来有“风化”“风俗”“政俗”“礼俗”等名称。风化是自上而下言;风俗是自一社团至一社团言;政俗是合法律与风俗言;礼俗是合道德与风俗言。被定为唐朝底书《刘子·风俗篇》说:“风者气也;俗者习也。土地水泉,气有缓急,声有高下,谓之风焉。人居此地,习以成性,谓之俗焉。风有薄厚,俗有淳浇,明王之化,当称风使之雅;易俗使之正。是以上之化下,亦为之风焉。民习而行,亦为之俗焉。”(68)许地山:《礼俗与民生》,《空山灵雨》,煤炭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117页。
如果说,孙末楠学说的一大贡献,就是发现了原始社会进化过程中由Folkways到Mores再转至Institution(从“风俗”到“礼俗”再到“礼制”)的文化发展规律,那么许地山则意识到,中国作为一个成熟的文明社会,有着“以礼化俗”“以礼节俗”的社会治理传统,因此还存在着一条从“礼制”到“礼俗”再到“风俗”的对向文化发展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呈现出“礼俗互动”的中华文明独特发展脉络与社会运行机制。事实上,传统中国社会中的文化政治模式,是冀望通过礼仪教化达至礼俗融合的社会理想状态(69)张士闪:《中国礼俗传统的田野考察与文化阐释》,《民族艺术》2020年第6期。,民众生活往往受到礼、俗之间多种文化准则的往复导引,因而用“礼俗”一词更能说明中国民众生活的实际状况。
在孙末楠学说的影响下,一批中国学者重新审视“风俗”这一概念,意识到民众日常生活并非自发而为,在俗以外,还有礼的约束。许地山的礼俗研究,正是基于这一认识而对中国现代民俗学本土化之路进行推进,因为“以礼节俗”作为中国传统的社会治理方式已是根深蒂固,由此导致礼与俗的界限也难以划分清楚。事实上,所谓“国家之礼”与“民间之俗”(70)张士闪:《礼与俗:在田野中理解中国》,齐鲁书社,2019年,第93页。只是相对意义上的划分,是呈混融状态的“礼俗”指引着民众日常生活,大致代表了所谓“民间生活”的文化准则。
五、余 论
贯穿于许地山中国礼俗史研究之始终的,是他对于礼俗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特别意义的推重。他认为,礼俗既是民众的生活准则,还是民族精神和文化的关键,“一个民族精神的生命是依仗着这两样来维持的。国家灭亡底内因之一在先舍弃固有的风俗,忘掉自己底礼仪底意义,或舍弃自己底礼仪去采用别个民族底”(71)许地山:《礼俗调查与乡村建设》,《社会研究》第65期,1930年。。殊为可贵的是,许地山的礼俗研究,并不全然服务于保存国粹的目的,也与对“种种特殊的礼仪与好尚”的鉴赏趣味无关,而是以严谨的学术态度“用物质的生活、社会制度、或知识程度来解释它们,并不是绝对神圣,也不必都是优越的”,从而可以“使我们知道民族过去的成就,促使我们更加努力地向更成功的途程上迈步”。(72)许地山:《国粹与国学》,《空山灵雨》,煤炭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121、124页。
不仅如此,许地山还试图将礼俗研究落实到现实社会生活之中,强调礼俗改革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在古时候,礼仪是一种德行,风俗是一种律例,现代生活越来越忙,礼仪便趋于简单,要保持古礼,是时势所不容。又法律昌明,风俗习惯也渐次失去威权,此后若要保持礼俗底优点,便得详加探究,不可由民众随时取舍就可以”(73)许地山:《礼俗调查与乡村建设》,《社会研究》第65期,1930年。。许地山的礼俗改革观念,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点:第一,礼俗调查是重要的前期工作。民国以来,针对民间的婚丧嫁娶以及庙会、节日等的改革,各地虽不时有条规宣布出来,但收效甚微,甚至有时还会增加很多非必要的仪式,难得民心。许地山认为,这是由于立法者不了解礼仪与习俗的本质而贸然改动的缘故,因此在改革前要先做调查,明晓其中的利害关系,才能实施“制礼作乐”“化民成俗”。他还强调在各处实地调查时,要注意礼俗和农村生活的关系,把能够弘扬民族精神的风尚提炼出来。(74)许地山:《礼俗调查与乡村建设》,《社会研究》第65期,1930年。第二,礼俗需要有新的解释,才能在现实社会中存续。许地山强调,调查礼俗并非立意在“制礼作乐”上,而是要对固有礼俗加以新的阐释,使它们合乎新的生活,特别是有些从野蛮的或古旧的仪式演变而来的礼节,需要不断注入新的解释才能得以保存,并让人们从思想上接受它。(75)许地山:《礼俗调查与乡村建设》,《社会研究》第65期,1930年。当然,礼俗改革还要考虑民众的承受能力,毕竟“礼仪与民生底关系至密切,有时因习俗所驱,有人弄到倾家荡产,故当局者应当提倡合乎国民生活与经济底礼俗,庶几乎不教固有文化沦丧了”(76)许地山:《礼俗与民生》,《空山灵雨》,煤炭工业出版社,2018年,第119页。。
要言之,许地山的“中国礼俗史”研究,是他结合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而探索出来的一条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路径。他认为礼俗即民间生活的精髓,之所以要从文化史的角度理解礼俗,是为了更好地探析民众日常生活习惯和思想的来源及变迁,为当下民众生活做指导,以礼俗改良促进社会进步。
不可否认的是,许地山由于民俗学论著较少,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的影响力有限。但统观他的民俗学教学经历与科研实绩,其蕴具的学术意涵与张力仍有待彰显。许地山与胡适、周作人、江绍原、郑振铎、赵景深等中国民俗学奠基人物有着密切的学术往来,更是培育了黄石、岑家梧、罗香林、罗致平等一批民俗学者,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留下了深刻印记。顾颉刚对他的学术功力钦佩有加:“人能博闻强记如落华生,则研究任何学问可以事半功倍。”(77)郭邑:《许地山补记》,(上海)《政治月刊》第2卷第3期,1941年。容肇祖曾赞叹他的求知精神:“他要找寻习惯、风俗、迷信、礼制等等的由来,遂深造于道、佛二教的研究。”(78)容肇祖:《许地山先生传》,《文史杂志》第1卷第12期,1941年。事实上,同代人对他的高度评价,与他在中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礼俗转向过程中所担当的重要角色有关。而他借鉴西方现代理论而不拘泥,在关心现实社会生活的同时,致力于探索中国民俗学的本土化之路,足为当代民俗学发展提供弥足珍贵的历史经验与学术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