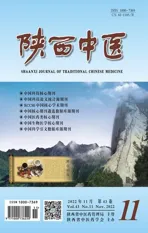基于肠道菌群探讨中医药治疗功能性消化不良研究进展
2022-12-21林瑞芳俞赟丰阳凌峰
林瑞芳,俞赟丰,阳凌峰,喻 斌,徐 寅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南 长沙 410007)
功能性消化不良(Functional dyspepsia,FD)是临床上常见的功能性胃肠病。据统计[1],欧洲FD的发病率高达10%~40%,亚洲FD发病率为5%~30%,FD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相关研究指出,肠道菌群是FD的关键调节因子和治疗靶点[2],中医药治疗FD不仅有可靠的临床疗效和良好的安全性,并且对肠道菌群有着显著的调节作用[3-4]。目前尚无中医药干预FD肠道菌群的系统总结。因此,本研究以肠道菌群为切入点,综述中医药治疗FD的研究进展,以冀为临床用药提供借鉴。
1 FD肠道菌群的变化
人类肠道微生物群主要由厚壁菌门、放线菌门、拟杆菌门、变形菌门、疣微菌门等组成,其中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是优势菌群(>98%),厚壁菌门和拟杆菌门的比值是反映肠道微生物群紊乱的重要指标[5]。按照对人体的作用,肠道菌群可分为三大类:①共生性的生理性细菌,如双歧杆菌、拟杆菌;②共栖性的条件致病菌,如肠球菌、肠杆菌;③病原菌,如韦氏梭菌、变形杆菌[6]。研究[7]指出,FD存在近端小肠细菌过度生长,尤其是PDS-EPS和PDS亚型。亦有研究[8]发现,相较于健康对照组,FD患者十二指肠黏膜的优势菌链球菌属的数量显著减少,其相对丰度与普氏菌属、韦荣氏球菌属和放线菌属丰度呈负相关。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十二指肠黏膜细菌总负荷的增加,细菌多样性降低,FD症状加重。Nakae等[9]对44例FD患者的胃液进行T-RFLP分析后发现,胃液中双歧杆菌属、梭菌属(Ⅸ、Ⅺ和Ⅷ簇)等肠道菌丰度显著升高,而普氏菌属的相对丰度下降,且普氏菌属丰度和PDS症状的严重程度呈负相关。Fukui等[10]用16S rRNA测序对FD患者和健康人的上消化道黏膜相关微生物区系进行研究后发现,FD患者的厚壁菌门显著增加,链球菌属明显增多,且该菌的相对丰度与FD患者的上消化道症状呈正相关。上述研究证实,FD肠道微生物群存在多样性、结构、丰度及分布异常,且菌群失调与FD症状存在相关性。
2 肠道菌群与FD发病机制的探讨
2.1 影响胃肠动力 消化期间胃和小肠移行性复合运动可将胃肠内容物和致病菌机械性地移行向远端肠道,而FD经常出现非传播性和逆传性MMC Ⅲ期活动,这可能诱导或加重近端小肠细菌随反流的十二指肠液迁移到胃,而胃排空延迟又导致反流菌能较长时间保留在胃和十二指肠中,在引起菌群分布失调的同时,外籍菌的增殖可产生内毒素脂多糖刺激免疫应答,进而抑制胃肠道蠕动,加重FD症状[11]。短链脂肪酸(SCFAs)是肠道共生菌发酵膳食纤维的代谢物,除了作为胃肠道动力重要能量来源,也可直接激活肠神经系统以调控肠内分泌细胞合成和分泌某些胃肠激素,如肠激素肽YY、胆囊收缩素、胰高血糖素样肽1、抑胃肽、胃动素相关肽[12-13],进而调节胃肠道动力及胃排空,而在代谢组学研究中发现FD大鼠存在SCFAs水平显著降低[14]。此外,5-羟色胺(5-HT)水平是影响胃肠道动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关研究证实肠道微生物群在调节5-HT合成中起着关键作用[15]。由上述研究可知,胃肠动力异常可能引起菌群失调,而菌群失调可反过来进一步影响胃肠动力,介导FD的发生发展,但菌群失调与FD的因果关系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加以验证。
2.2 影响胃肠道屏障功能和免疫功能 十二指肠的改变可能是FD的潜在发病机制[16]。相关研究发现,FD患者十二指肠上皮细胞存在黏附蛋白表达异常和细胞旁通道增多,且细胞间黏附蛋白的表达水平、通透性增加的程度和低度炎症的严重程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17]。此外,有研究指出,黏膜通透性的改变和黏膜屏障受损可能是介导FD患者内脏高敏性的重要因素[9]。最新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在维持黏膜屏障功能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胃肠道共生菌与胃肠道上皮细胞直接接触形成天然的生物屏障层,以此减少致病菌的黏附定植;另一方面,微生物通过合成和分泌多种代谢物,如SCFAs、吲哚衍生物等,在促进胃肠道黏液产生和分泌的同时,增加紧密连接蛋白和细胞骨架相关蛋白的表达,在调节上皮通透性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8-19]。除了影响黏膜屏障功能,微生物群也参与调节免疫系统的发育和功能,在先天免疫系统中起关键作用[20]。研究发现,肠道微生物区系通过激活肠上皮细胞的模式识别受体和内质网应激信号促进免疫系统的发育[21],从而促进肠上皮细胞的增殖、抗菌肽和黏液的产生,调节与免疫功能相关细胞因子的分泌,如IL-1β、IL-18和IL-25[22]。综上所述,肠道菌群失调在影响黏膜生物屏障的同时,可能也导致黏膜机械屏障、化学屏障及免疫屏障等多种屏障功能低下,并可能介导黏膜低度炎症和内脏高敏性的发生。此外,SCFAs在维持胃肠动力及肠上皮细胞形态和功能中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2.3 紊乱脑-肠轴功能 脑-肠轴功能紊乱是FD重要发病机制[16]。随着研究不断深入,越来越多证据证实肠道菌群与脑-肠轴功能密切相关[23]。一方面,肠道微生物能通过合成和释放SCFAs、次级胆汁酸和色氨酸等代谢物,与肠内分泌细胞(EECs)、肠嗜铬细胞(ECCs)相互作用,自下而上影响激活内源性中枢神经系统信号机制;另一方面,肠道微生物也可独立完成或促进某些神经活性物质的合成和分泌,如5-HT、γ-氨基丁酸、去甲肾上腺素、多巴胺等,这些小分子物质能通过与EECs、ECCs相互作用,激活肠神经系统信号机制[13]。此外,肠道菌群失调会增加LPS的产生和分泌,而LPS不仅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功能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还会促进其他炎症因子的产生,如肿瘤坏死因子-α、白细胞介素-1β、白细胞介素-6和诱导型一氧化氮合酶等,以上炎症因子可影响中枢神经系统的功能,紊乱神经肽的合成和分泌[24-25]。上述研究表明,肠道微生物群失调可能诱导脑-肠轴功能紊乱,其机制涉及神经、免疫和内分泌信号传导。
2.4 影响药物吸收代谢 药物经口服途径进入人体,不可避免地与肠道菌群发生相互作用。多项研究[26-27]表明,肠道微生物能通过编码多种酶,影响口服药物在体内的吸收、代谢、转化等过程,进而影响药物活性成分有效性和毒性。由上可知,中药经口服进入胃肠道其利用度可能受肠道菌群的影响,而中药又反过来调节肠道微生物群的组成和代谢。
3 中药调节FD肠道菌群
整体观念贯穿中医学认识人体生理病理和诊疗疾病的全过程,其中包含人体是一个有机整体的观念。肠道菌群被称为人体隐形“器官”,作为机体重要组成,其功能与宿主生理功能、疾病的发生发展密切相关。中药具有多成分、多靶点起效的特点。研究[28]证实,中药能逆转肠道菌群失调,维持肠道微生态平衡。以下分别以中药单药及其有效成分、中药复方为切入点,讨论中医药、肠道菌群与FD的关系。
3.1 中药单药及其有效成分 研究[29]表明,治疗FD的中药多以补虚药为主,其中以甘草、党参、白术为高频用药。叶清清等[30]在肠道特征菌(嗜酸乳杆菌、大肠埃希菌和粪肠球菌)的体外实验中发现,炙甘草、白术对促进嗜酸乳杆菌的增殖具有显著作用,但对大肠埃希菌的生长明显抑制,此外,炙甘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粪肠球菌增殖。刘丽莎等[31]研究表明,白术多糖对益生菌具有良好的扶植作用,其中对婴儿双歧杆菌、青春双歧杆菌、动物双歧杆菌和植物乳杆菌的促增殖效果最佳。王婷等[32]研究指出,FD大鼠肠道微生物中乳杆菌属、Ruminiclostridium9属、Alloprevotella菌属、拟杆菌属相对丰富度降低,而普氏菌科UCG-003属、普氏菌科NK3B31属、毛螺菌科NK4A136菌属、Treponema2属相对丰度增加,而麸炒枳实作用后能使肠道微生物群的失调正常化。Zhang等[33]研究证实,拟杆菌门与胃泌素的表达显著相关,疣微菌门与胆碱酯酶的表达呈高度负相关,而FD小鼠存在上述菌群失调,经神曲水提取液干预后FD小鼠肠道微生态失衡得以调整,胃容受性舒张功能和胃排空功能得到恢复,小鼠FD状态得到改善。
3.2 中药复方 香砂六君子汤是治疗FD脾虚气滞证常用方,其以四君子汤为基础。黄文武等[34]研究指出,四君子汤能显著逆转番泻叶诱导的脾虚大鼠肠道菌群多样性和结构的失调,使SCFAs产生菌的丰度显著增加,且发现方中对恢复肠道菌群的平衡起主要作用的中药可能是白术,其次为人参、茯苓。此外,胃祺饮(党参、黄芪、当归、莪术、八月札、枳壳、蒲公英等)具有健脾理气、活血和胃之效,也能有效改善脾虚气滞证FD状态。卞慧等[35]用RT-PCR技术测定FD大鼠粪便,结果表明粪便中乳酸杆菌、双歧杆菌DNA的表达量显著下降,经胃祺饮干预后,大鼠的粪便中乳酸杆菌、双歧杆菌DNA表达显著增加,其胃排空功能、小肠蠕动功能也得到改善。参苓白术散常用于治疗脾虚型FD,临床疗效确切。罗良[14]通过对肠道菌群-宿主代谢组学的研究发现,FD大鼠的SCFAs含量显著减少,经参苓白术散干预后不仅能上调SCFAs产生菌(瘤胃球菌科、毛螺菌科)相对丰度,使FD大鼠胃肠动力功能得到改善,而且能促进双歧杆菌的增殖,抑制乳酸杆菌属、黏蛋白降解菌(Mucispirillum和Akkermansia)、致病菌(肠球菌科和螺杆菌科)的生长,使菌群平衡得以重建的同时,减少细菌分泌的乳酸和内毒素,改善FD引起的腹泻及低度炎症反应。Zhang等[36]研究也证实,参苓白术散干预能使FD大鼠失衡的微生物群恢复正常,主要是抑制普氏菌属、Mucispirillum和阿克曼菌在内的FD生物标志物菌群的生长,促进SCFAs产生菌增殖,上调能量代谢途径,改善FD症状。逍遥散是治疗肝郁脾虚证的经典方。胡俊秀[37]对脾虚肝郁证FD大鼠进行研究发现,模型组大鼠粪便中厚壁菌门、变形菌门相对丰度高于正常组,且拟杆菌门的相对丰度较低,而逍遥散干预后可重建FD大鼠肠道微生态平衡。半夏泻心汤被广泛应用于FD寒热错杂证的临床治疗。梁琨等[38]的研究将半夏泻心汤分为全方组、辛开组(半夏、干姜)、苦降组(黄连、黄芩)、甘补组(人参、炙甘草、大枣),以探究各组对胃肠道菌的影响。结果发现:①全方组对幽门螺杆菌抑菌和杀菌作用最强;②各组对肠道条件致病菌(粪肠球菌、阴沟肠杆菌)均有一定抑制作用,其中全方组和苦降组对阴沟肠杆菌生长抑制效果最好,苦降组和辛开组对粪肠球菌的抑菌作用最强;③在一定浓度条件下,全方组和甘补组对肠道益生菌(青春双歧杆菌、嗜酸乳杆菌)均具有显著促增殖作用,而苦降组对益生菌的生长则表现为显著抑制作用。焦三仙(焦山楂、焦麦芽和焦神曲)具有健脾开胃、消积化滞的功效,也是治疗FD的常用药。Liu等[39]运用16S rRNA测序技术对FD大鼠肠道微生物群进行研究后发现,焦三仙汤能逆转FD大鼠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比值的显著下降,扶植益生菌生长,抑制病原菌增殖,改善肠道菌群紊乱,并调节脑肠肽的分泌,改善FD状态。此外,杨柳烟[40]的研究指出,调中健脾汤(炒枳壳、陈皮、白芍、姜半夏、白术、党参、鸡内金、神曲、佛手、丹参、柴胡、灸甘草)能扶植益生菌双歧杆菌、乳酸杆菌生长,抑制条件致病菌肠球菌、酵母菌增殖,并上调胃泌素、胃动素水平,改善胃肠动力。
4 小 结
目前,中医药对FD肠道菌群的研究仍处于探索阶段。大量的研究证实,FD肠道微生物群存在多样性、结构、丰度及分布异常,而FD的发生发展与哪些特定的菌群密切相关尚未有统一定论。现有的研究认为,肠道菌群主要通过影响胃肠动力、破坏胃肠道屏障功能和免疫功能、紊乱脑-肠轴功能及影响药物吸收代谢等机制参与FD的发生发展,但上述机制缺乏具体通路及靶点的直接证据,还有待进一步研究证实。
肠道微生物群和中药成分具有多样性、复杂性的共同特征,本文就中药单药及其有效成分、中药复方调节FD肠道微生物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分析后发现,中药可通过扶植益生菌生长、抑制有害菌繁殖,使FD紊乱的肠道微生物群恢复平衡。但中医药对FD肠道菌群的研究尚有许多不足之处。第一,中医药对FD肠道菌群的研究仍然较少,仅少数中药单药、中药复方对FD肠道微生物的影响得到初步探索,且现有的研究多局限在动物实验和体外细胞实验,缺乏临床试验验证。因此,更多的中药单药和复方对FD肠道菌群的影响有待探索,也需大规模的临床随机对照试验加以验证。第二,辨病与辨证相结合是中医诊疗疾病的基础,但目前缺乏符合中医证型的FD动物模型,FD证候与肠道菌群间缺乏充分研究。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在建立统一客观评价标准的实验模型基础上,探索肠道菌群变化规律与FD证候之间的关系,明确不同证型FD的特征性肠道菌群谱及代谢物。同时,中药复方的研究应与不同FD证型辨证结合,有助于临床对不同证型FD的个性化菌群干预。第三,中医药具有多成分、多靶点和多途径的优势,现有研究仅停留在观察中药干预对肠道菌群多样性、结构和丰度改变的层面,尚未对其具体机制进行阐释。因此,为更充分阐明中医药对FD肠道微生物群的作用,今后的研究应致力于对具体作用机制和靶点进行深入研究,这也有利于筛选对恢复FD肠道菌群平衡更具针对性作用的中药单药及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