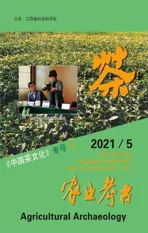晚清广东的茶叶技术与茶产业*
2021-11-04唐元平吴建新
唐元平 吴建新
清代广东并不是茶的重要产地,却是中国茶产业的重要地区。在鸦片战争以前,广州是唯一对外贸易港口,各地出口的茶都运到广州来加工出口或直接出口,故广州形成了本地茶和外地茶并存出口的局面。直至晚清,广州对外贸易的商品中茶仍然占据了重要地位。本文试图分析晚清广东的茶叶技术的情况,进而讨论广州茶产业在中国茶产业中的地位,以及广东茶叶技术与茶产业之间的关系。
一、晚清广东的茶叶技术
(一)产茶地
粤北茶:尽管在唐代陆羽《茶经》中已有提及粤北韶州的茶,但最终没有成为名茶。晚清时,《韶州府志》提到英德县产于产罗坑、大铺、乌泥坑的茶,“色红味醇,经宿不变”,也提到乐昌茶和南华茶[1](卷11),不过产量都不高。清代后期,南雄府的始兴县有一些村庄附近的山地改变了虎狼出没的现象,出现“沿村竞种茶”的景象[2](卷11)。清远县“茶以笔架山为最,黄藤峡次之,文峒坝仔又次之”[3](卷2)。后来文献中提到的出口茶只有英德和清远两地。
粤西茶:主要是肇庆府属县的茶。早在明代“鼎湖山……绕寺产佳茗”[4](卷8)。鼎湖山茶与南华茶一样都是寺庙茶,没有大规模生产。但高要、高明等县产茶较多,“茶,所在近山居之皆成树。此乐昌茶种也。高明植者作茶芥,称冷茶”[4](卷10)。清乾隆年间,鹤山茶引入西樵茶种和栽培法,至道光年间产茶地逐渐扩大,“自海口直至附城,毋论土著、客家,多以茶为业”[5](卷2下)。大雁山(鹤山名胜,跨鹤山、新会两县)“宜茶,来往采茶者相继不绝”[5](卷2下)。
粤东茶:罗浮山茶在唐宋文献中曾有记载。清代中叶,河源的“上管、康禾诸约居人,生计多半赖此”[6](卷11)。每年春夏之间,以及霜降之时,茶商就来买茶回去加工。河源桂山有野生茶,但产量不多。潮州附近有待诏茶,一度很有名,但产量不大。清康熙年间,饶平县的百花、凤凰山多有人工茶,但因为“采抄不得法,以致苦涩”[7](卷11)。晚清时有茶商传入制茶法,“近于饶中百花、凤凰山多有之”[8](卷11)。故凤凰山单丛茶大约从晚清时兴起。
粤中茶:主要是广州河南茶和西樵山茶。大规模种植是在明清时期。广州河南地多平衍,惟有些小山岗,清代屈大均谓此地茶生于“阳崖阴林之间”[9](卷14),可见当时的小山岗植被很好,茶生其间,“嫩芽紫笋”采之用作熏花茶,风味独特,大多供应广州城内茶楼。
(二)制茶法
广东本地的茶,由于缺乏定向栽培,故不少山茶都没有发展成为著名品种。能成为名茶的,大多是外省茶种传入。如著名的西樵山茶叶,传说是因唐末诗人曹松寓居于此。晚唐时岭北诗人曹松到了西樵山,将顾渚茶传播到西樵山。宋元大量移民迁徙珠江三角洲时,西樵茶开始出名,到明清时期是著名的茶品种,并多见于本地士大夫的茶诗歌中,其栽培法、采摘法、制茶法见于《广东新语》《西樵山游览记》以及《南海县志》等文献[10]。西樵茶园间作苦登莫、蝇树,是典型的生态茶园,并传播到鹤山等地[11](P67-68)。
广东的制茶法亦深受岭北产茶区的影响,特别是晚清时期,广东茶商从产茶区采购茶叶之外,还引进了外省茶区的制茶法。如番禺张氏的先祖张殿铨,清道光间人,寓居苏州,与安徽、浙江的茶商有联系。他将安徽的正皮珠、雨松萝两种茶的制作法带回广东,在十三行开茶行,为其工者多族人。张殿铨与族人由此致富,并将安徽来的茶全部买入。西洋商人闻其名,“争相采办”,十三行的茶商“是始叹服”[12]。
福建的武夷茶以“松萝茶”的炒制法出名。有人认为它是传统茶法的第三代技术,其特点是能将茶叶的苦涩去除,可以是乌龙茶或红茶,是一种发酵法。明代后期广东和福建都有了发酵茶。这种茶香味浓郁,更容易被人们接受,并且为中国茶叶打开了国际市场[13](P91-92)。广东有这种茶法,当是外地茶商或广州茶商传入。
光绪三年(1877)出版的岭南胡秉枢著的《茶务佥载》,该书大致可以反映清代岭南的种茶、制茶的技术水平。彭世奖认为其法针对欧美洋人的嗜好,增加了一些新的内容,可以说是一本讲述制作外销茶的茶书。《茶务佥载》认为出口的绿茶必须用滑石粉和干洋靛,每百斤茶要添加靛、滑石粉各八九两。书中指出二者有药用功能,于人体无害[14](P75-77)。在茶叶中添加这些异物,不见于其他古代茶书,当是清代广东茶业制作的新方法。但这其实是晚清广东茶制作法的误区。
广州外销画中茶叶制茶和包装茶叶的情景,反应了制茶场盛况[15](P125-128)。鸦片战争之后,广州茶的出产大增,以河南茶行最多。晚清陈坤的诗有注解云:“粤省河南地方,商贾辐辏,贫家妇女多往拣茶以资糊口。”[16](卷4)茶商将广州产的茉莉花、外地产的干菊,香烈异常的鱼子兰、树兰加入茶叶中,制成“花熏茶”(海关报告中亦称熏花茶),如清人有诗云:“酒杂槟榔醉,茶匀茉莉香。”[17](P306)“花熏茶”是将素馨、茉莉的干花窨入茶叶中,如明代陈献章的文章中记:“取花之蓓蕾者,与茗之佳者杂而贮之。又于月露之下,掇其最芬馥者置陶瓶中,经宿而俟茗饮之人焉。”[18](卷1)素馨、茉莉等香花种植广泛,所以“花熏茶”是岭南茶的独特优势。
江南茶叶的制作技术对岭南茶也有影响,“高要顶湖山茶,得制法于吴越,香色将与松萝龙井等,而味颇薄劣”[19](卷10)。其实西樵茶和河南茶的茶种和制作法也来自岭北。但是茶叶的制作方法限制了一些新茶区的发展,也制约着广州口岸的茶产业,从而对中国茶产业产生重大影响。
二、晚清广州的茶产业
产业的概念发展到今天,已经不专指生产领域,而是包括了技术、生产、经营、销售、服务等综合一体的方面。以下就从这一角度探讨晚清广州的茶产业。
(一)茶叶出口
广州茶产业从清乾隆年开始腾飞,乾隆二十二年(1757)通商口岸仅限广州一地后,广州成为我国唯一的茶叶出口商港。鸦片战争前夕,广州出口茶叶约在45万担左右[20](P22-23)。自嘉庆二十二年到道光十三年(1817—1833),广州出口茶叶货值193132325银元,占出口总货值318301541银元的64%,超过丝绸。鸦片战争以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广东茶叶出口货值仍占出口总货值的74.149%。咸丰元年(1851),广州出口茶422040000磅,占全国茶叶出口总量的53.5%[21](P81-82)。
但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广州茶出口量开始呈下降趋势。从表1可以看出,1860—1861年间,广州出口茶还保持平均每年26万担以上的数量,1863年下降到8万担,1864年稍有回升,但仍达不到20万担水平。1866年数量急剧下降,跌破十万担,以后在十万担上下徘徊,只有个别年份如1878年出口达16万担、1879年达17万担。可见,晚清广州茶出口总态势是下降的。

表1 1860-1888年广州口岸红茶、绿茶出口数量合计(单位:担)
(二)广州口岸茶的来源
广州茶产业分为内销和外销两部分。内销主要是本地茶以及外省茶。广州不是内销茶的集散地,而是佛山。佛山的茶叶外来之品有乌龙、水仙、龙井、六安、香片、普洱、红茶等,但是销量不大。大宗的内销产品来自清远、古劳、罗定等处。然后销往广西各地[22](卷6)。
广州口岸外销茶来源之一为西樵山茶。没有资料能说明西樵山茶产量,但广州本地的诗人在诗文中经常提到。西樵山茶主要供广州中上层人士消费,即使有出口数量也不是很大。河南茶在清初还有很好的评价,但在晚清的方志中开始评价说河南茶味道劣,只供下层民众消费。广州口岸外销茶来源还有英德、清远、鹤山、河源等县所产茶,具体数量不太清楚,不过从文献看,广东本地茶远远不能满足广州口岸出口茶的需求。在鸦片战争之前,广东茶商主要从外省茶区买入茶叶,以增加出口货源。晚清面临其他口岸的竞争,广东茶商就从省外茶区调入茶叶以增加出口量。这在文献上多有记载,举例如下。
湖北。晚清汉口有广东公所,为当地六帮公所之一,专办红茶销往西方国家,每年采茶季节,粤商令茶农“采细叶暴日中,揉之,不用火炒,雨天用炭火烘干,贮以枫柳木作箱,内包锡皮,给外箱卖之,名红茶。箱皆用印锡,以嘉名茶”[23](卷4)。刘正刚认为广东商人在20世纪初之前就控制了汉口所有的对外贸易[24](P319),确有道理。
湖南。广东商人以湖南湘潭为中心展开茶叶贸易,有专门从事茶叶生意的“广帮”。光绪《湘潭县志》记载:“海禁开后,红茶为大……专恃湘潭通岭南。”[25](卷11)湖南其他县也有粤商前往当地收购茶叶的记载。如祁阳,“粤之人,牵车架船,亦多萃集,贸迁有无,各得其所”[26](卷2)。
福建。福州有广东会馆,收购茶叶的粤商很多。海关十年报告(1882—1901)记载了福州广东会馆章程中的“一些引人注目的附则”,规定了广东买办替洋行购茶、买办本人购买茶叶、经纪人购买茶叶、向洋行出售茶叶都要按规定向广东会馆捐纳不等的银钱[27](P644-645)。茶叶是广东帮商人在福州经营的主要商品[24](P336)。清代福建茶业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广州是这个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广州外销画中,有茶叶加工场的画面。广州河南有不少加工场。除了上文提及的陈坤写有诗作,鸦片战争以后,英国驻广州副领事摩里逊描述了广州河南茶叶加工场的盛况:“很多大的茶行就在眼前,据向导说这正是我们要访问的对象。这些茶行都是宏大而宽敞的两层楼的建筑,下层堆满了茶叶和操作工具,上层挤满了上百的妇女和小孩从事拣茶和把茶分为各种各类的工作。”[28](P485-486)河南茶场制作的主要是花薰茶。花薰茶被统计入红茶中,它在全部出口茶中占有重要比例,1877年的海关报告中说:“广州出口的红茶大部分是经过熏香的”,花薰茶占全部红茶出口总数的60.24%[29](P194)。晚清出现一种所谓“新制功夫茶”,又叫“大山功夫茶”,“是由一种长叶捻制而成的,主要产于(外省)大山和(广东)鹤山地区。以后仿制福州功夫茶制法,而名之为‘新制功夫茶’”[29](P96)。除了广州茶场制作功夫茶,澳门茶行雇佣低价劳动力收购乡下的平价茶,就地加工成功夫茶出口。
(三)广州茶产业的购销体制
清代中国茶业的购销体制非常复杂。首先是茶贩深入茶山直接收购毛茶,转让给茶商或者茶庄。茶贩一般无专门职业,或受雇于茶庄。其次是茶庄,一般设在茶叶产地的中心地区。第三是在广州的茶商或批发商。外地茶入广州,先售给广州茶商变现。闽茶一般由水路运到广州,出售给广州的行商。第四是在广州的行商,也就是十三行的行商[30](P575)。这只是简略地勾勒广州茶的购销链条,情况可能还更复杂。全国各地茶区茶叶交易过程中,“存在非常复杂的关系,无论内销或外销都必须经过无数道中间环节才能最后完成交易手续”[31](P44)。
行商是茶外销链条中的顶端。行商要获得茶叶,必须资金雄厚。外省茶商到,要先付钱才拿到货,如果委托茶商或茶贩,还要先行垫付资金,或可以贷款给其他茶行,从其他茶行拿货,以增加自己的存货。如上文提到的番禺隆记洋行,“各行商凡贷隆记银者总数恒至数十万”[12]。洋行贷款给客户虽然获得资金利息收入,但也面临收不到本息的风险。而且如果出口茶被外商退货则成为“废茶”,洋行还要先行赔付外商。自乾隆四十八年东印度公司退回废茶1402箱,由十三行中的同文行垫付赔偿10000元,从此,废茶退赔由行商负责成为惯例[21](P267)。
三、晚清广州茶产业的衰落
晚清国际市场上茶叶价格下跌,导致国内茶业一落千丈,西樵山茶业也不可避免走向衰落。南海县官山墟市原有茶市,西樵茶农多往此地交易。西樵山因为一向被广府人认为是风水宝地,茶园所有者为谋生计,多将茶园售作墓地。清末时,西樵山上的茶园几乎全部被出卖为墓地。南海官山墟上卖茶的店铺全部关闭[32](卷4)。关于近代中国茶业出口衰落的原因,前人叙述多矣,如认为印度茶和锡兰(斯里兰卡)茶兴起,采用规模化种植和机器制茶,质量是传统制法的中国茶不能比拟的。但这仅是外部原因,如果从茶叶品质、制度与茶产业之间的关系来说,这个问题还有探讨的空间。
(一)晚清出口茶叶品质下降
早期广州茶由于其质量好,一度占出口茶的重要地位。1816年,美国“对于中国货物的征税额比早年多百分之二十至四十,仍对美国船只直接由广州运来的货物保持优惠待遇”[33]。可见19世纪早期,外商对广州茶的质量是满意的。至晚清广州口岸茶质量迅速下降,与茶树种植技术差以及原料、制作技术走下坡路有很大关系。此种情况,屡见于粤海关报告中。如1844—1885年报告称:“无论功夫茶和花茶,质量仍均较差,外地甚至本地客户都抱怨茶农对茶树关心不如往年,致使茶叶质量变坏,年复一年。”[29](P286)花茶和功夫茶,在1888年有9.4万担出口,1889年减少至7.8万担。1891年,“所出茶叶,其货质不如上年”[29](P324)。1892年,花茶等“出产尚属中平,惟下等茶碎末太多,制法亦不尽善”,华商“尽已亏本”[29](P333)。1894年,“茶叶由洋船出口者,依然跌落”。1896年,“茶叶一项……俱云不佳”[29](P362)。
熏香茶本来是广州茶的拳头产品,但是由于后来花的香味不足,使熏香茶质量下降,如1900年,“本年花香茶所有春造好景,俱被印度、锡兰两处下等茶搀夺净,日渐减少……本省花味甚劣,熏出之茶无香”[29](P404)。广东本地最畅销海外的古劳茶都是供给海外华侨的,如1903年,“茶出口与上年相等……古劳茶出口不少,俱往外国各埠,以供华人购用者”[29](P420)。花的香味不足可能与广州近郊的地力下降或施肥不足有关。宣统末年,广东农林试验场用正常的农家方法种植水稻,一造亩产有380斤。而附近农家一亩的收获量,一般300斤,最多也只有320—330斤[34](P47)。花圃和水田一样,施肥不足会导致花卉香味不足。花香不足,熏香茶的味道就薄了。
(二)购销体制滞后
在茶的制作过程中,掺杂是导致茶质量下降的重要原因。不少年份的粤海关报告指出这个问题。本来海外对广州高级“功夫茶”“需求甚殷”,但1844—1885年因为质量很差而滞销,掺杂物还有旧茶叶[29](P286)。1904年,“茶务已成江河日下之势,渐臻腐败,因业此者未知茶叶以质佳洁者为贵”,甚至全批茶叶因为掺杂铁屑、泥沙被拒入口[29](P428)。1905年,从省城出口到伦敦的茶叶“似澌减殆尽”[29](P438)。
绿茶的衰落早于红茶和熏香茶。自1872年以后,绿茶数量在逐渐减少。甚至有人说,从1873—1874年广州出口的绿茶包中可闻到臭味,茶的色泽太深,混有铁屑,用磁铁可以吸出来。由此贸易相应地转向死胡同,似乎陷于停顿状态[29](P192)。可见茶叶中的“掺杂”,包括加入滑石粉、洋靛,本地茶工以为是创新,殊不知到了外国市场则被认为是掺杂泥土和异物。外商认为“茶的色泽太深”,这是因为添加洋靛,是茶叶制作过程中的问题。但加入铁屑和非滑石粉的泥土,又是谁做的呢?笔者认为不是茶农,也不会是茶商、茶行和洋行,而极可能是茶贩。茶贩无正当职业,以茶叶重量和数量获得佣金收入,加入铁屑和非滑石粉的泥土,只要在交货时不被检查到就可以增加收入。
那么,为什么在数十年间这个问题一直不能解决?在这方面,行商要负很大责任。在外贸茶中,十三行茶商占有很大的出口份额,如怡和行在1793年到1833年中,每年与东印度公司的茶叶贸易额从10000担到30000担之间。广利行的数量比怡和洋行少些,但也在10000—20000担之间[21](P274-276,279-280)。十三行商人是主要的茶叶贸易商,还要负担起赔付废茶的经济责任,但却不负责检查茶叶质量。在如此复杂的购销环节中,茶叶销售的终端却不建立起产品出口的质量标准和检验制度,致使茶叶“掺杂”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这是晚清出口茶衰落的重要原因。
关于印度茶、锡兰茶的兴起对中国出口茶的不利影响,晚清粤海关官员已指出。印度的茶园,“内有千株万株之茶树”,从种茶到完成销售,“皆一事主,皆一事权”,茶属上等且价廉。反观中国茶,“于此各节正全属相反,以致色低而价昂”[29](P312)。粤海关建议中国茶界进行产、供销的全面改良。然而终清一代始终未解决这个问题。
四、晚清广州茶产业衰落的当代启示
晚清广州茶产业衰落对当代的启示不仅是区域性的,而且是全国性的。如何振兴广东乃至全国的茶产业,有不少学者做了探讨。如从茶文化产业的旅游文化结合、生态农业等方面提出了见解,也有人从茶产业这个角度写了研究报告[35](P200-206)。笔者以为可以从“全产业链”的角度去探索这一问题。茶产业不仅要内循环,还需要“外循环”,两者都需要订立严格的符合国际惯例的质量标准。
第一,依赖于独特资源的新产品仍然能在市场独占一席地位,但当资源禀赋消失时,新产品仍然会衰落。晚清广东的茶叶生产技术比岭北诸产茶区落后,不过由于有独特的花卉资源,利用茉莉等芳香原料,制成的熏香茶一度风靡海外。但当花卉质量下降时,或者是用低档茶窨香花,广州熏香茶亦随之衰落。
第二,面对个体化的小农,农产品的检验制度、标准化首先要建立在产业制度变革的基础上。晚清的松散而无效率、无购销目标的茶叶购销体制决定其数十年茶品质量走下坡路。只有在近代农业兴起才重视这个问题,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才逐步解决这一问题。如何将分散的小微茶企业通过规则和购销体制整合为大的茶产业品牌,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大问题。
第三,历史上一些传统茶叶技术应被视为农业遗产而予以重视,如西樵山的茶树与蝇树的间作,是生态茶园的一种形式,应用现代茶叶科技对这种生态茶园进一步研究而加以推广,利用生态除虫技术是减少茶叶农药残留量的有效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