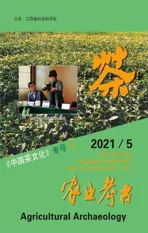辽代西京道忽洞坝墓葬出土茶具的多元文化审视*
2021-11-04李彦颉
张 磊 李彦颉
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对茶叶情有独钟,谚语“宁可三日无粮,不可一日无茶”就是游牧民族茶饮状态的生动写照。北方游牧民族本无饮茶习俗,《新唐书》为陆羽作传时言及:“其后尚茶成风,时回鹘入朝,始驱马市茶。”[1](卷196《陆羽传》,P5612)茶马贸易的繁盛表明唐代中期茶饮习俗已逐渐被北方游牧民族所接受。契丹在唐朝时期主要居于北方草原地区东部,活动于西拉木伦河流域,由于气候缘故该地区本身不产茶叶,其茶的来源全自于中原和南方地区。下迄辽代,饮茶之风盛极一时,辽墓壁画中形象生动地展现了辽人饮茶的场景,以宣化辽壁画墓为例,墓室中基本都绘有《备茶图》,其中M10前室东壁《备茶图》[2](P31)中展示了碾茶、烹茶、饮茶等茶事的全过程①,茶具有茶碾、茶壶、茶杯、茶盏、盏托,足见过程之考究,茶具之多样。
辽代丰富的茶具形制,为透过茶具考察辽茶文化的多元属性以及区域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从材质的角度对辽代茶具进行分类,主要有金银器与陶瓷器,其中金银质茶具在形制及纹饰上自成体系,有别于陶瓷质地的茶具。西京道为辽代五道之一,主要辖今山西北部、内蒙古南部以及河北西北部地区,以往的考古发掘工作中,大同市东风里辽代壁画墓东壁壁画“侍酒散乐图”(图1)前排一侍者手端托盘,盘内所置两盏为饮茶所用[3];出土的饮茶器具实物主要有大同市马家堡辽墓出土透明釉圆口盏[4]、呼和浩特市脑包沟辽墓出土白釉圆口盏[5]以及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卓资县忽洞坝墓葬出土的一对银质茶盏及盏托[6]。值得注意的是,忽洞坝墓葬出土的这套盏及盏托为辽代西京道地区首次出土的银质茶具,文化意义不言而喻。鉴于此,本文从内蒙古忽洞坝辽墓出土的这组银质饮茶具入手,将其置于同类器具中进行对比考察;同时以茶为“媒”,着重探究忽洞坝墓葬出土茶具背后的多元文化因素及其区域缘由,进而对区域视野下农牧交错与草原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现象进行深层次观察。
一、忽洞坝与辽代银质饮茶器出土情况
1980年,内蒙古卓资县碌碡坪乡忽洞坝村南端的一座辽墓中出土一批金银器,其中一套银质茶具以其独特的造型、精湛的制作技艺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这套茶具包含盏托1件、茶盏2件,盏托高3.6、口径15.0、圈足高2.2厘米,综合运用了锤鍱、錾刻、浮雕、线雕等技术,制作工艺臻于成熟(图2);茶盏高3.0、口径7.2、底径3.6厘米,锤鍱成型,器形为侈口五瓣花形(图3)[6]。在目前出土的辽代茶具中,银质茶具较为少见,忽洞坝墓葬出土的这套盏及盏托,是目前辽代西京道地区发现的唯一银质茶具。
银质茶具属于银质饮食器的一种,为银器大宗。根据王春燕《辽代金银器研究》的成果,辽代银质茶具的组合有两类,一为碗加盘,一为壶加盏托[7](P79)。实际上,作为饮茶器具,盏托与盏一般需要组合使用。除忽洞坝遗址出土银质茶具,一览辽代银质饮茶器的出土情形,从次页表1、表2可以看出,多数银质盏(杯)及盏托都发现于辽代东、中部,即今天的辽宁西部、内蒙古东部以及河北北部一带。与表1、表2所示辽代其他地区发现的盏(杯)及盏托相比,忽洞坝墓葬出土的盏及盏托规制略小,外形朴素,形制和纹饰均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区域的显著特征,因此分析器物背后的文化因素及缘由有一定必要性。

表1 辽代银质盏(杯)②出土情况

表2 辽代银质盏托出土情况
二、忽洞坝辽代银质茶具的多元特征
忽洞坝辽墓的这套茶器既属于特色鲜明的契丹银器,又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文化谱系而颇有韵致。具体而言,其独特性主要体现在:
(一)大唐遗韵——唐文化元素
盏托又名茶托、茶船等,晚唐时期李匡乂的《资暇集》记载蜀相崔宁之女在奉茶时“以茶杯无衬,病其熨指,取碟子承之”[17](P163),其中“碟子”即为文献中有关盏托的最早记载。唐代早、中期盏托一般饰有繁复的花纹,内托较低矮,唐中期至两宋时期内托不断增高,到宋代时流行高台式的盏托,立体感增强,以至于“有的托子本身就仿佛是盘子上加了一只小碗”[18]。受宋影响,辽代盏托一般内托高出托盘,如辽陈国公主驸马合葬墓、朝阳沟M2辽墓等出土盏托均与宋器形保持一致,是辽宋时期盏托形制的典型代表。忽洞坝盏托并非辽代典型盏托形制,其内托几乎与托盘齐平,且盏托上纹饰精美,雕刻立体,与唐代盏托相似,具有唐代遗风。
忽洞坝出土茶盏素面简朴,盏腹有四条短曲线将茶盏分成五瓣花形。张景明谈及茶盏器形特点时认为,唐代典型器一般以一条浅折棱将茶盏进行分曲,折线自然朴素,互不相连,以四、五、六曲花瓣形最为常见[19](P346)。忽洞坝茶盏口形、曲线均与唐代茶盏器型风格一脉相承。
总之,忽洞坝茶盏及盏托具有浓郁的唐代器形特征,推测其应该是受唐文化影响较深的银质饮茶器具。
(二)茶酒同器——草原文化元素
辽代所处的北方草原,冬季寒冷漫长,饮酒并非仅仅为了娱乐,更有驱寒蓄热的实用价值,而茶对于契丹人也是为了帮助消化油脂类食物,两个具有同等重要作用的饮品,契丹人需要经常饮用。辽代盏及盏托的实用性相较于宋朝来说要强得多,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茶、酒同用显得必要且合理。
盏在产生之初既是酒器也是茶器,到唐代末期才逐渐固定成为茶器的专属,两宋时期盏为饮茶器基本成为定制。与宋代情形不同的是,辽代茶盏重实用,茶、酒具难分,《辽史》中记载大臣进酒时“执台盏进酒,皇帝、皇后受盏”[20](卷53《兴宗二》,P870),表明辽代在盛大的典礼上用盏作为饮酒器的习俗仍然存在。从形制上看,忽洞坝出土茶盏属于侈口花瓣形式,区别于纯粹用于饮茶的斗笠式大盏和黑釉盏,一器两用的可能性较大。
辽代多样化的温酒方式,为盏托的普遍使用提供了可能。第一种方式是用温碗盛热水后,将装有酒的执壶浸入温碗,用物理热传递的方法加温,操作起来简单快捷,朝阳商家沟M1、喀左北岭辽墓M1、M4均发现有专门用于温酒的温碗。第二种方式为直接将装有酒的酒瓶放到炭火上加热,见于敖汉旗羊山M3的“火盆温酒图”[21],图中绘有火盆、红炭以及长颈瓶。契丹地处我国北方草原,冬季漫长而夏季短暂,气候寒冷而凛冽多风,对温酒的需求更加强烈,尤其是上述提到的第二种温酒方式,具有较强的民族特色。大火温酒对酒温也不好把控,温度过高是常有的事,这为盏托的使用提供了可能。忽洞坝墓葬出土盏托盘大而平坦,实用性较强,置茶置酒均可。
辽代西京道用盏饮酒的情况并非个例。虽然有学者认为烹茶与温酒的方式完全不同,温酒一般是用热水间接加温,所以酒温一般并不会太烫,不必像喝茶一样需要较高的足[18],然而辽代西京道地区已有考古成果表明高足类器具亦可用于盛酒。大同东风里辽墓中发现一对影青高足碗[3],六曲花瓣口,敞口高足,形制与盏几乎无异,仅口径较一般盏略宽,刘贵斌认为此类盏和碗可以互称[22]。大同东风里辽墓的影青高足碗是典型的饮酒器,而忽洞坝出土的茶盏足部狭高且瘦长,二者同出于辽西京地区,推测高足应该是此地饮酒器的一大特征。
(三)东西融合——域外文化元素
从忽洞坝墓葬出土盏托的制作工艺来看,盏盘与盏底是分开制作的,分别成形后再进行錾刻浮雕,最后焊接成形,盏盘四周饰有五条折线,使得成形后的盏托呈五瓣花形,俯看尤为明显。整体而言,忽洞坝盏托轻而薄,锤鍱与錾刻高度统一,工艺臻于成熟,具有盛唐制作工艺遗风。纹饰方面,其形成了三个圈层的浮雕图案:
第一,最外层等距离錾刻五支团花,一花连二叶,叶片略曲,团花之间的空隙錾刻莲瓣,纹饰卷曲而圆润,营造出一种繁华富贵的气息。相似纹饰还见于内蒙古克什克腾旗二八地M1金花银碗、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金花银碗等,团花纹饰是辽代早期最常见的纹饰之一。
第二,中间层以向外不规则的水花作为底衬,等距离刻有三条游鱼。鱼嘴微张,鱼尾分开,作游动状,显得活灵活现。鱼纹在唐代较为常见,如陕西耀县柳林背阴村出土的鱼纹羽觞、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出土的双鱼飞雁银浅盘等。鱼谐音“馀”,寓意美好,稍有不同的是唐代鱼纹一般以双鱼出现,而忽洞坝盏托底部鱼纹为三条,有可能是纹饰演变的结果或文化差异所致。
第三,最内层盏托中央点缀两条首尾相接的摩羯,双摩羯戏珠而彼此竞逐,呈现出动态之美。摩羯本为水中凸鼻獠牙的异兽,源于印度神话,经由佛教传入中国。唐末五代时期,摩羯纹在北方草原地区盛行,内蒙古科尔沁左翼后旗吐尔基山辽墓出土的银盆,底部亦为双摩羯戏珠,图案与忽洞坝盏托类似。
与盏托相比,忽洞坝墓葬出土茶盏显得大方而朴素。茶盏以花形为构思,盏口似五花瓣向外伸展,呈花朵盛开状。值得注意的是,多瓣形器原本源于粟特银器,忽洞坝茶盏与上述所述的盏托均为五瓣花形,一方面充分证明二者为成套茶具无疑,另一方面也是对金银器分瓣花形工艺的继承与发展。
忽洞坝茶盏及盏托做工精巧而朴素大方,錾刻细密而新颖别致,精心布局又寓意深刻,呈现出一种流畅美、动态美及和谐美,即便不作为实用器具,也是一件精美的摆件,具备一定的观赏价值。其中,摩羯纹为印度佛教文化的典型元素,多瓣形源于粟特文化同时又有所发展,多重域外文化同唐文化元素相互交融,彰显出辽代西京道地区较为独特的文化风貌。
三、忽洞坝墓葬茶具多元文化形成的区域缘由
忽洞坝墓葬出土茶具展现出的多元文化特征不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辽代茶饮礼俗的嬗变,更透露出辽西京一带在文明交流上的区位优势。地处“十字路口”式的文明辐辏地带,是忽洞坝墓葬出土茶具多元特色的区域缘由,具体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分析:
(一)农牧交错带——南北文化荟萃
忽洞坝墓葬处在阴山以南,阴山自古以来就是一条重要的地理界线。阴山北部是茫茫的草原与沙漠景观,南部零星分布有河流、湖泊以及高矮不一的植被景观。韩茂莉在《辽金农业地理》一书中用以区分游牧区与半农半牧区的重要地理界线即为阴山——燕山一线[23](P140)。
忽洞坝墓葬以南地区的另一关键标识为长城。正如拉铁摩尔所说,长城“是环境分界线上社会影响的产物”[24](P25),长城一般具有明显的界限属性,因而围绕长城形成了广狭不一的长城文化带。具体而言,长城一般位于高原地貌与平原地貌、中温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区域;其经济生产方式有一定的交叉过渡性,既有与草原环境相适应的游牧经济形态,又有与平原地貌相适应的农耕经济形态[25]。有辽一代,汉长城已经成为辽的内长城而不具备军事防御功能,但其农业生产方式的标示作用依旧显著,《辽史》记载:“长城以南,多雨多暑,其人耕稼以食。”[20](卷32《营卫志中》,P373)辽境内长城南北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人文景观。
考古与文献中的相关线索表明忽洞坝墓葬所处的西京道农业较为发达。距忽洞坝墓葬不远且几乎处在同一纬度上的天镇县夏家沟辽墓,出土了不少铁农具,如铡刀、车辖等,铁农具的广泛使用昭示出这一带农耕经济的活跃[26]。另外,《辽史》中载有诏命西京赈灾的记录也从侧面反映出该区域的农业发展情况,如“以东京、平州旱、蝗,诏振之”[20](卷10《圣宗一》,P111)。总体而言,辽代有五个行道,按照自然经济大致可以划分为以畜牧业为主、农业为辅的上京道,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的南京道和西京道,半农半牧的中京道[27]。
需要注意的是,即便反映辽西京地区农业发展情况的资料甚多,也不能过分夸大这一区域的农业承载性。美国学者魏特夫《辽代社会史》认为辽王朝虽然对中国本土取得了政治上、军事上的胜利,也吸收了大量的中原文化,但是他们没有因 此 改 变 传 统 的 游 牧 生 活[28](P5)。辽 王 朝 素 来 是以“行国”为基本特征的游牧国家,而行国政治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以畜牧业为经济依托,因此,虽然西京道地区以农业为主、畜牧业为辅,但畜牧业仍居于主体地位。由于自然条件所限,西京道地区的农作物大部分为一年一熟,农作物产量较低,只有农业和畜牧业结合,才符合自然条件以及当时的社会政治实际。
一定的生产方式孕育出一定的文化特色,如果生产方式没有发生变化,生活习俗一般不会轻易改变。韩茂莉认为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经济方式、文化习俗相当稳定,若没有强烈的异质文化冲击则轻易不会改变[23](P1-12)。可以说,忽洞坝出土茶具的文化多元性恰恰反映出西京道地区生产生活方式的多元嬗变,同时也揭露出这一区域多重文化碰撞、交融的局面。
随着农牧界限的逐渐模糊,在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逐渐强化过程中,榷场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榷场是宋辽金元时期一种特殊的交易场所,一般为敌对的两国在接界地所设。辽对宋设置的榷场主要集中在燕云十六州中南部,比较大的榷场有朔州城南榷场(今山西朔州城区)、振武军榷场(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永清榷场(今河北廊坊永清县)等,其中振武军榷场在大同府的西北侧,距忽洞坝墓葬直线距离约60公里,榷场经济的繁荣势必对这一带农牧文化的交流产生推动作用。
忽洞坝墓葬出土茶具的多元特征恰昭示出上述由经济生产方式嬗变以及南北贸易交流而带来的变化。如图4所示,忽洞坝墓葬地处农牧交错带的北缘,南北人口、财货的频繁沟通与交流构成了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之一。忽洞坝银器与唐代耀州银器在器形上高度相似,即是南北文化沟通强有力的证明。不同于辽代腹地的是,忽洞坝处于与宋对峙的前沿地区,生产方式上可农可牧,容易形成多民族人口聚集繁衍与多重文化和谐共生的局面。忽洞坝与耀州出土茶具分别代表了关中地区以及黄河以北地区两个文化区的同质文化因素,在文化传播的顺序上究竟是自南向北还是自北向南,这背后涉及更深层次的文化传播理论,需要更多同时期文化交流的遗迹予以说明,但无论如何,南北文化的交流是确定无疑的。
(二)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文化辐辏
辽代草原丝绸之路极其畅通,东西交往络绎不绝,逐渐形成了南北两线。北线是从辽上京(今内蒙古巴林左旗)行至漠北,再向西,经中亚、西亚地区抵达欧洲;南线是从中京(今内蒙古宁城县)或南京(今北京市)出发,经西京(今山西大同市)沿阴山以南地区过今集宁、呼和浩特等地,折转向北与北线会合[35]。草原丝绸之路是长期以来地理环境自然选择的结果,是一条经贸交流之路,更是东西方文化沟通的重要桥梁。忽洞坝墓葬处于辽代控制下草原丝绸之路南线的必经之地,其地商贸、文化繁盛。
辽通过草原丝绸之路积极开展与沿线诸国的贸易交流。文献中记载高昌、于阗、龟兹、大食、小食等国 “时以物货至其国交易”[30](卷346四裔考二十二《契丹下》,P2798),“三年一次遣使,约四百余人,至契丹朝贡”[31](卷21《外国贡进礼物》,P201),这些都是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实现的。草原丝绸之路不啻是一条民族交融的通道,辽王朝紧紧控制住草原丝绸之路,其实也就掌握了军事进攻、贸易朝贡的主动权,在此过程中,不同文化之间得以沟通融合。
地处草原丝绸之路必经之地的忽洞坝墓葬,其出土茶具所体现的融合特征,既显现出东西融合色彩的趋同性,又表达出一定的差异性。
首先,趋同性集中表现在同西方器物风格的相似性。忽洞坝墓葬出土茶盏,盏口为多瓣形,源于粟特地区的银器,表明了粟特文化直接或间接对忽洞坝出土茶具产生影响;盏托底部的摩羯纹饰源于印度佛教文化,与辽人的宗教信仰密切相关,很可能与草原丝绸之路传播印度密教图案相关[32]。忽洞坝墓葬处于辽代西部草原丝绸之路的活跃区域,是辽文化与外来文化融合碰撞的前沿,势必会对辽代其他区域银质茶具纹饰及形制产生影响。在目前出土的诸多辽代银质茶具中有诸多波斯、粟特、印度文化遗风,其文化传播的顺序极有可能为自西向东,即以草原丝绸之路为轴线逐渐濡染。
其次,差异性主要体现在同以往出土茶具的对比上。与大部分辽代墓葬所出土茶具为陶或瓷质地不同的是,忽洞坝茶具为银质并兼具东西方文化元素而成为同时期出土茶具中的“特例”。以目前所出土的辽代茶盏为例,除宣化姜承义墓、建平张家营子辽墓等少部分辽墓出土茶具盏托略低,显系继承唐代盏托风格之外,绝大部分辽墓所出土盏托都与同时期宋所使用的盏托相类似,即“托座高起若台”[33](P147),如宣化张文藻及张世卿墓、内蒙古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墓以及辽宁法库叶茂台M2、M23等。忽洞坝墓葬出土茶具的这一“特例”或非偶然,处于文化交融的前沿地带是其文化多元、形制独特的关键缘由。
四、结语
忽洞坝墓葬出土的这套茶具是草原丝绸之路上文明交流的象征,也体现了北方游牧文化与南方农耕文化的互动。契丹银器不仅作为东西方文明的载体,更是南北文化沟通的象征,将各种文化因素集聚于一身,形成了独特风格。物质与文化的流动在草原上融合升华,二者相辅相成,这是文化意义上的“守望相助”[34]。草原文化是包容多元的文化,物质文化的背后是深层次的文化交流,深入理解多种文化因素影响下草原文化的多元性,挖掘其背后的多重文化因子,有助于构建草原文化独特的文脉系统与发展方向。
费孝通说,游牧民族“落入精耕细作的农业社会里,迟早就会服服帖帖地、主动地融入汉族之中”[35](P141-142)。 忽洞坝墓葬出土的茶具是辽代西部地区茶事活动与茶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继承着唐风雅韵,融合中原茶文化的优秀元素,在继承中将文化交流的特征表达得淋漓尽致,在融合中将丝绸之路上文明互鉴的特质传递得生动形象。可以说,辽代忽洞坝墓葬出土的银质茶具,是草原丝绸之路东西沟通与农牧文化南北交流的产物与象征。
注释:
①本文所讨论之忽洞坝墓葬出土茶具,包括盏及盏托,属于饮茶器;碾茶及烹茶器不在本文探讨范围。
②西晋郭璞为《方言》卷五“盏”作注曰“最小杯也”,即便如此,扬之水先生仍言“大与小的界限也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扬之水:《扬之水谈宋元金银酒器——杯盘》,《紫禁城》2009年第3期)。目前考古发掘报告中,杯、盏、碗三类器物并无明确的划分标准。本文对于口径较小之器,不拘泥于发掘报告中所称,暂视作盏。
③本图根据《中国历史地图集》改绘而成。详见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第六册:宋·辽·金时期),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