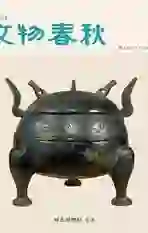明代墓葬出土獬豸补服考略
2021-09-26李昕
李昕
【关键词】獬豸补服;墓葬出土;官服制度;明代
【摘要】作为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獬豸因具善辨曲直的象征属性被应用于古代执法者冠服之中。元代以前,獬豸造型多见于冠饰,明代始用于补服。通过对目前明墓中所出獬豸补服进行梳理,并结合文献资料,对獬豸补与狮子补、麒麟补形象进行了辨识,认为原考古报告中认定的4例“麒麟补”图案实际具备獬豸的基本特征,应为“獬豸补”。獬豸补服的穿用人群主要是各级执法官员及获得封赠的家属,同时,獬豸补子不仅应用于常服,在忠静服、赐服及礼服中也有所体现。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中华民族服饰文化研究”(项目编号:18ZD20)的阶段性成果
獬豸形象在中国古代服饰中已存续两千余年。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曰:“廌,解廌兽也,似牛,一角,古者决讼,令触不直者。”[1]由于獬豸具有明忠奸、识善恶的特性,故被当成“法”的化身,象征司法廉明、监察公正,成为监察御史和司法官员等的身份标志。自先秦始,历代执法者多以獬豸为冠饰,相关研究已有不少[2—4],明清之际,獬豸又以补子的形式列入执法者的官服规制中。
补服是明代官服的一种,其胸前和背后各缀有一块不同图案、或圆或方的织物,即补子,具有标识身份等级的作用。按照洪武二十四年(1391)对文武官员常服补子内容的规定,公、侯、驸马等用麒麟、白泽,文官用飞禽,武官用走兽,风宪官用獬豸[5]。同时,还绘制了补子的图式,以便于参照执行。除了常服之外,獬豸补子在其它官服中也有应用,如忠静服、赐服及礼服等,本文将这些服饰也纳入讨论范围。
迄今为止,已有多座明代墓葬出土了獬豸补服,有学者从獬豸补子的形象、工艺以及复原等方面进行了考证和分析[6,7],为我们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参考。本文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以考古资料为依据,结合文献记载,对獬豸补服的出土概况、形制类别及穿用对象等问题作简单辩述。
一、明代墓葬出土獬豸补服概况
截至目前,明代墓葬出土的獬豸补服有以下11件:
1.江西玉山县明墓,墓主夏浚卒于嘉靖四十年(1561)[8,9]。出土獬豸补服5件,分别为:
①藏青色绢圆领大袖褶,3件。考古报告中仅提供了一种尺寸信息,说明这3件补服形制可能相同。衣长120厘米,袖长90厘米,袖宽48厘米,袖口宽18厘米。琵琶襟,领边一枚布纽扣。小襟处缝有一根布带与左腰系结,腰部左右各有布带圈一個,以系布带。前胸和后背各有獬豸补子一方(图一),图案为獬豸纹和云纹,采用刺绣工艺,尺寸不详。
②黄绫圆领大袖褶,1件。衣长122厘米,袖宽54厘米,腰宽56厘米,下摆宽90厘米。内有衬里。绫嵌金黄色线,似用织金。前胸和后背各缀有獬豸补子一方,长38厘米,宽34厘米,补子图案为獬豸纹和云纹,采用刺绣工艺。
③藏青纻褶,1件。袖长62厘米,下摆宽90厘米,贴边宽10厘米。大领大袖,袖口和衣周均贴绿色边。腰部用布带系结,领部有布扣一枚。有獬豸补子一方,补子尺寸及制作工艺不详。
2.江西上饶县白岭村明墓,出土獬豸补服4件。该墓出土的部分文物曾在上饶市博物馆展出,其中和服饰相关的文物包括头箍、衫、裙、补服、霞帔、鞋、背袋等,具体数据信息尚未发表。据观展所见,4件獬豸补服分别为:
①石青绸补服(图二,1),1件。圆领,大襟,宽袖,右领边有一枚纽扣。腋下和大襟处各有两副系带,腰间左侧有布带圈一个。前胸和后背各用金线织有獬豸补子一方。
②黄色杂宝花卉纹绸大袖衫(图二,2),2件。形制近同,只是一件衣长略短。圆领,大襟,阔袖。腋下和衣襟处各有两副系带。前胸和后背各用金线织有獬豸补子一方。
③黄色四季花蜂纹缎大袖衫(图二,3),1件。交领,右衽,宽袖。右腋下和大襟原应各有两副系带,已残损。前胸和后背各用金线织有一方獬豸纹补子。
3.宁夏盐池县深井明代墓地,出土深棕色四合云纹缎织金獬豸补服1件(图三,1),现存盐池县博物馆。据该馆提供的资料,补服整体保存较好,只是后衣身和左袖处稍有破损。衣长134厘米,通袖长226.5厘米,袖宽55厘米,袖口宽17厘米。交领,右衽,宽袖。领外有护领,腋下和大襟处各有两副系带。前胸和后背各有一方宽41厘米、高38.5厘米的獬豸补子,补子图案用金线织成。据已公布的考古资料介绍,该墓地属于王氏家族墓群,年代基本贯穿有明一代,重点发掘清理的7座墓葬共出土文物210余件,和服饰相关的有19件[10],但具体内容未明。
4.宁夏盐池县冯记圈墓M3,出土四合云纹缎刺绣獬豸补服1件(图三,2),现存盐池县博物馆。据考古报告介绍,补服保存较完好,仅腋下及侧摆有少许残损。衣长154厘米,通袖长246厘米,圆领宽4厘米,领深17厘米。胸、背处各钉缝刺绣獬豸补子一方。补子宽39.5厘米,高39厘米,以平纹织成,图案以捻金线盘绣而成。同时发掘的共3座墓葬,应为同一家族墓地,依次编号为M1—M3:M1、M2并列,M3距离二者稍远,位置也略靠后。关于墓葬的年代,M2墓志铭记下葬时间为嘉靖十四年(1535),M3出土大量“万历通宝”,下葬时间可能不早于万历年间(1573—1620)。此件补服在考古报告中的定名前后不统一,结论中又称其为“盘金绣狮子补服”[11]。
《大明会典》[12,13]及《三才图会》[14]中均绘有补子图式(表一),其中獬豸与狮子、麒麟的形象比较接近,不易辨识,但仔细观察,仍可找出各自的特征:獬豸均为昂首观望状,头顶独角,前足直立,后足蹲坐,鬃毛上扬,腿部或有鳞状片甲,足为爪趾;狮子为略微回首状,前足直立,后足蹲坐,鬃毛卷曲,身体无鳞,足为爪趾;麒麟则为回首观望状,头顶双角,前左足跪地,右足撑地,身体布满鳞甲,足为偶蹄。盐池冯记圈M3所出补子中间的兽为仰首蹲姿,头顶无角,嘴巴微张,鬃毛卷曲,身体无鳞,兼具獬豸的体态、嘴形和狮子的鬃毛、无角等特征,确实不易区分,反映出明晚期补子制作标准执行不甚严格。但该墓出土有墓主杨氏的铭旌,上书“明敕封骠骑将军先□之柩”,按骠骑将军为正二品武官散阶,依据补子图案“文职以鸟、武职以兽”的规定,武官二品恰好对应狮子补[13],因此该补子为狮子补的可能性更大。故本文不将此件补服列为讨论对象。
依据上述对补子图式的分析,笔者又对目前考古报告中定名为“麒麟补”的补服资料进行了梳理和鉴别,发现下列4件补服上补子图案中的“麒麟”均有明显的独角、爪趾特征,具备獬豸的基本特征:
1.浙江桐乡濮院杨家桥杨青墓出土四合如意云纹缎獬豸绣补袍1件,出土时穿在墓主身体的最外层,整体保存情况尚好。身长135厘米,通袖长230厘米,袖长81厘米,袖宽27厘米,袖口宽15厘米,领边宽3厘米。盘领,大襟,袖口渐收。胸、背部各有一方獬豸补子,边长34厘米,采用刺绣工艺(图四,1)[15]。墓中出土文书内容记有“天顺五年(1461)”,似对应杨青为官时间。
2.浙江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M4出土云鹤团寿纹绸獬豸绣补大袖衫1件,出土时已腐烂,只保留部分残片,后经修复,现藏中国丝绸博物馆。据展陈信息得知,衣长120厘米,通袖长224厘米。衣料华丽,为遍地云鹤团寿纹[16]。考古报告记载,其背部缀有补子一方,边长35厘米,采用环编绣、盘金绣等工艺(图四,2)[17]。李家坟明墓为四室合葬墓,主室为双室(M2、M3)合葬,墓主分别为李湘及其正妻,南北各一边室(M1、M4),分别葬李湘之妾陈氏和徐氏,补服出土于徐氏墓室。根据M1出土墓志铭,可知陈氏卒于万历十七年(1589),其子李芳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中进士。M4棺盖上有“明故庶母徐孺人灵柩”,徐氏既获封号,其墓葬年代应在李芳入仕之后。
3.广东广州戴缙夫妇墓,墓主戴缙仅上身敛装就有10件衣服,外面第二层为绸袍,胸、背用金线绣獬豸补子各一方,边长分别为32厘米、36厘米(图四,3)[18]。据墓志铭,夫人周氏下葬于弘治十八年(1505),戴缙于正德八年(1513)合葬其右。
4.江苏泰州刘鉴家族墓M4出土浅黄色素绸獬豸绣补长衫1件,出土时穿在墓主身上最外层。衣长146厘米,通袖长235厘米,胸宽60厘米,下摆宽115厘米。圆领,右衽,大袖。领口以扣襻系扣,腋下有双系带。胸、背部各有一方獬豸补子,宽29厘米,高26.5厘米,为先绣好后再缝制到袍服上(图四,4)[19]。该家族墓包括两座夫妇合葬墓,M1、M2墓主为刘鉴及其妻田氏,分别卒于正德十五年(1520)和嘉靖三年(1524);M3、M4墓主为刘鉴之子刘济及其妻储氏,分别卒于嘉靖十六年(1537)和嘉靖十一年(1532)。
至此,本文共收集到7座明代墓葬出土的14件獬豸补服。这些补服的年代分布如下:杨青墓在天顺五年(1461)或稍晚,戴缙下葬于正德八年(1513),储氏墓、夏浚墓及徐氏墓的年代均在嘉靖年间或以后,白岭村明墓及深井明墓无明确纪年,但与明代其它出土有风格相近补服的墓葬(如四川新都县明墓[20]、江苏武进王洛家族墓[21]及泰州森森庄明墓[22]、刘湘夫妇墓[23]、徐蕃夫妇墓[24],贵州玉屏县城关明墓[25]、惠水县城关明墓[26]等)相对照,可推知其年代应均在嘉靖至天启年间、。故目前发现的獬豸补服时代集中在明代中晚期。
二、出土獬豸补服的形制类别
上述獬豸补服中形制清晰可考的有12件,另外2件形制不甚明确:
其一,夏浚墓出土的藏青纻褶,可能是服装保存较差,结构不完整,考古报告仅提供了部分尺寸信息,介绍其款式为大袖大领,似乎区别于该墓出土的其他圆领衣服。另外,从文字表述来看,此件补服可能是忠静服。忠静服即古玄端服,为交领,颜色用深青,以纻丝、纱罗为之,三品以上云饰,四品以下素,缘以蓝青,衣身前后饰本等补子[13],藏青纻褶的材质、款式、图案、色彩及装饰等方面皆符合此制,故推测其领式应为交领。
其二,戴缙墓出土的包括獬豸补服在内的绸料、绢料衣服多已破碎,只能从敛装的搭配作大致判断:戴缙上身穿10层衣服,由外到内分别为绢袍、獬豸补绸袍,第三层开始依次为长衫3件、袍2件、贴里1件、长衫1件及短衫1件,多为交领样式。按江苏泰州徐蕃夫妇墓保存完好,墓主徐蕃上身穿8层衣服,最外层的孔雀补服为圆领,其内皆为交领衣[24]。戴缙所穿补服在外第二层,故推测其為圆领的可能性较大。
综上,考古出土的明代獬豸补服包括圆领袍9件,交领袍2件,圆领衣2件,交领衣1件(表二)。
从目前出土情况看,14件中獬豸补服中,圆领袍9件,占比64%,且男女服均有。形制特征为圆领,右衽,上下通裁。侧面可见褶摆,腋下有系带。不同时期的袖型呈现出鲜明的特征,由窄瘦合体渐趋疏阔宽松。洪武二十三年(1390)颁布的常服制度,对圆领袍的规格尺寸有明确规定:“凡官员衣服宽窄,以身为度,文官衣长自领至裔,去地一寸,袖长过手,复回至肘。袖椿广一尺,袖口九寸。”[27]即文献记载的袖宽和袖口宽分别约为32厘米和28.8厘米。上述9件圆领袍中,仅年代稍早的杨青墓所出圆领袍相对接近这一尺寸,为袖宽27厘米,袖口宽15厘米,其余8件,除戴缙墓和白岭村明墓出土的补服尺寸信息不详外,依据袖宽数据或参照已知补子尺寸进行推算,袖宽均超过“一尺”,结合明中叶以后僭拟越制、追逐时髦的服饰风尚来看[28],这种阔袖具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交领袍不如圆领袍应用广泛,仅见2件,1件为夏浚墓所出藏青纻褶,另1件为王氏家族墓出土的四合云纹缎补服。后者整体造型严整,交领,右衽,领部缀有白色护领。大袖收口,袖身有接缝,胸背饰以方补,大襟用系带两对。衣身两侧开衩,有内摆,即前襟左右两侧各接一幅折回缝于后襟,后襟为单独的一整片,似明代道袍。
圆领衣和交领衣皆为单层无衬里,又可称其为“衫”,3件上衣均出自江西上饶白岭村明墓。除领式不同外(2件为圆领大襟式,1件为交领右衽式),形制近同。袖身肥阔,衣袖有接缝。衣身较短,大襟处用两对系带系扎,胸背缀有方形补子。此类上衣通常为女性穿用,搭配裙子,称为“衫裙”,如果内有衬里或絮绵,则称“袄裙”。
从样式来看,夏浚墓出土的藏青纻褶属于忠静服补式。忠静服为官员燕居时所穿服装,创制于嘉靖七年(1528),阁臣张璁建议,效法古玄端服制品官燕居之服,更名“忠静”,以勉励百官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忠静服由忠静冠、忠静服、带、履、袜等组成。忠静冠即古之玄冠,冠顶呈方形,乌纱为之,两山列后,冠前饰梁,压以金线,四品以下官员不用金,改用浅色丝线缘边[13]。苏州虎丘明朝首辅王锡爵墓出土有一顶忠静冠实物,冠上五道梁和两旁如意纹自双侧盘及冠后,各压以金线[29]。即墨博物馆藏有一幅《北泉忠静冠服像》(图五),画中人戴忠静冠,穿忠静服,胸前缀獬豸补[30]76。“北泉”为蓝田的号。蓝田,字玉甫,嘉靖二年(1523)进士,授河南道监察御史,他为官时间恰在忠静服制颁布的嘉靖年间[31]。
除夏浚墓出土的交领袍忠静服以外,其余獬豸补服大体都属于常服补式。首先,圆领袍为常服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从文献记载和墓葬出土的补服实物均已得到印证。常服主要由乌纱帽、团领衫、束带等组成。杨青墓在清理时发现墓主头戴黑色乌纱帽,最外层穿獬豸补圆领袍,袍外还系着一条镂雕木腰带,体现了常服搭配的普遍形态。其次,胸背缀补的交领袍、交领衣、圆领衣尚未见相关文献记载,但在故宫博物院藏《徐显卿宦迹图》[32]中绘有穿交领袍、胸背缀补的官员与穿圆领补服的官员同时出现,中国国家博物馆藏《明宪宗元宵行乐图》[33]及传世的明代容像[34]中也有分别穿交领衣裙或圆领衣裙的贵族女性,因此这类服饰应该也具有常服的性质。
獬豸补服的衣料有绸、缎、绢、绫、纻等,绸制品最多,其中又有一半为提花绸。纹饰题材多样,图案风格较写实,多含有吉祥寓意,有四合如意云纹,古钱、银锭、方胜、金铤、莲花等杂宝花卉纹,蜜蜂、梅、莲、菊、牡丹等四季花蜂纹,流云、仙鹤、团寿等吉祥如意纹等。补子多采用环编绣、锁线绣、绒线绣、盘金绣等刺绣工艺,白岭村明墓和深井明墓的补子则采用了织金工艺。补子与服装的关联方式或为绣成后缝缀,或直接织成。相较官方文献中记载的品官常服令用杂色纻丝、绫罗、彩绣[35],忠静服以纻丝、纱罗[13],出土实物的衣料纹质更显丰富和精彩。
三、獬豸补服的穿用对象
通过对墓主身份的分析,可对獬豸补服的穿用对象进行探讨。
据戴缙墓志载,其历任湖广道监察御史、佥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等职,官至南京工部尚书,同年被罢职返乡。戴缙的落马与宦官汪直关系密切,受政治斗争的牵连,史志对其褒贬不一[36],而墓志却说“公论多为不平,而公独泰然不介意。继以恩诏,许复冠带”,此说或许是其子孙的溢美粉饰之词,但至少给其死后仍穿着官服下葬提供了合理的注脚。
夏浚墓中殉葬品清单抬头虽写明墓主为“明故会稽郡贵□□广西参政讳名夏浚”,但《明世宗实录》有载:“辛丑,升礼部郎中夏浚为福建按察司副使,提调学校”[37]。按察司主管地方监察,设有按察使、副使、佥事等职。按察使负责一省刑名按劾之事,副使和佥事负责分道巡察,如分领提学、驿传、清军、分巡、兵备等各项事务[38]。按察副使,为正四品,以提督学校为己任,又称“提学道”。
杨家桥明墓未发现墓志铭,但据墓葬位置和出土文书内容,发掘简报考证墓主为河南道按察使佥事杨青。按察使佥事,为正五品,隶属按察司系统。
李家坟明墓M4的墓主为李湘之妾徐氏。李湘一生并未建功立业,在其子李芳考取进士以后家族开始发达,成为嘉兴一大望族[39]。《万历嘉兴府志》载:“李湘,以子芳贵,封文林郎。”[40]文林郎为文职散官,秩正七品。徐氏为李芳庶母,按明制封赠七品官职母妻为孺人。
刘鉴家族墓M4墓主为刘济继室储氏。据刘济墓志铭载,其为鲁府引礼舍人,属九品官之外的未入流官,储氏如从夫之品则无封号。
还有两座墓葬缺少墓志信息,墓主身份暂难断定:其一,深井明墓M7出土一方墓志砖,有部分字迹看不清,從内容仅能得知该墓地属于王氏家族墓;其二,白岭村明墓出土的服装中包括一件孔雀纹霞帔,墓主可能是三品或四品命妇。
上述明墓中,墓主身份既有官员、命妇,又有未入流者,品秩高低不一而足。这种差异可以从史料所反映的历史演进中找到原因。
明代常服制度规定,风宪官补服用獬豸。关于风宪官的设置,据《明太祖实录》载,洪武十年(1377)十二月,朱元璋对回朝的各道按察使说:“朕以天下之大,民之奸宄者多,牧民之官不能悉知其贤否,故设风宪之官为朕耳目,察其善恶,激浊扬清,绳愆纠谬,此其职也。”[41]可知风宪之职是为服务明代专制皇权所设,主要职责是监察中央及地方政务。明代监察机构有都察院及提刑按察司,也称风宪衙门[42]。戴缙、夏浚、杨青三人皆曾供职于都察院或按察司,身穿獬豸补服与其风宪官身份相符。
命妇服饰是明代官服体系的一个子系统,服饰等级一般随丈夫或儿子的官品而定。徐氏封为七品孺人,随葬獬豸补服或即从子之封赠而来。
未入流属于杂职官一类,而杂职官常服补用练鹊[5]。以储氏未入流官员继室身份,穿用獬豸补服有僭越之嫌,这从补子的形制也能发现端倪——该补子是先单独绣成后,再简单缝合到袍服上,且尺寸小于研究所得“32~40厘米之间”[43]。可以说储氏所穿补服仅为“形似”。这种服饰现象在文献中也不乏记载,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载:“天下服饰僭拟无等者,有三种:其一则勋戚……其一为内官……其一为妇人,在外士人妻女相沿袭用袍带,固天下通弊,若京师则异极矣。”[44]
综上所述,出土獬豸补服的穿用对象主要是风宪官及获得封赠的官吏家属。明代风宪官一职涵盖面较广,包括都御史、佥都御史、监察御史、按察使、佥事等职衔,这一群体区别于传统文武官员按照品秩服用“本等补”,其补子花样无品级之分,从高位之官到封赠散官,风宪之职合用同一花样。同时,由于明后期僭越之风浓厚,亦有突破制度穿用獬豸补服的情况出现,这在明墓出土各类随葬补服中屡见不鲜,属越制之举,不在讨论范围内。
四、文献所见獬豸在其他服饰上的应用
由文献及图像资料可知,除常服、忠静服以外,明代其它官服系列中也应用到獬豸图案或形象,如赐服及礼服。
赐服是皇帝封赏给有关人员的各类服饰,其形式和种类都十分丰富。蔚州博物馆所藏郝杰画像(图六),其所穿曳撒就属于赐服之列。曳撒的形制为后身不断,两旁有摆,前襟分上下两截,下有马面褶,且腰部两侧各有一组顺褶,穿红色袍服则缀本等补子[45]。常服曳撒与赐服的区别在于服饰图案的不同,前者一般只在胸背位置缀补,而后者则在通袖膝襕饰以赐服图案。郝杰《明史》有传,为嘉靖三十五年(1556)进士,授职为行人,后任佥都御史、副都御史、都御史等职,为官忠正直言,亦不避权贵[46]。穿着布满獬豸图案的曳撒袍,更加彰显这位监察官员的审慎和严正。
獬豸在礼服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男子朝服冠和女子霞帔上。
朝服是参加重大典礼时使用的礼服,主要由梁冠、赤罗衣裳、白纱中单、赤罗蔽膝、带、佩绶、袜履等组成。梁冠,以梁数区分等级,御史官再加獬豸。穿朝服的御史画像所见不多,即墨博物馆所藏蓝章朝服像为一例(图七)[30]38。蓝章为成化二十年(1484)进士,先后任监察御史、佥都御史等职[47],此像可能正是其任职监察御史(正七品)时所绘。画上的他身着朝服,手执笏板,头戴二梁冠,颜题上饰有独角兽头,对应六品或七品官职。明代獬豸冠与前代相比,一方面以冠上梁数体现等差,另一方面,獬豸形象趋于具象化,而非仅凸显独角的抽象化表达,这或许和明代獬豸补子形象的明晰有关。
霞帔原属于命妇朝服配件,与大衫、褙子同穿。明中后期,也常和圆领袍搭配,成为常服的一部分。青州市博物馆收藏有一幅冯惟讷继配魏氏像(图八)[48]。冯惟讷为嘉靖十七年(1538)进士,累官陕西按察佥事、山西按察使、陕西右布政使、江西左布政使等职,官终光禄卿[49,50]。画中冯夫人头戴珠翠五翟冠,身穿红色云纹织金孔雀补服,外加獬豸纹霞帔,腰系獬豸纹革带。孔雀补对应等级为文官三品,或与冯惟讷担任按察使(正三品)一职有关。按照服饰制度规定,三品命妇使用云霞孔雀纹霞帔,冯夫人霞帔却装饰獬豸纹。由此可见,明后期命妇服饰所受制约较少,无论是穿着方式还是纹样搭配,都有很多细节上的变化。
五、结论
目前明代墓葬中出土的獬豸补服主要分布在江西、浙江、江苏、宁夏、广东等地区,时代集中在明中晚期,墓主人多是负责监察及执法的七品以上官员及家属。出土獬豸补服或穿于墓主身上,或随葬于棺内。其形制以圆领袍为主,体现了明代官服制度的有效执行;另外还有交领袍及圆领衣、交领衣等样式,补充了官服制度之外的服装形制。
從先秦至明代,獬豸具备的政治象征功能一直延续下来,但表现方式却发生了变化,不仅从发冠延伸至服装,还从造型转变为图案,应用于各级执法官员们的常服、忠静服、赐服及礼服中。獬豸冠服作为一种身份标识的象征,与爵位服等明代其它特殊服装一样,虽然它们的表现形式稍显特别,但实际发挥的作用并无本质区别,都是封建国家进行统治的有效工具。
————————
[1]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63:202.
[2]彭浩.楚人的纺织与服饰[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6:171—172.
[3]黄凤春,黄婧.楚器名物研究[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17—19.
[4]韩织阳.獬豸冠小考[C]//武汉大学历史学院.珞珈史苑:2016年卷.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7:60—71.
[5]张廷玉,等.明史:卷67:舆服志三[M].北京:中华书局,1974:1638.
[6]赵丰.明代兽纹品官花样小考[M]//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丝绸博物馆,盐池县博物馆.盐池冯记圈明墓.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48—159.
[7]蒋玉秋.明代环编绣獬豸胸背技术复原研究[J].丝绸,2016(2).
[8]胡义慈.玉山县发现明墓一座[J].文物工作资料,1962(4).
[9]江西省博物馆.江西玉山、临川和永修县明墓[J].考古,1973(5).
[10]耿志强,王仁芳.盐池县深井明代墓地[M]//中国考古学会.中国考古学年鉴:2010.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461.
[1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丝绸博物馆,盐池县博物馆.盐池冯记圈明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97,98,120.
[12]大明会典:卷58[M].明正德四年校刻本.1716(明正德六年).
[13]李东阳,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61[M].内府刊本.1587(明万历十五年).
[14]王圻,王思义.三才图会:衣服2卷[M].刊本.1609(明万历三十七年).
[15]周伟民.桐乡濮院杨家桥明墓发掘简报[G]//浙江省博物馆.东方博物:第二十五辑.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49—57.
[16]中国丝绸博物馆.梅里云裳:嘉兴王店明墓出土服饰中韩合作修复与复原成果展[M].杭州:中国丝绸博物馆,2019:24—25.
[17]嘉兴博物馆.嘉兴王店李家坟明墓清理报告[J].东南文化,2009(2).
[18]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戴缙夫妇墓清理报告[J].考古学报,1957(3).
[19]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明代刘鉴家族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6(6).
[20]赖有德.四川新都县发现明代软体尸墓[J].考古通讯,1957(2).
[21]武进市博物馆.武进明代王洛家族墓[J].东南文化,1999(2).
[22]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森森庄明墓发掘简报[J].文物,2013(11).
[23]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明代刘湘夫妇合葬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2(8).
[24]泰州市博物馆.江苏泰州市明代徐蕃夫妇墓清理简报[J].文物,1986(9).
[25]李黔滨.贵州省博物馆藏品集[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3:149.
[26]唐文元.惠水县城关出土明代纺织品介绍[M]//董有刚.贵州省博物馆馆刊:创刊号.贵阳:贵州省博物馆,1985:46—50.
[27]明太祖实录:卷200[M].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影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001.
[28]周绍泉.明代服饰探论[J].史学月刊,1990(6).
[29]苏州市博物馆.苏州虎丘王锡爵墓清理纪略[J].文物,1975(3).
[30]山东博物馆,孔子博物馆.衣冠大成:明代服饰文化展[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20.
[31]李开先.文林郎河南道监察御史北泉蓝公墓志铭[G]//李开先.李开先集.路工,辑校.北京:中华书局,1959:413—416.
[32]朱鸿.徐显卿宦迹图研究[J].故宫博物院院刊,2011(2).
[33]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M].香港:商务印书馆,1981:424—425.
[34]石谷风.徽州容像艺术[M].合肥:安徽美术出版社,2001:6,24.
[35]明太祖实录:卷209[M].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影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3113.
[36]陈鸿钧.广州出土明南京工部尚书戴缙夫妇墓志考[J].嶺南文史,2016(3).
[37]明世宗实录:卷263[M].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影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5224.
[38]张廷玉,等.明史:卷75:职官志四[M].北京:中华书局,1974:1840—1841.
[39]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1:52—53.
[40]刘应钶,沈尧中.万历嘉兴府志:卷17[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301.
[41]明太祖实录:卷116[M].国立北平图书馆红格抄本影印本.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1902.
[42]李东阳,申时行,等.大明会典:卷209[M].内府刊本.1587(明万历十五年).
[43]赵连赏.明清官员的补服[J].文史知识,2006(7).
[4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5[M].黎欣,点校.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157.
[45]刘若愚.酌中志:卷19[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166.
[46]张廷玉,等.明史:卷221:郝杰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5822—5823.
[47]林溥,周翕.即墨县志:卷9[M].刊本.1872(清同治十一年).
[48]潍坊市文物局.潍坊馆藏文物精粹:书画卷[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20:51.
[49]王家士,祝文,冯惟敏.临朐县志:卷3[M].刻本.1552(明嘉靖三十一年).
[50]姚延福,邓嘉缉,蒋师辙.临朐县志:卷14中[M].刊本.1884(清光绪十年).
〔责任编辑:成彩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