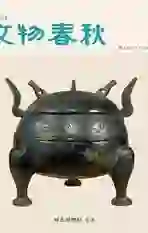甘青地区旧石器考古的回顾与思考
2021-09-26慕占雄问娜娜
慕占雄 问娜娜
【关键词】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迁徙;文化交流
【摘要】甘肃、青海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人群汇聚和交流的重要区域之一。近年来,随着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址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的持续推进和深入,在回顾与梳理甘青地区旧石器考古发现的基础上,讨论区域内旧石器文化面貌、古人类化石及古环境状况,对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行为及其与环境的关系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甘青地区主要包括甘肃、青海两个省区,地跨黄土高原、青藏高原两个地理单元,区域内山地、高原、河谷、沙漠、戈壁均有分布。该区域的旧石器考古工作开始较早,1920年法国传教士桑志华在甘肃庆阳的赵家岔和辛家沟发现了几件石制品[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该区域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陆续开展,先后发现了60余处旧石器时代遗址点,其中以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为主,还有个别旧石器时代早期和中期遗址,出土了大量石制品以及零星古人类化石和动物骨骼,为研究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活动提供了大量实物资料。
与此同时,谢骏义[2]、许新国[3]、张行[4]、仪明洁[5]等也对近20年来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进行了研究,但多是对青海地区史前考古发现的阶段性梳理,尚未涉及系统性的区域研究。因此,笔者拟将甘肃地区和青海地区的相关旧石器遗址纳入到一个大区域进行探讨,在分区梳理的基础上,从旧石器文化面貌、古人类化石及古环境状况等方面探讨早期人类在甘青地区的活动情况。
一、旧石器遗址
(一)甘肃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甘肃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出现了两次小高峰,一次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陇东泾河上游的一系列发现,另一次是21世纪以来陇东楼房子遗址的发掘和在陇中盆地的一系列发现,相对来讲,甘肃中、西部的发现要少一些。以下将甘肃地区分为陇东泾河上游、陇中盆地和甘肃中西部三个区域(图一),分别就旧石器时代遗址分布情况进行介绍。
1.陇东泾河上游地区
目前,陇东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时代贯穿早、中、晚期。早期遗址包括泾川大岭上遗址,镇原姜家湾遗址、寺沟口遗址;中期及稍晚的遗址有环县刘家岔遗址和楼房子遗址,西峰巨家塬遗址,镇原黑土梁遗址,泾川牛角沟遗址、合志沟遗址、桃山嘴遗址、南峪沟遗址等。其中除泾川大岭上遗址属于黄土旧石器遗址外[6],其他遗址点均位于泾河及其支流的二级阶地的河流相地层中。已经过正式发掘的遗址有环县刘家岔、楼房子遗址。
①刘家岔遗址(36°29′N,107°06′E),1977年发现于环县西川乡,石制品和动物化石出土于湖相杂色黏土堆积中,当时通过铀系法测定其年代为43.4ka B.P.。石制品多出自第⑤层地层堆积,共1022件。石制品原料以各色石英砂岩为主,多采用锤击法。工具毛坯以石片为主,类型以刮削器为主,还有尖状器、石球、砍斫器等,其中尖状器修理精细[7]。
②楼房子遗址(36°20′47″N,107°20′54″E),1963年发现于环县曲子镇楼房子村,地层堆积分为上、下两层,年代均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上文化层早于40 ka.B.P.。出土了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石制品共1632件,原料以采自河滩的石英砂岩为主。石核以单台面石核和双台面石核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多台面石核和盘状石核,剥片以硬锤锤击为主;石片多普通石片,未发现勒瓦娄哇石核及石片。工具类型以刮削器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的锯齿刃器、凹缺器和少量尖状器、齿状器等。修理技术以硬锤锤击为主,也有个别工具表现出莫斯特软锤修理的特征。下文化层详细资料尚未公布,可能处于旧石器时代中期早段[8,9]。
2.陇中盆地地区
陇中盆地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主要由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兰州大学、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单位与美国合作开展。目前发现的早期遗址仅有张家川杨上遗址;中期至晚期遗址包括张家川石峡口遗址,秦安大地湾F901地点、鱼尾村地点,庄浪滑沟口遗址、长尾沟地点群、徐家城遗址和双堡子Ⅰ、Ⅱ号地点及天水武山人化石地点等。这些遗址主要分布在渭河上游水洛河和清水河等支流的各级阶地上。其中杨上遗址、徐家城遗址、大地湾F901地点及石峡口遗址保存情况较好,文化内涵较丰富,其余遗址点仅采集部分标本。现选取近年来进行过科学发掘并有多学科参与研究的遗址点介绍如下。
①杨上遗址(34°59′50.13″N,106°10′13.79″E),2007年发现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杨上村,年代为220~100 ka.B.P.,属于旧石器时代早期[10]。共发现石制品1710件,原料以采自河滩的脉石英、石英岩砾石为主。石核中简单石核占64.08%,多台面石核占31.07%,盘状石核占4.85%;石片多长型,剥片技术为硬锤锤击。工具以片状毛坯为主,类型有刮削器、锯齿刃器、尖状器、石钻等,其中刮削器占主体;修理技术为硬锤锤击,以单向加工为主,刃缘修疤不连续[11]。
②徐家城遗址(35°04′44.8″N,105°47′49.0″E),2009年发现于庄浪县徐家城村,文化遗物出自马兰黄土中的古土壤层,年代为43~36 ka.B.P.,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共有石制品5442件,原料为采自河滩的花岗岩、脉石英。石核中双台面和多台面比例较高,剥片技术为硬锤锤击;工具以片状毛坯为主,类型主要为刮削器、尖状器、石锥等[12]。
③大地湾F901地点(35°0′54″N,105°54′14″E),1993年发现于秦安县邵店村,石制品出土于F901大厅地表下17米深的黄土中[13]。2006年发掘出土石制品877件,分为打制石器、石片和细石器。打制石器以来自河滩的石英砾石为原料,剥片以砸击法为主,年代为60~7ka.B.P.,属旧石器时代中期晚段至晚期;細石器主要以玉髓等隐晶质石料为主,包括细石核、细石叶及碎屑等,年代为20~7ka.B.P.,属旧石器时代晚期[14]。
④石峽口第1地点(35°07′58″N,106°10′31″E),2009年发现于张家川回族自治县石峡口村进村道路南侧,北距石峡口第2地点约100米。文化遗物埋藏于清水河右岸一级阶地的前缘,顶面距现河床约10米,年代为18.5~17.2ka.B.P.,属旧石器时代晚期晚段。2015年发现石制品406件,原料以石英和燧石为主,包括石核、石片、断块、细石器等;剥片技术有锤击和砸击两种,加工技术较简单。细石器有细石核、细石叶及器型规整的端刮器、两面尖状器等[15]。
3.甘肃中西部地区
甘肃中西部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比前述两区相对要少一些,包括中、晚两期:中期遗址仅有中部的夏河白石崖洞遗址,晚期遗址包括中部的东乡王家遗址和西部的肃北霍勒扎德盖遗址。其中只有夏河白石崖洞遗址经正式发掘,但材料尚未公布。
①王家遗址(35°34′26″N,103°22′48″E),1986年发现于东乡族自治县锁南镇,南距下王家村1.5公里,年代为14.5ka.B.P.,属旧石器时代末期。石制品采集于砾石层,共7件。其中5件为锤击法制成,其余2件为加工精致的半月形刮削器和圆头刮削器[16]。
②霍勒扎德盖遗址(42°25′N,96°10′E),1989年发现于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马鬃山区明水乡,南距明水乡政府约60公里,研究者推测遗址年代为旧石器时代末期。该遗址出土的3件石制品均发现于地表以下1米的黄色—灰色中细砂层中,原料为白色火石和黑色硅质岩。其中2件石片为硬锤锤击制成,台面均经过修理。另1件石叶(G. P.189)较有特色,形态规整,断面呈梯形,技术特征明显,石叶背后有两条平行的背脊,说明当时人类具有在同一工作面上连续剥片的能力[16]。
③白石崖洞遗址(35°26′51.50″N,102°34′20.88″E),位于夏河县甘加乡直格尔塔哇村北,年代为190~30ka.B.P.,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晚期[17]。2018年发掘出土石制品1400多件,以石片、石核为主,可见较多砾石面,多件石片有使用痕迹[18]。
(二)青海地区
青海的旧石器时代考古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在小柴达木盆地以南的三岔口和长江发源地霍霍西里等地采集到了零星的打制石器,只是年代尚存争议。进入21世纪以来,为配合青藏铁路建设,在昆仑河流域发现了多处旧石器遗址点。除此之外,通过主动性调查和发掘工作,还在青海湖周边发现了数十处旧石器遗址点[19]。为了方便研究,我们将青海地区分为三个区域,分别为柴达木盆地、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和过渡区域(图二)。
1.柴达木盆地
柴达木盆地区域仅发现冷湖1号地点和小柴达木湖遗址两处,均分布于柴达木盆地边缘。这两个遗址年代相近,均属旧石器时代晚期。
①冷湖1号地点(38°51′0″N,93°24′36″E),位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冷湖镇,海拔2804米,年代为30.5kaB.P.左右,为青海境内目前发现年代最早的旧石器地点。该地点未经发掘,文化层埋藏在保存良好的滩脊内,采集到3件石制品,为2件石核和1件石叶。石制品均以灰绿色石英岩为原料,石核与石叶具有与勒瓦娄哇石叶剥制技术相似的风格[20]。
②小柴达木湖遗址(37°27′32″N,95°30′32″E),位于小柴达木湖东南岸的阶地上,发现于1982年,1983—1998年又进行了几次考察,年代为30ka.B.P.左右。石制品出自高于湖面8~13米的一级阶地,原料以石英岩为主,类型有石核、石片、工具,工具又包括刮削器、凹缺器、雕刻器、钻等。毛坯多为石片,剥片技术以锤击法为主,砸击法为辅,修理技术有锤击法和压制技术[21]。此外,该遗址还发现有细石核、细石核毛坯、细石片等细石器[22,23]。
2.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
21世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联合国内外多家机构在青藏高原开展多项调查研究工作,其中在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发现了多处旧石器遗址点。年代上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5~10ka. B.P.,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末期,有共和县江西沟1号地点、黑马河1号地点、151遗址,海晏县娄拉水库地点、晏台东遗址等;第二阶段为8.5~4ka.B.P.,相当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晚期,有共和县江西沟2号地点、黑马河3号地点、沟后001地点,贵南县拉乙亥遗址、达玉台遗址等。另外,还有年代未经测定的海晏县白佛寺遗址和铜线遗址。
(1)青海湖盆地
青海湖盆地共发现7处旧石器遗址点,主要分布在青海湖周边海拔相对较低,环境、资源等条件较为适宜的区域,包括江西沟1号和2号地点、黑马河1号和3号地点、151遗址、娄拉水库地点、晏台东遗址、铜线遗址、白佛寺遗址等。
①江西沟地点,位于共和县江西沟镇青海湖南岸。2007年发现1号和2号两个地点。1号地点(36°35′23.89″N,100°17′44.52″E),海拔3330米。试掘划分出两个不同层位的灰堆。上层灰堆为长约50厘米、厚2厘米的透镜体,年代为14.8~14.16ka.B.P.左右,属旧石器时代末期。出土1件细石叶和2件细石叶碎屑。下层灰堆位于形状不规则的古人类生活面上,直径约65厘米,厚约1厘米,年代为14.92~14.2ka.B.P.左右,出土石制品107件,原料以黑灰色变质岩为主,长度5~ 10毫米,可能为预制细石核的副产品[24]。2号地点(36°35′25″N,100o17′47″E),年代为7.33~4.85ka.B.P.,相当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出土石制品有细石叶、石叶、似石叶和石片。其中石叶、似石叶台面为点状且具有平直刃缘,推测是从预制石核上剥离产生的,可能是装柄使用的复合工具[25]。
②黑马河地点,位于共和县青海湖西南侧黑马河镇,2004年以来发现1号地点和3号地点。1号地点(36°43′48″N,99°46′12″E),海拔3210米,年代为13.1~12.9ka. B.P.,属旧石器时代末期。在14平方米的试掘范围内发现古人类生活面及灰堆,出土有石制品、碎骨。石制品包括石核1件,细石叶残片2件,两面修理的刮削器1件及石片数件。此外,还有用于研磨的砾石。石器技术有细石叶压制技术和两面加工技术[24]。3号地点(36°43′32.48″N,99°46′38.81″E),年代为7.36±0.05ka.B.P.,相当于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中期。共发现石制品80余件,多数为以黑色变质泥岩、细砂岩为原料的碎屑以及少数为燧石工具的修理碎屑,仅发现1件绿色燧石细石叶和2件有修理痕迹的砂岩石片,总体表现出权宜性的特点[25]。
③151遗址(36°33′35.9″N,100°28′28.2″E),位于共和县青海湖东南侧,151景区内的山前斜坡,海拔3397米,发现于2007年,2014年经正式发掘。分上下两个文化层。下文化层发现少量石制品,以小石片石器工业制品为主,也有一定数量细石叶制品,年代为15.4~13.1ka.B.P.,属旧石器时代末期[26]。上文化层资料尚未公布。
④娄拉水库地点(36°52′16.8″N,100°52′41.9″E),位于海晏县,青海湖东北侧,娄拉水库西侧,海拔3395米,发现于2007年。发现有用圆形、椭圆形砾石砌成的不规则形火塘,地表采集有石制品、炭屑、烧骨等。石制品原料为石英,以石片、碎屑为主,含少量细石叶。年代为13ka.B.P.,属旧石器时代末期[27]。
⑤晏台东遗址(36°52′12″N,100°52′12″E),位于海晏县,青海湖东北侧,海拔3302米。发现10个火塘,采集石制品121件,其中石核7件、石片72件、细石叶15件、断块21件、工具6件。原料以脉石英、石英砂岩为主,其次为隧石。剥片方法以錘击法为主,未发现修理台面的现象。工具类型以刮削器和尖状器为多,辅以细石叶制品,加工多采用锤击法。年代为10.36±0.06 ka.B.P.,属旧石器时代末期[19]。
⑥铜线遗址,位于海晏县,青海湖东北侧的山谷中,2009年发现3个地点。第1地点(36°53′2.1″N,100°45′46.1″E),海拔3334米,发现石制品7件,包括2件锥形细石核、3件细石叶断片、1件石片及1件断块。第3地点(36°52′55.7″N,100°45′29.2″E),海拔3331米,发现3处火塘,火塘周边发现有石制品。第4地点(36°52′55.4″N,100°45′31.3″E),海拔3335米,发现石制品14件,其中13件原料为石英砂岩,1件为脉石英,石制品种类有石片12件、断块1件、工具(刮削器)1件,剥片技术及修理技术均为锤击法。年代未经测定[19]。
⑦白佛寺遗址(36°55′31.4″N,100°44′27.9″E),位于海晏县,青海湖东北侧,2009年在白佛寺后山腰上发现,海拔3399米。出土有原地埋藏的石制品等,包括细石叶、细石核、砾石等。年代未经测定[19]。
(2)共和盆地
共和盆地位于青海湖盆地以南,共发现3处旧石器地点,分别为沟后001地点、拉乙亥遗址和达玉台遗址。
①沟后001地点,位于共和县沟后水库附近,处于共和盆地边缘沟后峡的高河漫滩内,海拔3056米,发现于2007年。石制品发现于黄土和古土壤下的沙层中,数量少,仅有数件细石叶残片。原料以隧石和石英为主,年代不早于10ka.B.P.,即不早于旧石器时代末期[27]。
②拉乙亥遗址,位于贵南县拉乙亥乡,处于共和盆地的中部黄河河谷的二级阶地,1980年发现多个地点,并发掘了其中一个。发现较多的炉灶坑,文化遗物出自灰烬层或炉灶坑内。共发现石制品1480件,原料主要为石英岩,类型有石片石器和细石器。石片石器为简单锤击加工制品,有砍砸器、刮削器、带槽斧形器、研磨器、磨石、染色板等。细石器加工精细,39件细石核分为两种工艺模式:一种为似河套技术加工,有楔状石核体,毛坯石条呈三角形,两面修整,另一面为石条剥离面,台面从不同方向修整;一种为拉乙亥技术,包括半楔状石核、舌状石核、柱状石核、半锥状石核、扁锥状石核等。年代约为6.7ka.B.P.[28]。
③达玉台遗址,位于贵南县拉乙亥乡的达玉台地上,属于黄河的二级阶地。1981年发掘,发现942件石制品,分为石片石器和细石器。石片石器均为锤击法打制和修理,有砍砸器、尖状器、刮削器、雕刻器、石刀等;细石器占有较高比例,其中细石核221件、毛坯27件、细石叶109件。细石器加工精细,采用间接打击法制成并修整,石核包括具有拉乙亥技术特点的楔状石核、舌状石核、棱柱状石核、半锥状石核、锥状石核等[29]。年代未经测定。
3.过渡区域
过渡区域的旧石器时代遗址点主要分布于昆仑河流域和冬给措纳湖附近。昆仑河流域主要有野牛沟、纳赤台、三岔口和西大滩等4处细石器地点,年代均为7ka.B.P左右;冬给措纳湖附近主要有下大武地点以及冬给措纳湖阶地的10个地点,年代为5.3ka.B.P.左右。
(1)昆仑河流域
昆仑河流域位于柴达木盆地南部,是进藏的主要通道之一。21世纪以来,为配合青藏铁路建设,在该区域发现了几处旧石器地点,主要有野牛沟、纳赤台、三岔口和西大滩等地点,发现有小石器、细石器等。年代均晚于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的遗址点。
①野牛沟第Ⅰ地点(35°52′59.9″N,94°14′59.9″E),位于昆仑河支流奈齐郭勒河北岸的第四台地上,海拔3800米,发现于2009年。石制品集中分布在火塘周围,共402件。原料有石英岩、水晶、砂岩、硅质岩、辉绿岩等。类型包括细石核、细石叶和尖状器、刮削器等工具,以及制作石制品产生的碎石块。剥片技术为间接或软锤剥制石叶,二次加工技术特征极不明显。年代为7.5ka.B. P.左右[30]。
②纳赤台细石器地点,位于昆仑山北麓昆仑河南岸一级阶地,发现于2002年,次年发掘。该地点的细石器分布较集中,共100余件。原料有石英岩、蛋白石岩、硅质岩、流纹岩等。棒击法和压制法较流行。类型包括石片、石核、刮削器、尖状器等,其中以细石叶、细石片数量最多。未进行测年分析,研究者认为其年代与拉乙亥细石器遗址年代相似,约为6.7ka.B.P.[31]5—7。
③三岔口细石器地点,位于格尔木市西南110公里处,发现于2002年,2004年发掘。包括东、西两个细石器地点。东地点地表采集到170多件细石器,原料有硅质岩、石英岩、水晶石、玉髓、蛋白石岩、燧石流纹岩等。石核加工技术以砸击法为主,石叶加工技术主要有间接打片法和压制法两种。类型包括石核、石片、细石叶、刮削器、尖状器等,其中石片和细石叶数量最多。由于其石制品特征与纳赤台细石器地点基本相似,猜测二者文化性质相同,年代也大致相同,约为6.7ka.B. P.。西地点的相关材料未见报道[31]8—10。
④西大滩地点(35°42′36″N,94°15′36″E),位于三岔口地点以南25公里左右的昆仑河上游阶地上,海拔4300米。石制品包括普通石核石片、细石器及部分经过加工的工具,其中细石器具有亚欧大陆东部细石器的特征。年代为8.2~6.4ka.B.P.[20]。
(2)冬给措纳湖附近
①冬给措纳湖地点,位于玛沁县冬给措纳湖岸阶地,海拔4000米左右。2007年和2017—2018年的两次调查中各发现5个地点。10个地点的石制品原料以各种颜色的燧石为主,除石片、石叶、残片及工具外,还发现有细石核、细石叶等细石器产品。年代为5.3ka.B.P.左右[27,32]。
②下大武地点,位于玛沁县下大武乡,海拔3992米,发现于2007年。在黄土剖面采集大量原生层位石制品,原料以石英砂岩、燧石为主。石制品种类包括细石核、细石叶等,年代数据尚未公布[27]。
同時,过渡区域的延伸区域也有细石器遗址点的发现,如向南的通天河流域的细石器地点,发现的石制品以石片或石块为毛坯,单面或双面预制楔状缘,台面修疤浅平细小,剥片集中在石核的一侧等,均表现出与“阳原技术”和“拉乙亥技术”较高的相似性[33]。
二、其他发现
(一)古人类化石
目前,甘肃地区发现古人类化石的地点主要有夏河县白石崖洞、泾川县牛角沟、武山县大沟骨头沟3处,出土的古人类化石分别被称为夏河人、平凉人、武山人。另外,在石峡口第1地点还发现1枚古人类牙齿,属晚期智人[15],但相关的研究尚未报道。青海地区有关古人类的发现仅有贵南县拉乙亥遗址发现的拉乙亥智人牙齿[28]。
夏河人,1980年发现于甘肃省夏河县甘加乡白石崖洞遗址。出土有1件整体呈土黄色的人类右侧下颌骨化石,保存有完整的第一臼齿和第二臼齿,其他牙齿仅保留牙根部分[23]。研究发现其为中更新世古老型智人的一种,与西伯利亚Denisova洞穴发现的丹尼索瓦人亲缘关系最近,为Denisova洞穴以外首次发现的丹尼索瓦人,年代为190~30ka.B.P.,属旧石器时代中、晚期[17,18,34]。
平凉人,1976年发现于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的牛角沟。出土有一件不完整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包括一小片右额骨鳞部、右顶部大部、较完整右颞骨、枕骨的大部及一小部分左顶骨,属晚期智人。当时根据头盖骨各项特征及测量数据,认为其代表一个20岁左右的女性青年个体[35]。后来,李海军等通过对其颅骨顶矢状脊、乳突、耳孔上脊、枕外脊、枕外隆凸、枕骨上项线、枕骨圆枕和肌脊等8项非测量性状的观察,以及对星点间宽、星点至人字点距离、颅宽、耳上颅高、顶矢状弦、颞骨鼓板长宽等7项测量性状的分析,认为该人类骨骼应属于男性个体[36]。
武山人,1984年发现于甘肃省武山县鸳鸯镇的大沟骨头沟。古人类颅盖骨化石采集于灰黄灰褐色黏土中,包括完整的额骨和左右顶骨。根据其骨壁厚、额部后倾、眶上缘较圆钝、额骨眶突粗壮等特征以及各处骨缝愈合情况,认为其属于年龄20岁左右的男性个体。武山人眉脊不发达、前额稍隆起、脑膜中的动脉纹等都体现了现代人的特征,但颅骨骨壁较厚、眶上缘平直、眼眶外上角泪腺窝浅、顶骨后外交角有明显的角圆枕及颅骨盖低平、前囟点靠后、颅骨三段矢状弧长等特征则表现出一定的原始性。根据其出土层位的碳14测定结果,其年代为38.4±0.5ka.B.P.,属旧石器时代晚期[37]。
拉乙亥智人,发现于青海省贵南县拉乙亥乡。古人类牙齿出土于炉灶附近,磨损严重,牙根残。年龄在10~13岁之间,属智人。年代约为6.7ka.B.P.,相当于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早期[28]。
(二)古人类用火遗迹
旧石器时代古人类的活动痕迹多体现在用火遗迹上。
甘肃境内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用火遗迹较少,目前仅见于陇东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部分遗址和陇中盆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石峡口遗址。陇东地区的环县楼房子遗址发现有燃烧过的木炭屑,还有部分动物化石有燃烧过的迹象。如同一件化石一段呈黑色一段呈黄色;或数件化石成堆状分布,靠近中心位置的化石呈黑色,而边缘处化石呈黄色或者浅灰色[8,9]。陇中盆地的石峡口第1地点发现2处火塘类型用火遗迹(H1、H2)[15],每处用火遗迹中均有石制品、动物碎骨、烧骨、炭屑,H2还发现有集中分布的灰烬层、烧石等,说明当时人们在用火时有意控制火势。
青海地区发现人类用火行为的遗迹数量相对较多(如表一),以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发现为主,年代为15.4~4.85ka.B.P.,集中在青海湖盆地和共和盆地,过渡区域也有一定数量的发现,柴达木盆地暂无相关报道。用火遗迹多较为简易,用砾石简单砌筑,有设计合理、考虑通风的火塘,周围一般有石制品、骨器、碎骨等文化遗物。
(三)古动物化石与古环境
甘肃地区,在陇东的西峰巨家塬,环县楼房子、刘家岔,镇原黑土梁,泾川南峪沟、桃山嘴、牛角沟、合志沟等遗址均发现有动物化石;陇中盆地的张家川杨上和石峡口、庄浪徐家城和双堡子等遗址也发现有动物化石。其中以巨家塬遗址[38]和楼房子遗址[8]的研究较深入。两遗址出有文化遗物的杂色湖相黏土堆积与萨拉乌苏组同期,所含的动物化石也与萨拉乌苏动物群基本相同,包括披毛犀(Coelodonta antiquitatis)、野驴(Equus hemionus)、赤鹿(Cervus elaphaus canadensis)、河套中国大角鹿(Sinomegaceros ordosianus)、普氏羚羊(Gazella przewalskii)、恰克图转角羚羊(Spiroceros kiakhtensis)、原始牛(Bos primigenius)、水牛(Bubalus sp.)[8],在巨家塬龙骨沟地点还发现了纳玛古象(Paleoloxodon namadicus)[38]。過去,萨拉乌苏动物群一直作为晚更新世中晚期的代表动物群,近年来随着地层学和年代学工作的深入开展,萨拉乌苏遗址地层又被进一步划分:原萨拉乌苏组被划分为三部分,顶部为全新世大湾沟组,其下为城川组,最下部为现萨拉乌苏组[39]。其中萨拉乌苏组又被划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下部年代相当于以王氏水牛和诺氏古棱齿象为代表的末次间冰期,上部组合相当于以野驴和披毛犀为代表的末次冰期第一阶段[40]。据此可以推测,巨家塬和楼房子遗址的年代或许要早到旧石器时代中期。
青海地区在青海湖盆地的江西沟1号地点、151遗址、娄拉水库地点及共和盆地的拉乙亥遗址等发现少量动物碎骨,其中仅有151遗址进行了动物种属鉴定及相关研究。151遗址发现大量大型有蹄类动物(89.7%)骨骼,以野牛、野马、野驴为主,还有少量小型有蹄类动物(9.5%)和小型哺乳动物(0.8%)的骨骼,未见食肉动物骨骼。这些动物骨骼以火塘为中心分布,表面没有食肉和啮齿动物的啃咬痕迹,并且伴出一些人工制品,说明人类可能曾在此进行采食活动[26]。共和盆地及过渡区域的遗址点多出有火塘遗迹、较为破碎的动物骨头以及以细石器为主的石制品,说明此时的古人类继续保持狩猎采集的生业模式。
三、思考与讨论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可以发现,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考古研究工作开始较早,但一直以来发展较为缓慢,直到进入21世纪,这一区域的相关发掘和研究工作才陆续有所进展。下面将就石器工业类型、古人类行为及与环境变化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1.甘青地区旧石器工业特点
陇东地区的旧石器文化与华北北部旧石器文化有一些相似之处,属于石核—石片—刮削器的北方小石器系统。具体来讲,刘家岔遗址的石制品在原料和形制上都与许家窑—侯家窑遗址群出土者相近,楼房子遗址有类似莫斯特软锤修理风格的刮削器,其来源还需进一步探究。陇中盆地与陇东地区相邻近,杨上、徐家城等遗址均呈现北方小石器系统特征。除此之外,华北地区旧石器晚期常见的细石器工业不见于陇东地区,却在陇中盆地的大地湾、石峡口等遗址有所发现。需要指出的是,甘肃中西部的王家遗址出土了一件半月形刮削器,以往研究认为其与山西蒲县薛关出土的同类石制品有相似之处[16],加工技术应属细石器工业。但笔者认为,该遗址仅发现这一件半月形刮削器,很难就此认定该遗址属于细石器工业。
甘肃最西端的霍勒扎德盖遗址处于旧石器时代末期,发现的石叶具有规整的形态、细致修理的台面以及梯形的断面[16],与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41]出土的同类制品很相似(图三)。宁夏水洞沟遗址的石叶技术最早在40ka.B.P.出现[42],在此之前,西伯利亚的Denisova洞穴[43]和乌兹别克斯坦的Obi-Rakhmat洞穴[44]已经发现有60ka.B.P.左右和早于45ka.B.P.的石叶技术。另外,青藏高原也曾发现零星的石叶工业,尤其是西藏尼阿底遗址的石制品具有典型石叶技术的特征,年代不早于40ka.B.P.[45]。笔者推测,石叶技术可能是来自新疆阿尔泰地区及蒙古高原,在东进南下过程中进入甘青地区,甚至还进入了更南的青藏高原地区。
青海地区的石器工业在不同阶段和地域有着不同的特点。柴达木盆地内部的旧石器文化在形制和组合上存在一定的差异。30ka.B.P.左右,小柴达木湖遗址的石器组合与华北以刮削器为主体的小石器系统特征相同,而冷湖1号地点采集的一件似勒瓦娄哇石核则与宁夏水洞沟遗址出土者相似[20],说明这一时期两种工业技术均已进入柴达木盆地。近年来,勒瓦娄哇技术在新疆阿勒泰的通天洞遗址[46]、西藏的日土扎布勒遗址[47]均有发现,冷湖1号地点位于新疆与西藏的中间地带,所以勒瓦娄哇技术可能是以柴达木盆地为通道传播的。15ka.B.P.以来,青海湖盆地及共和盆地发现多处以细石器为特色的地点,如黑马河1号地点、江西沟1号地点等,说明此时细石器工业已经进入青海地区;同时,这些地点也出土有属于小石器系统的石制品,与同时期东北亚地区旧石器晚期文化的石器工业面貌基本一致[27]。到了7ka.B.P.,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及过渡区域在保留细石器工业的基础上,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如黑马河3号地点、江西沟2号地点、铜线遗址等发现有陶片[25],这一时期,仰韶文化的人群发生了大范围的扩散和迁徙,甘青地区也发现有马家窑、宗日等地方型考古学文化,青海湖发现的陶片或与此有关。所以,青海湖盆地及附近区域石器工业的阶段性特点,可能与不同阶段不同人群的迁入有关。
2.甘青地区旧石器时代人类活动
甘青地区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材料,以发现于青藏高原边缘的白石崖洞的夏河人时代最早,存续时间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与西伯利亚Denisova洞穴发现的丹尼索瓦人有紧密的遗传关系,也是目前东亚地区同时期除古老智人、现代人以外新发现的又一类人群,为探讨东亚地区古人类演化及现代人起源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该发现使丹尼索瓦人的分布范围进一步扩大至东亚的青藏高原边缘,反映了人类在高海拔地区生存的成功尝试[17]。对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平凉人和武山人,经研究,二者均属晚期智人,但尚不确定他们是否也含有丹尼索瓦人基因或者现代人基因。
甘肃地区目前发现的各个遗址点,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大岭上、杨上遗址,到旧石器时代中期的楼房子、巨家塬、刘家岔等遗址,再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徐家城、大地湾以及石峡口等遗址(或地点)等均发育于间冰期、末次冰期的间冰段、冰阶内的弱成壤层阶段等相对暖湿的时期。尤其是在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巨家塬、楼房子等遗址发现了大量属于萨拉乌苏组动物群的骨骼化石,反映了这一阶段人类生存环境的变化。楼房子披毛犀牙齿年龄结构“成年居优型”的特点,说明古人类可能已经开始有选择地利用动物资源,有针对性地选择成年披毛犀作为狩猎对象[48]。若与周边地区比较,就会发现该地区的地层堆积和哺乳动物群与泾河中游的陕西乾县[49]、长武窑头沟遗址[50]比较相似,说明当时在泾河中上游一带可能存在一次人类活动高峰。
青海湖地区目前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至新石器时代的一系列遗址,反映了当时人类在这一区域的活动与气候的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15.4~13.1ka.B.P.和12ka.B.P.前后,青海湖盆地受末次冰消期的影響,进入相对较暖的时期,温度上升,降水增多,植被由疏林草原代替了荒漠草原[51],生态环境较为适宜人类生存,食物资源相对丰富。自然环境的改善导致来自低海拔地区的先民开始进入,人群的分布范围有所拓展,151遗址及江西沟1号、黑马河1号等地点可能是这批迁徙者留下的狩猎采集临时性营地[52]。7ka.B.P.左右转入全新世大暖期,气温及降水条件均相对优渥,为当时的人群迁徙提供了适宜的自然条件[53],让他们有条件走向共和盆地及更远的过渡区域——冬给措纳湖流域及昆仑河流域。
用火遗迹较多发现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的陇中盆地及青海湖盆地各遗址,同时伴出有破碎或带有火烧痕迹的动物骨骼。特别是青海地区发现的用火遗迹,有的极其简陋,呈火堆状,如151遗址及江西沟1号、黑马河1号等地点;有的构筑讲究,呈火塘状,并充分考虑增氧助燃等功能,如晏台东、铜线等遗址。由此我们可以猜测,取火和控制火的技术的掌握使季节性的采集狩猎活动成为可能,而这些临时性营地出土的炭屑、火烧碎骨、石制品等,可能是人群在迁徙过程中遗弃的。这也进一步说明,这一阶段人类对动物资源及自然力的开发利用有了较大的进步。同时,也期待更多材料的发现,能更充分地论证人类的行为模式。
————————
[1]张多勇,马悦宁,张建香.中国第一件旧石器出土地的调查[J].人类学学报,2012(1):51—59.
[2]谢骏义,张鲁章.甘肃庆阳地区的旧石器[J].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7(3):211—222.
[3]许新国.青海考古的回顾与展望[J].考古,2002(12):3—11.
[4]甘肃省博物馆.甘肃古生物化石与旧石器时代考古[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1:112—150.
[5]仪明洁.青海省旧石器的发现与研究[C]//董为.第十三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12:187—194.
[6]刘玉林.甘肃泾川大岭上发现的旧石器[J].史前研究,1987(1):37—42.
[7]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环县刘家岔旧石器时代遗址[J].考古学报,1982(1):35—48.
[8]薛详煦.甘肃环县楼房子晚更新世哺乳动物化石及文化遗物[M]//王永焱,等.黄土与第四纪地质.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108—137.
[9]杜水生,杨宇霞,王辉.文化交流或适应趋同:甘肃环县楼房子遗址2011—2012年发掘的新材料[J].第四纪研究,2019(6):1443—1456.
[10]NIAN X M,Li F,CHEN F Y,et al. Optically Stimulated Luminescence Ages for Human Occupation during the Penultimate Glaciation in the Western Loess Plateau of China[J]. Journal of Quaternary Science,2016,31(8):928—935.
[11]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张家川县文广局.甘肃张家川县杨上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J].考古,2019(5):66—77.
[12]李锋,陈福友,王辉,等.甘肃省徐家城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J].人类学学报,2012(3):209—227.
[13]谢骏义,陈善勤.记甘肃大地湾遗址剖面和旧石器遗存[C]//董为.第九届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学术年会论文集.北京:海洋出版社,2004:233—242.
[14]张东菊,陈发虎,BETTINGER R L,等.甘肃大地湾遗址距今6万年来的考古记录与旱作农业起源[J].科学通报,2010(10):887—894.
[15]任进成,周静,李锋,等.甘肃石峡口旧石器遗址第1地点发掘报告[J].人类学学报,2017(1):1—16.
[16]谢骏义.甘肃西部和中部旧石器考古的新发现及其展望[J].人类学学报,1991(1):27—33.
[17]ZHANG D J,XIA H,CHEN F F,et al. Denisovan DNA in Late Pleistocene Sediments from Baishiya Karst Cave on the Tibetan Plateau[J].Science,2020,370:6516.
[18]张文静,李杰.考古证实:甘肃白石崖溶洞是青藏高原目前已知最早考古遗址[DB/OL].(2019-06-16)[2020-10-02].http://www.xinhuanet.com/2019-06/16/c_ 1124630418.htm.
[19]仪明洁,高星,张晓凌,等.青藏高原边缘地区史前遗址2009年调查试掘报告[J].人类学学报,2011(2):124—136.
[20]XING B G . Peopling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J]. World Archaeology,2006,38(3):387—414.
[21]黄慰文,陈克造,袁宝印.青海小柴达木湖的旧石器[C]//中国科学院中澳第四纪合作研究组.中国—澳大利亚第四纪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7:168—175.
[22]刘景芝.青藏高原小柴达木湖和各听石制品观察[J].文物季刊,1995(3):6—20.
[23]刘景芝,王国道.青海小柴达木湖遗址的新发现[N].中国文物报,1998-11-08(1).
[24]MADSEN D B,MA H Z,BRANTNGHAM P J,et al. The Late Upper Paleolithic Ooccupation of the Northern Tibetan Plateau Margin[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2006,33(10):1433—1444.
[25]RHODE D,ZHANG H Y,MADSEN D B,et al. Epipaleolithic/early Neolithic Settlements at Qinghai Lake, Western China[J].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2007,34(4):600—612.
[26]王建,夏欢,姚娟婷,等.青藏高原末次冰消期狩猎采集人群的生存策略研究[J].中国科学:地球科学,2020(3):380—390.
[27]高星,周振宇,关莹.青藏高原边缘地区晚更新世人类遗存与生存模式[J].第四纪研究,2008(6):769—977.
[28]盖培,王国道.黄河上游拉乙亥中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J].人类学学报,1983(1):49—59.
[29]青海省文物考古队.青海龙羊峡达玉台遗址的打制石器[J].考古,1984(7):3—7.
[30]汤惠生,周春林,李一全,等.青海昆仑山山口发现的细石器考古新材料[J].科学通报,2013(3):247—253.
[31]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再现文明:青海省基本建设考古重要发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32]陈宥成,侯光良,高靖易,等.青藏高原冬给措纳湖畔新发现的细石器及其同周边地区的技术关系[J/OL].人类学学报,2019(网络版):301—312[2020-10-02].http:// kns.cnki.net/kcms/detail/11.1963.Q.20190408.1555.001.html.
[33]韩芳,蔡林海,杜玮,等.青南高原登额曲流域的细石叶工艺[J].人类学学报,2018(1):53—69.
[34]CHEN F H,Welker F,Shen C C,et al. A Late Middle Pleistocene Denisovan Mandible from the Tibetan Plateau[J]. 2019,569(7756):409—412.
[35]刘玉林,黄慰文,林一璞.甘肃泾川发现的人类化石和旧石器[J].人类学学报,1984(1):11—18.
[36]李海军,吴秀杰.甘肃泾川化石人类头骨性别鉴定[J].人类学学报,2007(2):107—115.
[37]谢骏义,张振标,杨福新.甘肃武山发现的人类化石[J].史前研究,1987(4):47—51.
[38]丁梦麟,高福清,安芷生,等.甘肃庆阳更新世晚期哺乳动物化石[J].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5(1):89—103.
[39]祁国琴.内蒙古萨拉乌苏河流域第四紀哺乳动物化石[J].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4):239—249.
[40]同号文,李虹,谢骏义.萨拉乌苏动物群有关属种的修订与讨论[J].第四纪研究,2008(6):1106—1113.
[41]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水洞沟:1980年发掘报告[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42]LI F,KUHN S L,BAR-YOSEF O,et al. History,Chronology and Techno-Typology of the Upper Paleolithic Sequence in the Shuidonggou Area, Northern China[J]. Journal of World Prehistory,2019,32(2):111—141.
[43]DEREVIANKO A P. The Middle to Upper Paleolithic Transition in the Altai(Mongolia and Siberia)[J].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2001,3(7):70—103.
[44]DEREVIANKO A P,SHUNKOV M V,KOZLIKIN M B,et al. Who Were the Denisovans[J]. Archaeology,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of Eurasia,2020,48(3):3—32.
[45]ZHANG X L,HA B B,WANG S J,et al. The Earliest Human Occupation of the High-altitude Tibetan Plateau 40 Thousand to 30 Thousand Years Ago[J]. Science,2018,362(6418):1049—1051.
[46]于建军,王幼平,何佳宁,等.新疆吉木乃县通天洞遗址[J].考古,2018(7):3—14.
[47]BRANYUNG P J,GAO X,OLSEN J W,et al. A Short Chronology for the Peopling of the Tibetan Plateau[J]. Developments in Quaternary Sciences,2007,9(7):129—150.
[48]景明.甘肃环县楼房子遗址动物群的年龄结构[D].北京:北京师范大学,2014.
[49]裴文中.陕西乾县发现的纳玛象化石[J].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4):215—217.
[50]黄万波,郑少华.记陕西长武晚更新世人牙及共生哺乳动物化石[J].人类学学报,1982(1):14—17.
[51]LIU X Q,SHEN J,WANG S M . A 16000-year pollen record and Ancient Environment Evolution[J]. Chinese Science Bulletin,2002,47(17):1351—1355.
[52]侯光良,许长军,樊启顺.史前人类向青藏高原东北缘的三次扩张与环境演变[J].地理学报,2010(1):65—72.
[53]侯光良,张雪莲,王倩倩.晚更新世以来青藏高原人类活动与环境变化[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5(2):54—63.
〔编辑:迟畅;责任编辑:李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