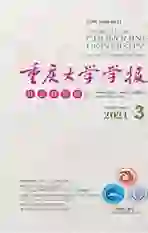刑法中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
2021-08-06梅传强刁雪云
梅传强 刁雪云
摘要:当前对兜底条款的主要解释方法为同类解释规则,但该规则在学术理解和司法适用过程中出现了误区和困境。该解释方法不能概括兜底条款的全部适用范围,还存在任意解释的缺陷,不能准确划定兜底条款的解释范围。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一方面,来源于同类解释规则本身的标准尚未统一;另一方面,滥觞于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的指导功能被遗漏忽视。立法活动总是围绕规范保护目的进行,例示条文与兜底条款作为法律文义表达的部分内容,均受具体条文的规范保护目的制约,发挥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解释的指导作用有助于限定行为入罪范围。此外,相较于模糊、抽象的兜底条款,例示条文具有明确行为类型的作用。因此,就同类解释规则的标准而言,应采用行为类型标准说,更有利于行为刑事违法性的判定,以避免规范保护目的成为兜底条款的唯一解释依据,从而产生将实质违法性作为唯一入罪理由的风险。重视规范保护目的及例示条文对兜底条款解释的双重制约,有助于实现法安定性与灵活性的协调。
关键词:兜底条款;规范保护目的;同类解释规则;刑法解释;法律适用
中图分类号:D924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21)03-0110-12
一、问题的缘起:由最高人民法院97号指导案例引发的思考
在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97号指导案例中,原审法院认为王某在未办理粮食收购许可证,未经工商管理登记的情况下,擅自收购玉米的行为,应当适用非法经营罪之兜底条款。而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在指定再审时提出,适用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应当根据相关行为是否具有与《刑法》第225条前三项规定的非法经营行为相当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进行判断”①。最终再审法院以王某收购玉米的行为未严重扰乱市场秩序为由改判其无罪。原审法院在审理此案时,运用了同类解释规则,将无证收购玉米的行为与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行为进行类比,两者在没有经营许可证,买卖行政法规规定的专营、专卖物品方面,具有同类性。表面上看,将同类解释规则作为理解兜底条款的方法,遵循了体系解释的规律,导出了法秩序统一的结论。但实质上,仅仅将同类解释规则作为兜底条款的唯一解释标准,容易忽视条文规范保护目的,最终损害刑法法益保护和人权保障的两大基本价值。
自储槐植教授较早提出同类解释规则后,在兜底条款解释的相关文献中,未提及同类解释规则者鲜有在知网上以“兜底条款”为篇名查阅到,2009年到2019年,71篇相关论文中有59篇论文提及了同类解释规则或体系解释。。其中大部分将同类解释规则直接作为兜底条款解释之方法,而对同类解释规则的质疑则从2016年始才有学者提出[1]。纵然这是不完全统计,却也间接说明了学者运用同类解释规则对兜底条款进行解释是普遍现象。虽然不能否认同类解释规则在阐明兜底条款内容时的作用,但“玉米案”充分说明了该规则并非解释兜底条款的唯一真理,如果仅使用同类解释规则进行兜底条款解释,结论未必可靠。最高人民法院提及的“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刑事处罚必要性”,实际上说明了在运用同类解释规则时,还应当重视条文的规范保护目的,从而形成例示条文与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的双重制约,有利于探明兜底条款的内涵,更有利于抑制兜底条款的滥用。
二、问题的分析:同类解释规则的来源及适用误区
(一)同类解释规则的起源
刑法条文的设定主要有三种模式:概念式立法,如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罪;列举式立法,如票据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综合概念式和列举式的例示主义立法,如虚假破产罪、非法经营罪。其中例示主义立法集中体现了法安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兜底条款的立法都属于例示主义立法,法律既列举了部分行为对象、行为方式、行为主体,又以“其他”涵括了潜在类似行为的入罪可能性。
同类解释规则是例示主义立法模式的主要解释规则,是解释兜底条款时运用最广泛的规则,但对同类解释规则的定义有所不同。部分学者认为通过同类解释规则可以得出结论是兜底条款隐含了与列举情形相似的行为[2]。亦有学者指出同类解释规则就是指兜底条款与例示条文具有相当性,兜底条款既然存在于相关罪刑条款之中,就必须与前面所列举的行为相当[3]。还有学者指出兜底条款规定之行为,应当与该罪明示列举的部分具有“同质性信息”,而“同质性信息”应当从该罪的实质中探析[4]。在我国,较早提出同类解释规则的学者认为,解释兜底条款必须结合列举事项,仅限于与之同類的情形,而不包括不同类的部分[5]。
同类解释的体系性思维值得赞赏,但同类解释规则并不能完全准确揭示兜底条款之真意,忽略了条文规范保护目的的同类解释规则,不当限缩或过分扩大了兜底条款的范围。
(二)同类解释规则的适用误区
首先,同类解释规则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来自其本身的疑问:同类的内容何为,即同类解释标准的问题,同类的对象究竟是例示条文还是例示结果。以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为例,该罪前三项列举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三种情形,第四项为“其他操纵证券、期货市场行为”的兜底条款。采用不同标准,对抢帽子交易行为抢帽子交易即证券机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买卖或持有相关的证券,并对该证券或其发行人、上市公司公开作出评价、预测或者投资建议,以便通过期待市场波动取得经济利益的行为。的定性则不同。如果从行为视角出发,则类比对象是“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或者持仓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期货交易”,“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自买自卖期货合约”三项行为,此时抢帽子交易的行为就不应该被兜底条款包含,应予出罪。理由在于,抢帽子交易的行为方式主要分为三步,即买入股票,发布推荐,快速抛出,本质上是通过发布虚假的咨询报告,误导投资人购买证券、期货,从而影响供求关系。而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规定的行为是联合买卖、连续买卖、相对委托和洗售,本质上是直接利用交易行为影响供求关系。结论为抢帽子行为与例示条文行为类型不相符,不构成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如果从结果视角出发,类比抢帽子交易行为与前三项行为所造成的结果,则会增加该行为的入罪可能性。因为抢帽子交易行为通过发布虚假信息等不正当方式,影响了证券、期货的交易价格和交易量,这与该罪前三项行为造成的“操纵证券、期货交易价格或者证券、期货交易量”之结果同类。可见,同类解释规则类比标准将直接影响行为成罪与否的判断。
其次,同类解释规则不能概括兜底条款的全部适用范围。同类解释规则的重要基点就是通过类比性思维限缩兜底条款“口袋化”的扩张功能,而兜底条款的设立目的是为司法预留空间,以增加法律的社会适应能力[6]。同类解释规则这种偏向于限制解释的方案,并不利于填补法律漏洞,更与阐明兜底条款适用范围无益,兜底条款的补充功能将被无差别削弱,这与兜底条款的立法初衷格格不入。如《彩票管理条例》第38条规定“擅自发行、销售彩票,或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发行、销售境外彩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种行政法规中包含的附属刑法,以刑事罚则确定了非法经营罪兜底条款的适用,已经超出了该罪以同类解释规则导出的结论。
最后,同类解释规则具有任意解释的空间,存在过分扩大兜底条款适用范围的风险。同类解释规则的出发点是,通过限制解释的方案,抑制兜底条款的扩张,防止与罪刑法定的渐行渐远。然而,该方案难以达到预设效果,不能对兜底条款的任意解释起到限制作用。哪怕同样使用同类解释规则方法的解释者,也会根据自身价值取向,得出不同结论。如面对抢帽子交易行为,有的学者认为要根据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已明确的行为类型,探索兜底条款的实质同等价值,同类信息应当从行为类型和实质内涵两方面获取。抢帽子交易行为虽然不满足既定行为类型的规定,但是具有操纵的实质内涵,因此抢帽子交易行为具有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的刑法属性[4]。相反,有的学者使用同类解释规则,认为抢帽子交易不具有同质性,应予出罪[7]。从体系解释的角度看,抢帽子交易行为与《刑法》第182条第1款前三项规定的行为不具有同质性,不属于操纵市场的行为[8]。总之,同类解释规则既能证成,也能证伪,如果仅使用同类解释规则,该方法就会沦为解释者论证个人价值预判的工具。
(三)同类解释规则适用误区成因
同类解释规则需要提炼出例示条文的特性,再通过已明确的特征类比导出兜底条款的隐藏含义。该规则的参照要素主要是条文已经明确的例示项,参照标准则存在行为类型、行为结果两种。同类解释规则属于体系解释的一种,重视了同一层级的例示条文对兜底条款的限制,但忽视了规范保护目的对例示条款及兜底条款的统领作用,最终既不能引领出兜底条款真谛,也背离了限制解释的初衷。
首先,将行为类型作为类比对象时,最容易仅考虑具体例示项的行为特征对兜底条款之借鉴作用,而置抽象的规范保护目的于不顾。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条明确了未经有关部门批准,以营利为目的,经常向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的,依照《刑法》第225条的兜底条款,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未获得监管部门批准进行贷款发放,与非法经营罪已列明的前三项具有行为上的同类性,但若忽视该条文对市场秩序的保护目的,则可能存在两种误区。其一是将仅向单位内部人员出借资金,将没有扰乱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纳入非法经营罪中,从而打击单位经营活力,不利于市场良性发展。其二是将以发放贷款为目的,特意吸收不特定的单位外人员进入到单位中,再向其发放贷款的行为排除在非法经营罪之外,轻纵单位非法经营行为。因此,将行为类型作为同类标准时,不能忽视规范保护目的而做出兜底条款解释。
其次,将行为结果作为类比对象,犯了用实质后果代替形式标准的错误,是刑法作为二次调整法对规制范围的僭越。不论是行政违法行为还是刑事犯罪行为,都具有社会危害性,刑法作为报应和预防犯罪不得已的“恶”,仅将其中具有相当程度的社会危害行为作为犯罪处理。而立法者最终将哪一部分社会危害行为视为值得刑法处罚的行为,就集中体现为刑事违法性。任何犯罪行为都具有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和应受刑法处罚性的特征,其中,犯罪客体主要体现了社会危害性,犯罪客观方面和犯罪主体体现了刑事违法性,犯罪主体及犯罪主观方面体现了应受刑法处罚性。具体到兜底条款当中,例示条文的行为类型就是对刑事违法性的举例,而例示条文造成的最终结果是社会危害性的体现。如若运用同类解释规则时,将行为结果作为类比对象,就会陷入只用实质危害后果评价行为犯罪与否的风险中,造成随意出入人罪的状态。
综上所述,不论同类解释采用哪一种同类标准,都存在难以化解的弊端,要走出同类解释规则的泥潭,就需要规范保护目的和同类解释标准的双重回归。当同类解释规则失灵时,回溯到特定类型所蕴含的规范目的[9]。
三、问题的解决:双重标准的提倡
(一)内在标准——用规范保护目的统领兜底条款解释
1.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解释的指导作用
上述最高人民法院在97号指导案例中要求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相当”之理由,就包含了规范保护目的统领兜底条款解释的理念。规范保护目的的概念和运用起源于客观归责理论中,是“制造法所不允许的风险”中的一大要素。这一概念的产出及运用的原始作用在于否认行为人的责任,限制刑法处罚范围。其实规范保护目的的意义不止如此,它不是单纯地限制处罚范围,而是准确揭示了立法目的,提高了行为认定的科学性。当行为和结果在规范保护目的之外时,处罚行为人不能达到一般预防的效果[6],處罚规范保护目的之外的行为让刑法失去意义。法律作为人类能动意识的创造,是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其本身的遵守并不是目的,遵守后所欲达到的效果才是目的。立法活动总是先有目的,再根据目的形成文字规范语言,因而法律是有目的的,而目的是可以探寻的。所有的刑法条文都有一个目的指引,在该目的下犯罪构成要件要素得以建立。对构成要件要素的理解必然受该条规范保护目的的制约,也即规范保护目的对构成要件要素同时具备建构和解构的作用。发挥规范保护目的的指引功能,旨在遵循法律构建规律的基础上,面对条文时始终优先思考,刑法为何做此规定,该规定旨在保护什么,从而探寻立法真谛。
兜底条款以“其他”的方式规定在法律文本中,具有堵截犯罪人逃脱法网的功能,堵截性犯罪构成具有极大的概括性和弹性,稍有不慎便会导致刑罚权的极度扩张。如2011年群情激愤的刘某生产销售“瘦肉精”案2007年初,曾在湖北某制药厂任职的刘某与奚某约定共同投资,研制、生产、销售“瘦肉精”用于生猪饲养,直至2011年3月,刘某等5人共研制、生产、销售“瘦肉精”2 700余公斤,非法获利250万余元。,最终为了安抚民意而追求重刑,法院适用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兜底条款,刘某获死刑。然而,刘某实施的生产、销售猪肉间接危害人体健康的行为与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直接、紧迫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明显不同,并不满足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设立的目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旨在禁止故意对不特定多数人直接造成人体危害,具有一定紧迫性的行为,意在保护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身体安全。反观刘某的行为并非直接作用于人,而是先要进入生产流通领域,不具有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保护目的规定的相当法益侵害紧迫性。主观目的上刘某也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而非危害公共安全。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中的兜底条款,在刑罚上虽然满足了民众的期望,却不具有法律上的妥适性。讽刺的是,同年河南省出现的第二批“瘦肉精”案件,事实与刘某案大同小异,法院却大相径庭地适用了非法经营罪中的兜底条款。两个在事实上差异甚微的案件却适用了不同的兜底条款,罪名截然不同,刑法适用后果天壤之别,可见脱离了对规范保护目的的考量,兜底条款的解释空间将被扩大,甚至沦为服务于政策、舆论的工具,成为司法者扩张犯罪圈、加重刑罚的利器。
在现实情况下,立法往往是通过例示项与兜底项相结合的方式规定兜底条款,从而达到具体性与抽象性、稳定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兜底条款是法律文义表达的一部分,源自规范保护目的,与例示条文一同受到规范保护目的的制约,因此与规范保护目的之间呈现为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鉴于兜底条款与规范保护目的的此种关系,要明确兜底条款的范围,就必须首先弄清条文的规范保护目的。规范保护目的的内涵是什么?规范保护目的如何探明?又如何指导兜底条款解释?要解答这些疑虑,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解释的立场问题。
2.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解释的应然立场
进行兜底条款解释时,只有在特定规范目的下,才能探寻例示条文类型的本来面貌,所以要用目的解释补足兜底条款的残缺要素[9]。而刑法解释是一种目的性的论证,裁判者对规范的理解是实质性的知识构建,以此弥补刑法规范适用的困境[10]。目的解释是还原规范保护目的的重要方法之一,目的解释是手段,探寻规范保护目的是目标。对目的解释采取什么样的立场,直接决定了规范保护目的的去向。目的的解释存在主观目的解释、客观目的解释两种立场。从主观目的解释出发,就会认为在进行条文解释时,应当按照立法者规范制定时所欲实现的保护目的作为解释的标准。从客观目的解释出发,则会认为因为条文一经制定就拥有了独立生命力,所以应当以条文本身的客观规范目的作为解释基准。
采取主观主义目的解释的立场阐明规范保护目的具有合理性,可以满足罪刑法定的要求和现代法治基本精神。为了避免司法恣意,罪刑法定原则要求法官作为解释者应当遵从立法者的价值设定,否则就是篡夺立法权,难以实现现代法治基本精神,目的的追溯要从立法者的视野出发。刑法规范创设的目的在立法阶段就已然得到了贯彻,法条并不能朝令夕改,创设阶段到适用阶段存在相当长的时间差,刑法规范的适用阶段也存在某些目的,但此时的目的并不一定是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有学者认为由于经济发展的日新月异,变迁迅速,应当在经济犯罪领域采取客观目的解释,在对经济刑法规范进行目的论解释时,使用以边际效益及边际成本为中心的经济分析法[11],但如若采取客观目的解释的立场,对法条的解释就可能脱离立法划定刑罚边界的缰绳。
采取客观主义目的解释的立场发现规范保护目的不具有合理性。在諸如兜底条款一类具有模糊性和扩张性的法条中,尤其不能使用客观主义目的解释的立场。当司法者持客观目的解释观点时,其以刑法法条本身的客观目的作为解释根据,就有可能背离由立法者根据立法时的情景创设出来的价值目标,这样一来,所谓的在探寻立法条文的真实含义前提下解释法律的过程,不过是法官基于个人价值判断预设案件结果,再论证预设结果的过程罢了。
以非法经营罪为例,如果采用客观目的解释论,不去探究该条制定时的规范保护目的,该条就容易成为现阶段打击某些行为的工具。在我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期,以及经济改革不断深化时期,自由竞争市场的开放为我国经济注入崭新血液的同时,也催生了大量新型经济违法行为。为了净化市场行为,将非法经营罪做违法行为时的客观目的解释,就会背离立法初衷。如有学者基于经济转型期,市场经济体制确立的背景,认为非法经营行为大量存在,因此必须发挥国家的“有形之手”,将非法经营罪的犯罪客体理解为正常的市场交易秩序[12],只要行为扰乱了市场秩序,就构成非法经营罪。还有论者指出非法经营罪破坏的市场管理秩序是整个国家经济活动的秩序[13]。令人困惑的是,国家整体经济秩序边界之大,甚至可以含括所有经济犯罪类型。如此一来,非法经营行为的内容将不胜枚举。对非法经营罪规范保护目的的理解决定着对该条第4项兜底条款的把握,决定着某些经营行为入罪与否的命运,在非法经营罪不断扩张沦为口袋罪的现状下,有必要回归立法时的规范保护目的,才能逃离犯罪圈漫无边际的现状。我国刑法是法律移植的产物,深受苏联刑法体系的影响。在俄罗斯学者看来,非法经营罪设立的目的在于预防经营活动事实上转变为非法的“影子”经济,从而预防经营活动脱离国家监督,因为这种情况一般导致经营者不履行对国家和公民负有的义务[14]。非法经营罪是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下的个罪,其侵害的法益除了宏观的市场经济秩序或国家整体经济秩序外,还存在个罪法益具体化的问题,因此不能广而化之地理解该罪侵害的法益,结合非法经营罪前三项规定来看,该罪并非是要将所有侵犯经济秩序的行为包含其中,而是通过保护特许经营形成的那部分市场秩序。因此,将非法经营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定位于市场准入秩序,更符合法律制定时的价值追求,也更能限制非法经营罪的滥用。
3.规范保护目的探明的实然路径
规范保护目的存在空间分为内部协调型(同一刑法条文内部)、总则分则型(总则条文与分则条文),以及内外交织型(刑法和所参照的法律、法规)三类[6]。而兜底条款本身的抽象性和模糊性决定了单纯从兜底条款出发无法复原法律规范保护目的。所以,需要从条文内部和外部两个面向探求规范保护目的。在条文内部,可以通过逆推法,分析、整合例示条文所欲实现的规范保护目的。在条文外部,可以通过总则与分则之间、不同条文之间呈现的逻辑关系推导具体条文的规范保护目的。再由该规范保护目的导出兜底条款的正确解释结论,这样既可以增加规范保护目的发现的科学性,又能制约兜底条款的解释结论。就顺序来说,应当遵循从外到内的顺序,即从条文外部到条文内部,这亦是由抽象到具体的过程。
首先,从条文外部看,可以大致明确具体条文规范保护目的的范围。条文外部的要素包括了章节位置,与刑法其他条文的关系,与其他所参照法律法规的比较。其一,刑法通过类型划分,将具有相同法益侵害类型的犯罪规定在同一章节,每个章节的具体罪名既有自己独特的规范保护目的,也能被所属章节总括性的规范保护目的所包含。如合同诈骗罪位于刑法第三章第五节金融诈骗罪中,其规范保护目的必然与金融管理秩序挂钩,并非在金融领域发生的诈骗行为就不能构成合同诈骗罪。其二,就与刑法其他条文的关系来说,除了要考察分则条文之间的关系,遵循不可能有两个规范保护目的完全重合的规律,还要将目光放到总则与分则的关系中去。在进行兜底条款符合性判断时,要用总则第13条“情节显著轻微不认为是犯罪”的规定检验行为入罪的结论是否合理。利用中国在犯罪成立上“定性+定量”的模式,将不具有刑罚妥当性的行为排除在犯罪圈外,形成对兜底条款适用的制衡。其三,刑法具有二次保障法的地位,其规范保护目的是行政法、民法等规范保护目的的盾牌。当其他法律并未确定某一行为的违法性时,刑法不得篡位,优先确定行为的违法犯罪性质,更不能用兜底条款将此行为解释为符合某一犯罪构成。如1999年出台的《刑法修正案》在将操纵期货市场的行为纳入操纵证券市场罪,由1997年《刑法》中的操纵证券市场罪变为了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但当时并没有期货交易相关行为被部门法确认为违法之现实,直到2007年才有了《期货交易管理条例》,那么1999年至2007年间,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的正当性就疑团莫释。
其次,通过条文内部观察规范保护目的,既可以细化其范围,也可以检验第一步之结论。立法制定时的“立法原意”会被表现在条文内部的规范文字中,同法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一样,立法意图亦是法的精神品格之所在。整个法案都是围绕立法意图设计的,要较好地完成法案起草任务,务必明确立法意图[15]。这反过来说明了,法律规范语言是探寻规范保护目的不可或缺的资料,通过可见的文字表达可以逆推语言背后隐性的规范保护目的。法律是行为规范,通过简单、明确的文字使社会一般人知悉和了解可为与不能为,具有可预测性的法律才能起到行为规范的作用。因此,在一般情形下,通过条文表面的文义就可以了解规范目的,法律解释的首要方法就是文义解释。条文内部的所指对象为兜底条款中的实质性规定和例示条文之文义表达。以《刑法》第193条贷款诈骗罪举例说明。该条第5项规定的兜底条款“以其他方法诈骗贷款”,其中“诈骗贷款”就属于兜底条款中实质性规定,能够大致反映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在于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财产所有权。加之基于前文所提及的条文外部关系,结合本罪所在章节,得知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还在于金融机构管理秩序。而本罪第1项至第4项属于例示条文,列举了规范保护目的下,符合兜底条款概括性规定的行为类型,“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等规定可以佐证本罪保护目的在于避免行为人在贷款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非法占有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损害金融管理秩序之行为。基于此,诈骗小额贷款公司的行为就不符合此罪的规范保护目的。
规范保护目的在确定行为是否满足兜底条款的实质上具有先决性,当行为并未损害某罪所欲保护的规范目的时,无论如何也不能将其纳入兜底条款的范畴。但这并不能颠倒着说,某一行为具有实质处罚性就必然适用兜底条款,是否适用还需另一项重要标准,即例示条文的形式特征对兜底条款的限制,此时用到的主要方法就是同类解释规则。
(二)外在标准——用例示条文特征限制兜底条款解释
1.例示条文对兜底条款解释的平行制约
从规范保护目的的角度出发,例示条文对兜底条款解释具有限制作用。规范保护目的决定了立法者的法律制定活动围绕某种意图展开,因而法条之间规范保护目的的融洽性会被考量,条文内部间的文字表达指向同一个规范保护目的。例示项与兜底项在条文整体的文义表达之中,也必然反应相同规范保护目的,不可能存在例示条文保护的是某一具体规范保护目的,而兜底条款却保护另一具体规范保护目的之情形。
从类型化的思维出发,应重视例示条文在兜底条款解释方面的作用。立法者并不一定是抽象生活中所有犯罪行为类型的高手,例示条文的行为类型是对某一规范保护目的下典型行为的明确归纳,而兜底条款正是对与例示条文所述相似行为的抽象补足。采取类型化的思维,让兜底条款涵摄范围与例示条文具有一致性,才能更加具体、细致地把握未被明确规定的行为类型。将兜底条文与例示条文作类型化的思考,可以将不同要素组合作为一个整体看待,通过要素间的联系与区分,清晰地显现整个体系的意义脉络[16]。因此,兜底条款的解释不能脱离例示条文行为类型的特征。
从刑事违法性的视角出发,应重视例示条文对兜底条款解释的形式制约,未被刑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即便具有违法性和社会危害性,亦只能按行政违法行为处理。例示条文是刑法明确规定的违法犯罪类型,是对典型犯罪行为的抽象总结,反映了在广泛的相似违法行为中,刑法选取作为犯罪的部分,而在同一条文中兜底条款隐含的行为类型应当与例示条文的行为类型在行为方法、严重程度上具有融洽性。因此,例示条文对未被明确规定的兜底条款具有提示和限制的作用。
2.例示条文对兜底条款解释的圭臬抉择
在明确了例示条文对兜底条款的限制作用后,就面临方法论的问题,即如何通过对例示条文的分析,提示兜底条款的潜在内容。同类解释规则穿针引线地连接着例示条文与兜底条款,其功能就是提炼出例示条文的特性,再比照新型行为是否满足该特性,最后确定能否适用兜底条款。同类解释规则的标准选择问题直接关系着例示条文特征内容,影响着兜底条款的解释结论。
同类解释要求兜底条款隐含的行为类型应当与例示条文所列举的行为类型具有相同的属性或者是同一类别,这无疑体现了对体系思维的融会贯通。运用这一规则可以明晰与兜底条款平行的比较基准,利用类比推断的方法在众多行为中揪出那些规范目的所欲打击的行为类型。然而不同的学者、司法实务者在运用同类解释规则作为兜底条款的解释工具时,却出现了截然相反的结论,形成此种泥潭的根本原因,并非来源于同类解释作为兜底条款解释之主要方法的错误,而在于对同类解释本身的理解出现了偏差。即判断行为是否满足兜底条款的规定时,将同类解释规则作为最常用、最基础的解释工具是正确的,差之千里的地方在于对工具内容标准的理解。这就好比建房都需要钢筋水泥,而不同质地结构的钢筋水泥却能影响房屋的质量。同类解释规则之于兜底条款解释,就像钢筋水泥之于房屋,不可或缺,而对同类解释规则内涵的理解就像不同质地结构的钢筋水泥,影响着对行为定性的妥适性。因此,要正确界定兜底条款所包含的范围,并非要对同类解释规则进行全盘否定,而是对其的重新定义与运用。
学界就同类解释规则的标准问题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行为类型标准说,其将具有与例示条文行为类型相似性的行为,认定为满足了兜底条款概括性规定。如有学者指出,兜底条款认定的行为必须与同一条文明确规定的行为类型在法律性质方面具有相同或类似的价值[8]。另一派则是实质相同说,认为要通过实质判断挖掘同质性信息,兜底条款涉及的行为都应当回溯到实质内涵所反映的行为事实属性[17]。实质相同说存在先天缺陷,因为其将本属于规范保护目的标准的判断,误入了例示条文特征对兜底条款的限制,消解了行为类型对兜底条款解释的制约功能,存在类推解释的风险。该说实际上只重视了规范保护目的对兜底条款解释的引导作用,忽视了立法者在列举例示条文时,对兜底条款适用的限制。兜底条款具有极強的概括性、模糊性,如果仅从例示条文造成的实质结果相似出发,那刑法适用将漫无边际,公民自由无从谈起,人们将在对国家法律的恐惧中惶惶不可终日。
总的来说,实质相同说从根本上将本应采用的双重标准,异化为实质代替形式的一重标准,具有扩张性可能,因而不利于兜底条款适用的明确性。只有采用行为类型作为提炼例示条文特征的圭臬,才能避免实质相同说的弊端。唯如此,才能同时考虑实质与形式双重标准对兜底条款解释的限制。面对兜底条款开放性、扩张性的顽劣天性,通过例示项所定之行为类型为兜底条款量身定做一个“紧箍咒”,为人们预测自己的行为提供标准,避免将兜底条款的触角延伸到仅与例示项具有结果相似性的行为上,具有限制法官权利滥用的作用。因此,对兜底条款的解释不能无视立法者提炼出的行为类型特征,而在立法行为类型外以规范保护目的为由另设其他行为。
四、问题的检验:双重标准的解释进路及具体运用
(一)双重标准的解释进路
在讨论双重标准的适用方法之前,有必要探讨雙重标准的关系,意义在于厘清规范保护目的、例示条文与兜底条款之间的关联,有利于在兜底条款解释的过程中,依次适用两项必不可少标准,避免因忽略其中一项标准造成的兜底条款解释错误。
由于规范保护目的是被反应、被揭示的对象,具有根源性本体之意义,因而能够指导例示条文及兜底条款在其涵摄范围内展开。首先,兜底条款是规范保护目的的进一步细化,规范保护目的统领了对细化概念的理解,也当然限制兜底条款的解释范围。其次,就例示条文与兜底条款的关系来说,虽然例示条文相较于兜底条文的模糊性具有明确性,在例示条文下法律是相对清晰的行为规范,但兜底条款隐含的行为类型与例示条文所列行为类型都指向同一个规范保护目的,两者处于平级关系并共同反应规范保护目的。综上所述,从整体上看,规范保护目的、例示条文、兜底条款之间可以刻画出一个等腰三角形关系,规范保护目的在顶端,例示条文与兜底条款分别在等腰三角形的两端。
这种等腰三角形的关系要求从整体上把握规范保护目的、例示条文及兜底条款,亦是对体系性思维的提倡。刑法条文的体系性包含了三个方面:其一是独立法条的条文内部体系,表现形式为该法条下的款、项能够共同反映出目的指向。如《刑法》第120条之二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中的第4项兜底条款的保护目的就应当结合前3项的规定,规范保护的范围主要为恐怖活动实施的准备行为,而不是烧杀抢虐等直接对公共安全造成事实损害的恐怖行为。其二是刑法条文的外部体系,每一法条存在独特目的,法条的目的应当是单一无重复的,因为如果既已存在条文能够实现某一目的,就无需为实现这一目的而另设新的具有罪刑构造的刑法条文[18]。对某一条文的规范保护目的进行理解时,应当与其他条文作出区分。如劫持航空器与劫持船只、汽车的侵害对象均是交通工具,也都是刑法第二章中涉及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是却被规定为两个罪名,是因为规范保护目的的范围、程度并不一样。劫持航空器比劫持船只、汽车更容易造成更大程度的损害,对前者的制裁也明显重于后者。
综上所述,对兜底条款解释的进路大体为:第一,通过上文所述的条文内部和条文外部,探明具体条文的规范保护目的,对其进行解构,找到条文的设定目的和价值追求。第二,将相对具体、明确的例示条文与规范保护目的相结合,寻找出为实现规范保护目的、刑法禁止的具体行为类型。第三,通过起统率作用的规范保护目的,以及起具体化作用的例示条文,共同揭示兜底条款包含的行为类型。
(二)双重标准的适用示例
《刑法》第162条之二规定的虚假破产罪,采用了列举式与概括式相结合的混合式立法模式,其中列举了典型的虚假破产行为,即“隐匿财产”“承担虚构债务”,同时也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实施虚假破产,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作为兜底,堵截除了例示项以外的,损害债权人、其他人利益的虚假破产行为,系典型的兜底条款。而就偏颇清偿行为能否适用虚假破产罪中的兜底条款还存在争议。笔者以偏颇清偿行为为例,尝试用双重标准得出结论。
偏颇清偿行为指债务人在宣告破产前,向债权人进行财产权利转让,让部分债权人优先获得比正常清算程序应得更多的清偿。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编著的《破产法立法指南》中列举的偏颇清偿行为包含了偿付以债务人资产相比数额相当可观的债务;偿付尚未到期债务;为无担保债务提供担保;以非正常支付方式偿付到期债务。偏颇清偿违背了同一地位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应受公正清偿的原则,为受偿的债权人利益将严重受损,故偏颇清偿根据破产法,系管理人可撤销事项。那么,在破产法中被禁止的偏颇清偿行为能否被虚假破产罪兜底条款所涵括呢?
首先,探寻虚假破产罪的规范保护目的范围,解构虚假破产罪之立法目的和价值追求。1997年《刑法》规定了妨害清算罪,未规定虚假破产罪,而清算时间的起点是公司企业被宣告破产之时,这导致在破产前的转移、隐匿等逃避债务行为就不能按妨害清算罪论处。鉴于这一立法空白,有学者认为对于虚假破产的行为可以按照诈骗罪论处,因为这一行为通过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侵犯了债权人个体的财产权益。然而,《刑法修正案(六)》还是通过增设虚假破产罪的方式填补了这一空白。新罪位于刑法第三章第三节,而并非同诈骗罪一样被规定在侵犯财产类罪名当中。可见该罪的规范保护目的不仅仅在于个体财产权益的保障,更在于对公司、企业管理秩序的维护,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良性发展的促进。《刑法修正案(六)》草案第二次审议稿亦说明了虚假破产罪设立的规范保护目的,明确了避免公司企业通过破产,逃避债务,转移、处分财产,惩治“假破产、真逃债”,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19]。该罪紧邻妨害清算罪,除了实行行为外,在主体、处罚对象、危害后果上都与妨害清算罪一致,具有弥合妨害清算罪规范保护不周全的功能,如此一来形成了破产清算前后对债权人利益的全面保护。对债权人进行保护并不是此罪最终目的,否则此罪就应当被规定在刑法第五章中,本罪的最终目的在于维护超个人的市场经济秩序。当债权人遭遇虚假破产时,可能会产生连锁反应:导致与其有经济往来的公司企业发生经济危机,这些被债权人影响的公司企业又会影响其他与之有关联的企业,导致资金受损如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最终危及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产生失业问题。公司企业拥有的员工众多,尤其是大型的公司企业,如果遭遇严重资金问题,那么失业人员的数量难以估量。企业的存在发展与经济景气和金融机构贷款政策有关,如果这两环出现问题,则会直接导致抗风险弱的企业破产[20]。虚假破产罪正是通过对债权人保护间接构建市场经济秩序的稳定发展。因此,当审查一项行为是否满足本罪的兜底条款时,不应该忽视行为造成的危害后果,如果债权人数量微少,且造成的危害结果只在极小范围,并没有危及市场经济秩序,就不能仅仅以行为损害了国家机关正常活动或破产制度为由将行为入罪,此时,应当将行为交由破产法等行政法规处理。
其次,结合例示条文的规定,将前述划定规范保护目的范围进一步细化和缩小,提炼虚假破产罪所特有的规范保护目的。虚假破产罪兜底条款中“严重损害债权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规定,说明此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区别于《企业破产法》,虽然两者都有维护企业破产程序,保全债权人权益,促进债权债务公平清算,稳定市场经济秩序的功能,但虚假破产罪仅对违法行为中具有一定严重程度的,扰乱了市场经济秩序的虚假破产行为进行规制。虚假破产罪的主要保护目的是经济管理中的破产制度观点[21],存在将虚假破产罪与《企业破产法》之规范保护目的相同之嫌。这样一来,《企业破产法》中列举的除隐匿行为、承担虚构债务行为以外的虚假破产行为就不能全部适用于虚假破产罪的兜底条款当中。虚假破产罪中明确的“实施虚假破产”,将本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區别于妨害清算罪,旨在避免公司、企业清算以前的债务人转移、处分财产,损害债权人利益,危害市场经济秩序的行为。前两项步骤共同揭示的是虚假破产罪兜底条款适用的上位概念,基于规范保护目的与兜底条款的种属关系,挖掘立法者设定堵截条款的价值目标。
最后,重视兜底条款隐性内容与例示行为类型的同质性,用同类解释规则连接例示条文行为类型,限制兜底条款解释范畴。虚假破产罪中的例示行为有两项,即“隐匿财产”和“承担虚构债务”。“隐匿财产”系公司、企业采取令他人难以知晓的方法,隐藏不报其所有资产,隐匿用于清偿债务的财产。“承担虚构债务”系通过制作虚假账目、伪造会计资料等方式,捏造并承担不存在的债务。不论是隐匿财产,还是承担虚构债务,都是破产人为了逃避债务,避免向债权人清偿进行的转移、处分行为,最终势必会损害债权人整体受偿权。就偏颇清偿行为的定性来说,有观点认为偏颇清偿属于虚假破产罪中的“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22],也有观点认为个别清偿这种偏颇清偿就不属于“以其他方法转移、处分财产”[23]。笔者认为,偏颇行为不应适用兜底条款,理由在于:第一,偏颇行为不具有“隐匿财产”“承担虚构债务”的同质性。偏颇清偿行为本质上属于优惠性清偿,债务人在破产前,向部分债权人优先清偿,可能会损害其他债权人公平受偿的权利,主要导致的是债权人内部的非公平清偿,与损害债权人整体受偿权的例示项相比,行为类型在程度上难以等同。第二,某些偏颇清偿行为得到了《企业破产法》的肯定,刑法就不能越俎代庖。《企业破产法》第32条规定了不得撤销让债务人财产收益的个别清偿行为。当债务人与债权人进行财产互换,且互换时间同时或几近同时完成,则只能证明当事人有损害破产财产的故意时才可撤销[24]。第三,虚假破产罪的规范保护目的并非在于对公平受偿程序的保护,因而偏颇清偿行为可以根据《企业破产法》被撤销,但不应当按虚假破产罪论处。
参考文献:
[1]王安异.对刑法兜底条款的解释[J].环球法律评论,2016(5):25-41.
[2]储槐植,宗建文.刑法机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3]张明楷.注重体系解释 实现刑法正义[J].法律适用,2005(2):34-38.
[4]刘宪权.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兜底条款”解释规则的建构与应用 抢帽子交易刑法属性辨正[J].中外法学,2013(6):1178-1198.
[5]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7.
[6]姜涛.经济刑法之“兜底条款”的解释规则[J].学术界,2018(6):145-161.
[7]李姗姗.浅析操纵市场行为之刑法认定:从首放案说起[J].现代经济(现代物业下半月刊),2009(10):106-120.
[8]何荣功.刑法“兜底条款”的适用与“抢帽子交易”的定性[J].法学,2011(6): 154-159.
[9]李军.兜底条款中同质性解释规则的适用困境与目的解释之补足[J].环球法律评论,2019(4):116-130.
[10]石聚航,秦靓.刑法规范适用中的困境与出路:基于目的解释的展开[J].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 96-103.
[11]王海桥.经济刑法解释原理的构建及其适用[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
[12]黄京平.扰乱市场秩序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9.
[13]张天虹.罪刑法定原则视野下的非法经营罪[J].政法论坛,2004(3):96-104.
[14]斯库拉托夫,列别捷夫.俄罗斯联邦刑法典译[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
[15]周旺生.论法案起草的过程和十大步骤[J].中国法学,1996(4):19-27.
[16]杜宇.类型思维的兴起与刑法上之展开路径[J].中山大学法律评论,2014(3):145-166.
[17]李谦.刑法规范中兜底条款的同质性判断标准—以全国首例“恶意刷单”案为切入点[J].法律适用,2017(18):39-43.
[18]冯军.论《刑法》第133条之1的规范目的及其适用[J].中国法学,2011(5):138-158.
[19]行江.虚假破产罪的理论与实践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
[20]林山田.刑事法论丛[M].台湾:台湾林山田发行,1997.
[21]王欣新.破产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2]李翔.我国刑法上之破产犯罪研究:兼论《刑法》第162条之二[J].法学论坛,2007(5)123-127.
[23]潘家永.虚假破产罪探析:兼论破产犯罪的相关问题[J].政法论坛,2008(3):142-149.
[24]许德风.论偏颇清偿撤销的例外[J].政治与法律,2013(2):22-33.
Abstract: Ejusdem generis as the main interpretation method of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shows misunderstandings and dilemmas in the process of academic understanding and judicial application. It cannot accurately determine the full application scope of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and has the defects of arbitrary interpretation and cannot accurately define the scope of interpretation of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The reason for this result, on the one hand, stems from the standard of ejusdem generis; on the other hand, stems from the neglecting of guiding function of the purposes of norm protection. Legislation activities are always carried out around the purpose of norm protection.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and illustrative methods as part of the legal texts are all subject to the purposes of norm protection, and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purposes of norm protection in explaining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helps to determine the scope of conviction. In addition, compared with the vague and abstract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illustrative methods have the effect of defining the type of behavior. Ejusdem generis based on the type of behavior is more conducive to the determination of the criminal illegality of behavior, to avoid the purposes of norm protection becoming the only interpretation basis of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thus creating the risk of taking substantive illegality as the only reason for criminalization. Emphasizing the double standards of purposes of norm protection and illustrative methods help to achieve the coordination of laws stability and flexibility.
Key words: miscellaneous provisions; purposes of norm protection; ejusdem generis; criminal law interpretation; application of law
(責任编辑 胡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