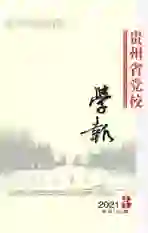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流变
2021-08-02唐爱军
唐爱军
摘 要:从方法论视角,探析历史上对意识形态的不同阐释路径,对于拓展意识形态基本理论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意识形态理论的诸多研究方法中,主要有四种典型的方法:两分法的实证主义、功能批判主义、结构主义、解释学方法。文章以特拉西的“观念学”、社会批判理论的技术理性批判、阿尔都塞的“主体建构”以及汤普森的深度解释学为例,描述了各自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特点。这些不同理论或方法,作为“他山之石”,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本理论提供了广阔视野。
关键词:两分法;功能主义;结构主义;深度解释学
中图分类号:B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 - 5381(2021)03 - 0039- 07
马克思在关于意识形态的一系列论述中,规定了意识形态理论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方法。马克思之后的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不同时期又进一步发展了这些观点,它们构成了系统成熟的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本理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基本理论是我们分析一切意识形态现象、指导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原则和根本方法。但是,不可否认,在分析与研究意识形态问题上,除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方法,还有其他的理论或方法。这些不同理论或方法,作为“他山之石”,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理论,有利于我们在研究意识形态现象的时候,具有更为广阔的理论视野和更为开放的思维态度。在意识形态理论的诸多研究方法中,主要有四种典型的方法:两分法的实证主义、功能批判主义、结构主义以及解释学方法。本文以特拉西的“观念学”、社会批判理论的技术理性批判、阿尔都塞的“主体建构”以及汤普森的深度解释学为例,深入阐述各自的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特点。
一、两分法的意识形态
对意识形态进行实证主义的书写与叙事,主要存在于英国和法国的哲学之中,它运用自然科学范式对意识形态进行观念学的研究。在科学与意识形态两分法的认识论架构中,对意识形态进行或是肯定性或是否定性的叙述,这是典型的知识学的经验分析与实证研究的风格。意识形态概念本身就是在一种启蒙主义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它承载着人们对知识的确定性和客观性的渴望,被科学的无上荣耀光环所笼罩着。近代实验科学的先驱培根提出了著名的“四假象说”,这成为意识形态概念的萌芽。“四假象说”直指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强调要破除人们心灵中根深蒂固的假象和错误的概念,必须诉诸真正的经验和科学方法。培根的“假象说”虽然表露出意识形态的个中消息,但没有明确提出“意识形态”这一概念。“意识形态”一词,最早是由法国哲学家、政治家特拉西(Antoine Distutt de Tracy,1754-1836)在其论著《意识形态的要素》中提出的,并将其界定为中立的为一切观念的产生提供一个真正科学的哲学基础的“观念科学”。[1]显然,特拉西构建的“观念学”模式是对文艺复兴以来欧洲科学精神的继承和发展,立足于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和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基础,将宗教神学从认识论中驱逐出去。特拉西是一个彻底的感觉主义者,认为人的思想认识活动只不过是感觉的创造和神经系统的活动,人的感觉是一切准确的观念的基础。在特拉西那里,人的感觉又主要是从生物学意义来考察的,道德和宗教因素都应当完全抛除。只有如此,真正的心灵科学才能实现。人作为高级动物,与低级动物并无根本的区别。同时,为了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意味着形而上学、哲学、宗教等所有的观念都必须摒弃。“意识形态”作为“观念科学”,在于研究认识的起源与边界、认识的可能性与可靠性等认识论中的基本问题。这种对观念的研究是建立在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觉经验上,是追求一种客观的科学的真理,与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幻想、错误意识有着本质的区别。客观性和科学性是其意识形态叙事的最基本的特征。正如齐格蒙·鲍曼指出的,在特拉西那里,“意识形态是关于科学的唯一科学,或者,关于社会的科学只能是意识形态”。[2]
迪尔凯姆继承了培根以来的经验主义传统。然而,不同的是,他把意识形态当作科学的对立面来加以考察,把意识形态作为科学的反向表征进行否定性的叙述与书写。在《社会学方法的准则》中,迪尔卡姆认为,意识形态是与科学尖锐对立的。“意识形态方法”存在于“运用概念来指导对事实的整理,而不是从事实中得出概念”。然而,科学是对社会事实的分析和研究,这些社会事实“构成一个固定的客体,永恒的标准,这一标准总是要传给观察者,它不为主观印象或个人观察留下余地”。[3]
但是,盖格尔认为,只有把意识形态置于认识论领域中才能真正得到理解。盖格尔站在实证主义立场,借助于两分法的认识论的理论构架,把“理论”视为知识的一个维度,而把“意识形态”视为知识的另一个维度。同时,他认为,“意识形态”只有在与“理论”的对置中,才能使自己的内涵得以显现。在他看来,“理论”是对外部世界和经验事实所作的描述,其基本特征是能够被证实或证伪;“理论”的本真特征是真实,即与现实的同一。“理论”的表现形式是陈述,结果是命题。“意识形态”虽然也以陈述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结果也是形成命题,但它陈述的内容与外部世界和经验事实相悖。盖格尔认为,意识形态本质规定就是“意识形态性”,即虚假性,一切有意的谎言和无意的谬论都属于“意识形态”的范畴,意识形态是科学或“理论”的反向表征。
二、功能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着眼于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消极功能,并将自己的社会批判理论看成是意识形态批判理论。霍克海默在《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社会批判理论”这一核心概念。他认为,“传统理论”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之中,把现存社会制度当作自然的、永恒的存在加以接受,以纯粹的技术劳动来维护现存社会制度的再生产,标榜为一种“科学知识”,实质上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而“批判理论”是产生于现存社会之外,强调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系统发展过程,其目的在于破除一切既定的东西,证明它们的虚幻性和欺骗性,必须加以否定。由此可见,“批判理论”首先是一种批判立场,一种政治实践。[4]
如果说霍克海默勾勒出“社会批判理论”的一般图景,那么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则是立足于发达工业社会发展的新特点,对技术理性和科技统治功能进行了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基于韦伯的合理化思想,他们进一步把科学技术指认为当今社会的新型控制形式,并对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特点和作用方式进行了描述,而现代科学则充当了有效控制的概念工具。在自然科学的概念框架中,“自然”只不过是被控制、被征服、被改造的潜在对象和工具,自然科學的底层理论架构暗含着一种技术先验论,它是一种征服自然的理性概念和逻辑的“符码”体。技术先验论所内含的对外扩张和统治的法则通过对自然的改造,从而导致了对人的改造,并游离到社会整体空间。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必然制约整个制度体系和文化系统,并且根据自身理性逻辑,筹划出一个技术化、工具化的总体世界。技术科学在这个谋划过程中实现了对人类社会的掌控。技术成为现代人的“座架”。不难理解,这种技术掌控必将与政治的统治形成“勾连”,达成某种“共谋”。因此,马尔库塞指出,技术先验论也是一种政治先验论。同样,哈贝马斯也指出,技术理性要实现的不是“合理性”本身,而是以合理性的形式实现对政治统治既定形式的承认。技术进步从自然界到社会领域,从生产力层面到社会关系层面,全面扩展并延伸到整个统治领域,它所带来的生产效率和增长潜力稳定了社会,使得发达工业社会把技术进步包含在统治的框架内。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了政治的合法性。“由科学和技术的成就给予证实,由其不断增长的生产率给予辩护的现状,否定一切超越”[5]17。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生产率的持续增长表征着社会获取统治人们的正当性和合法性。一方面,由于舒适的生活和物质利益的最大化,使人们沉浸在富裕的王国中无法自拔,统治当局则推行强迫性消费政策,制造了虚假的物质需求,并且借助于以技术为中心的文化工业娱乐产业去满足那些为了特定的社会利益而从外部强加在个人身上的“虚假需要”,在这种虚假的满足与自我身份的误认当中,丧失了内在超越向度,实现了对既定权力关系和制度的肯定与辩护。另一方面,它使得技术理性渗透到人们的意识结构当中,重构人们的思维方式,产生一种幸福意识,即相信现实社会是合理的,并且坚持这个制度终将不负众望。然而,这恰恰是一种新型的顺从主义。把技术理性编织的总体世界误当成真正的王国而加以接受和膜拜,一切批判的、否定的超越和创造的活动反而成为“不合理”的。由此可见,承载着“美好生活”的技术理性(和实践形态的科学技术)窃取了目的理性的“符码”,我们需要对之进行“祛魅”。
科学技术不仅仅是对自然进行有效统治的方法,而且为对人的统治和有效的社会控制提供纯概念。更为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在实践操作主义语境中的工具,其内在的支配欲望和统治理性必将现实化、具体化,并且侵入政治实践领域和私人领域,把既定事实无批判地接受下来,从而对一切反对派和反对意见进行清洗,利用技术去压服那些离心的社会力量。在物质利益和富裕生活掩盖下,技术统治潜移默化地扩展到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一切领域,从而使一切对立一体化,使一切不同的选择同质化。“技术的合理性展示出它的政治特性,因为它变成更有效统治的得力工具,并创造出一个真正的极权主义领域。”[5]18资本主义社会越来越成为技术理性占主导的社会,一切话语和行为领域都被技术化了、被管制了;个人需要的满足以及富裕生活的给予也使个人被纳入技术统治逻辑编织的肯定性图景之中,独立思考、意志自由和政治异议的基本批判功能都逐渐被剥夺了。这种“单向度”社会的极权化、一体化运作不是通过暴力或政治斗争来实现的,而是通过操纵人们的需要来实现的,是一种非恐怖的经济技术协作。由此,我们可以洞悉到当今社会的社会控制或意识形态运作的方式和特点。传统社会实现一种自上而下的政治统治,其统治的合法性依赖于对宗教、习俗、神话和形而上学等实体性意识形态进行所谓的“科学”阐释,政治统治的斗争或意识形态的辩护标准囿于实体性观念体系进行所谓的真假值的判断;而发达工业社会,科学技术的普通化和具体化以及向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侵入和扩张,使得理论关注点从“是什么”向功能性的“怎么样”转移,社会存在的合法性阐释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作为社会效益和物质财富的功能动力源,成为这个社会统治的牢固基石,成为极权社会意识形态的新的作用形式,同时也说明了意识形态由“存在本身”的问题让位于“存在工具”的问题。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运作方式不再依赖于对“真理”的言说与宣传,而在于技术的扩张和生产力的发展。“统治不仅通过技术而且作为技术来自我巩固和扩大;而作为技术就为扩展统治权力提供了足够的合法性,这一合法性同化了所有文化层次。”[5]144技术性的谋划绝不是纯粹的客观活动,因为它的现实化与维护存在的奴役状态遵循着相同的逻各斯。统治逻各斯嵌入其中的政治运动,只不过是用技术术语掩盖了政治术语,使意识形态色彩更弱,与以往的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然而技术科学的意识形态在社会控制作用中即意识形态功能中更为有效。“当今的那种占主导地位的,并把科学变成偶像,因此变得更加脆弱的隐性意识形态,比之旧式的意识形态更加难以抗拒,范围更加广泛。”[6]
由此可见,技术理性不仅仅作为既定话语和行为领域概念框架的精神操纵者,关键的是,它是既定话语和政治行为领域的具体而有效的意识形态实践操作者,实现了意识形态的现实运作态势和实践方式,使之成为意识形态现实叙事的最为根本的支点。
总而言之,法兰克福学派突破了实证主义两分法的认识论研究路径,在一个广阔的社会历史以及政治实践背景下,通过意识形态批判,从而使其对意识形态的独特的解释路径得以彰显出来。社会批判理论使得意识形态实现了由“观念性”到“政治性”、由“实体性”到“功能性”阐释方式的转变,通过对技术控制下的极权主义的一体化社会以及“单向度”思想的深刻把握与批判,揭示了科学技术是一种新型社会控制形式,或者说,揭露了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实现了从意识形态的科学性到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性的转变。立足于否定性的叙事学方法论架构即意识形态批判立场,批判了以科学技术绘图的、具有肯定性叙事风格的宏大理论叙事——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建构了自己的一般意识形态批判理论,指出意识形态不是一个理论领域,而是属于实践领域;它不是为了确证什么,而是直入话语和行为领域之根本,促成人们无条件地服从。功能主义的批判性的意识形态阐释向我们呈现了一种从肯定性逻辑到否定性逻辑、从观念性叙事方式到功能性叙事方式的意识形态叙事学的变革图景。
三、结构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
结构主义是一种普遍而又宽泛庞杂的思潮,它以索绪尔语言学理论为基础,并延伸到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研究当中。结构主义公开提出“反人道主义”和“反历史主义”的口号,它强调应当从结构和共时的法则解释社会文化现象;认为个体并不是导致社会-历史发展的基本因素,而是构成社会的因素,并且在强大而持久的社会结构面前,必须接受其选择和安置。阿尔都塞秉承马克思生产关系结构学说,将结构主义的方法运用到意识形态分析当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意识形态理论。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的理论具有强烈的决定论气息,在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空间隐喻式的方法论框架中研究意识形态。这种结构主义的方法,首先指向对人道主义和主体性哲学理论立场的最无情批判。主体性哲学预设了“绝对主体”和“自由形象”,认为主体是观念的制造者和社会整体结构的构建者;而意识形态作为一系列观念知识体系,以精神形式存在,并且只存在于个人的头脑之中,主体制造和生产出作为观念形态的意识形态。阿尔都塞对主体性哲学的意识形态叙述手法进行了本质性抵制,将意识形态纳入生产关系的讨论当中,通过对生产条件的再生产过程的分析与论述,进而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他抛弃了“个体是社会过程的决定者”的观点,揭露了自足性主体的虚幻性,且更多地强调个人的深层受制约性以及社会结构(生产关系)对个体的先在决定性。“生产关系的结构决定着生产者所占有的位置和所承担的功能,就他们是这些功能的承担者而言,他们不过是这些位置的占据者。因此,真正的‘主体(在过程的基本主体意义上)不是这些占据者或功能者,也不是——尽管表面上是——‘真正的人,而是这些位置与功能的规定及分配。真正的‘主体是这些规定者和分配者,即生产关系(及政治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但既然它们是关系,我们就不能在主体的范畴内来思考它们。”[7]作为生产关系的承担者和负载者,“主体”是受支配和主宰的,自身不具有独立存在和自主选择的可能性,从而使得依循主体范畴来理解主体(个体)的叙述逻辑不具有合法性。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结构的特定层面,与经济、政治一样,不能通过主体范畴、意识、观念等得到理解和呈现。恰恰相反,“在多数情况下,这些表现(意识形态)与‘意识无关:它们通常是一些形象,有时是概念,不过首先是加在绝大多数人身上的结构,这一过程并未经过‘意识”。[8]阿尔都塞并不否认意识形态作为表现体系的观念存在,但更多地强调它是一种客观的结构性存在,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客体,“意识形态‘层面也呈现一种客观事实,是社会结构——客观现实的存在所不可缺少的,即是说,这种现实性并不依赖于受制其中的个体的主体性,甚至当它涉及这些个体自身时也是如此。”[9]阿尔都塞之所以强调意识形态是客观的社会领域或社会结构的特定层面,就是澄明意识形态根本不是意识的一种形式,从而阻断了依循主体性范畴和囿于意识哲学书写意识形态的路径。那么,如何正确书写和叙述意识形态理论呢?阿尔都塞提出了意识形态质询与主体建构的理论。他认为,人天生就是意识形态的动物。这句话是指,个体(individual)绝不是不受污染的“纯洁体”,无处不在的意识形态必将个体质询为主体,而人们的社会角色和文化身份的指认只不过是意识形态本质性在场的澄明。表面看来,个体做出意识形态的陈述和表达,然而深层逻辑指向展现意识形态并非个人意识或观念的产物。相反,意识形态为个体建构出他们的身份和话语位置。由此可见,表达和叙述着意识形态真理的人们都不是真正的作者,只不过是剧中人而已,表达着剧作者的一切意愿和要求。意识形态质询并建构了主体,同时主体又体现了意识形态的意志。“主体之所以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只是因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功能定义了意识形态本身)就在于把个体‘构成为主体。”[10]我们可以察觉,阿尔都塞语境中的“主体”绝不是人道主义的先验设定的存在,而是意识形态建构而成的“屈从体”(subject)。“只有在所有意识形态都具有把具体的个体‘构成为主体这种功能(它界定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主体的范畴才由所有的意识形态构成。”[11]
阿尔都塞还借鉴了拉康的理论架构,把主体建构理解为拉康式的自我向“象征界”不断认同的过程。由此出发,揭示了意识形态质询与主体建构过程的四个阶段:①交织着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把个体当成介入社会实践的主体来召唤;②个体接受召唤,即个体对社会的屈从,把社会当作承认自己为主体的对象;③主体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承认、主体间的相互承认以及主体的自我承认;④把想象的状况当作现实的状况,主体向自己所认同的想象性对象靠拢,并依照想象性对象去行动。在主体建构的过程中展现的是意识形态的镜像结构。一方面,意识形态通过召唤个体从而实现着自身的复制;另一方面,镜像复制或主体建构的完成确保了意识形态的功能作用,并进一步增强了自身结构的稳定性和持久性。
毫无疑问,阿尔都塞继承了马克思的“社会整体结构”学说,并在空间隐喻的启示下,进一步阐述了意识形态在社会大厦结构中的独立性,把意识形态指认为一种物质性存在,提出了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即社会制度、学校教育、意识形态教化的物质载体,最直观最直接地洞悉到意识形态的现实运作态势。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涉及宗教的、教育的、政治的、工会的、传媒的空间场所或物质载体等诸多方面,进一步强调了个体在这些实实在在意识形态面前的受动性和被动性,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风格——决定论气息和悲观主义情绪。
四、深度解释学的意识形态理论
约翰·B·汤普森是英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和传媒研究专家,对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的多层面的诠释在现代西方社会学乃至文化哲学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汤普森在对前人意识形态理论批判性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以深度解释学为方法论架构的意识形态理论。
其实,汤普森在构建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时,依循了从一般到特殊的研究线索。他指出,深度解释学是分析文化现象的有效方法论,而意识形态作为文化现象之一,可以运用作为文化分析一般架构的深度解释学对之进行分析。意识形态分析是深度解释学的一种特定形式或版本。由此可见,如果要对汤普森的深度解释学的意识形态研究方法进行阐述,首先要对深度解释学的一般方法进行澄明。汤普森在狄尔泰、海德格尔、伽达默尔和利科等人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深度解释学方法。深度解释学强调社会-历史分析的解释学条件:社会-历史研讨的客体领域不仅是供观察与说明的客体和事件的联结,它也是一个主体领域,这个主体领域是由一些主体所组成,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参与了解自己与他人,产生有意义的行动与思想,并解释他人产生的行动与思想。总而言之,“社会-历史研究的客体领域是一个先期解释过的领域(pre-interpreted domain)。”[12]社会-历史领域具有先前解释性特征,我们只不过是设法再解释一个先期解释过的领域。汤普森接着指出,深度解释学是一个以解释(或再解释)意义现象为取向的方法论架构,从而用于对文化现象(即分析结构背景中的象征形式)的分析。深度解释学包括三个主要阶段:①“社会-历史分析”,研讨有关象征形式生产、流通与接收的社会历史条件;②“正式的或推论的分析”,把象征形式作为复杂的象征构造来研究,它显示一种联结的结构,研讨象征形式内部的组织,关注它们的结构特征、模式和关系;③“解释(或再解释)”,阐明一个象征形式说了什么或代表了什么,以及有关创造性地构建可能的意义。也就是说,解释或再解释过程利用社会-历史分析和正式或推论分析来显示象征形式的社会条件和结构特征,它还设法以此解释一个象征形式,详细阐明它说些什么、代表什么。深度解释学强调对结构化背景中的文化现象或社会流通领域的象征形式的解释(或再解释),这种解释实质上是意义的诠释、生成与构建;并且,象征形式所组成的客体领域同时也是一个主体领域,是一个由能够理解、能够思考并能够在这种理解和思考基础上行动的主体先行解释的主体-客体领域,因为组成社会领域的那些主体总是嵌入历史传统之中的。
在汤普森理论语境中,意识形态概念是指在特定情况下象征形式意义服务于建立并支持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方式。广而言之,意识形态指服务于权力的意义。所谓象征形式,指由主体所产生的并由主体和别人所承认是有意义的建构物的行动、言辞、形象和文本。意义则指包罗在社会背景中和流通于社会领域内的象征形式的意义。深度解释学的意识形态就是对意识形态的解释,这涉及象征形式的解释问题。象征形式是不是意识形态的,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意识形态的,其标准不在于象征形式自身,而取决于它们在具体社会背景下被利用和被理解的方式。在汤普森意识形态分析中,需要探询象征形式所调动的意义如何在具体背景下服务于建立和支撑统治关系的方式。“建立”指的是意义可以积极地创建和确立统治关系,“支撑”指的是意义可以通过生产与接收象征形式的过程来服务于维持和再造的社会关系。意识形态分析侧重于关注象征形式是否、以何种程度以及如何在它们制作、传输和接收的社会情景下被用于服务统治关系。我们无法从象征形式本身透视到象征形式的意识形态性质。这种象征形式的社会运用的意识形态分析框架吸收了功能性叙事的某些合理成分。
象征形式作为意义的构建载体,其在具体环境中的命运和价值的评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主体的理解和解释。所有的象征形式都是富有意义的建构物,不论它们被实证的科学方法分析得多么彻底,都无法避免理解和解释的问题。解释(或再解释)决定了象征形式建构意义的内容及其被运用的路径和方式。意识形态解释理论避免了结构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叙事中个体的被决定性的命运。意识形态解释过程是理解和解释不断发展的过程,涉及讨论、赞成、反对与整合等阶段;它可以允许人们重新解释一个象征形式,联系它所产生与接收的条件,联系它的结构特征与组织,从而质疑或修正他人对一个象征形式的先前理解和解释。意识形态解释过程是一个主动的潜在批判性的过程,人们在这过程中理解所接收的象征形式或信息,但不停留在被动吸收先行解释东西的阶段,而是设法对理解的信息进行批判性的自我塑造和自我理解,是一个再形成和再理解自己的持续过程。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解释具有批判性向度。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更准确地把深度解释学的意识形态理论定义为“批判性的深度解释学”,它开辟了批判性解释的路径。象征形式的生产、建构或使用,以及象征形式被接收它们的主体的解释,都包括了编码和解码的规则。这些规则实质上是结构性权力关系的象征机制,是不对称的社会关系在日常生活和社会互动领域中得以建立和维持的“意识形态的信条”。意识形态解释所展开的客体领域必然是一个众多主体为了服务自身利益和社会关系而进行“暗算”的编码和解码的斗争领域。
我们可以认为,以深度解释学为方法论架构的“意识形态解释”是这样的:解释意识形态就是阐述象征形式所调动的意义与该意义所维持的统治关系之间的联系。意识形态的解释依靠社会-历史分析和正式的或推论的分析,给予批判性强调,即它使用的目的在于揭示意义服务于权力。意识形态的解释是具有批判意图的深度解释学。总之,汤普森在意识形态理论的阐释中,解构了单线性的意识形态形成机制,包含了解释学循环的内在结构;对象征形式的结构化背景即它得以产生和接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强调,走出了内在主义的谬误;从象征形式的创造性理解和再解释,以及与权力关系的交互性,引申到深度解释学所具有的批判性向度。这必然是对确定性叙事风格的研究方法的反动,而这正是社会批判理论鲜明特征之一。怪不得,汤普森在《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一文结语中说,他的理论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批判理论的方案。
以上对意识形态理论及其内在方法的梳理,实际上是我们把握、理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他者”,其中很多有益的观点或思想可以吸收到马克思主义传统中。此外,诸多的观点或思想可以成为我们分析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现象的重要方法。比如,两分法强调意识形态的“认知属性”而非“功能属性”、社会批判理论突出了意识形态的“批判”功能、结构主义强调在社会结构中定位意识形态、解释学强调了意识形态服务于权力关系的这一“建构”功能,等等。
参考文献:
[1]俞吾金.意識形态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5-31.
[2]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34.
[3]E·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35-65.
[4]霍克海默.批判理论[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181-229.
[5]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6]尤尔根·哈贝马斯.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69.
[7]ALTHUSSER L. Reading Capital[M].London:Verso,1979:180.
[8]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233.
[9]ALTHUSSER L. Philosophy and the Spontaneous philosophy of the scientists[M].London:Verso,1990:23.
[10]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361.
[11]ALTHUSSER L.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M].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71:170.
[12]约翰·B.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22.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Ideological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thodology
Tang Aijun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From a methodological perspective,exploring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 paths of ideology in histo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expanding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ideology. There are four typical research methods of ideological theories among others:dichotomous positivism; functional criticism;structuralism;hermeneutics method. We mainly take Tracys “ideology”,the technical rational criticism of social critical theory,Althussers “subjective construction”and Thompsons deep hermeneutics as examples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ir respective ideological theories. These different theories or methods,as“An Alien Stone”, provide us with a broad perspective for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basic theories of Marxist ideology.
Key words:dichotomy;functional criticism;structuralism;hermeneutics method
責任编辑:王廷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