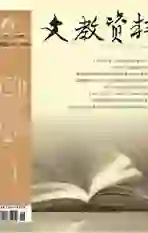明清江南官河侵占现象及其水权纠纷治理
2021-06-28邵蕾蕾
邵蕾蕾
摘 要: 明清江南官河侵占现象可归纳为占河为田、捞采渔芦、搭建庐室三种主要类型,官河侵占中一般市民、宗族、士绅、州县官府等群体因各自利益差异,所起作用并不同。透过官河侵占现象,可见明清江南因官河水权归属极复杂,导致侵占屡禁不止;地方官府的反应并非一味禁占,而是在治理实践中一再突破和变通。侵占现象的发生与官、民各自的反应体现了明清江南地方社会治理模式中制度的滞后性与官府实践的灵活性。
关键词: 明清 江南 官河侵占 水权纠纷
对于明清江南水域社会问题的研究,传统的水利社会史集中探讨了太湖流域洪水治理、河道疏浚、农田水利技术与组织、水环境变迁与社会生活关系等方面的问题。新兴的水域史研究从水上群体的生产和生活入手,探讨了以水为中心的制度、经济与地方社会问题①。可见,从水利与政治、经济、社会多角度互动探讨区域水利社会史,是十分有效的方法。本文从官河侵占的角度,探讨明清江南地方社会的相关问题。
一、明清江南官河侵占现象的主要类型
“官河”的概念最早出自宋代,是对与治水干系重大、由官方所有并管理的河道及湖泊的统称。在明清两代官方文献记载中,官河应由官方征收赋税,并承担地区运输职能[1](111-116)。结合已有研究成果及史料记载,本文认為:不注册在私人名下并且不由私人承办课税的水域、地方主要运输性河流为官河,反之为民间私业。在明清语境中,民间通过各种方式占据河道,导致河道淤塞,直至影响河道水利、航运功能,即构成官方话语中的侵占官河行为。河道具有灌溉、渔业、航运、防洪抗涝、日常饮用等多重价值。江南是典型的丰水地区,以太湖和“三江”[1](41-42)为核心,形成了密集的河湖网络。在江南地区的方志中,依据民间对于河道的利用形式,明清江南的官河侵占现象可分为三种主要类型,即占河为田、捞采渔芦、搭建庐室。
(一)占河为田
农业是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生产形式,明清江南地区受限于自然条件,采用圩田生产,以圩岸实现水、田分离。圩岸以外的河道须按时疏浚,遇河道自然淤涨,在不影响水利大势的情况下,淤涨地被视作官地,允许民间耕种纳税。嘉庆五年(1800),嘉兴府平湖县东湖“湖滨淤积成基,知县李赓芸给祠生管业”[2](904)。明永乐二年(1404),镇江府丹徒县民上疏反映:“境内旧有江通湖水,旱可灌溉,涝得疏泄。后因淤塞,居民垦以为田。”[3](517)
除河道以外,湖泊也会被民间占塞。清人郑元庆在《民田侵占水柜议》中谈及运河行运问题,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民间占河的具体方式:“滨水之民,贪利占佃,庸吏概令升科,水柜尽变民田……不独山东为然。如淮北之射阳湖,江南之开家湖,皆水柜也。今尽升科,蓄泄无繇,官民交困。”[4](3691)势家在占据水面以后,先向官府升科获得官方认可,后再佃予农户实现对湖面的占佃。
除指出民间占据官河的方式外,郑元庆还批评了官府对民间侵占运河水柜的纵容,指出“升科原为朝廷增赋,才吏之所为也。而于济运之处,独不可……升科之法,断不可行于两河之间。其为利甚小,而其为害甚大也”[4](3691)。可见,就一般性河道而言,官府与民间通过升科,在侵占官河问题上达成妥协,允许淤积土地以官地的性质由民间耕种。但是淮北“射阳湖”、江南“开家湖”为运河水柜,关系到漕运能否顺利进行,因此他极力反对州县官府对民间侵占行为的纵容。
(二)捞采渔芦
江南多水,渔业资源丰富。明初专设河泊所管理渔课,在江南地区亦多设置。河泊所作为官方渔课管理机构,对大多河湖水域均能征课,一定意义上赋予了这些水域官方属性。从明中期至清代,因河湖湮塞和河泊所裁撤,州县官府成为新的渔课管理机构,征收渔课的方式从登记渔户转变成标识征课水域。未被官府界定的水域一般水浅利薄,民间在此区域捞采获得的收入会计作沿河土地的田赋[5](204)。这样,明清两代官府以设立机构征收渔课或将水域产出摊入沿河田赋的方式,确认了河流为官方所有的事实。
河道为官府所有,官府决不允许民间私自占据水域。民间在官河中种植水产、置簖设网捕鱼危害水利的行为,会被官方禁止。康熙二十五年(1686),上海渔户沈元等人向官府陈请告豪强霸占渔利。于是官府立碑于各河流处所,碑文记载:“鱼虾,小民赖以资生,岂容豪强占据官湖视为己有?私收渔税,掊刻小民,大干法纪……于各官河处所,各刊木榜竖立。任听渔民采捕鱼虾,不许豪强插箔置簖,独占渔利……嗣后一切各河各港,任听渔民网捕资生,以取田地自然之利。永禁豪强,不许霸占勒索,巧立荡户头目,及私设看荡起荡。”[6](477)从这份告示可以看出,豪强采用“插箔置簖”、私设“荡户头目”的方式,抢占渔业资源,引起渔户不满,最终由官府出面禁止。
除捞取渔利外,从乾隆时曾任江南河道总督的庄有恭的奏疏中,还可发现江南地区广泛存在以种植茭芦占塞河道的问题。早在庄有恭巡抚浙江时,即亲自考察了嘉、湖地区,“目击滨湖溇港,茭芦弥望。询据绅耆,咸称干旱之年,湖滩呈露,滨湖之民,即于其中围筑埂岸,种植茭芦。草生之处,即有滟泥淤积,不数年中,渐图围筑成田,因致湖面被侵,港身日窄”[7](52)。此后,庄氏调抚江苏,发现江苏地区茭芦占塞河道的情况和浙江地区如出一辙,足见明清江南民间种植茭芦等水生经济作物导致河道淤塞的现象十分普遍。
(三)搭建庐室
明清江南地区民间侵占官河不仅出于生产劳动的需要,有时还出于生活起居的需要。明清官府主要通过征收宅基、间架、门摊、契税等税项管理民间住宅,如民居的宅基和交易过程按规定同官府订契纳税,并且房屋外观不违背礼法等级制度,官府并无太多限制。然而受江南水乡自然环境和“财富渊薮”市镇经济发展的影响,江南人地关系较紧张,沿河居民常常临河或跨河搭建水阁,用以居住或从事商业活动。致地方水运交通受阻,于是引发官府禁占居民违建侵河行为。
清代松江府上海县有肇嘉浜,“东濒黄浦,浦水贯城而西,名肇嘉浜……为上海第一要河”。此河支港甚多,是沟通县城内外交通的主干河道。同时,该河与本处居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城内外河道,尤居民血脉所系。可资灌汲,可免火灾,所关甚巨”。河道至明末已经淤塞,到清代更甚,河道淤塞的主要原因是沿河居民为展拓屋基侵占河道:“愚民贪于小利,筑架露台,展拓屋址,日侵月削,水势不得不微。”[4](3997)
乾隆四年(1739),湖州知府胡承谋开浚府城内子城河,子城河“由府署后子城巷至太和坊合,大河半为民居淤占”[2](790)。不过,此次疏浚子城河知府并未拆毁违建民居,而是另修暗渠疏通河道行水。
道光十年(1830),苏州府昭文县琴河淤塞严重,刘侯疏浚城河,城东皆通,唯西南不通。邑人孙原湘作诗了讽刺城西的水阁占河之景象,“大东门接小东门,跨水红阑界绿痕。阁下船行天不见,郞来只道近黄昏……琴水七弦存两弦,五条弦上尽民廛。笑郞苦守尾生信,黄柏桥头等下船”[8](174)。
上述材料表明,官府对民间的禁占,多是针对民间占河为田、捞采渔芦、搭建庐室等行为,这些行为不仅占据了官河河道,加剧了河道淤塞,还影响了河道的通航、抗旱排涝功能。事实上,江南河湖等水域均有公私之分,干流、支流为官河,以公用,禁私占。末端水域为私湖、私渠,由民间使用。既然官私分开,各自划定使用区域,就不应有民间侵占官河的问题。为何还会出現以上三类侵占?究其原因,一则,因官河所在位置水深河宽,鱼类资源更丰富,所以有捞捕者铤而走险在官河捕捞。二则,江南经济人口迅速发展,土地资源和居住空间相对紧张,修筑圩田和跨河搭建时有发生,官府禁令亦不能止。三则,江南水乡的自然条件养成了临河而居的文化习惯,临水而居既方便用水,又可获取河道的航运功能,一举多得。
二、侵占与禁占:明清江南官河侵占中的群体参与
在明清江南官河侵占现象中,商人与一般市民、宗族、士绅、官府四类群体都有不同程度的参与,然而因为各自的立场和利益诉求的差异,不同群体所起作用不尽相同。
(一)商人与市民的侵占
明清江南市镇经济发展迅速,市镇人口急剧增加。为拓展生产、生活空间,富户商人和各类手工业者成为侵占市镇内河及郊区官河的主体。有关市镇、街市的记载显示,明清江南的街道和集市多处在河流交汇处,围绕桥梁、坝头、堰等水利设施形成桥市、坝市。除依水成市以外,各市镇往来交通大多依赖水运,船只聚集之处,摩肩接踵。如每逢二月西湖香市开市,江南诸府“各乡村民男女坐船而来,均泊于松木场。或自上埠自寻下处,或歇各寺院,或在船中居住,其船何止千数”[2](1530)。又如湖州府归安县菱湖镇是以丝类交易闻名的商业市镇,“四方鬻丝者多廛临溪,四五月间,溪上货丝船排比而泊,自菱湖前后左右三十里”。又“菱湖人居舟中列诸货物市之,谓之水市”[9](81)。
民间沿河而居,建造可居可货的店铺,又依水成市,往来交通利用河道运输。不论商业经营、手工业生产,还是市民的日常生活,均需要利用河道资源。
(二)宗族对于侵占的支持
宗族是以血缘关系构筑的利益共同体,明清时期典型的宗族社会在华南地区,江南由于经济、文化较发达,宗族势力影响减弱[10](13-16)。即便如此,文献中不难发现江南地区宗族对于族内成员侵占官河的支持,势力较大的几家几姓常常联合夺取水域资源。清人赵振业曾痛陈势豪私占官河、专掌渔采之利的现象。“吾邑环水以居,太湖而外,为荡、为湖、为漾、为湾者以百数,菱、芡、茭、芦、鱼、鳖之利甲一郡。今大半入豪家,民之渔采者先归其利于豪,而后食其余焉”[4](1375)。
明清社会中,个人生活的各方面与所属宗族存在密切联系。依据江南家谱文献的记载,家族倡导和睦友爱的美德,宗族有力者对于生计困难的宗族成员负有帮扶责任,须为其提供居所、田地、举业、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帮助。如浙江海宁董氏“遵范文正公义田之规,以赈族党。岁又施药,以济困乏,礼延世医郜郭专其事。又为月给笃疾之食,岁亦不啻什百。又拨田周族之守节者,终岁衣食有给,终身棺殓有归”[11](14)。即宗族成员利益密切相关,为了维持一族的整体利益,宗族会成为侵占事件的助推者。
除要求互帮互助外,族谱还规定族内成员一旦涉及民间纠纷,无论是非曲直,都必须本着息事宁人的原则处理。若能自断则自断,不能自断则禀明全族尊长公议,不允许私自告讼官府。如常州王氏规定:“族中有因小嫌而忿争者,于理有亏自反可也;即非以理,自遣可也;纵极不堪,鸣之族尊,以俟公议可也;倘不禀入公祠,擅自惊官动府,虽系理直,亦必鸣鼓而攻。”[12](126)遇事由宗族率先调解的习惯,使民间纠纷常表现为宗族间的冲突。
(三)士绅的调停与助长
明清士绅阶层掌控着都图乡里基层社会的主导统治权力,韦庆远认为“这些地方基层政权、族权,乃至神权,几乎毫无例外地操纵在他们手中”[13](97)。杜赞奇提出“文化的权力”和“中间经济人”的概念,用以表述士绅居于官民之间的地位。归而言之,士绅在地方无疑是官府与民间的纽带。在官河侵占问题上,士绅更多扮演“为民请命”的调停者角色,代民向官府提交诉状,指斥侵占官河事实及危害。如前文万历二十九年(1601)前后,上海县赵家沟发生侵占官河渔利致河道拥堵的问题,“士民屡愬士官”,可见在此次事件中,案情由士绅向官府陈情,士绅发挥了组织领导的作用。
当然,以士绅的地方影响力,是否会是侵占官河的一员?明人谢肇淛在《五杂组》中记载:“缙绅喜治宅第,亦是一蔽。”[14](58)清初亦然,“顺治康熙间,士大夫独承故明遗习,崇治居室”[15](8)。巫仁恕认为明清士大夫兴建园林的目的在于展示“财力和成就”,城市为这一群体提供展示的平台,因此江南士绅的园林多选择在城市或近郊建造。规模之大,甚至到了侵占一般市民居所的程度。“凡家累千金,垣屋稍治,必欲营一园。若士大夫家,其力稍赢,尤以此相胜。大略三吴城中,园苑棋置,侵市肆民居大半”[16](346)。园林建筑多须以水构景,靠近水源,据此士绅或可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民间侵占官河的问题。
士绅以两种角色参与了侵占与禁占过程。士绅在地方有着较大的影响力,同时与地方官府、文人学者构建关系网络。这样的影响力和关系网络是明清江南士绅群体发挥作用的条件,给予了他们在地方事务中相当强的参与实力。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州县官府到平民之间存在权力真空,此种政治形态赋予了士绅在地方活动的空间,使其成为官民之间的桥梁。在官河侵占事件中,士绅正起着这样的作用,充当调停者的角色。另一方面,士紳为追求独特品位兴造园林,引领了江南民间造园风气,提高了土地空间的紧张程度,成了民间侵占官河的促成者。
(四)州县官府的禁占与变通
民间各群体侵占官河的行为,势必引发官方的应对。州县官府执掌地方的财政赋役、水利等各项政务,维护水利安危是其重要职责。在江南苏、松、常、镇等府,因漕运一项,地方官员还负有保漕、护漕的责任,必须维护运河河道的航运能力。除州县官府外,地方还有中央派驻的专门的河道官员。无论是州县官府,还是中央派驻的河道官员,对民间侵占官河的行为多持禁占态度。明正德年间嘉善县濒江濒海处,豪强通过种植茭芦、堆放木排竹筏、插簖置网等方式占据水域,其后只向官府上报十分之二的荡地完纳赋税。虽然向官府缴纳了税课,但是占据河道及沿河滩涂容易造成水域泥沙淤积,妨碍农业灌溉和河道交通。嘉善县于是勒令禁止[17](27)。前文中康熙二十四年(1685)长洲县“私占官河”一案,官府出令禁止,于各处湖泊立碑,永禁豪强侵占官湖、向渔户私收渔税。
官府禁占官河的原因,首先,民间侵占官河的行为阻碍水运交通,威胁水利设施的安全。其次,官府以父母官自居,需要通过抑制大户豪强的不法行为,达到展示自身形象、维护官府权威的目的。正如《官箴集要》所指出的:“为政者,当抑强扶弱为先。”[18](271)
然而官府的角色并非单一。对于民间侵占官河的行为,官方的态度并不总是严加禁占,而是保持一定的灵活性。明代官府鼓励民众于官地、河湖垦荒,借此表现其仁政。鼓励垦荒,必然使民众开垦湖滩、荡地有据可依,促使土地紧张的民户新辟沿河濒湖的土地。官府的默许与纵容还会以赋税的形式存在。明清江南地方志中常常清楚地记载了本地区湖荡地的数量和赋税收入,如《嘉兴府志》记载了隆庆二年(1568)、万历十六年(1588)、清初荡地摊税亩数的详细赋税账目[2](535-538)。可见,禁止与纵容的态度事实上是不稳定的,界限也不是绝对清楚的。
三、江南官河侵占中的水权争夺和地方治理
在官河侵占与禁占中,官民之间的各种反应将问题推向了一个焦点——水权视角下明清江南地方治理的制度和实践有何种关系?地方社会的各种力量如何发挥作用?
(一)产权不明引发冲突
已有研究表明,明清时期中国的土地制度存在明显的一田二主的情况,田面与田底权逐渐分离。虽然土地国有是一种传统观念,但是土地的实际占有呈现出一个私有化的过程,官民之间、地主与佃户之间逐渐通过赋税、地租的手段将土地私有化[19](77)。由此,在水域、山泽等本应为国家所有的公共资源上,同样存在类似土地制度的产权变更过程,即资源的各项权利在实际占有中逐渐分离、资源的国有属性私有化。
水是一种特殊的公共资源,具有边界不确定性和季节流动性,这一特性导致中国传统社会对水域产权的界定不明晰,相关权利关系不断变动。一般而言,水权国有的属性只存在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中,事实上水权常常为私人所有。祁建民指出,中国古代关于水权存在“王土王民”“以水随地”两种认识,在水资源的使用、管理、占有过程中既强调个人对于水资源的占有,又强调水资源“公”的性质,实际上水资源被私人占有的现象十分普遍。为了维护社会利益平衡,国家权力在解决纠纷时采用的是与“拥挤车厢”理论相似的原则,即在占有不均前提下倡导互谦互让[20](135)。
前文三类侵占官河的现象涉及淤积地开发、官河捕捞、搭建宅基、航运等事项的权利关系,需要官府从权利的生成、让渡等环节详细规定,并安排河道承担的多种功能使用顺序。然而,明清时期制度安排往往以完结赋役为目的,对于水域产权无明晰规定,无法为管理水域及其衍生权利的治理实践提供完善的依据,这是侵占官河现象形式和所涉群体众多的重要原因。
(二)官府对于制度的突破与变通
既然地方治理中缺乏明确的水域产权管理制度,那么州县官府在治理实践中便会变通行事。何时严行禁占的命令,何时稍加变通“悉听民便”?
首先,由州县官府在多种地方权利之间权衡结果。州县官府除专司地方政治治理、赋役征收、治安维护、赈黜灾疫等多种职责外,还要协同完成中央派出的各项任务,如协助漕运、维护水利等。在官河侵占事件中,当侵占不足以威胁水利安全时,官府为了鼓励垦种,并分摊定额财政带来的压力,便不加禁占,反而对被占淤积地或水域收税。如前文隆庆年间的吴淞江淤涨地“得田四百余亩”,征银“八十余两”,嘉庆五年(1800)嘉兴府平湖县知县李赓芸将东湖淤积地给“祠生管业”,同样的例子还有清人郑元庆所反映的江南民田侵占水柜后“尽升科”的问题,都是州县官府为增加赋税暂时牺牲水利功能的做法。唯有侵占严重危害水利、航运时官府才会强行禁占,如上海县赵家沟因严重影响当地通航官府下令“清占夺,复故址”,以及明清吴淞江的历次疏浚,官府出于担心太湖流域蓄泄不通所致,均是水利功能暂时占上峰时官府做出的选择。
其次,官府在治理实践中对水利、赋税制度的突破和变通是地方社会治理中利益群体博弈的结果。地方官府以征税的方式,客观承认侵占的既定事实,是为了增加地方赋税缓解赋役摊派压力,还是因为严令查禁官河侵占现象会触动士绅、势家等地方精英的利益,打破该区域内部的秩序平衡。清人赵振业提到民间反对严令查禁侵占吴江的理由有两点,一是“豪民据为世业,一旦夺之,是官为怨府”,二是“濒湖失业之民皆得食于水,而无粮则群起而争,是兹讼端也”。最终,为了兼顾豪民与贫民的需要,保持地方的秩序,确立了新的规定:有田者不得占水,无田者不得多占。占河后不许私卖,并还官告佃。最后特别强调,任何“有碍水道处,永禁告佃”[4](1375)。
(三)明清江南地方治理的制度与实践
本文中,官、绅、民各群体围绕官河博弈,体现了明清江南地方社会治理的模式。此种模式既反映了王朝国家制度的滞后与失序,又反映了地方治理实践中官府的灵活与无奈。
民间侵占官河的现象屡禁不止,州县官府的态度前后不一,首先反映了明清时期水利制度、财政制度的滞后性。从明清文集可以看出,部分官员所提出的对既有制度大调整的奏议多难付诸实际,最终不过是对已有制度的细微修补。这种对制度的细微修补是否足够调整水权关系,避免民间侵占官河、争夺水权呢?从不同类型侵占官河的现象来看,所起的作用应当十分有限。
然而,也要看到事情另外一面。民间的侵占、州县官府的变通更体现了传统社会治理模式中制度与实践的复杂关系,谢湜先生将其归纳为官府“务实化”与民间“合法化策略”的互动[21](80-95)。从官河侵占、禁占的视角出发,可发现州县制度运行与官府治理实践存在差距,官方依据制度主导地方社会秩序的构建,地方精英利用自身的影响力参与构建,民间力量基于生活实践在遵循与突破制度之间游离,地方实际秩序运行逐渐偏离既有制度。此时,官府开始采取灵活变通的办法,默认这种运行着的地方治理实践的秩序,以弹性的策略处理制度与实践的差别,这符合国家、州县官府、地方社会之间互动的地方治理模式。
注释:
①已有研究中,冯贤亮《太湖平原的环境刻画与城乡变迁(1368-191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从环境与人互动角度入手,刻画江南水乡环境的形成并讨论了水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钱杭《库域型水利社会研究:萧山湘湖水利集团的兴与衰》(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从水利共同体理论出发,考察了杭州湘湖库域水利共同体的制度、结构与衰落过程。冯贤亮《明清江南的州县行政与地方社会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重点讨论了在争夺濒河坍涨地的冲突中州县官府和士绅的群体角色。张朝阳《公共权益与17-18世纪江南官河、官湖纠纷》(《中国农史》2016年第3期,第104-114页)分析了官河纠纷中的权利让渡过程。此外,徐斌、刘诗古的水域史研究对江南水域问题也有所涉及。見徐斌:《制度、经济与社会:明清两湖渔业、渔民与水域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刘诗古:《资源产权与秩序:明清鄱阳湖区的渔课制度与水域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年。
参考文献:
[1]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2]彭润章,等.中国方志丛书[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8—1985.
[3]李时勉,等.明太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4]贺长龄.皇朝经世文编[M].台北:文海出版社,1972.
[5]尹玲玲.明清长江中下游渔业经济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4.
[6]上海博物馆图书资料室.上海碑刻资料选辑[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7]魏源全集编辑委员会.魏源全集:第19册[M].长沙:岳麓书社,2004.
[8]孙原湘.天真阁集[A].续修四库全书:第1488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9]陈学文.明清时期江南丝绸手工业重镇菱湖的社会经济结构[J].浙江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8(3).
[10]徐茂明.江南无“宗族”与江南有“宗族”[J].史学月刊,2013(2).
[11][出版者不详].董氏家谱(卷5)[M].刻本.海宁:董氏,[1796].
[12][出版者不详].魏墅王氏宗谱(卷1)[M].活字本.常州:王氏,1889(清光绪十五年).
[13]张显清,林金树.明代政治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14]谢肇淛.五杂组[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15]巫仁恕.江南园林与城市社会——明清苏州园林的社会史分析[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2008(61).
[16]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7]蒋兆成.明清杭嘉湖社会经济研究[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2.
[18]汪天锡.官箴集要[A].官箴书集成编纂委员会.官箴书集成:第1册[M].合肥:黄山书社,1997.
[19]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0]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山西水利社会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1]谢湜.“封禁之故事”:明清浙江南田岛的政治地理变迁[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60(01).
基金项目:湖北医药学院人才启动金资助计划(2019Q DJRW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