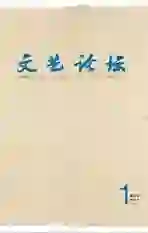“常态化”的主题如何才能达到“陌生化”的效果?
2021-05-17刘小波
刘小波
摘 要:关于长篇小说的综述性论述往往集中在主题层面,而忽视了形式层面的考量。其实小说的主题始终是有限的,写来写去,每位作家面对的主题几乎一模一样。很多作家写了几十年,奉献了数十部作品,似乎到了创作的瓶颈期,甚至是“穷途末路”,很难不重复自己,长篇书写呈现出的同质化局面自然形成。“常态化”的主题如何营造出“陌生化”的效果,创造出新的艺术境界,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一道难题。形式上的突破或许比主题上的新发掘更为有效。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如何让形式更有意味,作家们在不断探索尝试。大致来看,作家们的探索表现为:采用较为独特的文本结构;对细节精雕细琢;主题表达多元发散;文体边界拓宽;等等。
关键词:长篇小说;形式分析;陌生化;小说文体;“怎么写”
2020年长篇小说创作继续稳步前行,老中青几代作家都奉献了不少精品力作。作家们在延续文学传统的同时,也有意无意进行了一些革新,这主要体现在形式层面。从主题上来讲,2020年的长篇小说主要涵盖的依旧是司空见惯的主题,革命战争、日常生活、民生疾苦、家庭伦理、精神心灵,等等,但是在呈现这些主题的时候,小说文本往往显现出一些新的态势。“常态化”的主题如何营造出“陌生化”的效果、创造出新的艺术境界是摆在作家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从某种意义上讲,形式上的突破或許比主题上的新发掘更为有效。艺术是“有意味的形式”,形式很多时候也是内容,甚至比内容更重要。“写什么”和“怎么写”一直是摆在作家那里一个问题的两面。如何让形式更有意味,作家们在不断探索尝试。方方面面的恒常题材作家们在书写的时候都有新的突破。具体而言,一些小说精心设计文本结构,采用了较为独特的文本佳构;一些文本对细节敲骨吸髓、精雕细琢,在常态中有突破;在主题表达层面一般不具有唯一性,而是花开数朵各表一枝,多元的主题呈现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繁缛;此外,不少文本还具有文体上的探索,一方面在强化文体,另一方面似乎又在弱化文体,体裁的暧昧性也越发凸显了文本的丰富性。
一、独特的文本结构
结构是小说最基础的东西,如同人体的骨架一样,是支撑起小说的重要环节。在小说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其结构基本固定,很多时候还形成了套路,而每一次的文学变革似乎都在挑战小说的传统结构。2020年小说书写虽然没有形成声势浩大的革新运动,但是在一些细微处也有所体现,结构新变就是其中之一。
刘心武的《邮轮碎片》将叙述方略确定为“碎片式”,又称为“拼图式小说”,或者“乐高小说”,这是作家精心选择的结构。{1}作品用470多个片段拼贴出完整的故事图景,集中到邮轮这一有限的空间里,有限的空间生发的是无限的故事。碎片化的叙事看似没有中心人物,芸芸众生却都是生活的主角,作家聚焦的是“中产阶级”这一群体,但是生活具有高度的关联性,邮轮串联起了所有人的生活和命运。惠芝涌的扶贫题材小说《春山》也是一部形式上有新变的作品{2},这部小说没有明确的叙事线索,由大量相对琐碎的事件构成,也是一种碎片化的叙事模式,这样的形式用在这样的题材上具有很大的挑战性,惠芝涌选择这一叙事形式,既是对现实的写照,又是一种艺术的自觉。
胡学文的《有生》是一个大部头的作品,上下两卷呈现出皇皇巨制的样态。无论是百年历史的跨度,还是百岁老人这一独特的视角,抑或是文本描写到的种种大的历史和日常生活,都很普遍。小说基础的内容作家很容易处理,但是在结构上作家却颇花心思,最终采用了一种“伞状”的叙事结构,这是作家动笔前思索良久的结果。{3}而这样的结构,对百年历史进程这样的线性时间跨度其实有一种解构的意味。透过散点透视的新结构,将人物的命运跃然纸上,历史进程的曲折性恒定性都表现出来。刘诗伟的《每个人的荒岛》书写的故事较为平常,小说的结构却很精致,每一小节的标题也颇具匠心。陈家桥的《引水记》则选择了书信体,整部小说由两位主人公的往来书信构成,书信体的语态、时态和视角等都有所不同,由此也给作品增色不少。
“套盒结构”也是一些小说经常采用的结构,这种结构并不算新发明,在中国传统小说和西方现代派作品中经常使用,不过最近几年长篇小说没怎么采用了,而2020年的好几部长篇都使用了此种结构。孔亚雷的《李美真》比较典型,小说采用了“套盒结构”,文本中套文本,整体架构上十分繁复。文中引用了各种文献,有大段的没有标点的文字,有些还在内文中进行了奇特的排版,这些都与一般的小说有所不同,呈现出一种新的形态。李宏伟的《灰衣简史》开篇就用了十分奇特的文本形式,将小说主要内容进行了条分缕析的说明,这样“欲望说明书”已经将小说的形式发挥到极致,同时作者还套用了戏剧的结构。《灰衣简史》掺杂了两种明显的互文文本,一种是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说明书,只是将说明对象换成了几乎无法言说与阐释的欲望,另一种是沙米索的小说《彼得·史勒密尔的奇怪故事》,《灰衣简史》也就是在这两个维度展开书写,即欲望的说明书的形式和个体出卖影子的故事。他的另一部小说《月相沉积》也是如此,文中也有和欲望说明书类似的“新文明时期XX部分”的文字,这种戏仿历史书写体的文字也是一种结构的嵌套。这些文本是碎片化的、复杂的,处处充满隐喻和象征,表面来看甚至有些杂乱无章,需要经过二次叙述的梳理,才会理出一些头绪,这明显是作家故意拉长了文本与读者之间的距离,对一般读者而言明显有不适应的地方,但对小说技法的更新或许有帮助。
“套盒结构”是一种典型的互文书写,文本中嵌套另外的一个文本。《酱豆》就是如此。在这部作品中,贾平凹将之前的作品《废都》融入了进去。小说以《废都》的修订再版为开端,回顾了自己创作《废都》前后的心路历程及出版后的境遇。小说虚实结合,“贾平凹”作为小说人物出现,重塑了《废都》创作的时代背景,抛出了自己对时代的探究、对人性的拷问。文学史上的“废都事件”影响较大,而且还溢出了文学界,在社会上也有很大的影响,以此为契机的小说书写前文本自然同样重要,这种模式既是作家旧风格的回望,也是新写法的开拓。
吴亮的《不存在的信札》聚焦的是1990年代艺术圈的故事。小说是很典型的带着个人锋芒的艺术批评文本,因为作品涉及了很多的艺术现象、观念、流派、作品、思想的交锋与论争。很多描写都不是情节的书写,而是一些观念的探讨,具有批评的意味和理论的高度。除了信件,还穿插着谈话录、日记残章、自述、研究、残稿、讲义等不同形式的短章。这些或引用或编撰的文字,让小说蒙上了浓郁的神秘色彩。路内的《雾行者》也是一部结构新颖的作品。小说结构上是五个相互独立又彼此关联的章节,呈现出五种文本形态:梦境、寓言、当代现实、小说素材、文学批评。梅卓的《神授·魔岭记》嵌套的文本是藏族不朽史诗《格萨尔王传》,到了刘亮程的《本巴》中,就是蒙古族的史诗《江格尔》了。种种文本的嵌套能够让小说的结构更为精妙。陈丹燕的《白雪公主的简历》在多个方面都具有实验性质,特别是采用了图文形式。“盗梦空间”的营造也是一种套盒结构的变形。霍竹山的《黄土地》中插进了大量的信天游,小说几乎是嵌套在信天游歌词之中的。小说的故事线与信天游叙述的内容相辅相成。信天游是陕北地区的史诗,两套文本共同构成了生活的历史与当下。而这种音乐的安排,既是结构上的文本套用,也是对细节的精雕细琢。
二、精雕细琢的细节
小说批评家詹姆斯·伍德援引山多尔·马劳伊的话指出:“只能如此:只有通过细节我们才能理解本质细节……”{4}伍德的小说批评也多从文本的细节处着手。大部头的作品在阅读和阐释中其实很容易忽视细节,但作家不会无缘无故插入一些东西。当某些细节在作品中重复出现的时候,作家就寄寓了特殊的使命。比如被作家多次安排进作品的音乐就值得注意。
在路内的《雾行者》中,几次出现了音乐的场景,包括《孤独的人是可耻的》《我去2000年》等具体的流行曲目、去摇滚音乐现场的情节以及以歌手为职业理想的人物形象等。这部有关时代记忆与个体青春的小说,在音乐方面的提示已经昭然若揭了。房伟也是受音乐影响较大的作家,《血色莫扎特》中大量的音乐出场可以看出来,从开场《五环之歌》,到《G小调第四十交响曲》《你们可知道什么是爱情——凯鲁比诺的咏叹调》等古典音乐,再到钢琴教师这样的人物形象,甚至包括小说题目,无不展现出了作者的音乐思维。作者在创作的时候一直聆听着音乐{5},这也会让音乐直接进入小说。音乐的介入使得小说在主题上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悖论,小说算得上是悬疑题材,书写的是一桩谋杀案,而在血腥中却处处有音乐的身影,形成了巨大的张力。《等待呼吸》是一部情感主题的小说,音乐在其中多次出现。不同的感情阶段出现的背景音乐并不一样,这种细微的变化也是有一定叙事功能的。海男的《青云街四号》中刻画女主人公形象的时候,也多次提及某首音乐对她的影响。《妇女简史》中塑造了一个乐师形象,音乐在其中至关重要,透过音乐能够感受到一种特别的父女关系,对亲情的诠释也更加深邃。郭平的《琴殇》书写古琴家这一群体,音乐也是主角之一。须一瓜《致新年快乐》中音乐的误用产生了一种喜剧效果,尤其是用古典音乐来给蒸包子这一事件配乐,但是联系到整部小说的基调,音乐所起到的反讽作用不言而喻。
小说的音乐性是细节精雕细琢的一种体现。对细节的精雕细琢在徐皓峰的《大日坛城》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大日坛城》原作出版于十年前,因后半部文风陡转,引发了一定的争议。时隔十年,徐皓峰以更深的体悟重新改写,还原出一部气息圆融的精彩之作。这种改写,更多的是从细节出发,在原作基本的故事架构上丰富完善而来。对旧作的改写重新发表并不常见,以此也可看出其革新的决绝。小说还是一部有关战争题材的小说,也与传统的战争小说有些不同,将正面战场的较量转向了一种具有民间意味的“国技”围棋之战。姜戎的《天鹅图腾》继续书写草原游牧文化,距离上部作品已过去多年,算是慢工细活。
还有一些大部头的作品对细节也极为重视。王松的《烟火》最为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对人物的精细刻画,小说出场的人物超过百十号,以人物带故事,将百年间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涵盖进去了,而每一个人物几乎都是立体的,具有独特的个性精神状态,并没有几副相同的面孔,这种对人物的把握正是对细节的注重。薛忆沩的《“李尔王”与1979》更是一部宏大厚重之作,在《作家》杂志分三期刊发,这在当前的发表环境中实属难得,但是作品并没有尾大不掉,特别是在细节的处理上精益求精。小说是一部个体生活史,作品试图从时代的裂缝中寻找个人的价值与意义。长期遭受不公待遇的“父亲”获得了彻底的平反,站在命运的转折点上,他百感交集地重温自己经历坎坷的一生,对人性和历史进行了充满哲理的思考,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了希望和信心。在这部转型之作中,他将个人的命运融入到历史背景中,具有强烈的历史感和命运感,显示出作家的宽广格局与精神深度。马华作家黎紫书的长篇新作《流俗地》从题目开始就是直指日常生活的,但是作家也采用了日常生活史的笔法。小说对生活的细节描摹也值得称道。《流俗地》告别了炫技式的书写,就是用平和的笔法写一群生活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微缩在一个叫做“楼外楼”的居民楼里;除了华人,也涉及其他少数族裔的人群。小说流水账一般记录下了马来西亚小城的生活点滴。《流俗地》娓娓述说一个盲女和一座城市的故事,思索马来西亚社会的命运。作品以作家特有的温情关注马来西亚华人,特别是女性群体。小说主要聚焦在女性命运上面,不过与最近流行的女性写作又有所不同,既有生活的艰辛和磨难的描摹,也有蓬勃向上的坚韧,笔下更是流露出一种特有的柔情。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品和上部长篇《告别的年代》相比,几乎没有过多的技法,而是以细节取胜,这种突然的回归平实,也算一种新的突破了。
三、多元发散的主題
很多小说从表面看起来书写的依然是一些常见的主题,但在此之外有更多的发散和延伸,在中心主题之外旁逸斜出。战争主题的小说在主旨上的延伸值得一提,传统的战争书写往往描绘战争的残酷、和平的珍贵、英雄的无畏等,很多时候忽略了作为人的本性。而近年来的战争书写对此有所警觉,2020年的战争小说也有不少新变。上文提及的《大日坛城》将战争转向具有民间和个体意味的围棋技艺较量。徐贵祥的《穿插》《伏击》是战争小说的新样态,也是作家自我的突破。两部长篇《穿插》《伏击》合为《英雄山》出版单行本,作品分别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视角书写了中华民族的浴血奋战史,融进了现代叙事技法和谍战元素等,将人性的复杂性表达出来。近年来的战争书写除了展现宏大的史诗主题外,也有更多人情与人性的描摹,呈现一种书写的新变化,而这种新变,也被批评家捕捉到了。{6}
严歌苓的《666号》也是一部战争题材的作品,小说书写抗联传奇,讲述日据时期的监狱生活。小说内容有敌人的各种刑讯,有“犯人们”的各种周旋,也有“犯人们”监狱内部生活场景的描摹,甚至还有越狱的书写。作品通过一些旁敲侧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抗联的艰辛生活。与此同时,小说也写到抗联本身并不是一块铁板,参与其中的人也有着各自的目的和动机;但小说的核心是书写“假赵司令”的蜕变,这其实是在书写一种耻辱感与荣誉感的养成。严歌苓2020年的另一部作品《小站》也是一部关于战争的作品,不过作家将历史的战争与现实的军旅两条线并列起来。《小站》书写了军旅生活的另一面,牵出了与祖父有关的故事线,以及由祖父之口讲述的波兰士兵与棕熊福泰克的故事等多个主题。小说关于战争也有新的思索——战争总是带给人们悲伤和苦痛,但战争中残存的光芒和希望从未放弃过人们,而福泰克的故事就是在战争中闪烁着的一丝别样的光芒。《小站》将这种善移植过来,用人熊情缘这一奇特的故事表达出来;两种不同的物种却产生了如此深厚的情谊,这本身就已经是一种善的赞歌了。
其他还有很多小说也扩展了战争小说的主题。鞠庆华的《穷汉岭》书写了爱国妓女为抗击日寇所作出的贡献。王英的《母爱之殇》从一个特别的角度写抗日战争,其所揭示的“母爱之殇”在惯常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主题基础上,开拓了抗战题材的表现空间。王霄夫的《上海公子》书写富家子弟投身革命、实现自身价值的故事。赵大年的《羔羊》从普通个体逃避战难的角度展开书写腾冲这片土地上的抗战。
赵本夫的《荒漠里有一条鱼》主题也是极为开阔的。作家用一种寓言化的笔法探讨了一种坚韧的民族精神,表达了一种生命至上的理念,同时也隐晦地表达了一种历史的姿态。故事发生的场景鱼王庄这个地方虽然偏远荒凉,却不是一方净土,各种历史事件也延伸到这里,各色人物轮番出场推动故事。作品时间跨度大,从清代、近代,一直到当代,涉及到抗战、大跃进等鲜明的历史阶段。小说有两条相互交织的故事线,一条是历史传说,一条是现实生活。小说既是一部民族寓言,也是一部世纪中国史。历史不断在小说中出场,哪怕是荒漠里的存在也无法幸免——这里同样有抗日战争,有各种运动,也有梅子这样的需要批斗之人。《荒漠里有一条鱼》写出了一种原始的生命力,这种力量是任何东西也无法摧毁的,是一个民族的精气神。在小说题记中,作家交代了鱼王庄的由来,这是荒漠里出现的一条鱼,生命力的顽强显露无疑,这也是一种象征,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寓言。战争、历史、人性、民族寓言、原始生命力等,在小说中都有涉及。刘亮程的《本巴》延续作家的寓言书写,糅合了草原上的宽阔粗犷与温柔曼妙,作品虚构本巴国与拉玛国,并以两国的命运纠葛来书写民族英雄和地方历史,这种书写其实是关于民族的寓言。
扶贫题材是近年来较为盛行的主题,不少作品相似度较高,很多作家也开始寻找一些新的方向,比如将扶贫与个体成长、创业史等主题结合起来。龙志明、曾小雨的《噶莫阿妞》的“合作社”与经典《创业史》中的“互助组”一脉相承。李天岑的《三山凹》是三个发小不同的人生奋斗历程,三人分别从政、从商以及在农村奋斗,这个过程正好和国家改革开放的历程相契合,个体成长与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而这些,仍然构成了一部创业史,通过个体的创业史,多方位、多层次地呈现了改革开放的历程。于琇荣的《南风歌》则是聚焦农村政策的变迁及其带给农民的改变。与一般小说不同的是,在书写乡土的时候,作家反思农业与工业两种文明的互补与冲突,在此基础上生动地描画了新的农村土地政策在当今中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征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
在政治官场和反腐书写方面,张平的《生死守护》也有新突破。小说并不是仅仅停在传统的描绘腐败的表象上,而是深挖腐败的根源,反思造成腐败的土壤。小说通过书写一位正面形象的干部的遭遇,以小见大来书写有可能滋生腐败的方方面面。小说最后的落脚点是民生主题,作品的中心事件就是一段关乎百姓直接利益的断头公路打通的过程。这是张平近几部作品都有的新变化,反思滋生腐败的土壤,将人民福祉作为写作的中心主旨。王方晨的《花局》也是一部聚焦官场的作品。小说通过几个人物的独立故事的书写,作家将笔触指向的是基层的官场,隶属于反腐小说。不过《花局》与一般反腐小说不同,《花局》描写的是更加隐蔽的腐败行为。作品用寓言化的手法营造了一个独特的叙事空间“花局”,有很多地方越过了现实的书写,比如有一部分是关于动物世界的书写,通过“兽性”写人性,比一般的反腐小说思考更为深入。
梁晓声的《觉醒》是回望历史的作品,小说以特殊年代的一段故事作为引子,书写犯错的少女及她的救赎之路。总体来讲还是他一贯创作风格的延续,但是突破也是明显的。在这部作品中,书写的故事本身是特殊年代的荒诞经历,是较为沉重的,但是作家采用了黑色幽默的方式,以一连串的误会、笑话、巧合,将命运的荒诞性揭示出来,用一种轻佻的笔法写出了时代、岁月和命运的沉重。邵丽的《金枝》是一部跨越百年的作品,小说依旧是家族叙事的延续,梳理了近百年里中国普通农村一个周氏家族五代人的命运沉浮和感情纠葛,对家庭伦理的描摹细致入微。钟求是的《等待呼吸》书写的是较为通俗的爱情故事:异地他乡两人相遇并走到一起,因意外有一个人去世,留下巨额债务,另一个人开始踏上还债之旅。作家叙述的是极为常见的日常生活,如何超越,才能具有史的意味?作家以此为突破口,将一位具有替身意味的第三者引出来,并产生了肉体上的关联,最终引发了肉体的放纵与灵魂的煎熬。作者以此来进一步讨论爱与死亡、感情与欲望、债务与责任以及知识分子的命运等问题,将简单的爱情故事写得更加丰富而深刻。陈希我的《心!》用極端化的叙事手法直抵人性的最深处,书写人性的复杂性与多样化,揭秘躁动不安的灵魂;通过极端化的书写,撕碎掩盖在历史之上的遮羞布,拷问灵魂的深处;在灵魂的深度撞击中、在感官的强烈震撼中,感知事情的真相,穿透表象背后的东西。
儿童文学是另一个较大的类型写作,在2020年也有较大的收获。很多主流文学刊物发表长篇儿童文学作品,于是涌现出一大批作品,如叶广岑的《土狗老黑子闯祸了》、储成剑的《少年将要远行》、荆歌的《他们的塔》《爱你一生》、石一枫的《白熊回家》、张之路的《吉祥的天空》、李东华的《小满》、谢倩霓的《乔乔和他的爸爸》、肖复兴的《曾经少年》、葛亮的《儿郎》等都是儿童成长主题的小说。不少作家并不只是儿童文学作家,也是传统意义上的纯文学作家,他们的写作也与一般的儿童小说不同,仍有着成人文学的思索在里面。
长篇小说很容易确定其主题,但伟大的作品一定是发散、多元的,以映照人性的复杂性和社会的繁缛。多元化的主题使得小说文本的丰富性得到极大提升,这并不仅仅是落在内容上,而且也是一种技法的突破,是一種形式上的推进。
四、“弱化”与“强化”的文体
文体的区分既包括长篇、小长篇、中篇、短篇这样同一体裁之间的区分,也包括小说与散文、非虚构、剧本等其他文学体裁的区分。长篇小说具有取百家之长的特性,呈现出各种文体风景。近来年,很多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长篇也挂着长篇小说的名义,除了市场的考量,也有很多文体本身进化的因素。
马识途的《夜谭续记》就是一个文体独特的作品。小说延续《夜谭十记》的体例,内容为四川十来个科员公余之暇,饮茶闲谈以消永夜。作品仍以四川人特有之方言土语、幽默诙谐之谈风,闲话四川之俚俗民风及千奇百怪之逸闻趣事;既独立又关联的十个故事串联起一部主题统一的长篇小说。上下两卷将百余年中国历史进行了展示,呈现出个体命运的浮沉和人生的悲欢离合。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小说是马识途口述、他人笔录修改而成,这种口述体本身就是一种较为特别的文本类型。
莫言的《晚熟的人》是一部很有韵味的作品,这里单独来讲他的文体。徐则臣在论述这部小说的时候,指出作家强化了短篇小说这一文体{7},但是在出版推介的时候,并没有在显眼处标示其是一部短篇集,很多人将其当作长篇小说,这不仅仅是一种营销策略,也不光是读者对莫言长篇小说的期待,而是内在有着一种紧密的联系,如故事之间的逻辑与主题上的统一性,因此这部小说完全称得上“主题长篇小说”,可算作一种文体的突破。罗伟章的《寂静史》也是如此。小说由几个早先发表的中篇组成,但是出版时写上了“长篇主题小说”的字样。小说内容主要书写了一些“怪异之人”,在技法上有所突破,带有很明显的先锋性和后现代色彩,人物与情节之间也有着相似性。艾伟的《妇女简史》同样也是由两部中篇组成。孙频的《我们乘鲸而去》是一个中篇的篇幅,刊发在长篇专号,这个小说也有一定的创新性,通篇都没有成型的故事,与戏剧的互文也凸显了这种技术的创新意识。
阎连科的《她们》在文体探索上更进一步。作品有多个文体归属,非虚构、长篇散文、长篇小说都被用来指称它,从多个角度看确实更像一部小说,可以看做是一部自叙传、成长体小说。作品虽然书写的都是过往生活经历,但是经过精心挑选和取舍,本身是将底本素材用文学的手法加工成一个叙述文本的过程。作者选取的生活很有代表性,诚如文中的点睛之笔:生活其实很早就像小说了。生活即是小说,小说即是生活。其非虚构的文体和随笔体的笔法以及作者采用的很多早期作品所没有的艺术手段,体现出了作为小说家的阎连科为小说技法更新所做出的尝试和努力。《她们》在形式上有很多地方值得品味,非虚构的问题选择本身就是形式的问题,还有群聊的插入(聊言是经历了是是非非的回头打量)、脚注的安排(类似论文模式)、随笔体的文风(关于女性主义的深度摄入)等都是如此。这是一部关于女性的学术笔记,文本有大量的相关知识。作家将女性问题与女性命运的关注上升到一种学理的层面,这和近段时间大量的流于表面书写的女性文本有着很大的不同。再次,《她们》还是一部读书笔记,这是作者的知识谱系的建构,有一种百科全书式创作的企图。作品有很多段落直接摘录自一些名著以及他本人的作品,形成互文性书写。这些书写正是一种文体创新和文本实验,是技法层面的探索,也是小说家的技法自觉。朱琺的《安南怪谭》的文体也较为特别,文本背后还有一个嵌套的文本。作品写了九个越南志怪故事,似乎可以归入虚构类,可他并不满足于按部就班地讲故事,在每个故事后又附了一篇几乎同样篇幅的“琺案”,记下与故事相关或不相关的各种杂感乃至文字实验,形成独特的文体样态。
罗伟章的《凉山叙事》也是一部体裁暧昧的作品。作品是作家深入生活的作品,计划是写成报告文学,最后呈现出非虚构的特质,但是在《十月·长篇小说》刊发的时候并没有标示其是一部非虚构,而是默认为小说,据说单行本又会以报告文学出版。《凉山叙事》从切身体验出发,详实生动地反映了深度贫困的大凉山地区精准扶贫工作,但是在形式上,采用了书信体,这种明显将人称设定为第二人称视角与一般的第三人称视角的报告文学不一样。再看作品书写的点,从物质扶贫到精神扶贫都有关注,不仅仅是一部扶贫作品,也是一部探讨民族进程的作品。小说的核心是凉山少数民族地区的“移风易俗”问题,从历史、文化、教育、医疗、经济等多个方面来书写一个民族的变迁史。正是文体的暧昧,让作品呈现出丰饶的特性。铁翎的《灰雁》严格意义上说是电视剧脚本,但出版推介的时候归为长篇小说;小说主要书写巾帼抗战的故事。
五、新“小说革命”?
文体其实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命题。张柠发表《今天的长篇小说应该写多长?》{8}这样的文章,将小说的体量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很多时候,将非严格意义上的文体用长篇小说的名义出版是基于出版的考量,但同时也获得了其他方面意外的效果。这些小说文本并没有严格遵循固有的文体特性,并不是文体的弱化,反而是一种强化,通过边界的扩张,让长篇小说这一文体涵盖面更广、适应性更强,在形式扩张的同时扩展小说主题,丰富文学性。
近年来,关于小说“死亡”的论调不绝于耳,期待“小说革命”的呼声也很高。2020年,学者王尧发文呼唤小说界新的革命,并以1985年的“小说革命”为参照,分析当下中国小说创作的种种困局,对小说家的思想资源和认知方法提出了批评。王尧认为1980年代小说革命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观念转变,但接下来的三十多年,“形式”并没有真正地成为“内容”,长时间被庸俗化的个人主义话语侵蚀,小说家可能会丧失了“我与世界”的联结能力。{9}而王尧自己就是一位小说革命的践行者。他在2020年推出长篇小说处女作《民谣》。《民谣》是多个层面的形式创新。这是一部典型的知识分子心灵史。作家以一个少年的视角对历史进行了另一种回溯。主人公在村庄和镇子之间奔跑,在队史、家族史中出入;当少年历经岁月迈入中年,又以故事中的人和故事的看客这样的双重身份进入了历史,创作主体和人物主体发生了灵魂的共振,人与历史的联系生发的更多还是精神的世界的问题。
近年来的长篇小说虽然矩阵一步步扩大,作品不断涌现,但是存在的问题依然不少。“长篇小说同质化”这样的观点已经被论述得成为一个“同质化”的命题,期待小说的新革命在当下似乎成了一个很要紧的事。2021年张莉教授在《江南》杂志开辟专栏,专栏名字就叫《今天,小说如何革命?——关于小说革命的专题讨论》{10},从“今天的小说是否应该革命”和“小说如何进行革命”角度切入,向目前活跃在创作一线的小说家和评论家发起了问卷调查。这是源于在不少评论家眼中,中国当前小说总体上并不让人感到满意,小说界需要进行一场“革命”。而关于对作家作品的不满、指责,往往也是基于主题方面的过分集中、常见、普遍。其实很多作家将其文学情怀和创作特性寄寓在技法上、寄寓在细节中,而这些,都是需要深入挖掘和阐释的。
注释:
{1}刘心武:《碎片式叙事方略的选定》,《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6期。
{2}卢一萍在分析这部作品时,也强调了形式上的创新,见卢一萍:《他把自己的心灵与这块土地融为了一体 ——读惠芝涌长篇小<春山>》,《四川日报》2020年7月24日。
{3}胡学文:《<有生>创作谈》,《钟山·长篇专号》2020年A卷。
{4}[英]詹姆斯·伍德著,黄远帆译:《小说机杼》,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2页。
{5}房伟:《时代记忆的“雪花”或“忧伤”》,《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3期。
{6}汪政:《词客有灵应识我——评徐贵祥长篇小说<伏击>》,《长篇小说选刊》2020年第2期。
{7}徐则臣:《<晚熟的人>的文体意义》,《文汇报》2020年12月29日。
{8}张柠:《今天的长篇小说应该写多长?》,《文艺争鸣》2020年第11期。
{9}王尧:《新“小说革命”的必要和可能》,《文学报》2020年9月24日。
{10}张莉等:《今天,小说如何革命?——关于小说革命的专题讨论》,《江南》2021年第1期。
*本文系“四川大学川大学派培育资助项目”成果。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当代文坛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