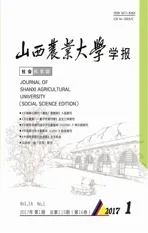旅游伦理研究的本土化反思
2017-04-03郭晓琳刘炳辉
郭晓琳,刘炳辉
(1.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2.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传媒与设计学院,浙江 宁波315100)
旅游伦理研究的本土化反思
郭晓琳1,刘炳辉2
(1.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商学院,浙江 宁波 315100; 2.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 传媒与设计学院,浙江 宁波315100)
发端于西方的旅游伦理学对国内影响甚广,国内的旅游伦理研究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却忽视了理论本身对中国现阶段社会事实的适用性,因此在研究中存在着一些基础性的缺陷以及未经严谨验证就下的判断。从旅游伦理研究的基本假设、中国旅游者的行动单元、非伦理现象出现的原因三个方面对当下国内的旅游伦理研究给予了批判和反思,认为未来的旅游伦理研究应该恢复常人的健全理性,将研究置于国家特定的发展阶段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观察,重视旅游的现代性功能和特定社会意义。
旅游伦理;本土化;反思
随着中国旅游业近十年的爆炸式增长,各地在争相开发旅游资源的过程中迅速积累经济利润,国人文化消费得到满足,精神生活得以丰富。与此同时,自然生态承受能力遭遇挑战和旅游地淳朴文化在市场化冲击下的蜕化,无疑也成为大众媒体的热衷话题。于是,上世纪90年代逐渐兴起于西方世界的旅游伦理学在我国开始受到重视。西方的旅游伦理学最早源于90年代初对酒店员工和顾客关系的研究,从开始的寥寥数文到后来的蓬勃之势,直至1999年在世界旅游组织的第十三届大会上通过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全球旅游伦理规范》(Global Code of Ethics for Tourism),终于在旅游的可持续发展与环境保护、经济利益的协调等方面形成了一些共识和规范。至此,形成了一个对政府、旅游目的地、旅游者、旅游经营者的行动指导框架。国内的学者深受西方研究范式的影响,近二十年来,在旅游伦理的学科定位、研究框架、基本议题、伦理主体等多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种源自西方的理论视野存在着一些基础性的缺陷以及未经严谨验证的前提,对我国旅游伦理研究误导严重。在旅游伦理学中居于核心位置的“旅游者”,到底是“个人”还是“群体”?围绕这个问题是否经过广泛的实证研究?未经实证研究而天然假设为个人又有何依据?并由此导致将强调“关系问题”的伦理学引向了研究旅游者(个人)与自然、当地居民、旅游从业者等所谓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却恰恰忽视了“旅游者内部之间”的伦理关系这一重要领域,是迄今为止国内外旅游学界在旅游伦理学中的最大通病。笔者拟从旅游伦理研究的基本假设、中国旅游者的行动单元、非伦理现象出现的原因三方面对当下的流行观点予以批驳和反思。
一、正功能或负功能:旅游伦理学的基本前提判断
(一)负功能的研究
通观国内外旅游伦理学的相关研究,就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不管其研究领域如何丰富,但基本的逻辑大致如下:旅游活动中出现各类道德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当然是负面的,为了解决这些负面的道德伦理问题,我们不仅仅需要外在的法律约束,还需要强调旅游伦理。旅游伦理的产生,就是因为先有“非伦理”现象的出现。当旅游业因其导致本地居民迁移、不公平劳动条例、文化腐蚀、环境污染、滥用人权等现象出现时,旅游伦理才会引起足够的重视。[1]如果借用社会学家默顿的正负功能视野看,这类观点的一个整体判断就是旅游活动具有负社会功能。
正如开头所言,这类判断并非没有道理和事实依据,但问题在于其观察事物的片面性和即时性,缺乏整体观和历史观。西方的旅游伦理学兴起为何在上世纪90年代之后,而不是上世纪初或者二战之后?是那个时期就没有旅游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任何理论的出现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抽离这个背景而空洞地照搬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都是肤浅的。时代选择适合它的理论,而不是相反。西方在上世纪70年代之后逐渐进入后工业社会,也称为后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其关注的重点从社会的宏大叙事转到个人主观体验,女权主义、性别意识渐起,从强调社会的功能结构逐渐转移到生态环保、女权主义、同性恋、主观感觉等方面。西方旅游伦理研究一开始就打上了这方面的烙印,对旅游者的权利、旅游与生态环境、旅游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入侵等问题颇为重视,批判色彩浓厚。
如King、Pizam 等在对斐济的研究中发现,纳底的多数居民都直接参与了旅游活动的环节,主流民意虽然也对发展旅游予以支持,但却有着对许多社会负面影响的担忧,包括犯罪、性公开、酗酒和交通拥堵。[2]Smith揭示了旅游者与当地居民间的不平等关系以及带来的文化殖民现象,他说道“旅游者像商人、雇主、征服者、统治者、教育者或者传教士,像文化间的代理人,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当地文化的改变,尤其是在世界上不发达地区。”[3]在有关性旅游的研究中,Hall指出,东南亚性旅游的伦理问题并不是卖淫本身的道德问题,性旅游是性别不平等和经济不平等的客观现实在旅游中的反映。[4]对当下旅游活动中发生的各种非伦理现象,国内学者也进行了总结,归纳起来有几方面:一是旅游业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的负面影响;二是旅游企业经营中出现的伦理道德问题;三是旅游者旅游过程中出现的道德失范现象。对于这些现象,学者们也给出了一些建议,如: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关注旅游企业不正当竞争、导游职业道德的旅游业经营伦理研究;关注旅游者道德失范的研究;旅游活动引起的两极分化、目的地社会影响研究。[5]
(二)正功能的反思
回归我们的生活常识和经验,中国人大量的旅游活动,涉及到对第三世界的文化奴役吗?中国的旅游资源在承受迅速增长的游客压力的同时,大量的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古迹因为旅游活动积累和吸引的资金而得到修复保护甚至是重建,不是更普遍吗?中国大大小小的家庭在旅游活动中增进了感情,不是每天都在发生吗?单位组织员工集体出游曾是最普遍不过的福利,为的不就是营造“家”的氛围吗?面对这些旅游活动及其广泛日常的影响,我们是否给予了足够的关注呢?市场化将人们从传统乡土社会的各种共同体中解体出来,成为孤立的个人。在人们日益感受到孤独的大时代背景下,如何重建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关系是中国人当下普遍的潜在焦虑。此时,旅游恰恰充当了“小康阶段”中国人强化家庭伦理建设的特殊载体。笔者认为,旅游活动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中,正功能依然是其最基本的社会功能和意义,而诸多正功能中最大的意义在于强化家庭伦理。
“西方的旅游伦理学”出现在一个以批判和解构为时代特征的历史时期,但需要指出的是,旅游伦理学并非旅游伦理事实本身。西方特定历史时期的理论产物有其时代局限性,我们不能不假思索和检验地拿来使用。特别是当中国仍处于一个建构为主的时代时,西方的理论与我们的现实之间会出现严重的错乱和不匹配。社会科学具有本土性,不但是应该,更是必然。“中国的旅游伦理学”一定不同于“西方的旅游伦理学”,在议题设置、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社会意义等方面都有着自己的特殊性,对此,我们应有充分的自觉意识和自主行动。
二、个人或群体:谁是中国的旅游者?
(一)旅游者的行动单元
旅游伦理学来自于西方,西方旅游学界在论述旅游活动时天然地将“旅游者”假设成独立的个体,并以此为基础讨论相关衍生问题。这种鲜明的个人主义旅游观对国内影响深广,至今仍是国内主流旅游学教科书的论调和出发点。
但正如西方主流经济学以理性人为假设前提一样,不过是便于分析的理论工具,但远远不是社会事实本身。旅游学界的这种个人主义视野也是未经严谨实证检验的,而旅游行动单位的认定,到底是“单数”还是“复数”,对旅游学的相关议题和结论影响甚大。据中国旅游研究院2014年在全国60个重点旅游城市就五一期间城镇居民的出游意愿的调查显示,选择自己组织、单独出游和参加旅行团出游的分别占46.69%、15.52%和35.74%。[6]而根据笔者2013-2014年间一次上千人的问卷调查显示,在旅游中通常与谁同行的选项中,选择和家人一起出游的占到40.30%,和朋友出游的是42.30%,和同事出游的是29.20%,选择独自出游的比例仅占13.30%。不难发现,中国人的旅游行动单位具有明显的“复数”性质,即谈到“中国旅游者”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家庭”和“单位”,是“一群人”,而绝不是“一个人”。
(二)基于行动单元的思辨
由此,我们很容易发现,为何“旅游者之间”的伦理问题长期在中西方旅游学界的关注视野里被忽视。而这个问题对于理解旅游在中国人生活中的意义是何其巨大!据笔者的问卷调查显示,在国人的出游动机和实际效果的对比上,增长见识和增进感情的实现效果相对于这两者的出游动机有近5.00%的增加,而休闲放松的实现效果却下降了近13.00%,这一数据说明,国人现阶段的旅游,在塑造家庭伦理上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它可以是丈夫对妻子的关爱,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晚辈对长辈的孝顺,正是有着这样难舍的义务和责任,在明知旅途和结果并不轻松的前提下,国人却依然有着澎湃热情,携亲带眷地踏上旅程,而实际也确实卓有成效。
就理论而言,西方也并非一开始就将个人作为理解社会的基本单位,也是有一个从部族等集体到逐渐重视个人的过程。如梅因在《古代法》中有精辟表述,“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在有一点上是一致的。在运动发展的过程中,其特点是家族依附的逐步消灭以及代之而起的个人义务的增长。‘个人’不断地代替了‘家族’,成为民事法律所考虑的单位。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处为止,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7]
以个人观为前提的旅游伦理研究必然走向“外向”的旅游伦理学,诸如对旅游者和当地居民、中介组织、地方政府等方面的互动关系的关注,因为“旅游者”既然是个人,是单数,自然不存在“旅游者内部关系”这一类问题,若存在也仅限于个人主观感受之类的心理学问题。而以群体观为前提的旅游伦理研究却恰恰相反,在既不忽视“外在”关系的同时,也注重“旅游者内部关系”这一领域的伦理问题。由此可见,旅游伦理问题的研究视阈会因对旅游者行动单元的基本假设不同而产生极大的差异。若持续深入探讨,我们更会发现,在中国的旅游伦理研究中,单位组织的集体出游也是一个有趣且值得探讨的问题,这与西方后现代的强调个性化、重个人体验的旅游活动产生了明显的分野。单位到底是国还是家,抑或是家国同构?通过旅游,在单位内部形成和谐的气氛,培养员工对单位的认同感,塑造类似于像“家”的格局和氛围。为何要去形成这种关系?旅游活动能否承载起这样的使命?这种关系的建构对于转型中国的意义又在哪里?值得我们深入探讨。
三、旅游与市场:谁才是非伦理现象的原因?
(一)市场化的影响
旅游活动导致旅游地当地淳朴民风被破坏和腐蚀,这是当前旅游学界关于旅游伦理问题的常见论调。不能说这样的观察和判断毫无道理,但却失之于表面和肤浅。与其说这些现象是旅游活动导致的,不如说是当代中国市场化浪潮深刻席卷整个社会所致。否则,未开发旅游业或旅游业尚不发达的地区,就保持了千百年来的风序良俗?
市场是发现和确定价格的地方,市场使得所有的参与者不得不进行成本核算和计较利益得失,传统乡土社会的礼俗传统和道德观念已经不再是人们市场行为的决策依据。这种市场化的影响极其巨大,西方对它的研究已经持续了两百年,而我们对此则重视较晚。马克思对此的论述极为精辟,“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他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情、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8]
西方是先有市场化,后有工业化;而我们是先有工业革命,再开始市场化,准确地说是改革开放之后才逐渐全面推开市场化,这对于中国而言,的确是千年未有之变。当下的中国工业化处于中等水平制造业向高水平制造业过渡阶段、城镇化率刚刚过半、市场化深刻展开不过二十多年,这三大特征注定了中国仍然是一个典型的现代化进程中的社会结构和状态,处于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中的旅游活动自然不可避免地体现着鲜明的时代烙印。
(二)旅游活动的市场化
旅游活动自古已有,随着交通技术、市场化运作的不断推进,在世界范围内到了近代才逐渐演变成为大众的旅游活动。中国历史上的文人墨客独行侠式的旅游并没有导致大量非伦理现象的产生。那时的旅游更多是一种非市场行为,旅游者的食、住、行、游、购、娱都并非市场化操作,在出游方式上更多的是亲友自发结伴同行。市场化的苗头到了明清时期得以萌芽并发展,随着士大夫阶层出游风尚的日益盛行,出现了一些专门为旅游者提供服务的机构,而且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诸如旅游交通工具与食宿的商品化、旅游手册的出版、导游服务的提供以及套装行程的出现。到了清代,旅游消费市场化的趋势进一步得到了增强,如:旅馆住宿业更为普及,交通出行愈加多元化,且设施设备更加华丽,价格也随着市场行情波动。
今日大量非伦理现象在旅游活动中产生,根源不在旅游,而在市场化发展的迅猛之势。正如Crick认为:“许多情况下,旅游成了社会文化改变的替罪羊,特别是被当地人从负面感知时。”[2]市场使得一切跟旅游有关的活动都以利益、效率为导向,将旅游者、目的地居民、服务提供商都裹挟其中,于旅游组织方而言,在最短时间内带着游客完成走马观花的行程意味着效率的最优,于旅游景区而言,招来络绎不绝的人流、满负荷地运行意味着利益的最大,为了保证效率优先、利益最大,麦当劳化的生产方式往往是行之有效的,与此同时,对环境的破坏、对旅游地居民的影响、对旅游者的不悦体验是暂时被搁置的。市场对于旅游发展的作用,西方不乏溢美之词,《全球旅游伦理规范》这么说到,“坚信世界旅游业就整体而言,在一个支持市场经济、私有企业和自由贸易的,适合发挥其创造财富和就业机会功能的环境中,可以取得更大的成绩。”[9]对此国内学者夏赞才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认为市场经济支持可持续旅游发展,既不是一个从理论中归纳或演绎出的假设,也不是从旅游发展实践中得来的经验假设,恰恰相反,这一命题在旅游研究中不断地被证伪。[10]
为何旅游伦理在今天会被反复提及,这促使我们必须深入现象背后不断发问。现代性隐藏在当下旅游活动之中,发掘现代性的特征及其与旅游融合在一起时的具体体现,才是我们发掘旅游伦理问题背后根源的更有效的途径,否则总将板子打在旅游活动上是隔靴搔痒的。
四、黑点与白纸:重新审视中国当代的旅游伦理
(一)旅游殖民的阶层基础
学者与记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学者关注广泛平凡的大量日常社会现象,试图找出其中的因果规律和关系;而记者关注极端个别和负面事件,试图吸引社会和读者的注意力。仅仅通过媒体的眼睛看待这个社会,得到的恰恰是片面的认知。对于中国当代的旅游伦理问题,我们宜放在国家特定的发展阶段和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中去观察,而不是在研究主题上跟随西方旨趣人云亦云。
旅游,是有闲有钱的产物,在西方旅游发展史上,导致对第三世界国家形成新殖民经济的社会基础是源于存在一个庞大的白领中产阶层,因为有着充足的闲暇时间和经济来源收入,因此中产阶层的旅游度假活动更为盛行和普遍。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群体在出国、出境游方面也有着较强的消费动力和消费能力,当他们来到第三世界国家旅游时,优渥的物质消费能力集中爆发了,伴随着物质和精神的享乐,白领们也实现着对自身社会地位渴求和认同。如米尔斯在《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一书中描述的,白领渴望阶段性地位周期的获得,而度假则是它的高潮。大多数的度假地都和这种地位周期相配合,职员和顾客向戏班一样共同演戏,似乎大家相互同意成为这种虚幻成功的一部分。[11]
而对于正处于城镇化进程中的中国而言,中产阶层尚在形成的过程中,在社会阶层中未占有绝对多数,为数众多的农民、农民工群体还尚无能力承受出国出境游,更谈不上对他国的殖民和文化入侵。即使在西方,将旅游视作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也不失为一种极端。据研究表明,至少需满足三种经济条件才有可能成立。一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已逐渐依赖旅游业作为收入保障,政府出台的政策也大多以旅游发展为导向;二是旅游者消费的大部分商品和服务经常不在目的地生产,目的地财富在旅游发展中向旅游来源地单项度流动;三是专业管理岗位经常聘用外乡人担任,进而通过薪酬和利润汇往旅游来源国而造成高额漏损。对于一个仍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仍处于关键攻坚阶段,现代化尚未彻底完成而后现代已经大量出现的巨型国家而言,忽视旅游的现代性功能和特定社会意义,显然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如同那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中,学生们只注意到了老师手中白纸上的黑点,而忽视了整张白纸一般。
(二)研究方法和议题设置
这种理论上的严重忽视和盲区,也与当下中国旅游学界的研究风向和方法有关。过去一段时间,国内学界过于重视对西方流行理论的引介,而忽视了扎实的本土性实证研究;过于重视经济学视角的观察分析,而在人类学、社会学和历史学上的分析阐述不足。在一些实证研究中,也存在着对西方理论的盲从现象。在一些岛国诸如加勒比海地区发生的现象,被不假思索地推演至具有普遍性,而没有去考虑它们的特殊性以及时空局限性,从而遮蔽了自己的研究视野和话语体系。由旅游发展产生的消极影响在国内的旅游伦理研究中已愈发受到重视,但旅游活动的积极影响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却未得到应有的关注,旅游活动对于转型期的中国在组织伦理、家庭伦理建设方面产生的积极意义,在以往的研究中仍然缺失。
旅游活动中的大量非伦理现象,根本原因不在于旅游活动本身,而是千年未有的大规模市场化对中国人的社会行为的深刻影响和冲击,这种非伦理现象充斥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而并非旅游活动中仅有。一味强调旅游的非伦理性,处处以苛责的态度和挑剔的眼光来对待国人的旅游活动,恐怕最终也是曲高和寡而应者寥寥。在中国社会进入到以后现代性为主要特征的阶段之前,以现代性的视角来观察和理解旅游活动的社会功能,仍然是具有较强解释力的,而且这种解释还需要与中国的特定社会文化和结构密切关联。旅游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恰恰是传统伦理面临剧烈冲击下,试图重建家庭伦理的一种努力尝试和有效手段。正确认识“中国式旅游”的社会功能和伦理意义,是中国旅游伦理学的重要使命。笔者以为,学术创新宜建设与反思并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而言,充分认识和尊重现代性的积极意义,同时也不忽视后现代所提供的反思视角,才是一种持平居中的态度,也才会对社会实践的发展有所引导和帮助。
在旅游伦理的核心议题上,以谁为主体来进行研究一直争论不休。之前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基础的旅游伦理研究主体设定,值得仔细推敲和探讨。当前国内外的旅游伦理研究普遍将重心放在确定“谁是利益相关者”这一问题上,如Sautter和Leisen将旅游利益相关者归为员工、居民、积极团体、游客、国家商务链、竞争者、政府、本地商户等8类。罗伯逊等[13]以不同的对象为主体,分别列举出了12类和18类利益相关者。[12]屈颖、赵秉琨将旅游伦理主体确定在旅游地居民和社区、旅游及相关企业、旅游企业员工、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旅游开发商及旅游媒体。[14]笔者并不是要否定利益相关者理论在此的适用性,只是当下的研究过多地将重点放在了“寻找利益相关者”,而忽视了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产生、运作机制以及行为后果的探讨。与其不厌其烦地寻找下一个利益相关者,终究难免落入“人人皆相关”的窠臼,毋宁将重心放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动以及由此引起结果。在诸多的利益相关关系中,应当要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要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放到时空的维度中去理解和把握,根据旅游地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资源禀赋状态做出区分和比较。
[1]付金朋, 肖贵蓉, 谢宇.近10年国外旅游伦理研究评述[J]. 旅游学刊, 2010(25):88-96.
[2]Wall G, Mathieson A. 旅游:变化、影响与机遇[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 178.
[3]Smith V L.HostsandGuests:TheAnthropologyofTourism[M].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9:37.
[4]Hall C M, Sex Tourism in South-East Asia, in France,L.The Earthescan Reader in Sustainable Tourism[M].London:Earthscan,1997: 119.
[5]孙欢, 廖小平. 国内旅游伦理研究之回溯, 论阈与展望[J]. 伦理学研究, 2012 (5):114-121.
[6]中国旅游研究院:2014年五一旅游市场全面升温出国游将达67%[EB/OL].(2014-04-28)[2015-09-10]http://www.ctaweb.org/html/2014-4/2014-4-28-11-20-94418.html
[7]亨利·梅因著.沈景一译.古代法[M].商务印书馆,1996: 97.
[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53.
[9]张广瑞. 全球旅游伦理规范[J]. 旅游学刊, 2000(3):71-74.
[10]夏赞才. 《全球旅游伦理规范》的脆弱基础和错误主张[J]. 伦理学研究, 2007 (6): 47-51.
[11]赖特·米尔斯. 白领:美国的中产阶层[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203.
[12]Sautter E T, Leisen B. Managing stakeholders: A tourism planning mode [J].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1999,26 (2):312-328.
[13]March N R, Henshall B.D.Planning Better Tourism: the Strategic Importance of Tourist-residence Expectations and Interactions[J].Tourism Recreation Research,1987,12(2):47-54.
[14]屈颖, 赵秉琨. 试论旅游市场中利益相关者的旅游伦理建设[J]. 陕西青年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2007(20):46-48.
(编辑:佘小宁)
A localized reflection on tourism ethics
Guo Xiaolin1, Liu Binghui2
(1.SchoolofBusiness,NingboInstituteofTechnologyZhejiangUniversity,Ningbo315100,China; 2.SchoolofMediaandDesign,NingboInstituteofTechnologyZhejiangUniversity,Ningbo315100,China)
Tourism ethics originated from the West had great influence on domestic society.But domestic researches ignored the applicability of western theory of tourism ethics to current Chinese society. This paper has given criticism and reflection from the basic assumptions of tourism ethics studies, Chinese tourists action unit and the cause of the non-ethical phenomenon. It argues that we should first restore normal and rational. Secondly,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which includes country-specific development stage and uniqu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Lastly, pay attention to the modern features and the specific social significance of tourism.
Tourism ethics; Localization; Reflection
2016-11-11
郭晓琳(1982-),女(回),浙江舟山人,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旅游社会学方面的研究。
B82-059
A
1671-816X(2017)01-007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