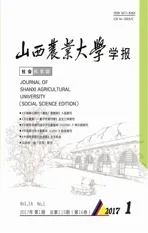南瓜传入中国对传统医学的影响
2017-04-03李昕升卢勇
李昕升,卢勇
(1.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2.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江苏 南京 210095)
南瓜传入中国对传统医学的影响
李昕升1,2,卢勇1
(1.南京农业大学 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江苏 南京 210095;2.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流动站,江苏 南京 210095)
南瓜在中国的引种和本土化进程对传统医学的影响深远,作为中药材价值颇高。历史上医书对南瓜的记载不单涉及其基本性状和相食相忌,南瓜在中医上的具体应用更是值得大书特书,在历史时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南瓜肉、南瓜藤、南瓜蒂、南瓜花等均有妙用。
南瓜;传统医学;中医;影响
南瓜原产于美洲,嘉靖年间分别从东南海路[1]和西南边疆[2]传入中国。南瓜是我国重要的菜粮兼用的传统作物,常见别名有倭瓜、番瓜、金瓜、饭瓜等。南瓜对环境的适应性很强,全国各地多有种植,单产很高,产量颇丰。
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南瓜生产国、消费国和出口国,但对南瓜史的研究很少,涉及南瓜的影响研究更是寥寥,医学影响是南瓜传入中国最重要的影响之一。中国传统医学博大精深,而且兼收并蓄,明代中期方传入我国的南瓜同样为传统医学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古人云“医食同源”,南瓜既是美食又是良药。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南瓜作为中药材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不但充实了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基础,更在救死扶伤方面建树颇多,对传统医学影响很大。甚至有人指出广西壮族某地很多人超过了100岁,这里的主要食物就是玉米、南瓜、毛瓜(冬瓜)以及野生的蔬菜,认为这种保健饮食肯定与长寿有某些联系。[3]
一、基本性状
明初兰茂《滇南本草》载:“南瓜,一名麦瓜,味甘平,性微寒,入脾胃二经,横行络分,利小便。(云南丛书本)麦瓜,一名南瓜,味甘平,性微寒,入脾胃二经,横行经络,利小便。(云南务本堂本)南瓜,味甘,性温。主治补中气而宽利。(汤溪范行准藏本)”[4]是现存最早最完整对南瓜基本性状的基本认识,虽然云南丛书本和云南务本堂本可能是后人托名兰茂编纂,但汤溪范行准藏本至迟可以追溯到1556年,在医书记载中全国最早。
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最早把南瓜收入菜部,并认为南瓜“甘,温,无毒。补中益气”[5],辨明了南瓜的基本性状。从此以后,明清几乎每本本草类、医药类典籍都会记载南瓜,兰茂、李时珍为南瓜融入传统中医做了开创性的工作,奠定了南瓜重要中药材的地位,他们的工作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中医科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入清以来,大部分医家对南瓜的性状有了较全面的认识,褒多贬少。清初医学大家叶桂在《本草再新》(1746)中不但指出南瓜妙用,也十分肯定南瓜藤作用:“番瓜藤,味苦辛,性凉,无毒,入肝脾肾三经,走经络,治肝风,滋肾水,和脾胃,和血养血,调经理气,兼去诸风。按番瓜大而皮糙各省均以作蔬为番瓜。”[6]《本草再新》流传到清中晚期,又有陈修园(1753-1823)点评本,进行了补充说明,陈修园点评之外的原本也略有不同:“南瓜,味甘性温无毒,入心经,补中益气,按,南瓜小而色红润者为南瓜。陈修园评:大而老者尤良,食之益人。南瓜藤,味甘苦,性微寒,无毒,入肝脾二经,平肝和胃,通经络,利血脉。”[7]
浦士贞《夕庵读本草快编》(1697)载:“南瓜亦能补中宫益气力,善发黄疸脚气之征。”[8]张宗法《三农纪》(1750)载:“本性:味甘气泠,养脾宽膈。”[9]吴仪洛《本草从新》(1757)载:“南瓜(补气)甘温。补中益气(时珍曰:不可同羊肉食,令人气壅)。”[10]在乾隆中期之前,典籍中对南瓜性状的描述以总结前人观点为主,围绕《本草纲目》中的“甘,温,无毒。补中益气”展开;但亦有创新,以《本草再新》为典型。
汪绂《医林纂要》(1758)载:“南瓜,甘酸温。种自南蕃,故名,又曰蕃瓜,或讹北瓜。补中益气。冬瓜善溃,此不溃,冬瓜酸多,此甘多,故功效不同。益心,酸以收散,色赤入心,敛肺,酸亦补肺,瓜形如肺。”[11]黄宫绣《本草求真》(1769)中认为“瓜菜又有分其寒热也”,南瓜即是“是性之温而不寒者也”。[12]在对南瓜的专门论述中提出南瓜“助湿、胀脾、滞气。南瓜,专入脾、胃肠。味甘气温、体润质滑”。[12]徐文弼《寿世传真》(1771)载:“南瓜,性温。红色者名金瓜,南人俗名番瓜,北名倭瓜。(宜)补中益气(忌)发脚气、黄疸并诸疮。”[13]乾隆中期以来与之前呈现出不同状况,不但对南瓜性状描述更加具体,而且增加了新的内容,并有与其他中药进行对比。
王学权《重庆堂随笔》(1810)颇有见地,他认为:“此吴氏(指吴仪洛《本草从新》中对于南瓜的说法)为两袒之说。不知南瓜本补气,即与羊肉同食,脾健者何碍?惟不宜于脾虚之人。如今人服参、耆,亦有虚不受补者,脾虚则不能运化补滞之物也。大凡味之能补人者独甘,色之能补人者多黄,南瓜色黄味甘,得中央土气最浓,故能温补脾气,不得以贱而忽之……疑其壅气,不敢多食,然食后反觉易馁,少顷又尽啖之,其开胃健脾如此……南瓜种类不一,性味亦殊,《纲目》之说是也。早实者其形扁圆,与黄瓜同时,杭人呼为霉瓜。嫩时充馔颇鲜,亦堪果腹,而性助湿热。”[14]王学权对南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去伪存真,以合理的解释加上王学权本人的临床实践经验,提升了南瓜在中医科学中的地位。
章穆《调疾饮食辨》(1823)载:“南瓜,味甘色黄。凡脾虚、久疟、久利宜食。俗医谓其有毒,非也。”[15]对南瓜有毒的说法进一步推翻。何克谏《增补食物本草备考》载:“南瓜,味甘淡性温,无毒,补中气。”[16]王士雄《随息居饮食谱》(1861)载:“早收者嫩,可充馔,甘温,耐饥。同羊肉食,则壅气。晚收者甘凉,补中益气。”[17]姚澜《本草分经》(1840)载:“南瓜,不循经络杂品。甘温,补中益气,同羊肉食则壅气。”[18]赵其光《本草求原》(1848):“南瓜,有二种,一种小而色红润,一种长大而皮白,皆甘温。入心解毒,补中益气,与番瓜大而皮糙者不同。蒸晒浸酒佳。其藤,甘苦、微寒。平肝和胃,通经络,利血脉。”[19]陈其瑞《本草撮要》(1901)载:“南瓜。味甘温。入手太阴经。功专补中益气。”[20]晚清以降,典籍中对南瓜的阐述已经非常可观,利用得当的话,几乎百利而无一害。
二、相食相忌
元末明初贾铭《饮食须知》载:“南瓜,味甘性温。多食发脚气黄疸。同羊肉食,令人气壅。忌与猪肝、赤豆、荞麦面同食。”[21]最早介绍了南瓜的相食相忌,该书中有关南瓜的内容可能系后人擅自增补,前文已有论证。兰茂《滇南本草》亦是如此:“胃中有积,吃之令人气胀,作呃逆,发肝气疼,有动气者,不宜多吃。(云南丛书本)胃有积者,食之令人气胀,作呃逆,发肝气疼。胃气疼者,动气,不宜多食。(云南务本堂本)多食发脚疾及瘟病,同羊肉食,令人滞气。(汤溪范行准藏本)”[4]
李时珍较早的认为南瓜“多食发脚气、黄疸。不可同羊肉食,令人气壅”。[5]该说法为历代医书所沿袭。王芷《稼圃辑》载:“与羊肉性相反。”[22]但王世懋《学圃杂疏》(1587):“更与羊食忌,是可废。”[23]江瓘《名医类案》(1591):“南瓜,不可与羊肉同食犯之立死。”[24]明末《致富全书》:“南瓜,甘温,多食发脚气、黄疸,与羊肉同食,令人气壅,宜忌之。”[25]以及周文华《汝南圃史》(1620):“多食发暗疾,食物本草亦不载。”[26]明代南瓜完全属于新鲜作物,无论是由于南瓜与极少数食物相克,还是由于人们对新生事物怀有疑惧的心理,总之南瓜的相食相忌被过度夸大,才会出现“是可废”、“多食发暗疾”这样没有根据的说法。
张璐《本经逢原》载:“南瓜,种出南蕃故名,甘温,有毒。发明。至贱之品,食类之所不屑,时珍既云,多食发脚气黄疸,不可同羊肉食,令人气壅,其性滞气助湿可知。何又言补中益气耶,前后不相应如此。”[27]《本经逢原》成书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尚处清初,部分中医学家对南瓜优势尚未有明确的认知,仅因为南瓜存在相食相克,就指出南瓜“食类之所不屑”,甚至认为南瓜“有毒”,同样是过于武断的。
黄宫绣(1769)对南瓜也存有偏见:“食则令人胀湿生,故书载此品类之贱,食物之所不屑。凡人素患脚气,于此最属不宜,服则湿生气壅。黄疸湿痹,用此与羊肉同食,则病尤见剧迫。”[12]事实证明南瓜虽有相食相忌,但却是重要补品,不可能是“食物之所不屑”,黄宫绣在《本草求真》下文中也肯定了南瓜的医学价值。
何克谏《增补食物本草备考》(1738)载:“多食发脚气及黄疸,同羊肉食令人气壅,忌与猪肝、赤豆、荞麦面同食。”[16]与《饮食须知》的内容完全一致。汪绂《医林纂要》(1758)载:“多食滞气。甘过缓,而南瓜肌肉如粉,故滞气,且有小毒。”[11]解释了南瓜滞气的原因,是由于“甘过缓,而南瓜肌肉如粉”。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1765)载:“南瓜蒂。纲目南瓜主治,只言补中益气而已,至其子食之脱发,令人以为蔬,多食反壅气滞膈,昔人皆未知也。”[28]赵学敏对《本草纲目》进行了补遗,强调了食用南瓜的弊端。张宗法《三农纪》(1750)载:“多食令人病痞,同羊肉食之壅气。”[9]包世臣《齐民四术》(1801)载:“南瓜不可同羊肉食,有脚气、黄胆病者忌食。”[29]从《三农纪》开始,农书中也开始记载南瓜对中医科学的影响,而不只介绍南瓜的栽培、加工利用技术,说明南瓜的医学价值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章穆《调疾饮食辨》(1823)载:“味过于甘,故性偏于壅。痈疽、痘疹、痢疾初起诸症忌之者,壅则生脓,壅则滞气。与忌白术同理,非毒也。凡嗜食此者,加细切,葱叶或花椒末为调和,则无弊矣。气滞中满,及素患脚气、黄疸者忌食(此二症虽已愈多年,犹当忌之)。又不可同羊肉食。”[15]饮食类典籍在清中期以来格外注意南瓜的相食相忌,并完善了南瓜的中医利用,《调疾饮食辨》就针对南瓜壅气第一次提出了改善方法,但依然强调脚气病和黄疸病患者忌食。
赵其光《本草求原》(1848)载:“甘,淡、温,有毒。助湿滞气,多食发脚气、黄疸。忌与羊肉、猪肝、赤豆、荞麦面同食,为食类之下品。”[19]陆以湉《冷庐医话》(1858)载:“方书言:‘白果食满千枚者死,以其壅气也’。由此推之,凡菱、芋、南瓜等滞气之物,俱不可多食,病人尤忌。”[30]王士雄《随息居饮食谱》(1861)南瓜条目载:“凡时病、疳、疟、疸、痢、胀满、脚气、痞闷、产后、痧痘皆忌之。”[17]在羊肉条目也提及了南瓜:“羊肉。甘温……多食动气生热。不可同南瓜食,令人壅气发病。”[17]文晟《急救便方》(1865)载:“南瓜不可与羊肉同食,犯之立死。”[31]晚清以来记载颇为频繁,表述也各有不同,亦有像《急救便方》这种过分夸大的记述。
郭柏苍《闽产录异》(1886)载:“金瓜,起瓣,大者三十斤,生疮、疥者不宜……酒坛瓜。亦金瓜之别种,长大如坛,重六七十斤,疮、疥不宜。”[32]文人笔记中首次提到南瓜的相食相忌,可见南瓜该特点的深入人心。
赵濂《医门补要》(1897)载:“发物忌食。一切发物为外症,尤当戒。误犯者,随加[火欣]肿溃痛,敛者复烂。医者须嘱咐病家宜先。若小儿痘后犯之,肢体骨节,隐痛漫肿,却如注痰,延绵难效,有发症随死者,有成生理残疾人士,即如牛羊肉、鱼、蟹、虾、蚌、鸡、鸭、海味、猪首、王瓜、芥菜、芹菜、茄子、番瓜……”[33]因为南瓜是“发物”代表之一。
吴汝纪《每日食物却病考》(1896)载:“南瓜,甘温无毒,补中益气,多食发脚气黄疸,不可与羊肉食,令人气壅。”[34]陈其瑞《本草撮要》(1901)载:“与羊肉同食,令人气壅。”[20]连横《台湾通史》(1895)载:“忌与羊肉合食。”[35]
方志中对南瓜的相食相忌也记载颇多,如“南瓜,形圆有瓣,忌同羊肉食”[36],“南瓜,有长圆二种,患疮癰者忌食”[37],“南瓜,皮黑味甘,熟食久病忌食”[38]等。
其实,关于南瓜不宜多食的说法,在晚清已经基本肃清,民国时期更多的人为南瓜鸣不平。“因为南瓜产量多,价值低,物以多为贱,人们都瞧不起他,还有人说它有毒,多食会发疮,只好拿来当作猪的饲料,真怪,南瓜有毒,猪吃了为什么不中毒,而反会长肉?我爱食南瓜,天天吃也不厌,精神肉体都没有异状,为什么硬说它有毒?”[39]所以有人断言:“南瓜之肉质厚软,富有甜味,虽不能生食,然与鱼肉、猪羊肉,及一切之兽肉混煮之,则其味极佳。”[40]
三、具体应用
南瓜在中医上的具体应用,也就是南瓜以何种方式用于救死扶伤,包括南瓜的医用和药用价值。南瓜在中医辨证施治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典籍中对其记载也很多。
顾世澄《疡医大全》(1760)载:“疔疮门主方。菊花甘草汤(《十法》)治疔之圣药也。菊花(四两)、甘草(四钱),水煎顿服,渣再煎服,反唇疔、擎珠疔,经霜南瓜蒂煅灰,加冰片少许研细,麻油调搓。”[41]“疔疮门主方”是有南瓜参与的最早的验方,标志在乾隆初年南瓜(蒂)就已经作为中药材开始了临床医疗实践。
黄宫绣《本草求真》(1769)载:“惟有太阴燥土,口渴舌干,服差见其有益耳。至经有言补中益气,或津枯燥涸,得此津回气复,以为补益之自乎,否则于理其有不合矣。”[12]诠释了南瓜“补中益气”的具体功效。
陈文述《颐道堂集》(1807)中《书鹊丹说后》载:“取南瓜根藤花叶,实涤净捣烂取汁,或翦藤瓜其汁饮之瓜治鸦片烟瘾神效,名曰鹊丹,其方与鸦片方均传自倭国,盖白倭受黑倭之侮诚感神降示以鸦片方因灭黑倭,太乙悯鸦片之流毒,无已也示此方以解之,此记不知何人所作,友人得自洋估为题一诗载之拙集,以备治瘾者一助焉。”[42]是最早记述南瓜可解鸦片毒的文献。王学权《重庆堂随笔》(1810)载:“解亚片毒。肥皂或金鱼杵烂,或猪矢水和,绞汁灌之,吐出即愈;生南瓜捣烂,绞汁频灌;甘草煎浓汁,候冷频灌。”[14]是最早记述南瓜可解鸦片毒的医学典籍,以《颐道堂集》和《重庆堂随笔》为始,由于鸦片泛滥愈演愈烈,南瓜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
王士雄《随息居饮食谱》(1861)记载了三种解毒方法:“肥皂或金鱼杵烂,或猪屎水和,绞汁灌之,吐出即愈;甘草煎浓汁,俟凉,频灌;生南瓜捣绞汁频灌;青蔗浆恣饮。”[17]其他两种方法或是古已有之,“生南瓜捣绞汁频灌”法是在晚清颇为主流的治疗烟瘾的措施。咸丰年间沈兆澐《篷窗续录》也载:“治生吞鸦片烟……或用南瓜脂浆灌之。”[43]用南瓜治疗的方法较其他方法简便很多。此外,南瓜花叶等,均有奇效,俞樾《春在堂随笔》(1899)载:“采南瓜花,连其叶与根藤,石臼中捣汁服之,亦效,并可救食生鸦片者。”[44]
方志记载也很多,如同治《韶州府志》“加糖煮食可断阿芙蓉瘾”[45],光绪《上虞县志校续》“久食可断鸦片烟瘾,生捣汁可解鸦片毒”[46]等。鸦片毒害我国的初期,以东南沿海一带最为严重。“南瓜以前,对于药用上,则向无用此物,唯自鸦片流毒深入我国以后,则有利用南瓜与白糖,烧酒混合煮食,以治烟瘾之用,自发现南瓜可疗烟瘾之后,其功用益广矣。”[40]据李治看来,在鸦片毒害我国之前,南瓜并无药用价值,因为鸦片客观“造就”了南瓜,南瓜受到重视之后,又开发了其他的医疗价值。
沈兆澐《篷窗续录》还指出南瓜可以“救服盐卤”,“夏月南瓜藤盛时,肥梗翦断,有脂浆流出,收瓷瓶内,随时可以救此患”。[43]
章穆《调疾饮食辨》(1823)载:“其内穰治铳子入肉,厚封之即出。”[15]南瓜可治汤火伤,枪炮伤。陈龙昌《中西兵略指掌》载:“中枪子简方,用南瓜穰敷之即愈,内服整骨麻药,开取炮弹箭头,不知疼痛。”[47]郑光祖《一斑录》(1843)载:“用老王瓜或番瓜烂瓮中,有用取涂伤处神效若回。”[48]方志记载如民国《恭城县志》“病人忌食。其瓤可以解火毒”[49]等。胡会昌认为:“(南瓜瓤)捣烂治损伤眼珠,厚敷用布包好,勿动,自然消肿。”[50]此外,《一斑录》中还记载南瓜可治牙痛:“或用番瓜蒂焙研擦亦效择便可也。”[48]
山野居士《验方家秘》记载了以南瓜为主要方剂的中药配方,该验方只记载了“血风疮”、“痈疽大毒及一切无名恶症”、“烟瘾”三种病症的治疗方法[51],疑似该书成书于清代中前期,以南瓜为主的验方尚且不多。晚清鲍相璈的《验方新编》(1846),可谓南瓜验方的集大成者,不但记载验方众多,且颇为实用,基本概括了南瓜中药材的各项具体应用,总共记载“眼珠伤损”等十二个南瓜为主药的方剂。[52]
清末至民国时期,罂粟成为西南地区种植比重最大的商品性作物,“种植罂粟,不但耗费地力,且其鸦片流毒,更足害人体之健康,结果致贵州人民,陷于贫弱之苦境”。[53]南瓜可以断烟瘾,在当时鸦片流毒严重的西南地区来说,无疑起到了很好的抑制作用。“南瓜白糖烧酒煑服可以断鸦片烟瘾”[54],“瓜瓤可取枪子,根藤晒干可救洋烟毒。”[55]张宗祥《本草简要方》(1943)针对鸦片的戒烟瘾诸方依然有:“南瓜藤取汁,红糖黄糖调服。”[56]晚清时期,戒烟圣品南瓜可以说已经家喻户晓了,直到新中国成立前期南瓜依然是戒烟的主流方法。
根据一些现代医书、草药志等的记载情况,即使到了当代,南瓜依然对中医科学很有影响,且更侧重于验方的具体应用。其中以《中国药用蔬菜》中对南瓜叙述最为详细。还有其他众多当代中医著作,均揭示了南瓜对中医科学的重大影响。
[1]李昕升,丁晓蕾,王思明.航海科技的发展与南瓜在欧亚的传播[J].山西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3):319-324.
[2]李昕升,王思明.南瓜在长江中游地区的引种推广及其影响[J].中国农史,2015(1):24-33.
[3][美]尤金·N·安德森著.马孆等译.中国食物[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175.
[4][明]兰茂.滇南本草[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130.
[5][明]李时珍著.李经纬等校注.本草纲目[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1:1029.
[6][清]叶桂.本草再新[M].道光二十一年清介堂藏版白从瀛刻本.
[7][清]叶桂著.陈修园评.本草再新(下册)[M].上海:群学社,1931:6.
[8][清]浦士贞.夕庵读本草快编[M].康熙刊本.
[9][清]张宗法著.邹介正等校释.三农纪[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89:296.
[10][清]吴仪洛,郭薇等整理.本草从新[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193.
[11][清]汪绂.医林纂要[M].道光二十九年遗经堂刻本.
[12][清]黄宫绣.本草求真 [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252,264.
[13][清]徐文弼.寿世传真[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86:51.
[14][清]王学权.重庆堂随笔[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91-92,108.
[15][清]章穆.调疾饮食辨[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192.
[16][清]何克谏.增补食物本草备考[M].刻本不详.
[17][清]王士雄著.宋咏梅,张传友点校.随息居饮食谱[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2003:13,13,69,13.
[18][清]姚澜.本草分经[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157.
[19][清]赵其光.本草求原[M]//朱晓光主编.岭南本草古籍三种.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1999:352,348.
[20][清]陈其瑞.本草撮要[M].上海:世界书局,1985:61.
[21][元]贾铭.饮食须知[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8:27.
[22][明]王芷.稼圃辑续修四库全书977(子部 农家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245.
[23][明]王世懋.学圃杂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5:13.
[24][明]江瓘.名医类案[M].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明]佚名,孙芝斋校勘、点注.致富全书[M].郑州: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27.
[26][明]周文华.汝南圃史[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
[27][清]张璐著.赵小青等校注.本经逢原[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6:152.
[28][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337.
[29][清]包世臣著.李星点校.包世臣全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7:180.
[30][清]陆以湉.冷庐医话[M].北京:中医古籍出版社,1999:128.
[31][清]文晟.急救便方[M].萍乡:文延庆堂,同治4年刻本.
[32][清]郭柏苍.闽产录异[M].长沙:岳麓书社,1986:54-55.
[33][清]赵濂.医门补要[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11.
[34][清]吴汝纪.每日食物却病考[M].光绪廿二年上海商务印书馆石印本.
[35]连横.台湾通史[M].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2005:354.
[36][道光]太平县志(卷一)[M].道光五年(1825)刻本.
[37][民国]青县志(卷十)[M].民国二十年(1931)刻本.
[38][民国]许昌县志(卷一)[M].民国十二年(1923)刻本.
[39]向清文.南瓜的营养价值[J].家庭医药,1947(13).
[40]李治.南瓜栽培法[J].农话,1930,2(5).
[41][清]顾世澄.疡医大全[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1276.
[42][清]陈文述.颐道堂集[M].嘉庆十二年刻本.
[43][清]沈兆澐.篷窗续录[M].咸丰年间刻本.
[44][清]俞樾.春在堂随笔[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1:91.
[45][同治]韶州府志[M].同治十二年(1873)刻本.
[46][光绪]上虞县志校续(卷三十一)[M].光绪廿五年(1899)刻本.
[47][清]陈龙昌.中西兵略指掌[M].光绪东山草堂石印本.
[48][清]郑光祖.一斑录[M].道光舟车所至丛书本.
[49][民国]恭城县志[M].四编,民国廿四年(1935)铅印本.
[50]胡会昌.南瓜栽培法[J].湖北省农会农报,1922,3(2).
[51][明]山野居士.验方家秘[M].刻本不详.
[52][清]鲍相璈.验方新编[M].天津: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41-642.
[53]经济部资源委员会,经济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贵州省农业改进所编.贵州省农业概况调查[M].贵州农业改进所,1939:38.
[54][民国]昆明县志(卷五)[M].民国廿八年(1939)铅印本.
[55][民国]古宋县志初稿[M].民国廿四年(1935)铅印本.
[56]张宗祥.本草简要方(卷四)[M].刻本不详.
(编辑:程俐萍)
The influence of pumpkin introduced into China on traditional edicine
Li Xinsheng1,2,Lu Yong1
(1InstitutionofChineseAgriculturalCivilization,NanjingUniversity,Nanjing210095,China;2PostdoctoralStationofCollageofEconomicsandManagement,NanjingAgriculturalUniversity,Nanjing210095,China)
Introduction and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pumpkin in China ha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As one of the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it has a great value. Records about pumpkin in Chinese medicine books not only relates to the basic traits, but also expounds its specific medical application. Pumpkin meat, pumpkin vine, pumpkin pedicle, and pumpkin flowers are of magical use.
Pumpk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fluence
2016-10-21
李昕升(1986-),男(汉),河北秦皇岛人,讲师,博士,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师资博士后,主要从事农业史方面的研究。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一等)(2015M580439);江苏省教育厅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16SJD770001);南京农业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人文社科基金面上项目(SK2016002)
N91
A
1671-816X(2017)01-005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