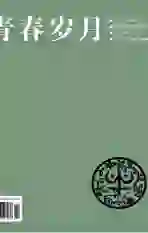北京·青春·现实
2017-03-14肖露露邓瑶
肖露露 邓瑶
【摘要】石一枫的小说里有一个独特的北京,不是外省人的北京,不是漂泊者的北京,是调侃、从容的北京,又是焦虑、荒凉的北京。成长于此,石一枫的青春写作也与众不同,没有过度自恋的疼痛忧伤,而是戏谑与自嘲下的“青春后遗症”。他的创作从未脱离过现实,随着阅历增长,笔触愈发深入到当下社会矛盾和时代症结,透过个体看破时代,他逐渐成长为了一个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家。
【关键词】北京;青春写作;现实主义;青春后遗症;成长
青年作家石一枫以他独特的观察视角和调侃戏谑的笔调对日新月异的北京进行文学性的记录,体现着北京的人情味与时代变迁感。在这样的城市舞台里,石一枫一边捍卫者着“青春后遗症”的合法性,一边尝试着从现实的角度记录80后一代人的青春经验,并逐渐将写作的触角伸向了时代病症,以一如既往的现实主义的关照对当下的社会和时代进行着审视和反思。石一枫凭借一开始就独树一帜的书写风格在青年作家中極具标示性,到现在凭借现实主义重新焕发生机,他笔下的北京、青春和现实都浸润着石一枫的个人特点,在群星闪耀的青年作家中展现着个人的光彩。
一、不一样的北京
“文学和城市之间有着一种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在某种程度上造就了文学,文学则以艺术的形式塑造了城市。”石一枫笔下的北京仿佛天然就是人物的活动舞台。这位地地道道的北京人用他独特的“京片子”语言和城中人的视角观察描写,透露着对北京的熟悉感和亲切感,从而以更广远的视角审视这座变化的城市。
在其他青年作家的作品中,北京常常被抽象成一个个富有象征意味的符号。徐则臣的《啊,北京》暗隐着北京政治上的召唤感和安全感。“大客车在傍晚时分进了首都,边红旗激动得哭了。”“首都”一词尽含一代人对北京无限的遐想,以及油然而生的国家自豪感。更多的时候,北京成为“北漂”或者城中人的奋斗之地与失落之地。徐则臣《如果大雪封门》、《居延》都写的是“北漂”试图在北京立足的挣扎与奋斗,马小淘《毛坯夫妻》和霍艳《失败者之歌》反映了北京人在巨大的经济生活压力下的生存困境与家庭矛盾。还有一些人物仅将北京当成人生的一个驿站,如张怡微的《后海之后,江南以南》中来此求学的弥生与璟妍。在大多数青年作家笔下,外围人想象中的北京神秘、伟大、迷人又给人以安全感。但这种想象与向往常常面临巨大的现实压力最终破灭,“北漂”不得不失落地回到故乡。一些通过努力暂有立足之地的人,也很难说融入了城市的圈子,“北漂”可能是过客,也可能只是异客抱团取暖。大部分青年作家笔下的北京似乎是当下时代的一个缩影,他们试图打破新中国成立后代表着政治安全感和崇高感的“北京”形象,而从外界进行观照,侧重于反映新时代下北京城里人的经济生存困境。北京只是时代变迁的一个缩影,某种程度上,它和任何一个大都市无异。
石一枫写北京,写的不再是地图上作为“一点”的北京,而是置于时代下的变迁的北京,是从北京城内部对北京进行状貌般地描写。《节节最爱声光电》故事跨度近三十年,从节节妈妈面临剧团事业单位改革写到节节为生活奔走于都市之中,节节成长经历中追求“声光电”的过程也正是北京城蜕变成充满声光电的大都市的过程。《恋恋北京》里赵小提和姚睫一同经历了两次旧户拆迁,现代化的商品楼与商业街层出不穷,更是北京飞速发展的剪影。这时,北京不再是漂泊者生活舞台上冷冰冰的一块背景幕布,它也有自身不可忽视的变化与发展,和人物的成长息息相关。
涉及到城中的人物时,生于斯长于斯,“操一口三环路以外的、北京话和普通话的混合腔写作”的石一枫比起自满于北京人身份,更看清光鲜亮丽的北京背后的现实。在这样一个飞速发展的都市里,走出大院和组织之后的“后顽主”内心的优越感被渐渐冲淡,他们的未来不再框定在固定的制度范畴之内,前程变得模糊不清。桀骜不驯的“后顽主”既厌恶按部就班的束缚,又不认同世俗利益的规则,在生活和经济压力的裹胁下常常面临“下一步走向何方”的困境。石一枫借此塑造了众多桀骜不驯、看似游手好闲的“后顽主”形象,他们尽管从未被社会抛弃,但也一直是这个时代的多余人。石一枫写“北漂”也不单纯写他们在北京的挣扎与奋斗,而是更深入地写“北漂”渴望跻身于上层社会的焦虑与北京人内部对“北漂”的排斥。生于政治文化中心的各种优势和优越,使他有着敢于自我嘲讽的胆识和勇气。《世间已无陈金芳》中同班同学欺负试图融入群体的农村女孩陈金芳,“我”一句“对于一个天生被视为低人一等的人,我们可以接受她的任何毛病,但就是不能够接受她妄图变得和自己一样”,“敌我”阵营的划分显露无疑。同时,“北漂者”在北京的奋斗之路又显得焦急与迫切,他们不仅需要经济上的认同,更急切地想要融入上层生活的圈子里。陈金芳变得光鲜亮丽之后不惜全盘投入追逐着上层阶级的高雅文化,但她却重复着失败的结局,自始至终都是“异类”。石一枫注意到的“北漂”的焦虑心与归属感,以及“后顽主”向何处去的问题,可以说非身处北京城内的石一枫难以描写。
二、不一样的青春写作
石一枫的长篇创作几乎都在描摹一种独特的“京味儿”青春生活,甚少涉及市场流行的那些青春元素。当下文坛上较为活跃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曾有不少被市场化青春写作影响的印记,如张悦然《小染》和七堇年《少年残像》的成长之痛,周嘉宁《寂静岭》中青春的残忍与背叛,张怡微《青春禁忌游戏》和《后海之后,江南以南》的苦涩校园恋情等等。但由于石一枫独特的大院经历,加上正值青春年少时极大地受到王朔的影响,石一枫对“大院文化”有深刻的认同,并“热衷于港台明星的同龄人划清界限,”从而形成了独特的青春写作。
石一枫笔下的“京味儿”青春生活首先直观地体现在他戏谑调侃的“京片儿”上。他不做无谓的无病呻吟,而是时常逞口舌之能幽默自嘲,刷贫嘴成了娱乐自己也娱乐别人的家常便饭。但这些恣意狂欢的语言的背后,是一群追逐快感的青年以玩世不恭的态度填补内心的寂寞。其次,石一枫笔下常见“大院文化”元素。他19岁发表的校园三角恋短篇小说《流血事件》中已经具备小痞子、小伙伴、拍婆子、打架斗殴等人物情节。即使是走出大院的“后顽主”也多是与兄弟连心共同面对成长与生活中的失落与迷惘,并无为了爱情勾心斗角而忧郁颓废的套路。
市场化青春小说中仿佛有意描写少年少女的“成人化”生活,他们在都市灯红酒绿的中挥霍青春和情感,沉浸在自我的“小时代”里,情绪与情节被夸张放大,心思琢磨得极深极碎。与之相比,石一枫则有一种“青春后遗症”。有“‘80后成长小史诗”之称的《红旗下的果儿》出版时,石一枫已进入而立之年。在其之后的长篇写的都是关乎青春成长的作品。从笔下的人物设置来看,石一枫似乎偏好一种“三角”模式:桀骜不驯的“后顽主”,讲义气的好兄弟,美丽自信的女孩儿。主人公在家长权威与世俗规则之间保持距离,无所事事又彷徨失意。“我”身边的兄弟常常是世俗场上的得道“老油条”、“我”与之也只仅限于“酒肉朋友”的关系,始终无心介入利益争夺的泥潭之中。成人的世界仿佛被商业逻辑和一元化的价值体系界定得生气全无,主人公在无处容身的自我寻找中显露出“拒绝长大”的姿态。与此同时,石一枫对笔下的“女孩儿”形象却有着一种偏爱与近乎美好的想象。张红旗、节节、姚睫、莫小萤、小米,她们无一例外美丽、自信、坚韧,同时又有几分“轴”和“倔”来保持着自己独特的品质,外象地体现着石一枫心中对某些美好事物的执着与坚守。石一枫对这种美好和纯真的偏爱也让他长篇小说的结局充满着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女孩儿们几乎都成为了拯救“我”的力量,带领“我”走出自我探寻的彷徨之境。
在人物情感的描写上,石一枫也不像市场化青春写作中极尽挖掘少男少女的私密情感之能事,他笔下的情感有着干净的质感。“口头流氓犯”们在语言上极尽戏谑与调侃,在友情、爱情和亲情上却保持着纯真和专一。赵小提给好友“B哥”至多搭线,绝不参与。面对前妻茉莉提出的复合要求,赵小提也是淡然拒绝。陈星12年间和张红旗分分合合,却也始终为她留下一个空间。杨麦在寻找到亲情与爱情的归宿后,将“吃货网”股权全数卖给好友,欣心成为“无业游民”。石一枫笔下的“女孩儿”们更以年少倔强的姿态明媚地追逐理想,坚守着自我和社会正义。石一枫在不涉及情欲的关系与情感中塑造起了人物,不单记录着个人的成长,更在呼唤这种普遍的纯真情谊。事实上,石一枫写青春成长小说注重描写人物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下的身心变化,使得个人的成长几乎成为一群人的集体记忆。除了引起记忆的共鸣,他试图借纯真的情感从多个角度理解别人的世界。正如石一枫的自我评价:“自负地说,在写北京青年成长史的长篇作品里,我做得比大多数人更像一个作家。”石一枫在青春写作中保持的这份纯真与“反成长”态度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大众已经麻木的关于青春的感受,带着现实的期冀开了一扇理想之门。
三、不一样的现实坚守
1、一脉相承的现实关注
独特的语言风格本就足以让石一枫在纷纭的作家中独树一帜,后期《世间已无陈金芳》的发表更是让他一时名声大噪,俨然成为了青年作家的代表人物。一时之间,各种现实主义重新焕发生命力的言论又如春笋般冒了出来。事实上,石一枫创作从早期开始就是走的关注现实的路子,一直延续至今。
石一枫的第一篇长篇小说《B小调进行曲》,即使带有科幻性质,但依旧大部分成于现实中,而石一枫早期创作中最具代表性的《红旗下的果儿》、《节节最爱声电光》、《恋恋北京》之类作品不必多说,带有着鲜明的现实主义成长小说的印记。个人的成长与时代紧密联系,主人公的成长反映的是时代的变迁、国家命运的缩影。美国轰炸大使馆、新世纪到来、非典、汶川地震等多个具有特殊时代印记的时间点在石一枫的作品中反复出现,主角也在这些极具代表意义的时间点完成了自我的定位与回归。剧烈变化的时代下是鲜明的人物角色,不同于一般的成长小说,石一枫的主角们都不约而同在时代下陷入了“反成长”的状态,他们叛逆、不合作、无所事事,日常活动就是打架、拍婆子,这不仅折射出时代转折中个人与民族国家或理想信念的分裂,也表现了作者对世俗现代性的拒绝和否定,而这种对于时代变化的敏感捕捉和强大的观察力在石一枫之后的创作有着更加鲜明的体现。
2、“返朴”的现实主义
当下的文学创作风格各异、多面开花,各种思想理论喧闹一堂,呈现出多样化的风格。相较于对新鲜事物的尝试,石一枫却在多年的成长历练中越来越“简单”,回归了最传统的现实主义,如他所言:“这些年来我的写作风格,应该还是比较主动地倾向于贴近现实,反映现实,思考现实。”从石一枫对文学的价值思量、小说的评价标准、文学创作观念到具体的写作技法都可以看到相关变化,他认同当下文学的边缘地位,也认同作家的应有责任与担当。创作手法也遵循着传统的理解“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而就创作实绩来看,看似被“用烂了”的现实主义在石一枫的笔下再次焕发了令人瞩目的生命力。
当下的文学作品已经极少能见到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小说人物,但就石一枫近年来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奉献至少一位以上的重要的人物形象,陈金芳、安小南、庄博益、李牧光……每个人物是时代下的典型,由个体命运映射了群体命运,甚至整个时代的命运。《世间已无陈金芳》可以简单看作底层人物奋斗小说,陈金芳是个来自农村的渴望在城里扎根改变命运的小女孩,这容易让人联想涂自强,但相较于他的木讷与僵硬,陈金芳则似乎通晓成功的规则,善于利用身体和美貌获得男人的金钱与人脉,懂得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有野心,有胆魄,但她与涂自强一样最终重复着失败的命运,开服装店失败、投资失败、办厂失败、炒股失败……而挖掘全文,只能从其他人物之口找到零星的对于陈金芳失败原因的相关解释,却是再粗暴不过的“不会做生意”、“不配和我们玩”、“玩不起”。她的挣扎与努力过看起来是如此的可笑,她从未真正融入上层的圈子,也从未被接纳,自始自终她都是“他者”,是个多余人。陈金芳的形象让我们再一次直面了当下固化阶层社会的难题,不仅如此,这逼问着这个社会,当所有的成功标准都指向资本,不成功就是失败,社会就只被这二元对立的观念所绑架,那么多生活在金字塔中下层的普通人该如何定位自我?该走向何方?他们的生存是否还能获得一点应有的价值和尊重?同样,安小男(《地球之眼》)也面临着与整个社会对抗的难题。家境贫困的他拥有常人难以企及的天才思维和能力,本可以轻松改善自己和家庭的生活,但他却被父亲自杀前的“道德”的追问给缠绕了一生。在老板的威胁、亲友的劝告下,他还是选择揭露老板李牧光的“洗钱”行为。他以一人之力对抗社会钢铁洪流般运转的规则,用蝼蚁之力成功地在现实厚重铠甲的缝隙中咬上了一口,完成了自己对于道德的回答与自我社会身份的反抗。但我们要注意,安小男他本身就是一个不普通的“蝼蚁”,相较于天才的安小男,他背后万千的普通的小人物又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翻腾起一点浪花呢?其实安小南个人曲折且辗转的对抗何尝不是另一种无力的挣扎和失败?纵是天才也无法对抗,这才是最大的悲剧。从安小男单个人物中,集中了學生毕业后的出路、社会底层的生存、经济贪腐、国家制度、中国人道德缺失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从一人到整个时代的命运,都浓缩在了其中。由此看来,《地球之眼》无疑是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而石一枫也已经是合格的现实主义作家了。
不是所有人都能代表社会,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强有力地说明和表现时代,而陈金芳、安小男这些人物就是石一枫基于生活观察和推衍出来的足以反映时代的典型人物。宣扬或者反对都不是现实主义的本意,作家更需要对现实有着独到的观察与思考。“简单”背后正是“不简单”,是在平常中看出不平常,在麻木中看出尖锐的矛盾,石一枫用属于文学的观察视角对这个社会的症结提出质问,展现了他成熟后的对于作家身份的思考与责任的担当。
3、现实之中的同情与悲悯
中国的现实主义曾与启蒙主义、社会改革的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而如今,在文学地位日益边缘化的今天,这样的使命与抱负显然不切实际。当文学不再被政治所捆绑时,文学一边失去了以往强大的号召力,也同时获得了自己独立思考的位置。石一枫积极地将作家自身思索介入到自己的创作中,通过作品中的人物命运表达自己的思索与态度。
《世间已无陈金芳》和《地球之眼》中的第一人称“我”就是作家积极介入的证明。“我”这个形象也不是突如其来的,能在石一枫之间的许多作品中找到影子,《B小调进行曲》中的小马,《恋恋北京》中的赵小提,《我妹》中的杨麦,“我”与他们是一脉相承的,有点小聪明又带着骨子里的清高与自负,自以为摸透了社会规则的犬儒的代表。这个“我”就如同是石一枫本人,也是顽主长大后的归处,成熟了,不再满足于语言的狂欢,不再无来由地戏谑人生,看待外物依旧机智、敏锐,但多了理解、同情和关怀。“我”虽然成为了一个第三方的观察者和参与者,但“我”的观察和思索却十分深刻,一眼道破症结,充满了形而上的哲思,“我”对我自己的要求:“我理想中的人生状态是活得身轻如燕,因而不愿与任何人发生实质性的利害关系;我知道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事业是通过怎样的巧取豪夺来实现的。”“我”对现实之后的金钱利益的关系看得如此的清晰和明白。“我”对安小男道德观的评价:“他虽然口口声声地宣称着‘道德,然而他是否能对这个词汇做出一个哪怕是个人主观意义上的定义呢?”他理智上完全明白安小男的坚守就是一场荒诞的冷笑话。这些充满哲思与理性的文字,既是文本内主人公自我形象丰满的一部分,也是石一枫个人对现实推敲后的思考,同时扩展了小说的思想容量和艺术表现力,调动着读者对小说中反映的社会现实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与自我反问。
而难得是,石一枫对于现实的诠释不仅仅停留在反映客观的现实,而是在其之上坚守着自己一点“幼稚”的理想主义。他表达过如果在一开始处理陈金芳这样的人物,他会用戏谑、调侃的笔调,但随着阅历与经验的增长,对这样的人,他开始理解他们的不容易,对之赋予了同情。较之涂自强得肺癌无声无息地死去,陈金芳自杀未遂还保留了一丝生机与对未来的希冀。而作家在安小男身上赋予的“一厢情愿”则更加明显,正是因为自身天才的智慧与能力才能让安小男在最后不仅用自己的方式为自己伸张正义,还能全身而退安身一隅。《营救麦克黄》中的颜小莉也是如此,她尝试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和筹码去惩罚在个人利益面前失去了良知泯灭了人性的黄蔚妮。“哪怕是写实的作品里,也有三六九等之分……很重要的一点,取决于他的写作有没有被一根高远的线吊着。或者说,他心里是否存在着一个明确的‘应然的世界。”这些被时代所吞没的渺小的在底层的人都在挣扎,都在努力发声,对这个荒诞而等级森严的社会做出自己的反抗与努力。作家不僅仅应该写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还应该尝试去写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实主义不意味更加认命和悲观,而是敢于直面和发声。在这个意义上,可见石一枫对自己文学创作的野心和抱负,他想写出这个时代,他想要穿透这个时代,为这个时代发声。
很多人在想,石一枫会走向何方?他能够走多远?但无论怎么样,石一枫都在确认了现实主义这片富有生命力的土壤后继续前行着。纵然人物的塑造、笔法上还稍显僵硬,但故事背后已经可见作家一个愈发坚定的灵魂。从年少启程走上写作的路,他就是文坛上风格独树一帜的石一枫,直到今天,让现实主义重新焕发生机的石一枫,都是独一无二的、不可替代的石一枫。而我们也相信,未来的他将在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 杨 会. 试析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北京情结[J]. 北京社会科学, 2012(2).
[2] 徐则臣. 啊,北京[J]. 人民文学, 2004(4).
[3] 李云雷. 石一枫:为新一代顽主留影[J]. 北京青年报, 2011-02-01(C2).
[4] 石一枫. 世间已无陈金芳[J]. 十月, 2014(3).
[5] 石一枫. 我眼中的“大院文化”[J]. 艺术评论, 2010(12).
[6] 石一枫. 对于“写现实”的一点想法[J]. 文艺报, 2016-04-08,2.
[7] 恩格斯. 致玛·哈克奈斯[M]. //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4:462.
[8] 石一枫. 地球之眼[J]. 十月, 2015(3).
[9] 田 超. 顽主时代已去,我们这代缺乏想象力[J]. 京华时报, 2016-03-26(011).
[10] 石一枫. 文学的“两个世界”[J]. 十月, 2015(3).
【作者简介】
肖露露,女,汉族,广东陆河人,吉林大学文学院本科生。
邓瑶,女,汉族,湖南永兴人,吉林大学文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