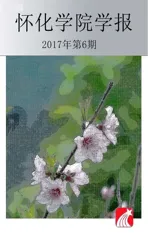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异化及其治理
——基于文献的梳理
2017-03-10王青
王 青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贵阳550000)
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异化及其治理
——基于文献的梳理
王 青
(贵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贵州贵阳550000)
仪式性人情是人情最为直观的一种类型,具有维护农村社会团结的功能,但近年来发生了严重异化,使农民产生了沉重的负担。要对仪式性人情进行有效治理,必须清楚仪式性人情的传统文化意涵和异化逻辑。基于文献的梳理,本文系统性地概括了仪式性人情的传统内涵及其异化逻辑,并对仪式性人情的治理提出了一些建议。
农村;仪式性人情;异化;治理
礼物交换是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的重点领域,某种程度上说,礼物交换在建构着社会秩序,是一种“总体性的社会呈献”[1]。在中国,作为礼物交换的一种类型的仪式性人情,在改革开放之后迅速异化,并曾受到诸如阎云翔、黄玉琴、贺雪峰、陈柏峰、宋丽娜等等一批知名学者的关注。仪式性人情的异化现象已经遍及湖北、湖南、贵州、浙江等地,可以说,它已经成为转型时期中国农村的一种“总体性社会事实”。另一方面,面对仪式性人情的异化,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治理措施,但因对仪式性人情内涵的认识不够、缺乏专门的干预人员、工作任务繁杂和干预合法性受到质疑等等原因,政府对仪式性人情的治理并未起着持续的效果①。要对仪式性人情异化进行有效治理,则首先需要对仪式性人情的传统内涵有着充分的认识,需要充分了解仪式性人情的异化逻辑。然而,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仪式性人情的异化进行研究的时候,大多是通过实地调查的方式进行,很少对仪式性人情异化的研究进行系统的文献梳理,导致了一定程度上的重复研究[2-3]。因此,本文的目的在于通过系统地梳理以往的文献,着重以文献嵌入的方式②论述仪式性人情的传统文化内涵和异化逻辑,并对治理提供相关的建议。
一、仪式性人情研究的整体脉络
基于既有专著和从CNKI数据库中选择的上百篇有关礼物交换、人情、人情消费及仪式性人情等研究文献的梳理,我们从礼物交换研究谈到仪式性人情研究,力图呈现较为完整的有关仪式性人情的研究脉络。
自莫斯和马林洛夫斯基对礼物交换的研究以来,人类学和社会学就从未停止过对礼物交换的探讨[4-5]。礼物交换研究中送礼、受礼、回礼的过程、规则及其功能一直是持续吸引着学者们研究的主题,如马林洛夫斯基通过描述“特罗布里恩群岛”上土著人的soulava和mwali两种物品的交换过程及规则,展现了一种叫“库拉”的交换制度;莫斯论述了送礼、受礼和回礼义务性,展现了“莫斯精神”在礼物交换过程中的重要性[1];翟学伟详细的论述了“报”这一交换内核,指出了中国人人际交换的运作方位等[6];阎云翔考察了中国一北方村庄的礼物交换过程,指出礼物交换是一种“总体性社会制度”,具有培育社会网络的功能[7]。诸如黄光国[8]、翟学伟[9]、金耀基[10]、李伟民[11]、胡先缙[12]等学者一般是通过研究人情、关系、面子、报等本土概念及其相关文化机制,对中国人礼物交换进行研究。换句话说,他们认为关系、人情、面子、报等观念深深的影响着中国人的礼物交换过程,这些观念形成的是一种特殊的交换规则。阎云翔指出,中国人的礼物交换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发生在诸如婚礼、丧葬、与祭祖之类的特殊仪式,另一种发生在诸如亲戚间的互访、邻里间食物与劳动的交换以及朋友间的日常性馈赠[7]。杨华进一步将第一种类型称之为仪式性人情,将第二种类型称之为日常性人情[13]。
在仪式性人情的研究方面,阎云翔曾描述过下岬村仪式性人情名目的增加,同时他还指出,下岬村1984年包产到户以来,人情支出已经迅速增加了[7]。黄玉琴[14]、陈云[15]等一大批学者发现这种异化现象也正从其他农村生发出来,给转型时期的农民带来了沉重负担和心理压力。因此,仪式性人情的异化成为学者们研究仪式性人情的首要的问题意识来源。
概括起来说,当前关于仪式性人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仪式性人情的功能研究,二是仪式性人情异化的现状调查及其异化原因分析。第一、在仪式性人情的功能研究方面,学者们探讨了仪式性人情的正功能和仪式性人情异化的负功能。林源[16]、田学斌[17]等从经济学角度出发,认为仪式性人情除了具有金融交易的风险管理功能、金融储蓄功能、融资功能等金融功能,还具有节约交易费用的效用;宋丽娜[18-20]、陈柏峰[21]、贺雪峰[22]等社会学学者认为正常的仪式性人情具有经济互助功能和社会功能等,这些功能维系了村庄的社会团结。朱晓莹[23]、杨华[13]、陈柏峰[21]、宋丽娜[18]、贺雪峰[22]等人还描述了仪式性人情异化的负功能,指出了异化的仪式性人情会破环仪式性人情中的情感意涵,形成一种攀比机制,使得农民产生严重的经济负担等,这些负面的影响甚至会使得农村社会因此解体。第二,学者们也调查了仪式性人情的异化现状,并对人情异化的逻辑进行了分析,这一点将第三部分进行详细论述,在此不做赘述。
总的来说,仪式性人情大多是作为一种礼物交换在研究中被提及,单独研究仪式性人情的文献并不多。将仪式性人情从礼物交换中隔离开进行研究源于对仪式性人情异化研究的需要。学者们通过大量的调查指出了异化的现状,但是在对仪式性人情异化原因进行分析的时候,显得零零碎碎,并没有系统地考虑仪式性人情异化的结构化因素③,他们要么只看到了市场经济的理性计算对仪式性人情的影响,要么只看到社会力量对仪式性人情异化的制约作用等等。此外,整个仪式性人情研究领域对异化的仪式性人情的治理并未有太多的涉及,因此显得头重脚轻,落脚点不足。本文通过文献的梳理,试图对仪式性人情的内涵和异化进行全面的概括,同时系统概括了仪式性人情异化的结构化因素,这可为进一步的仪式性人情的治理研究提供相关的参考。
二、仪式性人情的传统文化意涵
(一)仪式性人情是“人情”的一种类型
通过对人情、面子、关系、报等概念进行研究,进而达到理解和阐述中国人人际关系的目的,曾在上世纪80、90年代占据着社会心理学的主流地位[7]。在这种人际关系体系中,人情极其重要,甚至占据了中心地位。人情可以说是社会交换的媒介,也可说社会交换是靠人情来维持的[10]。因此,有学者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24],要理解中国社会的日常交往,就必须懂人情伦理规范。
人情规范是与面子、关系、报等观念相互联系形成的“权力游戏”[8]。人情的运行是一种礼物交换的过程,人们通过“送人情”、“收人情”、“还人情”④这一互惠机制(就是人们常说的“人情往来”),社会关系得以建构。同时,关系、报、面子等观念还嵌入这种礼物交换之中,共同影响着人情的运行。关系意味着我们应该向谁送人情、送多少人情以及如何送人情,这其中有着情感和规范意味;报意味着我们只要接受了别人的馈赠,就有回馈的义务,这其中有着强制和互惠的意味;面子意味着在进行礼物交换时不能太过“磕碜”,应顾及自己和别人的面子。因此,人情的运行事实上体现了人情的资源性、互惠性、关系性、规则性等属性。
杨华认为人情可分为仪式性人情和日常性人情。前者指仪式性场合中的表达性馈赠,后者则指非仪式性场合中的表达性馈赠[13]。具体的说,仪式性人情是指伴随着仪式的举办而形成的人的聚集和交往,常常是为了纪念某个人或者某件事,如生日、结婚、满月等,其他的则是日常性人情。仪式性人情与人情的运行逻辑相同,它是人情最为直观的一种表现。通过送礼、收礼、回礼,仪式性人情得以维系。同时,面子和关系也深深的嵌入其中,如亲戚关系和要好的朋友关系会随出较大的礼金,办酒者的人会为了面子而尽可能的办得豪华。总之,仪式性人情是人情的一种类型,具有与人情相同的内涵,所不同的是,仪式性人情是因特殊事件而举办,因此呈现出较强的仪式性、延期性和可预见性。
(二)仪式性人情是一种社会整合机制
仪式和随礼(赠礼)是仪式性人情两个最为主要表征。仪式性人情的举办名目虽不同地区会有不同的侧重,但大致包括生育庆典、婚礼、盖房、拜寿、丧礼等。在每种具体的场合,均有各种礼仪及其仪式,拿黔中大部分地区来说,因盖房举办的仪式性人情会在宴席当天中午会撒“抛梁粑”⑤、结婚时会行跪拜礼等。举办宴席则是仪式性人情必须要安排的盛会(仪式)。礼仪和仪式意味着人们的行为遵循着一定的规范,一切都得按礼来,这些礼符合人情规范,假如逾越了人情规范,人们就会认为你不懂礼(理)。因此,仪式性人情首先体现的是一种与仪式和礼仪等相结合的规范体系。宋丽娜认为这种人情仪式具有功能性、社会性和价值性,它们共同构成了人情仪式的社会整合机制。功能性能够满足农民在互助、交往、情感慰藉等各方面功能需要;社会性是指社会评价系统,人情成为一种“社会场”,是“控制——制裁”二维运作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价值性是人情赋予农民以人生意义体验,并且与集体价值相连,“分化——整合”再造熟人社会中价值合法性和正当性[18]。
仪式性人情另一个显著特征表现为客人的随礼(送礼)。正如莫斯提到的,送礼、收礼和回礼均具有义务性[1],这种义务性与报有着异曲同工之处,使得人情的延续运作成为可能。因此,随礼不仅体现的是一种礼仪,更主要的是它开启了收礼、回礼等一系列交换行为,这些行为体系把乡村社群联系在一起。通过客人随礼,办酒者可以弥补办酒的开销,同时还有相对多的剩余收入,因而有的经济学学者把仪式性人情的这种功能称为金融功能[16]。同时,举办仪式性人情给了人们一个相互联系交流的时间和场合,并且在这种场合中,人们相互帮助,极大地活跃了村庄的人际关系。从长远看,几乎每家都可能办事,这保证了仪式性人情的再生产。因此,陈柏峰[25]、贺雪峰[22]等社会学家认为仪式性人情是农村社会共同体很重要的日常生活,具有维护村庄社会团结的功能。
三、仪式性人情的异化及其异化逻辑
(一)仪式性人情的异化
人情的异化现象早在21世纪初就为学者们所关注。黄玉琴发现了生命礼仪其本初祝福的涵义逐渐被异化,生命仪礼空留了一副包含礼物、宴会、人情伦理的形式,无休止的频繁的人情给人们带来了沉重负担[14]。朱晓莹在对苏北农户人情消费进行个案分析时,指出了人情往来范围的扩大、人情随礼名目的增多和人情随礼金额增大的现象[23]。马春波和李少文对鄂北大山村调查显示了农民人情消费呈现货币化倾向,有50%以上的家庭年人情消费金额已超过其年收入的10%[2]。余芳指出,农民绞尽脑汁办酒,发展出办酒要趁早的逻辑,而随礼者送礼呈现出标准化、货币化的特点,整个仪式性人情呈现功利化特征[3]。
从上文的论述中我们知道,仪式性人情中的仪式和随礼是其最为重要的两个特征,在此,本文把仪式性人情的异化界定为在仪式和随礼两个方面的负向变异。仪式的变异表现在仪式已偏离了以往的文化内涵,仪式的过度简化甚至已经无仪式,仪式的过度娱乐化(如丧事上跳脱衣舞等)。随礼方面的异化主要表现在人们的礼金支出过大,给农民造成了严重经济压力。随礼的支出过大这涉及到农民想方设法增加办酒名目和次数,也涉及到随礼礼金基数增大等。仪式的异化只是给人们带来心理冲击,而礼金支出过大却给农民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以往对于人情异化的研究集中的体现在对农民的经济压力的分析上,而未来进行人情治理的首要目标也应着重于减轻农民的随礼压力。
(二)仪式性人情的异化逻辑
对于仪式性人情的异化的解释,学者们指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基础。市场经济的侵入和农民的流动,不仅使农民开始意识到原有人情过程的繁琐而开始求简,更使农民开阔了眼界并深刻理解了货币的作用,农村传统渐遭破坏,人情往来少了道德约束,人情成了可创收的途径[3]。因此,看到办酒的收益,一些人家开始创造各种名目办酒敛财。而随礼者为了收回自己的送出去的礼金,不得不都创出各种名目办酒,这样,滥办酒就成为一种社会风气而无法遏制。其次,办酒者和随礼者盲目的社会攀比,是导致了人情异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王宁认为,中国人的消费行为并不是无止境地进行炫耀性消费,也不是一味的依据固定规范进行消费,而是依据一种场域逻辑,场域不同,支配人消费行为的规范和规则也就不同[26]。在仪式性人情的方面,在不同阶层场域下,消费依据的规范是不一样的,表现在富裕阶层的高档消费、中间阶层的中档消费和贫弱阶层的压缩消费,这些都是被认为是正常的。但贺雪峰指出,仪式性人情在名的方向异化了,表现在有钱人为了面子送大礼和办好酒,而如果其他阶层的人达不到这种标准,就会被认为不体面,没面子,因而不得不进行这种盲目的攀比[22]。陈柏峰把村庄分为富裕阶层、中间阶层和贫弱阶层三个阶层,指出进行仪式性人情时,富裕阶层为了面子、名誉在“表演”,中间阶层勉强的以这种标准跟随,而贫弱阶层只能渐渐退出,这成为村庄的经济分层和社会确认的方式,并且异化为阶层排斥的一种手段[27]。
但是,对于农民来说,他们还可以有一个途径自己克服这种异化压力,即退出人情圈。那么为什么农民不退出人情圈呢?黄玉琴指出生命仪礼具有可加强农民间联系的客观效果,为农民提供了建构自己社会支持网络的机会,这又是农民所需要的。另外在集体性原则和不可逾越的惩罚性原则下,并不会轻易地终止人情圈[14]。张丽琴指出了随礼是必要的,一是人们有着“一家事大家办”的传统需求,二是感情沟通的需要,三是为了实现收支平衡[28]。此外,笔者调研时发现,仪式性人情作为一种传统,很多人认为“这是祖宗传下来的习俗,是必须参与的,要不然算什么中国人,再说,收了别人礼,你就不能不回礼,不然怎么做人”。
最后,村庄社会力量的式微,使得干预仪式性人情异化的力量不复存在。王宁认为消费者并不完全具备消费自主性,消费行为还有制度嵌入性[29]。消费的制度嵌入性指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受到特定的社会力量的制约的。根据耿羽和王德福对仪式性人情的研究,也证明了这种制度性力量的存在。他们把村庄类型分为伦理型人情村庄、情感型人情村庄和功利性人情村庄,指出并非所有的村庄类型的人情会发生异化。伦理型人情村庄存在着强有力的血缘性组织,构成了一定的社会力量,存在着较为明确的村庄规范,因而抑制了人情的异化;情感型人情村庄大多没有强大的自治组织,村民们的人情实践基于一种情感的自发性,人们进出人情往来是靠感情的亲疏,因此很容易发生异化。功利性村庄是一种舆论道德解体下的情感型村庄,农民举办仪式性人情大多是为了些拉关系、谋声望和敛财[30]。宋丽娜也认为社会力量与仪式性人情异化之间具有相关性,并且提出了一种公共性和私人性的分析框架。公共性是指仪式性人情受到社会规范的制约,私人性是指举办和参与仪式性人情的自主性,她指出了仪式性人情异化的原因在于现代社会的公共性向私人性的转变[20]。当前,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口流动加快,传统社会结构日渐瓦解,礼物交换向理性化馈赠的方式的转变,制约人情异化的社会力量式微,人情异化现象正在肆无忌惮地蔓延开来。
四、仪式性人情异化的治理
如何克服仪式性人情的异化?通过对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了一个吊诡的现象:学者们在描述和解释人情异化方面做了大量的研究,而对如何克服仪式性人情异化的研究却相当的少。总体而言,社会学学者和经济学学者的治理建议有着明显的不同。诸如像金晓彤[31]、刘军[32]、陈云[15]等经济学者们更关注制度因素,他们认为治理异化的仪式性人情一是应该进行制度创新,大力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二是要改善农村教育条件,提高农民文化素质,促进农民传统观念的更新;三是应拓宽农民投融资渠道;四是要推进城镇化的步伐,鼓励农民外出务工,使农名从异化的人情中摆脱出来。而社会学者更倾向从文化角度进行治理。如耿羽和王德福认为可以相互协定不随礼或者采取将礼金物化等形式,淡化仪式性人情运行中的“钱味”[32]。贺雪峰认为,可以通过三种实践应对仪式性人情异化,一是使人情频次高但礼金数额小;二是使人情频次低但礼金数额大;三是使人情频次低且礼金数额小。这三种实践可以保证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存在和再生产[22]。
但我们应该明晰的是,农民频繁的举办仪式性人情并不是融资的需要,而是赚钱的需要,因而拓宽融资渠道并不会阻止仪式性人情的异化;其次,笔者发现,大部分外出务工的农民并不会脱离仪式性人情,他们会请家中的亲戚帮忙送礼,或者回家来时补礼,所以所谓的推进城镇化步伐,使农民外出务工可以抵制仪式性人情的异化也不过只是一种幻象。最后,进行一些制度创新,推进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与完善和改善农村教育等措施并没有针对性,或者说与仪式性人情异化治理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明显。正如上文提到,经济的发展是导致仪式性人情异化的一个重要基础,因此通过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推进城镇化等并不是解决仪式性人情异化的“良药”。贺雪峰和耿羽等人提出从文化角度进行治理的思想,是一种核心的根本的诊治,但他们忽视了治理的主体,单纯想依靠农民自身进行反异化实践,这是不太可能的,因为并没有迹象表明农民可以自己从中抽离出来,相反,他们正无止境的参与在这种异化的仪式性人情之中。
故而,要对仪式性人情异化进行治理,应明确三个问题:治理主体、治理方向和治理措施。所谓的治理主体,指的由谁来治理;治理方向是指我们该从哪些方面进行治理;治理措施是一些具体的可实施的措施。要治理异化的仪式性人情,必须有一股力量作为治理主体。然而,大多人情异化的地方,都是一些原子化的农村社区,传统的社会力量已经不复存在[22,32],因此,政府应担负起人情异化治理的主体责任。其次,治理的主要方向应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培育起村庄的内生性的社会组织,作为未来反人情异化的自主力量;二是进行文化治理,重在挖掘和培育仪式性人情中情感文化,对人们的工具性观念和面子观念进行批评性的教育宣传;三是批评盲目攀比之风,形成良好社会风气。最后,在治理措施上:一是印发红头文件,规定党员干部应先做表率,规定办酒的名目和礼金基数等,形成制度;二是形成专门的领导组织;三是进行广泛地宣传;四是认真地贯彻落实,并形成长效监督机制等。当前,很多地方政府正在进行仪式性人情异化的治理,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出现了很多治理的困境,如干预人员不够、干预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干预人员未能一锅端平等等。因此,对于仪式性人情的治理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注释:
①若无特别说明,本文涉及的经验材料均源于笔者对黔中地区的调查,在此做统一说明。
②笔者这里所说的文献嵌入的方式是指通过引用以往研究观点的方式来充实文章内容的叙述方法。
③这里所说的结构化因素主要是指存在于农民主体之外的力量对仪式性人情的影响因素,包括市场、社会力量和传统的文化观念,这在下文的仪式性人情异化的逻辑部分会有所论及。
④人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送人情”实际上就相当于“送礼物”,这种礼物不仅表现为具体的实物,也表现在帮忙做事情上。
⑤站在新房房顶,向楼下的客人撒喜糖、红包以及糍粑等表示庆祝。
[1]莫斯.礼物[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
[2]马春波,李少文.农村人情消费状况研究——鄂北大山村调查[J].青年研究,2004(12):16-21.
[3]余芳.农村社会人情的发生及其异化[J].农村经济,2013(5):96-98.
[4]董敬畏.乡村社会交换研究述评[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1(3):161-164.
[5]林升栋.礼物、关系和信任[J].广西民族研究,2006(4):80-87.
[6]翟学伟.报的运作方位[J].社会学研究,2007(1):83-98.
[7]阎云翔.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42-120.
[8]黄光国.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C].黄国光编.面子:中国人权力的游戏[A].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9]翟学伟.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情理社会中的社会交换方式[J].社会学研究,2004(5):48-57.
[10]金耀基.人际关系中人情之分析[C].杨国枢主编.中国人的心理[A].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8.
[11]李伟民.论人情——关于中国人社会交往的分析和探讨[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2):57-64.
[12]胡先缙.中国人的面子观[C].黄国光编.面子:中国人权力的游戏[A].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13]杨华.农村人情的性质及其变化[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2008(1):41-44.
[14]黄玉琴.礼物、生命仪礼和人情圈——以徐家村为例[J].社会学研究,2002(4):88-101.
[15]陈云,顾海英,史清华.礼金成重负:农村人情礼往行为的经济学分析[J].消费经济,2005(6):60-63.
[16]林源,芮训媛.农村人情功能演化的金融学逻辑[J].农村经济,2012(10):74-77.
[17]田学斌,闫真.农村人情消费中的非正式制度:一个交易费用理论框架[J].消费经济,2011(3):85-89.
[18]宋丽娜.人情仪式:功能性、社会性与价值性[J].民俗研究,2014(5):148-155.
[19]宋丽娜.人情的社会基础研究[D].武汉:华中科技大学,2011:160-162.
[20]宋丽娜.人情往来的社会机制——以公共性和私人性为分析框架[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19-124.
[21]陈柏峰.农村仪式性人情的功能异化[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06-113.
[22]贺雪峰.论熟人社会的人情[J].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4):20-27.
[23]朱晓莹.“人情”的泛化及其负功能——对苏北一农户人情消费的个案分析[J].社会,2003(9):28-30.
[24]冯必扬.人情社会与契约社会——基于社会交换理论的视角[J].社会科学,2011(9):67-75.
[25]陈柏峰.熟人社会:村庄秩序机制的理想型探究[J].社会,2011(1):223-241.
[26]王宁.炫耀性消费:竞争策略还是规范遵从[J].广东社会科学,2011(4):196-209.
[27]陈柏峰.仪式性人情与村庄经济分层的社会确认——基于宁波农村调研的分析[J].广东社会科学,2011(2):206-213.
[28]张丽琴.随礼的历程考察与心理分析——基于东北农民K的随礼账册[J].中国农村观察,2010(5):75-84.
[29]王宁.从“消费自主性”到“消费嵌入性”——消费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转型[J].学术研究,2013(10):38-44.
[30]耿羽,王德福.类型比较视野下的中国村庄“人情”研究[J].青年研究,2010(4):14-23.
[31]金晓彤,陈艺妮,王新丽.我国农村居民人情消费行为的特征与基缘——以豫南杨集村为例[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3):123-129.
[32]刘军.农村人情消费的经济学思考[J].消费经济,2004(4):17-20.
A Review of Ritual Favors in Rural China and its Distortion and Correction——Based on Study of Related Literature
WANG Qing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Guizhou University,Guiyang,Guizhou 550000)
Ritual favors are the most intuitive type of favors with the function of maintaining rural social solidarity.In recent years,it has undergone serious alienation.If the rituals are to be effectively governed,the cultural meaning and alienation logic of ritual favor must be clearly understood.Based on the combing of literature,this article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connotation of ritual favor and its alienation logic,putting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on the governance of ritual favors.
rural community;ritual favors;distortion;governance
C91
A
1671-9743(2017)06-0034-05
2017-04-18
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消费社会学视角下贫困文化治理研究——以正安县为例”(研人文2017053)。
王青,1992年生,男,贵州开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农村社会治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