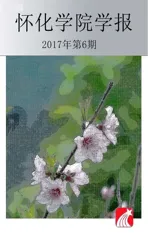认同与传承:花鼓灯文化推广略论
2017-03-10许振波
许振波
(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认同与传承:花鼓灯文化推广略论
许振波
(蚌埠学院文学与教育学院,安徽蚌埠233030)
当前,“东方芭蕾”花鼓灯的传承保护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调研发现,由于包括学界在内的各界对花鼓灯文化的认识不够、认同不足,导致当前保护传承工作仍出现诸多问题。基于文化认同的视角,在明晰花鼓灯文化推广原则的基础上,借助田野调查,从依托政府主导、立足自主创新等方面探讨其文化推广路径,供花鼓灯及其他有关民族民间艺术参考借鉴。
花鼓灯;文化;推广;认同
近年来,花鼓灯艺术依托“国家文化创新工程”(2011)、“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项目”(2013)等国家级文化工程,通过建设“花鼓灯原生态保护区”,在政府、业界、学界及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迅速复苏,成效明显。然而,与此同时,依据近期对“中国花鼓灯第一村”安徽省蚌埠市禹会区冯嘴子村的村民抽样问卷调查显示,当地花鼓灯原生态班子仍在锐减;艺人老龄化问题突出,表演技能处于消退状态;中青年传习者缺乏研习的热情与动力,动作只能停留在对老艺人的简单模仿上,一些特有的花鼓灯表演技艺濒临消亡。毋庸讳言,当前花鼓灯传承保护工作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同时,尚进展缓慢、任重道远。而上述问题表现中更值得注意的是,个别访谈发现,保护区的村民甚至部分老艺人对花鼓灯文化意蕴的理解并不清晰,认识欠缺统一,这种现象在年青群体尤其是播布中心区以外的受众中表现得更为明显,花鼓灯文化基因的延续与传递令人堪忧。由于缺乏文化认同的内在需求,面对市场经济大潮中其他强势的外来文化,其文化选择往往受制于功利驱动,花鼓灯保护、传承、发展的持续动力不足也就不难理解了。
花鼓灯作为首批国家级非遗,作为“迄今为止世界上单一语汇最多、最丰富系统的民族民间舞蹈语言体系”[1],其保护传承的意义无需赘言。当前,花鼓灯在保护传承发展工作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有着共同的根源。文化认同是保护传承的前提,只有在对民族文化充分认同的基础上,形成“认识共同体”,把握到其文化精神内涵与魅力,才会产生自觉的文化追求,从而萌发保护传承的原动力。花鼓灯文化的全民认同过程将对更好地保护传承花鼓灯艺术,进一步彰显其“凝聚人心、和谐乡里”的特质内涵,进而推动形成特色文化产业,带动地方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起到“定海神针”的作用。与此同时,文献研究发现,目前学界更多关注花鼓灯作为非遗保护和传承的具体做法,也有少量与宗教、体育、经济等学科的交叉研究,但立足一种文化本身的视角,就花鼓灯文化如何通过推广获得认同的研究似乎被遗忘。检索可见,目前以“花鼓灯”为题的约400篇现有文献中涉及文化主题的不足十篇,而就花鼓灯文化认同与推广方面的研讨更为寥寥,亟须引起学人的关注。
一、花鼓灯、花鼓灯文化与文化认同
被誉为“东方芭蕾”的花鼓灯是我国优秀的汉民族民间艺术,其源于宋,兴于明,盛行于清末民初,现已形成以安徽蚌埠、淮南、阜阳等为中心,辐射淮河中游河南、安徽、山东、江苏四省二十多个县、市。她不仅拥有潇洒奔放的舞蹈,还含有欢快热烈的锣鼓、抒情优美的灯歌和情趣盎然的小戏,集歌舞、杂技、武术、戏曲、锣鼓、吹奏表演于一身[2]。花鼓灯不但自身独具魅力,也是淮河流域一些艺术品种的根脉,如淮剧、泗州戏、凤阳花鼓等都是由她衍生而来,可以说,花鼓灯影响和丰富了淮河以北的民间舞蹈和民间艺术[3]。
作为汉民族民间歌舞文化发展到高级水平的标志性艺术,花鼓灯的流行必有其文化基因。但纵览花鼓灯艺术研究文献,“关于花鼓灯文化定位研究方面的文献,数量明显不足。可能是这一地域性较强的文化品类,尚未引起文化学专家们的足够重视”[4]。对于其艺术起源及文化功能,学者们有多种迥异甚至矛盾的说法。仅就“花鼓灯文化”字面来说,学界目前也尚未对其概念内涵做出专门界定,但一般认为其包含精神信仰文化、自然生态文化两大层面的内容。就精神层面而言,在当地人的思想观念中,花鼓灯就是“大吉大利的代表与象征,只要有花鼓灯存在,就会有驱邪、去秽、平安、健康和幸福……”。可见,花鼓灯之所以能够不断流传与推广,其所具备的精神信仰是其中相当重要的因素,尽管部分信仰缺乏科学论证甚至是迷信的,但毋容置疑其给当地广大民众带来了重要的精神寄托。花鼓灯鼎盛时期“千班锣鼓百班灯,村村都有花鼓灯”的文献考据、民间对花鼓灯老艺人“听了‘小蜜蜂’,无被管过冬;看了‘一条线’,三天不吃饭”的真切口述,佐证了花鼓灯文化的巨大价值。可见,花鼓灯艺术的文化功能难以替代。
“文化标定身份认同,它如同群体的指纹”[5],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总是与其认同过程相生相随。“认同”是指“在社会情境中,个体对其他个体或群体的意向方式、态度观念、价值标准等,经由模仿、内化,而使其本人与他人或团体趋于一致的心理历程”[6],认同感是使人们聚合在一个群体中的情感,体现为成员之间的亲切感,具有社会心理稳定性。与此同时,认同又是“动态的、自然发生的,认同会发生变化,具有可塑性;认同是客观社会存在与个体意识作用相结合形成的,既是个体意识作用的结果,同时也依赖客观社会存在的一些条件”[7]。由此,花鼓灯文化的认同也是在发展中嬗变而可控的。如何引领受众对花鼓灯的认识,通过文化推广培育有利于其保护、传承、发展的大环境,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道重要而紧迫的命题。
二、“认同”视阈下花鼓灯文化推广的原则
结合上述有关文化认同的理解,可以总结认为,“认同”其实表达的是一种关系,是指人与人、人与群体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作为一种关系,必然是双向和互动的[8]。有鉴于此,花鼓灯作为一种源于民众日常生活的“草根文化”,更应该也更可以从其作为文化的“认同”这一最本源的视阈入手,进行推广传递。而在这一进程中,作为“非遗”的花鼓灯的传承也就自然是水到渠成了。
基于此,参考国内外其他优秀民间文化传承推广的成熟经验,花鼓灯文化推广总的原则是,维护并加强花鼓灯传习者的文化自信,帮助他们保持文化生命力;以接受对象的立场、视角、话语,融入性地进行花鼓灯文化基因的延续与传递。具体而言,应注意以下方面:
(一)群众性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人民群众,花鼓灯文化的推广仅凭政府和学界的热情而没有民众的参与不可能成功。作为民间的活态文化,作为一种发展着的行为方式,花鼓灯遗产的保护和利用应以满足现实民众的需要作为根本出发点。群众是花鼓灯文化推广的真正主体,坚持群众性原则是花鼓灯文化推广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生动性
生动,谓之以灵态,给人以活的感觉,即通过各种创新、有效的路径将花鼓灯文化最大程度地展示给受众,进而激发其保护与传承意识。但与此同时也要注意,在文化传递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其内涵不变,在保有原生性的基础上发展,应避免盲目追求所谓生动而忽视文化遗产本身所具备的特殊规范性要求,特别需要避免为迎合受众求新求异需要而对花鼓灯文化进行过度包装甚至随意改装。
(三)完整性
花鼓灯文化既包含着丰富多样的内容和形式,又与特定的生态环境相依存。她由无数具体的文化事象构成,不是某些“代表作”和零散的“文化碎片”所能涵盖的。因此,我们倡导的保护是以全方位、多层次的方式来反映和保存花鼓灯文化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是要保护花鼓灯文化所拥有的包括传承人、生态环境在内的全部内容和形式。只有这样,才能更透彻地展现花鼓灯艺术的多面美。
三、花鼓灯文化推广的具体路径
(一)政府主导的“群众路线”式推广
近年来,通过设立国家“花鼓灯原生态保护区”等政策的施行,地方政府在花鼓灯文化传承中的主导地位得到加强。今后,应进一步贯彻“群众性”的推广原则,不断巩固强化政府的这一主导角色,发挥好财政支持的资金效益,为花鼓灯推广提供更适宜的文化生态环境。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在“保护区”的基础上,重点打造花鼓灯特色“民俗村”。围绕花鼓灯核心播布区,选择“中国花鼓灯第一村”冯嘴子村等适合村落,设立若干花鼓灯“民俗村”。民俗村中在保留部分传统民居的前提下,新建房屋统一以汉风为主,引导村民穿着汉服日常生活,构建原生态村落,吸引游客前来进行融入性的文化体验。要紧密结合新农村建设、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政策引导,借力2014年9月安徽省被确定为“国家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试点、首批已启动建设20个行政村农民文化乐园的东风,着手营建符合花鼓灯爱好者实际需要的场馆,购置演出服装、道具等装备,打造特色文化活动中心——“花鼓灯农民文化乐园”,通过“建成一个乐园、带动一片区域、活跃一方文化”[9],不断扩张花鼓灯文化的播布范围。
同时亟须引起注意的是,政府主导并非简单地制定政策、下拨款项,更要关注政策执行中的实际情况,考量资金的使用去向与效益。田野调查发现,目前花鼓灯核心保护区冯嘴子村在道路修建等方面尚可,但“演习所”等场馆的实际使用效率非常低,除接待重要来访客人外平日紧闭,更多作为一种“形象工程”而非真正为周边花鼓灯练习者所用,实际上反而挫伤了更多玩灯人的积极性,这种情况在淮南市陈巷子花鼓灯生态村的陈派花鼓灯歌舞艺术馆也有出现。上述问题亟待建章立制、加强管理,务求改观。
2.借鉴其他国家非遗文化推广传承的先进经验,发挥产学研用、校府合作等方式的效用。如韩国上世纪80年代就要求中小学生有到“民俗村”学习和体验生活的经历,并将这一经历视为与学生的考试成绩同等重要。通过在“民俗村”中收集、保存、展示本国民族民俗资料和文化遗产,体验传统民间生活,进一步强化了年轻人弘扬优秀文化、保护文化遗产的意识[10]。有鉴于此,建议花鼓灯播布区的地方政府充分认识花鼓灯文化推广的重要意义,引导在基础教育阶段开发花鼓灯传统文化校本课程,在高等院校中开设花鼓灯相关选修课,鼓励学生成立花鼓灯艺术社团。通过花鼓灯文化的日常化接触,让年轻一代沉浸于花鼓灯的习得氛围,使这一文化基因充分延续,不断焕发新的生命力。
花鼓灯文化推广要“从娃娃抓起”,近年来已取得一些实际成效。如蚌埠新城实验学校将花鼓灯列为特色校本课程;蚌埠学院音乐舞蹈系设立校地合作“花鼓灯研习基地”,将《花鼓灯》课程列为音乐学等相关专业的必修课,聘请花鼓灯表演大师长期担任专业教师;淮南师范学院将《花鼓灯艺术概论》列为校级特色教材重点建设;乃至北京舞蹈学院将之定为民间舞专业必修课,等等。但与此同时更要清醒认识到,花鼓灯文化教育的普及面、受益对象目前还相当有限,如何在相关中小学及高校进一步推广,更好地实现花鼓灯优质基因活体传承,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3.善用各种新媒体,谋划搭建交流平台,不断扩大花鼓灯文化的影响范围。花鼓灯艺术遍及沿淮流域,但目前还欠缺为各地爱好者交流与讨论的官方平台。建议由花鼓灯文化播布中心城市蚌埠、淮南两地牵头,创设“花鼓灯艺术振兴联盟”,举办相应节会、年会等大型活动,邀请有名望的花鼓灯表演艺术家、工作者研讨交流。与此同时,策划对花鼓灯省级传承人等领军人物的适度包装宣传,发挥明星效应的作用;迎合“互联网+”时代的发展趋势,发挥新媒体的积极作用,开设“花鼓灯艺术官方微博(微信)”、“花鼓灯原生态保护区”主题网站、相关APP等自媒体平台;积极谋划蕴含现代科技因子的花鼓灯艺术数据库建设,不断吸引更多人群尤其是年青群体对花鼓灯文化的了解。通过上述举措,使花鼓灯文化在交流传递中相互借鉴、融合发展。
(二)立足自身的“自主创新式”传递
文化只有在继承中不断创新,才有更持久的生命力。花鼓灯艺术的繁衍离不开自我展示,更需要自主创新。随着时代大潮的更迭,作为汉民族优秀的非物质文化遗存,花鼓灯文化基因的本质不应该改变,但其创作、表达不必再拘泥于农耕文明下的自娱自乐,不可墨守成规、裹步不前,而应主动求变,在坚持“生动性”与“完整性”推广原则的基础上,将传统花鼓灯文化魅力与时代文化需求有效融合,迸发出属于新时代的文化活力。
1.破除思维定势,改造表演形式,吸引更多关注。花鼓灯文化推广过程重要的一环是观念变革,力戒因循守旧。事实上,花鼓灯作为我国独具魅力的民间艺术形式,其自身文化基因中的关键词之一就是“变”。传统花鼓灯表演具有“场域”的灵活性特点,即根据表演时间、地点、对象等情景灵活变换,其灯歌常常是因境生字、信手拈来。老一代艺人在外出表演时,往往陈述的就是“出去玩”,他们把花鼓灯文化看作一种“玩”的文化,具有较强的自娱性、即兴性特征。但传统表演形式一般要求人数足够、动作相对程式化,有很多局限,可以尝试与其他舞蹈艺术乃至跨门类艺术形式如二人传、小品等联姻,以更好适应当今个性化、快节奏的文化消费生态。令人欣喜的是,2013年斩获代表全国专业舞蹈艺术最高成就“荷花奖”的花鼓灯独舞剧目《花鼓佬》,打破了传统花鼓灯表演至少两人以上的定势,并借鉴融合了一些西式舞蹈动作语汇,丰富了表演力,既吸引了一部分青年群体,也让其他忠实观众感觉别有韵味,这种保有原生态文化基因的大胆创新值得鼓励与推广。
2.挖掘花鼓灯文化元素,通过适度合理的艺术加工,与其他大众文化有机融合。基于形式创新之外,花鼓灯艺术同样也可考虑在内容、用途等方面加以调整。如结合芭蕾等舞蹈形式,编创特色花鼓灯健美操,赢得各类人群尤其是女性群体青睐;抑或追寻道家文化渊源,推行与养生相结合的广场舞、工间操等,使其不止适用于老年人,也适合在职员工;再如将花鼓灯灯歌、锣鼓、舞服等元素有机融入微电影、MTV等现代视听媒体,创意花鼓灯衍生影视艺术产品,吸引青少年等更多人群的目光,开拓花鼓灯文化传承更广阔的空间。
花鼓灯艺术是弥足珍贵的汉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接力花鼓灯文化的推广,在认同中传承发展,为其他民族民间艺术提供参考借鉴,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使命。文化传递是一个潜移默化的长期过程,一种文化的推广普及需要足够的时间,前进的路上可能不会一帆风顺,但目标与路径一经选定,当风雨兼程。相信通过各方努力,古老的花鼓灯艺术定将迎来更美好的明天!
[1]谢克林.从花鼓灯的保护探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机制体系的构建[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04(4):57-61.
[2]我国优秀的民族民间艺术——花鼓灯[EB/OL].(2011-08-09)[2015-12-06].http://www.people.com.cn/BIG5/192244/227553/227559/22810 9/15371227.html.
[3]花鼓灯[EB/OL].(2010-01-05)[2015-10-06].http://www.mzb.com.cn/ html/Home/report/113505-1.htm.
[4]杨传中.多学科视角看花鼓灯歌舞艺术中的文化[J].安徽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89-92.
[5]支运波.发现文化:淮河花鼓灯的景观与理解[J].文艺争鸣,2010(10):92-99.
[6]车文博.弗洛伊德主义原理选辑[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
[7]李素华.对认同概念的理论述评[J].兰州学刊,2005(4):201-203.
[8]秦慧源,刘红琳.从“认同”到“承认”——关于“认同”与“承认”关系的综述[J].怀化学院学报,2010(9):30-32.
[9]安徽探索建设“农民文化乐园”,架设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 [EB/OL].(2015-11-14)[2015-12-22].http://news.xinhuanet.com/local/ 2015-11/14/c_1117142563.htm.
[10]莫代山.韩国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的实践与经验[J].中华文化论坛,2015(4):34-38.
Identity and Heritage:Promotion on Culture of Flower-Drum Lantern
XU Zhen-bo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Education,Bengbu College,Bengbu,Anhui 233030)
In recent years,flower-drum lantern,known as the“oriental ballet”,has been made certain achievements in the inheritance protection.But a survey has found that culture awareness and recognition of flower-drum lantern is not enough from all sectors including academia,leading to many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heritage protection work.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identity,and the basis of clearing cultural promotion principles of flower-drum lantern,we propose relying on the government leading and promoting independent innovation through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so that it may provide references to flower-drum lantern and other relevant national folk arts.
flower-drum lantern;culture;promotion;identity
C953
A
1671-9743(2017)06-0012-04
2017-05-03
2016安徽省社会科学创新发展研究课题“新媒体视阈下安徽花鼓灯文化的传承与弘扬”(2016CX058)。
许振波,1974年生,男,安徽蚌埠人,副教授,研究方向:文化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