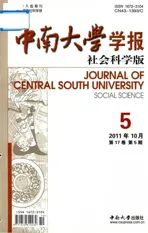罗蒂对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的超越——以命题“权利优先于善”为分析焦点
2011-02-09董山民
董山民
(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
上个世纪70年代自罗尔斯《正义论》发表以来,政治哲学界对于“权利(正当)和善何为先”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人们拥有的权利到底是自然天赋的,还是来自共同体及其法律制度的认可?回答这一问题,人们必须诉诸一些有关人的本性、自我等观念。新实用主义者代表性人物罗蒂认为,自由主义过于拘泥于权利的形式,而社群主义则侧重于内容。罗蒂把历史和语境引进了正当和善之争,以实用主义的方式超越了社群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
一、争论的焦点:权利优先于善吗?
众所周知,罗尔斯的《正义论》和《政治自由主义》发表后,政治哲学界发生了大范围的争论。争论的要点之一就是权利能否独立其隶属的共同体,换句话说,个体的具体权利是不是天赋的,跟历史和现实中任何具体的政治法律共同体及其认可是否有关系。美国学者桑德尔在罗尔斯的著作出版之后发表了《自由主义和正义的局限》。在该书中,桑德尔表述了社群主义与罗尔斯式自由主义争论的焦点:
罗尔斯的自由主义与我在《局限》一书中所提出的观点之间的争执关键,不是权利是否重要,而是权利是否能够用一种不以任何特殊善生活观念为前提条件的方式得到确认和证明。争论不在于是个体的要求更重要,还是共同体的要求更重要,而在于支配社会基本结构的正义原则,是否能够对该社会公民所信奉的相互竞争的道德确信和宗教确信保持中立。易言之,根本的问题是,权利是否优先于善。[1](2)
争论的焦点在于正义和权利能不能够不受一个共同体在自己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善观念的制约。在桑德尔看来,罗尔斯用来证实其正义原则的前提,即自我观,也就是那个处于原初位置隔着无知之幕进行理性选择的个体,是一种唯意志论的自我,这个自我脱离了其所在的历史境遇和共同体身份,因而是无法琢磨的古怪的“个体身份理论”。罗尔斯则认为,如果我们不从权利(正当)优先于善出发,那么,社会中的某个个体很可能受到以社会整体为名的伤害。正因为如此,罗尔斯主张:其一,某一权利如此重要,以致哪怕是普遍的福利都不能压倒、僭越之。其二,具体规定我们权利的正义原则,并不受制于任何特殊善生活观念已经获得辩明。必须提醒读者的是,罗尔斯阐述正义问题的思路是从他精心设计的思想实验开始的。我们在《正义论》中总是能够看到康德式先验论证,也只有这种超越经验约束的思想实验才能保证其理论的普遍必然性。
罗尔斯在《政治自由主义》中提出了这些权利并不需要凭借任何完备性的道德、宗教、或哲学观念的证明。譬如,现在有三个病人A、B、C,他们都急需器官移植手术以恢复健康,延续生命,而恰好另外一个病人D濒临死亡。碰巧的是,D拥有上述三个病人急需的器官,而且这些器官功能完好,可以满足A、B、C三个病人的医疗技术要求。根据功利主义有关效用的善观念,D为其它三人捐献器官,挽救其它三人的生命,其总体的效用肯定增大无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能不能进行三例器官移植手术呢?功利主义的回答是肯定的。因为社会总体功利增大的情况下,当然可以牺牲某个个体对自己的身体拥有的权利。但是,自由主义则认为不可,其理由是个体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最高的主权,任何以整体功利增大为理由,在没有获得D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做法,显然侵害了个体的权利。此时,整体的效用之和不大于个体对自己身体拥有的主权及其由这种主权所产生的利益。某种价值,这里是指效用价值,与另一种价值身体完整权不可通约。换句话,这是一种不同层级的效用,不能按照功利主义的计算方式行事。
社群主义认为,我们的共同体认为哪种行为具有价值是我们共同体的实质的善观念所决定的。如果某个共同体认为保存生命是实质的善,如果牺牲某个个体的身体的某个器官能够让更多的人获救,使得总体功利增加,那么,这种行为就没有违反个体的权利。因为那位捐献自己的器官帮助别人延续生命的人自己也接受了这个共同体的善观念。这里根本不存在冲突和价值不可通约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焦点在于,生长于某个政治、道德、宗教共同体之中的人是不是毫无条件地接受并按照某种善的观念采取行为?就是说,镶嵌在共同体之中的人不但认肯了某种善观念,而且还丧失了对此种善观念进行反思、反抗的意愿和能力。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二、争论背后的预设:权利的来源
为上述争论提供高层次理论的是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各自不同的预设。
现在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体有没有对自己的身体拥有最高的主宰权,如果有,这种权利又自来哪里?再者,如果我们否定了个体对自己的身体拥有全部的主权,社会一旦存在医学上的需要,就可以任意地处置任何人的器官,而不需要征询个体的同意,这样做的后果是什么?康德和罗尔斯认为,这必然导致一个危险的后果,即多数人的利益压倒个体和少数人的利益,整个社会形成“多数的暴政”。为了防止这种暴政,罗尔斯认为权利优先于善,其中隐含的价值诉求是个体对自己的任何部分拥有最高权利。但是社群主义立刻就会指出,你之所以坚持权利优先于善,恰恰是因为你认肯了人的尊严、身体完整性这种善的实质观念。因此,是这种善的观念决定了你拥有的权利及其具体内容,譬如要求尊重人的自决,要求尊重人的尊严。倘若一个共同体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善的观念,或者共同体所有成员并没有认可这种善观念,那么,他们就不可能为自己要求这样的权利,那个恰巧生活在这样的共同体之中的病人D就会献出自己的器官。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要点在于个体在为某个集体或他人牺牲自己的时候,他是否自愿,他还能不能具有一种自由意志。社群主义认为,只要个体生活在某个共同体,而且认可了这个共同体的价值观和善观念,他们就会愿意接受共同体以整体利益为名要求他做出的牺牲。此时,个体根本就丧失了批判自己所属共同体善观念的能力,而且反思性的学习能力也会被剥夺。他不会、也不能试图跃出自己的共同体的边界,选择另一种身份认同和另一种善观念。罗尔斯认为,社群主义把这种观点(权利不能独立其历史和共同体而存在)极端化、普遍化、理想化了。罗尔斯认为,权利固然离不开共同体的善观念,但是①共同体及其传统为个体的权利提供了背景,但是它们不能决定个体的权利观念。而社群主义混淆了为权利提供背景和决定权利内容这两个不同的层次;②在权利和善之间存在一种张力,个体在逻辑上优先于共同体,个体的意志仍然是自由的,个体具有学习和批判自己所在共同体善观念的意志和能力。但是社群主义否认这种张力的存在。罗尔斯为了建构其社会制度的正义性,特别强调个人行为正当性的重要性。在他看来,共同体确实为权利提供了背景,但是共同体不能为权利形式奠定基础,尤其不能决定个体的权利。因为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很多生活形式会不断涌现出来。譬如,洛克生活的年代,人们没有要求同性结婚的权利,但是现在同性恋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合法化。再者,罗尔斯后期接受了柏林多元论思想的影响。根据这种多元论,现代社会是一个没有了客观价值的社会,各种价值和善观念之间不可通约,人们没有一个上层价值或善观念,可以用来化解和解决上层价值之下的各种竞争和冲突性价值或善观念之间的矛盾。哈贝马斯也认可了这一点。他说:“随着多元主义世界观的出现,在现代社会里,宗教以及其中的伦理便不再是一种所有人都认可的公共有效性的基础。具有普遍约束力的道德法则的有效性无论如何都再也得不到完整的不容反驳的辨明,因为这些用来变化的理由和解释是以超验的创世主和救世主的存在作为前提的。”[2](11)这样一来,正义和善的基础就在规范的存在者自身当中。麻烦在于,我们的共同体不是纯粹的,单一的,只拥有一种“善观念”,或者在这个共同体内只有一种价值。譬如范跑跑也生活在我们儒家文化共同体中,但是,他为自己辩护的理由则不同于很多其他人认可的价值。
按照社群主义的理论,“善观念”决定我们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在善观念不再单一的多元社会中,基于各种善的多元性的权利也会发生冲突。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我们让善决定我们拥有何种权利,这就必然导致一种善观念和目的压倒了个体的权利。康德很早就看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人们对经验性的幸福目的及其幸福所在都有着各种不同的观点,所以,只要涉及到幸福,他们的意志就不可能服从任何共同的原则,因之也不可能服从任何与每一个人的自由和谐一致的外在法则。”[1](7)这种诉诸某种经验上善观念的做法,譬如功利主义推崇的效用最大化,将会导致社会中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人,强者或多数压制弱者和少数。因此,善观念的多元化趋势导致善和权利之间的尖锐冲突。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和以桑德尔为先锋的社群主义之间爆发的争论是罗蒂提出实用主义政治道德哲学的背景。从某种意义上说,罗蒂调和了两者。我们在本文余下的篇幅中讨论罗蒂的立场。
三、罗蒂对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超越
罗蒂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回应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争。
其一,实用主义不在任何具有可靠的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意义上谈论真理和善观念,根据这样的知识观,罗蒂坚持认为“自我”不是一个实体。在罗蒂看来,自我只不过是由信念和欲望之网所组成的叙事重心,在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条件下,自我还会不断地自我修正,新的信念和欲望将被编织进来。从他一贯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出发,罗蒂说:“在我看来,这个存在主义的自我,就像康德的只听从无条件的义务召唤的本体自我一样,是一个神话。这两个神话都假定,三个机能(理性、意志和欲望)的合而为一已经不幸地变成了规范的,那个三者合一恢复了柏拉图有关灵魂诸部分的邪恶等级序列。”[3](286)他认为,自我在交往互动中逐渐丰富自己的信念和欲望系统。在此意义上,他赞同桑德尔的观点,我们不能离开具体的历史和共同体来理解我们的权利和善的观念,自我镶嵌在具体的社会历史实践之中,构成自我的是大量的有关世界和意义的信念和欲望。罗蒂在这个问题上受到了米德如下观点的影响:自我并不是历史文化消极的剩余物,主我的一面具有原发性的创生能力,就像尼采所说的自我超越一样,自我会在新的经验和交往实践中找到重新编织自我信念和欲望之网的契机,并能够把握住这些契机。
但是,罗蒂不同意桑德尔对罗尔斯的一些批评。他认为,罗尔斯不像桑德尔批评的那样还预设了一种具有实体意义的自我。在罗尔斯那里,自我已经具体化为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而且这些公民是启蒙运动的传人,他们不再耽于私人的完美,而是倾注在公共领域,以具体的政治为目标,强调公共领域的自由。罗蒂为罗尔斯辩护道:“罗尔斯不一定是指一个被称为‘自我’的实体,它可以被用来区别自我所拥有的信念和欲望的网络。当他说我们不应当指望独立定义的善为我们的生活赋予形式时,罗尔斯并没有把这种‘应当’置于自我的本性这一主张之上。‘应当’不可以用‘由于道德的内在本性’来注解,也不能用‘因为选择能力是人格(personhood)的本质’来说明。”[4](185-186)因此,在罗蒂看来,罗尔斯根本上已经丢弃了自我的谈论,直接谈论的是接受了启蒙政治计划所倡导的一系列价值的自由民主社会的公民。也就说,罗尔斯不再纠缠哲学上形而上学问题,他关注的是政治。因此,罗尔斯在论证权利优先于善的时候,对自我的界定,与其说是一种哲学的或形而上学的考察,不如说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描述。[5](170)罗蒂界定了这些公民:“按照我的观点,不存在要把自我分裂为各项官能(faculty)的需要,只要把自我看作各种信念和欲望的网络即可。所有的自我总是同等地受到了拘束,只不过有些受到了良好信念的拘束,而有的则受到了不良信念和愿望的拘束。没有一个自我比另一个自我具有更强的意志、更多的理性和更强烈的嗜好。不过,与其他自我具有的从属关系相比,其中有些自我具有的从属关系将使之更加具备适合民主社会的公民资格。”[3](286)在罗蒂看来,自我不是一种形而上学的抽象的主体,类似康德的先验主体,也不是罗尔斯意义上的处于原初位置的参与订立正义契约的人。自我总是具体的历史和文化条件的产物,他是不断流动的,因为历史和现实条件的变化而变更着自己的内容和构成元素。在当前的形势下,自我就是接受了启蒙运动所倡导的大字眼,譬如自由、平等、民主等价值的公民。罗蒂的反本质主义立场导致他不从“人的本质是什么”这个角度思考权利问题,而是从人何时成为什么样的人、成为什么样的公民这个角度思考问题。对于“什么构成了人的本质”这个问题,罗蒂认为这是一种纯粹私人领域的形而上学问题,而“人成为何种公民”的问题则是公共领域的政治问题。在政治公共领域中,公民们面对多元价值和善观念的冲突应该怎么办?这涉及罗蒂第二点回应。
第二,各种社群、共同体引以为道德身份(moral identity)的善观念不是真理意义上的观念,政治公共领域的活动不应该让这些观念成为妨碍他们对话的因素。参与对话的行动者应该把自己终将诉诸为善观念的东西视为模糊的、非固定的、可修正的观念。罗蒂认为,主张实践优先的自由主义者把道德认知的问题弃置一边,他们在面对“人的生命起于何时?”等问题时,否认任何道德观念或宗教观念存在真理问题,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者尽力回避了富有争议的形而上学断言。罗蒂坦然承认:“我们不应该试图把文化划分为存在物质事实的认知部分和不存在物质事实的非认知部分。詹姆斯和杜威的确千方百计地模糊了认知和非认知的区分。我们应该继续保持这种模糊性。”[3](288)在实用主义那里,真理问题决不是静止地找到一个陈述,它能够准确地再现实在。我们使用在实践和历史文化传承中形成的语言来帮助我们应付环境,认知世界或对象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的目的是用语言做事,语言是人类自然史的一部分。至于各种各样的善观念,譬如功利、幸福、自由、民主、平等、宗教观念、道德信念,都是某些共同体在历史长期演化的过程中逐渐凝结起来的。某个共同体成员在传导和接受的历史文化传递中习得的知识、信念、自我的道德认同确实变成了我们无法拒绝的一部分,譬如一个出身并生活在儒家文化圈的人自然就会习得儒家家天下的观念,同样,长期在基督教文化中耳濡目染的人就会信仰上帝的存在、灵魂不朽等等。罗蒂并不否认,现代社会不同的共同体、社群都有自己的道德认同,譬如,某一时期的基督教团体相信圣餐变体,拒绝同性恋,反对堕胎,主张废除奴隶制,这些团体和社群把这些信念当成自己的核心价值,如果有人试图通过强制手段,或者以其他方式触犯、亵渎他们的核心价值和道德身份,他们就会发动革命,进行分裂活动。那是因为这些团体、社群、共同体中的成员把这些信念当作了不能被修改的真信念,因为它们是真信念,所以他们具有非凡的力量。罗蒂认为,这些人把私人领域的问题放到了政治领域,如果人们坚持他们的形而上学的信念,而完全拒绝在任何条件下进行没有任何终极前提的对话,那么,冲突不可避免。
罗尔斯看到了这个问题后(即多元主义)提出了政治自由主义。他主张在“重叠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对话,达成一些非原则、无本体论诉求的共识。罗蒂的主张是:我们不能在任何终极信念、核心信念、道德认同上达成一致,但是,我们不必把这些实质性道德问题当作不可修正,万世不移的真理。那些反对在社会合作层面进行对话的共同体成员其实都是某种原教旨主义者,这些具有宗教狂热倾向的人被罗尔斯排除在自由民主社会之外。一旦我们放弃了这种类似原教旨主义式的道德认同感,不再认为某种“善观念”具有压倒性的合法地位,我们就能在具体的实践中为了社会合作而进行商谈。对那些信奉某种价值观和接受某种“善观念”的社群,罗蒂说:“设法使他们把问题‘人的生命开始于何时?’改为‘人们对堕胎问题如何才能达成一些无原则的空洞的共识’。想办法使它们变得尽可能地灵活和空洞,想办法使他们对民主共识的重视超过对任何其他事物的重视。”[3](289)按照罗蒂有关成熟社会的思考,虽然我们相信我们现有的信念只是相对有效的,但是我们还要坚持这些信念。但是我们不能把这些信念当成终极意义上为真的东西。自由民主社会就是这样的成熟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我们相信启蒙运动倡导的价值,但是我们不把这些价值当成唯一为真的价值,而是当成人类社会发展到如今有史以来最好的、最有效的、最容易达成一致的价值。
第三,各个不同的共同体彼此拥有的善的观念和价值不是纵向的层级关系,而是平面的共存的多元关系。不同的共同体之间,共同体内部不同的个体之间的对话必须遵循程序正义,而不固守某种实质正义。罗蒂说:“我使用的‘哲学多元主义’这个词意指这种学说:存在一组可以引领人类生活的潜在而无限的具有同等价值的路径,这些路径不可按照优先程度进行安排,而只能按照它们对某些被它们引导的人和那些人们所属的共同体能够做出的贡献来处理。”[6](258)接受了这种哲学多元主义,我们就不会停留在形而上学和任何哲学、宗教和道德等完备性学说的基础上进行交往。价值多元化意味着我们不能把实质性的道德信念和道德原则当成我们生活的普遍指示物。罗蒂认为,认识到这一点,并不等于我们放弃了我们的信念和道德认同,而是让我们这些分属不同共同体的成员意识到:在对话中遵循程序正义时,我们这些负责任的政治共和运动的参与者所拥有的道德底线(譬如反对奴隶制和同性恋)不是最终的正确的底线,而是可以移动的、灵活处理的底线。一旦在我们的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我们万不得已为了一个共同的实践目的展开对话,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现有的信念和道德认同的底线予以模糊处理。做到模糊处理我们所持信念和道德认同的具体办法是坚持桑德尔所说的“程序共和制度”。他对程序共和制度做了界定:“程序共和制度是这样一些政治体制,在其中,尽可能地不把对实质性道德问题的解答——正如尽可能不把赞成为人行善的观点——融入政治制度中。”[3](287)罗蒂提醒我们,坚持程序共和制度不等于放弃任何道德底线,譬如反对奴隶制,只不过这种底线不是固定的,而要根据具体的实践目的和事务,在谈判和对话中进行淡化、松动、修改和调整。他说:“我们最低纲领的自由主义者认为,请求哲学家指出多大的淡化是过于淡化、多大的松动是过于松动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些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民主制度就达成妥协的原则做出政治决定。哲学家接着通过形成新原则来澄清谜团,那些新原则论证了与旧原则达成妥协的合法性。”[3](290)
四、结论:站在自由主义和社群主义之间
总之,罗蒂认为,社群主义指责罗尔斯预设了一个纯粹的唯意志论意义上的自我,并由此构建权利优先于善的理论,是没有道理的。任何诉诸实体性的自我,哪怕桑德尔和泰勒意欲借助黑格尔和海德格尔的理论来获得一个崭新的自我,都是不能成功的。因为这在罗蒂看来都是形而上学的,而不是政治的。罗蒂在为罗尔斯辩护的同时指出了罗尔斯保留完备性概念的不足。我们知道,罗尔斯为了既避免康德式的先验唯心主义和过于形式化的道德学说,又能够保持道德学说的普遍必然性,不得不在善的多元性的背景下放弃《正义论》中的思想实验(无知之幕、原初位置),转向理性多元论、公共理性以及重叠共识等观念。罗蒂批评社群主义误解了罗尔斯,没有看到罗尔斯的后期转变,即放弃哲学论证、转向政治公共领域。我们看到,罗蒂主张以对话和程序性共和制度来达成妥协,然后以此为前提解决各方共同面对的问题。换句话说,他呼吁人们不要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而要以务实的方式解决公共领域中的问题。这反映了罗蒂的实用主义立场。
[1]桑德尔.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M].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1.
[2]哈贝马斯.包容他者[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3]罗蒂.后形而上学希望[M].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3.
[4]Richard Rorty.Essays on Heidegger and Others [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5]罗蒂.后哲学文化[M].上海: 译文出版社, 2003.
[6]Richard Rorty.Philosophy and Social Hope [M].New York:Penguin Group,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