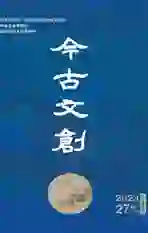柳宗元动物寓言的悲剧意识研究
2023-07-21吴丹
【摘要】柳宗元永州时期的动物寓言体现了一种独特的悲剧意识。柳宗元寓言采用动物视角,在动物世界中展开自己人生的论述。经梳理,其动物寓言中造成悲剧的事理原因有二:一是盲目的生活所导致的悲剧;二是善恶冲突强烈而导致善遭毁灭的悲剧。这些悲剧书写源于书写主体心中的悲剧意识,这与其年少时家庭沉重记忆的影响,贬官时期的感官体验与反思相关。柳子寓言散文发乎真性真情,对中国寓言史之丰富性和深刻性做出了自身的贡献。
【关键词】柳宗元;动物寓言;悲剧意识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3)27-003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3.27.011
动物寓言是指以动物为主角或者是以动物作为寓言中一个重要的意象且具有一定象征意义的故事,并且这些故事虽然表现的风格各不相同,但都是具有一定的劝谏或者讽刺意义。柳宗元永州时期的寓言,半数是以动物为主体,形象鲜明,如《临江之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憎王孙文》《罴说》《谪龙说》等等。
唐顺宗永贞年间,官僚士大夫为打击宦官势力,革除政治积弊为目的进行改革,持续时间一百多天,最后改革以失败告终。年少不谙世事的柳宗元因文气扬名,得到了王叔文的青睐,参与永贞革新。在这场改革中,柳宗元因没有注意到实际,以理想的方式进行改革,最终失败。此次失败也让柳宗元再无缘于京都当差,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贬谪生活。永州远离京都长安,是边荒之地。柳宗元在永州任闲职期间,留下了为数不多的寓言。在这些寓言里,他阐述了自己被贬谪之后的处境,求告无门,身体状况下降,精神世界痛苦,借寓言去宣泄自己内心的愤懑以及悲痛,摆脱自己精神世界的挫败感。
在过去的研究中,多数学者把柳宗元寓言作为整体进行研究,较少学者把柳宗元的动物寓言单独作为研究对象。对于柳宗元永州时期的动物寓言,大部分文章都没有把这些动物寓言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且较少有学者关注到柳宗元动物寓言中所隐含的悲剧意识。据此,柳子动物寓言如冰山一角,学界仅浅谈,其内涵与质性尚存深入解读的空间,其中所隐含的悲剧意识值得关注。拟从两个方面逐层探究柳宗元寓言散文的悲剧意识:一,论柳子动物寓言中的悲剧意识;二,阐述柳宗元的悲剧意识从何而来。希冀于柳宗元寓言散文的悲剧意识研究有进一步的推进。
一、动物寓言悲剧意识的体现
柳宗元寓创作于永州的寓言,也是体现其悲剧人生的一个方面。与先秦寓言相比,柳宗元的寓言采用动物的视角,使动物成为主角,甚至开口说话,在动物世界中展开自己人生的论述。
(一)盲目的命运和偶然的机会
柳宗元的寓言故事主角有两类,一类是动物,另一类是人。柳宗元的寓言中以动物为主角的有鹿(《临江之麋》),有驴(《黔之驴》),有鼠(《永某氏之鼠》),有蝜蝂(《蝜蝂传》),有猴子(《憎王孙文》),有蝮蛇(《宥蝮蛇文》),有罴(《罴说》),有龙(《谪龙说》)等等。这些动物可分为两类:一类是自然界可见物种;一类是虚构物种。常见的物种如麋鹿、驴、鼠、蝜蝂、猴子等,虚构的如龙。种类虽不同,但悲惨的结局却相似。
以《三戒》为例,共三篇,分别是《黔之驴》《临江之鹿》和《永某氏之鼠》,选取的动物形象是驴、鹿和鼠。《黔之驴》,当地本无驴,好事者船载以入,将驴置于山下,引来老虎。简短的寓言中详细记载了老虎与驴互动过程中的变化。老虎第一次见到时:“庞然大物也,以为神……” ①第二次则是“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 ②。紧接着,老虎慢慢从一开始的畏惧变成试探,“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 ③。最后老虎识破了驴的表面,将其杀害。《临江之麇》记载临江人得到了一只麋,将其畜之,并让其家狗与其嬉戏。狗一开始是垂涎,后与其戏耍,给鹿营造了一种两个不同物种和谐相处的假象。麋鹿稍大,忘记身份,认狗是同类,在路旁与其他狗玩耍,最后引来杀身之祸。狗与麋本非同类,麋在一同驯养中,忘记其本来身份,溺于表象。《永某氏之鼠》记载一人因自己生肖属鼠,视鼠为神,不养猫犬,而养鼠。鼠已习惯不被打扰,便放肆生活,但某氏后来搬离,鼠不知,仍行之如往,后居者不堪忍受,便对老鼠进行扑杀。鼠本非人,无法知人所想,只因前人不厌它,便忘了警惕,最终酿成大祸。
《三诫》中的动物中的驴、鹿和鼠皆是因偶然机会进入新的生活环境,新环境给这些动物的生活带来了新元素,人类营造的和谐氛围给它们带来了“归属感”,却也为他们悲惨的命运点燃了导火索,卷入一场动物界的优胜劣汰之争。对这些动物来说,它们无法选择,只能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三则故事中无论是哪一种动物,它们居于食物链的最低层次,因人为因素而进入到其他生物圈,面对更凶猛的动物,面对周遭环境短暂的安全,它们丧失警惕,甚至企图融入,掉入现实世界的陷阱,最后却被最残酷的方式杀害,粉碎了安乐生活。
(二)角色对比突出
柳宗元善于利用角色对比去表现美好事物的消逝,揭示理想和现实之间冲突的悲剧性。在《憎王孙文》一文中,将猿和猢狲进行对比。暴躁吵闹的猢狲德行败坏,互相残杀,咬死茂盛的美树却无法被处置,然而,“居相爱,食相先,行有列,饮有序” ④的猿却被凶猛的猢狲排挤打击。通过将猿与猢狲的对比描写,展示出猿的安分守己和猢狲的蛮横凶残。猿与猢狲这两个形象交相辉映,整篇寓言的构思和情节安排也都反映出柳宗元独到的心裁與手眼。在《憎王孙文》中,尊猿而贬猢狲,隐喻了柳宗元的是非判断。猢狲残暴而得势。这反映了永贞革新失败后的政治现实中的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小人当道,因而也同样包含着深刻的悲剧内容。
这种对比在《牛赋》中也有所体现,原文中描写了牛和驴两种动物。牛在古代农民家庭中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如“抵触隆曦,日耕百亩。往来修直,植乃禾黍。自种自敛,服箱以走。输入官仓,己不适口” ⑤。牛不仅能够在农业生产领域发挥作用,如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还能运输粮食,减轻农民生活的负担。相反,驴“曲意随势,不择处所。不耕不驾……喜则齐鼻,怒则愤踯” ⑥。牛与驴,一勤一懒,一静一闹,差异之大。但是,两种动物的结局却并未因能力强弱而呈正相关,牛因年老而逐渐力衰,无法再进行农业生产,农户试图将牛身上的全部好处榨干,全身骨肉无法自保护,而驴却因“善食门户,终身不惕”。两物结局截然不同,对劳于功,益于世的牛,人们是毫无惭愧,物尽其用;对不劳无功,无益于世的驴则是善始善终。此文章将牛与驴放在一起比较,紧紧抓住有利于天下和无益于世这一杠杆,在层层鲜明的对照描述中,牛和驴各自的特征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同时,处于封建时代的柳宗元虽说“命有好丑,非若能力”的宿命思想来安慰自己,但这也仅仅是表面的现象,是作者为维持自己的尊严时的愤慨之语,是一种更为强烈的宣泄,怨后说勿怨,更是一种难以平静的怨恨,表达了对奸人得道的不满,也流露出对自己悲剧人生的不平。
当时,柳宗元的挚友刘禹锡也写了有关动物的寓言散文,虽都是同时期被贬荒凉之地,经历相似,但刘禹锡的性格与柳不同,故创作的动物寓言与柳子寓言也有所差异。同样是写牛,刘禹锡的《叹牛》借刘子与老人的问答,对刘子之牛的一生的处境变化进行描述,牛从作为牲畜圈养时的过度劳作,再到衰老之时成为盘中物,可悲可哀。此文虽是在同情牛的遭遇,但更为主要是借牛之处境变化喻人之处境,在牛年老渐衰以后,使用价值的减少,处境的变化,悟出自己的人生道理,更多地站在人的处境去思考人如何在时代生存,抒发物尽其用之后的悲哀。而柳子的《牛赋》,虽写牛赋,并非单独以牛为描写对象,反而增加了羸驴,为牛的描写添加比照对象,两两对比中突出双方的矛盾冲突,情节引人入胜,充满故事性。文章让动物开口说话,绘其形,述其功,哀死尽其咏,一生劳作不止,结局却悲惨。进一步地抨击,将勤勤恳恳的、奉献所有的牛和懒懒散散、投机钻营的弱驴之间的结局进行对比,猛烈地抨击了不劳无功、无补于世的羸驴,抒发了对牛之悲惨境遇的愤懑之情,表达了对老实人遭到迫害的愤恨之情,影射了当时朝廷用人不明的官僚制度。对比两人的作品可发现,柳宗元与刘禹锡的寓言创作心态不同。柳宗元在寓言作品中注入了较为强烈的情感,既充满了悲观的情绪,又以悲悯之心关怀着世间的万事万物,更多地流露出对困境无法改变的郁闷之感;而刘禹锡的心态是更为积极的,更多的是从动物的境遇变化中探索人如何在变化动荡中求得生存,在所倾诉的苦难中获得生存经验,从而化解心中的苦闷。两人的寓言在表方式上的差异性大于相似性。
在柳子寓言中,这种美丑或善恶的对比亦尤为突出。从这些鲜明对比中,不难看出其中包含着善与恶的冲突。这些冲突表现出不合理性,给人以强烈的道德震撼。柳宗元在他的动物悲剧寓言中,通过对善的被损害和毁灭表明了他对美好理想的肯定和追求,对黑暗政治现实的强烈愤恨和鞭挞。
二、动物寓言悲剧意识的缘起
柳宗元深刻的悲剧意识来源于现实人生。他幼年饱尝战乱流离之苦、青年体验短暂得志之喜、壮年经历长期贬谪之郁。纵观柳宗元短暂一生,苦闷的日子占据三分之二。悲剧的人生不仅影响了他的性格,也反映在作品中。
(一)年幼时家庭沉重的记忆
柳宗元,祖籍唐蒲州解县(今山西运城市西南解州镇),出生于代宗大历八年(773),是“安史之乱”被平定的第十年,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失去了盛唐大盛之时的风范。在柳宗元的成长过程中,战乱不断,居无定所。在他出生前后的时期,他的家庭因战乱度过了一段艰难生活,柳家因战乱,再一次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于战乱中,举家汇入逃亡人流中,一路逃到吴地。在南方,经常面临生计困难的窘境,父亲柳镇甚至不时地需要外出求贷以供给薪米之需。有一次,他骑驴外出途中,经过一个山涧,被山洪裹挟,险些丧生。柳宗元的母亲卢氏,为了供养亲属、子女,常常自己节食挨饿。柳宗元在文章中屡次提起这段经历,可见年幼时的经历给这个家庭留下了极其沉痛的记忆。柳宗元在九岁时曾亲眼看见战争的发生,写下一篇《夏口破虏颂》。在789年,柳镇外贬为夔州司马,柳宗元的家庭受到权官的直接迫害,父亲因此被贬谪。甚至在后几年的贬谪生活中,父亲逝世。对于柳宗元的幼年成长时期来说,家庭屡遭不幸的经历对他的影响更为直接。像柳宗元那样普通的小官吏家庭,受到当时社会动荡和政治形势的波及和纷扰也是极为严重的。从四岁时,懵懂的柳宗元在长安度过,对当时朝廷的腐坏,社会的动荡有所见所感。在九岁时,因战乱跟随家人离开长安,直到公元785年后,才返回自己的出生地。在幼年时期,他的家庭一再卷入动乱的漩涡之中,这使他自幼对社会灾难和危机有着更为真切的感受,个人对痛也有更深切的体悟。
(二)贬谪生活中的感官体验与反思
青年时期的柳宗元意气风发,年少中举,有一腔报国的热血,却因永贞革新早早退场,一贬再贬,被贬永州十年。一个在政坛上想施展自己才能的年轻人梦想夭折了,于荒凉之地开始自己的贬谪生活。被贬永州给柳宗元的身心带来巨大的伤害,“永州于楚为最南,状与越相类,仆闷即出游,游复多恐。涉野有蝮虺、大蜂……近水则畏射工、沙虱,含怒窃发,中人形影,动成疮痏” ⑦(《与李翰林建书》),“蛇虺之所播,狸鼠之所游,茂树恶木,嘉葩毒卉,乱杂而争植,号为秽墟” ⑧(《永州伟使君新堂记》),永州环境恶劣,毒虫众多,杂乱荒僻。“至则无以为居,居龙兴寺西序之下” ⑨(《永州龙兴寺西轩记》)。柳河东被贬此地,无官舍,只能借居于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龙兴寺。“诊视无所问,药石无所求” ⑩(《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袝志》),居无所,病无医,药难求,这使柳宗元生活的最低要求都无法满足。“行则膝颤,坐则髀痹” ?(《与李翰林建书》),“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 ?(《寄许京兆孟容书》),环境的恶劣对柳宗元的身体造成了严重的损害。除肉体的折磨外,还有心灵的磨难。居永州十年,柳宗元担任永州司马外置同正员,无公务,无事可做。此外,作为永贞革新中被贬的“罪臣”,他还需忍受世俗环境的压力,他在《答问》中说道:“独被罪辜,废斥伏匿。交友解散,羞与为戚,生平向慕,毁书灭迹。他人有恶,指诱增益;身居下流,为谤薮泽。” ?人本是利益结合体,利尽缘散,孤身处于荒地的柳宗元,忍受冷眼与谩骂。在永州十年贬谪生活里,柳宗元忍受肉体的折磨、理想的幻灭,丧失了自信,走向人生的低谷期,开始政治中心之外的市井、乡野生活。
纵观柳宗元的短暂一生,幼年感受国家战乱,壮年得志一时,被贬永州数十年,朝中始终无人为其美言,“众畏其才高,惩刈复进,故无用力者” ?。在苦苦等待与期盼之中,柳子始终没能使自己超脱。柳宗元在柳州走完了其痛苦生命历程的最后时光,结束了悲剧的一生,享年四十七岁。但柳宗元的悲剧人生与其文学建树实则难以两分。
总之,柳宗元贬谪永州后,从年少时的意气风发沦为困苦耻辱,职位的闲散,环境的恶劣,身体的不适,都对他的永州时期的作品产生了影响。他的作品也随着自我处境的变化而变得悲凉,如寓言作品中通过动物的死亡来揭示永貞革新时自己的处境的艰难,这或许也是柳宗元对自己在长安为官得出的失败经验总结。因此,通过对柳宗元寓言的探析,对他这一时期的寓言创作有进一步的认知,有助于进一步了解他贬谪永州的心态变化和变化原因。
注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349页,第1349页,第1349页,第1257页,第126页,第126页,第2008页,第1805页,第1860页,第826页,第2008页,第1955页,第1072页。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一六八,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136页。
参考文献:
[1](唐)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3.
[2]尚永亮,洪迎华编选.柳宗元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4]孙昌武.柳宗元评传[M].北京:中华书局,2020.
[5]张妙丽.刘禹锡与柳宗元寓言文学比较研究[D].西北大学,2020.
[6]丁光清,孟修祥.柳宗元作品的悲剧意识及其有限消解[J].晋阳学刊,1994,(01):80-84.
作者简介:
吴丹,女,汉族,江西赣州人,闽南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古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