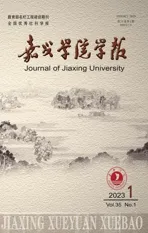论木心的中国古典小说研究
——以《文学回忆录》为中心
2023-01-17赵东旭
赵东旭
(浙江外国语学院 浙江文化“走出去”协同创新中心,浙江杭州 310023)
1989年1月15日到1994年1月9日,木心先生在纽约讲授“世界文学史”,后陈丹青将其整理成册,名为《文学回忆录》,该稿在2013年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木心学识渊博,学贯中西,对中国文学和海外文学都有着深刻的认识,尤其是他在论述中国古典小说方面的造诣,对今天学界的古典小说研究,仍有着重要的参考意义。本文基于学术史的视野,拟对木心有关中国古典小说的论述进行详细探究。
一、视唐传奇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
木心《文学回忆录》[1]1093的章节编排,虽然参考了郑振铎的《文学大纲》(1927),但就中国古典小说本身的编排来说,颇另有深意。现将两部文学史著作中有关中国古典小说的章节编排,对比如下:
如表1所示,与郑振铎的《文学大纲》相比,木心对古典小说的章节编排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木心淡化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分期。他对古典小说的论述虽然仍有分期意识,但并没有予以重点强调,而更注重个人化表达,即主要提出自己对古典小说的认识。第二,木心显然更加突出曹雪芹在中国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因此,目录中出现了将“十八世纪中国文学”与“曹雪芹”并称的标题。

表1 《文学回忆录》和《文学大纲》古典小说章节编排对比
在木心看来,唐传奇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唐前小说只能称作是“叙事性的散文”,是中国小说的萌芽。他在第二十九讲《中国古代小说(一)》中提到:“在我看来,古代小说是叙事性的散文,严格说来不能算小说。直到唐代,真正的小说上场,即所谓‘传奇’。”[1]360木心认为,唐传奇精美、奇妙、纯正,作者的写作技巧一下子就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唐传奇堪与契诃夫、莫泊桑和欧·亨利等西方短篇小说名家的作品相媲美,且有过之而无不及。他把唐传奇分为“恋爱、豪侠和鬼怪”三类。在第一类“恋爱”类故事中所提到的《霍小玉传》,其爱情传奇实在罗曼蒂克,感情张力之猛烈,悲欢喜怒之千般百味,表现力极佳。木心还提到志怪类小说写得更好,《聊斋志异》的文笔虽好,但论情节叙事,却难有一篇比得上《枕中记》或《南柯太守传》。这些志怪小说虽是怪异的寓言,却写得人情深刻,阔大自然。总之,在木心看来,唐传奇注重小说的写作技巧感情充沛,不输于欧美现代短篇小说,已经具备现代小说的多个要素。
木心对唐传奇文学价值的肯定,很好地呼应了鲁迅提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学术命题。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唐之传奇文》(上)中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2]69首次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论断,认为唐传奇在叙述和文辞上都较六朝小说有很大改观。他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1924)一文中也说:
小说到了唐时,却起了一个大变迁。我前次说过:六朝时之志怪与志人底文章,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到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而且文章很长,并能描写得曲折,和前之简古的文体,大不相同了,这在文体上也算是一大进步。[3]
鲁迅认为,与六朝简短的志怪与志人文章相比,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时,文章篇幅很长,且描写曲折,在文体上也算一大进步。这一观点对学界认识和研究唐传奇产生了深远影响,得到了学界的认可。郑振铎在《文学大纲》第十八章《中国小说的第一期》中论述唐传奇时说:
像以上(唐前)所举的小说,都是琐杂的记载,不是整段的叙写,也绝少有文学的趣味,所以不足跻列于真正的小说之域。到了唐时,才有组织完美的短篇小说,即所谓“传奇”者出现。这些“传奇”所叙事实的瑰奇,为前代所未见,所用的浓挚有趣的叙写法,也为前代所未见,于是便盛行于当时,且为后人所极端赞颂。[4]
郑振铎认为,唐前的小说都是一些琐碎的杂记,并不完整,缺乏文学趣味,称不上真正的小说。唐传奇“组织完美”,内容“瑰奇”,叙述“浓挚有趣”,为“前代所未见”,为后人所赞颂。因此,木心认为,直到唐代中国才有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出现,并对唐传奇予以高度评价。
同样,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也把唐传奇视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开端。他在上卷第十二章《唐代文学的新发展》第四部分“短篇小说的进展”中介绍唐代小说时提到,中国的文言短篇小说之所以能在艺术上产生价值,在文学史上获得地位,都源于唐传奇。
那些传奇,建立了相当完满的短篇小说的形式,由杂记式的残丛小语,变为洋洋大篇的文字,由三言两语的记录,变为非常复杂的故事的叙述。在形式上注意到了结构,在人物的描写上,注意到了个性。内容也由志怪述异而扩展到人情社会的日常材料。于是小说的生命由此开拓,而其地位也由此提高了。[5]
在刘大杰看来,唐传奇已经具有相当完备的短篇小说形式,不再像六朝时代还未成形的小说作品那样,只是一些没有结构的“残丛小语”式的杂记,叙事没有布置,形式与描写较为拙劣与贫弱,文笔亦极俗浅,实际上并不能称作小说。但唐传奇在形式上“注意到了结构”,在人物描写上“注意到了个性”,叙述内容也由志怪述异扩大到了现实生活。因此,他认为小说的生命在唐代“由此开拓”,其地位由此提高。其他诸如谭正璧、余锡森和刘开荣等学者,都把唐传奇看作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
可见,木心与郑振铎、刘大杰等文学史家、小说史家一样,都把唐传奇视为中国现代短篇小说的开端,与鲁迅提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也是一致的。不过,近年来学界对“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甚至提出质疑。陈文新在《“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命题不能成立》一文中认为:
“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前提“传奇者流,源盖出于志怪”本身就站不住脚,鲁迅把有意以虚构的方式叙事写人视为“有意为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实际状况不符,没有任何一个“唐人”是按照与今人相近的小说观念而“有意”写作的。[6]
因此,在陈文新看来,鲁迅提出“唐人始有意为小说”的前提站不住脚,与中国文学的实际发展状况不符,其观点值得商榷。刘晓军在《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辨》中也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个论断的得出,源于鲁迅在西方小说观念主导下的心证,不但学理依据缺乏正当性,逻辑推理也经不起推敲。”[7]他认为鲁迅的这一观点缺乏学理依据,逻辑上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完全是在西方小说观念主导下的论断,是“无效的证言”。
综上所述,木心在其《文学回忆录》中视唐传奇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小说,为当今学界重新认识学术史上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论断提供了新的佐证,有助于学界更加深入地探讨这一问题。熟谙西方文化的木心结合自己的小说创作实践,显然是从西方小说观念出发,基于现代小说的评判标准,来审视唐传奇的,这与郑振铎和刘大杰等文学史家的古典小说研究有相似之处,丰富了学术界对唐传奇的研究。
二、用西方小说观念审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论述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时,更多的是“以西律中”,用西方现代小说标准来衡量中国小说,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
首先,不同于郑振铎、刘大杰等其他文学史家,木心特别重视民间社会的“说书”,将其看作是民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中国文学大多古奥渊雅,专供士大夫欣赏,给成年人欣赏,也没有儿童文学,但一直有民间社会的存在。[1]363木心结合自身经历,提到“说书”对于民间文化的重要意义。他提到“说书”即宋代的“平话”(评话),即以口语敷演故事,带有动作,重点是说白。说书分大书和小书,宋代盛行说书,平话尤盛行江南。木心甚至还举出古代许多说书大师,如孔云霄、韩圭湖等,最有名的如柳敬亭。他还提到1949年之后的说书集团,如苏州的光裕社、上海的润裕社。木心把它们与“五四”新文学时期的创造社、新月派和语丝社相比,认为前者是民间文化的中心,对说书人可以作教育鉴定,后者是临时性同人杂志,并非教育人才、指导群伦的文学机构。
在木心看来,作为说书人底本的评话本,是中国民间的历史教科书,也是中国文化起源、流传和变化的重要因素之一。在古代,靠着说书人的口传,使得大多数人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历史概念。不过,可惜的是,民间社会最终消失,只保留下文人士大夫这条路。木心甚至绘声绘色地描写出自己亲身经历的热闹的说书场景:
这些书,民间影响极大,我是听家里大人们讲的。春夏秋冬,每天晚上听。这间屋里在讲薛仁贵大战盖苏文,那间房里在讲杨宗保临阵私配穆桂英,走廊一角正在讲岳飞出世,水漫汤阴县,再加上看京剧,全是这些传奇故事。我清晰记得上辈都为英雄们忧的忧,喜的喜……[1]429
从他的叙述中,不难看出民间说书对其影响之深刻,也让人们重新意识到说书对于传承与发展民间文化的重要意义及其在民间社会的重要地位和价值。木心也提到,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古典小说对民间社会中的说书场景却很少提及。《红楼梦》对于说书一点儿没有提及,《老残游记》《儒林外史》也只是稍稍点到,浅尝辄止。即使以鲁迅、周作人为代表的反封建、反礼教的新文化运动健将,也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木心给予说书以前所未有的重视,这是郑振铎、刘大杰等其他文学史家所容易忽视的,让我们看到现今学界对民间说书价值的发掘还不够深入,还有待继续研究和开拓。
其次,木心认为,与西方的史诗相比,中国以古代讲史平话为代表的英雄故事,并不能称得上是一流的历史小说。这些讲史的感人力量近乎西方的史诗,但中国的英雄传多半是虚构的,过于想入非非,没有处理好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的关系。如《三国演义》把诸葛孔明写成了妖道,严格地讲,不能算“艺术”。这与鲁迅的观点十分相似。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五篇《明之讲史》中说“至于写人,亦颇有失,以致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2]152在木心看来,历史小说不容易写得好,倘若太真实,显得呆板无趣味,如《东周列国志》《两晋演义》;倘若离真实太远,则荒诞无据,如《杨家将》《薛家将》。所以,讲史虽盛极一时,但都是中国文学中的宝塔,并非塔尖。当然,木心心目中最理想的状态是一部历史小说兼具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为一体,即“让历史的还给历史,艺术的还给艺术”。[1]365因此,木心认为《三国演义》是纯粹的艺术,不能以现代小说去要求它,要消除现代人的迷障,但又要隔岸观火,跳过此岸,回到古代。木心认为这是欣赏文学作品的艺术的态度,而艺术的态度是瞬间的、灵感的、认识变化的。
再次,木心把西方小说的观念作为评判中国古典小说的基本标准,认为《西游记》《金瓶梅》是纯粹的艺术创作,是中国文学的塔尖。他认为吴承恩灵感洋溢、幽默丰富,在《西游记》中精彩地刻画了人性。小说中的八十一难关,关关不同;一魔一妖,一怪一仙,都各有性格,活龙活现;唐僧和三徒弟,性格毕现,绝不混淆。其中任何一段都是绝好的短篇小说。木心称小说前七回孙悟空大闹天宫写得最好,他还把孙悟空称为“猴子中的拜伦”——中国文学中的异端。中国文学史中从来没有一个像孙悟空这样的皮大王,一个捣乱捣上天的角色,也没有哪个作家如此大规模地以动物拟人、以人拟动物,即使放在那些世界范围内写神话、童话的作家面前,也值得佩服。
关于《西游记》的版本问题,木心也有独到而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吴承恩本《西游记》是在杨致和本《西游记传》的基础上修改放大而来的。这种观点与鲁迅、赵景深关于《西游记》版本的认识相一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七篇《明之神魔》(中)说:
又有一百回本《西游记》,盖出于四十一回本《西游记传》之后,而今特盛行,且以为元初道士丘处机作。
…………
《西游记》全书次第,与杨志和作四十一回本殆相等。……惟杨志和本虽大体已立,而文词荒率,仅能成书;吴则通才,敏慧淹雅,其所取材,颇极广泛。[8]
赵景深在《中国文学小史》中也说:
在杨本仅“遂去灭法国”五字,在吴本却变成两回,几有万字,在杨本仅“过了八百里荆棘山”八字,在吴本却变成半回,也有三四百字;在杨本叙破牛魔王不过百余字,在吴本却变成奇恣雄伟的洋洋万余言。——可见吴本是比杨本要扩大到数十百倍。[9]
赵景深在鲁迅研究的基础上,更加仔细地分析了吴本《西游记》与杨本篇幅和内容的差异,认为吴本比杨本扩大了数十百倍。不过,胡适和郑振铎等文学史家却认为,杨致和本《西游记传》是从吴承恩本删减而来的。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一文中就提到,朱鼎臣本和杨致和本似从吴本删节而来,《永乐大典》本则为吴本之所本。[10]
木心的高超之处在于,进一步肯定了吴承恩对杨致和本《西游记传》的改编,并进行深刻阐发。他认为,所谓天才者,就是有资格挪用别人的东西,而且令人拜倒。世界上只有这种“强盗”是高贵的、光荣的,莎士比亚就是其中的“强盗王”,吴承恩当然也毫不逊色。他在杨致和本的骨架上大展身手,找到自己,找到风格。木心由此想象吴承恩的性情,必是个快乐、有趣的人,是“孙悟空的模特儿”。这恰好印证了木心所谓的“风格是一种宿命”的观点。[1]430他还提到,在文笔方面,吴承恩的天才和功力远超《东游记》《南游记》《北游记》的作者。《西游记》的命运可谓极好,其流行之广很像现代的畅销书,但一些续书,如《后西游记》《西游补》等等,都是狗尾续貂。那些关于《西游记》的解释,如讲道、谈禅、劝学,把小说肢解为道书、佛经、《大学》、《中庸》,更是无稽之谈。这些都表现出木心对《西游记》艺术性的精准把握。
木心认为《金瓶梅》是一部近乎现代的“心理小说”。这部小说描写的女性个个特点鲜明,语言处处生动,在文学上有特定的价值。小说中的女性充满心机、谋略,细节中的你死我活,半句不让,阴森可怕。这种“方法论”影响到了曹雪芹。曹雪芹的“意淫”还是唯美的、诗的、慢条斯理的、回肠荡气的;而《金瓶梅》则是“肉淫”,是变态的、聃溺的、不顾死活的。因此,《红楼梦》是浪漫的,《金瓶梅》是现代的。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称《金瓶梅》既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又是一部最符合现代意义的小说,特别擅长展现市井人情以及平常人的心理,其语言之精练,其行文措语之雄悍横恣都是罕见的。[11]在木心看来,《金瓶梅》由于太像性书,容易被误解,其最污秽的地方,即使是英国文学大师劳伦斯(D.H.Laurence)也无法与之相比,几乎成为“性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438。《红楼梦》明朗,《金瓶梅》幽暗,正如托尔斯泰明朗、陀思妥耶夫斯基幽暗一样。不过,木心也指出《金瓶梅》的不足之处在于,作者缺乏艺术家的自觉,这一点无法与曹雪芹相媲美。
最后,木心还特别注意透过中西小说的比较视角,来突出中国古典小说的内涵。他把明代短篇小说集《三言二拍》《醉醒石》《石点头》等作品,与莫泊桑、契诃夫和欧·亨利的现代短篇小说进行对比。由此,木心指出:虽然中国古代短篇小说很有趣味,叙述宛转生动,保留下了诸多民间当时的风俗习惯、生活情调和活气,但其缺点在于,描写的对象大多是才子佳人,呈现出概念化特征。一面是淫秽描写,一面作道德教训,不懂得剪接,事事从头说起,缺乏写作技巧和结构,且文字落入俗套,口语也不够生动。即使文笔极好、十分精练、留有余韵的明代笔记小说,也存在渲染色情和宣扬名教的弊端。木心由此推而广之,认为许多中国古代小说都存在类似倾向,即宣扬忠孝节义,把道德标准提到人性的可能之外,继而扼杀了文学的生命力,作品也提升不到纯粹性、世界性的艺术高度,对于平民百姓的教育也极为不利。显然,木心对于中国古代短篇小说提出的这些观点,背后都是以西方现代小说为参照的,深受西方小说观念的影响。
总而言之,熟悉西方文化和西方小说观念的木心,在论述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时,更多的是从西方小说观念出发,提出自己独到的观点。不同于其他文学史家,木心尤其重视“说书”这一民间社会特有的文化形式,其底本评书则成为中国民间的历史教科书。他认为《西游记》《金瓶梅》是纯粹的艺术,它们都刻画出丰富而深刻的人性,颇具现代性。
三、对《红楼梦》的全新解读
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十分重视曹雪芹与《红楼梦》,他特意把第三十八讲的标题命名为“十八世纪中国文学与曹雪芹”,以突出曹雪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这是对郑振铎《文学大纲》的超越,其背后显然有自己的深刻思考。《红楼梦》作为中国古典小说的代表性著作,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对其进行了多视角的细致解读,颇具个性化色彩和创新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提出以“时、空、名、景”为核心的阅读方法。木心认为,阅读《红楼梦》,不能只看故事、排场和细故,而要从空中鸟瞰,弄清楚小说的家谱、人物、关系这三大纲,这样才能胜券在握。这里的“时”是指小说的朝代选得奇妙、高超。曹雪芹虽入旗,但仍是汉文化的继承者,他以汉人的眼光将时代虚拟,甚至以唐宋之气表现汉文化。因此,整个荣国府、宁国府、大观园及其庭院和生活道具等等,尽显纯粹的汉文化,有唐宋遗风,看不到满族人的习俗,给人带来十足的美感。所谓“空”是指地点选得好。曹雪芹把地点放在首善之区的京城,四季变化,但又不明写南京,避免流俗。时间空间的安排,堪称大手笔,是对其他古代小说的超越。小说看似没有时间、空间,但达到的效果却是“有时间处就有《红楼梦》,有空间处就有《红楼梦》”,[1]498-499睥睨千古。“名”是指小说中的人物姓名既有关联,又无关联,包含着巨大的潜台词。曹雪芹先取贾(假)姓,另外如秦可卿(情可亲)、秦钟(情种);元春入宫,迎春、探春、惜春则在家;贾政,官也;王熙凤,要弄权称霸的;黛玉,是忧郁的;宝钗,是实用的;妙玉,出家了;尤三姐,女中尤物也;柳湘莲,浪子也。[1]499在木心看来,曹雪芹为小说人物取名字的技巧,连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福楼拜、司汤达也会甘拜下风。“景”是指场景布置。宁国府、荣国府是旧建筑,大观园是新建筑。曹雪芹别具匠心借元春探亲而建造大观园,否则众多人物挤在宁荣两府的小空间内,无法下笔。木心准确地勾勒出曹雪芹的巧妙构思,正如他所谓的阅读《红楼梦》的难处在于,在观点上必须要高于作者,这样方能了悟此书巨大的潜台词。
第二,用“虚构说”替代“自传说”。木心不同意以胡适为代表的学者提出的曹雪芹自传说。[12]他认为《红楼梦》有自传性,但又自觉地摆脱了自传的局限。在木心看来,《红楼梦》纯是虚构的,背景则来自曹雪芹的记忆。作为艺术家的曹雪芹,具有灵智的反刍功能,凭借记忆再度感受从前的印象。这种超时空的感受是艺术家的无穷灵感。同时,小说中的人物是生活的幻化。唯美主义的曹雪芹写出幻化的、超现实的美男美女,内心有一种占有感,即所谓“意淫”,但他又发乎情,止于艺术,这正是曹雪芹的伟大之处。另外,曹雪芹才大于文,具有深厚的“自我背景”,他精于绘画、书法、工艺、烹调、医理,《红楼梦》仅仅是其才能外现的一部分,实则深不可测,涵藏无穷。木心认为,这正如西方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三杰”的才智能量,远远不是他们表现出来的这点东西。又如肖邦是杰出的演员;梅里美能做极好吃的点心;舒伯特会在琴上即兴画朋友的肖像;安徒生善跳芭蕾,剪纸艺术也一流,等等。曹雪芹可谓这方面的典范。
第三,从中西方比较的视角出发,认为曹雪芹具有艺术家的自觉,《红楼梦》的艺术原理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相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木心认为,曹雪芹的伟大分为两极:一是细节伟大,玲珑剔透,比法国小说家描写的还要精细;二是整体控制得伟大,绝对冷酷,不宠人物,一点儿也不可怜书中人,始终坚持反功利,反世俗。因此,他觉得曹雪芹虽然不知道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但其艺术的自觉程度与后者相比,毫不逊色。不过,木心也指出曹雪芹仍然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其艺术的自觉毕竟是有限的。其宇宙观是释、道、色、空,他的叛逆还是反孔孟,还缺乏悲观哲学、自由意志的概念。木心由此还形象地探讨了宗教和艺术的关系。他认为宗教不在乎现实世界,而艺术却要面对这个世界。
宗教是面值很大的空头支票,艺术是现款,而且不能有一张假钞。宗教说大话不害臊,艺术家动不动脸红,凡是宗教家大言不惭的话,艺术家打死也不肯说,宗教说了不算数,艺术是要算数的,否则就不是艺术。[1]432
在木心看来,与形而上的宗教相比,艺术是形而下的,因此,艺术家在处理艺术的时候,显得更加丰富多样,也更加谨慎。
总之,木心结合自己的创作实践,对《红楼梦》进行了多视角解读,很有新意。他指出阅读小说时应该注意“时、空、名、景”这四个要素;反对自传说,主张虚构说,提出曹雪芹具有灵智的反刍功能,其艺术原理能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相媲美。这些都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之上,表现出木心对古典小说的熟稔。同时,木心认为评论家要以艺术的眼光对待《红楼梦》,反对曲解小说而成为穿凿附会的好事家。
实际上,从木心对《红楼梦》的解读中也可以看到他自身的影子。他所评判曹雪芹的“无政府主义者”“艺术至上者”“对自己的天才,有足够的自信”“早就立定志向,为艺术而殉道”等等,完全也是木心自身的标签。木心甚至说“曹雪芹应该有个弟弟,来纽约,租一间‘自己的房间’,好好写”,[1]504他自己实际上正是这样做的,颇值得深思。
四、结语
木心的《文学回忆录》是一部非常具有个性化色彩的世界文学史著作,是对世界文学的真知灼见,其中关于中国文学的论述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他关于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彩介绍,直到今天仍有巨大的意义。就有关古典小说的论述本身来讲,木心在《文学回忆录》中参考了郑振铎的《文学大纲》,但又有所超越。他没有刻意强调中国古典小说的分期,同时,明显突出曹雪芹在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在木心看来,唐前小说只能算作中国小说的萌芽,唐传奇注重小说结构和写作技巧,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短篇小说,在一定程度上很好地回答了鲁迅提出的“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一学术命题。不同于郑振铎、刘大杰等文学史家,对于白话小说,木心特别关注民间社会的“说书”这种独特的文化形式,认为它是传承和发展民间文化的重要纽带,说书人的底本——评话则成中国民间的历史教科书。熟谙西方文化和小说观念的木心,常常用西方现代小说的标准来评判中国通俗小说,把《西游记》《金瓶梅》称为纯粹的艺术,视为中国文学的塔尖。对于中国古典小说的“明珠”《红楼梦》,木心更是从阅读方法、小说来源和中西比较等视角,进行了全新解读,为读者打开了新视野,开拓了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