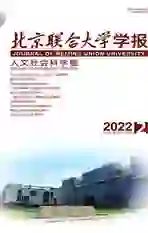14世纪末朝鲜朝文人权近《应制诗》中的中国形象书写
2022-04-27韩梅
韩梅
[摘要] 1396年朝鲜朝文人权近访明,遵照明太祖朱元璋的旨意创作《应制诗》24首,将明王朝塑造为“同文轨”“最好游观”的“上国”,表达出对明朝政治、文化及现实实力的认同,反映出权近一贯的对明认识。该形象主要源于书写主体——朝鲜民族社会集体体验和记忆及作者个人的对华体验与认知。长期奉行封贡制度、实施科举制度使朝鲜民族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认同,作者权近亲明的政治倾向、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以及两次访明的正面体验促使其更为鲜明地书写出这一中国形象。明太祖朱元璋直接促成了该形象的书写,并对满足自身期待的作品做出积极反馈,为推动权近《应制诗》成为朝鲜王朝文学典范并引领中国形象书写发挥了作用。
[关键词]朝鲜朝文学;中国形象;权近;应制诗;朱元璋
[中图分类号]中图分类号I31209[文献标志码]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2-4917(2022)02-0076-07
异国形象是一个民族对异国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是一个民族与对象国家直接或间接接触过程中的体验与相关自我想象相结合的产物[1]。个人如果书写了关于某异国的鲜明形象,且被自己民族广泛接受,该形象就可能作为该民族对该异国的体验与想象沉淀下来,成为一种社会集体想象物,对该民族此后对该异国形象的塑造持续产生影响。从这一角度来说,对于异国的个人体验、认识与想象和所属民族对于该异国的社会集体体验、认知与想象之间存在着一种循环互动关系。不仅如此,“对该异国形象的体验”本身包含着被书写的客体——该异国在这一异国形象形成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如果被书写的客体关注自身在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形象并参与其构建,就可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朝鲜朝初期文人权近1396年出使明朝,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作《应制诗》24首,得到明太祖赞赏,被奉为朝鲜对明外交文学经典,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和发展做出了贡献,对以后的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在有关权近《应制诗》的现有研究中,《从〈应制诗〉看权近的世界观》介绍了权近《应制诗》的创作背景,从朝鲜建国的合理化、中世秩序与事大、历史认识与统治理念三个方面分析了权近的世界观,认为权近在《应制诗》中主张朝鲜建国的历史必然性,强调朝鲜王朝的正统性,也表现出强烈的事大倾向[2]。论文关注的是权近的民族意识,未对集中描写中国的作品做出论述。《权近〈应制诗〉创作及其诗赋外交意义》一文认为权近的《应制诗》表达了朝鲜王朝的政治立场、诉求以及个人的感谢之情,指出这些作品消除了明朝和朝鲜王朝之间因“表笺事件”引发的誤会[3]。但对作品何以能轻易消除两国间的误会,文中未做出充分的解释。《文本沉浮与外交变迁——朝鲜权近〈应制诗〉的写作、刊刻及经典化》一文梳理了权近《应制诗》写作、刊印即成为朝鲜王朝外交文学经典的过程[4]。此外,《论权近的尊周事大思想及其使行诗》[5]《权近的中国使行与汉诗创作》[6]主要以权近第一次使行时创作的《奉使录》为研究对象,认为这些作品表现出强烈的尊华崇明思想和事大的诚心。以上研究对理解权近的《应制诗》的思想意识及传承情况、《奉使录》的内容特点做出了贡献。
不过,权近《应制诗》的主要特点和价值在于作品塑造了朝鲜朝文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并在明太祖朱元璋代表的被书写客体的参与下,成为朝鲜朝文学中中国形象的典范。因此,本文拟以权近《应制诗》为主要研究对象,考察权近《应制诗》中塑造的中国形象特点,结合文学作品、史书中的相关内容,分析朝鲜民族社会集体体验与记忆、作者个人具体体验和认知在其中产生了何种影响,参与其中的明太祖朱元璋发挥了何种作用,以期较为全面、客观地揭示该形象的形成并成为经典的原因。
一、权近及《应制诗》的创作
权近(1352—1409年)是高丽末年到朝鲜朝初期著名的官员、文人、性理学者,字可远、思权,号阳村,谥号文忠。
《阳村先生年谱》记载,1369年,年仅17岁的权近文科及第,直拜春秋馆检阅,30多岁担任成均馆大司成、礼仪判书、宝文阁提学、同知春秋馆事等正三品官职。1389年,权近出使明朝,回国不久被流放。1392年,李成桂建立朝鲜王朝,高丽灭亡。1394年,朝鲜太祖李成桂幸鸡龙山,权近随驾还京,被任命为春秋馆大学士兼成均大司成[7] 9,重返仕途。1396年,明与朝鲜之间发生“表签问题”,朝鲜王朝几番遣使,未能解决问题,权近自请赴明,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年)命题,令其“赋诗若干首”,读后“御制长句四韵诗三篇以赐”,表笺风波告一段落[7] 11。凭这一功劳,权近回国后获封花山君,1398年获赐原从功臣录卷。权近“自检阅至为宰相,常任文翰,历扬馆阁”,“凡经世之文章,事大之表笺,亦皆撰述”[8] 8,引导了朝鲜朝馆阁文学的走向。
权近有《阳村集》《入学图说》《五经浅见录》《三国史略》等著作,在文学、儒学、史学领域皆有建树。他1396年访明时所做的《应制诗》24首作为朝鲜朝外交文学的典范之作,在文学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二、“同文轨”“最好游观”之“上国”:权近《应制诗》中的中国形象
权近的24首《应制诗》分三次写成,第一组的《王京作古》等8首作于1396年9月15日,主题为朝鲜兴废缘由和访明途中见闻;第二组作于同年9月22日,为《始古开辟东夷主》等共10首,主题为朝鲜的历史、地理、邻国形势;第三组作于10月27日,题目为《听高歌于来宾》等6首,主题是楼台观览。在这24首中,仅从题目来看,以中国为题材的作品是第三组的6首,但实际上,第一组8首中,《李氏异居》《出使》《奉朝鲜命至京》《道经西京》《渡鸭绿》《由辽左》《航莱州海》7首作品都用很大篇幅描写中国;第二组的10首诗歌题材虽然是朝鲜的历史、地理,但《新京地理》《大同江》《马韩》3首诗也都写到了中国。因此,在24首《应制诗》中,书写中国的作品合计16首,可见中国即《应制诗》的主要描写对象。
从多篇诗作的内容来看,权近《应制诗》从政治、文化及社会现实几个方面描述了当时的中国,即洪武年间的初期明王朝,“幸今四海同文轨,最好游观上国光” [7] 15 ,基本概括了诗中描写的中国形象特点。
“况今逢圣代,远俗被同仁”[7] 15,在权近的诗歌中,当时中国圣君在位,开启了一代盛世,帝王仁政惠及周边;“圣主龙兴抚万方,远人来贡有梯航”[7] 14,太祖开国,君临天下,安抚四方,感召“远人”跋山涉水前来朝贡;“海国千年遇圣明,我王归附贡丹诚。牧民宠受朝鲜号,作室新开汉邑城”[7] 15,两国在封贡体系内互动良好。这些诗句强调明朝皇帝“代天理物”“安抚四夷”,履行宗主国的权利与义务,施行仁政,惠及周边国家。《应制诗》中还用形象的手法描述明朝的这种“仁政”——“皇风不限华夷界,地理何分彼此疆?任见波涛掀小艇,欣瞻天日照遐荒”[7] 15,穿越国境的“皇风”和照耀偏远地区的“天日”隐喻明王朝的德与仁。“晓雾收开仙仗日,天风吹送御炉香” [7] 15,将明朝皇帝的宫殿描绘为神仙居住的天上,来朝的使臣“自是浮槎便上天”[7] 16,暗喻明朝在政治上的宗主国地位。
权近的《应制诗》还以“同文轨”强调明与朝鲜半岛文化相通,关系密切。“箕子遗墟地自平,大江西折抱孤城”[7] 16,《大同江》一诗首句便提及“箕子遗墟”,引用《史记》中武王封箕子于朝鲜的记录,表示朝鲜半岛是箕子分封之地。《道经西京》也以“千载箕封枕海门,八条遗俗至今存”开头[7] 14,引用平壤曾为“箕子朝鲜”国都之说,强调数千年前箕子传入“犯禁八条”等中国典章制度,已经化为朝鲜半岛文化的一部分。诗中特意指明“幸今四海同文轨”[7] 15,明确表示与周边文化相通的是“今”之明王朝,而非昔之元王国,表现出对汉族政权的文化认同。
“最好游观上国光”[7] 15,《应制诗》将中国描写为适合游观之地,并通过第三组诗歌,集中描绘出其繁华、富庶的景象。第三组诗歌以1394年明朝首都金陵(即今南京)新建的来宾楼、重译楼、南市楼、北市楼、醉仙楼、鹤鸣楼为题,多角度描写酒楼的场景及街市的景象,描绘出明初一派升平的社会现实。
“万国来宾会玉京,高楼为向路傍营”[7] 16,金陵街道上行走着各国来宾,道路两侧高楼耸立。“百尺高楼压市廛,游人登眺兴悠然。长街万货纷交错,华屋千甍远接连”[7] 17,寥寥数语,勾勒出金陵作为国际都市的热闹与繁华。在酒楼内,“美酒不辞成酩酊,珍羞且得饱芳鲜”[7] 17,“屡引金觞看妙舞,更闻瑶瑟赋新篇”[7] 17,“风动佩环珠玉碎,香飘舞袖绮罗轻”[7] 16,“笑语诙谐诚可喜,腰肢娈转更堪惊”[7] 17,不仅有美酒佳肴,还有精彩的歌舞、滑稽表演。饮食美味,器具华贵,表演精湛,衣饰华美,处处显示出明朝人生活的富足与精致。6首诗以明初首都金陵的酒楼、街市为中心,描绘出一幅国泰民安、歌舞升平的盛世图景。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将《应制诗》中的中国形象归纳为“上国”“同文轨”“最好游观”的繁华之地三个特点。
但是,这些《应制诗》的写作背景极为特殊,两国之间的表笺问题尚未解决,明太祖朱元璋是诗歌的命题者,也是阅读者,这有可能使作者权近感到压力,书写中国时有意迎合。为此,本文将《应制诗》中的中国形象与1389年作者作为高丽朝使臣第一次访明时所做的《奉使录》进行简单的比较。
《奉使录》共收录诗歌130多首,其中120多首创作于中国境内。由于总数多,《奉使录》中描写明太祖和明王朝的诗句比《应制诗》更多,表述极为相似。“今逢天下泰,帝德隆唐虞”[7] 61,称明朝为盛世,太祖为圣君;“迩遐同一体,圣德大如天”[7] 63,赞颂太祖德政泽被四方;“金陵朝万国,钟阜镇中邦”泛写周边国家使节来朝,“幽并丑虏降”[7] 71则以胡人举家降明的事例证实明朝的感召力[7] 63。《奉使录》中“轩墀仙仗集,宫殿瑞云低”[7] 68等诗句也将皇帝的宫殿描绘成了天上仙境,“谁知朝宗意,与水俱沛然”[7] 64以河流为喻,表明了尊明的决心。
《奉使录》中也多次用“同文”“同文轨”,强调两国文化的共通性。如“奉使远游胡不乐,如今天下正同文”[7] 60,“幸今四域同文轨,及壮何辞万里游”[7] 70,“如今”“幸今”同样表达出对明王朝的文化认同。“夷语居民杂,华风外国传。交通无彼此,四海一家年”[7] 60,描写“华风”对周边国家产生影响,形成“四海一家”般的文化共同体。
关于明朝社会现实,《奉使录》中以“都城形胜壮,市巷物华繁”[7] 63“市廛连郭外,墙屋接河边”[7] 63描绘了都市商品经济的繁荣,“闾井一村桑欲落,田原千亩稻初收”[7] 70勾勒出乡村的丰收景象,“转舰机轮壮,开河水驿通”[7] 68描写了交通的发达。很显然,《奉使录》中對明朝现实的描写比《应制诗》中更为多样。尽管如此,权近感叹“城池之大,宫室之壮,甲兵舟车之富,人物财赋之繁”,而此行“所见既广,而笔力有不逮,不能尽其详,姑举其略尔”,“以海外蕞尔之儒,得逢天下同文之日,御使命而朝帝庭,因以广其观览,以偿平日远游之志,豈不幸哉”[7] 59。
通过以上考察,可见权近第一次访明所作的《奉使录》中塑造的中国形象与《应制诗》一致。实际上,权近在《应制诗》后所作作品中也表现出相同的对明认识。“皇明帝天下四方,海内外靡不臣附”[7] 203,表达了对明朝宗主国地位的认同。“箕子之所受封,孔子之所欲居。礼俗文物,侔拟中夏”[7] 188,用“箕子东来说”和《论语》中“子欲居九夷”的说法,强调两国文化密切的关联性和共通性。
如上所述,权近的《应制诗》将中国描写为“四方来朝”的“上国”“同文轨”的文化共同体、值得“游观”的富庶国家,表达出对明朝的政治、文化和现实实力的肯定。而且通过对其《应制诗》写作前、后作品的考察,可以发现权近一直将中国描绘为文化相通、繁荣富强的宗主国,表现出对中国的政治、文化及经济实力的认同,《应制诗》中的中国形象反映出作者这种一贯的对华认识。
三、制度性记忆与体验和个人体验与认识:权近《应制诗》中中国形象的形成
异国形象是作者及其所属集体、民族的体验、记忆及想象的产物。作为本民族的一员,作者塑造的异国形象一般源于本民族的社会集体记忆及想象。此外,作者也拥有很大的创作自由,新颖而丰富的个人直接体验往往成为新异国形象的源泉。权近《应制诗》中的中国形象形成过程中,既有朝鲜民族对华相关集体记忆与想象的作用,也有作者个人体验与对华认识的影响。具体而言,可以从对民族文化与心理产生重大影响的封贡制度、科举制度和权近的个人经历、政治倾向等方面解释其形成原因。
在朝鲜半岛古典文学中,中国“上国”“天朝”的形象很早已经出现,它来源于东亚历史上曾经长期存在的封贡制度,其形成是基于孟子的“事大保国”思想——“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畏天者保其国”[9] 13。中国与朝鲜半岛山水相连,很早就开始交往。在“事大”思想的影响下,经过一段时期的探索,到唐朝中叶,双方建立起较为稳定的封贡关系。此后在大多数时间,双方维持了这种关系。因此,描述中国宗主国地位的“天朝”“上国”等表述频频出现在朝鲜半岛的文学作品中。
现存新罗、高丽的诗文多以“上国”或者“天朝”尊称唐、宋、元等王朝。新罗文人崔致远(856—?年)在唐留学期间表示“上国羇栖久,多惭万里人” [10] 151。对于蒙古民族建立的元朝,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后,高丽文人也开始尊称为“上国”“天朝”,这在李奎报(1168—1241年)、李承休(1224—1300年)、李谷(1298—1351年)等人的作品中得到确认[11] 147-149。明朝建立后,很快和高丽建立了封贡关系。1388年,高丽亲元派派军攻打辽东,诸将上表反对,提出三条理由,即“以小事大,保国之道”,“我国家统三以来,事大以勤”,高丽已“服事大明”。李成桂(1335—1408年)顺应军心回军,趁机掌握了高丽的实权[12] 22。这一“威化岛回军”事件表明事大思想、封贡制度在高丽已经深入人心。1392年李成桂取代高丽建立朝鲜王朝,将对明“事大”视为基本外交原则,登基后第二天便遣使向明请封,可见中国是“天朝”“上国”的观念自朝鲜朝开国便是基本国家理念之一。
从作者个人角度而言,权近亲明的政治倾向、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访明中的正面体验促使其积极塑造明王朝的“上国”形象。
1368年,明朝建立,高丽朝廷内部形成亲元、亲明两大政治派别,权近站在亲明的阵营,主张“事大亲明”。1374年,高丽恭愍王(1330—1374年)暴毙,北元朝廷遣使到高丽颁赦,试图恢复两国关系,权近等亲明派上书“请毋纳元使”。1388年,亲元派核心人物崔莹(1316—1388年)当国,“有抗中国之志”,“凡申朝廷之事,不用事大旧例,欲以草檄移之”。权近“面斥其非,竟不用草檄” [8] 8,说明他力主对明事大,且极为重视对明外交文书遵守事大礼仪。
不仅如此,权近还通过两次出访积累了丰富的对明体验。1389年,权近以高丽使臣的身份首次出使明朝,加深了对明朝的好感。例如,听说朱元璋前往颍国公傅友德府第问病,他感叹皇帝仁德[7] 69。他也听到“北胡”左丞胜吉携家眷降明[7] 71,感受到明朝的感召力。这些个人体验加深了他对明的政治认同,促使他在诗歌中突出了“上国”的形象。
在文化方面,两国的交流比封贡关系的建立更早。以“同文”字面上所指的汉字为例,至少在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公元前87年)设立汉四郡起,朝鲜半岛已经开始使用汉字。此后,朝鲜半岛积极接受了汉字及以其为载体的汉文学、儒释道等哲学思想、各种典章制度,等等。
新罗时期(公元前57年—935年)起,很多人以游学等方式学习中国文化,但这些多是个人行为,而真正促使整个民族关注中国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是科举制度的实施。公元788年,新罗设立国学和读书三品科制度,规定“读《春秋》《左氏传》、若《礼记》、若《文选》而能通其义,兼明《论语》《孝经》者为上,读《曲礼》《论语》《孝经》者为中,读《曲礼》《孝经》者为下。若博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书者,超擢用之”[13] 3-4。读书三品制以培养儒学素养和汉文学写作能力为目标,引导年轻子弟自幼学习中国文化。958年,高丽设立了完善的科举制度[14] 7,将选拔文官的考试分为制述和明经两科,制述科考察诗、赋等汉文学写作能力,明经科考察对儒家五经的理解。1392年朝鲜朝开国当天便对科举制度做出明确规定,经学、文学仍然为考试的主要内容。
科举制度作为唯一正式的官员选拔制度,在朝鲜半岛沿用了一千多年,是所有人踏入仕途的必经之路。它的实施促进了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的全面吸收,在其引导和激励下,文人们将中国古典文学名作和五经四书封为圭臬,在学习过程中逐渐达到了对中国文化的認同。高丽后期文人李齐贤(1287—1367年)就认为,“天下同文,家有程朱之书,人知性理之学”[15] 600。就这样,科举制度造就了朝鲜民族对中国的共同认识——“同文轨”的社会集体体验与记忆。
就作者个人因素而言,权近出身诗书之家,自幼修习中国文化,17岁考入国学——成均馆,此后,他在各级科举考试中屡次以第二、三名高中,意味着他对经学和汉文学极为精通。其著作《入学图说》代表高丽性理学的最高水平,《五经浅见录》对五经的“体用”提出了独特的见解。这两部儒学著作是朝鲜民族最早的儒学研究成果,开启了朝鲜时代的经学研究[16] 112-125。他在中国文化方面的造诣自然影响到其思想、政治倾向,如程朱理学中正统的华夷思想使他倾向于严格区分“华”与“夷”,在文化上认同汉族政权,“幸今四海同文轨”[7] 15即这种意识的表现。
在权近创作《应制诗》之前,描绘中国都市繁华的作品较为少见。此前书写中国的崔致远等新罗文人前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求学、应试,博取功名后荣归故国,高丽文人李齐贤、李承休、李谷等人的中国体验则多与公务有关,很少有机会深入市井游览或高坐酒楼饮酒赏乐,描写相关体验的作品极为罕见。
权近《应制诗》中反映的酒楼体验得益于明太祖为他提供了特别的机会——“勑有司,备酒馔具妓乐,使之游观三日,亦命赋诗以进”[8] 8。明朝官方安排“游观”,让权近直接体验到明朝的宴乐游乐,感受到明朝社会的太平安逸。基于此,权近在《应制诗》中细致描摹了酒楼、街市的场景,塑造了繁华富裕的中国形象。
综上所述,权近《应制诗》中的中国形象基本源于朝鲜民族长期的对华体验与记忆,权近个人的直接体验和认识使中国形象更加鲜明而丰富。“上国”形象基本源于朝鲜民族对封贡制度的社会集体体验与记忆,作者亲明的政治倾向使这一点更为突出;“同文轨”的形象主要源于朝鲜半岛长期实施的科举制度引导人们积极学习汉文学和儒学经典,作者在中国文化方面造诣深厚,这些都促使其对明王朝具有强烈的文化认同;值得“游观”的繁华形象很大程度上源于作者访问明朝的个人体验,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为此后塑造朝鲜文学中的中国形象提供了新的维度。
四、期待與认可:朱元璋与权近《应制诗》的“视域融合”
在权近《应制诗》的写作与经典化过程中,明太祖朱元璋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他极为重视文学的礼仪功能,认为“以小事大,至敬之礼,莫贵乎修辞”。因此,他极为关注外交诗文,认为朝鲜朝的表笺“文辞之间,轻薄肆侮”,文书中“引用纣事,尤为无礼”[17] 4,致使权近入明,并“命题赋诗二十四篇”[18] 8,促成了权近《应制诗》的写作。如前所述,从指定的题目来看,朱元璋有意从《应制诗》中了解对方对明朝的认识,而且他对此有自己的期待。
从历史记录来看,明太祖认为明朝皇帝“君位中原,抚诸夷于八极,相安于彼此”[19] 86,希望与周边国家建立传统的封贡体系,明朝宗主国的地位得到认可。为此,洪武元年,他向四方遣使,告知明王朝的建立。在给高丽国王的书信中,他声称,“昔我中国之君,与高丽壤地相接,其王或臣或宾,盖慕中国之风,为安生灵而已。天监其德,岂不永王高丽也哉?朕虽德不及中国之先哲王,使四夷怀之,然不可不使天下周知”[20] 49,希望高丽遵循传统,奉明正朔。
在对外交涉时,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重视文化的作用,强调明朝的文化正统性。他依据程朱理学基于民族的华夷思想,指出“元非我类”,元朝的统治导致“华夷扰乱”,明王朝“北逐胡君,肃清华夏”,匡正了华夷秩序,恢复了汉文化,因而更为正统。他还指出朝鲜半岛历代王朝“慕中国之风” [21] 22。这都说明,他意识到了文化的重要性。
明太祖也有意对周边展示国力,增进其对明的认可。他以“海内太平,思欲与民同乐”为由,“命工部作十楼于江东诸门之外,令民设酒肆其间,以接四方宾旅。其楼有鹤鸣、醉仙、讴歌、鼓腹、来宾、重译等名。既而又增作五楼,至是皆成。”[22] 2这就是著名的“金陵十六楼”,它们建在金陵街市的繁华之地,建筑高大宽敞,内部设有官妓的伎乐表演,但并不售卖官酿。这些酒楼专门用来招待官员、富商以及因公事往来者,来宾、重译二楼主要接待外国使节。因此,很多人认为,明太祖命令修建这些酒楼的目的不仅仅是促进经济发展,还有鼓吹升平、怀柔四方的意图[23] 64-65。他数次“诏赐文武百官钞,命宴于醉仙楼”[22] 2。1396年他特意下旨让权近等使臣游观三日,且在酒楼赐宴,其目的显然是让其通过亲身体验感受明朝的富庶与太平,认同明朝的实力,也希望通过这种特殊待遇增进其对明的好感,进一步坚定其尊明的决心。
从上述言行来看,明太祖朱元璋期待周边国家对明朝宗主国的地位、正统汉文化继承者的身份由衷予以认同,也希望自己治下的明王朝以国泰民安的现实得到认可。这与上述权近《应制诗》中描绘的“上国”“同文轨”“最好游观”等中国形象基本一致,意味着作品中表现出的对华认识基本符合朱元璋的“期待视野”。就中国形象而言,权近《应制诗》与朱元璋实现了“视域融合”。
因此,读过诗作后,“帝嘉赏之,令从仕文渊阁,且赐御制。”[18]7在朱元璋的御制诗中,《使经辽左》一诗——“入境闻耕满野讴,罢兵耨种几春秋? 楼悬边铎生铜绿,堠集烟薪化土丘。驿吏喜迎安远至,驲夫忻送稳长游。际天极地中华界,禾黍盈畴岁岁收”[18]5,借外国使臣的视角描写了中国社会的太平安乐、中国人的周到热情,将“际天极地中华界”描绘成了一个理想世界。换言之,朱元璋在诗中描绘了自己希望展示的明朝形象。《鸭绿江》一诗则吟咏“逋逃不纳千年祚,礼义咸修百世功”,表达了以礼义维护两国长久和平的愿望。朱元璋让权近回国将勑慰诏书、宣谕圣旨、御制诗转交朝鲜国王,在圣旨中赞扬权近“老实”,称国王“至诚”,不再追究表笺问题[18]5,对权近《应制诗》中的对华认识和态度表示认可。
综上所述,为了将朝鲜半岛纳入以明朝为中心的“天朝礼治体系”,明太祖关注朝鲜朝文学中对华形象的书写和对华态度的表述,通过安排《应制诗》写作、根据自身期待视野作出反馈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朝鲜半岛对理想中国形象的书写。
五、结语
14世纪末,明与朝鲜王朝立国不久,相互间的认识尚未完全定型。明太祖朱元璋希望以“礼”规范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也很重视文学的礼仪作用。因此,他非常重视周边国家文学中的明朝形象以及对方在文学中表现出的对明态度。出使明朝的朝鲜朝文人权近遵其旨意作《应制诗》24首,将明王朝塑造为“同文轨”“最好游观”的“上国”,表达出对明的文化、实力及政治上的认同,反映出其一贯的对明认识。
从社会集体记忆与想象的角度来看,该形象的形成与朝鲜半岛很早加入封贡体系、实施科举制度有关,这些制度在朝鲜半岛长期施行,促使朝鲜民族自然而然地实现了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认同。此外,作者权近亲明的政治倾向、深厚的中国文化素养以及两次访明的正面体验进一步加深了其对明的好感,增加了其对明朝繁荣昌盛的直接体验,促使其更为鲜明地书写出这种中国形象。
值得注意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权近《应制诗》写作及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作用。他认为文学应该表达“礼”,希望通过文学了解明王朝的域外形象,促成了《应制诗》的写作。权近所作的《应制诗》基本满足了朱元璋的“期待视野”——政治上得到充分的尊重,文化上得到由衷的认同,自己治下的明王朝国泰民安、歌舞升平。明太祖赠其御制诗,明确表达肯定的态度,对朝鲜王朝奉其为文学经典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作为最高规格的诗赋外交成果,权近《应制诗》与朱元璋的御制诗被奉为“天下万世之所共宝” [24] 63,在朝鲜朝的官方和民间都受到重视。诗歌全文被收录在《朝鲜王朝实录》之中,并被制作成了单行本,成为文人必读的文本。朝鲜国王和文人将其视为外交文学的典范,多次向访朝的明使展示,并得到高度评价[25] 33。为满足两国交流的需要,国王还特意下令刊印[26] 75。官方的重视进一步提高了诗集在朝鲜朝文人中的影响。后代文人或次韵[27] 166,或引用[28] 318,直到19世纪中期,仍有文人表示,“自学语习文字便知有阳村文忠公应制集,及长,益端拜庄诵。”[29] 477作品中书写的中国形象在此后的朝鲜朝文学中得以继承和发扬。
总而言之,1396年朝鲜朝文人权近《应制诗》将中国描写为“同文轨”“最好游观”的“上国”,其形象特点主要源于主体——朝鲜民族的社会集体体验、记忆以及作者个人的对华正面体验和认知,而客体——明朝的太祖朱元璋促成了该形象的书写,并做出了积极的反馈,对推动该作品在朝鲜朝的经典化并进而引领正面的中国形象书写发挥了作用。
[参考文献]
[1]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郑载喆:《从应制诗看權近的世界观》,《汉文学论集》1990年第8期。
[3]何修身:《权近〈应制诗〉创作及其诗赋外交意义》,《长春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11期。
[4]陈彝秋:《文本沉浮与外交变迁——朝鲜权近〈应制诗〉的写作、刊刻及经典化》,《外国文学评论》2018年第3期。
[5]李岩:《论权近的尊周事大思想及其使行诗》,《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5期。
[6]尹允镇、张宝双:《权近的中国使行与汉诗创作》,《东疆学刊》2020年第2期。
[7]权近:《阳村集》,《韩国文集丛刊》第7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版。
[8]《朝鲜太宗实录》第17卷,(韩国)太白山史库本。
[9]孟轲:《孟子》,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10]崔致远:《长安旅舍,与于慎微长官接邻》,《孤云先生文集》第1卷,《韩国文集丛刊》第1集,(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版。
[11]舒健、张建松:《韩国现存元史相关文献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12]《朝鲜太祖实录》第1卷,太白山史库本。
[13]金富轼:《三国史记》第10卷,《新罗本纪》第10卷,(韩国)玉山书院本。
[14]郑麟趾等:《高丽史》第44卷,(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
[15]李齐贤:《更张治道》,《益斋乱稿》第9卷下,《韩国文集丛刊》第2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1988年版。
[16]尹丝淳著,邢丽菊、唐艳译:《韩国儒学史——韩国儒学的特殊性》,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
[17]《朝鲜太祖实录》第9卷,(韩国)太白山史库本。
[18]《朝鲜太祖实录》第11卷,(韩国)太白山史库本。
[19]郑麟趾等:《高丽史》第84卷,(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
[20]郑麟趾等:《高丽史》第23卷,(韩国)首尔大学奎章阁藏本。
[21]《明太祖高皇帝实录》第37卷,(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红格抄本。
[22]《明太祖高皇帝实录》第234卷,(原)北平图书馆所藏红格抄本。
[23]李舜华、陈惠卿:《明初教坊制度考略》,《文化遗产》2014年第4期。
[24]权擥:《应制诗跋》,徐居正编:《东文选》第103卷,(韩国)庆熙出版社影印本1966年版。
[25]《朝鲜世祖实录》第19卷,(韩国)太白山史库本。
[26]《朝鲜中宗实录》第90卷,(韩国)太白山史库本。
[27]李东标:《懒隐先生续集》第1卷,《韩国文集丛刊续》第47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7年版。
[28]高傅川:《月峰集》第1卷,《韩国文集丛刊续》第19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6年版。
[29]洪翰周:《海翁文稿》第3卷,《韩国文集丛刊》第306册,(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2003年版。
The Image of China in Korean Classical Literati Kwon
Geun’s Ordered Poems in Late 14th Century
HAN Mei
(School of Asian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In 1396, Kwon Geun, a literati of the Joseon Dynasty (a historical dynasty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392-1910), was sent to China in the Ming Dynasty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and wrote 24 Ordered Poems (eulogistic poems written following the order of the emperor)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er of Zhu Yuanzhang, the founding Emperor Hongwu of the Ming Dynasty. In his poems, the Ming Dynasty was depicted as a unified and powerful state, reflecting his recognition towards national power and consistent understanding of China. The image is mainly derived from the collective experience and memory of the Korean society, which is the writing subject, and the author’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cognition of China. The long-term adherence to the tribute system and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 system enabled the Korean nation to naturally realize the identification of Chinese politics and culture. The image of China in Kwon Geun’s poems indicates his two positive visits to China, pro-Ming political inclination and profound Chinese cultural literacy. Moreover, the positive feedbacks of Hongwu Emperor directly contributed to the writing of the ordered poems, which played a role in promoting Kwon Geun’s Ordered Poems to become a model of Korean classical literature and the positive image of China.
Key words:Korean classical literature; image of China; Kwon Geun; Ordered Poems; Emperor Zhu Yuanzhang
(责任编辑 刘永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