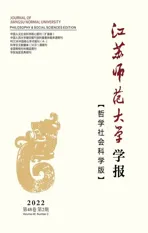山西传统剧场遗存现状调研报告
2022-03-31王潞伟张浩然
王潞伟 张浩然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太原 030000)
传统剧场大体可分为固定剧场和非固定剧场。非固定剧场即临时搭建剧场或“划地为场”,由于其简繁不一、灵活多变,且往往用毕即拆,故学界对其关注不多。而传统剧场中大量的固定剧场建筑遗产,不仅是物质文化遗产,还是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艺术、建筑工艺、美术、书法等)的重要载体(1)吴开英等:《中国古戏台研究与保护》中强调“古戏台是我国古代建筑的组成部分,是研究我国建筑史、戏曲史和民俗史的重要实物依据,也是传承中华民族文明的重要载体”,中国戏剧出版社,2009年版,第249页。,属于双遗产范畴。康保成先生认为,传统剧场建筑是至少具备了“非遗”载体、文物保护单位、营造技艺等三重属性的特殊文化遗产(2)康保成:《古戏台研究专题》,《文化遗产》,2019年第5期。。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传统固定剧场(为行文方便,后文将“传统固定剧场”仍称之为“传统剧场”)的调查研究已成为戏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山西境内传统剧场遗存数量居全国之首,不仅历代时序演进明晰,而且类型多元,布局形制丰富多样,了解其遗存现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山西传统剧场调查概况
山西省位于太行山以西,黄河以东,故可称山西,也可称河东。山西之所以被誉为地上文物大省,与山西省境内遍布城乡的古建筑遗存有着重要而密切的关系,在全国古建筑遗存(尤其元代之前)中比重较大。笔者对照已公布的“三普”数据及各级文物保护名单,对山西元代以前木构建筑遗存进行了统计:山西境内目前调查遗存唐代建筑3座、五代4座、宋代34座、辽代3座、金代113座、元代339座,共计496座。全国共遗存金以前木构建筑191座,其中山西遗存157座,占全国同期的82.2%;全国共遗存元代木构建筑389座,山西占全国同期的87.15%;全国共遗存元代以前木构建筑580座,山西占全国同期的85.55%(“国八”前数据)。山西古建筑遗产不仅时代脉络清晰,数量庞大,类型丰富,而且建筑结构、用材尺度和制作手法等区域特征明显,在全国享有重要的地位,堪称中国古典建筑建造和遗存的极盛之地。其中传统剧场是其重要的建筑类型,广泛散布于山西境内各个城镇村落,闪烁着历史的光芒。
关于山西省传统剧场的调查研究,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末期在编撰《中国戏曲志·山西卷》时有过相关统计,原文曰“经文物部门普查,山西仍有清代以前庙台2887座,仅及原数十之二三”(3)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中国戏曲志·山西卷》,中国ISBN中心,2000年版,第538页。,这个统计数据非常精确,但对于这些古戏台的确切名录至今没有相关的公布,到底是哪些戏台,不得而知。对于山西这样的文物大省而言,对全省境内所有的传统剧场作专业的实地调查统计,绝非易事。对于此方面的工作,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今戏剧与影视学院)团队成员功不可没,团队师生百余人通过近40年的调查研究,加之各级文物管理部门以及一些地方文化学者的共同努力,对山西传统剧场的遗存状况有了较为专业的调查研究,对于山西传统剧场建筑遗产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和较为充分的认识。
目前,以有依据、有图像为原则,统计出山西传统剧场数量为3515座(有详细名录)。在此之前,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中对180余座神庙剧场做了专门的考证(4)冯俊杰:《山西神庙剧场考》,中华书局,2006年版。,冯俊杰、牛白琳、王潞伟《山西省志·古戏台志》收录古戏台1063座(5)冯俊杰、牛白琳、王潞伟:《山西省志·古戏台志》,中华书局,2016年版。,笔者《上党神庙剧场研究》收录山西境内上党地区(晋城、长治行政区域)古戏台1887座(6)王潞伟:《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颜伟《被倒置的“金字塔”:山西古戏台保护现状及启示》对山西古戏台做过相关统计(7)颜伟:《被倒置的“金字塔”:山西古戏台保护现状及启示》,《戏曲研究》,第114辑。,该文中表1(山西部分县市区域古戏台调查报告情况)统计数量为1839座,数据来源主要依据硕、博士学术论文,其中襄垣县、阳城县、泽州县、高平市、沁水县、陵川县、晋城市城区等地戏台与笔者《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中重合部分为1031座,其余县市共计808座。笔者经过10余年的调查统计,其最新数据为3515座,数据来源主要有以下路径:
①2008年以来实地田野调查所得;
②2010年以来相关著作、硕博士学位论文、期刊论文中的辑录;
③2010年以来地方文化机构或地方学人出版的相关书籍中辑录;
④2010年以来网页、博客、微信、抖音、快手中发布的。
上述3515座传统剧场,应该以动态观念理解。由于传统剧场建筑历时久远,并多被“废弃”,且自然损毁严重,就近十年时间而言,可能有些传统剧场已经荡然无存。也有的可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修缮,能否客观认定为传统剧场,有待具体的专业鉴定。当然,由于山西境内山高岭深,便于藏匿,客观上仍有未登计在册的“漏网之鱼”。但尽管如此,这个庞大存量足以证实山西传统剧场建筑遗产在全国传统剧场建筑中的重要地位。兹从以下几方面分析报告:
(一)山西历代传统剧场遗产数量及区域分布
从山西历代传统剧场遗产数量及区域分布看,宋代传统剧场没有建筑实物遗存,仅有文献载录;金元时期传统剧场建筑实物遗存以“舞楼”“舞亭”等演出场所为主,均属神庙剧场,目前调查统计为16座,全部位于山西境内中南部,除吕梁市石楼县前山乡张家河村殿山寺圣母庙元代舞楼外,其余15座全部位于晋南和晋东南地区,有确切纪年者7座,其余9座均为通过剧场布局、建筑风格、建筑技法及建筑形制、佐证史料等要素鉴定。
明代传统剧场建筑遗存目前统计全国现存为87座(8)王潞伟、张丹妮:《中国古戏台遗存及其文化价值》,《中华瑰宝》,2019年第10期。,其中山西境内46座,可确定创修时间的为39座。有40座分布于山西南部,仅有6座剧场位于中北部地区,分别是宁武县东寨镇二马营村广庆寺成化十四年(1478)戏台、阳曲县侯村乡洛阳村草堂寺嘉靖十二年(1533)戏台、太原市晋祠嘉靖三十四年(1555)水镜台、忻州市忻府区西张乡东张村关帝庙万历九年(1581)戏台、代县新高乡刘家疙洞村古松寺天启二年(1622)戏台、右玉县右卫镇马营河村五圣庙明代戏台。从庙宇属性看,明代城隍剧场建筑遗存数量较多,为6座,其规模较大,保存也比较完整。
清代至民国山西传统剧场数量庞大,除去金、元、明三代62座以外,其余全部属于清代至民国时期建筑。其中民国时期的传统剧场也多是在清代建筑的基础上修缮而成,其基本的建筑形制和风格样式仍属于古典式传统建筑。分布区域上,上党地区晋城、长治数量最巨,为1887座(9)王潞伟:《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第525-560页。,其中泽州县的传统剧场遗存为428座(10)王潞伟:《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第531-540页。,高平市传统剧场建筑遗存为342座(11)王潞伟:《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第553-560页;颜伟:《山西高平神庙剧场调查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9年版,第196-326页。。其次为运城、临汾、晋中地区,北部忻州地区和雁北地区存量相对较少,但各县区亦多有分布。
(二)山西传统剧场的属性及区域分布
从传统剧场属性,即剧场的所属场域和功能看,大致可分为四大类:一是神庙剧场、祠堂剧场等祭祀性场所剧场;二是勾栏瓦舍、茶园酒楼、戏园子等商业性剧场;三是同行、同乡等群体聚集场所的行会公所剧场;四是皇家仕宦豪族等私密性、等级性较强的宫苑厅堂剧场。这其中多数为固定建筑剧场,但亦不乏临时搭建的剧场建筑(图1),通俗地讲,上述四类属性的剧场在一些特定的时期,或特定的领域均有临时搭建戏台及观剧设施的相关图像和文献记录。

图1 临时搭建的剧场
这其中神庙剧场建筑存量最大,分布最广。神庙剧场的整体布局为坐北面南,中轴线上自北向南一般为寝宫、正殿、献殿(或舞亭)、二道门、戏台(山门戏台),两侧一般自北向南为侧殿、耳殿、配殿、厢房(二层看楼)、社房(二层戏房)。但由于时代、地域不同,庙宇供奉的主神及祭祀仪轨又有差异,一些神庙剧场布局显得略有个性。一些金元时期神庙剧场,“舞亭”“舞楼”往往位于庙宇中央,如平顺县北社乡东峪村九天圣母庙剧场(图2)、阳城县驾岭乡封头村剧场、阳城县泽城村汤王庙剧场等(图3)。从神庙属性看,民俗神系神庙剧场较为普遍,且有地域分布差异,如各地城隍庙剧场,由于其具有官方主导、民间参与的特殊属性,故遍布各地,且规模宏大,建筑用材均为优质材料,其顶制普遍使用琉璃瓦饰。分布较多的神庙剧场为关帝庙、玉皇庙、三教堂等剧场,就上党地区关帝庙剧场遗存而言为113座,玉皇庙剧场为106座,三教堂剧场63座,汤王庙剧场在阳城地区较为普遍,现存剧场88座,炎帝庙剧场主要分布于上党地区羊头山周围,以高平与长子地区为多,后土庙剧场多分布于汾河流域两岸。从时代角度看,明末清代一些佛教寺院出现了专门的演剧场所,就上党地区佛教寺院剧场遗存而言在85座以上。

图2 航拍平顺县北社乡东峪村九天圣母庙

图3 阳城县泽城村汤王庙剧场
除大量的神庙剧场外,宗祠剧场、会馆剧场、私人宅院剧场、皮影偶戏剧场也多有遗存。如宗祠剧场现存21座:沁县郭村镇仁胜村田氏宗祠剧场、晋城市北石店镇中河东村刘氏宗祠剧场、泽州县巴公镇西郜村李氏祠堂剧场、泽州县巴公镇西郜村张氏祠堂剧场、泽州县柳树口镇井洼村北李街李氏祠堂剧场、襄垣县上马乡夏庄村郭家祠堂剧场、阳城县河北镇匠礼村杨氏宗祠剧场、陵川县西河底镇东王庄村段家祠堂剧场、翼城县西阎镇十河村侯氏宗祠剧场、翼城县隆化镇两板村李氏宗祠剧场、灵石县静升镇静升村王氏宗祠剧场、灵石县集广村何家祠堂剧场、代县枣林镇鹿蹄涧村杨忠武祠(宗祠)剧场、永济市卿头镇西卿头村钟家祠堂剧场、原平市中阳乡南头村杨家祠堂剧场、平遥县岳壁乡南西泉村赵家祠堂剧场、平遥县东泉镇遮胡村霍家祠堂皮影戏台剧场、平遥县段村镇横坡村张家祠堂皮影戏台剧场、祁县罗家庄罗家祠堂剧场、闻喜县郭家庄镇杨家庄村杨氏祠堂剧场、晋中市榆次区车辋村常家庄园常氏宗祠剧场。调查统计可知,北方宗祠剧场建筑总体上没有南方遗存数量多,分布广,山西境内也有少量的遗存,但从建筑风格上看,山西宗祠剧场建筑同神庙剧场建筑差异不大。
山西境内皮影偶戏台遗存14座,形成精致小巧的剧场。如孝义市下堡镇马术岭村关帝庙皮影戏台、孝义市下堡镇桃树沟村关帝庙皮影戏台、孝义市下堡镇前庞沟村佚名庙皮影戏台、孝义市高阳镇神福村皮影木偶两用戏台、平遥县东泉镇东戈山村玉皇庙皮影戏台、平遥县朱坑乡庞庄村狼神庙皮影戏台(图4)、平遥县东泉镇遮胡村霍家祠堂皮影戏台、平遥县卜宜乡敖坡村十王庙皮影戏台、平遥县段村镇横坡村张家祠堂皮影戏台、平遥县段村镇希贤村关帝庙皮影戏台、临汾市尧都区吴村镇南太涧村皮影戏台、介休市绵山镇小靳村道马巷皮影戏台、翼城县南梁镇故城村故城观音堂皮影戏台、新绛县城隍庙二层大戏台之皮影偶戏台等,主要沿汾河中下游两岸地区分布,呈现出带状分布特点,且与皮影偶戏流行区域有一定的吻合。晋北地区、晋东南地区尚未发现有固定的皮影偶戏台建筑实物遗存。

图4 平遥县朱坑乡庞庄村狼庙皮影戏台
会馆剧场极为罕见,目前仅发现陵川县府城镇府城村陵邑会馆剧场1座。与清代晋商遍布天下有密切关联。
清代,出现了私人宅院剧场,且有少量遗存。如高平市原村乡良户村田宅剧场、太谷县白塔区上观巷孔家大院剧场、祁县渠家大院剧场、太谷县北洸乡北洸村曹家大院(三多堂)剧场等4座是专门用于家庭节日礼仪及日常娱乐演剧的专门场所。
(三)山西传统剧场建筑及区域特征
从建筑用材、技法、形制等角度看,山西清代传统剧场建筑呈现出多样化的形态。从建筑风格的地域差异看,山西传统剧场建筑多为砖木结构的抬梁式殿堂形制,这与山西煤炭和特殊的土质资源丰富有极大关联,这两种资源的结合使得山西古建在建筑用材上得心应手。除大量的抬梁式剧场建筑形制外,晋中平遥、汾西等地遗存了大量的窑洞式剧场建筑,具有鲜明的地方建筑特色。窑洞式建筑一般分为靠山窑、平地箍窑、窑洞与穿斗式形制结合的复合建筑。平遥、汾西等地大量的窑洞式戏台剧场多为窑洞与穿斗式形制结合的复合建筑体,前为砖木为主的穿斗式结构,后为典型的窑洞建筑,即后部窑洞往往作为演员化妆或临时休息的戏房使用。如平遥县岳壁乡梁村神宫剧场之戏台(图5、6)、平遥县岳壁乡赵壁村子夏庙剧场之戏台、平遥县岳壁乡赵壁村西神庙剧场之戏台、平遥县朱坑乡六合村三官庙剧场之戏台、平遥县卜宜乡靳村超山庙剧场之戏台均为此种形制。据杨阳运用专业设备测试,其音效确有特殊效果(12)杨阳:《山西古戏台声学效应研究》,山西大学2015届博士学位论文;杨阳、高策、丁宏:《平遥超山庙古戏台声学效应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2014年第4期。。

图5 平遥县梁村神宫剧场之戏台外部砖木抬梁式半坡硬山顶制

图6 平遥县梁村神宫剧场之戏台内部窑洞形制
晋中地区传统剧场建筑常用卷棚顶制,或悬山卷棚、或硬山卷棚、或歇山卷棚,其中歇山卷棚顶像极了倒扣的元宝,故最受欢迎,当地形象地称其为“元宝顶”。上党地区的传统剧场擅长于运用后悬山加前歇山檐角的组合顶制。雁北地区的传统剧场则擅于用半坡悬山顶或半坡硬山顶,且屋顶举折较为平缓,这与当地常年气温较低且雨水较少有很大关系。
清代以来,传统剧场在布局和形制上出现了多样化形态。布局方面,出现了“一庙多台”布局。首先是“品”字布局。如长子县下霍村三嵕庙剧场三座戏台呈“品”字形,东西两座相对而建,当地俗称“对台”;蒲县柏山东岳庙剧场三座戏台也呈“品”字形布局,东华门、西华门上两座戏台相对而设,正南方向是山门戏台;万荣县庙前村后土祠剧场布局也呈“品”字形,只是在“二连台”基础上的“品”字布局。其次是“连台”布局,或“二连”,或“三连”,如定襄县受禄乡大南庄便有一座二连台剧场遗存,运城市盐湖区池神庙剧场、介休市后土庙群关帝庙等剧场、运城市芮城县东吕村关帝庙群剧场、壶关县神郊村真泽宫剧场等均为“三连台”。这样的剧场建筑布局充分显示出清代演剧文化的兴盛。
形制方面出现了“一台多用”现象。常见的山门式戏台即是兼具山门和戏台双重功能。再者,也有一些过路式戏台,将戏台底部中间改造为通道,平日里车马行人不断,演剧时戏台基座通道上搭起木板便可使用。还有一些“关防式”戏台,如高平市康营村关帝庙剧场,具备通道、防盗、演剧三重功能。这种位于村镇主要街道上的通道式戏台,一是考虑交通位置,在通讯不便利的时代便于民众知晓演剧信息;二是能够在神庙空间位置受限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扩大观众区域。另外还有一些“双开口”“三开口”戏台,繁峙县东庄村三圣寺旧有双开口戏台,应县寇寨村也有一座双开口戏台遗存,当地称其为“鸳鸯台”,“鸳鸯台”虽是前后开口,但是一般前后不远处各有一庙,神灵圣诞演剧时互为前后台;“三开口”戏台目前山西境内发现的有介休市板峪村龙天庙“三开口”戏台,三个台口分别对应龙天庙、噤狮庙和远处山上的山神庙。这种布局是在保证民间礼乐规制的基础上做出的灵活变动,演戏敬神,戏台要正对神灵,但将本该“一庙一台”的规范礼制建筑做了灵活的“节省”处理,经济又实惠,可以看出晋中地区民众聪明的商业思维。
再者,也出现了一些建筑群组式样的复合式戏台剧场。如介休后土庙、太原晋祠水镜台剧场、襄垣县城隍庙剧场、大同市云冈石窟剧场、阳城县郭峪村成汤庙剧场、介休三结义庙剧场、黎城县城隍庙剧场、晋中榆次区城隍庙剧场、长治潞安府城隍庙剧场等,虽然没有宫廷剧场的福台、禄台、寿台的结构宏敞繁复,但对于地方、民间也极尽奢华气派。可以显现出民众对神庙剧场的重视和推崇。
明代中期以来,神庙剧场中开始出现专门用于观剧的建筑设施。车文明在《中国神庙剧场中的看亭》中指出:“出于增加观众席的需求以及受封建礼教男女有别、防止在公共场所男女混杂之礼法影响,大约在明代末期,神庙剧场出现了一种新的建筑‘二层看楼’”(13)车文明:《中国神庙剧场中的看亭》,《戏曲研究》,第87辑。。目前,最早的关于观剧设施的记载是万荣县解店镇东岳庙明正德五年(1510)《重修子孙神母殿堂记》载录的重修“看亭”之事。阳城县凤城镇下孔村成汤庙明正德十六年(1521)《重修土地庙碑记》,也有相关记载:“列看楼于兑方,起崇门于离方。……西看楼推旧为新者。”(14)下孔村志编委会:《下孔村志》,世界华人艺术出版社,2001年版,第355-356页。清代神庙剧场内有关看楼的建筑实物遗存和碑刻文献载录数量惊人,已经成为一种非常流行的剧场布局形制流行开来。
从上述可知,山西传统剧场有以下特点:一是数量之巨,为全国之首;二是分布之广,散布境内各城镇村落;三是时序完整,演进脉络清晰,金、元、明、清至民国均有遗存;四是形制多样,因地制宜,地方特色明显。总之,无论从时代、数量、类型看,还是从形制、遗存分布现状看,山西传统剧场建筑遗产是中国传统剧场文化的重要标本。对山西境内传统剧场现状的调查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参考价值。
二、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
山西传统剧场遗存数量巨大,虽然部分得到了有效的保护和利用,但是仍面临一些较为严重的问题和困难,概述如下:
(一)“占用”“改造”“闲置”“废弃”等现象较为普遍
笔者在十几年的传统剧场调查中,发现大量的传统剧场被“占用”“改造”,或“闲置”“废弃”,以致无人问津,损毁坍塌。新中国成立后,破除迷信,兴校办学,由于大量的神庙剧场属于村社的公产,所以大量的庙宇包括剧场在内被“占用”或“改造”为学校、村委办公、粮站等专用公共场所,从功能上发生了质的改变(15)钱生槭、康保成《古戏台修复如何贯彻“修旧如旧”原则》一文,对甘肃省正宁县等地的调研中也发现类似情况,载《文化遗产》2019年第5期。。由于建筑技术相对落后,故对神庙剧场建筑主体构造改造的程度相对较小,其损伤也相对较弱。山西传统剧场留存较多,与其经济落后,未能开展大规模建筑更迭有很大的关系。
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发展、科技进步,一些村委办公场所、村落中小学校、粮站等均另辟新地;再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戏改政策”的广泛推广和落实,遍布城乡的传统剧场由于不能够满足新式剧团较大规模的演出需求,各村社纷纷建起了规模庞大、气势宏伟的新型“人民剧场”。原有的庙宇包括剧场或被“占用”,或“废弃”(图7),或“闲置”,甚至有的成了“垃圾场”(图8),致使长期得不到有效保护,故损毁坍塌严重。

图7 平遥县卜宜乡东安社村关帝庙戏台“废弃”残损严重

图8 平遥县卜宜乡永城村大庙戏台已成为垃圾场
由于神庙剧场归属和功能主旨发生变更,致使修缮工作得不到保障,颜伟认为“如今情形发生了转变,维修神庙及戏台的主旨从‘世俗生活必需’变为‘文化遗产保护’,维修与保护的主体从村社百姓变为政府以及相关部门,致使很多在古建方面价值不大的神庙戏台荒废”(16)颜伟:《被倒置的“金字塔”:山西古戏台保护现状及启示》,《戏曲研究》,第114辑。。进入21世纪,官方对文物遗产更加重视,民众普遍认为所谓被认定的“国字号”“省字号”等各级保护单位,就应该由各级政府来负责保护修缮,而这些被认定的恰恰是少数,所以从覆盖面上看,大部分传统剧场得不到有效保护,处于“废弃”状态,广大民众从“主人公”变成了“旁观者”。这些被认定了保护级别和登记在册的神庙剧场建筑遗迹,级别越高,保护修缮力度越大。相反,那些保护级别低或未登记在册的则任其坍塌殆尽,而山西境内多数属于后者。
(二)损毁严重未制止
传统剧场建筑主要面临自然损毁和人为盗毁两种危机。
1.自然损毁案例
建筑遗产不同于自然遗产,需要不断地科学有序地维护修缮,从我们多年的调查所知,庙宇修缮周期一般在30~60年。对于建筑物而言,一般来自自然界损伤主要是地面反湿、雨淋或水淹等情况,如果在有效期限内得不到科学的维护修缮,建筑主体将会遭受更大的损毁,一般古建筑先是屋顶漏雨,之后椽子、梁腐烂,最后柱、基受损便会坍塌。我们在实地调研中,看到的自然损毁坍塌的剧场不计其数(图9)。当然,也有遇到不可抗力的较大的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等,四川省都江堰二王庙戏台便是在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中坍塌。

图9 航拍平顺马家山村苍龙庙剧场戏台屋顶已坍塌
2.人为盗毁案例
近年来各地纷纷恢复古城、重建古街,使得建筑文物“黑市”交易猖獗,一些“废弃”“闲置”的神庙剧场、民居老宅中雕刻精美的老建筑物件便成了盗贼的“猎物”。盗贼的手段之残忍,令人惊叹,被盗毁的神庙物件之多,令人惊讶。如壶关县沙窟村玉皇庙山门戏台外檐柱础被盗后不久,外檐柱便倒塌(图10);阳城县泽城村汤王庙山门戏台外檐柱础、泽州县大箕镇申匠村普渡寺山门柱础、阳城县蟒河镇泥河村兴隆寺多处柱础、高平市北王庄汤帝庙多处柱础、阳曲县北小店乡将军庄村五龙庙戏台、阳曲县北小店乡音子沟村三郎庙戏台、晋中市榆次区庄子乡冯家局古戏台等等,均遭盗毁,以致所涉古建筑遭到了致命的“打击”。还有一些传统剧场建筑由于防火意识淡薄,遭遇火灾,其建筑遗产毁失殆尽,如祁门县会源堂古戏台、平遥县城内武庙剧场、长子县南鲍村汤王庙剧场、长子县西南呈村天神庙剧场、沁源县涧崖底村介子推庙剧场等均是毁于火灾。

图10 壶关县沙窟村玉皇庙山门檐柱倒塌
3.双重损毁案例
也有遭受双重损毁的情况。如高平市晁山村白龙庙山门戏台,该庙宇位于晁山村北部白龙山顶,距离村社较远,早已被民众废弃,偶尔有香客供奉,但也力不从心,故长年风吹雨淋,未有任何保护修缮,故坍塌非常严重。再加上盗贼的人为损坏,更是雪上加霜。山门檐柱下原有精美的石狮柱础,在文物“黑市”买卖中价值不菲,故在2012年左右四座雕刻精美的石狮柱础被全部盗走(图11),致使该山门戏台遭受双重损坏(图12),危在旦夕。

图11 高平市晁山村白龙庙山门戏台外檐石狮柱础被盗

图12 高平市晁山村白龙庙山门戏台损毁严重
(三)保护修缮不科学
1.受到有效保护的传统剧场仅仅是少数。颜伟博士对车文明先生《中国戏曲文物志·戏台卷》中收录的424座山西传统剧场做了相关统计,其中属于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占15%,省级文物保护单位者5%,市级4%,县级2%(17)颜伟:《被倒置的“金字塔”:山西古戏台保护现状及启示》,《戏曲研究》,第114辑。。《中国戏曲志·戏台卷》中收录的传统剧场均为专门遴选出的具有代表性的剧场,国保级单位中的戏台剧场全部收录,故所占比例15%看似较高,实际上仅有60余座。如果按照此次最新统计3515座作为基数,那么属于国保范围的传统剧场仅仅占到1.7%。当然,除了一些被认定级别较高的文物保护单位中的剧场能得到相应的保护修缮外,位于山西境内15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96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的传统剧场也得到了相应的保护修缮。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全国799个,山西111个,位列第一。其中,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全国487个,山西96个,位列第一;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全国312个,山西15个,位列第六。如泽州县大阳镇中即有西大阳村汤帝庙剧场、一分街村资圣寺剧场、三分街村关帝庙剧场、西大阳西街佛堂剧场等4座剧场;灵石县静升镇中有王家大院剧场、后土庙剧场。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的传统剧场,我们对高平市原村乡良户村进行过专门的调查,村落内外原有大小庙宇24座,现仍保留有松蓬庙、大王庙、玉虚观、皇王宫、关帝庙、山神庙、观音庙、牛王庙、文昌庙、白爷宫、奶奶庙、九子庙、真武庙、扶风阁、西阁、鼓楼阁、汤帝庙、石泊庙、佛堂庙等遗构;其中松蓬庙、大王庙、玉虚观、皇王宫、关帝庙、汤帝庙均设剧场,加上田宅(田逢吉家族)私人剧场,共计7座传统剧场(18)王潞伟:《上党神庙剧场研究》,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版,第376-390页。,如今良户村已经成为旅游胜地,这些传统剧场也得到了科学有效保护修缮。再者如平遥县岳壁乡梁村神宫剧场、介休市龙凤镇张壁古堡(张壁村)中的关帝庙剧场、可汗庙剧场、沁源县王和镇古寨村龙王庙剧场、泽州县北义城镇西黄石村玉皇庙剧场、三官庙剧场等,均得到了有效的保护修缮。
尽管受到有效保护和修缮的传统剧场已数以百计,但是从总量上看,仍有大量的传统剧场得不到有效保护,如壶关县集店镇集店村东岳庙剧场(图13),戏台为硬山顶五楹,前带歇山檐。一面观。两侧耳房各一间,稍低于戏台,戏台整体风格恢宏气派、错落有致,且戏台上留存了三幅精美的石刻对联。总体上判断,该戏台极具代表性,2008年笔者前往考察,该戏台处于“废弃”状态,损毁严重。2019年前往调研,损毁更加严重,甚至紧靠戏台正前方盖起了民房,荒唐至极。沁水县龙港镇上木亭村城隍庙明代“移牮舞楼”也是一座由宋代舞楼向金元舞楼布局过渡的具有代表性的剧场建筑实证,村委在2014年进行了“撑伞式”抢救性保护(图14),笔者几次前往考察均未见到有效的修缮。

图14 沁水县龙港镇上木亭村城隍庙明代舞楼“撑伞”后
2.非专业修缮破坏现象较为普遍。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有专门性和依附性两类,临汾市尧都区魏村牛王庙戏台、临汾市尧都区吴村镇王曲村东岳戏台、晋城市高平市寺庄镇王报村二郎庙戏台等均有以古戏台保护为主的专门性保护单位。即便是一些传统剧场位于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或历史文化古城、古村当中,但由于传统剧场与神庙、宗祠、会馆、古城、古村等建筑群为依附关系,且多处于从属地位,故专门性保护缺失。民间自发修缮,对于传统剧场建筑更具毁灭性,如近年来宁武县二马营村广庆寺剧场的修缮就比较失败,钱生槭、康保成先生前往实地调研,只见台口四根檐柱已经刷了红漆,脊枋原“大明成化十四年(1478)重新”及“大清道光四年(1824)重修”题记全被涂抹(19)钱生槭、康保成:《古戏台修复如何贯彻“修旧如旧”原则》,《文化遗产》,2019年第5期。。近年来,由于改革开放,农村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再加上国家对传统文化的弘扬,一些村社开始大规模修缮或改建村社庙宇,由于施工方没有专业的古建技术施工资质,即便是仿古建筑,也与原来的建筑风貌大相径庭,有的甚至直接“以新代旧”,推倒重来,原先旧的庙宇和剧场全盘地“焕然一新”,毫无历史文化痕迹。这样的修缮实则是对历史文物遗产的毁灭,是不值得提倡的。
(四)脱离民众无意义
一些得以修缮的国保、省保庙宇剧场,在修缮后虽然有专人看管,但往往大门紧闭,纯粹地“保护”了起来,以致完全脱离了民众,而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作为文物遗产的文化价值,这并非国家保护修缮文物的宗旨和初衷。如,平顺县西青北村大禹庙剧场、平顺县侯壁村夏禹神祠剧场、临汾市尧都区东羊村东岳庙剧场等,均处于纯粹 “保护”状态。如何将这些珍贵的传统剧场建筑遗产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是当前面临的又一重要挑战。
结语
传统剧场建筑是中国历史建筑遗产的一个重要类型,是一种浓缩了中国社会发展、风俗习惯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建筑遗存,应该认真研究,并予以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做好传统剧场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工作,应坚持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方针,加大投入力度,运用现代科技手段,提高保护传承的整体水平,积极推动传统剧场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贯穿国民教育始终。
中国传统剧场是见证戏曲产生、发展和走向辉煌的宝贵实物。从世界范围看,只有中国保存了数以万计的传统剧场,其受众之多,分布之广,建筑之美,影响之巨,在世界戏剧艺术史和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堪称奇迹。中国传统剧场建筑遗存具有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巨大潜质,山西作为传统剧场建筑遗产的典型区域,应担当重任。对传统剧场进行大量实地调查和深入系统研究,为了解中国百姓真实的文化生活面貌打开了一扇门,为探究传统中国民间礼乐观念打开了一扇窗;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保护传承传统戏曲,振兴乡村文化,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等方面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