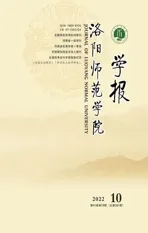明代王恕治滇研究
2022-03-18黄超
黄 超
(云南师范大学 历史与行政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王恕,字宗贯,陕西三原人。 明正统戊辰年(1448),王恕考中进士,以“庶吉士授大理左评事”[1]4831的身份,开始了其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 在四十余年的宦海生涯中,王恕先后辅佐明英宗、 代宗、 宪宗、 孝宗、 武宗,“刚正清严,始终如一”[1]4837,推行了许多利国利民的善政。 时有民谣称赞“两京十二部,独有一王恕”[1]4834。 在王恕所推行的诸多善政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其在担任云南巡抚期间所推行的善政。 在治滇期间,王恕革除弊政,与民休息,与时任云南镇守太监钱能的不法行径做了坚决斗争。 据《明通鉴》记载,恕居云南九月,威行徼外,黔国以下咸惕息奉令。 疏凡二十上,直声动天下[2]1310。 然而,在治滇九个月后,王恕却接到了朝廷让他“改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参赞军务”[2]1310的诏令,结束了治滇生涯。
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看,多数成果聚焦于王恕在治滇过程中与镇守太监钱能的斗争,忽视了王恕推行的善政,对王恕被迫停止治滇、 改任他职的时代背景及深层原因也关注不够。 鉴于此,笔者拟对该问题加以研究。
一、 受命治滇与推行善政
成化丙申年(1476)八月,大学士商辂上疏: “云南僻远,中官不法,议遣大臣有威望者巡抚镇压之。”[2]1296明宪宗同意“改王恕为右都御史,巡抚云南,治钱能之狱也”[2]1296。 成化丁酉年(1477)年初,王恕到达云南。
此时的云南“灾荒不收,今岁尤甚。 军民憔悴,日不聊生”[3]281,再加上中央政府征收“络绎不绝,行居骚然”[3]293,额外贡赋不断加码,更有甚者,当地流官侵田占地,“各官占伊前项村寨田地,以致百姓逃窜,差发拖欠”[3]296,特别是镇守太监钱能“怙势贪纵”[4],“掊克土司,凌虐绅士”[5],加剧了云南社会动荡,云南一时间出现了“滇人如在水火”[6]209的悲惨局面。 身为云南巡抚的王恕,在充分了解实情的基础上,推行了一系列善政。
(一)弹劾钱能,罢斥贪吏
据《明宪宗实录》记载,成化戊子年(1468)二月癸丑, 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琮上奏朝廷: “太监罗珪、 梅忠二人同镇云南,今珪卒,乞免更差。 盖二人同事,往往相持不决,反致违误,忠明敏不偏,可以独任事。”[7]1044沐琮的本意是让梅忠独任云南镇守太监。 然而,四天之后,朝廷却下达了“内批召忠还,而以御用监太监钱能往代之”[7]1044的诏令,由此开始了钱能镇守云南的时期。
钱能,女真人,正统年间入宫为宦,因在家中兄弟中排行老三,故号三钱。 其本性“怙宠骄蹇,贪淫侈虐,古所未有”[8]46。 在其接受任命、 途经贵州期间,钱能便开始表现出贪婪凶狠的本性,据《弇山堂别集》记载,钱能途经贵州,从行官舍,需索百端,民吏骇窜[9]2255。 到任后,钱能大肆纵容手下到处侵田占地,大肆掠夺民众财物,贪权纳贿,“私通安南”。 据《明宪宗实录》记载: “旧制,使安南者,道必由广西,而景乃取道云南,能以玉带、 宝绦、蟒衣、 罗缎、 犬马、 弓箭、 鞍辔诸物附景,私遗安南王,遂由云南至其国,受馈遗甚夥。 及还,诱其贡使仍道云南,至中途,绐以他语先行,及贡使至云南边境,守者阻之,不容入,边民以为安南人入寇,相率惊疑,欲避之。 总兵、 三司官遣人谕贡使至再四,其人始还,朝廷未之知也。”[7]3042-3043
当时的诸多云南官吏,不仅不揭发钱能的行径,甚至还上奏朝廷,为其歌功颂德,其中以巡按云南监察御史郭瑞最为著名。 据其所奏: “镇守太监钱能刚果有为,政务归一,先尝奏乞专命镇守,已蒙恩许,今能有疾,恐召还京,伏乞圣恩悯念,永令镇守。”[7]1609-1610
王恕赴滇后,在核实相关情况后,向朝廷上交了弹劾钱能及其党羽的奏疏,其在奏疏写道: “臣仰惟我太祖高皇帝统驭天下,虑恐大小官员、 军民人等假托公差为名,前往外夷衙门生事扰害,需索财物,致生边患。 故降敕谕、 金牌、 信符,及勘合底簿,关防诈伪,以尽抚绥之道。 列圣相承,率由旧草,每于践祚之初,换堪合底簿。 敕谕昭昭,篇首立法甚严,是以臣民遵守,不敢违犯。 夷人得以安生,莫不慕义向化,恪修职责。 顷自太监钱能到云南,侮慢自贤,罔遵圣训,不时差人前去外夷衙门,假公营私,需索搅扰,失夷人心,职贡因之以缺。”[3]289“臣窃惟外夷之人,性如犬羊。 驭之以道,则归顺; 驭之失策,则背叛。 故祖宗时因其慕义向化,臣伏中国,是以待之以诚信,抚之以恩义。 尝降敕禁止官员军民人等,不许假托公差前去夷方扰害。 非徒安外夷,实所以安中国也。 若外夷安,则边方无事,而中国自安。 外夷不安,则边方多事,而中国亦不得安。 今外夷南甸宣抚百夫长刁克蛮告称: 各官占伊前项村寨田地,以致百姓逃窜,差发拖欠。 节缘系侵扰外夷地方事理,若不拿问处置,诚恐失夷人心,因而激变,引惹边衅,不无劳师费财,为中国忧。 所系甚大,非但区区田土而已。”[3]296
王恕的上奏直指钱能及其党羽的不法行径,且是站在维护国家边疆安全及国计民生的角度予以揭露,并将其上升到了“失夷人心,因而激变,引惹边衅,不无劳师费财,为中国忧”的安邦高度。 王恕上疏朝廷后,钱能大为惊骇,便通过其在朝廷的权贵进行疏通。 其结果虽然是“上既宥能罪”,但跟随钱能的党羽则遭到了严惩,其手下的指挥使郭景,自知罪孽深重,以投井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由此,钱能的气焰受到了极大打击。
(二)直言极谏,为民请命
明代学者朱孟震在其所著的《西南夷风土记》中,对云南等地的物产,做了如下记述: 土产,孟密东产宝石、 金,南产银,北产铁,西产催生文石。 芒市亦产宝石、 银。 孟艮、 孟琏亦产银。 迤西产琥珀、 金、 阿魏、 白玉、 碧玉。 茶山产绿玉,干崖产黑玉,车里产贝。 缅甸西洋出大布,而夷锦各夷皆出,唯古喇为胜。 象牙诸司皆产,独老挝居多[10]。 由此可见云南物产富饶。
物产富饶的云南自洪武平滇后,逐渐成为朝廷岁取贡品的主要地区之一。 从奇珍异兽到名贵宝石,几乎无所不有。 王恕治滇之时,云南正遭受“天灾”,民众的生活苦不堪言,面对朝廷依旧如常的“贡品”索取,王恕本着为民请命的心愿,直言上疏: “臣闻昔汉之时,鼠巢于树野,鹊变色,识者以为不祥。 夫鹦哥本绿羽,而今黄其羽,岂非所谓‘野鹊变色’之类?不知钱能何取于此?遣人远涉徼外,扰害取之,将以进献。 不知朝廷何少乎此?亦不知朝廷无此何所损,有此何所益乎?然而,此物有无既不足为朝廷损益,抑不知钱能何忍故违目前诏旨,而必欲进乎?万一朝廷纳之,何以使天下臣民之无疑乎?是乃因小失大也,其可乎哉?臣愚以为,此物诚不宜受。 况云南数年以来,盗贼窃发,地方不宁。 若禽鸟,若金灯笼、 宝石、 屏风等项之贡,络绎不绝,行居骚然。 近来少息,人心稍宁。 若又容进此物而不却,则希宠徼幸者,将必过求奇巧以进之,岂止前数事而已?其弊盖有不可胜言者。 臣又闻: 不宝远物,则远人格。 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即今外夷久缺朝贡之礼,交人渐有不服之心。 此正朝廷及内外臣邻无迨无荒之日,忽不虞之戒!伏望陛下念祖宗创业之艰难,今日守成之不易,明降诏旨,痛却钱能此贡,仍通行各处守备、 镇守、 内外官员,今后除常例岁贡外,其余一应花草、 禽鸟、 宝石玩好物件,一切禁止,不许贡献。 愿陛下留心圣学,专意政事,永为华夷之主,天下幸甚,生民幸甚。”[3]293
王恕的谏疏,以儒家学说中“仁政”立场为出发点,旨在规劝皇帝要爱惜民力,停止向百姓征收无休止的额外贡赋,其间闪烁着“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 谏疏上奏后,明宪宗下发朝议讨论。 在内阁辅臣商辂等人的建言下,明宪宗最终下发了“乞敕内外臣,自后皆毋进”[6]209的诏令。 自此,饱受困苦的云南民众终得一丝生机。
(三)留心武备,巩固边防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描述云南的地理位置虽称荒服,而绸缪防御不可不周者,以滇、 黔与楚、 蜀辅车唇齿之势也。 说者谓云南山川形势,东以曲靖为关,以霑益为蔽; 南以元江为关,以车里为蔽; 西以永昌为关,以麓川为蔽; 北以鹤庆为关,以丽江为蔽。 又云南要害之处有三: 东南八百、 老挝、 交阯诸蛮,以元江、 临江为锁钥; 西南缅甸诸蛮,以腾越、 永昌、 顺宁为咽喉; 西北吐蕃,以丽江、 永宁、 北胜为阨塞。 识此三要可以筹云南矣[11]。
明初平定云南之时,为了安定云南地区的统治,除设置了云南承宣布政使司等行政机构外,还在广大地理位置险要之处设立了卫所制度,并在“踵元旧事, 悉加建设”理念的指导下,保留了元代的土司制度,并予以必要的革新。 上述举措,对于维护、 巩固明初时期的西南边疆治理是有极大作用的。
然而,明朝正统年间以后,卫所制度被逐渐破坏,士兵大量逃亡,此时的土司制度也逐渐有名无实,当地土司“控制稍疏,动多自恣”[12]6。 当时的实情也在王恕的奏疏中有所反映。
“今临安府密迩交阯,本处虽设一卫,实在官军除屯种、 守哨等项差拨外,见操止有二百余人。 通计云南二十五卫所,实在官军除屯种、 守哨等项差拨外,见操不及一万三千人。 每处见操官军,多者不过七八百人。 其他诸多夷杂处,该征税粮数少,且又不通舟楫。 官军粮饷银,止靠屯田供给,别无来处。 见今所在食粮不彀一年支用。 况兼频年以来,灾荒不收,今岁尤甚。 军民憔悴,日不聊生,盗贼在在生发,动辄劫掠杀人,东备西出,殆无宁日。 加之以广西、 广南、 元江、 丽江、 罗雄等处土官连年仇杀,不听抚化。”[3]281
面对这种情况,王恕在积极整顿军备、 抑制动乱事件频发的同时,坚决打击土司的不法行径,推动寻甸等地的改土归流。 “成化中,寻甸安晟死,兄弟争袭。 巡抚王恕与黔国公沐琮,请罢寻甸土官,改设流官知府。”[12]162根据实际需要奏请朝廷重新更置临元、 澜沧、 金腾、 曲靖四道防务。 其间,王恕还挫败了安南企图发起的边衅,“安南纳江西叛人王姓者为谋主,潜遣谍入临安,又于蒙自市铜铸兵器,将伺间袭云南。 恕请增设副使二员,以饬边备,谋遂沮”[1]4832。 由此可见王恕的远见卓识。
二、 民众称赞与改任离滇
王恕治滇期间始终清廉爱民。 据《南园漫录》记载,王端毅公恕来巡抚云南,不挈僮仆,唯行灶一,竹食罗一,服无纱罗,日给唯猪肉一斤,豆腐二块,菜一把,酱醋水皆取主家结状,再无所供[8]78。 为了拉近与民众的距离,王恕还专门让人贴出了一张告示,告示上写道: 欲携家僮随行,恐致子民嗟怨,是以不恤衰老,单身自来,意在洁己奉公,岂肯纵人坏事[8]78。 正因为王恕清廉爱民,所以每逢王恕视察巡行之时,沿途的民众均以“焚香礼之”的礼节来迎接王恕,由此可见王恕在云南民众心中的地位。
王恕推行善政,赢得了民心,却招致了一些人的憎恨,其中尤以钱能为最。 据《滇云历年传》记载为,能怨恕益深[6]210。 王恕治滇前,作为镇守太监的钱能在云南为所欲为,甚至纵容指挥使郭景“逼淫曩罕弄孙女,许以开设衙门治事”[9]2256,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王恕治滇后,钱能的权势受到极大的压制,不仅手下的诸多官吏遭到王恕弹劾被罢免,甚至连钱能本人也屡次遭到王恕的弹劾,几经陷入“去能苏困”的境地。 因此,钱能为“谋急去恕”,“广以金宝馈当路”。 接受钱能贿赂的内阁大学士万安、 兵部尚书王越等官吏,在明宪宗面前,对王恕弹劾钱能罪行的奏疏,进行了“沮之”的处理,并对王恕本人进行了百般诋毁,最终促使朝廷对王恕发出了“召还之命”,并将王恕改派南京任职。 而在王恕离滇后,钱能“复肆如初”,云南民众广受其苦,以至云南民谣都传唱“王恕再来天有眼,钱能不去无树无皮”[6]211。 虽没有华丽词汇的修饰,却是底层民众心声的直接写照。 仅从这句民谣中,就不难看出云南民众对钱能的憎恨程度,对王恕治滇成就的高度认可。
三、 离滇背后的原因分析
王恕离滇后,云南按察司副使陈麒、 巡按御史许进等官员出于对钱能不法行径的不满,相继对其进行了斗争。 可从实际结果看,前者反遭钱能“诬奏”,被革职为民; 后者则得到了朝廷“不从”的决议。 直到成化庚子年(1480),朝廷才派遣太监覃平来代替钱能镇守云南,算是以行政调动的方式解决了“钱能扰滇”的问题,而这距成化戊子年(1468)钱能受命镇守云南,已经过去了12年时间。
透视王恕“受命治滇—担任巡抚—改任南京”的全过程,朝廷的本意是要“治钱能之狱也”,即任用王恕来治理钱能的不法行径,而王恕的诸多举措,从实际效果看,不仅极大约束了钱能的不法行径,使其“虐焰少挫”,还维护了地方稳定,赢得了民众认同,甚至连世代镇守云南的黔国公沐氏家族都严格遵守王恕的命令,不敢有所造次。 应当讲王恕的治滇成果远远超出朝廷预期。 然而,就在王恕治滇初见成效之时,却被朝廷改任南京赴职。
实际上,如果把“王恕治滇”置于整个“成化政局”中,便会发现“王恕治滇”早在他赴任之初,便会有这样的结果。 重要因素有以下两点。
(一)宦官弄权是王恕改任离滇的制度性因素
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在其所著的《明夷待访录》中,对有明一代的宦官弄权做过如下评价: 奄宦之祸,历汉、 唐、 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有明之为烈也。 汉、 唐、 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 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 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 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 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 其它无不皆然。 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奉行之员而已[13]。
作为中国传统官僚体系中的特殊一环,早在西周时期,周王室就已经在宫廷中设置了宦官。 据《周礼》记载,内竖掌内外之通令,凡小事[14]168。 从这一时期的记述可以看出,尽管在西周时期,宦官就已经成为“王”的传令者,但传递的都是小事情,且“若有祭祀、 宾客、 丧纪之事,则为内人跸。 王后之丧迁于宫中,则前跸。 及葬,执亵器以从遣车”[14]168。 客观来说,这一时期,宦官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 然而,西周以降,随着中国传统官僚体系的日益复杂,宦官参政、 干政现象逐渐增多,如战国时期赵惠文王的宦官缪贤推荐蔺相如使秦、 秦汉时期秦二世宦官赵高发动沙丘政变等,都是宦官参政、 干政的突出例子。 到东汉时期,宦官势力膨胀,终于引发了其与士大夫阶层的激烈对抗,并酿成了中国历史上的著名的“党锢之祸”。 “窃持国柄,手握王爵,口含天宪”[15],恰是对宦官干政的生动写照。
东汉之后的几个朝代,宦官弄权的现象一直未得到有效控制。 到了明朝开国之初,鉴于宦官干政的历史教训,明太祖除颁布“敕内官勿预外事,凡诸司勿与内官监文移往来”[16]的诏令外,还在宫中竖立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1]7765的铁牌,并对宦官势力进行了一系列从官阶、 月俸到品级的限制。 明太祖后,继任的明惠帝坚决执行了明太祖关于限制宦官势力的决定,并规定“诏出外稍不法,许有司械闻”[1]7765。 然而,由于宦官在靖难之役中协助燕王朱棣夺权有功,燕王朱棣继位后,开始给予宦官诸多特权,如监军、 镇守等。 “盖明世宦官出使、 专征、 监军、 分镇、 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1]7766此后,明代宦官的权力逐渐扩大,不仅可以在地方“权埒开府,藩、 臬而下不敢抗也”[17],甚至可以在中央对朝廷的正常选官产生很大影响。 据《今言》记载,是时四方白丁、 钱虏、 商贩、 技艺、 革职之流,以及士夫子弟,率夤缘近侍内臣,进献珍玩,辄得赐太常少卿、 通政、 寺丞、 郎署、 中书、 司务、 序班,不复由吏部,谓之传奉官[18]。 冯天瑜教授在研究明代宦官弄权后指出,阉宦拥有考察、 监督官吏,决定官吏任免、 升迁的大权。 又由于宦官有权参奏各地督抚,其势力也伸向地方。 阉人还自成独立系统,设立诸衙门,任命许多官员,隐然而为又一政府[19]。 冯天瑜教授的结论与明末清初思想家黄宗羲所描述的史实基本吻合。 由此可见,明代宦官弄权之严重。
尽管王恕的上奏给钱能以沉重打击,但王恕仅有内阁辅臣商辂等人支持,钱能背后的势力却庞大得多。 翻阅《明实录》《明史》《明通鉴》《南园漫录》,可以看到,钱能不仅与同为宦官的梁芳、 汪直等权宦私交甚密,还与内阁辅臣万安、 兵部尚书王越等官员有所往来,甚至还与明宪宗的宠妃万贵妃有一定交集。 据《明史》记载,佞幸钱能、 覃勤、 汪直、 梁芳、 韦兴辈皆假贡献,苛敛民财,倾竭府库,以结贵妃欢。 奇技淫巧,祷祠宫观,糜费无算[1]3524-3525。 这既和钱能本人善于活动交际有关,又是明代宦官弄权这一大的时代背景所使然。 其中最重要的是明代宦官弄权的制度性因素。
(二)人主昏聩是王恕改任离滇的非制度性因素
方铁教授在《古代治理边疆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构想》中,就“影响治边理论与实践”提出了“非制度性因素”概念,指出“非制度性因素”大致包括统治集团内部出现的外戚干政、 宦官擅权与政权的非正常更迭,边疆地方政府由于腐败、 擅权与混乱对治边造成的干扰,以及天灾、 瘟疫、 暴乱、 战争等带来的影响[20]。造成王恕改任离滇的因素,除了宦官弄权这一制度性因素,还不能忽视人主昏聩这一非制度性因素。 王恕改任离滇的最终决策者——明宪宗当时出于何种考量应引起学界关注。
清代史学家谷应泰在《明史纪事本末》中,对明宪宗有如下评价: 宪宗躬法桓、 灵,养奸甫、 节。 卿贰大臣,直皆收问; 局司近侍,直得更张。 槛车逮治,南署空曹; 缇驰行边,北门不守。 明世中人,多窃宠灵,亦未有显挈利器,授人断割如宪宗者[21]。 谷应泰将明宪宗类比于东汉时期汉桓帝、 汉灵帝,虽然有些不符合历史实际,但从中不难看出明宪宗对于宦官的信任确实要超过对一般的大臣的信任。
明宪宗在即位之初,积极革除前朝弊政,如平反于谦冤狱,召还浙江、 江西、 福建、 陕西、 临清镇守内外官及诸边镇守内官,重新起用商辂等被罢黜的前朝贤臣。 然而执政后期,明宪宗不仅任用了“日以请托取贿为事,深结诸阉为内援”[22]的万安担任内阁辅臣,还大肆任用汪直等宦官,并允许其开设西厂,以作侦查民臣言行等之用。 就在王恕改任南京的前几个月,明宪宗还与支持王恕治滇的内阁辅臣商辂、 兵部尚书项忠等官员围绕“西厂之罢”,展开了激烈争论,最终结果竟以项忠被罢斥为民、 商辂被迫致仕而告终。 以此事件为标志,“士大夫皆俯首事直,直势愈恣”[23]146,成化政局逐渐走向了衰败。 “成化中叶以往,朝政浊乱。”[23]143明史学者孟森的评价可谓一语中的。 因此,当内阁辅臣万安等人诋毁王恕时,明宪宗不顾王恕治滇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不查其中的是非曲直,听信奸臣、 佞宦的谗言,把王恕改派南京任职,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究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就是人主昏聩这一非制度性因素。
王恕在离滇赴任南京之前,给明宪宗上了一道《改南京都御史参赞机务谢恩疏》,其中有一段话这样写道: 臣以迂拙庸材,虽尝误蒙任使,不过因人成事。 其余前数者之善,实无一焉。 今蒙圣恩授以此寄,拜命之余,惊忧失次,深恐不称,以负圣明用人图治之意[3]303。 在这封奏疏中,王恕将自己称为“迂拙庸材”,称自己的治滇举措为“因人成事”“实无一焉”。 百年之后,细细品读,后继者依旧会从“谢恩”的外衣下,品出作为“臣子”的王恕内心的辛酸、 凄凉。 治国必治边,在当今的中国边疆治理中,仍需要王恕这样清正实干的“能吏”“廉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