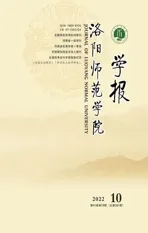《重游缅湖》中的自然与生态书写
2022-03-18李伟
李 伟
(安徽科技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凤阳 233100)
作家E.B.怀特被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 1953年5月23日,怀特在《纽约客》杂志上撰文提及梭罗的名著《瓦尔登湖》时,称该作品是他最喜爱的一本书: “《瓦尔登湖》是我所拥有的唯一一本书……我认为,每个人在他的生命中都读过一本书,这本书是我的。 或许,它不是我所遇见的最好的一本书,可它对我来说是最好用的一本,我就像随身携带手帕一样把它放在身边——在文思枯竭和绝望时寻求安慰。”[1]68作为“梭罗精神的传人”,怀特从梭罗的自然写作中获得了无穷的灵感,其作品以行云流水般的清丽文字描绘了一个个灵动的自然意象,构建起一个和谐的自然世界,字里行间充满着深邃的人生哲思。 怀特的散文代表作《重游缅湖》是美国文学史上的佳作名篇,本文聚焦于《重游缅湖》的生态内涵,从生态意象、 生态环境、 生态叙事三个层面解析怀特的生态书写。
一、 生态意象
怀特的许多作品都体现了他的生态主义思想,散文《重游缅湖》便是其中之一。 《重游缅湖》最初发表在1941年8月的《哈泼斯》杂志上。 根据评论界的说法,这篇散文从酝酿到成稿,历时三十余载,相当于数易其稿。 缅湖在怀特的生命中占据着非同寻常的地位。 怀特的父亲1904年首次带他来此度假,自此他便与缅湖结下不解之缘,直到怀特81岁生日最后一次故地重游,从童年到少年至中年,作者多次来到缅因州的贝尔格莱德湖上,三次详细记录了游湖的见闻和观感,每一次与前次相比不仅增加了篇幅和细节描述,而且其生态意识的体现也渐次增强。 怀特初次尝试这个题材是在1914年,这位15岁的少年自编了一本介绍贝尔格莱德湖的小册子,此前十年间他每年8月都要随父来到此地野营,这个背景在《重游缅湖》开篇有所交代。 小册子以平实的语言和客观的视角简要介绍了这座湖的地貌特征,其中的一条分支溪流“长几英里,深度足够,可以有机会一整天泛舟湖上了”“这湖足够大,为各种小船提供了理想的条件” “游泳也是一个特色,因为中午时分天气变得暖和起来,游泳感觉会很好”[2]36。
1936年,成名的怀特在父母亡故后故地重游,随后给兄弟斯坦利写了一封长信,以生动的文字和饱满的情绪细致地描绘了贝尔格莱德湖从早到晚的景致变化,包括沿岸湖底清晰呈现的鹅卵石和漂流木、 投入水中的黑色水生昆虫、 跃出莲叶的小鱼、 饱餐后在深水里懒洋洋游动的大鲈鱼、 夜间湖水轻拍岩石的低吟声等。 其中也不乏对人在自然中活动的感受描述: “水盆里的水冰冷刺骨,早餐的甜面包圈飘香,厨房里淡淡的臭气挥之不去,炎热的午后远处传来汽艇马达的嗡嗡声,宿营地充满木材的潮湿气息,人们乘小船前来垂钓,细长的导航船尾部激起白色的浪花。”[3]101总体上讲,文中视觉、 听觉、 嗅觉和触觉感官描写交相呼应,人与自然的活动相映成趣,多个意象构成一幅人类在自然界美好生活的图景,主观情思与客观景物浑然一体,整体意境静谧温馨,展现了人类与自然之间和谐的生命律动。
1941年,怀特带着11岁的儿子再游贝尔格莱德湖区,《重游缅湖》一文由此诞生。 文中保留了1936年那封家书的一些细节,但是在“湖”与“海”的对比中带了一定的象征意味。 作者反复强调“这块独特、 圣洁的地方”所具有的“宁静”“沉静”的特质,这种特质在海的衬托下得到强化。 文章一开头,作者回忆了往昔在缅因湖区的美好假期,随后作者写和儿子“将船泊在湖面,开始垂钓,微细的涟漪轻抚船帮,还像旧日一样”。 作者不由得感叹道:
夏日,哦,夏日,生命中的印记留存不去,那永不消失的湖泊,永不摧折的林木,牧场上遍布香蕨木和桧树,年年岁岁,郁郁蓊蓊,夏日没有尽头; 这是背景,湖边的生活是画面,度假者勾勒的一幅单纯而安谧的图画……这些记忆时时涌上心头,对我来说,那些时光,那些夏日,似乎无比宝贵,值得珍藏。 那是曾经有过的欢乐、 宁静与美好。[3]94
在这个广为传颂的经典段落里,缅湖的“宁静与美好”使之成为世人流连的世外桃源和永恒的避风港,成为人类精神家园的一个象征。 同时,与湖相关的其他自然意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一象征意义起到了强化作用,扑面而来的是原生态的生命活力和健康气息,如“浅滩处,黑黢黢的、 给水浸泡的长枝短条,或平滑,或腐朽,一簇簇在波纹累累的沙子上摆荡,湖蚌爬过的痕迹清晰可辨。 一群米诺鱼游过,每条小鱼都投下自己细细的影子,阳光下截然分明,数目就平白扩大了一倍”。 轻描淡写之间,大自然悠然自得的生命节奏跃然纸上,文字间洋溢着自然生命的欢愉。
作者在构建湖意象时不仅铺陈渲染大自然本身的宁静与美好,也突出了人类与自然万物的和谐共存。 如文中所述: “那湖泊从来不是人们通常所谓的野湖。 岸边散落着房舍,这是块农耕的乡园,却也无碍湖边林木繁盛……”[3]91这湖虽然具有原生态的自然美,但绝非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让人在与自然生命相处时很容易感受到“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的悠然意境。 更为重要的是,人类通过自身的努力,在自然界取得了自己的生存空间,在亲近自然的同时又与自然保持着彼此和谐相处的距离。 破晓时分,作者“溜到空气清新的户外,登上小划子,借松林长长的阴翳沿湖岸划行。 我记得必须小心翼翼地不让船桨碰了船帮,生怕打扰了教堂那般的岑寂”[3]91。 父子垂钓时作者写道: “我们默默盯牢钓竿的梢头,蜻蜓来而复去。 我将竿梢缓缓沉入水里,老大不忍地赶走蜻蜓,它们疾飞出两英尺,悬停在空中,又疾飞回两英尺,落回竿梢的更远端。”[3]92在文字描述中体现出作者的生态意识,即人类对非人类生命的怜惜及对自然规则的尊重。
二、 生态环境
在1936年的那封书信里,怀特几度欣喜地慨叹“一切都未曾改变”或者“一切都变化不大”,言辞之间传达出一种昨日重现的释然情绪,书信也的确着重于记录那些记忆中不曾改变的细节。 作者在重温旧日时光之后特意重申道: “我回到了贝尔格莱德,一切都变化不大。 我觉得应该让你知道。 ”值得注意的是,这句话在措辞上发生了些许微妙的变化,第一次出现是完成时态,表示从过去到现在的持续状态和结果,后来都用一般现在时来表达一种常态,仿佛缅湖本身就是一个超越时空的存在,而保持原样是一个客观事实。 同样,“不曾改变”在《重游缅湖》中反复出现,如“一切都还是当年模样”[3]91; “一切都不曾改变,岁月不过是幻影,时光并没有流逝”[3]92; “一切都那么熟悉”[3]97; 等等。 然而,不同的是,《重游缅湖》的侧重点从“求同”转向了“寻异”,作者一方面强调缅湖无异于往昔,另一方面却感慨时过境迁,将视线投向了种种切实的改变,怀旧的怅然之情溢于言表。
文章一开篇,作者便写道: “去往湖区的路上,我开始琢磨那里变成了什么样子。 不知时间会怎样侵蚀了这块独特、 圣洁的地方——小湾和溪流,落日的山峦,木屋和屋后的小路。 我相信那里必然修了柏油路,又不知道它还有哪些可悲的变化。”[3]90-91对于变化,文中用了“可悲”二字来形容,直接表露了作者对此所持的消极态度。 具体说来,他在文中不动声色地指出了柏油路的修建、 交通方式的改变、 汽艇马达的噪声、 电影对村姑的影响、 可口可乐的引进等五种细微变化。 这些变化虽然都不算大,却集中体现了工业文明对自然的侵袭和商业文化给乡村生活带来的冲击。
首先,柏油路代替了泥土路,汽车出现在乡间,表明了现代工业文明朝向乡村的次第推进。 事实上,文中三次提到柏油路: “我对柏油路的预感果然不错,它伸入湖岸半英里”[3]91; “公路只有两条车道,中间的一条消失了,那条道上,曾留下牲畜的蹄印,散布了牛马的粪干。 以前始终是三条车道,你可以择一而行,现在只剩下两条道。 有那么一刻,我深深怀念中间的选择”[3]93; “店外,道路铺上了柏油,汽车停在商店门前”[3]96。 与柏油路一样,汽车也是工业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 以往,“在火车站,农庄的大篷车停过来,闻到松树第一缕浓郁的香气,瞥见第一个笑呵呵的农夫……坐在大篷车上,经受十英里的漫长颠簸,在最后一道蜿蜒伸展的山顶,头一眼望见那湖,这片念兹在兹的水面,一别就是十一个月。 其他的度假者见到你,一片欢呼叫闹声,行李箱子得打开,卸去它们的重负”。 现如今,“游客的抵达不那么热闹了,你开车悄没声地进入,将车停在小屋旁的树下,拎出行李袋,五分钟的时间,一切安排妥当,不再大呼小叫,不再欢天喜地地围着行李箱子闹腾”[3]94-95。 在作者看来,与汽车相比,往昔从火车站到营地的那段大篷车之旅更加亲近自然,也更富于人情味,给八月初抵达湖区的游客完全不同的感受,工业文明的发展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人与自然、 人与人之间的隔绝和疏离。
其次,从汽艇马达发出的刺耳噪声来看,技术进步既给人类生活带来便利,又制造了打破自然宁静、 破坏人与自然之间和谐氛围的噪声。 在咏叹缅湖的“宁静与美好与欢乐”之余,作者指出“如今惟一不对头的地方是这里的声响,汽艇的尾挂发动机陌生而恼人的声响。 这声音很刺耳,时时打破你的幻觉,让你感受到时代的推移”[3]95。 以往的内置发动机发出的“声响只带给人安慰,成全了你的仲夏之梦,如今的尾挂机艇则不同,“白天,炎热的上午,这些发动机任性地、 怒冲冲地吼叫,夜晚,夕阳残照的恬静湖面上,它们像蚊子一样在人的耳边嗡嗡聒噪”[3]98。 以往驾艇需要带着“头脑冷静”的智慧去揣摩才能把握规律,“那台带有沉重飞轮的老式单缸发动机,只要从心里与它亲近,使唤起来,自然能得心应手”,如今的汽艇只消掌握简单的操船技术就能熟练驾驭。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此对驾艇技术进行了细致的文字说明。 借用彭程的说法,怀特“解构了人们对技术的过度崇拜,一种现代意义上的迷信” “科技呈现的还更多是好的一面,对科技的赞美也是一种共识,几乎是一种‘政治正确’。 如今,技术的负面效应已经是频发常见,足证怀特当时即已经拥有一份敏锐的预见力”[4]113。
再次,村姑的外貌发生了城市化的改观,乡村商店里的传统饮料也被可口可乐取代,这些细节都体现出商业文化对乡村生活的影响。 农庄饭馆大体上“不见岁月的流逝”,就连馅饼也还是那两种馅,“女招待仍是些乡下姑娘”“依旧十五岁”,但“唯一的区别”是“她们的头发浣洗过”[3]93。 作者将其归因于“她们去过电影院”,试图模仿“银幕上的淑女”的样子,把头发收拾得很清爽。 电影成为主流文化传播的有效途径,使得乡村不再闭塞,“原生态”的生活方式在电影的影响下悄然发生着改变。 同时,商店里“还是当年的景象,只不过多了可口可乐,少了些‘勇气’牌软饮料、 根汁汽水、 桦啤和菝葜汽水”[3]96。在这个意义层面上,这一细节表明,城乡生活方式即将日渐趋同,似乎暗示着城市化的进程在不知不觉间向乡村逼近了。
三、 生态叙事
生态意象的构建和生态环境的理想重构是怀特生态写作的两个重要层面。 此外,《重游缅湖》还集中体现了怀特精湛的生态叙事技巧,尤以叙述视角的巧妙转换、 第一人称内聚焦视点的准确把握、 文字的和谐韵律为主要特征。
刘文良认为: “生态文学特别重感染力,这也就要求生态文学家在视角的选择方面要更加慎重。 生态文学叙述视角的选择往往是多样化的,孩童的角度、 物事的角度、 未来的角度等都是生态文学比较常用的叙述视角。”[5]192在《重游缅湖》中,作者通过视角转换的手法将三代人分别代表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联系起来,从而实现了时空的跨越。 因为与儿子同行,人到中年的怀特感觉自己成为一种“双重的存在”,当清晨听见儿子悄悄溜出去亲近大自然时,“我开始产生幻象,似乎他就是我,因此,简单置换一下,我就是我父亲。 这种感觉徘徊不去,我们在那里的日子,时时萦绕在心头”[3]91。 当有蜻蜓落到钓竿梢头时,“我望望儿子,他正默默地看那蜻蜓,是我的手握了他的钓竿,我的眼在观看。 我一阵眩晕,不知自己是守在哪一根钓竿旁”[3]92。 “不管走到哪里,我都不免疑惑我究竟是谁,是我旁边走着的这个,还是穿着同一条裤子的这个。”[3]97在这几处视角转换的叙事之中,作者描述的是时光驻足的幻象,强调的则是大自然恒常不变的特质。 儿童未受尘世经验的影响可以忽略周围环境发生的那些“可悲的变化”,因此作者借助于儿童视角,不仅可以重新发现自然的美好,还可以坦然发出“一切都未曾改变”的慨叹,同时也避免了成人怀旧所引发的遁世之嫌。 如果说成人视角关注工业化进程给自然和人类生活带来的负面影响,那么儿童视角看到的则是自然生命的永恒,两种视角在过去和现在之间生成一种张力,使作者的思绪得以在这双重维度之间摆动自如,从不同角度向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方式发起了质疑和挑战。
另外,第一人称内聚焦视点的运用在生态写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法国叙事学家热奈特将聚焦分为“零聚焦”“内聚焦”“外聚焦”。 零聚焦是全知全能的叙事角度; 内聚焦就是作者自己参与叙事,通过主观感受和意识来呈现事物; 外聚焦则是一种客观的叙事,叙述者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动、 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涉及人物的动机、 目的、 思维和感情。 就生态写作而言,内聚焦型视角是作家比较看重的,原因在于作家得以调动感官,“教人们以五官去体验自然,用心去寻求一种与自然的最淳朴、 最直接的联系”[5]192。 可以说,第一人称内聚焦视点是作家生态意识最恰当的载体。 怀特在《重游缅湖》中也是通过视觉、 听觉、 嗅觉、 触觉等各种感官感受,全面构建起缅湖具有“宁静”之美的生态意象,有效地突出了自然内在的生命活力和欢愉。 不仅如此,作者也正是通过自身的主观感受来实现时空跨越并赋予作品更深远的意义,这篇散文的结尾作者写“雷暴过后一切重归平静,天光重现,希望再生”,在这个场景中,雷暴暂时击碎了永恒“宁静”的幻象。 自然界瞬息万变,人生起伏跌宕,生命则表现为一个新陈代谢、 循环往复的自然过程,完全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 人类只是自然生命的一种形式,个体也只是宇宙生命链条的一环,根本无法逃脱自然法则的制约。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在描写景物时,怀特的文字具有一种个性十足的音韵美,节奏和谐流畅,生动地再现了自然之美。 如文章末尾处对雷暴场景的描述: “最初是一种压抑和燥热的感觉,沉闷的氛围笼罩营地……后半晌……乌云密布,万籁俱寂,静得能听到生命的悸动。 随后,一阵微风轻刮,雷声隐隐逼来,系泊的船只突然侧身摆荡。 定音鼓敲响,小鼓敲响,跟着是大鼓和钹,噼啪作响的电光划破乌云,山上的众神龇牙咧嘴,兴奋地鼓噪。 接下来是一片沉寂,雨点不疾不徐地打在平静的湖面上,天光重现,希望再生,心情豁然开朗。”[3]97在英文原作中,作者中途放弃了完整的句式,先是用一系列简短的名词和分词短语制造出一种急促、 紧迫感,随后短语结构渐次加长,从稍加缓冲到归于平缓,直至彻底恢复常态。 仅此寥寥数语便将大自然发威前后的动态变化、 暴风雨的壮观气势及给人带来的情绪变化完全表达出来,作者在此将人类用语言构建自然原生态的能力发挥到了极致。 如评论家所称: “唯有把自己也融进环境,而不是把‘环境’当成身外之物来‘保护’,才可能有这样入微的观察,这样恳切的笔法。”[6]92
《重游缅湖》呈现了一种自然的积极文化建构方式,它以极具生态意识的文字建构起大自然的美好意象,正是怀特跨越时空界线对他的精神导师所做的回应。 作品通过生态意象的描绘、 生态环境的理想重构、 生态叙事技巧的运用,在文化价值选择上强化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试图引导人们找回在现代工业化发展进程中失去的生态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