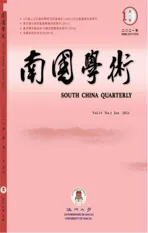移民時代的中國城市治理轉型
2021-12-28周大鳴
周大鳴
[關鍵詞] 國際移民 城市轉型 綜合治理
當今中國正在向現代化國家邁進,所經歷的轉型是整個世界潮流的一部分,即從單一的民族國家向移民國家轉變(儘管中國境內除漢族外,還有55個少數民族,但都是中華民族共同體的一員)。①周大鳴:“從地域社會向移民社會的轉變——中國城市轉型研究”,《社會學評論》6(2017):3—10。以往人們經常使用的西文詞彙“Nation/Nationality”,本義是指單一的民族和國家;而中國學術界在引入時,並沒有注意到這個詞的特殊性,所以,很多學者將“nationality”既用於中國的“國家”,也用於中國的“民族”。例如,中央民族大學曾一度被翻譯成“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這在語境上就容易引起他國人士的誤讀,感覺像是一個聯合國的大學。又如,國家民委也曾被翻譯成“National”,後來接受了人類學民族學專家的意見,改用“Ethnic”這樣一個族群的概念。其實,過去的歐洲原本也是單一民族國家狀態,現在已發生很多變化,歐盟最後一個宣佈進入移民國家的是德國(2005年)②宋全成:“外國人在德國的人口社會學分析”,《德國研究》3(2014):143。,主要標誌就是移民數量達到了該國總人口的10%左右。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看,中國目前正在經歷一場從地域文化到多元文化的轉變。造成這一轉變的根本因素,便是中國的城市已從地域性城市逐漸轉變爲移民性城市。
一
判定中國的城市正在從地域性城市轉變爲移民性城市,首先需要釐清中國地域文化的本質。長期以來,中國作爲一個統一的國家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但在國家內部,文化多樣性也長期存在,地域文化就是這種多樣性之一。所謂地域文化,是指在特定區域源遠流長、具有特色、傳承至今、能發揮作用的文化傳統。由於它是特定區域的生態、民俗、傳統習慣等的文明表現,在一定的地域範圍內形成並發展,從而带有地域色彩,具有獨特性。
中國地域文化的特徵,首先是語言,或者說方言、次方言。如在上海、天津、西安、武漢、廣州等城市的居民以使用某一種方言的人群爲主體。其次是地方性的飲食,地方的民間信仰、民間建築,獨特的地理環境,因移民因素所導致的地域文化。再次,受行政區劃的長期影響。從秦始皇時代開始,中國的郡縣制度被承襲下來,人們長期生存在這個地域,形成了文化認同,如人們所講的三晉文化、齊魯文化、湖湘文化、吳越文化、嶺南文化,其實都是一種地域性文化。中國的區域性差異最早可追溯至新石器時代,如黃河流域的仰韶文化、龍山文化,長江流域的大溪文化、良渚文化,遼河流域的紅山文化,珠江流域的石峽文化。從考古學的類型學上看,這些文化所出土器物的組合、形制都有着地域性特徵。以仰韶文化爲例,彩陶上面的魚面紋,是它最顯著的特徵,衹要出現,即可斷定。這些新石器時代所形成的文化特徵,成爲後來春秋時期諸侯國的基礎。
地域文化之所以形成,與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有關。在傳統文化裏,人們比較安於本鄉本土,不願意隨意搬遷,所謂“安土重遷”。這在《漢書• 元帝紀》裏就有記載:“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它強調了古代中國人對土地、親緣的依賴性。所以,在傳統的鄉土社會裏,人與土地是緊密嵌合在一起的——農民依附在土地上,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血緣與地緣的關係相互交叠,形成了在空間上的相對孤立與隔閡,形成了極具地方性的社區單位——一個個村落。以村落爲單位構成的鄉土社會,是一個有機的和有自身社會結構特徵、人際關係特徵、權力結構特點的等級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裏面,土地不僅是農民的主要生産資料,也是群體生活與認同的家鄉。因此,家族觀念極爲重要,文字無足輕重,人們依據差序格局劃分親疏遠近。這個就是社會學家費孝通概括的“鄉土中國”。③費孝通:“文字下鄉”,《鄉土中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所謂“鄉土中國”,便指中國的血緣與地緣相互交叠,形成這樣一個“鄉土”的社會。
中國“鄉土”社會的總體特徵就是地緣、血緣和姻緣。與血緣相連的,是一套宗法、宗族制度;與姻緣相連的,是一套親屬制度(如九族);與地緣相連的,是民間信仰制度。民間信仰是把血緣、姻緣、地緣加在一起所形成的一種聚落整合制度。①周大鳴:“廟社結合與中國鄉村社會整合”,《貴州民族大學學報》6(2014):19—25。在這樣一個地域文化基礎之上,形成了地域性的城市。古代城市的居民,多是以周邊農村的人爲主體;即使是近代的上海,居民也主要來自周邊的蘇南和浙江。所以,上海話以吳語爲基礎形成,衹是調子比蘇州話要重一點,由此形成了“滬語”方言群體。
地域城市除了有特色的方言、特色的飲食外,還會形成特色的建築。因爲建築與環境的影響密不可分,所以,每個區域的建築都會形成自己的特徵。例如,北方人蓋的房子,最重要的特徵是窗戶數量少,多數建築的北面一堵墻是封閉的,一個窗戶也沒有;顯然,這在南方不會出現。同樣在北方,一所住宅中的主人房,多是北面的正房;而在南方,靠南面、通風好的纔是主人房。由於中國歷史悠久,城市一旦形成,也會成爲一個區域的中心——既是區域的行政中心,也是區域的文化中心,它自然就影響到周邊的語言、習俗等。此外,嚴格的戶籍制度限制人們遷移,這也是地域文化得以長期存在的重要原因。
地域文化形成之後,大部分居民會形成認同。這種認同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産生了對自身所持文化的認同,另一方面會産生文化中心主義,認爲自身文化比他者的文化優越,並在此基礎上産生地域性歧視。在舊中國,地域性歧視不僅普遍存在,而且還具有層級性——在一個縣內部,這個鎮的人看不起那個鎮的人;在一個市內部,市區居民看不起縣裏人;在一個省裏面,省城居民看不起其他地方的人。而在省與省之間,也存在着地域文化的歧視鏈。
隨着時代的變遷,很多過去的地域文化已經悄然發生了改變。以中山大學爲例,在改革開放之初,各系的任課老師多數用粵語(廣東話)與學生交流,這就逼着外地學生學粵語,否則就無法正常學習。也有部分老師試圖用粵語的腔調說普通話,但學生們多半難以聽懂。現如今,這種情況已發生了本質的改變,在人類學系,真正意義上的廣東人衹剩下一位。所以,單從教師籍貫結構的變化,就可以看到一個城市的人口結構所發生的劇烈變化。
隨着新世紀移民時代的到来,中國人的跨市、跨省、跨國的遷徙量越來越大。根據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後改爲衛生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對外發佈的《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顯示,2011年,全國流動人口總量已接近2.3億,佔全國總人口的17%;2015年,全國流動人口總量爲2.47億;之後,流動人口數量雖有所下降,但總量一直不低於2.4億,其中1980年以後出生的新生代流動人口佔比已超過六成。②《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2)》(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13);《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2018)》(北京:中國人口出版社,2019)。。當然,有的城市如上海、北京對流動人口有較多限制,但是這兩个城市的流動人口比重也佔到了40%。而像深圳、東莞這樣的城市,外來流動人口大大超過有本地戶籍的居民人口。根據深圳市統計局網站公佈的2017年數據,管理人口2000萬人,常住人口1077萬人,其中有深圳戶籍的衹佔367萬人。這從一個側面顯示出,深圳的活力因素所在。如果再對比2000年與2010年的全國人口普查材料,還可以看到每個區域(東南地區、東北地區、中部地區、西部地區)的流動人口變化。例如,最初是東南地區的流動人口所佔比重最大,佔了總人口的16.8%。但到了2010年以後,流動人口發生了兩大變化:一是西部的流動人口增速超過了東部。在全國的每個區域,人口都開始向外流動。二是東北人口的流動性相對較低。它的淨遷出人口高於淨遷入人口,而且淨遷出人口的文化程度較高、年齡結構較低,即年輕的、有學歷的人口外遷。所以,東北地區經濟發展滯後、城市活力下降,與年輕的、有學歷的人口大量外遷有很大關係。③周大鳴:“移民與城市活力”,《學術研究》1(2018):45—51。
二
隨着中國城市從地域文化向移民文化的轉型,城市人口越來越龐大,群體構成越來越複雜,文化形態越來越具有多樣性,這就導致了以往的城市治理方式亟需作出調整乃至轉型。從文化角度而言,城市在轉型過程中大致會遭遇三方面問題:首先,移民在吸納當地城市文化的同時,也在輸出着來源地的文化,這不可避免地會帶來各種文化之間的碰撞。其次,大量的文化傳播外溢所帶來的正負效應,是城市轉型中不可忽視的因素。最後,在轉型過程中,還會出現一些原住民與外來移民(包括海外移民)互不適應的文化心理問題。
如果從治理視角觀察,城市轉型將會面臨四個方面的問題:其一,地域性歧視問題。最近,筆者作了一個關於地域與行業的實地調查。其中的一個問題是:爲什麽“滴滴打車”在廣州比在北京、上海發展的障礙少?經調查發現,主要原因是在過去很長時間裏,廣州開出租車的不是本地人,最早是湖南人,後來是河南人。所以,“滴滴打車”進入廣州市場時,犧牲的不是本地人的利益,這樣的一套商業運作方式也就容易實行。而在北京,出租車司機多數是本地人,尤其是來自本地郊區,故一旦觸及出租車行業的根本利益,這樣一套東西就不容易實行下去,這是與地域文化有關聯的一系列産物。過去,地域歧視對民衆的現實生活影響並不大,因爲大家生活在相對區隔的環境中,但現在生活環境變了,當不同地域的人要生活在一起時,就會出現問題。
其二,傳統道德倫理的弱化問題。隨着改革開放的持續深化,也帶來了從集體主義到個人主義的轉變;或者說,從群體取向到個體取向的轉變。這樣的轉變過程,有人說是“原子化”“碎片化”,閻雲翔則認爲是中國人的“個人化”,並且加了一個定語,叫做“無公德的個人化”。①閻雲翔:《私人生活的變革——一個村莊裏的愛情家庭與親密關係(1949—1999)》(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 2005),龔小夏 譯。也就是說,在中國急劇發展的過程中,在個人性格得到張揚的同時,公共道德並沒有相應建立起來;在傳統道德倫理弱化的同時,新的核心價值觀並沒有及時建立起來。管理層也意識到此問題的存在,自2012年以來不斷倡導“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但怎樣把傳統道德倫理融入到人們的日常生活、使之成爲人們的行爲規範,依然是一個有待解決的問題。費孝通所講的熟人社會,即鄰里之間非常熟悉,如果延伸到地域城市來看,顯然還是一種熟人社會、鄉村社會的延續。一些研究者照搬美國芝加哥學派的城市理論,把中國城市當做陌生人社會的模式來分析,這種思路是典型的食洋不化。中國過去的地域城市通過單位制整合居民,也是把鄉村的熟人社會放到城市里的結果。在一個單位裏,大家都非常熟悉,可能一家人都在單位內工作,即使兩個人之間不直接認識,但在一個圈子裏還是有交集的,這是另一種熟人社會的模式。隨着中國真正開始進入一個以陌生人爲主的社會,就與過去的地域城市出現了巨大差別。當中國真正進入一種陌生人社會狀態時,由於缺乏一種公共道德規範,進而出現一系列新問題,就會使法律變得極爲重要,但任何事情都要依靠法律,又會導致過髙的治理成本。所以,陌生人社會的治理良策就是治理轉型。②周大鳴、陳世明:“城市轉型與社會治理”,《公共行政評論》5(2017):218—219。
其三,複雜的人際關係問題。現在社會上有各種各樣的職業,形成各種地域的人群、不同民族的人群、不同信仰的人群,以此又形成無數種圈子,基於這些圈子的人際關係也比過去更複雜。所以,關於社會網絡的研究在當下的社會學研究中佔據重要位置。例如,各種形式、類型的傳銷活動,就是利用這種複雜社會網絡騙取財物的一個突出問題。因此,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我們如何在此背景下進行社會治理?
其四,族群關係的複雜性問題。不同人群在一起接觸,可能産生不同的變化,會有多種情況出現:有可能是融合、同化,也可能是對抗、分離。從國家對族群政策的思路來看,堅持倡導“中華民族是一個命運共同體”,各個民族之間要加強交流、交往、交融(“三交”),共享美好的精神家園。但在實踐層面,一些政策執行者的理解存在偏差,往往在實行過程中採取區隔的、分離的簡單化手段,這就很容易導致衝突。隨着全球化的加速,中國已成爲移民目標國,中國向移民城市與移民國家的轉化指日可待。在這一情勢下,人群的國際流動所帶來的族群複雜性已日見端倪。中國人對數千萬華僑在海外工作生活具有一種強烈的自豪感,但與此同時,對其他國家與族群遷入中國則心存疑慮,內心充滿排斥。假設有一天國家之間互相驅逐,被趕回來的華人大概要比從中國趕走的外國人還要多。
在北京、上海、深圳、廣州這些世界性的城市中,外國人的社區開始不斷涌現。例如,在北京,望京新城是著名的韓國人居住區,長富宮形成日本人的聚居區。又如,在廣州,早年日本人、韓國人來得比非洲人要多。日本人來得多,是因爲所有的日系汽車都在廣州設廠,跟着各公司來廣州的技術人員數量很多;韓國人來得多,也是因爲有大量的韓國企業如“三星電子”進入中國。過去人們想當然地以爲,這些日本人、韓國人都是白領人群,我們後來調查發現,到珠江三角洲的製造業當技術工人的也不少。以“美的集團”爲例,雇傭了大量來自日本、韓國的藍領技術工人,主要原因是中國的模具鉗工、裝配鉗工經驗積累不足,水平比不上日本、韓國,即使是一綫的模具鉗工、裝配鉗工,在生産能力方面也存在差距。①周大鳴、楊小柳:“淺層融入與深度區隔:廣州韓國人的文化適應”,《民族研究》2(2014):124。過去人們對優質的海外技工在珠江三角洲產業的重要性認識不足,忽略的原因是日本人、韓國人與中國人的外貌、皮膚差不多。此外,來自越南的務工人員也是一個龐大的群體。上述族群因爲與中國人的外表沒有明顯差異,所以沒有引起媒體和大衆的關注。
三
受傳統思維方式的影響,人們對流動人口、移民的負面效應關注較多,從正面角度審視較少。所以,流動人口不僅在改革開放前被稱爲“盲流”,即使在改革開放初期,包括農民工在內,也被稱爲“盲流”,認爲他們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這種認知,近些年來已大有改觀,農民工群體的重要性越來越被城市居民所認識。在這一觀念轉變過程中,國外媒體也給予了很大關注,《時代週刊》2009年最後一期封面上出現的就是中國農民工群體。他們認爲,中國能夠持續三十年增長,并且能夠保持8%的增長率,與這群任勞任怨的工人默默做出的貢獻密不可分,因此將中國的農民工評爲年度人物中唯一上榜群體。當然,殘餘印象的徹底消除不是一朝一夕之事,某些城市的管理者依舊陷於過時的思維不能自拔,依舊將農民工看成是底層的、可以隨時排斥的群體;然而,由於外來農民工所從事的各種行業已成爲城市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旦將其清理出去,城市的日常運轉勢必難以持續。
從世界歷史看,美國能夠迅速崛起,超過大英帝國,與它持續的、規模化的移民大有關係。大量的外來移民,一是促進了中西部農業開發,二是爲美國的工業和基礎設施建設提供了大批廉價勞動力,三是帶來先進的技術與豐厚的資金。所以,外來移民在美國從農業國向工業國轉變、從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中發揮了積極而重要的作用。同時,移民也參與城市本身的構建,對美國城市社會的結構産生影響,也直接對美國城市文化風貌的塑造發揮了積極作用。所以,美國的太平洋西岸與大西洋東岸的文化差異很大,這與移民的來源地不同有關。
具體到中國而言,珠江三角洲地區的發展是最好的例子。改革開放以來,珠三角區域能夠先行一步,迅速完成工業化和城市化,直接獲益於龐大的外來人口。因爲,它最初是由勞動力密集型産業推動發展起來。一方面,外來人口提供了年輕強壯的勞動力;另一方面,大量的“離鄉不離土”的人給珠三角本地人種地,成爲“代耕農”。②黃志輝:“自我生産政體:‘代耕農’及其‘近閾限式耕作’”,《開放時代》12(2010):24—40。而本地農民在1980年代就不從事農業生産,進入到工廠裏打工。隨着工廠的增多、規模的擴大,本地人已滿足不了需求量,外地農民也開始到工廠裏打工,這就是“農民工”一詞的由來——以農民的身份到工廠打工。除了進入工廠、各類服務業外,還有一些分散在建築工地、礦山、餐飲、保姆行業等,這些人都未被正式機構雇傭,故稱之爲“散工”。③周大鳴、周建新:“‘自由的都市邊緣人’——東南沿海散工研究(一)”,《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8(2006):8—17。
由於外來移民起到了人力、物力、財力、信息的集聚效應,所以,哪個城市的移民越多,它的發展便越快,活力便越強。珠三角區域正是得益於移民的大量涌入,直接推動了農業現代化和工業化的轉型。在過去四十年裏,珠三角各地都進行過從農業村向工業村的轉變,然後再經歷從工業村向城市社區的轉變,所以很快地實現了城市化。中國現在有省級市、地級市、縣級市,接下來還要發展鎮級市。2014年7月,國家十一個部委聯合下發通知,試點“镇级市”,珠三角有四個鎮入列。像東莞市虎門鎮,常住人口63.8萬,其中戶籍人口13.33萬、外來人口約60萬。這還不是高峰期的數字,高峰期超過100萬人。①周大鳴、鄭夢娜:“從‘二元社區’到社區融合——以東莞虎門太平村爲例”,《青年探索》5(2019):48—60。大量移民的進入,先是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化,繼而促進文化轉型,最後導致了城市的轉型。
近年來,關於移民價值觀問題出現很大爭議,主要有多元文化主義與同化論兩種觀點。像加拿大、美國、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國,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強調文化多元主義。但特朗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後,文化強制同化的論調又開始佔據上風,不斷發生的驅趕非法移民、有色人種事件就代表了這種取向。過去是強制同化,後來強調文化多元,現在又流行文化同化的理論,這樣一種循環究竟是螺旋式進步還是退步到原點,還有待進一步觀察。
四
儘管一個城市的快速發展與外來移民的大量湧入有着直接關聯,但城市原住民對新移民所產生的疑懼、排斥心理也客觀存在。2005年發生的巴黎騷亂,2011年發生的倫敦騷亂,都是因爲新移民與原有居民發生衝突而產生。而在中國的廣州,社會大衆及媒體關注更多的是來自非洲的黑人群居問題。
在過去討論非洲人問題時,人們有一個常識性偏差,即總是將所有非洲人看做一個整體。然而,非洲不論是國家、民族、語言還是宗教信仰,都是世界上最爲複雜的區域;即使存在一個非盟,它也決不是一個整體。在筆者參與的一項研究中,曾經做過一百三十個人的訪談,用滾雪球的抽樣方式,一個人最多滾三個。訪談結果表明,這一百三十個人來自非洲三十多個國家,這足以證明在華非洲人的多樣性。
非洲人最早來到廣州是因爲參加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簡稱廣交會)的緣故。廣交會從1957年開始,每年春秋兩季在廣州舉辦,是中國層次最高、規模最大、到會採購商最多且分佈國別地區最廣的綜合性國際貿易盛會。早期廣交會爲了體現參與國家的廣泛性、惠及非洲朋友,資助了許多非洲國家參加。這樣一代代人下來,來廣州做生意也成爲一種習慣,所以,在廣州活動的非洲人比較多。
在廣州的非洲人大體分爲三類:一類是非洲的僑民,本身有充足的資本,持有長期的商務簽證,他們通過正式渠道與中國廠商合作。第二類是獨立經商的客戶,經常在香港和東南亞國家有獨立的業務,通過短期的商務簽證或者旅遊簽證進入中國。第三類是爲數衆多的小客商,數量比較龐大。他們有點像中國早期的背包客,去俄羅斯等地方“練攤”,類似個體的商販。另外,還有逐年增多的留學生群體。
如果將這些非洲人按照移民群體分類的話,他們可分爲經營型移民、智力型移民兩大類。前者多是改革開放前就來到中國的非洲人,他們能夠來到中國做生意,是因爲他們的受教育水平普遍高於中國的貿易夥伴。而後者多是改革開放以後進入中國的非洲人,他們多是獨立的客商和小客商。所以,前者多是通過中間人的渠道與中國人接觸,後者則是繞過中間人直接與中國人接觸。非洲客商之所以能夠與中國廠商建立起信任關係,全靠遊走於兩者之間的中介群體。因此,在廣州的非洲人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做中介商。但他們經常遇到兩個問題,一是出租車拒載,二是簽證延期。從後者來說,目前管理部門對大量非洲人的湧入持審慎態度,想取得連續簽證較難。爲了滯留,這些中介商採取了兩種對策:一是不再簽證,成爲非法移民;二是花一筆錢,交給中介公司去辦簽證。這反映出,在政令執行過程中存在漏洞,容易讓人誤解爲,花錢就可以辦到簽證。其實,有一個特殊群體容易獲得簽證,這就是大量的非洲留學生。由於他們喜歡廣州,又有語言上的優勢,所以,他們不按照規定的時間修滿學分畢業。因爲,如果一旦畢業,那就意味着要離開廣州,所以就乾脆不畢業,永遠保持一個學籍,這樣可以在廣州做生意,或者到飯店、工廠去打工掙錢。
需要說明的是,在新世紀的移民時代,既要看到有大量非洲人在中國做生意,也要看到還有大量中國人在非洲做生意。伴隨着非洲人對中國國內市場的熟悉度增高,越來越多客商的採購點會從香港到廣州、再從廣州向中國內地生産廠商轉變。同時,在華的非洲留學生,畢業後留下來從事各種貿易活動,也會對非洲未來的工業化、城市化起到重要的影響和作用,他們在用自身行動實踐着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從歷史上看,廣州與“一帶一路”國家和地區早就有着密切關聯。從更廣闊的空間來看,廣州乃至粵港澳大灣區,未來會成爲中非貿易環境中重要的貿易、製造、金融節點,這些非洲人通過廣州將中國與非洲連接起來。作爲中國居民,在享受多元文化帶來的豐富和開放之時,也要承擔傳統文化、地域文化削弱所造成的不適。由於社會融合是牽涉到宏觀政策和微觀政策兩個層面的問題,也是轉型中的城市和諧發展的核心,所以,不同地域、不同族群、不同膚色的人之間的社會融合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總之,中國成爲移民目標國指日可待,從移民城市向移民國家的轉化也指日可待。但是,移民不可能是單向的,不能衹是自己可以移到別的國家,而拒絕別的國家的人移到自己的國家。外國人來中國,就跟中國人去國外是一樣的。中國人建立唐人街,是用一種相對區隔的適應方式來適應新的環境;外國人也一樣,也會以一種區隔的方式在某些城市相對集中居住,形成自己的日常生活、就餐等可以消費的街區。當地域性城市轉變爲移民性城市後,治理思路轉型的核心要素就在於,健全相應的制度和法規,培養具有專業背景的管理人員,培養民衆多元文化交流的習慣與能力。由於現實的變化速度大大快於法律法規的制定,如何處理和管理國際移民已是一個非常緊迫的問題。廣州已率先成立了外國人服務管理中心,並且延伸到了一百多個街道。這是地方政府自發的行爲,處於合法與非法之間,但不進行管理是不行的,一點小事就可能演變成大的國際問題。因爲,在全球化的互聯網時代,任何一個地方的小事情都有可能産生蝴蝶效應,變成一個大事件。對於學術界來說,如何讓國人樹立一種文化多元的理念、尊重他者文化、建立一個文化多元的城市與國家,任重而道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