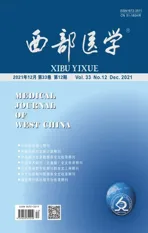非药物治疗肺动脉高压研究进展*
2021-12-21杨红综述金家贵吴奇审校
杨红 综述 金家贵,2 吴奇,2 审校
(1.成都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四川 成都 610500;2.成都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核工业四一六医院,四川 成都 610057)
肺动脉高压(Pulmonary hypertension,PH)是一类肺血管持续收缩及重构,导致肺血管阻力进行性增高,并最终导致不同程度右心功能衰竭的疾病。目前最新诊断金标准为海平面状态下、静息时,右心导管测量肺动脉平均压(mean pulmonary artery pressure,mPAP)≥25 mmHg(1 mmHg=0.133kPa)。2018年2月在法国尼斯召开的第6届世界PH会议再次更新了PH的临床分类,由动脉性肺动脉高压、左心疾病所致肺动脉高压、肺部疾病和/或缺氧所致肺动脉高压、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hronic thromboembolic pulmonary hypertension,CTEPH)及不明或多种致病因素所致肺动脉高压五大类构成[1]。
我国PH最常见病因为先天性心脏病,其次为特发性PH和结缔组织病相关PH[2],一旦确诊断PH,其5年生存率为20.8%。近年来随着靶向药物的临床应用及治疗策略的不断优化,特发性PH的3年生存率可达到75.1%,PH患者5年的生存率从约20%提高到50%以上,基本达到西方发达国家水平[2-3],但仍有部分患者长期预后不理想,且第二、三类PH缺乏靶向药物治疗的循证医学支持。此外,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及对PH机制的深入研究,针对药物治疗的局限性[4],临床上提出了非药物治疗PH的方法。研究[5]表明非药物治疗方法可治愈部分PH患者,也为难治性PH患者提供新的治疗选择。
1 以介入为基础的治疗方法
1.1 房间隔造瘘术(Atrial septostomy,AS) 20世纪80年代后,多项研究[6-7]发现存在心内分流的重度PH患者生存率优于无心内分流的PH患者,提示可通过房间隔造口使血液右向左分流的治疗策略来改善PH患者的右心功能及缓解体循环静脉淤血等。1983年Rich和Lam首次报道了AS姑息治疗难治性原发性PH患者[8]。但由于最初的AS使用导管扩张房间隔穿刺术,其不良反应较多,随后改进为逐级球囊扩张房间隔造口术(graded balloon atrial septostomy,BAS)。Chiu等[9]对46例PH行BAS患者回顾性分析,结果示术后1、5年无肺移植和无重复BAS生存率分别为61%、32%。Khan等[10]系统分析BAS术对晚期PH患者的影响,发现术后(48 h)、短期(≤30天)和长期(>30天,平均随访46.5月)死亡率分别为4.8%、14.6%和37.7%,提示BAS在重度PH患者中是安全有效的。但上述两种方法均无法精确控制房间交通的大小,可造成部分患者术后出现严重的低氧血症及房间交通缩小或自发闭合[11]。Yan等[12]采用导管射频消融进行AS动物实验研究,结果示射频消融组术后2个月房间交通大小均稳定,表明射频消融可防止房间隔造瘘口的自发闭合。由于射频能量可减少对周围组织的损伤,从而降低并发症的发生率,并能精确地控制房间隔开口的大小,该技术有望成为AS新策略,但该技术现处于动物实验阶段,其临床实用性有待进一步研究明确。
1.2 球囊血管扩张术或肺动脉支架置入术 对于由肺动脉狭窄(pulmonary artery stenosis,PAS)导致的PH的治疗一直是临床上比较棘手的问题,尤其是远端分支肺动脉狭窄常常无法行外科矫治。随着血管介入技术的开展,肺动脉球囊扩张术(balloon pulmonary angioplasty,BPA)及肺动脉支架植入术成为治疗PAS所致PH患者的重要治疗方法[13]。此外,BPA也适用于不能手术的CTEPH患者及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pulmonary thromboendarterectomy,PTE)后残留(20%)或复发的PH患者[14]。Siennicka等[15]随访160名CTEPH患者,发现BPA+内科治疗的患者的生存率明显优于单用PTE或内科治疗的患者,2年生存率为92%。尽管如此,单纯BPA在临床应用中仍存在一定局限性。Gu等[16]对在2012~2016年间接受BPA治疗的40名患儿进行回顾性分析,发现BPA治疗PAS成功率仅为40.0%~52.4%;此外,并表明BPA可导致部分或全部血管内膜和中层撕裂,最终血管发生重塑,这可能是导致BPA成功率低的原因。针对单纯BPA的不足,朱家德等[17]对PTE后出现进展性PH合并心功能改善不佳的患者进行序贯式BPA治疗,1年后随访发现mPAP从38(29~47) mmHg下降至29(25~39) mmHg(P=0.043),心功能(NYHA)Ⅲ~Ⅳ级均改善为Ⅰ~Ⅱ级(P<0.05)。此外,Kusa等[18]采用切开球囊血管成形术(cutting balloon angioplasty,CBA)治疗儿童PAS的研究发现,肺动脉近端收缩压从(74.33±20.4) mmHg降至(55±16.7) mmHg(P<0.001),远端收缩压从(19.8±3.82) mm Hg增加到(30.3±13.3) mmHg(P=0.04);1年后右心导管检查提示血管充分扩张,右心室压力降低。Bergersen等[19]进行一项PAS患者随机研究,发现采用高压BPA治疗PH成功率为52.4%,55%患者的狭窄血管对BPA有抵抗作用,使用高压BPA治疗过程中改用CBA,而CBA治疗成功率可达85.1%。因此,CBA是治疗PAS安全有效的选择,尤其是对BPA有抵抗力的PAS患者。
近年来,随着经皮血管内支架置入术在临床上广泛应用,临床研究发现支架植入术后,患者的近期临床症状、6分钟步行试验和狭窄区域的血管口径明显改善[20]。但有研究[21-22]发现,在肺动脉支架植入术治疗儿童PAS后随访过程中,支架发生变形、移位及支架内血栓等并发症,因此,其临床有效性及安全性仍有待深入研究。随后有学者为避免普通支架的弊端提出生物可吸收支架植入的治疗方法,由于其能够适应患者的成长和肺动脉狭窄,生物可吸收支架置入为PAS所致PH患者的治疗提供新的选择[23]。但目前该技术常处于研究阶段,其临床实用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明确。
1.3 先心病相关性肺动脉高压(Congenital heart disease associated pulmonary hypertension,CHD-PH)的封堵术 先天性心脏病(CHD)是我国引起PH常见原因之一,CHD-PH发生率约占CHD总数的10%[24];我国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就诊的CHD-PH患者中PH占39.8%[25],现主要根治方法为内科经皮导管介入封堵术,其次是外科修补术。早期通过介入封堵术可降低或治愈CHD-PH,避免高压力对肺动脉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形成阻力型PH[26]。重度CHD-PH原则上失去封堵术指征,但有学者针对此类患者提出了带孔封堵器治疗方案。朱鲜阳[27]对带孔房缺封堵器治疗重度CHD-PH患者的研究发现,封堵术后mPAP从(56.43±5.13) mmHg降至(43.71±8.64) mmHg,在长达5年的随访中,所有患者心功能均得到明显改善,肺动脉压力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未出现左心功能不全表现,可见带孔房缺封堵术不仅可降低肺动脉压力,而且遗留的小孔可缓解右心压力负荷。目前置入此类封堵伞的病例较少,远期疗效有待进一步观察,此种方法的开展可能为重度CHD-PH的患者提供治疗机会。
目前临床上常用X线引导下行介入封堵术,不可避免会对患者及术者造成放射线损伤,同时其对患有PH的孕妇及婴幼儿的临床应用存在一定限制性。近年来,已有大量的经胸超声或经食管超声引导下行CHD封堵术的临床报道[28],并长期随访表明其安全有效[29]。超声引导下CHD封堵术无需使用昂贵的大型造影设备,而且避免了放射线对患者及术者可能造成的伤害,具有广泛的临床推广价值。
1.4 肺动脉去神经术(Pulmonary artery denervation,PADN)
PADN治疗PH原理同肾交感射频消融术治疗恶性高血压。研究[30]发现肺动脉交感神经多发于分叉部和肺干后部,通过导管消融切断分叉部位的交感神经后,肺动脉压力明显降低,并临床症状改善。Zhang等[31]进行PADN-5研究评估PADN治疗PH疗效,PADN组与西地那非+假PADN组比较,结果显示PADN组6 min步行距离平均增加83 m,对照组平均增加15 m,PADN组临床恶化率较低(16.7%vs40%,P=0.014)。由于人类肺动脉的神经支配主要是交感神经(71%),其中>40%的神经分布深度>4 mm[32],PADN可能达不到明显的治疗效果。Rothman等[33]在超声PADN的临床前期试验中证实其能量可传达至人类交感神经的深度,不伤及血管内膜及中层,并能有效降低肺动脉压力。PADN及超声PADN对药物治疗不佳的PH患者的临床试验中取得专家认可,为PH患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34]。不过该技术具体应用范围、疗效及安全性仍有待进一步证实。
2 以外科手术为基础的治疗方法
2.1 肺动脉血栓内膜剥脱术(PTE) CTEPH主要由于急性大块血栓或复发性血栓栓塞肺动脉致肺血管截面积堵塞50%以上引起慢性持续性PH,最终进展致右心衰竭,甚至死亡。CTEPH是常见的潜在致命性疾病,病死率为20%~35%[35]。PTE是治疗CTEPH的首选方法,并能立即纠正大多数CTEPH患者的血流动力学参数及改善心功能,1年生存率可达91.2%[36]。Quadery等[37]研究发现,接受PTE的CTEPH患者的存活率高于那些符合但拒绝手术的患者(55%)(P<0.001),并血流动力学指标及症状得到改善。50%~60%的CTEPH患者可以通过PTE治愈[38]。因此,符合条件的患者强烈支持考虑PTE治疗。但仍有40%多的CTEPH患者不符合PTE条件和大约20%的患者在PTE后有持续性PH[39],这种可通过BPA[17]及PADN[34]等治疗改善。目前,PTE在临床上较为成熟,但其并发症较多,控制术后合并症以及术后早期的不良事件是提高患者术后生活质量的决定因素[40]。
2.2 经胸肺动脉去神经术(Transthoracic pulmonary artery denervation,TPADN) 由于PADN治疗效果有限,Huang等[41]对PH大鼠进行TPADN处理,与假手术组相比,TPADN组mPAP降低(P<0.05),右心室及肺血管重构减轻,右心功能改善。此外,TPADN还可抑制交感神经系统和肾素-血管紧张素-醛固酮系统的神经激素过度激活,调节局部组织中神经激素受体的异常表达和信号转导,从而减缓PH进展。TPADN相关研究较少,其有效性及安全性有待进一步临床研究验证。
2.3 Potts分流术(Potts shunt,PS) 有研究[6,42]发现合并艾森门格综合征的重度PH患者较单纯重度PH患者的预期寿命长且血液动力学更稳定,其原因在于重度PH导致的右心负荷增加可以通过左右心系统之间的异常通道得到一定程度缓解,从而延缓了右心衰竭的进程。PS是连通降主动脉和左肺动脉使血液右向左分流来降低肺动脉压力的一种外科治疗方法。与AS相比,PS可以避免缺氧的血液对大脑和冠状动脉循环的影响;此外,对于任何mPAP级别,PS对分流大小的影响要比AS小得多[43]。
2004年首次报道[44]PS成功治疗两名难治性PH患儿,随后一项多中心研究[45]表明,姑息性PS可延长重度难治性PH患儿的生存期,并改善其心功能。Aggarwal等[46]对2013~2017年行PS的12名PH患儿进行随访及评估,结果表明PS后右心室收缩功能改善(P=0.03),右心室后负荷减少(P<0.01),可见PS可改善大多数PH患者的心功能和提高无移植存活率。有研究[47]支持姑息性PS作为重症特发性PH患儿肺移植的新选择。尽管如此,对于重度难治性PH的患者,开胸手术或胸骨切开术的风险以及在手术中进行PS的风险是很大的,因此有学者提出经导管Potts分流术(transcatheter Potts shunt,TPS)治疗重度PH伴右心衰竭患者的策略。2013年,Esch等[48]首次报道了TPS治疗4例重度PH患者的临床研究,其中有2名中期幸存者,症状改善且无晚期并发症,可见TPS治疗重度PH是可行的。近年来,研究[49]发现TPS可改善重度特发性PH患儿的症状和心功能,并作为外科PS可靠的代替疗法,已应用于重度PH的大龄儿童[50]。
由于PS/TPS血流是双向的,且行PS成年患者死亡率可能远超过儿童,这可能与双向分流导致外周供血量减少有关,随后有学者提出改良Potts分流术(modified Potts shunt,MPS)。MPS在重度PH时允许右向左分流,降低肺动脉压从而改善右心功能,当肺动脉压力低于体循环压力时可以防止左向右分流进入肺动脉。Keogh等[51]应用MPS治疗伴反复晕厥的重度PH患者,发现MPS术后主动脉与肺动脉之间压力立即达到平衡状态、晕厥消失,随访中发现右心室大小及功能逐渐恢复到完全正常状态。MPS可确保上半身的氧饱和度及动态改善右心功能,从而提高运动耐力并减少晕厥和心血管衰竭的风险。2017年,Salna等[52]报道MPS成功治疗重度特发性PH成人患者,该技术对难治性PH患者可被视为目的疗法或通往移植的桥梁。
2.4 单向活瓣补片术(Unidirectional valve patch,UVP) 先天性心脏间隔缺损合并PH双向分流患者常伴有不同程度的心功能受损及肺血管病变,直接修补术后易出现肺动脉高压危象、急性右心衰竭等并发症,临床上处理非常棘手。随着心血管外科技术的进步,根据卵圆孔原理设计的UVP应用于间隔缺损合并重度PH双向分流的矫治手术逐渐开展起来[53]。早在1995年Zhou等[54]通过UVP治疗24例先天性心脏间隔缺损合并重度PH患者,术后死亡2例,中期随访无死亡病例,mPAP从(80±12) mmHg降至(56±18) mmHg,肺动脉压/体动脉压比值由(1.1±0.1) mmHg降至(0.7±0.1) mmHg;在术后随访中,症状和运动耐量均有显著改善。随后Talwar等[55]采用UVP治疗室间隔缺损(VSD)伴重度PH双向分流患者,发现术后mPAP明显下降,并且无患者出现重度PH。此外,赵玉彪等[56]在房间隔缺损(ASD)合并重度PH患者中采用UVP技术,发现UVP治疗ASD伴PH总有效率提高(P<0.05);UVP组术后并发症发生率降低(P<0.05)。UVP可有效改善VSD/ASD合并PH双向分流患者的肺动脉压力及症状,具有极大的推广价值。但也有研究[57]发现UVP不利于VSD合并重度PH患者的早期和长期生存。由于关于该技术的研究报道并不是很多,仍有待进一步研究其疗效及预后。
2.5 肺移植(Lung transplantation,LT)或心肺联合移植(Heart and Lung transplantation,HLT) 目前主要移植方式有单肺移植、双肺移植及心肺联合移植。而选择移植方式术前需严格评估患者心功能,对于严重PH患者,如果心功能正常,可以进行单纯LT。对于晚期PH患者及药物治疗无效的患者来说,LT可能是唯一有效的治疗方式[58]。根据世界心肺移植协议的数据显示PH是HLT的手术适应证[59]。严重PH伴随严重的右心衰竭或左心衰竭患者需行HLT,此时若行单纯LT,右心功能不一定会恢复,对移植后的双肺功能产生不可逆的损害。上海胸科医院2017年报道LT的1、3和5年生存率分别为60%、50%和41%[60]。Brouckaert等[61]进行一项为期24年的单中心回顾性研究,PH患者行LT术后5、10年生存率分别为70%、47%,而PH患者行HLT术后5、10年生存率分别为61%、48%。与LT相比,PH患者HLT后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较低,复杂的CHD患者除外。LT仍然是我们治疗所有形式的毛细血管前PH的首选方法。
3 干细胞移植治疗
近年来,干细胞移植、基因治疗等再生医学技术在血管生成及血管重塑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并成为了治疗PH新型方式。国外学者在野百合碱诱导PH的动物实验中发现,移植自体或同系骨髓来源的内皮祖细胞(endothelial progenitor cells,EPCs)可以显著降低肺动脉压力,甚至有的可以达到逆转PH的疗效[62]。关于内皮型一氧化氮合成酶的血液生长内皮细胞[63]、骨髓间充质干细胞[64]治疗PH的研究取得一定的进展。最近Suen等[65]进行系统评价44项关于再生细胞治疗PH实验模型的动物研究发现,再生细胞治疗可降低右室压(Smd 2.10;95%CI:2.59~1.60)、mPAP (Smd 2.16;95%CI:2.97~1.35)和右心室/左心室+室间隔重量比(Smd 1.31;95%CI:1.64~0.97)。国内外均有学者进行小样本EPCs移植治疗PH的临床试验,提示EPCs移植可改善大部分PH患者血流动力学及运动耐量[66]。由于干细胞移植可修复和替代损伤的内皮细胞,并参与血管重塑,防止PH进展,可将成为治疗PH的一种新方法。目前该技术主要处于动物基础试验,其需要临床大样本量验证其安全性、可行性等。
4 肺康复(Pulmonary rehabilitation,PR)及心肺运动试验
近年来,以运动训练为主的康复治疗日益受到重视,欧洲心脏病学会(ESC)2015年肺高血压指南即建议PH患者可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进行康复锻炼。研究[67]表明经适度运动和康复训练,PH患者的运动耐力有部分提高,心肺功能整体状况水平及生活质量出现改善。但目前国内对PH患者运动康复的研究较少。然而,早在20世纪中后期,国外的呼吸康复就广泛应用呼吸疾病领域,尤其美国目前在PR领域的研究已经逐步走向稳定发展的道路。Koudstaal等[68]研究显示PR可明显改善PH患者的运动耐量及生活质量。王天骄[69]对中美肺康复文献进行综述发现,治疗PH除了使用特异性药物外,PR干预对改善PH患者的生活质量和运动耐量有明显帮助。近年来PR被推荐为PH管理计划的一部分,但是目前国内PR对PH患者的治疗及预后研究仍是空白区。
心肺运动试验是通过定量检测气体的交换进而同步评估人体呼吸、循环及代谢等系统在静息及持续运动下的功能状态,现广泛应用于疾病的诊断、鉴别、术前风险评估以及心衰严重程度分级等,对评价PH的病情严重程度、疗效及预后等具有重要意义[70]。但在既往研究中,心肺运动试验评估经靶向药物治疗后PH患者的心肺功能状况研究较少。
5 小结
PH是一组严重的进行性肺动脉重塑性疾病,病因机制复杂,且致残致死率高。近年来随着靶向药物的合理运用和不断更新,仅改善轻中度患者的症状及为重度PH患者过渡至手术治疗,但不能治愈PH。伴随影像学的发展,各种非药物治疗方式也在不断的改进和发展,非药物治疗(尤其是干细胞移植治疗及PR治疗)PH是比较前沿的技术,有待更深入的研究,其将为各种PH患者带来崭新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