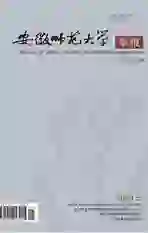道教与隋末唐初的政治
2021-09-14周奇
周奇
关键词:道教;谶言;隋末唐初;政治;合法性
摘 要:隋末天下大乱,道教在向各种势力兜售谶言,也对李唐势力夺取政权建立王朝出力甚多。李唐兴起利用李氏当王的谶言来应谶,建立政权后冒认老子为先祖,李唐王朝利用谶言本质为神道设教。李唐王朝与道教合谋制造谶言并利用道教谶言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同时也借助道教无为之教的思想资源来消除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道教在唐初的政治介入并不是屈服于国家的过程,而是上层贵族道教影响唐代国家治理之道的成功实践。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1-2435(2021)05-0061-08
Taoism and Politics in the Late Sui and Early Tang Dynasties
ZHOU Qi (Academic Monthly Magazine, Shanghai 200020, China)
Key words: Taoism; prophecy; from the late Sui dynasty to the early Tang dynasty; politics; legitimacy
Abstract: At the end of the Sui dynasty, the world was in chaos. Taoism peddled prophesy to all kinds of forces and also contributed a lot to Li Tangs seizing power and establishing a dynasty. Li Tang Dynasty began to use the prophecy of Li as the king to answer the prophecy.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regime, Li Tang Dynasty pretended to recognize Lao Tzu as their forefather, and they used the nature of prophecy to set up religion for Shinto. The Li Tang Dynasty conspired with Taoism to create prophecy and used it to enhance the legitimacy of the regime. Meanwhile, it also made use of the ideological resources of Taoism to eliminate the legitimacy crisis of the regime. The political intervention of Taoism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was not a process of submitting to the state, but the successful practice of the upper aristocratic Taoism influencing the way of state governance in the Tang dynasty.
——————————————————————————————————————————
一、道教与国家关系的演变
道教在历史上有着复杂的面相,从最初的道家方术到道教,经历了很多演变。东汉时期,太平道就是以辅助汉室的面貌出现,[1]与政权的关系不是东汉后期那样的紧张对抗的。二者关系的演变到后来才完全发生了质变。这时出现了仿效政府与军队的形式来管理信仰者的,太平道的“三十六方”组织与“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的军队官员似的称号,五斗米道的“二十四治”组织与“师君”“祭酒”“鬼卒”称号等等,这些教团组织方式,既是现实政权的仿效,也是對想象中天上神界的模拟,《太平经钞》里说,天上“一师四辅”,“从属三万六千人,部领三十六万,人民则十百千万亿倍也”。万绳楠曾经推测,太平道就是效法这种天上的形式,这是有道理的。[2]8把宗教组织与世俗政权重叠起来,建立政教合一的社会体制,是以宗教理想以及宗教权威来建立社会秩序的基础。相当多的宗教在初起时都有过这种尝试,道教也不例外。1据史书记载,早期道教确实有过类似的想法和行动,五斗米道以“师君”“治头大祭酒”“祭酒”和“鬼卒”构成的组织秩序,“各领部众,多者为治头大祭酒”2,一方面取代国家的经济职能,要求信仰者的租米钱税,即“输米、肉、布、绢、器物、纸笔、荐席、五采”,一方面控制了本来由国家控制的刑法,即“犯法者三原(一作令)然后乃行刑”3,这就是刘勰在《灭惑论》中愤愤然批判的“爵无通侯,轻立民户,瑞无虎竹,而滥求租税,库费产业,蛊惑士女”。4如果说,在这种基础上还增加了宗教信仰的动员力量,实质上就取消了地方政权而以宗教教团取代。有了这样一个严格的组织和清楚的秩序,又很容易使宗教走上政教军合一,即宗教、政权和军队重叠,以对抗世俗政治权力和国家意识形态的道路。早期有张角的黄巾起义和张鲁的割据汉中,4世纪20年代的李脱,凭着“以鬼道疗病”,可以“署人官位”,使得“自中州至建邺”的人纷纷信仰[3]1575,40年代的李弘,他“连结奸党,署置百僚”,用道教自己的话说即“称官设号、蚁聚人众,坏乱土地”5,一直到4世纪最后那几年的孙恩,“自称征东将军,逼士人为官属,号其党曰长生人”。和卢循搞起叛乱。[4]卷111
齐梁之际,著名的文人刘勰回忆到这些历史,还心有余悸地说道教,“事合氓庶,故比屋归宗,是以张角、李弘,毒流汉季,卢悚、孙恩,乱盈晋末”。6特别是与道教一直在竞争,在向官方乞求庇护的佛教,也在反复暗示道教的这一似乎不光彩的历史,像释玄光《辩惑论》就说,道教“挟道作乱……不以民贱之轻,欲图帝贵之重”,而后来的释道安、释明概等等,也一再地提起从汉代的张角、晋代的陈瑞、孙恩、卢悚一直到隋代的蒲童,“汉魏以来,时经九代,其间道士,左道乱朝,妖言犯国者,披阅图史,何世无之”,并且反复暗示说,“今者道士……人数既多,共结贼党”,“自尔迄今,群娈相系,依托治馆,恒作妖邪”,7其实,由佛教徒发动的起义和叛乱也不少,正如吕思勉所说:“佛教最谓称柔和矣,然自传入中国以来,假以谋乱者,亦迄不绝;以其所成就,不如张角、张鲁、孙恩、太平天国等之大,读史者遂多忽略焉;然其性质实无以异……魏晋以后,佛教之流通愈甚,其徒之反侧亦滋多。”[5]973只是规模和影响都不及道教。
道教除了对王朝的叛逆之外,不乏合作和投机的表现。隋文帝杨坚的开国年号开皇就是取自道教经典。揆诸道教史,我们就可以发现,经过六朝到唐代,道教发生了相当重要的变化,由陆修静和寇谦之对道教进行了清整。对国家而言,最重要是半军事化半行政化的、容易与世俗皇权形成对抗的“治”渐渐消失了,道教教团的地域分布由实际区域的“治”变成想象的“洞天福地”,这样,与国家控制民众欲望的冲突也就日益消解。[6]117即使这样,国家与道教的关系依然还是紧张的。
二、道教与隋末唐初的谶言
谶纬,又有图纬、纬候、图谶、图录、符谶、图书等多种称谓。也就是说,“谶”指的是指示预言的书。“纬”本来相对“经”而言,“‘纬,织衡丝也……汉人左右六经之书谓之秘纬。”8纬书是依附经义,以五行术数的方式解释经书,主要是依托经书来对谶进行解释。1这样的谶纬也是一种政治话语,因为谶纬能够蛊惑人心,也容易被野心家用作篡夺政权、改朝换代的舆论武器,故在汉代以后,各代皆严禁谶纬。尤其是在夺位时利用过谶纬的各朝统治者,他们都深知其中弊病,即位后都转变态度,对谶纬采取了严厉的打击。隋朝建立后,统治者对谶纬之学采取了最为严厉的禁绝手段,《隋书·经籍志》论曰:
及高祖受禅,禁之愈切。炀帝即位,乃使人四出,搜天下书籍与谶纬之涉者,皆焚之,为吏所纠者至死。自是无复其学,秘府之内,亦多散亡。[7]卷32
但是隋末天下大乱,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各种谶言又流行开来,其中“李氏当王”2的谶言最为流,影响也最大。各地起义的势力都响应这个谶言。
如李密:
会有李玄英者,自东都逃来,经历诸贼,求访李密,云“斯人当代隋家”。人问其故,玄英言:“比来民间谣歌有《桃李章》曰:‘桃李子,皇后绕扬州,宛转花园里。勿浪语,谁道许!‘桃李子,谓逃亡者李氏之子也;皇与后,皆君也;‘宛转花园里,谓天子在扬州无还日,将转于沟壑也;‘莫浪语,谁道许者,密也。”既与密遇,遂委身事之。[4]卷183
西凉李轨:
李轨,字处则,武威姑臧人也……时薛举作乱于金城,轨与同郡曹珍、关谨、梁硕、李赟、安修仁等……乃谋共举兵,皆相让,莫肯为主。曹珍曰:“常闻图谶云‘李氏当王。今轨在谋中,岂非天命也?”遂拜贺之,推以为主。轨令修仁夜率诸胡入内苑城,建旗大呼,轨于郭下聚众应之,执缚隋虎贲郎将谢统师、郡丞韦士政。轨自称河西大凉王,建元安乐,署置官属,并拟开皇故事。[8]卷54
李唐夺取国家政权的过程也是如此。如楼观道士歧晖就为李渊鼓吹,茅山道士王远知则在“高祖龙潜”时,就“秘传符命”。3李渊当举反旗时,则当仁不让,说什么“隋历将尽,吾家继膺符命”。[9]4李渊集团为了应“李氏当王”的谶言,对李玄英编造的“桃李子歌”做了一番不同于李玄英的解释,据《大唐创业起居注》载:
又有《桃李子歌》曰:“桃李子,莫浪语,黄鹄绕山飞,宛转花园裹。”案:“李为国姓,桃当作陶,若言陶唐也;配李而言,故云桃花园,宛转属旌幡。”汾晋老幼,讴歌在耳。[9]11
“李氏当王”这种谶言的变种还有很多,各种谶言无非都是制造政治话语。对这些话语的内容的诠释皆是为了各种势力的利益来服务的。李唐政权建立之后,还制造了道教教主老子为李唐帝室先祖的神话。这为李唐王朝论证“天命所归”“君权神授”提供了理论依据。
武德三年五月,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谓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10]卷50
李唐取得政权后的内部权力之争,也要利用谶言。如李世民:
武德八年,拜中书令,尝夜于嘉猷门侧,见一神人,长数丈,素衣冠。呼太宗进而言曰:“我当令汝作天子。”太宗再拜,忽因不见。[11]卷21
又如:
武德中,太宗平王世充,与房玄龄微服以谒之,远知迎谓曰:“此中有圣人,得非秦王乎?”太宗因以实告,知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惜。”[8]卷192
每朝帝王兴起时常引谶纬自炫,来论证自身统治的合法性与神圣性。谶纬如同利刃,既可伤人亦可伤己,因此官方又严禁图谶,对其控制日益严格。但谶纬依旧屡禁不绝,在民间大量流传。原因是政治上需要利用谶纬根深蒂固的传统影响,宣扬君权神授,有助于获得政权和巩固君主的统治。谶纬在政治上特点鲜明,谁都可以利用,当取得国家政权之后,统治者对待谶言又是另一嘴脸。如:
高祖初行军于汾、晋,休止其家;因蒙顧接,及为太原留守,引为行军司铠。时盗贼蜂起,士尝阴劝高祖举兵,自进兵书及符瑞,高祖谓曰:“幸勿多言。兵书禁物,尚能将来,深识雅意,当同富贵耳。”……初为义师将起,士不预知,及平京师,乃自说云:“尝梦高祖入西京,升为天子。”高祖哂之曰:“汝王威之党也。以汝能谏止弘基等,微心可录,故加酬效;今见事成,乃说迂诞而取媚也”。[8]卷57
太宗也是一样,夺取政权后,对待谶言也是如此。
上以近世阴阳杂书,讹伪尤多,命太常博士吕才与诸术士刊定可行者,凡四十七卷。己酉,书成,上之;才皆为之叙,质以经史。1
还对谶纬之类的书进行了清理。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
朕此见众议以祥瑞为美事,频有表贺庆。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无祥瑞,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有芝草遍街衢,凤凰巢苑囿,亦何异于桀、纣?尝闻石勒时,有郡吏燃连理木,煮白雉肉吃,岂得称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爱祥瑞,遣秘书监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对考使焚香,读《皇隋感瑞经》。旧尝见传说此事,实以为可笑。夫为人君,当须至公理天下,以得万姓之欢心。若尧、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爱之如父母,动作兴事,人皆乐之,发号施令,人皆悦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后诸州所有祥瑞,并不用申奏。2
对利用谶纬造反作乱的,唐太宗则严惩不贷。
陕人常德玄告刑部尚书张亮养假子五百人,与术士公孙常语,云“名应图谶”,又问术士程公颖云:“吾臂有龙鳞起,欲举大事,可乎?”上命马周等按其事,亮辞不服。上曰:“亮有假子五百人,养此辈何为?正欲反耳!”命百官议其狱,皆言亮反,当诛。独将作少匠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上遣长孙无忌、房玄龄就狱与亮诀曰:“法者天下之平,与公共之。公自不谨,与凶人往还,陷入于法,今将奈何!公好去。”己丑,亮与公颖俱斩西市,籍没其家。1
事情不可能一两次的打击就完全停止,道教谶言里面的东西时不时被人拿出来说事。如《老君音诵诫经》中有:“老君当治,李弘应出,天下纵横反逆者众,称名李弘,岁岁有之。”[12]221到高宗武则天时期,为了应谶,武则天将自己的儿子取名李弘。这样她就能为自己的儿子夺取太子之位有了很好的神学依据。并在李弘当太子八年后,将太子写的《洞渊神咒经》流布天下,强化了其所生太子李弘应谶当王的信息。[13]279-285其实历代各朝统治者虽然打击谶纬,但在政治斗争时,依然要利用谶纬来背书。
三、制造谶言与神道设教
谶纬与道教有着相同的渊源。谶纬假称是上天所降下的符命,道教吸收和发展了谶纬中的“天人感应”时,强调天所具有道德属性,实现道教的“天人合一”。在隋末唐初,谶言受控于统治者并成为操控和引导社会舆论的有力武器。谶言在社会影响上,特别是民众安全感和情绪焦虑方面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每当社会冲突和动乱出现的时候,普遍感到格外的无助和缺乏安全感,“而谶言可以给当前境遇一个合理的解释说明,因而易于滋生和传播”。[16]90而相关谶言作为一种负面舆论对社会生活秩序产生强大的冲击和破坏力,导致民众的恐慌与骚乱。政治化的谶纬加速了动员群众,鼓动民心,操弄社会群体的情绪,这种政治传播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以期赢得舆论的主动权。谶纬往往能够在民众中产生和凝聚共识,形成共鸣。如唐高祖李渊起兵前积极利用桃李子歌等谶言造势,“以符冥谶”“自尔已后,义兵日有千余集焉。二旬之间,众得数万。”[9]卷1数万民众得以快速地聚集,得力于李渊集团对谶言大力传播。谶言的传播速度快,范围广,很快民众响应谶言纷纷投奔到李渊集团,这是利用谶言掌控主导社会舆论影响并迅速动员民众的一种表现。
在道教思想中,上天与人“交感”之时,通过神仙作为媒介,传达上天的旨意,譬如被道教尊为神仙的老子便是最常见的代表。这些符命通过所谓神仙的口传和道教徒的诠释,便是道教中继承和发展谶纬思想的表现。谶纬所具有的预言神秘性一直备受统治者或野心家的重視,在传承与延续的过程中逐渐走向政治化。在唐初时期,谶纬更多是被用来宣扬将来君临天下的统治者为何名何姓。李渊利用李氏谶言和天文祥瑞的同时,更是通过编造“羊角山”神话的方式,指称其为太上老君后裔,大大加深了李氏之谶与李渊之间的关系,在对李氏谶言的利用上抢得先机,使其行为显得更顺乎天意、人心,进一步构建了李唐皇权“神授”的正统地位。“羊角山”神话,主要保存在《唐会要》《混元圣纪》和《历代崇道记》中,内容大体较为接近,其中以《混元圣纪》中的记载完整地还原术士编造“羊角山”神话的过程。2李渊集团认老子为祖宗的时间,目前最早有明确史料记载的是武德三年之前。早在李渊太原起兵时,“有突厥来诣唐公,而先谒老君”,这里李渊有可能就开始认老子为先祖了。[9]卷1正式作为诏敕出现是在武德八年。“老君是朕先君。尊祖重亲,有生之本。”[15]卷2上述神话谶言的出现可以看出是道教与李唐王朝的合谋。
李唐王朝统治者为什么要冒认老子为先祖?我们知道谶言是道教的来源和重要的组成部分。道教所制造的谶言的威力是李唐统治所熟知的,谶言可以用来反对隋代的统治,也就意味着别人也可以利用来反对李唐的统治。为了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李唐统治者在夺取政权之后对谶言的禁止就不难理解了。这只是一方面,要避免这种可能性,需要一个更为长远的方法。唐高祖对道教谶言的利用,开始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夺权的需要。在取得政权之后还需要一个较长远的考虑,要进一步利用谶言来为取得政权增加神圣合法性,就出现冒认老子为祖宗的举措。这样的话,道教教主是李唐统治者先祖,那么道教就被李唐所绑定,相关的很多谶言只会对其有利,相应的害处就少得多了,既然如此,冒认老子后裔能消除谶言的负面影响,那么又何乐而不为呢?我们说李唐的李氏是不正宗的,这一点陈寅恪有过考证。其实当时的人也清楚这一点。如法琳认为李唐的李姓出自“代北李”而非“陇西李”。[16]卷50因为需要,李唐可以冒认士族。所以认老子为祖先就更好理解了。冒认士族这一点,很多人认为此举是为了增加血统的高贵,冒认老子后裔则更多的在于增加李唐政权的神圣性,也可以认为绑定道教、消除谶言的负面作用则是一个实在的原因。
李唐王朝利用谶纬为统治服务的事例就是典型的神道设教。中国“神道设教”的传统由来已久,这是“古人政理之要言”,所谓“神道设教”乃为“借鬼神之威,以申其教”。[17]在古代,“普通群众思想中大量充斥的依然是对于鬼神的笃信与虔诚,客观外在的神灵世界依然风光无限地、玄秘地存在于社会之上……这个传统在整个中国古代一直是绵延不绝的”。[18]世代相传的敬神事鬼的形式中就包含着神道设教的意义,但并非由统治者命令所形成,而是社会习俗的表现,1非统治者为愚民而特设,但秦汉以降的“神道设教”之功用发生了变化。首先是施行设教的主体在变化,原先是圣人来设教,后面因为主体资格的降低,导致主体泛化和主体的迷失。[19]当社会政治从充满“人道”精神的“德政”转向“神政(神权政治)”的时候,社会观念亦由“德教(道德教化)”转向了“神教(神道设教)”。这时所谓“神道设教,可以理解为统治者借用民间已有之信仰,对其加以改造后,用作治民之具。在史书里,神道设教往往沦为巫史的妄说和政治的工具,而不是教化的圭臬。2统治者用“神道设教”之法治天下很是得心应手;对被统治者来说,则为解脱疾苦的途径之一。此即“君子以为文,小人以为神”者也。3但是如果君主对神道设教进行意识形态化,会带来对神道设教的反意识形态利用,如隋末农民起义各种势力对谶言的利用。有鉴于此,唐初统治者一方面要利用道教谶言来愚弄百姓民众即用神鬼祭祀来设教,一方面还得继续打击和限制谶纬谣言,防止危害自身的统治。
四、唐初政治中的道教
对王朝而言,最好的统治莫过于以神道彰显王朝的合法性,4体现为用君权神授,天命论等为王朝政治合法性提供支持。人们对古老传统的神圣性信仰,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信仰。这种意识形态适应古老的传统社会,在传统社会中具有很强的合法性。李唐王朝认老子为祖先,自然而然的为自身增加了神圣性。我们知道古代王朝的合法性,就是意识形态的合法性,世俗的和宗教的意識形态都可以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因此,道教的参与使得王朝的意识形态合法性更为充分。
意识形态合法性的核心是对于某种价值观或者说信仰的遵从,传统和个人魅力就是特殊形式的价值观和信仰,也都是意识形态合法性的特殊表现。这种意识形态合法性不应被单纯理解为民众对于国家政权的忠诚和信仰,合法性不是也不会来源于政治系统为自身的统治所作的论证或证明。因此一种政治是否包含着被认可的价值,才是其有无合法性的最好证明。君权神授和天命论就是古代社会认同的价值。道教谶纬提供了老子是李唐王朝先祖的这点资源,对李唐消除合法性危机是大好事。当然意识形态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当社会转型时,原有的意识形态往往会被质疑,出现认同危机。隋末天下各种谶纬谣言大流行就说明这一问题。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常常基于两个前提:第一,他必须正面确立规范秩序;第二,依法结合的人们必须相信规范的正当性。当社会规范不足以解决社会问题或者人们对规范正当性产生怀疑时,就会产生合法性危机,而合法性危机会导致理性权威的动摇。这时,如果权威是意识形态所提供,理性权威的动摇就会导致人们开始怀疑甚至批判意识形态,从而导致意识形态的认同危机。所谓这种合法性危机在古代社会也会产生,并不在于合法性的两个前提“确立规范秩序”和“规范的正当性”。其实质就是绩效合法性不足,说明王朝统治者做得太烂,导致民不聊生,所以仅仅依靠冒认老子为祖先是不可能获得长治久安的。
作为政治合法性而言,还需要一定的绩效合法性才能稳定政权。如何稳定政权,对古代王朝来说,必须在大乱之后实行大治,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否则无法恢复残破的经济,老百姓稳定生产生活秩序无法获得保障。那么唐初修无为之教,行修养生息之策,就是增强王朝的绩效合法性,可以消解合法性危机。尤其是太宗上台,所作所为颇合老子的无为政治,一方面是出于形势所迫,二则道教的无为之治刚好契合这个局面,可以认为是道教的无为之教的思想资源对唐初的国家治理局面做出了贡献。
无为之治的道家思想被道教继承下来,在太宗朝被用作政治指导思想,就此推论导致太宗推崇道教,这种说法是看似有理,好像太宗所做是对道教的回报。其实,道教的无为之教很难落实到具体的政治操作层面,顶多作为一种思想资源,而且这种道家无为思想也早已被儒家所吸收。所以说很难分得清孰是儒家孰是道家的思想在起作用。实际上,太宗时期的道教与佛教一样只是作为一般的宗教存在而已,道教与政权的关系也仅仅是轻微的地位变化,道教获得了一定的优先待遇。之外,某种程度上恐怕是唐太宗对道教的负面作用的控制而采取的更为高明的手段罢了。从太宗的言行来看,他是奉行儒家的一套,但是唐初的国家治理确实体现道教的无为之治的思想。
五、余 论
道教人士一直以各种方式积极介入隋末唐初政治也是不争的事实。至于说道教到唐代对国家政权屈服了,这是一个误解。从道教的发展史来说,早期道家与后来道教是一脉相承,不可分割,就如原儒与汉儒一样。早期道教缺乏的是制度仪轨建设这一块,给人感觉是与巫觋方术没有太多差别,佛教的传入使得道教在制度仪轨建设方面越来越系统精细化,这也是佛教刺激的结果。无论是早期道家还是儒家,在没有成为统治阶级的思想之前,都还是一个学派。汉初的黄老之治,武帝的独尊儒术还是后来的内儒外法,无一不是儒道法各家互补,被用于辅助王朝统治。各家介入政治只是方法方式上有差异。
唐代佛教和道教在政治地位上的变化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道教开始超越佛教之上是在高宗时期,道教不是仅作为宗教来对待,道教所信仰的道开始转为唐代国家的治国之术和理想,老子也与道在某种程度上重合了。武周时期虽有反复,到玄宗时期,则是国家追求的理想和目标。相应的道教也出现变化,萌芽于南朝的重玄思想,在玄宗朝达到顶峰。此时,国家出现了以道为体、以儒佛为用的局面。某种意义上说是道教的胜利,或者说是贵族道教的胜利。
道教给世人的从来不是单一的面相。唐代道教制度建设取得空前的进步,一些看似巫术迷信的成分被贵族道教所排斥,连道教谶纬也受到李唐王朝的限制,但道教并不是一直按照贵族道教的方式来发展的。例如谶纬并没有因此消亡,而是转向下层社会中寻找生存空间,“以谶谣的形式向大众传播各种寓意国家兴乱的预言和信息”。[20]231在唐代历史语境下,上至统治者,下至百姓,都认可谶纬观念,并成为了一种社会共识。即使谶纬虽整体走向衰落,但其思想效力仍存。
要之,道教在隋末唐初的表现,从一开始兜售谶言到身体力行支持李唐夺取政权,道教作为宗教为社会提供各种知识信仰,为国家提供合法性和治理思想的资源支持。因此,隋末唐初的道教与政治的关系改变了之前的紧张对抗,是合作利用关系。分化出来的上层贵族道教成功进入唐代国家治理思想体系,这是道教的成功。
参考文献:
[1] 冯渝杰.“致太平”思潮与黄巾初起动机考——兼及原始道教的辅汉情结与终末论说[J].学术月刊,2018(5):138-153.
[2] 万绳楠.魏晋南北朝史论稿[M].台北:昭明出版社,1999.
[3] 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5] 吕思勉.读史札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6] 葛兆光.屈服史及其他:六朝隋唐道教的思想史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7] 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8] 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9] 温大雅.大唐创业起居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0] 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1] 帝王部·应征类[M]//册府元龟.北京:中华书局,1960.
[12] 道藏:第18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
[13] 左景权.《洞渊神咒经》源流式考——兼论唐代政治与道教的关系[J].文史(第23辑).北京:中华书局,1984.
[14] 吕宗力.汉代的谣言[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
[15] 唐文拾遗[M]//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16] 唐彦悰.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M]//大正藏:No.2051.
[17] 钱锺书.管锥编:第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8] 晁福林.试论先秦时期的“神道设教”[J].江汉论坛,2006(2):93-98.
[19] 李定文.“神道设教”诸说考释[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7):73-78.
[20] 侯外庐.中国古代思想史[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马陵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