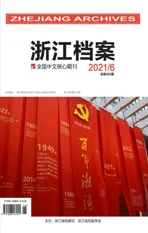历史上“户籍”一词源流考
2021-08-04沈阳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吴 哲/沈阳建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丁海斌/广西民族大学管理学院
中国“户籍”制度起源非常早,其端绪可上溯至商周时代。商代王者蹈履而耕,所谓“帝耤千畝”也,使民如借,以伺国中公田,即籍田之萌芽期。至公元前八世纪的西周,按《周语》所记,宣王已然“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料即数也,通过计点、核查民户,以征兵役、军赋等。此时并非户籍档案管理制度的成熟期,但已经体现出后世户籍档案管理制度的重要功能之二:赋税、军役。所谓“户籍”,其中似隐含着中国传统社会的两种极重要的关系,以“户”表征血缘,以“籍”表征地缘。“血缘”加“地缘”,此二者相合,渐形成中国古代统治阶层管控丁口、征发赋役的基础与保障。而在这一漫长发展与演变过程中,“户籍”本身亦作为文档名词,至今保存延续、为人所共知,并因其功用而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版图”与“户籍”的渊源
中国语言文字的历史,有一个从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多音节词的发展过程,相对而言,单音节词的内涵较为丰富,但专指性较弱;而双音节词则增加了规束,使得内涵与外延缩小,但专指性增强,这也是符合语言发展渐进性规律的表现。大略在春秋战国时代之后,双音节词开始迅猛增长,而早期历史上使用单音词的情况非常多。所以,在我国更早期的语言文字历史上,尚无双音节词“户籍”之明确指称,所谓“户籍”的涵义,大率以“版”字指代、体现。春秋以降,双音词开始大量涌现,才渐而由“版图”之“版”衍生为“户籍”,所以“版”即可视为“户籍”一词早期渊源之所在。而在纸张尚未发明之前,录籍于“版”,是可以想见之事。
“版”字与“图”字于先秦时代即已经组成合成词,这就使得至今仍然通用的“版图”一词成词颇早,至少要早于“户籍”,所谓“内宰掌书版图之法”等。版图是“版与图”的全称,其中“版”与“图”分别表达各自意思,属于联合结构,其专指性意味显然要低于后起之“户籍”一词。在联合结构的“版图”一词中,是户籍与地图,二者并列而合的意思[1]。其中,将“人之多寡”体现于“版”字,复将“地之广狭”体现于“图”,而此“人之多寡”即“户籍”之所由来。
《周礼·天官冢宰》“司书”中有“司书掌……邦中之版”[2]。此中之“版”,即表达户籍、名籍之义,其使用方式如:《周礼·夏官司马》“司士”中“掌群臣之版,以治其政令”[3];又,《周礼·天官冢宰》“宫伯”中亦有“凡在版者”[4],郑玄注:“版,名籍也,以版为之,今时乡户籍谓之户版。”[5]版图中的单音词“版”渐而向双音词“户版”演化,从而使得语辞的专指性为之加强,表意也更加精准起来。“户版”即户籍之版,而古文“户”字写作“㦿”,其字从木,与“版”相合。
《周礼·春官宗伯》中复有“大胥掌学士之版”,郑玄注引郑司农云:“今时乡户籍,世谓之户版。”至唐代,贾公彦疏:“閭里之中有争讼,则以户籍之版……听决之。”[6]郑注、贾疏都已经非常明确地将“户籍”与“版”相关联起来,我们亦可因此而识得语言文字发展过程中二者之间的历史渊源(此时之“版”至后世,渐可写作“板”,其中缘由不外乎因为古“版”之材质多为木质,即可供书写之木片或木板)。
二、“户”“籍”的涵义
《说文》训“户”曰:“护也,半门曰户,象形。凡户之属皆从户。”[7]《玉篇》训“户”曰:“户,所以出入也。一扉曰户,两扉曰门。”将此两者结合而观,则“户”的涵义清晰可见。不过,由于语言文字的发展与演变,我们亦需分辨一些古代与现代不同的使用规则。
门与户之别:现代我们使用成语如“门户之见”等,已经将门与户二者合为一义,表征派别或狭隘之类的涵义。但即便是现代人自称“小户人家”时,也不可能自称为“小门人家”,这就体现了门与户之间的差异。普通百姓只能称“户”,而难能称“门”,因为古时贵族或统治阶层才可以“名门”“高门”“朱门”称之。虽然现代社会多已不在意“两扉曰门”,在口语中很少使用“户”而多使用“门”,如家门、串门、叩门等等,“门”字已然顶替了大部分“户”的用法,但是若干自古流传下来固有的“户”词汇,却不能将之轻率更易成“门”,比如万户、农户、户口、户籍等。
户与家之别:家与户涵义颇相仿,皆表居于一处之亲属,所以有成语家家户户。《说文》“家,居也”,而户之单扉,则代表一家人共同的出入口,所以户即可表征家庭之单位。相对而言,现代社会“家”更多是自称,偏于自身血缘方面,而“户”则有他指的意味,偏重于公众事务方面,所以人们常说“我家”,却少见“我户”之类称呼。因此某种程度上,家可视为亲族的单位之一,而户则可视为政府统计的单位。
《说文》训“籍”曰:“簿书也。从竹耤声。秦昔切。”[8]藉藉无名的“藉藉”与“籍藉”二词互通,都是形容纵横交错、人语喧哗、杂乱的样子等,而“籍”与“藉”的单字则某些时候可通用,某些时候不可。“藉”以“艹”头为部首,强调与“草”有关,作垫子、席之类释义时,不能与“籍”相混;而“籍”则大多代表登记隶属关系的簿书用其称谓。籍、簿字皆形声,因“从竹”,可知早期书于竹简或木版。
“籍”的涵义有多种,《汉语大字典》释“籍”的第一种涵义即是“关于贡赋、人事及户口等的档案”。《释名》亦有:“所以籍疏人名户口也。”[9]“籍”与人事、户口等互相关联,是因为政府需要以“籍”来“分田里,令贡赋”,“籍”与贡赋紧密相关,所以后来“籍”的涵义甚至发展为直接等于“税”,即:籍者,税也,如《墨子·节用上》“其使民劳,其籍敛厚”。而由于“籍”与政府财税系统紧密相关,并且“籍”又必然直接或间接地关联到其他制度或政策,如土地制度、徭役制度、军户世袭役制、里甲制度等,故此历代政府皆将“籍”之一事视为大事,所以在古代刑法历来对“脱户”“逃籍”者严厉打击,并且有一种后果相当严重的刑罚,将人削名除“籍”(财产充公、亲眷为奴),属于重刑之一,此种重罪即定名曰“籍没”。
从“户籍”词义的内涵角度来看,“籍”的范畴更大,除“户”籍外,尚有多种“其他籍”,如:宦籍、弟子籍、游士籍(类似现代暂住证)、市籍(商人)、私奴籍等。“户”者,可用来约束表义宽泛的“籍”字,而成专指性词义。
三、早期文献与历代使用频次
前述“户籍”及其制度的萌芽、起源固然可上溯至商周,如“料民于太原”“王登人三千”“掌万民之数”“与人民之数”“献其数于王”等,但历史上“户”字与“籍”字正式相合、组成双音合成词,据现有资料考察,恐怕是在战国时期。有学者认为我国历史上作为合成词的“户籍”,最早的出处是《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10],即“献公立七年,初行为市。十年,为户籍相伍”,虽然秦献公十年即公元前375年“为户籍相伍”,但《史记》却是西汉太史公所作,故此,这是相当于将“户籍”的最早成词时间认定为汉代。
但是在更早期的《管子》一书中,已可发现“户”与“籍”二者的连缀使用。在《管子·禁藏第五十三》中,有“户籍田结者,所以知贫富之不訾也”,并且《管子·国蓄第七十三》篇中“人君非发号令收啬而户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谨,而男女诸君吾子无不服籍者也”,《管子·轻重乙第八十一》“故不欲收穑户籍而给左右之用,为之有道乎?”[11]“户籍”一词在《管子》一书中出现多次,此似可见,在《管子》时期,“户籍”已成专有之名词。
《管子》一书非一人之笔、一时之书,《管子》今本乃汉代刘向所编定,当下学界共识应为稷下学士群体之创作,类于丛书,并且只能是“稷下学宫鼎盛时期的产物”,因此,据现有资料而言,我们或可将“户籍”一词之早期出处上推至战国时期。
“户籍”虽然成词很早,并经常在官方文本中出现,但纵观历代,其使用频次并不算高,远低于“籍族”文档名词中的“载籍”一词[12],与“册籍”“图籍”的数量与使用频次相差仿佛。“户籍”一词在形成之初期,即秦汉以前,数量稀少,其使用频次几乎可以忽略,只有特定的寥寥几次。随着战国以降语言文字中双音词的迅猛增长,“户籍”的使用频次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但是随着书籍、典籍的增加,其使用频次亦难称为高频。之所以使用频次在元代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扬曲线,大概与元朝文献相较我国历史上其他时期文献略少的缘故(如宋与元代,“户籍”一词的使用数量差不多,都是80余次,但宋代文献数量远高于元代,因此显得宋代使用频次为低)。发展至清代,使用数量与频次都达到一个小高峰,不过总体而言,“户籍”在我国历史上仍属于低频词(小于1)。
明明“户籍”这一文档名词,不只民间耳熟能详,对于政府的丁口籍册、制度发展而言,甚至宏观来看,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王朝的盛衰兴亡,其实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几乎历朝历代都离不得它,但其使用频次却相对较低,究其原因,恐怕与该词专指意味较浓,并非民间用语,多为官方文本的指称有相当大的关系。通俗地讲,即是“户籍”一词多居于官方文本,民间使用量较少。今为参考起见,特将历时态使用频次、数量录于下图:

图1“户籍”一词历代数量与使用频次示意图
四、“户籍”起源期的主要内容与功能
据现有资料考察,秦代以前历史文献中并无“户籍”制式、原件留存,所以关于“户籍”起源时期之内容及功能即无法确证,但我们或可从其他出土简书中管窥一二,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竹简之“封守”篇,述之如下:
以某县丞某书,封有鞫者某里士五甲家室、妻、子、臣妾、衣器、畜产。●甲室、人:一宇二内,各有户,内室皆瓦盖,木大具,门桑十木。●妻曰某,亡,不会封。●子大女子某,未有夫。●子小男子某,高六尺五寸。●臣某,妾小女子某。●牡犬一。●几讯典某某、甲伍公士某某,党有当封守而某等脱弗占书,且有罪。某等皆言曰:甲封具此,毋它当封者。即以甲封付某等,与里人更守之,侍令[13]。
“封守”之涵义,黄盛璋先生在《治狱〈爰书〉分析》中释为“查封审讯者家”[14],似遗落一“被”字。张金光先生认为:“此当略仿户籍式之习惯用语,或即抄自户籍。”[15]亦因此,则我们或可从出土之“封守”行文中查知先秦时期“户籍”各项内容。
从《乡某爰书》之内容大意来看,据县丞某文书,须查封者为:房屋、妻、子、奴婢、衣器、牲畜等。其房屋、家人合计:堂屋一间、卧室二间,房屋皆有门、有瓦盖,木质家具全,门外十棵桑树。妻因逃亡未被查封,女儿无夫,儿子身高六尺五寸。女性奴婢,尚有公狗一只等。所谓应查封的都封在这了,没有其他应当被查封者。由上述诸详密信息可见,举凡“户籍”者,其登记之信息几乎涉及该户的方方面面,包括但不限于“性别”“婚姻状况”“身体情况”“家庭成员”“家庭成员之关系”“家庭成员婚姻状况”“身份关系”“社会地位”“职业”“家庭显、隐各种财产状况”及“明细”等。此外还有姓名、籍贯,即秦律所谓专有名词“名事里”[16]。“户籍”所掌握的信息详密至此,成年与否、健康甚至连身高信息(可以之定大、小,定服役工作量等)都无所藏匿。此则可见,“户籍”制度之所以可作为保证赋税、军役等,并成为支撑一国、一社会的基本根基性制度之由来。
户籍的主要功能:户籍档案管理制度为一国、一社会之根基性制度,甚至可以上升到“国本”的高度,因为需要以此来“分田里,令贡赋,造器用,制禄食,起田役,作军旅”等。所以主要体现在对劳动力数量的掌控、赋税征收无遗漏、人丁服军役无遗漏等角度,所谓“编户齐民”。“编户”,将男女老少统录于册;“造籍”,目的是方便管理、深入管理。所谓齐民,即统治阶层治理人民,可见一个国家、一个政府是否掌握“户籍”,直接关系到国家治理的程度和对统治阶级之统治力的维护。而每当“逃户”“脱户”“黑户”者增多,政府无法统计与掌控之际,即是该朝代统治力下降或朝代衰亡迹象的明显表现,所以发展到后世,“户籍”档案管理制度愈发严密时,常出现“脱户者,家长徒三年”之类重罪。而在历史周期率中,所谓王朝更替,从“户籍”角度亦有迹可寻,诸如每当大范围隐匿户口、迁徙逃亡、非法庇荫、非法兼并等破坏“户籍”管理制度的现象频发之际,即是国家衰或亡之征兆。
先秦时期《商君书·去强篇》中有言,强国须知十三数,其中排第一位即是“境内仓口之数”。而以户籍档案来控制劳力、增强赋税或徭役,是国富的途径,即欲国富国强,先要“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所谓生著死削,训诂学家朱师辙注曰,此户籍之法也。而国内所有人口皆着于户版,尽量使无遗漏,此或可视为自古至今户籍档案管理制度的一项基本性原则,即所谓“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17]。户籍之功能尚不止于此,因非本文所重,且关于户籍功能之细分研究,已有若干学者为之先行,兹不赘言。
五、“户籍”的发展与演化
秦汉之际,“户籍”一词仅一见,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恒以八月令乡部啬夫、吏、令史相杂案户籍,副臧其廷”[18],到魏晋南北朝时期,“户籍”的使用率较之秦汉有明显上升,如陈寿《三国志·卷十二·魏书十二》中记太祖言:“谓琰曰: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通过户籍统计,可知征军役者之多寡。《魏书·帝纪卷七》中记载,孝文皇帝于太和五年之秋七月,“甲戌,班乞养杂户及户籍之制五条”,即七月十六日,颁布了乞养杂户及户籍的五条制度。又,《南齐书·魏虏传》中亦载,永明四年,“造户籍。分置州郡……”[19]。
隋唐之际,杜佑《通典·卷九十四·礼五十四》“沿革五十四”(凶礼十六)中,“名户籍如故”;“食货三”中,更有非常明确记载的“大唐令”:“……天下户为九等。三年一造户籍,凡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20]可见唐代户籍为三年即增削一次,以人口增减重新编定。此外,李延寿《北史·卷三·魏本纪第三》:“二月甲戌,初立党、里、邻三长,定民户籍。”另外,在某些规定官吏职能的条目下,易见“户籍”一词出没,如《唐六典·三府督护州县官吏》中执掌“户籍”为明确之职能,“户曹、司户参军掌户籍”。
愈向后世发展,法律条文愈发齐整细致,系统化程度日渐加深,这是古代律法发展的特点。而在这一过程中,法律规定亦愈发严密起来,相比于秦汉时期,隋唐之“户籍”制度在“刑”“罚”的角度来看,是加强了的。比如户口登记一项,若脱漏户口或增减年状,汉代皆耐,罚金四两;发展到唐代,则刑罚要严重许多,比如杖六十,甚至再加上“徒一年半”等。这其实或可表明随着法律体系的发展,统治阶层对“户籍”的管控更加严格、对“户籍”的重视程度更加提升。
另,邻国日本曾以遣唐使学习我国制度,其国户籍档案管理皆仿我国唐代格式以为模板,由于唐代户籍档案存世者稀,近代考察隋唐户籍档案制度,尚可以“皆按唐制”之日本保存的户籍资料为较重要之参考。日本户籍档案管理制度,始于孝德天皇之大化年间(又一说为持统女天皇鸬野赞良在位期间)——其制度较我国唐制远为粗率,如唐代三年一造户籍,而日本由于人力、组织、行政、语言文字水平等因素,难与中国同日而语,只能六年一造,且唐户籍分天下户为九等,日本亦仿此语,只不过却无标准以区划九等之异,故此其户籍档案管理较之中国显然更为松散与混杂。
至两宋,据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三》记载,公元728年“制户籍,三岁一定,分为九等”;欧阳修《新唐书·卷五十二》记载玄宗后期户籍废弛之事,“天下户籍久不更造”;《太平御览·卷二百六十三·职官部六十一》,曾引《魏志》原文“昨案户籍,可得三十万众,故为大州也”;又,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十三·太祖开宝五年》复有记载,“又诏:‘自今民有逃亡者,本州具户籍顷亩以闻,即检视之,勿使亲邻代输其租’”,另“卷七十六”,记述宋真宗大中祥符四年“河北忠烈、宣勇军士本自户籍选置”。一为赋税,一为军役,将户籍档案管理制度的主要作用体现得分明。又由于“户籍”档案管理制度与赋税、军役两者最为相关,则在军制类典籍中亦可见“户籍”一词之踪影,如陈傅良《历代兵制·卷四南朝》之中,“更定户籍,虽有其意,无其法”[21]云云。
有宋一代的“户籍”制度较之隋唐时期又进一步,更加严谨与复杂。仅与户口相关的各类簿册,计有:五等丁产簿、桑功帐、户贴、丁帐、形势税簿、户钞、升降帐、甲册、典卖析居割移税簿、鼠尾帐[22]等诸多种类。宋代以前,“户籍”一词多见于官方正史或律书类典籍,私人记载则仅见于庾信“邸客城池,门阑户籍”,可见“户籍”一词民间使用并不多。两宋之后,渐于个人文集、手札、日记等民间记述中皆可见,比较有名的如《苏轼集》《漫塘集》《彭城集》《夷坚志》等。这也是“户籍”一词在宋代较之唐以前的使用率有较大增加甚至倍之的缘故之一。
发展到元、明时期,元代《全辽文·卷五》记述职官“閤门舍人”之职权范畴时,出现掌管“户籍”之语:“权阁门舍人公是供遥建彼皇都。营筑劳神。板图任重。加授户部使。掌户籍。”到马端临著名的《文献通考》中,则多次可见“户籍”一词踪迹,《文献通考·卷四·田赋考四》,引《宋纪》“本州具户籍顷亩以闻”;《卷五·田赋考五》,“以税赋户籍在第一等、第二等者支移三百里”。除上述与“户籍”紧密联系的“田赋”条目之外,在与“户籍”一事更加明确相关的卷十一“户口考”中,记载当时应对外来人口的政策“许依格式申入户籍”[23]等。
脱脱等撰《辽史·卷一百十六·国语解》,记述辽代北面官名为“常衮”者(一说“敞稳”),典族属之官,设遥辇帐大常衮,并大国舅司四帐各有常衮,其职能为“掌遥辇部族户籍等事”。另,《金史·卷五十五·志第三十六》,描述百官职名、职能者,于“户部”条目下,有尚书一员、侍郎二员、郎中二员,除此之外,尚有员外郎三员,此员外郎职级为“从六品”,位于郎中职级而下,“皆以一员掌户籍、物力、婚姻、继嗣、田宅、财业”等[24]。
元代时期,废除了一直以来的九等户制,分为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四种。以社会分工或民族差异或所在阶层等不同,又可细分为若干小类,如驱良户、站赤户、诸色人匠户、儒人户、放良民户、回回畏吾儿户、复业户、答失蛮迷里威失户等,其整个户籍管理体系较之前代颇显杂乱、无序,此时“户籍”一词多出没于官方文本之中,而民间少用。至明代,则可于个人文集中屡见,如大儒王阳明《申谕十家牌法》“凡置十家牌,须先将各家门面小牌挨审的实,如人丁若干……及户籍田粮等项俱要逐一查审的实”[25]。而阳明先生之南赣,将尽心尽力审实“户籍”项,甚至置于剿平匪乱事务之前,不审实户籍则不可剿匪,“户籍”之重要性可见一斑。
明代除个人文集以外,“户籍”一词开始于各种小品文、笔记类撰述,如《谰言长语》《涌幢小品》《泉南杂志》之中频繁出现,并且更进一步,还出现在彻底面向大众的评话、话本中,如明代末期,冯梦龙《喻世明言》中“单公时在户部阅看户籍册子”,又如《英烈传》《三国演义》等,皆有“户籍”一词出现,则“户籍”一词深入民间,大体已完成从官方语向世俗语转向的通俗化过程,其约定俗成之通俗义至近现代几乎无人不知,于此可见端倪。
至清代与其后较短暂之民国时期,“户籍”一词的发展与使用,基本延续了元明时代的特点,即“户籍”语辞既出没于各类官方典籍之中,亦同时出现于民间、文人之札记、日记、笔记类撰述之中。如清初时期,朱彝尊《日下旧闻考》,其“卷七十二”谈清代八旗之制:“定鼎以后,即旗色以颁户籍,分田授宅。”清末时期,魏源《海国图志》之“卷二十九”,似引《佛国记》中之描述,记“中天竺”国,其国“寒暑调和,无霜雪”,同时亦无官法与“户籍”。著名外交家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卷十四”中,亦有“初诣日本公使上野景范谈,兼晤希腊公使宅那剔阿斯。上野景范见给《日本户籍表》……”云云。至民国时期,赵尔巽所撰《清史稿·卷一百十六·志九十一》之“职官”条目中,谓基本行政单位一县之中,正九品之主簿官“分掌粮马、征税、户籍、缉捕诸职”[26]。
又,“户籍”档案管理制度虽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居于官方体制之中,但多存在于文件解释、律令规定、官员职能等条目下,似一直不曾单行、单列。而以法律条文形式,将之通行而为单行法规,地位更加提升,则似在近代清末1911年,清政府制定的专门之《户籍法》[27]。其后清帝逊位,袁世凯北洋时期,颁布《县治户口编查规则》等条文;至蒋介石民国政府,复于1931年重新颁布《户籍法》,并辅以《保甲条例》等规定。
上所述综而言之,“户籍”一词在我国源流悠久,虽然使用数量较之“文书”“载籍”等文档名词为少,古代属于低频词,但该词实为我国古代文档名词群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研究价值。并且,不同于一些古代常用而现代衰落或退化消亡的“历史”文档名词,“户籍”一词在现代社会,依然在政府和民间等诸多层面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并与制度、改革、人口、管理、变迁、歧视、城乡、农民工等诸多词汇相结合,形成若干词组或固化短语,除了在文档领域的专业化特征外,作为专指性文档名词的“户籍”实在已经在我国完成了基本口语化或大众化的进程,其使用频次在未来或将表现出比古代更为稳定或上扬的演化与发展曲线。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档案史史料学”(19BTQ095)阶段性成果。通信作者为丁海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