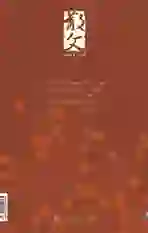为明天的日子
2021-05-07阿微木依萝
阿微木依萝
刚坐下没吃几口饭, 我那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就带着她的“团队” 来到城里,她比我大十岁,今天打扮得和从前一样朴素,穿过席间所有客人,在桌子边扭着屁股走到我身旁。
嗨! 她说,今天你参与吗?
我咽下一口饭, 心里想: 今天是丧宴啊!
你参与吗? 她再问。
我睁大眼睛看向她的眼睫毛, 她的眼睫毛还是那么长那么好看, 在她那双很大的眼睛上面, 眼睫毛像一片青草盖在目光之上,我很难拒绝这样充满期待的目光,我说,好的呀!
她很高兴。
可是我心里怕得要死。我像上一次吃酒席那样没有事先准备塑料袋子。但这个话我不能说。她最讨厌像我这样出门吃酒席不拿塑料袋的人。
她知道我没拿塑料袋就会跟我说:你是舍不下面子……你是故意不拿塑料袋子……你没有过着艰难日子不知道日子难过……我教给你的经验一样也学不会……早知道这样, 小时候你被大水险些冲走我就不该伸手将你捞上来……你从来不和我们一路……你打心眼儿里看不起我这样的人!
我不要听她说这些伤心话。这样的话听过三次就够了。即便我可能就是不高兴跟她们这么干,可她是我一起长大的姐姐,不是亲生姐姐,感情却是亲生的。我不要与她分道扬镳。我要铭记她的救命之恩。所以我要说一些连自己也厌烦的鬼话。
今天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心里乱成一团。说完“好的呀”这句话,我的碗就有些端不稳了。
很快她们干的事情将和之前每一次相同,在场的人都会眼睁睁地,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 看着她们将酒席上每一桌的好菜全部倒进塑料袋,然后扬长而去。她们可能连肉汤也不放过,像前几次一样,车屁股流汤滴水而去。
我恐怕得把她们这种行为叫作“工作”才妥当。
那些人不会知道这个工作我的好姐姐已经干了不下十年。她輕车熟路、干净利索,十年如一日,但凡熟人宴请,无论生孩子满月酒, 无论婚丧嫁娶, 她都会热情参与。吃完再把桌上剩饭剩菜一扫而光,打包带走。宴请的主人谁也不会真正跟她计较。计较也没法追究。
她就是这样过来的。十年。
十年前她一个人, 现在她有了一帮队友。队友也就三个人,加她四个人。如果我加入,就是五个人了。
我咽下一口汤。差点被烫死。
你吃完了没有? 她说。
我急忙站起来。
现在我必须站起来了。一抬眼撞见她目光里有些逼迫的味道。她安排那三个队友继续守着饭桌, 一旦那些人吃完就动手装菜。三个队友点头答应,她们身经百战的样子。
我跟着姐姐一路走到房子的巷道深处。再往前就是殡仪馆焚烧尸体的地方,那房子的上空还冒着一股死者的青烟。我们这次参加的宴席正是因为我们两个共同的亲戚, 一位年过七十的老头子两天前死去了,这会儿他的尸体在前方的炉子里焚烧。
我可不要再往前走了。她也不打算往前走。
你没有拿袋子是不是? 她问我。
是的。我说。我望着前面房顶上的青烟。
你看房顶干什么? 她说。
有烟。我说。
我就知道你和以前没什么变化。她话语中含着怒气。
我俩一来二去说了一百多句, 她最后说,我就知道你不清楚日子难过。说完扬长而去。
我一个人站在巷子里。前面房顶上空青烟淡了下去。那个死去的亲戚彻底没有了。
我有点难过(这太难得了,我终于感觉到了一点难过)。于是立马张口喊住已经快要走到巷子尽头看不见背影的姐姐, 把她喊停下来。
她又走回我身边,问有什么要说的。
我其实也不知道有什么要说。我只是突然觉得这个死掉的人是我们共同的亲戚, 可为什么刚才我和姐姐站在巷子里没有一点伤感?难道这不是一件伤心事吗?姐姐只关心饭桌上那些剩菜剩饭, 她跟我聊了一百多句,尽是在追问为什么十年过去,我仍然活得像个白痴。
我喊她回来是想说, 我总算感觉到一点难过了。今天这场丧事,本来就是我们共同的亲戚的死期。他在那儿烧成一股青烟,青烟都淡了,他彻底没有了,我才好不容易尝到一点难过的味道。我想问她有没有难过,哪怕也是短暂的一丁点。
她比先前更疲惫的样子。
她一屁股坐在地上。这是我见她最伤感的一次。我以为伤感终于像一只黑色蚂蚁,从她脚背爬到头顶的山坡,然后从高处一口咬下来, 让我这位姐姐的心也痛起来了。
———可她只是瞌睡来了。
我伸手去拽姐姐的衣领。在死者面前睡得像个死者是大不敬。
她眯缝着眼。含糊其词。
由她睡吧。我想。坐下来让她靠在我的肩膀上。这个时候她的眼睫毛离我更近。有人早年跟我说,眼睫毛长的人容易做贼。我眼睫毛也不短。所以长大以后每一天我都保持在正道上行走,保持善良,保持不占人便宜, 口袋里钱多的时候会往路边乞丐的碗里放下十块钱。因此,我也总是保持在乞丐与富贵之间。我怕一个人有钱了会做贼,太穷了也会做贼。
姐姐的呼噜声像河水, 驮着滚石而去的河水。我稍微动一动肩膀,呼噜声就小一小,但不会消失。她的喉咙松弛得像一根两指宽的皮带,贴在她活命的颈项上。她坐下来比站着更臃肿。整个给我的感觉就是:她是个有弹性的人。也可以说她活得比我明白和胆大。也可以说她顾不上那些异样的眼光。从她自衣兜里“刺啦”扯出塑料袋那天开始,她就是一个全新的她,谁也别想把往年那个战战兢兢的她再换回来。
往年她很瘦小,年纪也轻,仿佛一直要保持自己的身体只装得下一把月光。自从死了父亲后, 委屈就开始像沙子一样把她填满。
那天她死了父亲。她一个人紧紧贴着墙根站着。我也贴着墙根站着。你怕不怕?我这么问的话。不怕,死的是我亲爹。她这么回的话。
我们两个都还是孩子(至少心理上没有长大), 不知道如何招待丧礼上的客人。我们搓着双手仿佛若无其事。客人们挂完礼金就去旁边找熟人聊天。不知道他们为何那么开心:打扑克,打麻将,喝酒聊天说笑话。有一瞬间,我的耳朵一直在关注“一筒、幺鸡、八万”和东西南北风,姐姐也走神了,她眼睛直直的。后来到了饭点,女客们吃完就开始打包桌上的饭菜, 她们说这是在她们那个地方流行的,杜绝浪费,吃不完要打包带走。就在我和姐姐面前,表面上交头接耳,热热闹闹,实际上手脚麻利,抢来抢去,恨不得吵起来。后来院子里每张桌上只剩下一大片空碗,还有地上一大片垃圾。我们两个互相看了又看, 以为刚才发生的一切是在梦里。姐姐往前走了一步又退回来,退回来又想走出去,她战战兢兢像只落汤鸡,汗水把整张脸打湿了。我不知道她为何流那么多汗。
她父亲入葬以后过了好几天, 她跪在坟头突然说: 我感觉那天他们把我爹分吃了。
这个话我本来已经忘记, 到现在我跟她坐得近才想起来。
她睡醒了。脑袋从我肩膀上拿开。
起来,我带你跑一圈,练一练精神! 她说。说得那么清醒,像是刚刚从深水里游一趟出来。
我跟在她身后慢慢放开步子。她在前面左摇右晃,一个悲哀的大屁股,腰粗得像箩筐,上半个肚子和下半个肚子是平齐的,要不是胸部外扩挤着两边胳肢窝, 可以借此看出来她还有胸, 那就根本不知道她还有胸,头上毛发油腻并紧紧贴在头皮上。她跑了一百多米,风吹来吹去,也没吹起她的头发。
你多久没有跑步啦? 她问。
很久啦。我回。
你多少斤啦? 她问。
一百二十五斤九两。我回。
她在前面哈哈笑了两声。我就知道她要笑。并且她心里恨不得将过去说过的话再来一遍:死要面子。
我就是死要面子。一百二十五斤九两绝不说成一百二十六斤。我这么斤斤计较如何能有出息。她是这么看我的。我知道。
她回头拉着我的袖子, 往前狠狠跑出几步。我喊她跑慢点,我们又不是马,灰尘都踩起来了,她不听。
我们跑到殡仪馆外面的山包上。前两日刚刚过完立冬, 树木还绿, 青草没有发黄,但是天气瞬间就凉了。
她躺在条形石板上, 望着天空也望着我。她很平静,这个样子像个要讲故事的老年人。然后她跟我说,并非那些饭菜有什么好,而是她这么去做的时候,觉得心里很畅快。
想了想,认为是她父亲死的时候,那些人所做的事情给她留下了很重的阴影,毕竟当初我们还是少年, 毕竟心里还很空荡, 我们长在山区的孩子没有太多经历和见识,我们都很穷,无论谁家办了宴席,都很珍惜桌面上剩下的食物, 哪怕剩菜中掺着别人筷子上流下来的口水, 哪怕食物已经不干净, 我们都不在意。一头猪要喂一年,一只羊牵着跑几片山坡才长大,这样的我们不容许食物被蛮横地无端哄抢。何况那天的宴席并不是高兴的, 那天是她父亲的忌日, 她以为所有人都会悲伤得吃不下东西,谁知道他们吃不了还兜着走了。一些伤害轻易就能钻入少年人的心底。这种遭遇使她后来也陷入困局, 做梦似的无法走出困境。只有做出和那些人相同的举动,她才能感到一点点畅快。
我现在才明白她为何在父亲丧礼上满头大汗。如果是我,也会是那个样子。就好比轻伤的人容易喊疼掉眼泪, 重伤却是哭不出来的。
她从石板上坐起来, 望着山包下殡仪馆的丧宴,她的队友已经在“打扫”桌子了。
不要再倒那些东西,姐姐,那些东西吃多了不好。我说。我感觉自己始终压着火气,像什么人掐着我的脖子,虽然很生气却不得不慢慢地将说话的声音从喉咙缝隙里挤出来。我其实想说,我们已经长大了,有些事情忘了算了,反正它已经过去那么远。反正回想起来只让人痛苦。
她这回没有很生气骂我, 目光平缓地落在脚前草地上,她说:你没有经历艰难的日子,你不知道日子……
……我知道日子难过。
我抢了她的话。心里顿时有火燃烧,我在失去耐心。就像我母亲断定的那样,我是个心肠很硬的人。刚刚我愿意跟她出来跑步,就是想跟她说,过去的事情就算了,总不能翻来覆去就在那件事情里受折磨—哦,同时也折磨别人,人只要肯活着,就该抬起眼睛,哪怕眼睛里填满泪水也抬起来,只要不低头,总不至于哭得很难看。啊,我说糊涂了!我的意思是,她如今四处搜刮剩菜剩饭的行为比低头哭一场更难看, 一些馊了的饭菜她也打包带走, 那玩意儿能有什么用? 还不如正儿八经找个没人的地方哭一场。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跟着她出来跑一趟就是想把心里话说出来。可是一直没有说出来。
现在她又说起明天的日子难过。我就更难过了。我现在就感觉很难过,翻来覆去总是这句话对付我!
该死的!我说。不知道这话怎么就说出来了。
她抬起眼睛, 这会儿她的眼睫毛像一把屋檐草, 被大风掀翻了贴在上眼皮的陡坡上。她整个人瞬间变得好可怜、好穷的样子。我以为她将低头哭一场。谁知道她哈哈笑了起来。
你感到不耐烦了吗?她说。又说要是放在从前, 我这种态度会让她伤心好长一段时间,现在不会了,她觉得人是黑色的,黑色的东西容易沾灰,时间一长就越沾越多,越多越厚,越厚越动弹不得,越是如此,她心里的一些感觉就会变得迟钝, 像城墙一样厚的东西把她所有的感受都压得死死的。这样并不是一件坏事。对她来说是一件好事。她不再像从前那样敏锐地时刻感到惶惑不安、伤心和怨恨,不再做噩梦,不会在梦中看到父亲站在一片寸草不生的旱地上,满脸被日光晒得通红,在仿佛经历大火焚烧的土地上悲伤的模样。虽然,她偶尔觉得浑身沉重,也觉得被时间茧起来,也突然想从自己的壳子里钻出来, 可这种想法只是一瞬间就淡化了。
我被她的话震住。到此刻似乎才模糊明白,一些人的痛苦会变成硬壳。
我把她扶起来, 站在身旁。抻了抻脖子,像鸡啄米一样,说点什么说不出,就把所有话吞下去了。
姐姐,我说,我们吃饭去。先前没吃饱。
她好像很高兴我没有说一些安慰的话。伸手就把我的手牵着。是以前把我从激流中捞起来的那只手。右手。不用看就感觉出时间的刀片曾一天天割它, 在掌心边缘有刺,在掌心的中间也有刺。我不能低头,我不敢看。它是救我性命的手。它变成这样了。
我们手牵手, 仿佛小时候她牵着我在河边的田埂上找鱼腥草, 我们一人摘一把过年才开的黄花,然后她摇着花在前面走,我像傻狗一样跟在后面。她在前面边走边跟我说,头一天学校里教了一首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然后她就摔进水田。我拉她出来。那时候她很瘦,人也少年,水田也浅,轻易就能拉她出来。眼下我只是被她拖着走,也像个傻狗,连可以勇敢地“汪汪”叫两声都忘记了,在灰尘堆积生硬的水泥路上,手快被她捏成饼子。
到殡仪馆大门她才放开我的手。她突然说,今天难得高兴,就不要那些剩饭剩菜了。
我们走进吃饭的场地。她在前,我在后,她突然一下刹住脚步,险些被我给撞倒了。
好多人在抢剩饭剩菜,闹哄哄的,有说有笑, 就在我们两个的前方。她们都很麻利,一口吹开干瘪的塑料袋,抬起盘子盖下去。她们都很高兴,在桌子间穿来穿去,像蚂蚁,也像蟒蛇。
你不要去。我说。我看见她眼神在发呆。
她推开我,脸上没有笑容,也不愤怒,也不无奈, 熟练地从衣兜里掏出一只大号塑料袋,指头在舌尖沾一点口水,搓开塑料袋口,快速向桌子走去。像个灵活的……木偶。
晚间,死者入葬后,最后一顿饭顶着黑夜开始。殺了一只灰山羊。晚饭摆在露天场坝里。
姐姐又来到我身旁。一切像白天的重复,我还端着碗,一块羊肉咬到一半。
你今天真的不参加吗? 她说。
她只是习惯性问一问, 就像熟人见面好歹打一声招呼, 实际上不会有兴趣听我说什么答案。她端着一个喝水用的一次性纸杯(塑料袋肯定是用完了),拿着一双折成两半的一次性竹筷, 伸到我面前的盆中挑拣羊肉。哆哆嗦嗦的,半截竹筷捏在臃肿的手里不太能看见,就看见一个拳头,在菜盆上空晃来晃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