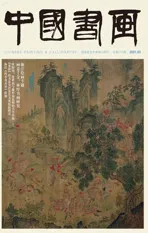陈淳《四季花卉屏》析微
2021-04-13闫子清
◇ 闫子清
现存最早的写意花鸟画卷轴作品是南宋法常的《蔬果图》。宋代开创了写意花鸟画的先河,明朝发展至鼎盛。在写意花鸟成形到风格成熟的这段时间,陈淳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陈淳继承并开拓了沈周、文徵明平稳静逸的画风,将其转换为奇逸肆纵的飞动风格,将书法融入画法。他的成就也影响了之后的徐渭,后世将二者并称为“青藤白阳”。陈淳是明代写意花鸟发展的承前启后者。本文对陈淳《四季花卉屏》展开研究,在陈淳作品中这幅画有独特地位,同时此立轴的细节处处体现陈淳风格成熟时期的笔墨特征。
陈淳,明朝中叶画家,字道复,号白阳山人,生于1483年,卒于1544年,跨越明代成化、弘治、正德、嘉靖四朝。苏州府长州县(今苏州市)人。苏州在宋朝便是全国米仓之一,被运河贯通,又处太湖旁,至明朝,随着当地织造业的兴起更是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中心。深厚的文化底蕴,造就了如赵孟頫、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沈周、唐寅、仇英、文徵明等一大批书画大家、巨匠。
陈淳生于一个传统的士大夫家庭,祖辈、父辈皆于朝廷任职,家境殷实。陈淳的祖父通晓诗赋,热衷收藏,与当时名家如沈周、吴宽有所交结。陈淳的父亲陈钥与文徵明私交甚好。幼时的陈淳聪慧伶俐,深得祖父宠爱,便在稍长时送入文徵明门下为徒。青年时亦步亦趋地跟随文徵明习画。继承发扬吴门画派本应是陈淳发展的正常轨迹,而《四季花卉屏》是在嘉靖二十二年(1543),也就是陈淳因一次冬日出游而意外染上风寒病逝的前一年创作的,展现的是在陈淳遭遇青年丧父,寄托于玄学,放弃仕途,转向承袭祖师沈周,师生疏远,家道衰败,这一系列转变之后沉淀下来的老道而纵逸的画风。
一、《四季花卉屏》创作背景
《四季花卉屏》创作于1543年,陈淳正值花甲之年,这个年龄对于一位文人画家而言,正是创作的高峰期,或自我风格纯熟的时期。实际上,从陈淳44岁所作的《和欢葵图卷》起,他的手法就脱离了对老师文徵明亦步亦趋的模仿,转而获得一种疏朗自如的动势。更突出的是《和欢葵图卷》画面的简洁,手法上不再是双钩填彩,转而使用了粉黄色直接依花瓣的形质没骨点写,用墨色混以花青色,施涩笔顿挫而形成叶片残破的自然状态;构图上则仅有主干一支花叶组合,一叶向右偏去,花、叶、枝仅靠笔墨和造型的变化来呈现。也就是说,从《和欢葵图卷》起,陈淳开始了新的风格尝试。之后的《写生花卉卷》《牡丹图》《竹菊图》可见陈淳在此新方向上的发展。陈淳真正开始得心应手地“大量”创作的时间点,应当是55岁,这一年有记载的手卷创作便有十六幅,间以立轴与扇面,而间诗间画的长卷正是陈淳非常有特色的布局,大量手卷题跋部分超过绘画。而到了创作《四季花卉屏》的1543年,这一年陈淳的作品数量在记载中倒是10年来最少的,尤其是对比下一年,也就是陈淳在世的最后一年,或许是他在对之前作品的反思。《四季花卉屏》纵341.5厘米,横100.9厘米,如此尺寸的巨幅在陈淳传世作品中极为少见。陈淳擅长的长卷,间书见画,几个部分为诗文、题跋所分割,但绘画部分却并不一定按照所绘事物实际情形分布,如《花果图卷》中的荷花、菊花、兰花、葡萄,到中段的竹石、秋葵,末段的水仙,这些花卉植被不需按照季节、品性而分组,可以互相穿插,也可以没有道理地凭空而出(如最后的折枝梅),这样的创作是极为随性,毋须有所顾虑的,每组花卉的疏密、走向,乃至节奏,全凭作者意兴,很是符合陈淳的性格。反观《四季花卉屏》中的排布则是极尽功力,将画面铺设得非常丰满,这样的构图在陈淳作品中并非孤例,尤其是立轴作品,如《湖石牡丹图》《山茶竹石图》,但这些作品从未在尺寸上接近《四季花卉屏》。1543年这个陈淳创作的“低潮”期,与这样一组“巨作”的创作有所关联。
二、《四季花卉屏》艺术特征
陈淳所作四季花卉的记载十分简略。但是这样尺寸的作品,显然不是即兴而作怡情养性的小品,此屏的题跋并不突出。四条屏为两两相对的形式创作,春夏对秋冬。

[明]陈淳 合欢葵花图卷 23.7cm×76.4cm 纸本设色 故宫博物馆藏
先是春屏,从画中最深处说起,是画面右上角的折枝桃花与杨柳。杨柳从屏画的右侧边缘伸出,主干在接近画面中心时直转而上,用笔老练苍劲,浓墨勾线枝条,加深褶皱与树洞,施淡墨于其他部分。杨柳两支主枝陡然直上,冲出画外,营造出一种充满力量的动势。柳叶用淡花青点染,疏密有秩。整株杨柳的下半部分被湖石遮住,并不显露。而这样一株“无根柳”,在画面仅仅显露的一枝,显得十分粗硕有力,亦有两分枝延出画外,是一种典型的代表活力的隐喻。杨柳与桃花的垂枝皆出画外,桃花用白色调少许胭脂直接点染,为画面注入呼应主题的春日的生意。垂柳与梅花多垂下,少有几支桃花向上,与柳枝形成对势,如此整个画面的上部便十分丰满,不见留白。再把视线向下,一湖石于杨柳下部,也同杨柳只露部分,用墨上浓淡参差丰富,边缘有所点厾。围湖石一圈,为没骨法画就的牡丹,用色浓艳,花繁叶茂,以至于枝条只能若影若现的穿插之中,牡丹填补了画面的中部,虽面积不大,但体积很重,平衡了整个画面。以上二者加以陂岸,构成了整幅画的中景。中景的湖岸向画面的左侧伸出,应出作为近景的对岸,近景屈于画面左下角,只一湖石,一株牡丹,些许兰草,但借此一块,与对岸共同造成了水流的一次转折,将画意延伸至画外,增添了一处动势。
到夏屏,首先占据画面大部的是一株芭蕉,在技法上使用了白描,十余片芭蕉叶各有姿态,虽无用色,但叶片的或老或新,或整或残,叶面的正侧背、翻转,穿插,都有所体现,画面繁而不杂,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功力,给予画面一种节奏上、空间上的秩序感。与上屏不同的是,此屏主题的芭蕉竖直挺立,虽有湖石遮挡,但细瘦的湖石没有妨碍画家交代的根部、茎部,且芭蕉也未伸出画外,这样几处不同,就使得春夏二屏的意境,或是说画意区隔开来,并不单调。芭蕉叶隙处,有点点紫薇穿插其中,紫薇的疏对芭蕉叶的整,设色对白描,细碎对宽大,形成了对比,同时也增加了画面的深度,与芭蕉互衬,更显繁茂。画中湖石姿态诡奇、高耸,比起春屏中湖石的完整,又是一种形态。湖石多孔洞,多凹陷,显出相当的前后深度,用浓墨勾线,淡墨皴擦,突出了其沟壑纵横的特点,在画面中,占据了相当的体积,与同样高大的芭蕉,一同组成画面中心。湖石之后,有数丛夏菊,红色间以黄色,不论是叶片还是花瓣,用色比春屏之中的牡丹更为浓艳、深沉,加之白描手法的芭蕉,使得夏屏颜色上的层次要丰富于春屏。近景中,以一株更小的芭蕉为主体,先前所说的芭蕉的特点,亦体现在了这一株,一小一大、一近一远形成对比。芭蕉前后,掩映了夏菊、芙蓉,周围散落小石,独成一景,与占据右上方几乎整个画面的主体形成照应。
再说秋冬二屏。秋屏以二棵松为主体,松树皮用勾圈笔手法,形质俱佳,松树的姿态蜿蜒,一部分伸出画外,一部分盘旋回来,显出一副老干虬枝的样貌。松树枝干用重墨勾形,淡墨皴擦,树干下部,从湖石背后伸出片片芙蓉,大小错落有致,勾茎手法爽利,质感上,中和了较为粗糙的松树乃至湖石,相当巧妙。湖石于二松之间,上部裂为两半,向右一半充实了画面中右,这是四季屏四幅画所共有的特征,即画面饱满,未有过多留白。回到画面上部,第二棵松树笔直向上,枝干上左转,伸出画外,又在画外转回到画内,与右下部的松枝形成相对的势。二松后皆有石榴花探出,石榴花的重色和长短交错的叶片,同大小相近的丛丛松针形成对比。作者如此安排处处对比,可以窥见他不希望让画中单独的一草一木成为绝对的重点,而是意在形成一种整体感,突出季节主题。

[明]陈淳 湖石牡丹图轴 122.5cm×52cm 纸本设色 广东省博物馆藏

[明]陈淳 秋葵图扇 故宫博物院藏

[明]陈淳 花卉竹石图扇 故宫博物院藏
冬屏像是与春屏相对,在构图上左右对称,在湖石与乔木的前后关系上,垂柳与柏树的枝干走向上,亦是相对的。柏树位于画面的最前,较之秋屏中的松树,更显苍劲,手法上主要以皴笔擦出树皮的纹理,形态上与松树一致,多转折,只是枝条画法快利,不似松树枝条多起伏;柏树的叶片较为细碎,与松叶的规整区别开来,但画中柏叶凝而不散,点叶的聚散则展示了柏叶的深度。柏树后的湖石,在四屏中走势最为明显,很好地占据了右侧的画面,将人目光引向画面右下角的一丛水仙。水仙叶用淡花青没骨写出,花则是双勾勾出,花间穿插二三根荆棘,水仙整体上的质感与冬屏整体上不同,较为柔软、幼嫩,中和了画面。再向上看,柏树后伸出数枝山茶,与石榴花在秋屏中的形态类似,只是花瓣较为分散,花蕊用淡黄色点染,花叶较为扁圆,不似石榴花叶细长,二者都很好地祛除了秋冬的肃杀之气。与春屏相同,冬屏也营造一处对立的陂岸,只是一处与较大的湖石走向一致的小石,掩住了水流的入口,使得水流较之春屏,更添一份静态。
三、《四季花卉屏》与写意花卉
继陈淳之后,进一步将写意花鸟发展到巅峰的,当属徐渭。从《四季花卉屏》来说,这组作品在陈淳大部分作品中算不上“意气”,或是说是出于“墨戏”的动机而创作,但是《四季花卉屏》中能传达的,恰恰是写意花卉中一个基本的理念,即“以形索影,以影索形”。陈淳认为,写意花鸟,区别于南宋院体花鸟之处在于对形的抽象,好比是灯下观影,对于一个物象,不再机械地去模仿其在自然下的形象,而是在观察它的“影”,一种更加模糊、更加直观的形象,而画家在从这样的“影”中重新提炼出“形”,经过这样形到影,再由影到形的过程后,在复现物象的形象同时,也可以传达出临摹所没有的“意气”,烦琐的自然形理在“影”的主观变动之下,为画家笔墨和造型提供了延展的空间,是画家个人风格的反映。而徐渭提出了“舍形悦影”,与陈淳一样提到“形”同“影”的关系,却更加激进,否定了形却用“悦”这样一个相当感性的词,拔高了“影”,反映到陈淳、徐渭二者风格上的差异。若陈淳的部分作品可归于“逸气”,那么徐渭的代表作品就可称为“狂气”,后者对于情感的传达更加强烈、露骨。
当然,就算从陈淳晚年的一组呈“收敛”姿态的作品中,也还是处处体现了对后世画家如徐渭的影响。以夏屏为例,陈淳对于多个物象,并未采用一种统一的风格,比如对比芭蕉的完整连贯的线条,再到紫薇上,便是相对松散自如的细碎,可见陈淳对物象的描绘方式的选择,是根据其本身特色而决定的,所谓以形索影,物象在保持对形的提炼的同时服务于对应的意味。同样徐渭在简化用笔的同时,在凝练对象的特征的基础上,也是为了传达一种情感。故而《四季花卉屏》尽管在风格上与陈淳的“典型”差异较大,也因为这样的冷静的秩序感而与后来徐渭的代表作有了更大的差异,然而将《四季花卉屏》从细节上审视一番后,在理念上是与徐渭一致的,即对于写实的重新解读,摒除“习气”而发扬“意气”。
总结
陈淳所作《四季花卉屏》画幅巨大,作于同一时间的《瑞珠仙影》可以与之媲美。但实际上,陈淳遗世作品中,鲜有规格如此之大的,且《四季花卉屏》四屏,画面中的湖石、花木品种繁多,画面之满意在不给作品太多留白,没有了通常的“戏作”“既醉,不知其草草也”的随性姿态。这可以结合陈淳当时处于稳定的创作环境有关,虽然经历了从生活变故到创作观念转向这一段时期,实际上到了晚年,陈淳与文徵明恢复了交往,后者也为其题诗,在这样一个风格已经有所成就的时期,陈淳在“老态日增,不能复事”的状态下,《四季花卉屏》实际上是一次“逆反”而又严肃的作品。
《四季花卉屏》中的每一屏实际上都能觉出一种繁茂的态势,就算是秋冬二屏,就所选取的意象而言,绝不透露出一分一毫的萧瑟之感,取而代之的则是颜色艳丽的如石榴、山茶等花卉与松柏相互穿插。
《四季花卉屏》抛去它的独特性,从画面中透露的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显示了陈淳在晚年的创作成熟。在这四幅画中,陈淳对各种花木使用了不同的技巧,如白描、双钩设色、没骨、大小皴擦,但却用熟练的穿插关系,使得整个画面统一起来。其中的任何单一的花卉,如牡丹、水仙、芭蕉、菊、桃花,都能在陈淳的作品中找出原型,这说明了陈淳对于各个物象的熟练。较之稍早的作品如《湖石牡丹图》《水仙湖石图》《四季花卉屏》中的湖石造景更为收放自如,细节也更加丰富,但是写意的逸气略微收敛,对应到笔法上即为用皴擦、浓淡、勾线让湖石偏向写实,更加工质。

[明]陈淳 四季花卉屏 341.5cm×100.9cm×4 纸本设色 广东省博物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