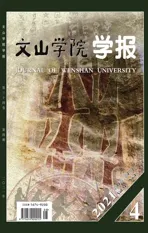从原乡记忆到民族家国:论楚图南的云南书写及文学思想
2021-03-08罗杰
罗 杰
(1.文山学院 人文与传媒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2.云南大学 文学院, 云南 昆明 650091)
云南书写是伴随着异质文化视野的开拓而兴起的一类文学书写,自“他者”将云南作为审美对象书写进文学文本中,云南形象从此逐渐在中国文坛中展现异域魅力。民国时期大批作家因国难机缘旅居云南,创作出大批关于云南形象的作品。而“一生心事问梅花”的楚图南,一生从云南开始又因学习、工作关系在大江南北留下轨迹,但其在文学著述中仍对云南怀以深厚的情思。楚图南以云南作为生命的启程,先后在昆明学习、生活、工作、革命,积淀了云南的情感体验,并通过大量的散文游记反复表述云南的原乡记忆和生命体验。其在昆明工作期间书写的《悲剧及其他》《刁斗集》《旅尘余记》等著述,以云南为文学创作的对象书写了思念家乡和追忆故友的家国情思,呈现了楚图南作为有良知的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的民族家国观念与思乡文化情怀,造就楚图南的云南书写能与20世纪初众多外省作家的云南书写形成对话,我们可从中窥探其独特的文学话语与文学思想。
一、原乡记忆中的云南书写
楚图南的文学创作和文化寻根活动基于云南承载着他童年经验的原乡记忆,对云南书写的原乡记忆暗合书写者审美意识的文学诠释。原乡记忆是指书写者出生地及成长时期形成的原初审美经验,即“原初审美经验作为经验元却伴随着审美主体的一生,是审美主体个人的生活环境中的人生经验、家庭教育、童年经验等形成的潜在生命基本结构。”[1]原乡记忆是书写者一生携带在审美意识中的创作原动力,它并不是作家当下及时的审美创作,而是书写者时过境迁或返乡后凭借对故乡过往的回忆进行书写,且已被植入在其后的社会活动变动和文学创作过程中,这也是影响楚图南文学著述中的云南书写及文学思想形成的重要因素。从《楚图南自传》中大致可以厘清其原乡记忆生成的轨迹,“一八九九年八月二十日,农历七月二十三日,生于云南文山县一个困苦的家庭。一九二三年,在高师毕业,回到云南昆明,任教于云南省立一中、省立女中和明德中学等校。抗战期间,回到昆明,担任云南大学教授和文史系主任。”[2]在楚图南的人生轨迹中,云南作为出生地与回忆中的故乡,集中体现了他的原乡记忆,折射出他作为一名“有为”作家如何敏锐感知民族家国的动荡变化。伴随着他学习、工作、革命斗争等少年时期的“离乡体验”与青年时期“返乡回忆”形成互动演化,建构起原乡记忆这股创作的原动力,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楚图南的书写云南的缘由。在云南积淀的情感体验为楚图南提供了对比其生活时间较长的北京与上海的认知态度,故其著述中有了多篇纪实性较强的关于云南点滴的散文书写。这也意味着抗战时期楚图南的返乡是接受进步思想后的新使命,乃至以跨文化心理诉求来开启原乡记忆中的云南书写。
书写者总是会以原乡记忆作为书写的对象,并且往往依据儿童经验来勾勒出文学想象中的故乡印象,彰显出此类文学书写纯真质朴的色调。楚图南原乡记忆中的故乡是这样的:“只是在我不知怎的,从这时起,幼小的心灵上,总是怅惘的。”[3]94“怅惘的”原乡记忆表述出其童年及成长经历过的生活苦楚,正如其所取笔名“高寒”的寓意,楚图南通过表述和想象书写了真正意义上的原乡“云南”。他从比照北京、上海等地中洞察到原乡云南自有“边地”落后的一面,但这正是促使他走出故乡到昆明求学,势必要离开“边地”到“大都会”去看看,成为通过努力得到去北京完成学业的动力。当学成归来原乡“边地”云南时,楚图南在昆明期间投入到传播优秀知识、致力边疆教育、投身社会活动、进行文学创作与研究,不间断地进行外国文学译介活动中。曾经生活过的云南构成其原乡记忆中的重要元素,这些生活阅历往往都会通过云南书写在文学文本中呈现。楚图南对云南观察的视角与其他外省作家自是不一样的,他在来去云南的返乡时空交错中获得了体悟生命的原乡记忆,正如楚图南所言:“我的故乡,也正是自己的清泉和草地啊。”[3]94以“清泉”与“草地”来形容故乡,如此这般深情的原乡体验蕴含着复杂的“三迤”情感和边地情怀,原乡记忆的文化情结成为其作为云南本土作家书写云南时的创作源泉之一,为其提供了丰富的生活题材、浓厚的原乡情感和众多真实可信的生活事件,在文学文本中体现出云南本土作家“原乡记忆”的本色。在这些蕴含着思乡情愫的原乡记忆背后透露出楚图南建构在文学文本中云南形象的审美形态,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他心灵深层中对云南的情感和依恋。
楚图南缘于原乡记忆的云南书写,并不是简单地对云南某人某物某事的文学再现,而是经过其文学思想的提炼,凝聚了一定的审美情感倾向。当我们考察楚图南的原乡记忆时,思考的是以何种记忆方式进行书写,以何种文学建构方式呈现。带有“怅惘的”原乡记忆包含着楚图南自身救亡图存的心理诉求与生命体验,是一种对云南本土文化自我反思后的文学表述。纪实性成为楚图南云南书写的重要审美特征,在其著述中表现为:在文学表现形式上,楚图南并未停留在对云南回忆性的一般书写,而是形成充满原乡话语和纪实性表述的散文体;在主题思想上呈现出基于书写者第一视角民族家国、民族文化的多重内涵;在表现手法上,展现了冷峻客观的写实笔触,将笔触深入最底层民众的心里;在情感态度上,蕴含着对原乡的浓情思虑,以此承载起其云南书写散文的朴实而厚重的原乡情感。在某种意义上,作为自我文化关注者且生于斯长于斯的楚图南,通过原汁原味的方言话语在文学文本中建构了真实的云南,这离不开源自生命冲动的原乡记忆。
在对云南书写的过程中,楚图南或许找到了离开故乡后又返乡时的身份认同,一种割舍不了的原乡记忆成为云南书写的初衷。源于对云南民族文化、文学发展的“原初性”反思,故楚图南的云南书写及文学思想必然受到其原乡记忆的影响,可以以此作为观照楚图南文学思想的一个视角。
二、作为民族家国的云南书写
抗战时期,大后方云南作为民族家国受难的文学镜像,昆明曾被冰心、老舍、沈从文等知名作家想象为“北平”。在旅居或寓居云南作家笔下,云南经众多作家的多重角度书写难免成为“落后”与“怀旧”、“野蛮”与“平静”、“边地”与“家国”交织在一起的社会总体想象物。当民族国家危机四起时,这些文学想象自然转化为书写者的民族家国意识。而楚图南笔下的民族家国是其云南书写永恒的主题,渗透着他与云南社会变迁的复杂情感,体现在原乡记忆的双重矛盾与审美反思中,在《悲剧及其他》中对人、地、事之类情愫的生命咏叹,《旅尘余记》中脚踏实地回归对现实层面的书写在《碧鸡关的故事》《记棕树营》《路南夷区杂记》《难忘的……》关于云南的人、事、景等纪实性散文中,从《记碧鸡关》昆明近郊的碧鸡关说起,到《棕树营》中昆明百姓生活的细节,再到路南彝族民俗风情,云南边地民众的劳作生活,《赶街子》中赶街时的底层百姓百态,都是浓重情感书写的体现。作为一个接受了且译介了外国文学作品的知识分子来说,用良知之眼来关注着这片土地上的每个生命,在大时代的苦难面前,云南世间众生百态激起了他的创作热情,也无不透露出楚图南浓烈的民族家国意识。关于云南的书写是作者切身的体验,楚图南是在民族家国意识下来关注云南本地人民生活疾苦,在深入到民间街头和田间地头后,他说:“可以看见我行走在天空或梦幻中的步履,已渐渐地踏在人间,踏在人间的泥土里了。”[4]此外,《村子里的疾病和瘟疫》《农村副业》等书写中,也透露出他深切关注云南百姓的生存境况,这类纪实性散文的主题总体上都忠实于云南百姓的真实生活和所遭遇的苦难,直面民生疾苦时楚图南是怀着鲁迅般“救救孩子”的呐喊来书写云南的。缘起原乡云南这份特殊的情感,转换为文学书写时楚图南以云南想象民族家国,云南成了当下苦难中国的缩影,这种书写是对故乡故人故事追忆的,也是对云南命运和困境的思考。从文学创作的题材到创作手法的运用,都表明了楚图南力图通过云南书写这一途径,以纪实手法极形象地呈现云南地域文化空间中的现实生活,以此来传达可以与外界交流的“文学对话”,以达到实现“故乡”与“家国”共有美好的未来。
为此,有必要了解一下楚图南云南书写中蕴含其人其文的独特话语。作为一名有良知的作家,他并未停留于文艺工作上的口头呐喊,更多的是深入云南底层民众中去了解民间疾苦,感知普通老百姓的所思所想。曾在河南开封、上海从事进步文化教育的楚图南,在昆明任教期间,看到了云南与中原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从救亡图存角度发表了多篇关于云南教育发展论述,如1921年在《云南教育杂志》上发表了关于《云南职业教育商榷》的讨论,1924年在《云南教育会月刊》上发表了《云南中等学校教师问题:我以为云南中等学校教师问题有急需解决者三项》《十三年度上学期投考省立一中学生成绩之研究》等。他科学理性地分析了云南地处边疆造成思想落后的教育现状,以及与北京上海地区的差距,但他认为抗战让云南原先的闭塞转变为大后方,并认为云南保存着良好的文化资源,这些涉及云南教育思考方面的报刊论述作为非文学层面的认知,亦是认知其为何以民族家国思想为云南书写途径之一。云南在战时的地理位置、文化教育、文化资源逐渐成为云南书写中的重要主题,云南文学形象自然也成为楚图南民族家国的云南书写内容。由此可知以教育思考改变云南命运与以文学唤醒劳苦民众的思想定位,促使楚图南成为携带着原乡记忆的理想追求者,同时又是心怀民族家国的文艺工作者,楚图南的云南书写体现了对文学“真实性”和“审美性”的反思。因此,在其云南书写的题材、主题、情感、表现手法等各方面有了明显的纪实性倾向,这与其他作家对云南书写时多采取抒情与怀旧的游记相比,多了浓重的原乡记忆与民族家国意味,形成了楚图南云南书写的纪实风格。将原乡记忆与民族家国意识交织在一起,楚图南的原乡记忆在云南书写过程中因民族家国而生成恋乡情结,云南书写因楚图南的民族家国意识被赋予强烈的“本土味”“人民性”和“人情味”,更贴近了云南人心中的云南形象。
民族家国意识视角的引入,可以洞察楚图南著述中云南书写的文学思想和政治文化维度。一方面,楚图南依据原乡记忆的期许和对民族家国的想象生成了更具思想深度的审美反思,突显出作为云南本土作家恋乡的文化情结,极力追寻原乡记忆中的情感体验。同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启迪的楚图南通过返乡工作,将个人的救民于水火之心投入到云南文艺建设上来。由于学界对楚图南有学者、革命家多重身份的既定印象,而对于楚图南在云南民族文化、文学发展、教师教育建设方面的探寻,对云南在近代社会变化中的思考,都不能脱离云南特定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考察。楚图南作为文艺工作者、云南教育工作的直接参与者,更能体会到云南社会生活的变迁。这些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渗透了楚图南的民族家国意识,在表述方式和思想内涵上拓展了楚图南云南书写的情感张力,可深切地感知到他对云南的忧患与用心。作品中真实自然流露出来的人道主义情怀,提升了楚图南云南书写的文学意味和审美指向,一种在原乡记忆与民族家国交织在一起的云南形象被建构在文学文本中。
三、云南书写与楚图南的文学思想
楚图南的云南书写是一面云南本土形象审美建构的文学镜像,从中折射出云南社会文化、民族生态、教育经济和书写者的文学想象,呈现了楚图南文学思想的生成演变历程,从勾勒原乡记忆的情感形式到赋形民族家国的审美主题,赋予了云南在社会变迁中新的文学生命和时代精神。对于寓居或旅居云南的众多外省作家,如朱自清、闻一多、汪曾祺、老舍、冰心等名家笔下的云南,与楚图南笔下的云南形象的差别表现为原乡记忆与民族家国的思想深度表述。外省作家虽然也携带着其原乡记忆和民族家国观念来对云南进行书写,不时有“淳朴”“闲静”“怡然”等臆想式赞美云南之词涌现出来,也在文本中建构关于云南的文学想象,只不过他们作为旅居云南的避难者,云南暂时填补了他们的家国梦和舒缓了战时的焦虑,故没有如原生作家楚图南与生俱来的认同感。然而作为原生书写者楚图南,在审视经济、教育落后的云南时,“纪实呈现”却为何成为其云南书写时在文学作品中反复表述的方式?这既与他本土作家身份和原乡记忆和民族家国有关,也与楚图南在云南文艺创作中倡导的文学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坚守了文学应有的人文关怀,“描绘平凡或不平凡的人生,以及作品受鲁迅、尼采的影响。”[5]楚图南与20世纪中国社会民主革命、中国传统文化及外国文学文化译介的关系十分密切,当他心怀民族家国的忧思来书写云南时,他为云南少数民族的未来呐喊:“永远逃避,也永远为灾害所迫袭的民族啊!我想总有这样的一天,中国的社会,会使你们从山林里重新走出来,抹去了你们心上的陌生和怀疑的心情,并看到了欢迎你们的衷心的微笑,和张开了的两手。”[3]57可见,楚图南的云南书写并不同其他外省籍作家,他对云南少数民族的新生活充满了期望,并努力为实现此目标而奋斗。他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思想的轨迹不能回避其在此间是如何认知云南社会现实的,所以究其著述中云南书写及文学思想的影响而言,应该思考楚图南与同时期旅居或寓居云南外省作家的云南书写,在自我与他者的比照中可以分析出同为中国知识分子在对待云南书写时的多样形态。
从原乡记忆到民族家国看楚图南的云南书写,结合其一生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外国文学译介等文艺工作来思考,如上文所述的云南书写及其所译介的外国文学活动,可以梳理出其文学思想包括了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坚守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启迪和指引。在北京高师学习期间受李大钊影响开始翻译马克思主义相关书籍,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提出了文艺创作要忠实生活的创作主张。这些学习心得均在其后的文艺工作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不仅在文学创作方面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现实主义文学创作原则,也在文艺评论方面要求文艺工作者要坚守历史使命与社会职责,提倡文艺有开启民智的认知功能。楚图南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学以致用,针对抗战时期云南文艺工作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二是提倡文学创作的人民性。他认为“真实的诗人,总是这么勇猛地唱出了时代的预言,也燃烧了民众胸中永不会熄灭的火焰”[6],包括欧美重要作家,如尼采、惠特曼、涅克拉索夫等。他注重选择民主自由观念强、提升民众身心自由的作品,以拓宽青年知识视野和提升精神士气,这些凸显了楚图南文学思想的“民主性”和“人民性”。楚图南提倡文学的人民性旨在拓展民众的知识视野,从中汲取有益于中国社会文化发展的养分,运用到云南书写的主题上,尤为明显地体现了写实风格,“死耗子是穷苦孩子的玩具”“口吐白沫倒地抽搐的战士”“穷苦妇女肿大的头”等真人真事真情的形象表述,真实反映人民群众的生活境遇,具有极强的震撼力。三是凸显“质朴且多彩”的滇云文化。为云南本土民族文化发声,是楚图南在云南文艺工作方面的努力,他不仅收集了数十首原汁原味的云南民歌,还发表文艺评论来思考云南文艺发展,如《抗战文学的现实主义与云南文艺》一文,对抗战时期云南文艺工作者提出了要从云南底层人民的苦难生活着手……,要担负起让云南人民觉醒的重任。这些彰显出楚图南践行“云南书写”的文学思想,与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变动之间有着复杂关系,给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云南书写找到了新依据,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从原乡记忆、民族家国与文学思想渗入云南书写中,可以看到由“走出大山”到“返回原乡”不同时期心理诉求的变动。楚图南在原乡记忆的苦楚中“探索”民族家国的前途,以及投入文学创作中以期寻索可以“对话”的云南书写,这些层面的思考,是将楚图南的文学思想置于20世纪中国的宏观政治文化中考察。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许多作家不约而同地书写了云南这个曾经被遗忘的“边地”,以及由此形成了文学想象中的云南。依此追寻云南本土作家楚图南因原乡记忆及云南印象所采取的文学策略,即通过楚图南对特定“故乡”云南的书写等文学活动考察,探讨楚图南文化记忆中原乡的审美特征和民族家国意识,以及楚图南“云南书写”生成的根源。概括来说,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原乡记忆作为文学创作的原初审美经验,凸显了楚图南云南书写的“原初性”。“原初性”体现了楚图南文学思想的“原创”与“根植”云南的审美特性,深厚的文化根基与恋乡情结融于纪实散文的笔触中,“回归原乡”成为其创作的动力,也是其文学思想的深度之一,楚图南的云南书写具有了一定的原创性和开拓性。另一方面是学成归来后楚图南的云南书写更强调“民族家国”。将原乡记忆转换为渴求改变云南落后现状的“文学对话”,以及从宏观大局来掌控文学作品的思想倾向,让其云南书写提升了文学创作和文学审美的格局。无论是基于原乡记忆的云南书写还是外国文学译介,影响着楚图南的文学思想能够参与其后的文化交流活动,或是主题思想、表现手法、文学样式等方面的审美倾向,都体现了楚图南对文学社会功能的总体思考。
目前,学界已从社会活动、民族文化、外国文学译介等角度考察楚图南的文学创作,楚图南的创作及文学思想如何缘于云南“原乡记忆”的影响,以及与其在云南出生、学习、工作、生活期间积淀的情感体验有何关联;楚图南的著述承载着其重要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思想,应反思“原乡记忆”具有怎样的价值?关于这些问题,尝试回归创作主体的情感体验,从一个创作主体审美体验的生成及对其创作的影响来看,集翻译家、作家、外交家、民主革命家于一身的楚图南,能与不同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构成“文学对话”,且与同时期外省作家的云南书写形成比照,楚图南著述与文学思想关系以及其民族家国观念的生成,突破了传统思维模式方法。云南本土作家应思考如何在文学文本中书写建构出云南形象,对“云南形象”在不同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的文学建构规律进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