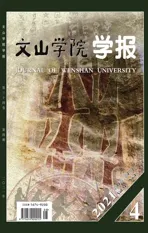文山壮族铜鼓舞的视觉审美元素及静态传承
2021-03-08李春燕
李春燕 ,刘 刚
(1.文山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2.文山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云南 文山 663099)
文山是铜鼓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有名的铜鼓之乡,目前全国8种类型的铜鼓(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遵义型、麻江型、西盟型)在文山均有发现,文山也是东南亚铜鼓文化的重要传播通道。云南文山壮族是学术界公认的古代越人后裔,也是从句町时期延续下来的句町古族的后裔。[1]在丰富的句町文化遗产中,承载着壮族自然崇拜与宗教信仰的铜鼓舞,是壮族铜鼓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积淀着壮族历史、文化、生产、生活且具有宗教寓意的民间舞蹈。文山壮族铜鼓舞的表演形式、风格特点反映了壮族人民的思想意识、社会面貌和审美心理等。每当有重大的节日庆典、婚丧仪式和宗教祭祀时,壮族都要祭铜鼓、跳铜鼓舞、喝铜鼓酒和唱铜鼓歌,如打鼓过年、三月三“祭竜节”和广南县贵马村的祭铜鼓仪式等都保留了远古朴质的遗风。
一、铜鼓舞的文化渊源
文山壮族铜鼓舞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主要分布于广南、富宁、麻栗坡、西畴、马关和丘北等县的壮族村寨,以广南县那洒镇贵马村、者兔乡里玉村的铜鼓舞最具代表性和独特性,至今仍保持原始的击鼓伴舞通神、祭神、娱神和祈福禳灾、繁衍后代的习俗。这些习俗世代相传,功能和作用及其蕴藏的深层文化内涵与铜鼓文化、壮族宗教文化和以“那”为主的稻作文化等紧密相连,探究其审美倾向,分析其视觉审美元素,了解其文化渊源,分析其艺术价值,契合国家倡导的关于民族文化传承、保护、创新的相关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铜鼓舞是铜鼓文化的构成要素
铜鼓是我国古代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重要的礼器,云南文山是铜鼓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其数量众多、类型齐全、分布密集是其他地区少有的。壮族作为文山的土著民族,早在青铜时代,其先民就创造了灿烂的铜鼓文化。壮族关于铜鼓起源的传说很多,流传较广的如始祖布洛陀为子孙创造铜鼓的传说,“这东西叫阿冉(壮语铜鼓),它就是地上的星星,他会帮助你们杀死毒虫恶兽和妖魔鬼怪,保护村寨,它会教你们唱歌跳舞,他身上有许多图案,还会教你们学本事的……”[2]181文山壮族铜鼓舞是壮族使用铜鼓时配套的舞蹈,其社会功能、文化内涵也附属于铜鼓文化。主要表现的是壮族传统宇宙观——三元观,即“天、地、水”三元,鼓面为天界,鼓身为人界,鼓足为水界,三者与生态系统中的人构成了一个复杂的内在观照的三元观。我们在对近现代出土的和民间传承的铜鼓纹饰研究中,可以洞察古代铜鼓舞及铜鼓文化的遗存。
1.鼓面多与图腾崇拜相关,通过图腾纹样和舞蹈纹饰祭祀“太阳神”“蛙神”等。图腾纹样包括太阳纹、乳钉纹、翔鹭纹、蛙纹等,舞蹈纹饰如云南文山开化铜鼓的鼓面“第七晕有舞人2组,每组有奏乐者4人(含吹笙击鼓)、徒手舞者7人,他们或手舞足蹈,或吹或奏,一派欢乐景象”[3]37鼓面代表“天”,主要用于娱神,祈求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和国泰民安等。从铜鼓人物动态上我们可以比对早期与现今铜鼓舞蹈动作的异同,蛙纹的频繁运用也反映出壮族先民的蛙图腾崇拜。
2.代表“地”的鼓腰和代表“水”的鼓足,纹饰主要与民俗文化相关。鼓腰的部分是古代壮族生活习俗的生动再现,舞蹈作为自娱,以鼓伴舞欢庆节日。如羽人纹、牛纹、鸟纹、船纹和干栏式建筑纹等;舞蹈纹饰分为羽人舞、仿生物舞(剽牛舞)、手巾舞和徒手舞等。又如广南铜鼓鼓腰上有14组羽人对舞和剽牛等图案,舞人们有的头戴羽冠,有的上身裸露,或手执钺、斧,或徒手,围绕神柱下拴的牛而舞,营造出剽牛热闹的场面。鼓足则主要以水族纹、水波纹、鼍纹等装饰,与壮族聚水而居的生活习俗一致。这些纹饰可以让人们对古代壮族民俗活动场景和壮族舞蹈文化的源流有一些直观的认识。
由此可见,铜鼓就是古代壮族宇宙观的臆想承载物,从铜鼓舞蹈纹饰所传达的丰富信息可以看出,铜鼓舞依附于铜鼓文化,体现了壮族的创造才能与审美情感。
(二)铜鼓舞中万物有灵的文化观念
壮族祖先相信万物有灵,包括日月星辰、山石水木、花鸟鱼虫等都是有灵性的,刮风下雨、打雷闪电即是神灵在作法,人们的日常劳作、生活习俗等都是由自然界的神灵来掌控的,因此把自然当作神灵来崇拜,认为任何生命个体都是值得尊重的。“万物有灵”的思想观念构建了壮族原生的巫术文化和麽教文化,同时衍生出师公、道公、僧公等再生型宗教文化。古代铜鼓舞受万物有灵的观念影响,主要用于巫术礼仪,包括宗教祭祀和丧葬祭祀,以祭祀神灵、祖先和死者等为主。
1.壮族祭祀的神灵是以麽教中最大的神布洛陀为核心,信奉“自然神、氏族神、图腾神、职能神”等的神灵系统。铜鼓乐舞是壮族先民敬神、娱神、通神和祈求功利的重要手段之一,以舞蹈为主体对其顶礼膜拜,如化身图腾、双手高举、屈膝、跺脚、踏步等,场面宏大,形式感极强。
2.壮族的祭祖仪式非常隆重,从其文化传承来看,壮族经历过“生殖崇拜、太阳崇拜、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历史过程”[3]112,而祖先崇拜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因此壮族对祭祖十分重视。祭祖用品主要有两类:一是食物类,花糯饭、米酒、鸭子、土鸡、“刀头”(一块正方形煮熟的猪肉)等;二是物品类,染了鸭血的冥币和供香,纸或布制成的冥间生活用品等。食物中颇有特色的就是花糯饭,也叫五色糯米饭,由红、黄、蓝、白、紫五种颜色组成。除了祭祖用品,壮族祭祖最有特色的首推祭铜鼓和跳铜鼓舞。祭铜鼓必须用粽粑、米酒、鸭血祭祀,将铜鼓“洗面洗身”后,将酒、鸭血滴在鼓面,焚香祭鼓。“跳铜鼓舞,壮语称‘弄宁董’,主要分布在文山州境内的广南、麻栗坡、富宁、西畴、马关、丘北等县的壮族村寨”[4],而同一个县不同村寨的祭祖所重视的节日是不同的,如广南县城里“跳铜鼓”祭祖以春节最为隆重;广南那洒镇贵马村最为盛大的铜鼓舞是在“七郎节”时跳。
(三)铜鼓舞受农耕文化影响
壮族村寨的居住模式:“聚族而居,面对稻田,背靠大山,河流环绕”[5]。文山壮族世代靠水而居,靠稻而活,创造了以“那”为特色的稻作文化,包括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和色彩斑斓的精神文化。文山州广南县用“那”为地名的就不少,“那”在壮语里即稻田的意思,同时以“那”为核心衍生了一系列的与稻作相关的舞蹈。如铜鼓舞、“弄娅歪”(即牛头舞)等。广南县那洒镇就完整地保留了一套与农耕相关的铜鼓舞蹈,如正月开始、二月开荒、三月撒谷种、四月拔秧载插、五月薅秧、六月栽棉花薅棉花、七月过七郎节、八月打谷、九月收棉织布、十月收粮酿酒、冬月摆桌子谢酒宴、腊月刷鞋洗衣过大年。舞蹈表现了一年十二个月每个月的农耕生产过程,在伴奏上,使用雌雄两面铜鼓,雄鼓较大代表太阳,雌鼓较小代表月亮,可演奏组合成十二种音调,简称十二调。人们利用舞蹈来祈愿丰收、祭告神灵、祈盼甘霖和祛除灾祸等。
二、铜鼓舞的视觉审美元素分析
铜鼓舞的视觉审美元素内容丰富,表现手法古朴,其自然性、愉悦性和代代相传的承袭性贯穿始终。铜鼓舞的美包括了自然美、生活美和艺术美,统一了视觉审美元素。
(一)自然美元素
自然赋予了古人最早的审美,朱光潜说“中国人对待自然是用乐天知足的态度,把自己放在自然里面,觉得彼此尚能默契相安,所以引以为快。”[6]在这里人与自然是和谐统一的,它的自然性和社会性也是统一的。自然性是形成自然美的必要条件,包括自然物本身的属性,以及形状、色彩、线条和声音等基本要素;社会性则根源于实践活动。壮族先民崇尚神灵,不仅敬奉它们,而且还幻想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影响自然现象或社会现象。壮族人民通过铜鼓“可以冲刷心灵的痛苦和烦恼,获得吉祥和慰籍;可以聚集力量、克敌制胜、度过难关;还可以表达心愿和诚意,并祈神保佑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国泰民安。”[7]壮族铜鼓舞的自然美元素表现在通过形体模仿自然时所表现出的“天人合一”,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景象,如有用羽毛装饰身体模仿鸟类和蹲在地上,双臂高举,手指张开模仿青蛙的造型;还有对神灵、祖先祭祀和祈福时敬神、娱神的舞蹈动作。这样的美我们还可以从壮族的礼乐重器的舞蹈纹饰、重大的节日庆典和祭祀等上找到一些线索。如1919年出土于广南县阿章村的“阿章铜鼓”是目前文山州发现体型最大的铜鼓,鼓腰饰有装束讲究、头戴羽冠的舞人对舞图案和杀牛图案,舞人化妆成鹭鸟或作腾飞状、或手持斧钺作杀牛状、或作饮酒猜拳状。从一些古代舞蹈文献上看,阿章鼓上的舞蹈纹样似乎和古代舞蹈中的“羽舞”或是“皇舞”相似,“羽舞舞者持白色鸟羽而舞,也有说就是执雉尾而舞的翟舞,用于祭四方”。“皇舞舞者头上插着鸟羽,上衣也饰以翡翠的羽毛。手持五彩鸟羽而舞,用于祈雨。”[8]有的铜鼓纹饰模仿青蛙、鱼、马、翔鹭等自然生物,舞人的造型有站的、蹲的、坐的、躺的,有的双手高举,有的手执斧钺等,这些审美元素可以看出壮族先民敬畏自然。在“祭牛魂”“祭稻魂”“祭竜”等习俗跳的祭祀舞,及与图腾相关的舞蹈元素都体现了壮族热爱自然,亲近自然的审美观。
(二)生活美元素
舞蹈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把生活中琐碎的素材提炼加工,使之能发生秩序和联结,舞者通过模拟生活中的场景,调动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根据积累的生活素材,重新组织对生活的认识,利用逼真的情绪来感染自己和观赏者。这是一种生活经验的集中提炼,是“一杯能使他们陶醉的醇醴而酷烈的酒”[9]。壮族铜鼓舞传承至今,原始舞蹈中的宗教神秘元素已逐渐淡化,生活本身的幸福与美好逐渐成为壮族铜鼓舞的审美追求。而作为追求美好生活的壮族铜鼓舞中的生活审美元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作为生产生活审美素材的提炼。壮族铜鼓舞仍保留着农耕文明时期社会生活的痕迹,如砍柴种田、养猪养鸡等农业生产和饲养禽畜的元素依然是铜鼓舞的主要表现内容。广南县那洒镇的铜鼓舞亦是典型,通过稚拙朴实舞蹈动作将生产技能、天文历法、四时节令等传授给下一代,把生产和生活中所具有的地域环境、风俗习惯等民族特色文化转化成舞蹈的神韵。二是由宗教审美演变而来作为节日、婚嫁等具有娱乐性质的审美。壮族铜鼓舞是重大节日庆典、讨亲嫁女等生活习俗的重要仪式,壮族村寨会在寨中场院或是办喜事的主人家跳铜鼓舞表示庆贺或迎客。如广南县者兔乡大寨村的壮族铜鼓舞“在敲打铜鼓时,用牛皮绳拴住铜鼓耳朵,吊在支架上,一人手拿木棒敲打鼓面,另一人手拿竹条敲打鼓身作伴音,后边一人手拿木盆或桶在鼓腔处合音,一敲一合,使鼓声优美、洪亮。”[2]192“舞者以鼓声为节奏,围城圆圈起舞,气氛欢乐祥和,热闹非凡。”[2]192在这样的庆典仪式中,同样包含壮族人民对生活的娱情娱己的审美愉悦,正如壮族民间故事中表述的:“人们要唱歌跳舞了,也擂响铜鼓。人们庆祝节日了又用铜鼓盛糯米饭、肥牛肉和甜米酒……”[2]184壮族铜鼓舞的生活美元素除了以上两个方面,还包括古朴稚拙、粗矿奔放的动作;平缓稳健、节奏缓慢的舞步;构思巧妙、独具特色的服饰等,这些元素与壮族人民生存的地域环境、农耕文化、宗教信仰密切相关。
(三)艺术美元素
艺术美是人们审美的主要对象,是艺术家的审美认识,是理想美的现实存在,它唤起观赏者特殊的情感,满足观者的审美需求。文山壮族铜鼓舞源于生活,是对本民族的历史进程和生活的写照,却不同于现实生活,它的艺术美体现在铜鼓乐的“乐想”和舞蹈的“意想”上,前者满足听觉需要,后者满足视觉需要,又共同承载了本民族的心理需求。铜鼓舞的艺术美主要表现于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铜鼓是铜鼓舞形成艺术美的物质媒介,它承载着古老浓厚的壮族文化,独特的形式美和原始的自然美。同时我们从铜鼓纹样上也可以看到,原始铜鼓舞的视觉元素,如石寨山型的广南铜鼓的纹样中,舞人装束非常讲究,化妆成鹭鸟,舞姿有双手两侧摆伸或曲肘张指,“作翔鹭腾飞,或一手执钺,或一手执斧,举手蹬腿,作等待上场砍牛之状”[2]78;文山州的开化铜鼓第7主晕,也有两组舞人“每组有奏乐者4人(包括吹葫芦笙、击铜鼓者),徒手舞者7人”[2]77等造型元素。这些包含于铜鼓文化中详实的舞蹈动作今天已经无从考证,但这些保留在铜鼓纹样中的审美元素却以形式美的方式向观者传情达意。千百年来,由于生活习俗、生态环境、生产方式等的变化,壮族铜鼓舞在动作、节奏、风格上都发生了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其艺术美都与壮族人民性格特点、精神气质和审美需求息息相关。
其次,舞蹈是空间与时间组合形成美的艺术,主要的形式单位是线,通过线的流动、组合来引起人们的审美快感。正如英国艺术评论家克莱夫·贝尔所说“以某种独特的方式组合起来的线条和色彩、特定的形式和形式关系激发了我们的审美情感。”[10]4他还说到:“把线条和颜色的这些组合关系,以及这些在审美上打动人的形式称作‘有意味的形式’,它就是所有视觉艺术品所具有的那种共性。”[10]4文山壮族铜鼓舞从形式元素上可以从音乐和舞蹈两个方面来看。从音乐来看,主要以铜鼓为主,并配以其他乐器伴奏,铜鼓音色浑厚、翁脆,声音悠远、立体,彰显了铜鼓乐的古拙沉稳。从舞蹈方面来看,铜鼓舞属于集体舞蹈,队形变化多样但不复杂,如半圆形、一字型、交叉对跳等;舞蹈和肢体动作矫健有力、简单朴实,如屈膝颤动、跳步向前、直(屈)肘甩手巾等;舞蹈内容主要表现对神灵的敬畏和农耕文化的生活状态。这些不正是贝尔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吗?古拙沉稳的音律节奏,农耕、祭祀等的场景营造,简单朴实的肢体动作,对心中信仰和生活的热爱,使平凡的现实融入审美意境,既是和谐的形式,也是心灵的表现。
三、“静态”的视觉传承
随着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文山壮族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面对新文化的冲击,铜鼓舞这项民间传统表演艺术生存的空间也越来越小,而且铜鼓舞的表现方式是以现场展演为核心的“活态”传承,不但要依靠传承人的表演,还需要一定数量群众的参与,这些都是导致铜鼓舞在现当代社会中艰难生存的重要原因。在国家和政府对非遗文化保护的各项措施及努力下,铜鼓舞传承的一些问题得到了初步的解决,如传承人的延续,资料数据库的收集存储,重大节日的组织、宣传、表演,媒体和网络的信息传播等,以提高人民大众对铜鼓舞的认知和喜爱来达到保护传承的目的。但这些措施在传承的方式上主要还是以传统传承方式为主,审美元素不够清晰、信息传播较为零碎,很难使每天要面对庞大信息量的受众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何在既保持传统的“活态”传承基础上,挖掘利用铜鼓舞和铜鼓文化中的视觉审美元素,集合新的更具时代性的文化创意、包装、宣传手段和形式,拓展“静态”传承的可能性和思路,以更具当代性、更为清晰的铜鼓舞视觉审美元素和通过设计、升华、整合的信息碎片给人们带来更新颖的审美体验,丰富铜鼓文化的传播和传承途径。
(一)视觉信息图像化编码
美国传播学专家保罗·M·莱斯特说过:“今天的现实是,我们周遭的世界以视觉为主要媒介,我们对世界的理解不是通过文字,更多是通过视觉信息。”[11]视觉信息的来源主要有三类:一是眼睛直接从客观事物的表象上获取;二是将客观事物的表象先经过图像化编码,再使用媒介传播;三是大脑里存在的虚构信息。在这里,我们就第二点对壮族铜鼓舞进行分析。铜鼓舞具有瞬时性、多样性和现场性等特点:瞬时性,即审美对象不是静止的,获取的审美感受是瞬间、即时的,这一特点不能使受众放大或放慢视觉去深层体悟,加强审美感受,这就需要对铜鼓舞进行直接地、即时地从审美对象上提取审美造型和元素转化为图像并为之编码。现场性,观众在现场观看时,受现场气氛的影响会产生和现实生活某种相似性的联想,而这种联想也是瞬间的,离开现场也就随即消失了。因此对现场图像化编码,将原型提炼并经过艺术联想再现的形式对审美对象再创造,既可以保留原生文化的特点,又可以使审美对象个性化、普及化、图像化。视觉元素编码后的丰富性和时尚性可以增强审美对象的传播速度和宽度。
(二)开发视觉审美创意产品
在经济全球化和飞速发展的旅游业大背景下,文化创意产业给民间“非遗”艺术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民间工艺品的价值定位已不再是“粗糙廉价”的低层次产品,而是不可替代、唯一的具有专利性,能够产生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的文化创意产品。文山壮族铜鼓舞经过视觉审美图像化编码,系统地从形式、内容上整体设计;在保证原汁原味的传统审美魅力上,从现代科技、现代设计思维中拓展创想思维;同时建立明晰的铜鼓舞文化相关设计品牌,将铜鼓舞的视觉审美元素有机地融入各种文创产品的包装、装饰图形,民族生态旅游的环艺设计、网络平台页面设计等,把壮族铜鼓舞推向国际市场,才能更有效地将铜鼓舞文化传承下去。
(三)合理利用公共文化设施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日常生活里已不仅限于物质生活和低级、表面的精神的追求,越来越多的人走进博物馆、美术馆和演播厅等寻求艺术带来的高层次精神享受。公共博物馆教育、美术馆教育等早已不是陌生的词汇,提取壮族铜鼓舞审美元素以“静态”的呈现方式进入博物馆、美术馆,对人民大众宣传教育,潜移默化,不仅可以提升民众的视觉审美素养,还能达到传承“非遗”的效果。铜鼓舞的“静态”呈现方式如绘画、雕塑、模型、摄影、标志、招贴、吉祥物、卡通、热转印等等。另外,网络、手机平台的广泛使用和普及,又为铜鼓舞“静态”呈现提供更广泛的的空间和可能性。
四、结语
文山壮族铜鼓舞是文山壮族人民集体智慧的创造和壮族文化的结晶,是一种有声有形的独特的艺术语言形式。千百年来它一直以“活”的、动态的形式传承至今。通过对铜鼓舞的视觉审美元素的分析和提取,将“活态”的舞蹈传承,变为“静态”的艺术创新型传承,结合现代媒体、现代设计,商业、文化等运作手段,使更多的人了解文山多彩的民族文化、了解独特的句町文化、了解神秘的铜鼓文化,在追寻民族历史和先人足迹中,在时代精神的引领下,走出新的文化传承、文化自信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