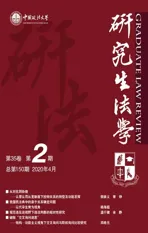破除“交叉询问迷思”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交叉询问与职权询问比较研究
2020-06-10邓皓元
邓皓元*
一、问题的提出:“交叉询问迷思”的产生、表现及其破除进路
交叉询问(cross-examination)[1]在中文的语境下,“交叉询问”一词有多种含义:(1)指英美法系对抗制审判模式下进行人证调查的基本模式,由主询问、反询问、再主询问、再反询问等环节构成;(2)特指由申请传唤证人一方的对方向该证人发起的“反询问”,是对抗制人证调查中的一个环节;(3)指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所规定的对质权(the right of confrontation)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文在第一种含义上使用“交叉询问”概念,在第二种含义上则用“反询问”一词。和职权询问[2]本文将职权主义诉讼形态下典型的人证调查模式概括为“职权询问”。学界对职权询问模式的系统性研究较少,故在此略作说明。与交叉询问相比,职权询问的特征是:(1)法官依职权主导询问;(2)包括控辩双方以及被告人本人、被害人及其代理人在内的多种庭审主体都有询问权,而非仅控辩双方有询问权;(3)各询问权主体根据审判长的安排依次发问,而非由控辩双方交替询问;(4)同样实行不当询问禁止制度,但更强调法官职责的作用。职权询问模式的具体内容会在下文随论证的深入逐渐展开。 还需说明,本文避免使用“轮替询问”这一术语。林钰雄教授首先将德国职权询问制度归纳为“轮替诘问”(Wechselverhör),并指出其是与“交叉询问”(Kreuzverhör)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询问模式。参见林钰雄:“轮替询问之法庭活动(上)”,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0年第12期,第2页。此后,“轮替询问”成为学界指称德国人证调查制度的特定中文概念。然而,在德语文献中,Wechselverhör指的是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讨论德国刑事诉讼改革的语境下提出的新的由当事人主导的人证调查制度。尽管Wechselverhör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39条规定的Kreuzverhör有所区别,但两者都是当事人主导的人证调查制度,因此在不严格意义上,两者有时也被视作同义概念。因此,以Wech selverhör或其中文直译“轮替询问”指代德国职权询问并不妥当。关于Wechselverhör和Kreuzverhör两个术语在文献中的使用情况,vgl.Roxin, Die Reform der Hauptverhandlung im deutschen Strafprozeß, in: Jescheck/Lüttger (Hrsg.), Pro bleme der Strafprozeßreform (1975), S.56; Weigend, Wechselverhör in der Hauptverhandlung?, ZStW 100 (1988), 733; Roxin/Schünemann: Strafverfahrensrecht, 26.Aufl.(2009), S.332; MüKoStPO/Gaede, 1.Aufl.2016, StPO § 239 Rn.2.分别是当事人主义[3]“当事人主义”和“对抗制”是指称英美法系典型诉讼形态的两个概念,一般认为,前者更多地用于指称民事诉讼,后者用于指称刑事诉讼。本文对此不作特别区分,在相同意义上使用“当事人主义”和“对抗制”两个概念。和职权主义诉讼形态下人证调查的典型模式。我国奉行职权主义诉讼传统,然而在人证调查制度改革问题上,学界却一直对对抗制下的交叉询问情有独钟;在职权询问备受冷遇且理论研究尚不充分的前提下,引进交叉询问制度却似乎已成通说——本文将这种现象称为“交叉询问迷思”。
(一)“交叉询问迷思”的产生
早在20世纪末,便已有观点主张中国借鉴日本,实行审判长指挥下的交叉询问。[4]参见叶向阳:“质证制度及立法之完善”,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2期,第45页;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7~268页。世纪之交,美国著名律师弗兰西斯·威尔曼所著、系统介绍交叉询问制度魅力及其技术经验的《交叉询问的艺术》一书的中译本[5][美]弗兰西斯·威尔曼:《交叉询问的艺术》,周幸、陈意文译,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进一步激发了学界对交叉询问的热情,系统译介英美交叉询问制度的文章开始在我国发表,[6]参见龙宗智:“论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交叉询问制度”,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第82~93页;陈健民:“美国刑事诉讼中交叉询问的规则与技巧”,载《法学》2004年第4期,第109-115页;易延友:“英美证据法上的证人作证规则”,载《比较法研究》2008年第6期,第65~81页。移植交叉询问制度呼声渐起。
移植论者多主张建构控辩双方主导询问、法官补充询问的询问构造,确立申请证人出庭一方先行询问规则以及完善不当询问禁止规则(特别是对全面禁止诱导性提问规则的改革),[7]参见甄贞:“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程序设计与论证”,载《法学家》2000年第2期,第39~50页;左卫民:“刑事证人出庭作证程序:实证研究与理论阐析”,载《中外法学》2005年第6期,第661页;陈卫东、王静:“我国刑事庭审中交叉询问规则之重构”,载《人民检察》2007年第22期,第18~21页;龙宗智:“我国刑事庭审中人证调查的几个问题——以‘交叉询问’问题为中心”,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5期,第22~32页;顾永忠:“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辩护突出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85页。更激进的观点还主张引入反询问范围受主询问范围限制的规则。[8]参见陈岚:“我国刑事审判中交叉询问规则之建构”,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6期,第112页。另一种更温和的主张是,只有征得审判长同意,才允许在反询问中就主询问范围以外的事实进行提问。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证据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97页。这些主张多以交叉询问的事实真相发现功能为根据,个别研究还阐明了交叉询问的程序正义价值。[9]陈永生教授指出,在美国,交叉询问是作为基本人权的质证权(即对质权)的一个要素,参见陈永生:“论辩护方当庭质证的权利”,载《法商研究》2005年第5期,第89~96页。易延友教授指出,对质权的核心内容是对证人进行交叉询问的权利,参见易延友:“证人出庭与刑事被告人对质权的保障”,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第162页。这些研究多认识到交叉询问制度需要包括庭前证据开示、保障证人到庭、传闻证据排除、询问技术训练在内的前提条件,其中的少数研究揭示了交叉询问制度与陪审制的内在关联。[10]龙宗智教授指出了专业法官审判与事实认定者的被动性存在冲突,参见龙宗智:“论我国刑事审判中的交叉询问制度”,载《中国法学》2000年第4期,第84页。樊崇义教授主编的研究成果也指出,陪审制是交叉询问制度的需求性制度基础:(1)陪审团只负责事实裁决而不负责法律适用;(2)陪审团保持被动,不主动询问;(3)陪审团审判无需说明理由。参见樊崇义主编:《刑事证据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553页。总体上看,这些研究的基本思路往往是,首先考察英美交叉询问制度内涵—然后分析我国人证调查制度与交叉询问制度的差异—最后对交叉询问制度进行“取舍”,择其“可用部分”主张加以引进。至此,移植交叉询问蔚为通说,这与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和证据法学学界以英美法知识背景为主不无关系。[11]关于这种状况,可参见左卫民:“从引证看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载《法学研究》2013年第5期,第75~96页。
(二)“交叉询问迷思”的表现
“交叉询问迷思”有两大表现,一是“功能迷信”,二是“移植偏执”。
—“功能迷信”是指对交叉询问功能优越性的迷信。学界似乎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在发现事实真相的意义上,交叉询问的功能必定优越于职权询问。然而,实证科学并未证明交叉询问与职权询问何者更有利于发现事实真相。[12]See Mirjan Damaška,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and Factfinding Precision, 123 U.Pa.L.Rev., (1975), pp.1095-1103.制度功能的根据存在于制度结构之中,要对两者的功能进行比较,应当从制度构造中寻找依据。当前,我国学界对交叉询问制度功能和制度构造关联的系统性研究还比较缺乏。在功能视角下,仍没有得到回答的问题是:交叉询问通过何种制度构造、在何种意义上对发现客观真实发挥作用。在相关研究尚不充分的前提下贸然得出交叉询问具有功能优越性的结论,似乎有先入为主的嫌疑。
—“移植偏执”是指,在对交叉询问所依托的制度和文化环境缺乏系统研究的前提下,不顾我国与英美法系国家截然不同的司法制度和文化环境,执着于移植交叉询问。发源于英国的交叉询问制度运行于特定的司法制度和文化传统之上,交叉询问功能的发挥以这些制度和文化要素为前提。如要将交叉询问制度移植到我国,必须回答的问题是,这些条件在奉行职权主义诉讼传统的我国能否得到满足。如同达玛什卡教授所指出的,“跨越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之间事实认定制度的移植将给接受国司法制度带来严重的压力。必须仔细研究预期移植与新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必须始终考虑接受移植的文化是否已经准备好,或者是否能够准备好接受预期改革的更广泛影响。”[13]Mirjan Damaška, The Uncertain Fate of Evidentiary Transplants: Anglo-American and Continental Experiments, 45 Am.J.Comp.L.(1997), p.852.日本、意大利、法国乃至德国等诸多职权主义国家都曾在不同程度上引进了交叉询问制度。交叉询问在这些国家的实践状况如何?交叉询问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与这些国家的职权主义诉讼传统发生冲突?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仍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14]在这一方面有所贡献的是张卫平教授在民事诉讼领域所作的研究,参见张卫平:“交叉询问制:魅力与异境的尴尬”,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第143~157页。由此可见,对交叉询问与司法制度和文化环境的关联,无论在理论意义还是在经验意义上,研究都还很不充分。
与“交叉询问迷思”并行的是对职权询问的冷遇。[15]值得注意的是施鹏鹏教授从职权主义诉讼传统出发对职权询问所作的系统性研究,参见施鹏鹏:“职权主义与审问制的逻辑——交叉询问技术的引入及可能性反思”,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4期,第57~67页。在现代法治国家中,德国是实践中奉行职权询问而不采交叉询问的典型;然而,中国大陆对德国职权询问的研究凤毛麟角,[16]值得注意的是肖晋副教授所作的研究,参见肖晋:“德国刑事庭审询问方式改革:司法对立法的背反及启示”,载《刑事法评论》2008年第2期,第318~329页。相关知识来源几乎完全限于《德国刑事诉讼法》法条、教科书和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所作之基础性研究。[17]这里的教科书指[德]克劳思·罗科信:《刑事诉讼法》,吴丽琪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德]托马斯·魏根特:《德国刑事诉讼程序》,岳礼玲、温小洁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台湾地区学者所作的基础性研究,可参见林钰雄:“轮替询问之法庭活动(上)”,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0年第12期,第1~25页;林钰雄:“轮替诘问之法庭活动(下)”,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0年第13期,第18~39页;林山田主编:《刑事诉讼法改革对案》,元照出版社2000年版,第270页及以下。语言障碍和资料匮乏导致对德国职权询问的研究往往停留于法条文义,对职权询问制度规则的教义学阐释、职权询问制度和职权主义诉讼形态的关联研究都还比较匮乏,对职权询问实践样态的认识更是付之阙如。由此可见,在比较法意义上,学界在人证调查制度方面的知识结构仍是很偏颇的、不完备的。
(三)“交叉询问迷思”的破除进路
在实践方面,2017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人民法院办理刑事案件第一审普通程序法庭调查规程(试行)》(下称《法庭调查规程》)等“三项规程”并开展试点,标志着人证调查制度规范化改革进入新阶段。日益深化的庭审实质化改革要求理论界提出符合国情的洞见,而在诉讼形态的意义上,职权主义仍然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在理论方面,职权询问和交叉询问是两种成熟的人证调查模式。职权询问和交叉询问的对立统一,是职权主义和当事人主义这一对基本范畴的对立统一[18]学理上,当事人主义——职权主义的二元对立历史悠久。据达玛什卡教授的考据,这种区分在12世纪便已出现。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比较视野中的法律程序》(修订版),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页。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学术成果中,目前已知较早提及两种诉讼传统区分的是英国法官、思想家福蒂斯丘爵士在1468~471年用拉丁语写就的《英国法律之礼赞》(De laudibus legum Angliæ)一书。该书分析了大陆法系和普通法系刑事诉讼程序的区别,并“在描述性和规范性意义上使用这些区别”。See Maximo Langer, In the Beginning was Fortescue: On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Adversarial and Inquisitorial Systems and Common and Civil Law in Comparative Criminal Procedure, in Liber Amicorum in Honor of Professor Damaška, Duncker & Humblot, 2016.在法国,刑法学家奥尔特朗1839年出版的《比较刑事立法教程》据信是首次将职权主义与对抗制进行学术比较的著作。关于法语文献中“职权主义”“对抗制”概念的起源,可参见施鹏鹏:“为职权主义辩护”,载《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第279~280页。在德国,法学家密特麦尔(Mittermaier)在其1834年出版的《刑事证据论》中明确提出,“刑事诉讼程序可分为两种基本形式,即控告式(die Form des Anklageverfahrens)和纠问式(die Form des Inquisitionsprocesses)”,并分析了两者的区别。Vgl.Mittermaier: Die Lehre vom Beweise im deutschen Strafprozesse nach der Fortbildung durch Gerichtsgebrauch und deutsche Gesetzbücher (1834), S.29ff.尽管有其局限性,但这一对范畴在比较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中一直处于基础地位,并启发了诸多研究成果,至今仍富有时代意义。See Máximo Langer, Strength, Weakness or Both? On the Endurance of the Adversarial-Inquisitorial Systems in Comparative Criminal Procedure, in Jacqueline E.Ross & Stephen Thaman (eds.), Comparative Criminal Procedur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8, pp.519-536.在人证调查领域的具体展开。专研交叉询问而忽视职权询问,于改革实践而言似有舍近求远的嫌疑,于理论发展而言也是不负责任的。“交叉询问迷思”立基于偏颇的知识结构和不充分的理论研究,不符合时代要求,应当予以破除。
“交叉询问迷思”的知识论成因是对职权询问的不了解。因此,破除“交叉询问迷思”的知识前提是将职权询问与交叉询问共同作为研究对象,对其进行同样细致的考察与检视。德国是实践中只采职权询问而不采交叉询问的典型国家,故本文对职权询问模式的展开以德国为样本。本文将运用德国法学文献和庭审笔录,还原德国职权询问的制度样貌及其实践形态。美国是将当事人主义诉讼的对抗性发挥到极致的国家,也是交叉询问制度之运用最具典型性的国家之一,故本文对交叉询问制度的展开将以美国为重点,必要时兼及其他国家的情况。
本文对交叉询问和职权询问的比较研究,采结构—功能主义(the 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方法。在比较法学领域,结构—功能主义方法主张从制度结构、制度功能及其相互联系入手,进行制度比较。在制度内部,制度结构是制度功能存在的根据;在制度外部,制度结构与制度环境的联系是制度功能得以发挥的条件。人证调查制度的结构可划分为三个方面:横向构造、纵向构造和微观构造。横向构造反映的是人证调查过程中各诉讼参与方之间的关系。纵向构造反映的是人证调查过程各阶段在时间序列上的关系。微观构造反映的是人证调查制度对调查方式和调查内容的规制关系。从制度结构入手,可对交叉询问与职权询问的功能原理与制度环境作出公允比较,并对中国人证调查制度的定位和发展方向形成清晰判断。
二、交叉询问与职权询问的功能比较:破除交叉询问“功能迷信”
作为证据调查制度,交叉询问的基本功能是发现事实真相,英美法系国家的理论和实务界都对此赞赏有加。然而,交叉询问在功能上是否优越于职权询问制度?制度结构是制度功能存在的依据。下文从制度结构入手,对交叉询问和职权询问进行功能比较。
(一)横向构造
1.交叉询问的横向构造及其穷尽式信息挖掘功能
交叉询问的横向构造是两极化的辩论式询问。在对抗制审判模式下,控辩双方各自主张不同的案件事实,学理上,控方主张的案件事实称为“控方案件”(prosecution’s case),辩方主张的案件事实称为“辩方案件”(defense’s case)。庭审中,控辩双方各自提出证人,通过交叉询问证立己方的事实主张并驳斥对方的事实主张。相应地,对每一证人的询问中,本方通过主询问证立己方的事实主张,对方通过反询问对本方的事实主张加以驳斥。陪审团处于居中地位,被动观察双方的举证活动,不主动介入。因此,在交叉询问中,各诉讼参与方的关系集中体现为控辩双方的高度对立关系。
交叉询问的横向构造具有穷尽式挖掘信息的功能。基于双方诉讼利益的高度对立,主询问中未被提及的事实、影响证言精确性的事实、影响证人可信度的事实会在反询问中得到披露,由此增加人证调查环节所提供的信息量。而信息增量是发现真实的前提。[19]对这一观点的精辟论证,可参见元轶:“庭审实质化压力下的制度异化及裁判者认知偏差”,载《政法论坛》2019年第4期,第94~95页。司法中的事实认定,不是裁判者通过亲历方式利用感官系统能动地直接认识知识客体的过程,而是根据证据进行经验判断的过程,是对过去事实的观念重建,这个过程只能充分接近案件事实而不能完全复现。为此,需要在可采性的范围内为裁判者提供尽可能充分的证据信息作为判断资料,使其发现更多事实部分之间的相互连结,以实现对案件事实的构建。威格莫尔指出,“在这一点上,交叉询问的功用是独一无二的。”[20]John Henry Wigmore, Treatise on the System of 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 Including the Statutes and Judicial Decisions of All Jurisdi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04, §1368.
2.职权询问的横向构造及其穷尽式信息挖掘功能
职权询问的横向构造是多极化的研讨式询问,即审判长指挥并主导询问的同时,多个诉讼参与方享有询问权。在德国,法院负有澄清义务(Aufklärungspflicht),“为查清真相,法院依职权应当将证据调查涵盖所有对裁判具有意义的事实和证据材料。”(《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44条第2款)[21]参见《德国刑事诉讼法典》,宗玉琨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年版,第193~194页。本文引用的《德国刑事诉讼法》法条译文均来自本书,下不赘。据此,审判长(Vorsitzende)主导证人询问并在证人陈述后首先向证人发问。其后,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40条的规定,参审法官(besitzender Richter)、检察院、被告人、辩护人及陪审员(Schöffe)均享有向证人提问的提问权(Fragerecht)。提问权的主体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诉讼参与人。[22]Vgl.MüKoStPO/Gaede, 1.Aufl.2016, StPO § 240 Rn.4-5, 10-18.
多极化研讨式提问的功能在于,“允许可能从中受益的诉讼参与人通过尽可能充分地利用人证,实现对诉讼证据的充分研讨(vollständige Erörterung),从而助益于实体真实之发现。”[23]MüKoStPO/Gaede, 1.Aufl.2016, StPO § 240 Rn.4.“对法官而言,这是形成自己意见的必要前提;对被告和辩护人而言,这是正确辩护的必要手段。”[24]Löwe/Rosenberg/Gollwitzer StPO, 23.Aufl., StPO § 240 Rn.1.为使多极化研讨式询问的功能机制得到形象化的说明,现举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地下党案第21个庭审日(2013年7月10日)中对证人Sabine的法庭询问为例。当日法庭就被害人Enver Şimşek的谋杀案听取证人证言。2000年9月9日,被害人被两名持枪男子从面部枪杀。案发时正好开车经过现场的证人Günther B.出庭作证。
证 人 我星期六与儿子一起出门,首先去回收中心处理旧家具,然后我们开车返回。当时车窗是放下的,我们驶过那个停车场,那里有辆卖花的车。那一刻,我们听到了几下巨大的金属撞击声。两名身穿自行车服的男子迅速离开流动卖花车。我也不知道他们跑向什么方向了,我必须往前开,因为我身后还有车。这两个男人大约有二十岁,也许更大些,其中一个戴着Base-Käppi款式的帽子。当时肯定已经是接近下午1点了,回收中心要在下午2点关闭。货车的方向传来了三、四次重击,车门还是开的。我记得,自己当时特别惊诧:这样的地方竟然还能做生意。
审 判 长 您怎么知道那是金属的撞击声呢?
证 人 如果今天回想一下的话……但是当时看不到具体动作,那两个男人手里什么都没有。确实够让人担心的,但仿佛也不必做些什么。周一,我们在报纸上了解了这一事件,并向警方报了案。
审 判 长 您当时开车多快?
证 人 不超过50,那是市区。(审判庭里传来笑声)
审 判 长 关于那辆白色车,您还能想起什么?
证 人 推拉门是敞开的,正好向着从行车道上能看见的那一侧。那两个人没有奔跑,但是走得很快。他们穿着自行车服,但我根本没有看到自行车,根本没有。现在整个事情已经过去13年了,我已经不记得了。我只知道,当我们开车经过那里时,我能听到两声金属的声响。这不是正常现象。
审 判 长 您能形容一下那两个男人吗?
证 人 他们20到30岁,个子很高,超过一米八。他们穿着黑色骑行短裤和深色T恤。
审 判 长 在2010年,您曾受过纽伦堡刑警的询问。那时他们给您看照片了吗?
证 人 没有。
(法庭向证人展示科隆Keup街的通缉犯图像,这些图像是2004年6月9日发生炸弹袭击后拍摄的。可以看到一个有尖下巴,戴帽子、穿T恤的男人。)
被害人代理人 您对此是否有印象
证 人 我只能大概确认这个人的身高。当时他穿的衣服不一样,更运动些。但是他的脸我不记得了。
辩 护 人 您是否曾经被问过,这个人看起来像哪种人?在您2007年的询问笔录中,您说:“我认为这两个是南欧人,因为我注意到他们黑暗的肤色。”
证 人 我不认为我这么说过。
辩 护 人 您印象中的男人,是皮肤黝黑、黑头发的男人吗?
证 人 他们的发型很短。无论是黑色还是棕色,我都不记得了。[25]Ramelsberger/Ramm/Schultz/Stadler: Der NSU-Prozess (2018), Tag 21.
这段笔录反映了德国职权询问的典型形态:首先由证人进行连续的自然陈述。此后,审判长通过发问对证人证言进行必要的检验(“您怎么知道那是金属的撞击声呢?”“您当时开车多快?”)并引导证人提供更多信息(“关于那辆白色车,你还能想起什么?”),案卷所载的证人先前陈述会成为比对的依据。之后,其他各诉讼参与方均有权就自己关心的问题向证人发问,以为法官心证基础之补充。在这一过程中,法官询问占主导地位。
尽管法官在证人询问中起到主导作用,但各诉讼参与方行使提问权的独立性受到很高程度的保障。具体而言,只要问题不违反不当询问禁止条款(《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41条),则法官既无权改变问题,也无权要求提问者撤回问题。法官无权要求提问者事先将问题提交法院。只有为判断问题准许性(Zulässigkeit)之需要,法官才可以要求提问者解释问题。另外,《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40条的提问权不仅保障提出问题的权利,还保障获得答案的权利—在证人不援引沉默权的前提下,法官在必要时有义务致力于答案之获取。[26]Vgl.BeckOK StPO/Gorf, 35.Ed.1.10.2019, StPO § 240 Rn.3-4.
由此可知,德国职权询问制度和美国交叉询问制度都保障控辩双方不受任意干预的提问权,职权询问制度还保障更广泛庭审主体的提问权利,各诉讼参与方均可基于自身诉讼利益通过向证人提问挖掘有利信息。因此,德国的法庭询问制度同样能起到穷尽式的信息挖掘作用。具体而言,(1)法官的职责和专业能力会将法官提问涵盖所有对裁判具有意义的事实;(2)被法官所遗漏的,证人隐瞒或未提到的,对某一方有利的事实,可以通过该方的提问得到揭示;(3)影响证言准确性和影响证人可信度的事实可以从享有提问权的各方—实践中往往是由富有经验的法官—的提问中得到揭示 。
事实上,职权询问所能提供的信息量比交叉询问更大。[27]值得注意的是,达玛什卡教授和托马斯·魏根特教授都持这一见解。See Mirjan Damaška, Presentation of Evidence and Factfinding Precision, 123 U.Pa.L.Rev., (1975), pp.1093-1094; Thomas Weigend, Is the Criminal Process About Truth: A German Perspective, 26 Harv.JL & Pub.Pol'y, (2003), p.160.从询问主体上看,职权询问允许广泛的庭审主体参与询问,而交叉询问只允许控辩双方询问,尤其是不允许作为事实认定者的陪审团提出任何问题。这意味着,如果说交叉询问下待证事实只能被两道相反方向的光束照亮,那么职权询问下的待证事实是被来自各个不同方向—包括作为事实认定者的法官—的光束照亮。从询问方式上看,交叉询问只允许证人回答提问者的特定问题,职权询问则允许证人首先作大段自然陈述。这意味着,就提问所未涉及但对案件具有意义的内容,证人在职权询问下仍可提供信息,在交叉询问下却无能为力。与此同时,如在下文中所要提到的,证人进行自然陈述的顺序、方式和内容本身也对判断证人证言的可信度有重要意义,这一维度的信息在交叉询问中却没有存在空间。
(二)纵向构造
1.交叉询问的纵向构造及其反对补强功能
交叉询问的纵向构造,是乒乓式的交替询问。证人出庭宣誓后,首先由本方对证人进行主询问,之后由对方进行反询问,此后双方认为必要时,本方、对方还可进行多轮的再主询问、再反询问。也就是说,询问权在“本方—对方—本方—对方”间呈现“乒乓式”的交替轮换。
在威格莫尔看来,这种纵向构造具有反对补强功能。一方面,反询问在主询问后立刻进行,通过反询问所揭示的证词改变或不实之处更容易被法庭察觉,这有助于补强反询问者所要实现的反驳效果。如果反询问与主询问之间有更长的时间间隔,这种反驳的效果将大打折扣。另一方面,在反询问中,对证人证言进行驳斥的信息源,正是由该证人本人提供的。与由其他证人作证提出反驳相比,这种自己否定自己的“戏剧性对比可以使证明效应得到倍增”,“从其他证人那里得到同样的事实与反询问之间的区别,就像缓慢燃烧的含硫火药和快速闪光的炸药之间的区别。”[28]John Henry Wigmore, Treatise on the System of Evidence in Trials at Common Law: Including the Statutes and Judicial Decisions of All Jurisdic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Little, Brown, and Co., 1904, §1368.反对补强功能的作用机理在于,在一方陈述己方案件的过程中,通过突出和强调的方式提示裁判者注意另一方的反对意见,以维持这一过程中裁判者注意力在双方间的必要平衡,促进裁判者作出公允判断。
反对补强机制通过快速引出反驳和突出证言矛盾来强化反对意见,其作用机理是非常微妙的,意义也非决定性的。
2.职权询问的纵向构造
职权询问的纵向构造,是线性的依次询问。证人出庭后首先进行陈述,之后由审判长对证人进行提问,此后其他庭审参与方几乎都享有询问权。提问的顺序由审判长安排,没有明文规定。实践中,一般的顺序是参审法官,陪审员,检察官,辩护人,被告人,其他诉讼参与人。[29]Vgl.Kraß, Die Frage in juristi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körpersprachlicher Sicht, ZRP 26 (1993), 266 (267); MüKoStPO/Maier, 1.Aufl.2014, StPO § 69 Rn.11-14; KK-StPO/Schneider, 8.Aufl.2019, StPO § 240 Rn.9.
值得注意的是,学理上认为,提问的顺序并不具有特别的意义,平等武装原则(Waffengleichheit)对提问顺序也不构成任何要求或限制。[30]Vgl.KK-StPO/Schneider, 8.Aufl.2019, StPO § 240 Rn.9.实际上,人证调查制度纵向构造是其横向构造在时间维度上的自然延展。与横向构造相比,纵向构造的意义往往是附属的。
至于威格莫尔所言之反对补强功能,在职权主义制度下并无存在的必要。在职权主义国家,法官由于负有全面调查事实之义务并受过专业训练,无需通过这种机制维持其注意力在对被告人有利和不利证据之间的平衡。
(三)微观构造
1.交叉询问的微观构造及其证言质量保障、证人保护与庭审效率保障功能
交叉询问通过禁止不当提问,以保障证言质量,保护证人并保障庭审效率。
典型的不当询问,是不当使用诱导性问题(leading question)。原则上,主询问中不得使用诱导性问题。因为主询问中的证人是由提问一方申请传唤的,一般而言对本方是友好证人,很可能因为受到本方的诱导、迎合本方的意思,做出不符合其本意或回忆的证言,从而妨害真实之查明。但当本方证人变为敌意证人时,则允许使用诱导性提问,因为此时敌意证人已站到对方的利益立场上,不存在受到本方不当暗示的危险。另外,在为展开证人证言所必须时[31]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611条(c)款规定,“在主询问中不应当使用诱导性问题,除非为展开证人证言所必须。”如在儿童或者成年证人十分无知、羞怯、低能或者英语非常糟糕以至于适用其他方法也不能明白律师意图的时候,或在证人记忆已枯竭,即证人在已被引导到询问主题上却没能说出律师所希望他说出的全部信息时,往往允许使用诱导性问题。参见[美]约翰·W·斯特龙主编:《麦考密克论证据(第五版)》,汤维建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6页。,或与案件核心问题无直接关系的预备性、入门性、过渡性事务上,或对专家证人进行询问时,一般也允许使用诱导性问题。此外,不当询问还包括重复问题、意在引发争论的问题、复合问题、臆测性/评论性问题等。回避问题的回答也被视为不当。[32]See Mueller C.B, Kirkpatrick L C, Evidence, 4th ed., Aspen Publishers, 2008, pp.580-585.这些不当情形,与交叉询问的价值目标相悖。
庭审中,一方在认为对方提问构成不当询问时可提出异议。法官根据《联邦证据规则》第611条的规定,有义务对询问证人的方式与顺序作合理控制,以使这些程序能够有效地确定真相,避免浪费时间以及保护证人免受骚扰或不当困窘。
2.职权询问的微观构造及其证言质量保障、证人保护与庭审效率保障功能
德国职权询问制度也有类似的不当询问禁止规定,并同样起到证言质量保障、证人保护和庭审效率保障的功能。《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41条第2款规定,对于检察院、被告人、辩护人及陪审员在法庭询问中所提出的不适当或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审判长有权驳回。
这里的“不适当问题”(ungeeignete Frage)是规范概念,学理上分为基于事实原因不适当的问题、基于法律原因不适当的问题、重复性问题、暗示性问题和诱诈性问题(Suggestiv- und Fangfrage)。基于事实原因不适当的问题,是指无助于发现实质真实的问题,价值判断问题、法律问题、不明确问题均属此类。[33]Vgl.MüKoStPO/Gaede, 1.Aufl.2016, StPO § 241 Rn.9-10.基于法律原因不适当的问题,包括不当询问证人住所(在《德国刑事诉讼法》第68条第(二)项规定的证人有权不披露住所的情况下)、不当询问有损名誉的事实和前科(《德国刑事诉讼法》第68条a)、证人对其享有拒绝回答权的问题(《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5条)、某些涉及商业秘密或专利秘密的问题等。[34]Vgl.MüKoStPO/Gaede, 1.Aufl.2016, StPO § 241 Rn.13-18.重复性问题的本质特征是对事实之发现全无助益,但就已提问过事项的具体细节进行追问时不在此列。[35]Vgl.MüKoStPO/Gaede, 1.Aufl.2016, StPO § 241 Rn.19-20.暗示性问题基本相当于交叉询问制度中的诱导性问题,诱诈性问题是指其中隐含逻辑谬误的问题,暗示性极强。传统理论主张,暗示性问题应一律禁止。[36]Vgl.Kraß, Die Frage in juristischer, sozialwissenschaftlicher und körpersprachlicher Sicht, ZRP 26 (1993), 266 (267); Roxin/Schünemann: Strafverfahrensrecht, 26.Aufl.(2009), S.320.新近的有力观点则主张对暗示性问题的准许性作具体判断。一方面基于类型化方法,对暗示性较强的几种问题形式进行严格控制;另一方面通过考察证人的年龄、记忆可靠程度、心智水平和作证状态等因素,把握证人的易受暗示性程度。基于对问题暗示性程度和证人易受暗示性程度的权衡,对暗示性问题的准许性做出决策。[37]Vgl.Ott, Das Fragerecht in der Hauptverhandlung, JA 2008, 529 (531f); MüKoStPO/Gaede, 1.Aufl.2016, StPO § 241 Rn.23.
“与案件无关的问题”是指与待认定事实及其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在直接和间接意义上都没有关联的问题。旨在测试证人记忆力和可信度的问题不在此列。判例认为,典型的“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包括不适于确定真相的问题、只涉及与被告人之外其他人有关之事实的问题、在实体和程序意义上均无意义(bedeutungslos)的问题等。[38]Vgl.MüKoStPO/Gaede, 1.Aufl.2016, StPO § 241 Rn.28.
德国职权询问中的不当询问种类,可总结如上表一。审判长基于上述原因驳回问题时,必须附有明确的理由。这里的“明确”,是指提问方可据此调整其问题或就该驳回决定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38条第2款提出异议(Beanstandung)。[39]Vgl.MüKoStPO/Gaede, 1.Aufl.2016, StPO § 241 Rn.6-7.另外,在证人回避问题时,在证人不援引沉默权的前提下,法官在必要时有义务致力于答案之获取。[40]Vgl.BeckOK StPO/Gorf, 35.Ed.1.10.2019, StPO § 240 Rn.4.
作为(证人证言)质量保障条款(Qualitätssicherungs vorschriften),《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41条第2款对不适当问题和与案件不相关问题的禁止性规定服务于保障证言质量进而发现实体真实这一基本价值目标,其中“基于法律原因不适当的问题”之禁止集中体现了职权询问的证人保护功能,“重复性问题”之禁止和特定条件下对暗示性问题之准许集中体现了庭审效率保障功能。
总体上看,职权询问和交叉询问所禁止的不当询问种类大体相当,两者的微观构造功能等价。两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对诱导性问题(暗示性问题)的态度上。另外,在交叉询问,对不当询问的禁止主要通过当事方的法庭异议实现;在职权询问,不当询问之禁止在根本上是审判长的职责。
(四)小结
基于制度结构,本节对交叉询问和职权询问的功能进行了细致比较,比较结论可总结如表二。

表二 交叉询问与职权询问制度功能之比较
作为事实调查制度,交叉询问具有(1)穷尽式信息挖掘功能;(2)反对补强功能;(3)证人保护与庭审效率促进功能。职权询问制度同样具备第(1)(3)项功能,而第(2)项功能则不为职权主义审判所需要。因此,交叉询问和职权询问制度功能等价,两者并无优劣之分,将交叉询问移植到大陆法系国家的职权主义法庭中,并无必要性。
三、交叉询问与职权询问的制度构造成因比较:破除交叉询问“移植偏执”
交叉询问和职权询问功能等价,两者之所以形成不同的制度构造,是制度外部环境不同所致。在诸法律部门中,程序法的功能的发挥尤其依赖于外部环境。“如果激发国内改革的源泉是一种外来的理念,而且这种理念所来自的国家具有一套不同的程序制度,这种程序制度根植于人们对待国家权力结构的不同态度以及不同的政府职能观念,那么,改革者们必须对此保持高度的谨慎。”[41]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致中国读者的引言”第2页。作为事实查明制度的交叉询问和职权询问,其功能的发挥仰赖于本源国特定的司法制度和文化观念。本节依次从横向构造和纵向构造的角度分析交叉询问和职权询问制度构造的成因和根据,以揭示两者制度环境之显著差异,从而破除不顾外部条件一味主张移植交叉询问制度的“移植偏执”。
(一)横向构造成因之比较
交叉询问和职权询问横向构造风格迥异。林钰雄教授分别以“辩论赛”和“研讨课”比拟两者:前者“目标在于贯彻自己主张,打倒对造论点”,后者则“由参与者轮流问答,可以陈述自己意见或对他人提问题,以期越辩越明。”[42]参见林钰雄:“轮替诘问之法庭活动(上)”,载《台湾本土法学杂志》,2007年第12期,第10页。人证调查制度横向构造的差异,取决于两种司法制度下不同的证明格局。
1.交叉询问横向构造的成因是对抗制下的两极化证明格局
交叉询问的横向构造是两极化的辩论式询问,其成因是对抗制下两极化的证明格局,即每一方都极力证明己方的事实主张并驳斥对方的事实主张。具体而言:(1)在开庭前,律师会与本方证人进行接触并对法庭上的交叉询问进行预演。这种预演,往往就证人陈述的内容、方式等作出安排。[43]美国律师实务中的常见做法是与证人就证词和法庭询问进行反复的预演和练习,参见[美]托马斯·A·马沃特:《庭审制胜(第七版)》,郭烁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7页及以下。一种反对的观点则认为证人准备的重点不应是让证人记诵证词,而应是让证人熟悉法庭环境并建立自信,这种观点可参见Herbert J.Stern and Stephen A.Saltzburg, Trying Cases to Win,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2013, Chapter 13.(2)在主询问中,证人陈述受制于律师提问。具体而言,无论律师使用封闭式问题还是开放式问题,证人的陈述都会被律师的问题切割成多个部分。[44]律师实务上认为,无论在主询问还是反询问中,都有必要通过问答方式将证人陈述切割成多个部分,以实现对证人证言之逻辑和顺序的控制。See Tanford, J.Alexander, The Trial Process, 4th ed, LexisNexis, 2009, pp.228, 315; Robert McPeake, and Evan Ashfield, Advocacy, 17th ed, Oxford Univ.Press, 2014, pp.151, 169.证人只能在律师问题的引导下按照其规定的顺序和逻辑进行陈述,既不能自行安排讲述的方式,也没有机会就提问事项以外的问题向法庭提供信息。在这个意义上,证人实际上只起到传达本方事实主张的喉舌作用。(3)在反询问中,律师通过语言技术控制证人证言。法律语言学的研究表明,在美国法庭的反询问中,律师往往通过攻击证人可信度、施加压力迫使证人同意和控制信息的方法促使证人说出与其本方立场相反的内容,从而达到提问方的证明目的。对语法结构、程式和语篇策略的巧妙安排都可以达致这种目的。[45]参见[美]John Gibbons:“法庭上的语言运用和权力支配”,陈文玲译,载《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5-13页。大量的研究表明,“反询问不仅用于检验证据,而且还用于陈述证据,以便加强本方案件、严格控制证人,使他们只给出有用的答案,并通过提问直接与事实认定者‘交谈’。”[46]关于这些研究的情况,See Gavin Oxburgh, Trond Myklebust, Tim Grant, and Rebecca Milne (eds.), Communication in Investigative and Legal Contexts, John Wiley & Sons, 2016, p.183.

图一 对抗制审判结构示意图[47] See Paul R.Rice, Roy A.Katriel, Evidence: Common Law and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6th ed., Matthew Bender, 2009, p.3.
这种对抗性极强的两极化证明格局,是对抗制审判结构(参见图一)决定的。在对抗制审判中,法庭不对事实查明负有职责。原则上控方承担证明责任,而庭审事实之提出则全仰赖控辩双方之提出。案件在观念上划分为“控方案件”“辩方案件”,证人也被划分为“控方证人”“辩方证人”。从庭审流程上看,对抗制刑事审判的完整构造中涉及案件实体内容部分的四个阶段是:(1)公诉方主讼(prosecution’s case-in-chief)。这一阶段是对控方案件的展开,其基本方式是对控方证人进行主询问。借由控方证人之口,控方所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各个方面得以在陪审团面前建构起来。每个证人的主询问后,辩方有权进行反询问(此后还有再主询问、再反询问)。(2)辩护方主讼。这一阶段是对辩方案件的展开,其基本方式是对辩方证人进行主询问。借由辩方证人之口,一幅更有利于被告人的事实图景得到构建。例如,辩方证人可能证明被告人一贯品行良好,正直亲和等。每个证人的主询问后,控方有权进行反询问(此后还有再主询问、再反询问)。(3)控方的反证(rebuttal)。当辩方在展开辩方案件过程中提出新事实或证据,控方认为有必要加以反驳的,可以经法庭同意在这一环节中传唤反证证人(rebuttal witness),通过对反证证人的主询问对辩方案件中的某些内容进行反驳。辩方有权进行反询问(此后还有再主询问、再反询问)。(4)辩方的答辩(rejoinder)。如控方进行了反证,辩方经法庭同意可传唤证人,通过对该证人的主询问作出答辩,就控方在反证阶段提出的反驳作出回应。控方有权进行反询问(此后还有再主询问、再反询问)。[48]See Judy Hails, Criminal Evidence, 6th ed., Wadsworth Cengage Learning, 2008, pp.38-44.由此可见,交叉询问两极化的辩论式询问构造,契合了对抗制下控方案件和辩方案件的对立;基于这种横向构造,诉讼两造无论在哪一证明阶段、面对本方证人还是对方证人,都可利用交叉询问促进本阶段证明目的之达成。
2.职权询问横向构造的成因是职权主义下的一元化证明格局
与对抗制不同,在职权主义,案件事实由法官负责查明,因此不存在“控方”“辩方”案件的区分,法庭上的证明结构是一元化的。尽管控辩双方都可提出证人作证申请,但观念上所有证人都是法庭的证人,各诉讼参与方提问的目的在于共同揭示客观真实。(1)庭前尽管允许律师与证人接触,但这种接触必须限于确定事实以及为庭审进行准备的范畴。律师应当向证人表明,与证人的谈话只服务于其了解事实情况和提供真实证词的目的。[49]Vgl.https://anwaltsblatt.anwaltverein.de/de/serie/darf-man-mit-zeugen-sprechen, überprüft am 22.02.20.教唆他人作虚伪陈述、诱骗他人作虚伪陈述的,还应当负刑事责任。(《德国刑法典》第159-160条)(2)证人出庭宣誓后(《德国刑事诉讼法》第59~67条),审判长首先询问证人的个人情况(同上,第68条),之后“应当让证人连续陈述其所知的询问事项”(同上,第69条第1款)。这一规定旨在确保证人的证词最初不受提问和其先前陈述的影响。[50]Vgl.MüKoStPO/Maier, 1.Aufl.2014, StPO § 69 Rn.1.这一规定的法理基础是陈述和询问的分离(Trennung des Berichts und der Befragung)。证人的连续陈述有独立的意义,不允许仅以问—答形式完成证人询问。[51]具体而言,证人享有连续陈述的权利。必要时,审判长有义务防止证人被插话打扰。只有当证人离题太远或作出明显不实陈述时,审判长才可谨慎地进行干预。但审判长不应立刻干预,因为证人报告或陈述事件的方式也可能提供有关陈述真实性的信息。如果过早地以证人先前的陈述作提示,证人则会感到受约束而失去作证的中立性(Unbefangenheit),这也无益于证据评估和事实调查。当证人陈述出现停顿,审判长应当用一般性的、开放性的、能够激发证人话语的问题促使证人继续作证。基于上述原因,必须保证证人首先进行连续陈述。Vgl.MüKoStPO/Maier, 1.Aufl.2014, StPO § 69 Rn.11-14.只有将陈述和询问进行分离,裁判者才能区分哪些信息是证人无需借助外部提示就回忆起来的,哪些信息是证人在法庭帮助下才回忆起来的,这种判断有利于彻底、准地评价证人陈述的证明价值。[52]Vgl.MüKoStPO/Maier, 1.Aufl.2014, StPO § 69 Rn.11-14.(3)证人连续陈述后,审判长“为阐明和完善证言,以及查清证人获知的证据,在必要的情况下应当进一步发问。”(同上,第69条第2款)此处,审判长发问的意义在于细化和补充证词,消除证词中的模棱两可和矛盾之处,对证词进行检验和审查并澄清证人了解其所表述情况的信息源—是亲身感知还是道听途说。[53]Vgl.MüKoStPO/Maier, 1.Aufl.2014, StPO § 69 Rn.16.(4)此后,参审法官、陪审员、检察官、辩护人、被告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根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40条的提问权规则进行提问。
这种一元化的证明格局,是职权主义的审判结构决定的。职权主义下的刑事诉讼奉行职权调查原则(Untersuchungsgrundsatz):法院自行查明事实,不受诉讼参与方之动议和解释的限制。尽管法院的调查与裁判仅限于起诉所称犯罪行为和所指控人员,但“在此范围内,法院有且仅有义务独立活动;尤其在刑法的适用上,不受提起的控告约束。”(《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55条第2款)“为查清真相,法院依职权应当将证据调查涵盖所有对裁判具有意义的事实和证据材料。”(同上,第244条第2款)这也就意味着,一方面,在证据调查和法律后果上,法院都不受其他诉讼参与方的约束;另一方面,查明客观真实是法院自身的职责和义务。[54]Vgl.Roxin/Schünemann: Strafverfahrensrecht, 26.Aufl.(2009), S.79.基于职责,“在主审程序中的主审人并不满足于一个不偏不倚主持审讯的位置:他自行审理,讯问被告,询问证人”[55][德]拉德布鲁赫:《法学导论》,米健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76页。,并以主动的姿态从证人处尝试引出更多信息并检验信息的真确性。另外,检察机关也负有客观真实义务:“检察院不仅应当侦查对被指控人不利的情况,还应当侦查对其有利的情况,并且负责收集有丧失之虞的证据。”(同上,第160条第2款)
(二)横向构造根据之比较
两种司法制度形成不同的证明格局,其根据在于两者所奉行的真实观不同。
现代诉讼制度均以发现事实真相为价值目标,职权主义和对抗制概莫能外。这是因为,刑事诉讼本质上是证立国家刑罚权发动之正当性的过程。实质意义上,基于查明的犯罪事实才能发动刑罚权是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形式意义上,将判罚立基于客观事实是达致判决可接受性的前提。所以, “实现客观真实(objective truth)既是德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同样也是美国刑事诉讼法的基本原则。”[56]Hans-Heinrich Jescheck, Principles of German Criminal Procedure in Comparison with American Law, 56 Va.L.Rev.(1970), p.240.
尽管如此,职权主义和对抗制在客观真实这一价值目标之下预设了不同的价值构造。这种价值构造的差异,是比较刑事诉讼法学中长盛不衰的议题,代表性的表述包括:对抗制下的真实是“形式真实”[57]Vgl.Trüg, Erkenntnisse aus der Untersuchung des US-amerikanischen plea bargaining-Systems für den deutschen Absprachendiskurs, ZStW 120 (2008), 331 (346).,职权主义的真实是“实质真实”[58]Vgl.Roxin/Schünemann: Strafverfahrensrecht, 26.Aufl.(2009), S.2; Beulke/Swoboda: Strafprozessrecht, 14.Aufl.(2018), S.3; Eicker: Die Prinzipien der „materiellen Wahrheit“ und der „freien Beweiswürdigung“ im Strafprozeß (2001); 许恒达:“‘实体真实发现主义’之知识形构与概念考古——以中世纪至现代初期之德国刑事程序发展史为中心”,载《政大法学评论》2008年第101期,第137~192页;施鹏鹏:“论实质真实——以德国刑事诉讼为背景的考察”,载《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1期,第126~135页。;对抗制下的真实是“各个当事方都能接受的版本”[59]See Thomas Weigend, Is the Criminal Process About Truth: A German Perspective, 26 Harv.JL & Pub.Pol'y,(2003), p.157; [德]许乃曼:“论刑事诉讼的北美模式”,茹艳红译,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8年第5期,第19页。;职权主义的真实是“对历史事实的接近”[60]See Thomas Weigend, Is the Criminal Process About Truth: A German Perspective, 26 Harv.JL & Pub.Pol'y, (2003), pp.170-171.;对抗制信奉真实的“认识论”观念,只有通过现实的认识途径揭露的事实才是客观真实,职权主义信奉真实的“本体论”观念,利用证据可以实现对历史真实的客观重建[61]See Máximo Langer, Strength, Weakness or Both? On the Endurance of the Adversarial-Inquisitorial Systems in Comparative Criminal Procedure, in Jacqueline E.Ross & Stephen Thaman (eds.), Comparative Criminal Procedure,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8, p.520.等等,不一而足。
在哲学意义上探讨本问题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畴,仅从证据范围和认识方法两个方面进行比较,足以揭示两种真实观的本质差异并服务于本文的论证目的。在证据范围上,对抗制的证据范围局限于当事人之提出,而职权主义的证据范围则不受此限,涵盖所有对裁判有意义的证据。在认识方法上,对抗制采取综合方法(synthetische Methode),认为通过听取两种对立的事实主张,可以认知唯一的事实真相;职权主义采用分析方法(analytische Methode),认为通过综合分析各种证据,可以将事实认定建构在理性客观的基础上。[62]Vgl.Mittermaier: Die Lehre vom Beweise im deutschen Strafprozesse nach der Fortbildung durch Gerichtsgebrauch und deutsche Gesetzbücher (1834), S.29 ff.在这一意义上,本文将对抗制的真实观称为“综合的真实观”,将职权主义的真实观称为“分析的真实观”,对两者可列表三比较如下。

表三 综合的真实观与分析的真实观之比较
综合的真实观与分析的真实观反映了两种司法制度不同的价值偏好。交叉询问服务于综合的真实观,而综合的真实观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局限,是职权主义国家所不能容忍的,这导致交叉询问在职权主义国家面临水土不服。
第一,事实认定之被动。交叉询问制度首先意味着询问由当事人推动,而裁判者保持被动。在对抗制下,陪审团成员在毫无准备情形下进入法庭,在冗长的庭审中不能主动提问,甚至不能作书面记录。对其事实认定过程中的疑惑之处,只能仰赖当事方通过交叉询问借助证人之口作出解释。认知科学上认为,“人类的认知器官并非现实经验的被动感受器,在事实认定者认知过程的关键时刻,他们可能需要从特定的角度去探讨并阐明某一问题。否则,他们可能会轻易错过一个重要词汇或问题的含意。如果他们的人之需求未能得到满足,那么他们就会迷惑,他们对证据的理解力也就会严重—并日渐—受损。”对陪审团而言,“没有一个可以据以组织证据的法律框架,他们需要颇费时日才能领会问题的本质。”[63][美]米尔建·R·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4页。这种认识方法违背事实认知规律,并非认清事实情况、理清案件脉络的有效途径。因此,在一些职权主义国家,尽管已经引入了交叉询问制度,然而法官由于承担事实查明责任,在交叉询问过程中无法实现“自我克制”。如在日本,学者观察到,法官会在交叉询问过程中“随意穿插”乃至径行接手,亲自询问。[64]参见王兆鹏:《路检、盘查与人权》,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24~229页。
第二,事实认定之割裂。在聆听交叉询问时,裁判者面对的是两个版本的事实叙述,对每一事项,都需要从两种叙述所提供的两套信息中作出判断。这种派性特征极强的证明结构,不但可能影响证人记忆的准确性,也影响证人的心理,使其产生对己方阵营的“归属感”从而威胁证言的准确性。“在这种方式下,每一方最终引出的证言都仅仅是只是证人知悉的部分,每一方都对法庭上的证人证言作了明显的编辑式控制。”[65][美]米尔建·R·达马斯卡:《漂移的证据法》,李学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05页。这种情形不能为职权主义的法庭所接受。在日本,正是因为无法容忍这种割裂,法官会在当事人提问后打断介入,改变询问的内容和方式,以期获得更加客观的回答。[66]参见王兆鹏:《路检、盘查与人权》,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24~229页。
第三,事实认定之偏狭。在交叉询问制度下,事实证据范围受制于控辩双方的提出,职权询问则不受此限。也就是说,一项对裁判具有意义,但控辩双方所都不希望提出的事实,不可能进入对抗制的法庭,却往往属于职权主义法官的职责查明范围。假设被告人患有间歇性精神病,在对抗制下,控方可能未发现或为胜诉而不提出这一事实,辩方则可能由于顾及社会声望也不愿提及这一事实,在此情形,法庭对这一事实无从了解。但在职权主义,被告的精神状态是法庭主动查明的内容。在日本,正是因为负有事实查明的职责,法官往往进行补充询问,乃至问出一连串问题,“让出庭检察官或律师无所事事”。[67]参见王兆鹏:《路检、盘查与人权》,元照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224~229页。
由此可见,尽管对抗制和职权主义在价值追求上都聚首于“客观真实”这面大旗之下,然而两者所追求的真实具有不同的构造。强令原本服务于一种真实观的诉讼制度转而服务于另一种真实观,功能上的龃龉和价值上的紊乱自然在所难免。
(三)纵向构造成因之比较
1.交叉询问纵向构造的成因是对抗制下彻底的预断排除机制
交叉询问的纵向构造,即主询问——反询问——再主询问——再反询问,其特点是询问权在本方—对方之间乒乓式的循环往复。以辛普森案中对警员Dennis Fung的交叉询问为例。控方指控辛普森杀害被害人高曼的证据之一,是在高曼的衬衫上提取到了和辛普森车内一致的头发和纤维。Fung是控方证人。在案发后他参与了证据收集工作。在控方对Fung的主询问中,Fung介绍了证据收集的过程。反询问中,在辩方律师Scheck的提问下,Fung承认,验尸官曾将高曼的遗体放置在来自另一被害人、辛普森前妻妮可·布朗住处的毯子附近,并承认这可能导致高曼的衬衫受到来自毯子上所附的头发和纤维的二次污染:
辩方律师 将这条毯子从屋子里放到犯罪现场的中间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因为有可能会交叉污染头发和纤维。
控方证人 取决于毯子的清洁程度,那会影响我的回答。
辩方律师 现在,根据您当天在犯罪现场的观察,妮可·布朗·辛普森小姐的尸体在那条毯子附近?
控方证人 是的。
辩方律师 还有高曼先生的尸体最终被放置在毯子的区域?
控方证人 是的。
辩方律师 并假设毯子上有头发,纤维和其他痕迹证据,那可能是后来在高曼先生的衣服上发现的任何东西的污染源吗?
控方证人 我相信死因裁判官在将高曼的尸体放在毯子上之前,在毯子上铺了一层隔垫和一层塑料布。
辩方律师 假设毯子覆盖着头发和纤维,并将其放置在犯罪现场的中间,毯子中的头发和纤维从犯罪现场散开,并进一步假设当高曼的尸体被移动时,手套或帽子被拖入该区域,它们可能被毯子上的头发和纤维污染了吗?
控方证人 可能。
辩方律师 重要的是要知道毯子是否包含与辛普森先生的野马车上一致的纤维?
控方证人 可能,是的。
辩方律师 但是那条毯子留在了犯罪现场,再也没有拿出来做进一步的分析?
控方证人 是的。
辩方律师 那是一个错误,不是吗?
控方证人 可以被看作一个错误。[68]参见辛普森案1995年4月4日法庭笔录,http://simpson.walraven.org/apr0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2月22日。
就这一问题,在再主询问中,控方反驳道:
控方律师 现在,假设验尸官回到邦迪犯罪现场,将验尸官的白布放在妮可的毯子上,并在上面盖上一块塑料布。这是在罗恩·高曼被放到塑料布上之前发生的。在这种假设下,您是否期望从毯子到罗恩·高曼的任何转移证据(transfer evidence)?
控方证人 不。[69]参见辛普森案1995年4月17日法庭笔录,http://simpson.walraven.org/apr17.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2月22日。
除了死者高曼身上纤维和毛发的来源,在对Fung的交叉询问中,控辩双方还就血迹取证过程的规范性、案发现场保存之完整性(特别是案发现场一只袜子的位置)等问题进行了多轮交锋。
这段笔录典型反映了交叉询问纵向构造的功能逻辑。从内容上看,交叉询问的纵向构造中不仅包括“询问”的内容,还包括归纳事实争点和辩论的内容。具体而言,在主询问中,证人所了解的案件事实得以铺陈。反询问中,对方会就这一案件事实中的几个要点展开质疑。未被质疑的部分便是双方都认可或反方认为无关紧要的内容,在接下来的询问过程中被舍去。而留下的几项被质疑的内容,便是经过一轮询问(主询问—反询问)所归纳出的争点。对于这些争点,本方可在再主询问中再次就进行论证补强,反方也可以在再反询问中进行反驳补强。可以看出,主询问—反询问—再主询问—再反询问的过程,既是展开证据的过程,也是归纳事实争点的过程,又是就事实判断中(所难以避免同时伴生的)规范判断的内容进行辩论的过程。因此,交叉询问的纵向构造客观上包括了归纳事实争点和辩论的内容。
之所以需要通过冗长的交叉询问来归纳事实争点,是因为裁判者对案件内容一无所知。对抗制审判纵向构造的根本特征是彻底的预断排除。“决策者必须毫无准备地进入案件……他应当拥有一片‘心智的处女地’,等待着举证和论辩这一双向过程的开发。”[70]参见[美]米尔伊安·R·达玛什卡:《司法和国家权力的多种面孔》(修订版),郑戈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致中国读者的引言”第2页。对于裁判者而言,主询问和反询问是双方就该一证人所涉范围内的事实主张的初步展开。在此时,事实争点刚刚显露端倪,裁判者对此也只有浮光掠影的粗浅认识。只有经过接下来的若干轮询问,事实争点才水落石出,纷繁纠缠的事实关系冰释理顺,裁判者方能贯通融会,形成判断。
2.职权询问纵向构造的成因是职权主义下的案卷制度
职权询问则呈现另一幅图景。职权主义传统上实行全卷移送制度,全面阅卷是法官职责的重要内容。[71]Vgl.KK-StPO/Schneider, 8.Aufl.2019, StPO § 199 Rn.7-16; MüKoStPO/Wenske, 1.Aufl.2016, StPO § 199 Rn.27-35.基于全面阅卷,法官得以主导证人询问。具体而言,经过阅卷,法官已对证人在侦查阶段所作陈述有所了解,对案情全貌也了然于胸,对需要向证人进一步核实的问题已经心中有数。在证人陈述后,法官通过补充追问,即可对案件事实有所洞察。此后由其他诉讼参与方依其意愿轮流询问,以对其所关心的或对其诉讼利益有影响的事实作出补充。在各方的提问中所引出的信息也都汇集至法官处,成为法官自由心证之资料的一部分。
由此可见,在对抗制下,由于裁判者事先不了解案件情况,交叉询问的纵向构造同时包括了案件呈现、争点归纳、辩论等内容。在职权主义,基于全面阅卷,裁判者已了解案件情况,此后的提问只服务于对证词进行补充、澄清和检验的次要目的。
(四)纵向构造根据之比较
交叉询问独特的纵向构造,系根源于陪审制的要求。
对抗制采用外行人士组成陪审团进行事实认定。外行人士的组织具有临时性,加之其知识和经验有限,故对抗制不将事实查明的任务交由陪审团,而是完全交由当事人,陪审团只在当事人提交的事实范围内作出判断。又因为知识和思维能力的限制,外行人士被认为难以摆脱前见的影响,因而为诉讼之公平,他们必须以空白状态进入案件。这两方面决定了,对抗制中的决策者在庭前接触证据材料,既无必要性,也无正当性。因此,案卷移送制度在此没有适用的余地。由此产生的结果,一是案件事实只能在包括交叉询问在内的庭审过程中铺陈;二是对证人证言的检验必须完全依赖于交叉询问—没有案卷所载的先前证言作比对,对证人证言可信度的攻击只能从证人庭上的陈述入手。又因为对抗制推定作为外行人士的裁判者在所有证据材料都得到呈现之前过早形成判断会导致之后的证据听取产生偏见,故对抗制要求裁判者在整个庭审过程中保持被动。因而尽管经过一轮询问后双方的立场已得到呈示,但由于裁判者的被动性,对争议事实的进一步补充、挖掘和澄清仍然只能仰赖于当事人,这使得循环往复的交叉询问成为必要。
与此相反,职权主义采用专业法官(主导)审判,推定法官经过专业训练,拥有良好的分析判断能力和不偏不倚刚正不阿的审判态度,因此将事实查明的任务交给法官。而全面阅卷是法官开展事实调查的基础性工作,是法官尽责的体现。法官作为专业人士,被推定为能够克服其阅卷产生的前见,不至因阅卷而丧失公正性。因而法官阅卷既有必要性,又有正当性。在案卷中,法官已经对证人在侦查阶段的陈述有所了解。由此产生的结果,一是法官对案件事实的了解不全仰赖于法庭,法官阅卷和听审共同构成其知识来源;二是对证人证言的检验不完全依赖于法庭询问。在证人陈述时,法官内心已经在将证人的陈述案卷所载的证人先前证言作比对。此后,法官得以基于案卷知识和证人证言提问,以为证词之补充和检验。此后,其他诉讼参与方通过提问,从各自的角度揭示法官所没有注意到的其他事实,一并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法官,以为心证之参考。由于法官在提问中已经涉及了证人所了解信息的主要内容,控辩双方在此处展开辩论的必要性便相比于交叉询问的情形大大降低。总而言之,法官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因而其认知需求主要通过自己的主动询问实现,其他各方的提问只起到辅助作用。
由此可见,交叉询问循环往复的纵向构造,只在陪审制环境下有其需求。在实行专业法官主导审判的职权主义国家,对证言疑点的追问和释明,是法官的职责,也只有法官通过自己组织语言进行询问,才足以让法官产生确信、形成心证。正是因为如此,
日本刑事庭审实践几乎未出现过所谓询问与反询问的激烈交锋,甚至可以说反询问在日本的审判模式下形同虚壳。控辩双方越是进行反询问,也越容易产生对己方不利的证言,这也是为何当事人对反询问有一种自然的抵触心理。“日本的反询问与其说是对主询问所作供述的审査,不如说是要让法官借助证人对反询问者所作的供述以形成心证。”甚至有法官声称完全不在乎反询问的有效性。[72]施鹏鹏、谢文:“审判中心主义的源与流——以日本刑事诉讼为背景的制度谱系考”,载《江苏社会科学》2018年第5期,第181页。
(五)小结
本节依次从横向构造和纵向构造的角度分析了交叉询问和职权询问制度构造的成因和根据,比较结论可归纳如下表四。

表四 交叉询问与职权询问制度构造成因和根据之比较
本节的分析表明,在横向构造上,交叉询问之所以形成两极化的证明格局,是因为对抗制下控方案件和辩方案件的对立。这种对立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抗制审判所奉行的“综合的真实观”。与之相反,职权主义奉行“分析的真实观”,不存在双方案件的对立,交叉询问的横向构造便无所附丽,日本实践为此提供了佐证。在纵向构造上,交叉询问之所以形成主询问—反询问的循环往复,是因为对抗制下裁判者只能从庭上了解信息,争点的归纳和争议事实的深入探知一概仰赖当事人,因而只能采取这种辩论式的结构。这种结构的根本原因在于陪审制,平民审判要求裁判者保持被动,因而其认知需求只能通过当事人实现。与之相反,在职权主义,专业法官负有查明义务,不但审前阅卷,而且在人证调查中保持主动姿态,因而主询问—反询问的循环往复没有生存空间。日本实践也为此提供了佐证。是故,将交叉询问制度移植到职权主义国家,必当南橘北枳,不具有可行性。
四、结论:职权询问阵营中的中国人证调查制度
上文的考察表明,职权询问功能上毫不逊色,交叉询问不能适应职权主义的制度环境。因此,职权主义国家引进移植交叉询问制度,既无必要、也不可行。
中国是职权主义国家。从法律规范和实践上看,中国的人证调查制度是典型的职权询问制度。中国人证调查制度与交叉询问制度的不同之处,并不是中国人证调查制度的劣势,而恰恰反映了中国人证调查制度作为职权询问制度的典型特征。
在查明中国人证调查制度内容的基础上,可对中国现行人证调查制度的功能和制度环境作出分析,由此可对盛行的“交叉询问迷思”作出系统性的回应:中国移植交叉询问制度,同样既无必要、也不可行。
(一)中国人证调查制度的横向构造
从横向构造上看,中国对证人享有询问权主体包括审判人员、公诉人、当事人和辩护人、诉讼代理人以及被告人本人(《刑事诉讼法》第194条)。这意味着,中国人证调查制度采多极化研讨式询问,而非两极化辩论式询问。例如,在于欢案二审中,证人苏银霞出庭作证。在审判长向证人说明如实作证的义务和作伪证的法律责任并安排证人签署保证书后,公诉人、辩护人、被害人杜志浩近亲属委托的诉讼代理人、被害人郭彦刚的诉讼代理人、被害人严建军的诉讼代理人、被害人郭彦刚依次对证人进行了发问,发问的主体范围非常广泛。[73]参见“刚刚!‘于欢案’庭审结束,择日宣判(全实录:开庭,调查,辩论,陈述)”,“法务之家”微信公众号,2017年5月27日,https://mp.weixin.qq.com/s/elwJzKyUbpfWvu_aOt-KGg,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2月22日。
在横向构造上,中国人证调查制度保障多种主体的询问权,具有穷尽式的信息挖掘功能。不过,实现这一功能的前提是证人出庭作证。庭审实质化改革试点中,学者观察到,在证人出庭作证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庭审中“有利于被告的证据、事实、观点被发现、提出,不断影响、改变着法官的心证和立场,从而促使‘意外’的裁判结果不断发生。”[74]马静华教授报告了中国证人询问制度戳穿伪证、揭示真实的三个典型案例,参见马静华:“庭审实质化:一种证据调查方式的逻辑转变——以成都地区改革试点为样本的经验总结”,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7年第5期,第69页。
有观点主张,中国“在交叉询问制度中应当明确控辩双方证人的分野”[75]顾永忠:“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的刑事辩护突出问题研究”,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2期,第85页。,这种观点意味着放弃多极化的研讨式询问,转向两极化的辩论式询问。然而,中国与德国刑事诉讼都具有一元化的证明格局,都实行职权调查原则,奉行分析的真实观。如前所述,在人证调查领域改行两极化的对抗式制度所带来的事实认定之被动、割裂与偏狭,与中国奉行的实事求是的真实观不能契合,也是中国法庭所不能容忍和接受的。
(二)中国人证调查制度的纵向构造
纵向构造上,中国证人询问制度实行线性的依次询问。证人出庭后,发问“应当先由提请通知的一方进行;发问完毕后,经审判长准许,对方也可以发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2]21号,下称《最高法解释》)第212条]试行的《法庭调查规程》第19条还允许审判长根据案件审理需要对发问顺序灵活安排。此后,其他有询问权的主体也可以发问。上述于欢案中证人苏银霞出庭作证的过程,也同样典型地反映了这种线性询问的纵向构造。不过,这种线性构造并不排斥有询问权的主体在必要时进行补充询问。例如,在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案一审的第二、第三个庭审日中,王某某作为控辩双方共同申请的证人出庭作证。公诉人、被告人、辩护人依次对其进行询问后,公诉人和被告人又分别进行了一轮补充发问。[76]参见“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5天庭审文字实录”,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0827/c 1001-22704644.html,最后访问时间2020年2月22日。试行的《法庭调查规程》第19条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准许补充发问的精神。
在纵向构造上,中国人证调查制度设计符合职权询问制的基本原理,没有功能缺陷。有观点认为,美国交叉询问制度中,反询问范围受到主询问的限制,这种纵向构造具有明确争点和促进庭审顺利进行的作用,中国也应当设立此种规则。[77]代表性观点参见陈岚:“我国刑事审判中交叉询问规则之建构”,载《法学评论》2009年第6期,第112~113页。本文不赞同这一观点。这种对反询问范围进行严格限制的规则,只适用于美国部分法域。产生这一规则,只是服务于理顺案件呈现顺序的需要。在对抗制下,由于案件在观念上分为控方案件和辩方案件,证人也划分为控方证人和辩方证人,控方在通过对控方证人的主询问建构其控方案件的叙事时,若辩方通过在反询问中引入不相关事实进行打断,一方面会导致控方案件、辩方案件叙述的混淆,不利于陪审团理顺事实关系,另一方面还可能造成证人立场的摇摆,不利于对证人的可信性进行检验和弹劾。然而,即使在将庭审对抗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美国,也有一些法域采取不限制反询问内容范围的宽松性规则,因为宽松性规则的优点在于“允许一次公开证人所了解的所有情况,从而防止对手介入己方的案情叙述并通过控制性的事实披露误导陪审团。”[78]Paul R.Rice, Roy A.Katriel, Evidence: Common Law and Federal Rules of Evidence, 6th ed., Matthew Bender, 2009, p.4.因此,在对抗制审判中,反询问范围受主询问范围限制规则的意义是有限的。职权主义环境下的人证调查制度则更不需要这种规则。法官通过庭前阅卷,已经对案件情况有所了解;在询问证人过程中,首先由证人连贯陈述,接下来由审判长和其他各有询问权的主体进行法庭提问,整个询问过程都在法官掌控之中。
(三)中国人证调查制度的微观构造
从微观构造上看,中国同样有系统的不当询问禁止制度。无关问题、诱导性问题、威胁证人的问题、损害证人人格尊严的问题不被允许(《最高法解释》第213条)。询问权主体有权对不当询问提出异议(《最高法解释》第214条),提请审判长制止或对由不当询问引出的陈述或证言不予采纳(《人民检察院诉讼规则》第402条)。根本上,主动制止不当询问是审判长的职责(《刑事诉讼法》第194条)—在这一意义上,中国人证调查制度的微观构造与职权询问更加类似。
中国人证调查制度的微观构造同样具有证言质量保障、庭审效率促进和证人保护功能。中国庭审证人询问中产生无序现象,并不能归因于相关规则的不完善。众所周知,法律规则本身不可能事无巨细。与德国立法文本相比,中国相关规范甚至更加细致。中国问题在于理论界对不当询问禁止制度原理的认识不足,对相关法律条文的教义学阐释严重欠缺,这导致实务界对“不相关问题”“诱导性问题”等规范概念的理解还很粗浅,进而在人证调查环节产生秩序混乱的问题。因此,学界的首要任务应当是对相关理论进行深化。
诱导性问题的准许性是不当询问禁止制度中的核心问题。有观点认为,中国应该借鉴交叉询问制度,确立原则上禁止诱导、对表现出敌对态度和倾向的证人允许诱导的规则[79]参见龙宗智:“我国刑事庭审中人证调查的几个问题——以‘交叉询问’问题为中心”,载《政法论坛》2008年第5期,第30页。甚或主询问禁止诱导、反询问允许诱导的规则[80]参见樊崇义:“刑事证据规则立法建议报告”,载《中外法学》2016年第2期,第312页;薛正俭:“‘审判中心’背景下刑事庭审质证交叉询问规则之完善”,2015年广西南宁“以审判为中心与审判工作发展——第十一届国家高级检察官论坛”会议论文,第4页。。然而,在中国,所有的证人都是法庭的证人,不存在“控方证人”“辩方证人”的阵营划分—在双方共同申请某一证人出庭时更是如此。由此,中国的法庭询问也不可能区分出主询问和反询问。即使认为询问本方申请出庭的证人构成主询问、询问对方申请出庭的证人构成反询问,“实质意义上的诱导性问题”与“单纯以核实笔录为目的的问题”之间也难以区分,更不可能在“主询问”中一概禁止后者。总之,这种对抗制下处理诱导性问题准许性的进路在中国不具有可行性。如前所述,问题的诱导性不是全有全无的,而是存在程度区分的,必须在对问题的诱导性程度作实质判断的基础上裁决其准许性。这需要通过对相关的法律规定进行教义学的阐释,构建从实质上判断诱导性问题准许性的系统性方法。为此,前述的对诱导性问题进行类型化的德国进路可资借鉴。
总而言之,中国人证调查制度是典型的职权询问;在横向构造、纵向构造、微观构造上,中国人证调查制度的功能都是完备的;在这三方面中的任何一方面试图转向交叉询问制度都不具有可行性。
五、余论:法律移植浪潮下的人证调查制度,兼论中国制度向何处去
早在2001年,张卫平教授在民事诉讼领域考察了日本引入交叉询问制度以来引发的争论和问题,分析了交叉询问与司法制度环境之间的关系,敏锐地意识到了交叉询问制度与职权主义传统的内在张力。[81]参见张卫平:“交叉询问制:魅力与异境的尴尬”,载《中外法学》2001年第2期,第157页。在实行处分原则和辩论主义的民事诉讼领域尚且如此,在实行职权查明原则的刑事诉讼中,如同前文所提到的,交叉询问制度的不兼容性显然更加突出。
从更长久的历史尺度上看,早在19世纪,交叉询问的魅力便已为德国学界和立法者瞩目。早在1852年,交叉询问便作为与职权询问并行的、由当事人自行选择的另一种人证调查方法出现在普鲁士法典中,并在此后的《帝国刑事诉讼法典》中得到延续。[82]Vgl.Mayer: Der Entwurf einer deutschen Strafprozessordnung mit besonderer Berücksichtigung ihrer praktischen Gestaltung in den wesentlichsten Beziehungen (1874), S.183.除在纳粹时期曾被短暂废止[83]Artikel 9.§ 4(1)RGBl.I 1942, S.508.Vgl.Gabriele Zwiehoff: Änderungsgesetze und Neubekanntmachungen der Strafprozessordnung und strafverfahrensrechtlicher Bestimmungen des Gerichtsverfassungsgesetzes, 1.Aufl.(2013), S.340.外,这一条款自诞生以来便一直存在于德国刑事诉讼制度中。时至今日,德国立法上仍然规定:“询问由检察院和被告人提名的证人与鉴定人,应当依检察院和辩护人的一致申请,经审判长同意,由检察院和辩护人进行。对由检察院提名的证人与鉴定人,检察院有权首先询问,对由被告人提名的证人与鉴定人,辩护人有权首先询问。”(《德国刑事诉讼法》第239条第1款)要适用这一条款,只需控辩双方针对适格证人一致提出交叉询问的申请,无需法庭认为对于实体真实之发现有必要,对该证人的询问可立即转入交叉询问程序。[84]Vgl.BeckOK StPO/Gorf, 35.Ed.1.10.2019, StPO § 239 Rn.5.询问中,除非出现不当询问,否则审判长必须保持被动、不能做出任何干预。可以说,这一条款最大限度地维持了英国交叉询问制度的原貌。然而,近二百年历史上,这一条款几乎从未被使用过,以至被称为异物(Fremdkörper)、死法条(totes Recht)。[85]Löwe/Rosenberg/Gollwitzer StPO, 23.Aufl., StPO § 239 Rn.1; MüKoStPO/Gaede, 1.Aufl.2016, StPO § 239 Rn.1-2.实践中,控辩双方对这种询问方式既无准备、也无兴趣,因为职权询问已足以保障真实发现与程序正义。
近半个世纪,奉行职权主义的欧陆意、西[86]葡萄牙1987年刑事诉讼法改革引进了交叉询问制度,确立了交叉询问的横向构造和纵向构造(《葡萄牙刑事诉讼法》第348条第4款),但也保留了裁判者随时介入的权力:“如果为作出正当裁判,确有必要要求证人对证言进行解释,各法官和各审判团成员可以随时向证人提问。”(《葡萄牙刑事诉讼法》第348条第5款)条文参见《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欧洲卷》(中),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版,第1267~1268页。、葡[87]西班牙人证调查制度中,审判长最先发问,此后“请求其作为证人的当事人可以向其进行适当的提问。其他当事人也可以向其提出合理问题,以及根据证人的回答向其询问与本案相关的问题。”(《西班牙刑事诉讼法》第708条第1款)西班牙制度更接近职权询问而非交叉询问。条文参见《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欧洲卷》(下),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版,第1597页。、法等国也开展了人证调查制度改革,这些改革与其说反映了交叉询问的广泛影响,不如说是证明了职权主义旺盛的生命力。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意大利1988年刑事诉讼改革借鉴了交叉询问制度,在横向构造上把多种询问权主体划分为“申请证人作证的一方”和“与该方诉讼利益相反的另一方”两大阵营;在纵向构造上设置了主询问(L’esame diretto)、反询问(Il controesame)、再主询问(Il riesame)(《意大利刑事诉讼法》第498条第1-3款);在微观构造上禁止不当提问,特别是在主询问中禁止诱导性提问(domande- suggerimento)(同上,第499条第3款)。为确保当事人在证人询问中的主体地位,规定庭长向证人提问“只能在主询问和反询问之后进行”(同上,第506条第2款)并设立双重卷宗制度,避免法官庭前形成不当预断。[88]相关条文参见《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编辑委员会编译:《世界各国刑事诉讼法:欧洲卷》(下),中国检察出版社2016年版,第1717页及以下,下不赘。不过,与英美的交叉询问制度相比,意大利制度的特征是“仅复制这些规则的顺序,并选择赋予法官对询问的穿透性控制。”[89]P.Tonini, Manuale di procedura penale, Giuffrè Editore, Milano, 2017, 716.庭长有义务“确保问题的相关性、答案的真实性、审查的公正性和争端的正确性”(同上,第499条第6款),有权利“向当事人提出有助于全面考察情况的、新的或者更为广泛的问题”(同上,第506条第1款),庭审结束后,法官还可以决定主动调取新的证据材料(同上,第507条)。可以说,意大利制度模仿了交叉询问的表面特征,却拒绝了对抗制下“纯粹‘竞争性’的程序概念”(concezione meramente “agonistica” del processo),仍然服务于职权主义的诉讼传统。[90]P.Tonini, Manuale di procedura penale, Giuffrè Editore, Milano, 2017, 36.See also Giulio Illuminati, The Frustrated Turn to Adversarial Procedure in Italy (Italian Criminal Procedure Code of 1988), 4 Wash.U.Global Stud.L.Rev.(2005), p.567.
与意大利相比,法国人证调查制度改革更加保守。法国2000年的刑事诉讼改革“在《刑事诉讼法典》中增设第312 条、第442-1条及第454条,允许轻罪及重罪案件的检察官、被告人、民事当事人及当事人的律师‘请求审判长提供发言机会,向被告人、民事当事人、证人以及所有传唤至法庭的人员直接发问。’”[91]施鹏鹏:“职权主义与审问制的逻辑——交叉询问技术的引入及可能性反思”,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4期,第57页。这一改革只是确立了法国人证调查制度中多极化研讨式询问的横向构造,是在职权询问制内部所作的完善,与仿造交叉询问制的意大利式改革有着根本区别。尽管如此,这些新增设的条款在实践中也极少得到运用,法国的人证调查仍然严重依赖法官的职权审问。[92]法国人证调查制度的实践运行情况,See Richard S.Frase, France, in Craig M.Bradley (eds.), Criminal Procedure: A Worldwide Study, Carolina Academic Press, 2007, p.234.
德、意、日、法四国人证调查制度改革的实践,反映了法律移植浪潮下交叉询问制度在职权主义环境中的命运:若交叉询问作为选项与职权询问并行,交叉询问无人问津(德国);若将交叉询问强行嫁接,只能得其外观而不得其神髓,产生价值龃龉和功能紊乱(日本、意大利);职权询问在人证调查中的根本性地位难以撼动(法国)。学者观察到:“在美国制度向欧陆环境移植的过程中,原始的制度安排最终受到了高度修改,新的环境改变了它们的原始功能和性质。他们已经失去了对抗性的理论基础,也失去了美国模式中与对抗性的刑事诉讼自由主义思想紧密相关的特征。”[93]Eliabetta Grande, Comparative Approaches to Criminal Procedure: Transplants, Translations, and Adversarial-Model Reforms in European Criminal Process, in D.K.Brown, J.I.Turner & B.Weisser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riminal Process, Oxford Univ.Press, 2019, p.85.
中国的职权询问制度构造合理、功能完善,符合中国作为职权主义国家的基本国情。因此,中国制度的发展方向不应是另起炉灶求诸交叉询问,而是继续坚持职权询问制度,加强职权询问的理论研究,结合庭审实质化改革的需要,为我国职权询问规则提供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阐释。在这一过程中,包括德国在内的欧陆有关国家关于职权询问的丰富智慧成果是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