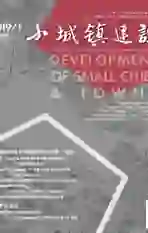乡村振兴视野下的社区(生态)博物馆本土化研究
2019-09-10潘梦琳
潘梦琳
摘要: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城镇化、全球化给乡村社会的生存带来危机,社区博物馆理念正是将人类文化与经济可持续发展有机结合的媒介。由于理念引进之初被解读为一种“文化保护”“社会动员”的工具,以及对社区博物馆蕴含的经济发展职能研究相对薄弱,使得本土化地域实践难以处理保护与发展、资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造成了早期实践“普遍充满失败感”。文章以此为切入点,通过对社区博物馆理论性解读和实践性分析,厘清了我国乡村地域发展与社区博物馆本土化所承担的经济职能及彼此的关联,并进一步融合对内生式发展的思考,提出了符合我国乡村发展需求的本土化途径。
关键词:乡村振兴;社区博物馆;本土化研究;经济发展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01.015·中图分类号:F320;G268.9·······
文章编号:1009-1483(2019)01-0113-06·文献标识码:A
A Study on the Localization of Community (Ecology) Museu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Cultural Protection to Regional Development
PAN Menglin
[Abstract] Since the idea of community (ecology) museums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most of them were understood as cultural protection tools. In the practice of localization, cultural heritage was also the main purpose. The feasibility of its economic functions was not discussed in depth. Taking this as an entry point,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theory of community museums and the localization practice, this paper proposes the feasibility of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concept to realize economic value in the countrys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inevitable demand for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localization of community museums, puts forward sound suggestions for the practice of rural rejuvenation strategies in China.
[Keywords] rural revitalization; community museum; localization research; economic development
1研究動态与关联性分析
生态博物馆自上世纪70年代诞生以来,其理念始终处于“进化”中,因此没有标准定义和固定模式, “生态博物馆究竟是什么?”“包含了什么?”一直都是学者们争辩的议题,这恰恰显示出理念的应变能力。生态博物馆(Ecomuseum)词源的本意是“栖息地” “居住地”,可理解为“社会环境均衡系统”,可见它关注的重点并非自然生态,而是居住地与居民,所以下文称之为社区博物馆。
上世纪80年代,社区博物馆理念被介绍到我国,一直被理解为以“保存生活记忆,传承文化精神,服务地域居民”为主旨的一种社会文化工具。当下社区博物馆与时俱进,其理念被赋予了新的涵义,如“六枝原则①”中指出“社区博物馆既要保护文化,又要发展经济”。社区博物馆的中国实践也出现几种不同观点: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马吉在贵州和内蒙社区博物馆的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本土化实践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强调发展经济,在保护文化的同时,还要负起消除贫困、发展当地经济的责任;另一种认为社区博物馆本来就是一个文化项目,其职责是保护与传承地域特色文化,而不应承担太多的责任[1];我国学者型官员单霁翔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开拓了我国社区博物馆的新局面并指出“本土化是中国社区博物馆发展建设的必由之路”,社区博物馆应推动社区经济社会发展,激发居民投身社区发展的主动性和积极性[2];费孝通先生的弟子方李莉教授在参加贵州国际论坛后敏锐地指出,这一理念的确让人感到振奋,在这里人们似乎找到一条能够将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的保护,以及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的新道路,这似乎是一条真正的人类文化和经济的可持续之路[3]。因此当下最需要明确的是社区博物馆是否具备承担经济发展的职能,以及应该如何践行该职能,并推动地域发展,这是本研究的主要目的。
根据上述研究梳理可知,其一,“居住地”作为社会有机体,其地域振兴必然是时代环境下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反映,“文化虽然可以相对独立于经济,但文化最终不能脱离经济基础”。我国的国情村情决定了社区博物馆在我国实践必然承担起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经济发展”是中国社区博物馆绕不开的话题。其二,我们应意识到,如果将地域经济发展作为社区博物馆应承担的义务,那么社区博物馆实践将会从一个文化项目,转变为一个社会发展项目,这就意味着社区博物馆在保护文化的同时,需要承担起社会综合性极强的乡村扶贫脱贫的职责,这或将成为社区博物馆本土化的重要使命。
在我国社区博物馆概念出现伊始其本土化要求便随之而出,1995年课题组在贵州考察之际,提出我国社区博物馆的三项基本原则:(1)社区博物馆本土化;(2)政府主导、专家指导、村民参与;(3)既要保护文化,又要发展经济,社区博物馆的经济职能也由此产生。然而社区博物馆本土化是地域综合性推进的结果,经济发展只是其指标之一。“既要保护文化,又要发展经济”对本土化实践是挑战更是动力。从实践历程看,社区博物馆因其区位条件、地缘优势、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的不同难以形成统一的地域发展模式,这强烈地显示出社区博物馆与生俱来的本土化要求;从社会变革看,由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型,传统乡村面临城镇化、全球化的重新分工合作,其乡村社会生存环境面临危机,而社区博物馆正是应对这样的社会现实。
我国社区博物馆的选址大多在贫穷落后的山村,当地政府与村民理所当然地将社区博物馆理解成一个“投资项目”,社区博物馆本土化应主动回应这一诉求,并以此为切入点,结合我国乡村振兴战略,特别是当下脱贫攻坚的政策优势,发展乡村经济,让乡村与村民真正富裕起来。社区博物馆的历史使命不是仅仅停滞在“保存记忆、传承文化、服务居民”的层面,社区博物馆本土化的本质就跳动着地域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升华的时代脉搏。
综合上述观点,本研究以乡村地域发展为目标,从社区博物馆本土化的理论性、实践性两方面进行可行性分析,结合日本内生式发展理念,探讨社区博物馆本土化对乡村地域发展的合理途径。
2社区博物馆本土化理论性分析
社区博物馆理念能否实现本土化,首先要分析该理念的适用性。苏东海先生指出,只有适应当地环境,一切从国家的、社会的、本地的实际出发,社区博物馆才有希望生存与发展下去[4]。下面就从三方面论述该理念适用于我国乡村的现状。
2.1理念的“空筐”特性
人类发展应该能够给人、社会和自然带来和谐与长远发展的“综合效益”,社区博物馆的实践正着力于这样的共生关系,把人居环境和生活空间作为“馆区”与“藏品”,有效地阐明时间(历史文化)与空间(地域格局)和人间(居民生活)三而合一的“空筐”特性。所谓“空筐”可借用“艺术空筐”来解释,艺术之所以具有永久的魅力,其原因就在于它像纯粹数字一样具有“空筐”结构特性,能够容纳天地间的万事万物和人的精神世界,当然这个“空筐”能够装得进“居住地”。理解“空筐”功能可以借助海洋牧场(Ocean Ranching)概念,在特定海域设置的人工生态渔场,首先营造一个适合海洋生物生长与繁育的生境(Habitat),再由所吸引来的生物与人工放养的生物一起,依靠一整套系统化渔业设施和管理体制,以此达到各种不同的生物都有适合自己生长的环境生态链,形成一个复合渔场。如果这个“特定海域”就是“居住地”,而一整套的“设施与管理体制”就是“社区博物馆”本土化的应用,通过“兜底结网,网箱养殖”的保护方式来表示对居住地的“整体保护”“原址保护”“自我保护”“开放性保护”“可持续发展”,收获的定然是社区博物馆本土化的美好未来。
2.2理念的时代要求
乡村发展是地域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的综合。然而以“居住地”“居民”为主体的社区博物馆理念,在欧洲实践中对地域经济发展问题表达得不明确,其原因与理念诞生的时代背景相关,社区博物馆源于欧洲后工业化时代,理念的产生和实践是建立在当时经济积累之上的,是对工业化发展出现的一系列社会现象、环境问题的反思,换言之理念的出发点是站在当时经济发展对立面。因此,社区博物馆理念强调地域文化、生活传承的一面,而刻意“淡化”地域经济发展的另一面,这是理念的时代性所决定的,并不是理念自身的缺失。
但是理念引入我国,由于我国国情的不同,使理念本土化实践需要在承担文化保护的同时,推动地域经济发展的双重任务。因而不能将理念理解为单纯的文化传承的工具,无视它对地域经济振兴发展的促进作用。社区博物馆理念不仅包涵了经济发展的因子,其理念也是因它而起,不过这一落脚点常常被忽略,使人们错误认为社区博物馆的作用与意义仅仅是对文化、生活的传承保护。事实上,今天所有被称之为文化遗产的事物,无一不是过去经济繁荣的象征,贫穷既保护不了今天的文化遗产,也创造不了明天的文化遗产。社区博物馆欧洲实践“淡化”“回避”经济问题是当初的时代要求,而我国本土化实践强调经济对地域综合发展的意义也是当下的时代要求。
社区博物馆本土化的意义绝不意味着对农村贫穷与落后的保护,也不是“完全回归农村时代”而是“从生长的地方寻求文化的根源,思索如何面对未来,向越来越高度的物质文明、缺乏人情的生活环境挑战”。因此必须明确:地域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发展应该成为社区博物馆本土化实践的第一要务,也是地域综合性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更是地域扶贫脱贫的基本保证。社区博物馆本土化正是为了响应时代变革、顺应乡村发展进程、满足民生需求,必将成为促进我国乡村地域发展的新动能。
2.3理念的进化:从文化到经济
社区博物馆理念的“进化”脱胎于“文化生态学”(Cultural Ecology)理念,而“文化进化”的过程,就是“文化变迁”和“文化适应”的过程,这是“文化生态学”的重要观点。美国学者怀特在《文化的进化》中提出:“文化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需要”,其中的方法之一就是靠开发自然资源来满足。而今社区博物馆本土化实践中,经济课题对于乡村发展显得越发重要而且无处不在,这就让社区博物馆理念与乡村地域可持续发展具备了融合的前提与基础。
因此,社区博物馆理念的本土化,必然需要实现从文化保护到经济发展的转变,它之所以成为必然,是人们寻求生存、改善生活而做出的调整与改变。戴瓦兰先生在《未来社区博物馆》对里维埃“进化”作了明确的诠释,并强调“社区博物馆的任务是为了文化自助而展开的社会动员,但是必须永远铭记它的存在是为今天的社区服务,而不是昨天的社区,如果它丧失了对社会变化的敏感,它就会死亡,而应该死亡”[5]。当然从宏观乡村发展来看,文化是区域发展的一项重要的战略性资源,但乡村发展需要综合推进和多元机制,可持续的经济振兴应以地域资源與传统创新为起点,克服急于求成以牺牲地域特色的短视行为而逐渐发展壮大,内生式发展才能够既保护地域文化又促进经济发展。所以,社区博物既要保护文化,又要振兴经济是理念自身对时代变革的响应,是理念自我“进化”的结果,是内源性的要求,而非外来的给予。毫无疑问社区博物馆本土化只有为地域社会的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作贡献,才能实现自身使命。
3社区博物馆本土化实践性分析
贵州六枝特区的社区博物馆是我国与挪威在国家层面上的合作项目,各级地方政府给予大量人力、财力的帮助,使这个深藏大山之中的村寨满足了建设社区博物馆的前期要求,并在该地区通路、通电、通水及修建小学,但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并没能取得人们所预期的那样成功。由于贵州社区博物馆地域情况特殊性,它们本应需要一个更长的哺育期与陪伴期以应对外来社会的冲突,但不可否认贵州早期项目对我国社区博物馆发展的意义,并成为我国社区博物馆本土化的标志,维护它的存在远胜于对它的求全责备。本研究从社区博物馆的本土化过程、开发模式和人的作用作如下思考。
3.1项目的本土化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社区博物馆是舶来品,本土化又应如何实现?从理念的引入到本土化实践,地域社会的进步不仅需要一个长期的演进过程,还要有正确的推进时序。乡村的地域发展必然要经历几个过程,而本土化实践采取的措施应与地域发展所处的阶段对应吻合。具体的阶段性策略可划分为:萌芽期政府、专家存在的必要性;摸索期自我拟定规划、探索尝试的努力;成长期、发展期规模扩大、管理提升和多样化的目标实现必须要对整个产业链进行巡视关注。可见在这个成长轨迹中,决策者与营造者必须认清并掌握这些问题且采取应对行动,这在本土化实践过程中尤为重要。
以日本三岛町地域振兴过程为例,战后的三岛町是一个人口过疏,产业衰败的农山村,在寻求解决对策过程中发现,单纯的企业引进或借助第三方的乡村开发,所获利益几乎无法返还当地。因此决定靠自己的力量探索乡村振兴方案,并以“新娘愿意嫁来的村落”为目标,通过五个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关联的运动逐步展开方案:首先提出“乡村运动”也就是“农家乐”,让城市人到农村来感受田园之美和质朴人情为地域振兴的起始;其次的“生活工艺运动”是利用当地特产桐木、藤蔓资源发展家具与藤编等手工艺产业;三是在前两项的基础上推出“有机农业运动”,目的是培养以乡村为基地的生态农业本土带头人,这是十分关键而又必要的过程;四是开展“地区自豪运动”从历史、风土、生活等方面重新认识家园,唤醒居民的自豪感;最后以“健康呵护运动”鼓励全体居民参与其中。如此,三岛町乡村发展的过程,就成为全体居民参与并找回自我追求的过程,也是村民成为乡村发展各个侧面主体力量的过程。
相比较而言,贵州实践由于居民参与缺失,没能有效地使外来理念转化为契合地域发展的行动,因此贵州项目出现这样的一幕:中外学者们为保护与学习当地的特色文化而来,而村民却拿着自己的特色文化(刺绣作品)追着客人售卖,这一现象虽然不能说明村民对文化与经济的“取舍”,但深刻反映社区博物馆本土化是地域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综合发展的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断面,需要地域居民逐步接受、付出与努力。所以,因地制宜、循序渐进才是社区博物馆的科学准则,也是本土化“真经”所在。如果我们急于求成一味生搬硬套外国的模板,而无视自身的实际情况与特色,必将会迷失自我。
社区博物馆贵州实践在有些学者看来不仅不能起到维护地域文化的作用,反而引来现代潮流的冲击而加速灭亡。笔者认为贵州实践的不足并不是理念本身问题,而是理念本土化过程中的阵痛,是人对理念的理解与操作的结果。“尽管社区博物馆运动已经发展成为一场超越学术的社会运动,但由于人们对社区博物馆背后的理性深意缺乏探索精神,导致社区博物馆普遍充满失败感”[6]。而当下正值地域发展机遇期,社区博物馆应主动对接并承担起地域发展的社会责职,促进社区博物馆进化机制在本土化发展中的完善。
戴瓦兰在总结世界社区博物馆成功与失败的经验后感慨地表示:社区博物馆“心”(进取的态度)比“头”(外在的规则)更重要,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社区博物馆本土化实践,项目的过程比结果更重要。
3.2社区博物馆不是旅游机构的复制品
我国对社区博物馆本土化实践在乡村发展方面常常寄希望于“乡村旅游”带动“乡村经济”,这种“挂靠式发展”的模式,并不符合社区博物馆理念,极有可能造成以牺牲地域居民正常的生产生活环境和乡土风貌的原真性为代价,使传统村寨和文化遗产成为粗俗旅游收入的工具、乡村公共旅游资源极易变成乡村旅游的“公地悲剧”,难以实现乡村“真正意义上的发展”。
达格·梅克勒伯特在2005年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中提出:“中国的管理层对社区博物馆的认识存在差距,中间管理层存在对旅游发展的误解”,并强调“我们必须牢记,建立起来还不够,没有成熟的管理、主动的经济和人力资源投资仍将会前功尽弃”[7]。我国相当部分的社区博物馆一味谋求投入少、见效快的乡村旅游方式,使之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主要模式,由于未经社区博物馆理念的组织与引导,将本应给予居民的关注转向附和旅游者的需求,因此削弱了地域自身内源经济发展的能力,甚至对地域經济和文化协调共生造成较大障碍。“仅仅将旅游作为主要目标就不是社区博物馆,旅游是社区博物馆的其中一个目标,必须保证平衡”[8]。所以乡村发展应在“守护”与“激活”之间寻求平衡,维护文化与生活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才能进一步激活自身优势与特色魅力,为乡村旅游健康发展,为大都市逆城市化发展提供优良的环境与承载空间。
怎样才是社区博物馆理念所表达的地域发展与乡村旅游的关系呢?社区博物馆理念给出的答案是:社区博物馆应支持地域旅游事业发展,但必须牢记它的设立不是为旅游者,而是为地域居民的生活。因为,他们不需要改变自我以迎合外来的客体,一个别具特色的地域环境,必然吸引旅游者的目光。因此旅游不是乡村经济发展的唯一路径,社区博物馆也不是旅游机构的复制品。
3.3“人”是本土化实践的重要资源
意大利学者毛里齐奥·马吉也强调:地域负责人的才能是地域发展的基础,居民参与仍然是社区博物馆最大问题,所以培养领导是最重要的投资,必须在投资“东西”时,同时投资“人”[1]。社区博物馆理念强调“自我保护”,但在实践过程中,需要分解成一个“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自我受益”→“自我提升”的过程,必须通过“人”来层层落实、向内挖掘。乡村发展以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为出发点,着力解决居民最关心、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从而保证居民参与积极性。
浙江安吉社区博物馆本土化实践中就形成一套调查民意、汇集民意、尊重民意、采纳民意的机制,将乡村振兴工作建立在农民群众需求基础之上,使得政府相关决策和工作部署有效转化为居民群众自觉建设家园的行动,将乡村的特色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的动力,提高居民生活质量,将乡村营造成一个优美、自然、富裕和有人情味的故乡[9]。日本乡村振兴中强调地域负责人应为“风之人”与“土之人”的结合,他们不仅熟悉村落的资源与传统,还了解外界的先进技术和制度,能够在实践中将地域传统,对接现代需求,进行革新与再创造。日本大分县知县松平守彦(一村一品运动的发起人)说过:“推进一村一品运动的原动力首先是人,并且始终是人的精神发挥作用,单纯依赖行政产生不了真正的运动,也收不到好的效果”[10],所以,乡村发展最主要不是“品”,而是如何推动品的“人”。这一观点如今广泛实践于日本各地的乡村振兴计划项目中,成功地激励当地居民对农业的参与热情。
社区博物馆贵州实践,我们在对其进行物质条件与经济资助之外忽略了对人的投资,特别是本土化实践中的关键人物——馆长的重要性,所以,“人”或許是贵州本土化实践的最大缺失。
4本土化途径的再思考
所谓本土化,是外来事物在本土生存适应的过程。社区博物馆的本土化,应深化为是理念自身的完善与进化过程,同时也是促进居民参与、文化传承、经济发展、社会综合提升的过程。
社区博物馆在促进乡村产业经济的同时,必须与当地的生产、生活、文化、环境的产业机能相结合,只有如此地域居民、当地企业家才有可能成为地域开发的主体,现有产业和传统生活的经济形态才有条件进一步彰显地域特色,实现本土产业的经济增长。由此可知,社区博物馆本土化推动产业经济发展的观点契合于内生式地域振兴模式,其意义就在于不以破坏与牺牲地域文化实现经济增长,而是表现出依靠本地资源、根植于传统文化,使地域与居民共同发展受益的内源发展形式。这样才能从单纯的文化、生活的乘载工具,“进化”为促进地域发展的乘载工具。在此对本土化实践途径有以下认识。
4.1保护乡村的本真性
虽然,我国已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但必须认清“我国社会性质是乡土社会”这一特征,我国的乡村形态(无论是“传统村落”还是一般村落)都应被理解为是农耕文明的遗产形式,并且是我国社会文化、生产生活绵延不绝的源头,理应倍加珍惜本已十分脆弱的乡村生存环境,吸取我国经济开发之初,对城市历史环境、社会生态造成破坏的教训。随着国家对农业农村的政策倾斜及其社会资本大量涌入,诸多乡村开发项目正如火如荼地展开,在当下的乡村振兴战略实践中,我们应该铭记钱穆先生所讲 “中国文化是自始至终建筑在农业上面的”这样一个事实,认清我国乡村社会的特征,乡村发展必须坚持“整体的、综合的、内生式的”多维方式,只有如此才能守住我国乡村的本真。
4.2内生式发展模式助力本土化途径
乡村发展是人类社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目标,因此社区博物馆本土化实践应坚持以人为主体的“内生式乡村发展”理念。“内生式发展论”最初由日本提出,并在日本地域振兴中得以充分的运用,与“造町运动”“一村一品”“社区营造”等实践互为验证,取得丰硕的成果。内生式发展的基本特性是以地域居民为开发主体,不依靠外来力量,自主自立、因地制宜对地域资源的活用与保护。“内生式发展”是否适合我国农村社会?这一问题在“国家社科基金‘九五重点课题——百村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结论中给出了答案:我国农村并没有像大多数西方国家那样,在现代化过程中使传统乡村社会体系普遍解体的原因,是我国农村一直秉持从自身资源出发,积极利用与吸收外部条件与经验,自觉践行因地制宜、自主自立的内生式发展方式。所以,它必然成为我国当下乡村发展方式。
社区博物馆本土化的乡村发展,就是以村落为载体,充分利用乡村特色资源和居民生活场景,组织村民参与产业经营,并从中受益,由此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集体经济实力,促使乡村传统文化、生产生活和自然生态的多样性得到有效的保护与传承,这都与内生式的乡村发展有多方面的契合之处,非常适合以内生式发展理念来推进社区博物馆本土化实践。只有如此,地域振兴才能通过自己的力量实现“主动的经济”和“真正意义上的发展”,所以,社区博物馆本土化为复兴乡村经济提供了新的思路。
4.3从人居环境角度重新衡量乡村发展的方向
1993年吴良镛、周干峙、林志群等专家首次提出 “人居环境科学”体系,认为应将人类聚居场所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我国乡村既是一个文化综合体,也是社会有机体,应将“人居环境”作为乡村振兴一项重要组成部分,并以此作为衡量乡村经济质量和水平的标准之一。人居环境在乡村实践中强调“融贯”发展,就是从具体情况出发,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主动从相关学科中吸取方法与智慧,并综合地域各种要素将自然、人、社会、空间等人类聚居场所,作为一个有机体来综合性考虑,从而达到人与自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目标[11]。人居环境概念下的社区博物馆本土化,正是保护农村完整的人居环境,其实践活动应超越眼前的短期经济利益,投身到更加长远的乡村可持续发展的“营造”“深耕”与“培育”理念之中,并将关注的触角延伸至对乡村环境、乡村社会和居民生活的课题之中,实现乡村发展从“造景”“造产”到“造人”的综合性提升,使社区博物馆“这颗思想的种子”在乡村发展与居民参与中落地生根。
5结语
在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引领下,乡村振兴已成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重要方向。在城镇化、现代化不断推进的过程中,需要对乡村的社会特性、文化背景与发展理念的融合等方面重新认识与理解。
整体的、综合的、内生式的地域振兴关键在于重视文化、经济的同时,应强调人类与自然的协调,将自身作为自然、社会主体的一员,来营造适合人类生存的场所和对人性真善美的追求,体现国家在推进乡村发展的过程中对乡村社会本源性思考,并将此转化为解决当前我国“三农问题”的核心思想。社区博物馆在本土化实践中应当注重内生式发展的运用,将“三农问题”和文化传承、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整合在一起,使“三农问题”转变为乡村发展的关键与抓手,“三农”不仅不会成为乡村发展的“问题”,而且将成为乡村发展最大的资源优势和产业纵深。经济是乡村衰败的原因,但一味地强调经济绝不是拯救乡村社会的手段,社区博物馆本土化实践应探寻与乡村地域发展的契合之处,使文化保护与经济发展能够从矛盾的困境中化茧成蝶,成为我国乡村发展的“新引擎”。
注:
①“六枝原则”是中国和挪威合作建设贵州生态博物馆群项目的核心原则,是2000年由中挪专家及贵州4个生态博物馆的村民代表、地方政府管理层等,在六枝特区举办研习班时讨论提出框架后逐步完善的。
参考文献:
[1]毛里齐奥·马吉,张晋平.世界生态博物馆共同面临的问题及怎样面对它们[J].中国博物馆,2005(3):31-33.
[2]单霁翔.本土化是中国生态博物馆发展建设的必由之路[N].中国文物报,2010-8-25(1).
[3]方李莉.谁能拥有文化解释的权力——生态博物馆理念所面临的挑战[M]//陶立璠,樱井龙彦.非物质文化遗产学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4-9.
[4]苏东海.生态博物馆的思想及中国的行动[J].国际博物馆,2008(z1):29-40.
[5]戴瓦兰,宋向光.未来的社区博物馆[J].中国博物馆,2011(z1):54-58.
[6]傅斌.生态博物馆与生态文明建设[N].中国文物报,2017-03-14.
[7]达格·梅克勒伯斯特,张晋平.从挪威观点看贵州省生态博物馆项目[J].中国博物馆,2005(3):17-21.
[8]玛葛丽塔·科古,张晋平.生态博物馆:政府的角色[J].中国博物馆,2005(3):48-51.
[9]翁鸣.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实践和创新的典范——“湖州·中国美丽乡村建(湖州模式)研讨会”综述[J].中国农村经济,2011(2):93-96.
[10]松平守彦.一村一品运动[M].王翊,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11]肖正华.开彦:人居环境是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核心[J].中国民族建筑,2015(5):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