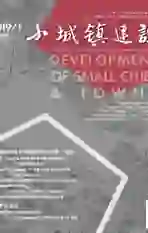城市历史景观视角下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研究
2019-09-10李和平张栩晨
李和平 张栩晨



摘要:“城市历史景观”将城镇理解为时间和空间的统一体,把动态发展的城镇及其与周边环境的联系都作为遗产保护的范畴,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方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通过对城市历史景观内涵的深入分析,提炼出“层积性”与“关联性”两个核心概念,并在基础上提出基于多元价值层积识别的整体性保护框架,包括时间维度的“动态层积”识别方法和空间维度的“整体关联”保护方法,强调对遗产整个生命周期价值规律识别的基础上,对遗产及其关联性要素进行整体性保护。最后以河北明清大名古县城为例进行案例研究,以期为其他名城保护提供一些借鉴。
关键词:历史文化名城;城市历史景观;动态层积;整体关联;大名古城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01.014·中图分类号:TU984
文章编号:1009-1483(2019)01-0102-11·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A Case Study of Daming Ancient Cit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Hebei
LI Heping, ZHANG Xuchen
[Abstract] The "Historical urban landscape" regards the city as a unity of time and space, and the dynamic development of the city and its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are related as the scope of heritage protection, which provides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This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situations and problems of the protection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Through the in-depth analysis of"HUL", the two core concepts of "stratification" and "association" are extracted. Then, the paper proposes a holistic protection framework based on multi-value layering recognition, which including the "dynamic stratification" of the time dimension and the "overall association" of the spatial dimension. And it emphasizes the overall protection of the heritage and its related elements on the basis of the identification of the entire life cycle value of the heritage. Finally, the paper takes Daming ancient city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in Hebe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with a view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other famous cities.
[Keyword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y;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 dynamic stratification; global correlation; Daming Ancient City
引言
近年來,我国许多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遗产正在受到城镇发展的影响,历史遗迹被现代化城镇建设空间挤压,慢慢形成孤立分散的文化碎片[1],有的甚至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开始危及到城镇历史文化脉络的保护和传承。城镇人口的膨胀和城镇的不断扩张、现代化和经济化的发展每天都在侵蚀着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历史文化名城在其保护和发展过程中如何实现文化价值的传承和历史风貌的延续,已成为当前我国名城保护的难题。
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布了《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强调从历史发展的层积性、价值内涵的多样性、空间的关联性与广度等方面去理解城镇遗产的价值、规律、特点和保护、管理要求,提出应将历史城镇的发展与其价值属性相结合,将相应的保护措施融入更广泛的城镇发展框架。其作为国际层面关于历史名城保护最新的纲领性文件,对当前的保护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在此背景下,本文尝试从“城市历史景观”的新视角出发,在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两个层面去探讨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旨在找寻一种名城保护的新思路和新方法,让身边的历史文化遗产继续“活”下去。
1城市历史景观的内涵
1.1城市历史景观的由来与发展
1992年,“文化景观”理念被正式提出[2],为“城市历史景观”这一概念奠定了基础。2005年5月,在“世界遗产与当代建筑”国际会议上签署的《维也纳备忘录》中最早正式提出了“城市历史景观”这一术语[3]。后经过数次国际重要会议讨论,UNESCO于2011年11月通过了《关于城市历史景观的建议书》(下文简称《建议书》),给出了“城市历史景观”的明确的定义,并对其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运用、政策、管理方法等方面提出了指导建议[4]。2013年,UNESCO出版《城市历史景观保护方法详述》小手册,其针对《建议书》作了延伸和推广,增强了可读性和宣传性。
1.2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
在《建议书》中,城市历史景观被定义为“文化和自然价值及属性在历史上层层积淀而产生的城市区域,其超越了‘历史中心或‘整体的概念,包括更广泛的城市背景①及其地理环境。应考虑其物质形态、空间布局、自然特征和环境与社会、文化、经济价值的相互关联性”[5]。上述概念界定实际上将历史城镇视为特殊景观对象,是经过岁月积累在环境中形成的多重层积,是“文化景观”遗产理念在历史城区(城镇)保护中的应用和拓展[6]。城市历史景观的思路明确了在城镇认知和保护中“层积性”和“关联性”两个重要的概念,“层积性”的概念强调了历史城镇发展变化的动态特性,又反映了城镇的发展是沿着一定的脉络和轨迹进行的。“关联性”的概念既强调了景观物质空间特征与其地域自然、人文背景之间的联系,也承认了这些关联性体现在城镇建成区与其所根植的地域环境及各种景观遗产的形态关系与组织关系之中[7]。
《建议书》的开篇指出“城市历史景观方法作为一种保存遗产和管理历史名城的创新方式具有重要意义”。这是第一次在官方文件中将其与“方法”连接使用,《建议书》为在城市大背景下识别、保护和管理历史区域提出了一种景观方法。其与张兵教授的观点不谋而合,他认为“城市历史景观”是一种方法并提倡关联性的研究途径和系统方法[8];但是张松教授在做澳门历史的保护研究时,将“城市历史景观”用于总结澳门的文化遗产类型[9],将其看作是一种遗产品类。在近年来的历史城镇保护实践中,我们主要在探讨和思考如何在系统研究自然、人文、经济、社会、环境的基础上形成一套全面识别其价值内涵并合理确定保护内容和保护措施的方法,这其实和《建议书》所倡导的价值观和整体保护方法是吻合的,所以,笔者更倾向于将“城市历史景观”理解为一种景观方法,即一种基于历史文化价值层积识别的整体性景观保护方法。
城市历史景观英文是“Historic Urban Landscape②”。首先,“Historic”译为历史性的,是对时间层面的限定,强调遗产对象的历史意义,包含遗产从产生到现在的整体视角的历史性。其次,“Urban”译为城市的,是对空间层面的限定,即“城市历史景观”意在探索在“城市”范围内如何平衡遗产保护与发展的议题。最后,“Landscspe”译为景观,是对研究对象的限定,也是整个概念的落脚点。“景观”概念不仅描述了物质的、有形的要素,更包含了其非物质、无形的要素,对于遗产丰富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具有很高的表意性[10]。通过构词法分析可以看出,“城市历史景观”是通过“城市”“历史”的内涵对“景观”内容进行的限定与丰富,可从时间维度的“历史”和空间维度的“城市”去理解这个概念。
不难发现,这和上文所提到的“层积性”和“关联性”两个重要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应的。在时间维度,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不再是从传统的“过去”和“现在”相分离的角度去理解文化遗产的保护,而是将遗产的整个演变过程作为研究对象,强调以“历史层积”的角度看待历史遗产的景观变迁。不同的时代便是不同的历史“层积”,每个“层积”包含着不同的景观特质和历史记忆,也就是不同的“价值内涵”。在空间维度,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强调历史城市与所在区域、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关联性,应放眼于历史城区之外更大的地理环境。另外,城市遗产保护应综合考虑物质性要素所映射出的城市经济、社会、文化等多样要素的发展和特征。
1.3城市历史景观的构成要素
城市历史景观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关系层层累积的结果,具有物质和文化的双重属性,物质系统是文化内涵的外在表现和载体,其受到文化价值的作用,两者相互影响,文化价值则是促成物质系统空间的动力因素,其蕴藏在不同的载体要素中。具体来讲,物质系统要素可以分为自然环境要素和人工环境要素。其中,自然环境要素指景观格局,即城镇形成与发展的整体景观空间与自身相融的空间结构关系;人工环境要素包括城镇布局、簇群地段、历史街巷和建筑空间,是城镇发展过程中最能反映历史文化内涵和信息的物质要素,其中城镇布局一般由一个或者多个簇群地段组成。文化系统要素主要指物质要素所表征的无形文化要素,一般体现为历史城镇中的地方文化、传统习俗、曾经发生的历史事件及原住居民的思想观念等[11](见图1)。其中,历史事件指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当地带来影响的较为重大的事件,如“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在明清时期,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招抚流民垦殖的相关政策,使得大量移民进入四川地区[12],其对川渝地区的会馆建筑带来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湖广会馆、广东会馆、陕西会馆等均是那一时期的产物。
2城市历史景观视角下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思路
2.1保护框架:基于多元价值层积识别的整体性保护框架
如上文所析,“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对当前保护工作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其强调以“历史层积”的角度看待历史遗产的动态变迁,重视历史城市与所在区域、自然和社会文化环境的相互“关联性”,有助于我們更加全面且深刻地认识蕴含在各种空间与文化、空间与时间联系中的内在价值内涵,厘清城镇景观发展演变的规律和历史逻辑,从而在此基础上提出一套有针对性的历史城镇整体性保护方法。因此,对于历史城镇的保护和研究便涉及对价值内涵识别和整体性保护方法的深入挖掘。
对此,本文从遗产保护的时空角度出发,提出时间维度 “动态层积”和空间维度 “整体关联”的工作方法,以回应《建议书》中“层积性”与“关联性”的相应概念,试图探寻一种基于多元价值层积识别的历史文化名城整体性保护新路径(见图2)。时间维度的“动态层积”强调以发展的视角看待历史的“动态”性和“层积”性,应关注时间维度上不同“层积”的积累和动态发展,以识别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与特色,作为对空间维度的指导;空间维度的“整体关联”强调各历史空间要素之间及与文化属性的“整体”性和“关联”性,应关注同一“层积”上物质系统要素的相互关系,承接时间维度的内容,并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提供思路与方法。
2.2识别方法:时间维度的“动态层积”
從时间维度来讲,城市是沿着一定的轨迹变化、发展和进化的有机体,一般都会经历初生、成长、成熟、衰退和再生长的演变过程,在过程中也会面临多样的不可控因素,对城市及历史文化遗产造成影响,体现出一种“动态性”(见图3)。这与传统过于关注遗产某一时期价值属性的静态方法是不同的,大同古城近年来大量建造假古董,搬掉新建筑,其宣称要“回到明朝”的做法引起国内遗产保护界的广泛讨论,这种忽视遗产演进动态性过于强调某一时期遗产的静态性行为受到各位专家的批评。
历史文化遗产在不同时间维度会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记忆和历史痕迹,这些文化和历史要素在不同时间维度上产生多元反应,表现出一种“层积性”。这种“层积性”包含共时性和历史性两个层面,共时性的“层积”是某一时段文化系统要素和物质系统要素相互联系组合的结果,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一个“层积切片”,即使某一时期的遗存已经碎片化,但它仍存在特定的价值属性;历时性的“层积”是从整个时间维度,去发现和挖掘城市不同时期的文化价值,不同时期的“层积”之间体现出一种逻辑联系,这是对其价值完整识别的必要条件[13]。比如纽约高线公园通过历时性层积分析其各时期的演变进程,最终确定保留铁路线,打造新的市民公共空间,带动整个地区的发展,高线地区的成功便是建立在各“层积切片”价值识别的基础之上[14]。
因此,名城保护应从时间维度的“动态层积”出发,按时间序列对其遗产层积进行叠加和研究,摸清历史遗产的演进规律和相互作用,实现对遗产整个生命周期的价值识别和文化判断,这是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础,也是下一步提出保护方法和思路的依据。
2.3保护方法:空间维度的“整体关联”
从空间维度来讲,我们应该在保护过程中将历史城区置身于其之外更大的地理环境,从更广阔的角度对其进行保护,这是一种“整体性”的思维。比如张兵等人在编制太原名城保护规划时,将太原城置于更广阔的背景中便发现了多处关隘驿站分布和文化路线的存在,这些外围遗产的保护和主城处于同等保护框架之下[8]。“整体性”的概念除了强调遗产与环境的协调统一,还强调遗产与其文化、社会等无形要素的关联性。本文主要从物质系统层面的空间维度出发,故重点强调物质层面的“整体性”,主要从空间维度去探讨名城的整体性保护方法。
另外,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强调历史遗产与其他遗产点及其所根植的外围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也就是一种“关联性”的体现。这种“关联性”包括遗产与环境之间的关联、遗产与遗产之间的关联,我们在保护这些遗产时就得注意对遗产及其关联性要素进行整体性的保护和展示。换句话说,这种“关联性”一方面可以表现在一个基于遗产更广阔环境的整体区域尺度上,另一方面表现在遗产本体尺度上的内在联系,对于历史文化名城,遗产本体尺度又包括古城格局、街巷场所和建筑本体等不同尺度。比如,我们在讨论庞贝古城的保护时,应该将10公里外的维苏威火山考虑进来,探讨两者之间的关联性并进行整体性的保护。另外,我们在探讨遗产本体的保护时,也应注重其所处背景环境,其实遗产本体与遗产本体之间是互为“背景环境”的,我们应注重对这种关联性的保护,如果遗产周边的环境遭到破坏,那么遗产的价值将极大削弱,也将导致“孤岛化”“碎片化”遗产的出现。
因此,“整体关联”的保护方法主要是从空间维度的物质层面出发,从区域尺度和遗产本体尺度,对遗产及其关联性要素(或是其他遗产、其所处的环境要素)进行整体性的保护(见图4)。
2.4两者的关系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基础是对其价值的识别和判定,构成遗产价值的基础是各个时期的“层积切片”,而每个城市的文化遗产价值不应是一个简单的“堆”积状态,它应当具有某种结构。“整体关联”的保护方法也不是停留在对“全部”的保存,而是要深入地循着这个结构对历史文化的逻辑加以保护和体现。“动态层积”便是对历史文化价值及其中所蕴藏逻辑的识别和挖掘,可以说是实现“整体关联”保护的基础,是历史文化名城整体保护时制定策略和措施的充分依据。反过来,“整体关联”的保护方法将名城的多元价值内涵落实到空间层面的物质载体之中,是对价值的展现与传承。
举个简单的例子,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做嘉兴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时,通过对古城格局的动态层积识别,得出嘉兴 “子城居中、四门通衢”的府城格局、运河枢纽城市格局、“西城东工”的近现代城市格局,并在保护规划中有意识地将代表相应格局的城墙、水利工程遗产、宗教设施、工业设施和文化设施保护下来,实现对价值内涵的传承[15]。
3 以河北邯郸明清大名古城为例
大名县地处河北省邯郸市,位于冀、鲁、豫三省交界处,因其较高的历史地位和丰富的历史遗存,2014年被评为河北省历史文化名城。明清大名古城位于县城区中南部,引河以西,整个历史城区保护面积约为3.2平方公里,护城河以内的整个明清古城,面积为1.17平方公里。明清大名古城具有完整城墙护城河体系,前朝后市,合理分区,空间秩序规整,传统风貌协调统一,是古代传统形制建城的典范,具有非常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随着古城人口的增多和城市化的快速建设,古城内人居环境压力、交通压力和基础设施压力不断增大,古城内传统街巷肌理和一些较为重要的历史建筑遭到破坏,无人管理和维修,传统繁荣商业街的经济、物质和环境逐渐衰退,古城开始呈现出物质衰败、活力不足、历史遗存“碎片化”等现实问题,古城传统风貌逐渐消失,古城历史的保护和传统价值特色的延续受到威胁。
3.1·时间维度的“动态层积”——明清大名古城价值与特色识别
3.1.1府城格局的演变
明清大名古城一直處于大名县城发展的核心位置,其历史的发展对大名县城有较大的影响,通过相关文献分析,明清大名古城历史沿革可分为:明清及以前时期(1840年以前)、清末时期(1840—1912年)、民国时期(1912—1949年)和建国后至今(1949年以后)四个阶段(见图5)。
(1)明清及以前时期——前朝后市的府城格局
古城是按照周礼城制思想进行规划建设的,“方形城池,衙署居中南部,中轴对称,四向城门”的规制,古城的南部是原来当时政治和商业的中心。政治中心是因为大量公共机构布置在府前街和道前街,包括府署、道署等;商业中心是因为南大街这一条著名的商业街。在这三条街内,店铺林立,商业文化氛围浓厚。此时期,“前朝后市”的古城格局逐渐形成,功能分区逐渐完善。
(2)清末时期——以宗教功能与教育功能为主的近代城市格局
文教建筑开始兴盛,古城兴起了“书院热”,在古城内新建了三所书院:贵乡书院、广晋书院和天雄书院。此后,古城内来了一批外国传教士,随之开始兴起以天主教堂为代表的西洋教会建筑,多位于东大街,逐渐形成“众星抱日月”的城市天际线格局。
(3)民国时期——延续十字大街轴线交叉的现代城市格局
府署撤销,大名县衙搬到府署办公。在这个时期,道署和元城县衙被撤掉,新建了直隶省立第五女子师范学校。此时期,古城中心仍在古城南部,呈十字大街交叉的格局。但是由于战争的破坏,古城墙损失惨重,拆掉了城楼和瓮城,外侧城砖也被扒掉。
(4)建国后至今——以北关为商业中心的当代城市格局
20世纪50年代,古城内旧衙署和庙堂的功能开始转换,服务于政府机关和企业;80年代,在城墙南部和北部一些位置上修建了住宅,护城河也有一部分遭到填埋;90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现代式的建筑所进入古城,破坏了原有风貌,北关附近的大名古城路开始成为城市商业中心;2000年至今,古城内商业文化氛围减弱,人流逐渐减少,活力不足。
3.1.2文化特色
(1)运河漕运文化——辉煌运河,繁华绵延流经之域
京杭大运河曾流经大名古城城东,也就是现在的卫河。大名古城凭借着优越的水利交通位置,经济得以快速发展。并且在经历了唐、宋和金等朝代之后,大名古城逐渐发展成为河北甚至华北地区最繁华的地区,在经济、军事等方面都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运河漕运文化。
(2)宗教信仰文化——开放包容,宗教信仰传播一隅
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大名古城广泛吸纳新事物,没有任何地域的偏见。吸收周边燕赵、齐鲁和中原等地域的不同文化,在此碰撞交流;大名古城内还存在数十个少数民族和五个宗教组织,包括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等,相互之间友好相待,丰富了大名的多元文化。
(3)红色革命文化——艰苦卓越,红色革命策源之地
在经过五四运动之后,大名古城逐渐发展成为冀南的革命摇篮。直隶大名七师素来被称作红色七师,1926年成立共产党支部,培养了以谢蕴山、赵纪彬为代表的优秀革命人物,另外,大名还出现了以柴鸿儒和郭隆真为代表的有较大影响力的革命家。
(4)冀南民俗文化——多样繁荣,传统民俗异彩纷呈
历史悠久的大名古城不光现存大量的物质形态遗产,还传承着大量非物质形态的文化遗产,共分为5大部分12中类39小项。其中传统手工技艺技能和书画艺术最为出名。
3.1.3明清大名古城历史文化的“动态层积”
在分析古城格局演变和梳理文化特色的基础上,从动态发展的角度去将各时期的“层积切片”进行叠加研究,梳理古城的历史发展脉络,厘清历史文化层积的规律,识别出大名古城的历史文化资源和文化价值特色,并从中总结历史与空间的相互逻辑关系(见图6)。大名古城的文化价值特色主要包括隋唐运河文化、北宋陪都文化、清末教会文化、民国革命文化和现今民俗文化等;物质文化资源主要可概括为“一城、两教堂、四湖、多点③”的现状遗存和“一寺、两学、三居、四庙、五书院、六官署、八牌坊”的历史遗址等;其逻辑关系主要包括“前朝后市,十字交叉,四向城门”的典型格局和完整反映历史演进的古城总体空间肌理和遗存建筑体系等。通过“动态层积”识别出遗产资源与文化价值体系,为下一步实现碎片化空间遗产的“整体关联”保护提供了依据,以实现明清大名古城更好地保护。
3.2·空间维度的“整体关联”——明清大名古城保护思路的建立
在对遗产资源和价值内涵挖掘和识别的基础上,从区域尺度和遗产本体尺度两种不同尺度探讨大名古城的“整体关联”保护方法,即从大名县域尺度和明清大名古城本体尺度进行探讨,通过对遗产及其关联性要素的整体性保护,落实文化价值在空间维度的保护和传承。
3.2.1区域尺度——古城与区域景观格局的整体性保护
大名县域存在较多的历史文化遗产,包括10余处古文化遗址、2处古城址、1处古河道、20余处古墓葬、10余处古村镇和多处古石刻等,这些历史遗产要素共同构成了大名的城市历史景观体系。明清大名古城的保护需要着眼整个县域层面,从活态保护维度进行审视,将其与其他遗产点建立有机联系,形成相互关联的遗产网络保护框架,进行整体性的保护(见图7)。
在大名县域还存在一条大运河故道——卫河,其作为线性遗产是大名遗产网络从空间层面进行活态保护的必备条件,也是实现整体保护遗产环境及关联历史要素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大名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形成了“一带,两区,多点”的保护框架,其中“一带”指隋唐大运河故道保护带,“两区”包含明清大名古城和北宋大名府故城遗址保护区,“多点”指各级文保单位。

另外,大名古城保护规划中还通过划定历史城区、历史城区风貌协调区、历史文化街区形成一个整体性的保护体系(见图8)。其古城所在的历史城区总体保护面积约为3.2平方公里,保护范围包括护城河以内的整个明清大名古城、两条护城河水系和周边的四关厢。另外,在保护规划中还划定了古城的两条历史文化街区,其保护和利用的价值较高。
3.2.2古城本体尺度——“城区—街巷—建筑”的整体性保护
(1)城区格局的整体保护
明清大名古城的空间格局尤为整体和严谨,其风貌之美在于它的规整与和谐大方。目前,古城空间格局保存较为完好,但仍有遭到破坏的地方。
依据前文对于古城演进历史逻辑和遗产资源的分析,规划保护和延续“前朝后市,十字交叉,四向城门”的典型府城格局,古城墙每边中间开一门,其十字形大街直接通往四座城门,构成大名古城的脊梁,另外结合“市”“朝”分区,可规划形成民俗休闲娱乐区和历史实景体验区;保护城区建筑肌理格局,目前城区的肌理是数次重要时期层叠演进而来的,每个时期产生的肌理不同,其建筑风貌也不一样,反过来这些肌理代表着不同时期城区的生长变换,应当予以延续,保留多样的建筑风貌(见图9);保護棋盘式的路网格局,保护东西南北大街,18条小街,60多条胡同。如果说十字大街构成古城的脊梁,那么再加上其他的棋盘式的方格路网,就组成古城的整个骨架,在骨架的基础上形成以院落为基础的居住体系;保护灵活分散的城市湖面格局,包括古城内四角较大的湖面和一些零星分布的湖面,营造古城宜人的景观格局;保护“众星抱日月”的城市天际线格局,其中,“日月”分别为46米高的天主教堂和东南西北四个方向的门楼,大量的传统民居则为“众星”,古城中的高17米的卧龙槐为点缀。
(2)街巷空间的整体保护
街巷空间承担了交通的基本功能,也是居民生活的舞台与交往的场所。为保护整体风貌,应注意保持城区内的街巷肌理和历史环境风貌。对其整体保护主要从街巷肌理、街巷界面、街巷尺度三个方面进行。
对于街巷肌理的保护,可以通过拓宽街巷、打通街巷、取消街巷和恢复街巷四种方法来实现,规划拓宽北马道、西马道等街巷到6米宽度,打通大布袋街向南通向县前街、满洲街北段,由西向东连接东马道的街巷宽度为4米,取消南厢门外侵占护城河的道路,恢复西马北段道路和东马南段道路。另外,应该注意对节点开敞空间、转折空间及古树等标志性空间要素的保护,共同形成古城街巷空间系统,实现街巷空间的整体保护。
对于街巷界面的保护,主要是保持建筑体量的连续,对古城内现状的街巷界面进行调研评估,确定需要修缮或改建、重建的建筑,提出对应的具体改善方式,并在材质、色彩等各种方面与整体的街巷立面协调起来,延续整个街道立面。
对于街巷尺度的保护,首先要控制关键通视廊道。大名古城需要加强古城内四周和零散开阔湖面及古城外围护城河整个通视廊道的控制,不能在廊道间增加任意建构筑物。注意满足各类重要历史建筑之间的通视要求,保护西关街东向西城门的视线通廊和满洲街南向天主教堂的视线通廊,保护四个方向城楼之间的视线通廊。在此基础上,再对古城内外的建筑高度进行控制。在城墙内部,80米内建筑不宜超过7米,街道沿街建筑应采用1~2层为主,以保护传统街巷尺度。
3.2.3建筑本体的整体保护
建筑本体作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中微观的组成层面,是最容易被感知的部分,也是价值内涵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对建筑本体尺度的整体保护主要从建筑格局、建筑材料工艺、功能更新三个方面进行。
建筑格局包括建筑内部格局和外部格局,对内部格局的保护即将其历史信息完整的延续下来,本文主要探讨外部格局的保护。如上文所述,建筑本体之间互为“背景环境”,共同叙述大名古城的历史和文化,对于每个单体建筑,均需要注重与周边环境的关系,将其与背景环境协调统一起来,实现整体保护。对于文保单位等重点建筑而言,还需要划定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并提出相应管控要求。每个建筑都由相应的建筑材料修建而成,修建的过程中会融入大量的建筑工艺,最后体现在建筑的结构、装饰等方面,我们在对建筑进行整体保护时也应该将这些要素考虑进去。另外,古城内的建筑在考虑历史功能的同时也应结合当前时代环境的要求变化,适当调整更新功能,让历史建筑在当代焕发出新的活力,这也是实现建筑本体尺度上整体保护的一种方式。
4 结语
历史文化名城作为我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的保护显得尤为重要[16]。“城市历史景观”视角的出现,给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式,其强调需要从动态的视角看待历史城市的“层积性”和关注遗产与遗产及其环境之间的“关联性”。基于此,通过对“城市历史景观”内涵的深入分析,提出一种基于多元价值层积识别的整体性保护方法:包括 “动态层积”的识别方法与“整体关联”的保护方法,通过梳理历史脉络和分析文化“层积”规律,去挖掘和判别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与特色,并以此为指导从空间上对遗产与遗产、遗产与环境之间进行整体性的保护。本文以河北明清大名古城为例,从府城格局演变与文化特色的层积分析探寻其文化资源与历史逻辑,并从区域尺度、古城本体尺度和建筑本体尺度提出不同的整体性保护方法,实现大名古城更好地保护和可持续的发展,也希望为我国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工作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注:
①根据《建议书》,上述更广泛的背景主要包括: 遗址的地形、地貌、水文和自然特征;其建成环境,不论是历史上的还是当代的;其地上地下的基础设施;其空地和花园、其土地使用模式和空间安排;感觉和视觉联系;城市结构的所有其他元素。背景还包括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做法和价值观、经济进程及与多样性和特性有关的遗产的无形方面。
②在早期译本中,“Historic Urban Landscape”被译为“历史性城市景观”,从2011年《建议书》开始,官方译本将其确定为“城市历史景观”。
③目前,大名古城内的文保单位和重要历史建筑主要包括庞爱之母大教堂、城墙、天主教堂旧址、南街张氏旧居、南街杨家贞洁牌坊、黄家祠堂、王藻故居、南大街药房、南大街洋布庄、南大街鞋店、南大街市政府旧址、南大街基督教堂、黄小街口基督教堂、南大街西侧院、南大街临街店铺、南大街西侧药房、南大街西侧院等。
参考文献:
[1]肖洪未.关联性保护与利用视域下城市线性文化景观的构建[J].西部人居环境学刊,2016,31(5):68-71.
[2]罗·范·奥爾斯,韩锋,王溪.城市历史景观的概念及其与文化景观的联系[J].中国园林,2012,28(5):16-18.
[3]杨箐丛.城市历史景观保护规划与控制引导——《维也纳备忘录》对我国历史城市的启示[D].上海:同济大学,2008.
[4]刘祎绯.中国的城市历史景观研究10年综述——缅怀吴瑞梵先生[J].中国园林,2016,32(2):74-77.
[5] UNESCO.Recommendation on Historic Urban Landscape[EB/OL].(2011-11-10).http://portal.unesco.org/2011-11-10.
[6]张松.历史城区的整体性保护——在“历史性城市景观”国际建议下的再思考[J].北京规划建设,2012(6):27-30.
[7]李和平,肖竞,曹珂,等. “景观—文化”协同演进的历史城镇活态保护方法探析[J].中国园林,2015,31(6):68-73.
[8]张兵.历史城镇整体保护中的“关联性”与“系统方法”——对“城市历史景观”概念的观察和思考[J].城市规划,2014,38(z2):42-48,113.
[9]张松,镇雪锋.澳门城市历史景观保护策略探讨[J].城市规划,2014,38(z1):91-96.
[10]麦琪·罗,韩锋,徐青.《欧洲风景公约》:关于“文化景观”的一场思想革命[J].中国园林,2007(11):10-15.
[11]肖竞,李和平,曹珂.西南地区城镇历史景观的特征识别与层积解译[J].南方建筑,2017(3):18-25.
[12]邹登顺.论明清移民与巴渝文化的新变[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5):93-97.
[13]张杰.作为城市历史景观的街区价值属性识别方法[J].小城镇建设,2012,30(10):47-48.doi:10.3969/j.issn.1002-8439.2012. 10.055.
[14]杨春侠.历时性保护中的更新——纽约高线公园再开发项目评析[J].规划师,2011,27(2):115-120.
[15]赵霞.基于历史性城市景观的浙北运河聚落整体性保护方法——以嘉兴名城保护规划为例[J].城市发展研究,2014,21(8):37-43.
[16]任洁.浅谈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性保护——以云南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为例[J].小城镇建设,2008,26(1):84-88.doi: 10.3969/j.issn.1002-8439.2008.0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