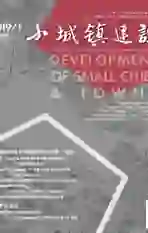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乡村聚落韧性评价
2019-09-10岳俞余高璟
岳俞余 高璟



摘要:在当前“乡村振兴”战略的背景下,如何应对我国乡村聚落环境污染、经济衰退、人口流失、社会结构瓦解等问题,实现乡村聚落的可持续发展成为当下乡村振兴的迫切目标。本研究通过对韧性理念及乡村聚落韧性的研究,以适应性循环理论为基础,提出基于社会生态系统视角的乡村聚落韧性的实证分析框架。文章以河南省汤阴县非城镇建设区内的乡村聚落为研究对象,构建汤阴县乡村聚落社会生态系统发展演变的评价体系,通过对汤阴县5个典型乡村聚落30年来各个关键指标的演变趋势研究,判断乡村聚落各个子系统的发展演变阶段与路径,研究外部干扰下汤阴县乡村聚落韧性特征和相对韧性值,从而提出韧性乡村聚落的培育策略。
关键词:乡村聚落韧性;社会生态系统;适应性循环理论;汤阴县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19.01.002·中图分类号:TU982.29
文章编号:1009-1483(2019)01-0005-10·文献标识码:A
Revaluation of Rural Settlement Toughness Based on Social Ecosystem Perspective: Taking Tangyin County Henan Province as an Example
YUE Yuyu, GAO Jing
[Abstract] The concept of resilience provides a new research idea for rural settlement development. This paper selects rural settlements in non-urban construction areas in Tangyin County of He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studies the resilience in rural settlements under external disturbances, and proposes strategies for cultivating resilient rural settlements. Under the external disturbances, it studies the universal change of the six elements in rural settlements in Tangyin County, which constitutes an index system for judging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rural settlements in Tangyin County. Through the evolution trends of key indicators in five typical rural settlements in Tangyin County over the past 30 years, we can judge the development stages and paths of each subsystems of rural settlements. According to the adaptive cycle theory, the resili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relative resilience values of rural settlements can be inferred. Based on the study, some cultivated approaches are proposed to the resilient rural settlements.
[Keywords] resilience in rural settlement; social ecosystem; adaptive cycle theory; Tangyin County
1鄉村聚落韧性的研究意义与背景
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1],然而改革开放后成千上万的乡村聚落被人为地终结,似乎都宣告着乡村的衰落及乡土社会的分崩离析。进入21世纪之后,这一趋势更加明显,2005年至2015年十年间中国消失了90多万个乡村聚落[2]。据《国家人口发展规划(2016—2030年)》预估,至203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达到70%,这意味着更多的乡村人口将离开乡村,城镇化进程下的乡村衰退将成为一种客观的必然[3]。在这种剧烈的社会变迁过程中,乡村聚落是反映乡土社会深刻变革的主要空间和集中体现,担负着承载农业生活和调节社会文化的重要作用[4]。中国的乡村聚落不仅不会终结,更会成为判断中国城镇化发展质量的重要标尺。
2004—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连续15年聚焦“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中共十九大会议更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高到国家战略层面,提出要实现乡村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总要求。健康发展的乡村聚落将成为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点。社会各界已公认,如果单纯依靠政府主导的补贴扶持形式,难以触及乡村聚落发展的内生机制,并不能实现乡村聚落真正的振兴。韧性理论的引入为乡村聚落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以此指导乡村聚落规划将更有效地促进乡村振兴与乡村可持续发展。只有培育具有韧性的乡村聚落,不断提升乡村聚落面对外界干扰抵御、适应和转型的能力,才能实现乡村振兴与乡村可持续发展。
2乡村聚落韧性的概念界定
韧性是指一个系统遭遇外界干扰时,维持稳定的能力,或者在固有平衡被打破时适应、转型的能力[5]。Mcintosh等认为乡村聚落韧性是乡村聚落在演变成城镇聚落或者消亡前能够处理和适应外部变化并可持续发展的能力[6]。
根据适应性循环理论,在外力干扰下乡村、乡村聚落发展阶段可以划分为快速发展、平稳发展、衰败和重构几个阶段[6]。这个发展过程不是绝对的、固定的周期,但一般乡村聚落大体沿着这样四个阶段不断发展。在外力干扰下,若乡村聚落具有良好的韧性,将快速渡过衰败阶段,进入重构阶段,或者进一步完成重构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阶段,呈现出螺旋式上升发展的趋势;若乡村聚落缺乏韧性,那么它将困于衰败阶段,难以完成系统重构,最终走向衰亡。
韧性理念的发展经历了从工程韧性到生态韧性,再到社会生态韧性的重要拓展[7]。通过对三种不同的韧性观点进行总结和对比发现,社会生态韧性抛弃了对平衡状态的追求,强调持续不断地主动适应和调整,其最终目的是系统在多尺度上的可持续发展,而非追求某个尺度下某一固定的稳定状态[8],这样的观点更加适用于乡村聚落的研究。
因而,在本研究中韧性理念是指社会生态韧性,即认为韧性是“系统在遭遇外界干扰下能够主动抵御(系统维持)、适应(系统逐渐变化)或者转化(系统重构)的能力”[9],它不等同于系统的稳定性,而是强调系统不断主动发展的能力,是社会生态系统在应对外部干扰时主动抵御、适应及转化的能力,强调系统的恢复力、适应性和可變性。
3乡村聚落社会生态系统分析与评价的理论框架
乡村聚落是乡村地域人类与自然相互作用关系最为紧密的区域[10],在这里,人类通过行动改变自然环境,环境又把人类对其产生的影响反馈给人类。Schouten和Heijman在研究荷兰乡村聚落韧性时,指出乡村聚落是包含自然生态、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为一体的社会生态系统[11]。自然生态系统为经济生产和社会生活子系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和发展空间。社会生活系统通过人类生活活动不断消耗自然资源,侵占生态空间,改变自然生态系统的生态景观;通过劳动力配置、社会制度和社会组织的改变影响经济生产系统的经济活动。经济生产系统则通过农业集约化专业化改变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和空间多样性,同时经济生产子系统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直接服务于社会生活子系统。乡村聚落内部三个子系统之间不是相互独立发展的,而是彼此交织,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了这个变量众多、机制复杂、开放式的乡村聚落社会生态系统[11]。
对于社会生态系统韧性的评价,本研究借鉴了韧性联盟提出的RATA(The Resilience, Adaptation& Transformation Assessment)评估框架。2010年韧性联盟提出了《社会生态系统韧性评估:从业者手册》2.0版本①,展示了RATA框架的5个步骤,即:系统构建、系统动力分析、探索系统与更高层级或者更低层级的互动、研究系统治理、基于评估的行动,为社会生态系统的韧性认知和评估提供了重要思路(见图1)。
4汤阴县乡村聚落韧性评价的系统建构
4.1汤阴县乡村聚落的基本情况
汤阴县隶属河南省安阳市,地处中原腹地,自古就是南北交通要冲,具备独特的区位优势,东邻油城濮阳,西接煤城鹤壁,南望省会郑州,北靠古都安阳(见图2)。
汤阴县素有“豫北粮仓”之称,境内包括丘陵和平原(包括泊洼)两种地貌类型,平原占比达到71.4%。同时受农业劳作半径的影响,造就了汤阴县乡村聚落的均质分布。平原地区聚落密度高,规模相对较大;丘陵地区聚落规模相对较小。近年来,人口流动成为乡村聚落社会结构变迁的主要动力,部分乡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大量乡村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季节性迁徙。
4.2汤阴县乡村聚落社会生态系统构建
汤阴县乡村聚落社会生态系统划分为社会生活、经济生产、自然生态三个子系统,在城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变迁的干扰下,其系统内部要素变化如图3所示。
社会生活子系统主要包含各种人力资源和社会组织,在城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变迁两个主要外部干扰下,人力资源大量外流、社会组织多元化程度弱是汤阴县乡村聚落社会生活子系统缺乏韧性的表征,相应地,人力资源适度流动、社会组织多元化发展是汤阴县乡村聚落社会生活子系统韧性发展的表征。本研究选取劳动力外出比作为量化外力作用下人力资源演变评价的关键指标,社会组织发展指数作为量化外力作用下社会组织发展演变的关键评价指标。
经济生产子系统主要包含各种农业经济活动和非农经济活动,若二者的多样性良好则表示经济生产子系统韧性发展,若二者的多样性差则表示经济生产子系统缺乏韧性。研究选取农业活动多样性指数和非农活动多样性指数作为量化汤阴县乡村聚落农业经济活动和非农经济活动在外力下演变的关键评价指标。
自然生态子系统主要包含各种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土地集约利用度低、生态空间被大量侵占是自然生态子系统缺乏韧性的表征,相应地,土地集约利用度高、生态空间合理调整是自然生态子系统具有韧性的表征。最后选取土地利用集约度作为量化外力下汤阴县乡村聚落自然资源演变的关键评价指标,选取生态空间类别和面积作为外力下生态环境发展变化的关键评价指标(见图4)。
5汤阴县典型乡村聚落韧性的分类评价与基本判断
汤阴县非城镇建设区内共有218个乡村聚落,根据地形地貌、区域位置、人均纯收入选取5个典型乡村聚落——南张贾村、部落村、小贺屯村、南阳村、岳儿寨南村,其中涉及丘陵、岗地、平原三种地貌及其过渡地带,分布跨越东、中、西3个区域。本研究首先对这5个聚落的社会生活子系统、经济生产子系统和自然生态子系统进行核心要素评价,判断其相对韧性,根据三个子系统的韧性对5个聚落的韧性进行排序,最后对汤阴县乡村聚落韧性的发展状况提出基本判断。
5.1社会生活子系统的社会韧性评价
5.1.1核心要素测度
人力资源要素的核心表征为劳动力外流状态的测度。就五个乡村聚落1983—2015年的劳动力外出比作对比,发现其演变过程可以划分为三种路径:第一种,南张贾与部落村劳动力外出比先增大后降低,意味着这两个聚落的劳动力经历了大量外出后又回到本聚落的过程,并且目前其常住人口中劳动力本地化都处于一个较高水平,即其劳动力在回流后已实现重构,即将进入新的快速发展阶段。第二种,岳儿寨南村的劳动力外出比一直呈现增长趋势,但从近十年的增长速度来看,岳儿寨南村劳动力外出比的增长速度有放缓的趋势,在实地调研中也发现有少部分返乡创业的劳动力,证明其劳动力正在进行重构。第三种,南阳村和小贺屯村的劳动力外出比一直呈现增长趋势,尤其是在农业税取消之后的近十年里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趋势,并且均已超过65%,结合实地调研情况,两个聚落本地劳动力基本为女性和50岁以上男性,基本没有返乡创业人员,可见由于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南阳村和小贺屯村的人力资源发展经过衰败阶段,已陷入贫穷陷阱(见图5)。
根据1983—2015年5个乡村聚落的社会组织发展指数演变,可以看出,2005年之前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农村集体经济走向衰败,各聚落均呈现社会组织弱化的趋势;但在2005年之后的10年,乡村聚落社会组织呈现出衰败和多元的两极分化(见图6)。小贺屯村和南阳村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公共服务设施供给出现困难,大量社会主导型社会组织没落,例如,中小学拆并、村医减少、传统宗祠空间废弃、宗族组织解体;同时大量精英阶层的流失,导致社会组织发展难以为继,组织能力愈加弱化,进入衰败阶段。而部落村、南张贾村及岳儿寨南村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逐渐出现城乡之间人口、资金的双向流动,一些返乡人群开始积极加入聚落社会经济建设、空间管理等公共事务,出现了新一代村民为主体的新型农村合作社,甚至出现了一些新兴的以政府——社会主导型的社会组织,例如部落村的村民房产监管小组。可见,这三个聚落的社会组织已经历或正在重构阶段。从社会组织发展指数来看,目前部落村社会组织发展最多元、组织能力最强,南张贾村次之,岳儿寨南村再次之。
5.1.2社会韧性小结
根据前文的比较,可以对5个聚落的社会生活系统发展演变进行总结(见表1)。根据适应性循环理论,乡村聚落发展阶段可以分为快速发展、平稳发展、衰败和重构4个阶段,其中重构阶段可以分为4种路径,每个阶段和路径其韧性值是在不断变化的,形成了不同的乡村聚落发展演变阶段与路径对应不同的相对韧性值。
可知,部落村社会韧性最好,南张贾村社会韧性次之,岳儿寨村社会韧性一般,南阳村社会韧性较差,小贺屯村社会韧性最差(见表2)。
综上,在城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变迁的外力下,乡村聚落社会生活子系统不韧性的特征是人力资源大量外流,社会组织衰败。具有社会韧性的部落村和南张贾村能够抵御这样的外力干扰,并适应这样的外部干扰,最终实现人力资源和社会组织的重构,维持令人满意的生活水准,并可持续发展。
5.2经济生产子系统的经济韧性评价
5.2.1核心要素测度
在农业经济活动多样性指数上,1983—1995年,由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村聚落农业活动的多样性普遍上升;1995—2005年农业活动的多样性普遍略有下降,这是由于机械化规模化种植提高了种植效率,解放了部分劳动力,同时外出务工和非农经济活动带来的高收入吸引剩余劳动力开始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流失导致农业经济活动趋于单一。2005年后城镇化进程进一步加速,城乡間人口、资金互动更加通畅,但由于聚落自身韧性的差异,出现多样性增加和急剧降低的两极分化——部落村、南张贾村和岳儿寨南村农业活动多样性开始增强,呈现出重构和新一轮快速发展的趋势,而南阳村和小贺屯村农业活动多样性呈现继续降低的趋势(见图7)。
对非农经济活动而言,例如小贺屯村非农经济活动极度不活跃,1983—2015年间均无工业,除零售外也无其他第三产业,因此不考虑小贺屯村非农经济活动的演变过程,可以认为小贺屯村的经济韧性最差。对其他4个乡村聚落1983—2015年的非农经济活动的类型和从业人员数量进行分析,明显可见历年来部落村和南张贾村的非农经济活动多样性指数都要比南阳村和岳儿寨南村高,前两者的非农经济活动发展相对更加活跃(见图8)。
5.2.2经济韧性小结
根据经济生产系统中农业活动和非农经济活动多样性演变过程的比较,得到5个聚落经济生产子系统的发展评价(见表3)。农业活动是汤阴县乡村聚落最主要的经济活动,非农经济活动是乡村聚落经济差异化发展的主要表现,因此在经济韧性评价时对两个方面赋予相同的权重。根据适应性循环理论,可以对5个乡村聚落的经济韧性进行初步判断:部落村经济韧性最好,南张贾村次之,岳儿寨村经济韧性一般,南阳村经济韧性较差,小贺屯村经济韧性最差。
综上,在城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变迁的影响下,乡村聚落经济生产子系统缺乏韧性的特征表现为农业经济活动单一,非农经济活动多样性差。经济韧性最好的部落村,在城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变迁的影响下,不管是农业经济活动还是非农经济活动都朝着多样性提高的方向发展,展示出适应这些外力干扰的能力,为人们提供令人满意的经济收入和多样化的工作机会。
5.3自然生态子系统的生态韧性评价
5.3.1核心要素测度
在本研究中自然资源的发展演变主要关注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尤其是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从1983—2015年5个乡村聚落土地利用集约度的演变过程中可以看出,2005年之前5个聚落都呈现出土地利用集约度下降的趋势,但在2005年之后,部落村和南张贾村随着人口回流和聚落空间的有效治理,土地利用集约度得到有效提升(见图9)。可见部落村和南张贾村的自然生态子系统处于重构阶段。2005年后,随着汤阴县城镇化进程的加速和户籍制度的改革,岳儿寨南村土地利用集约度下降速率变缓,处于衰败阶段后期,有进入重构阶段的趋势;而南阳村和小贺屯村土地利用集约度进一步大幅度降低,可见其已进入衰败之后的贫穷陷阱。
通过对5个乡村聚落土地利用集约度演变情况的分析可以判断,南张贾村和部落村自然生态系统已进入重构阶段,岳儿寨南村自然生态子系统已进入衰败阶段,南阳村和小贺屯村自然生态子系统已进入贫穷陷阱。
就生态环境要素而言,典型乡村聚落内生态环境主要是指农田、沟渠水系和林地三类生态空间。对比5个乡村聚落1983年和2015年的生态空间数量占比,可以看出5个乡村聚落的农田都呈减少趋势,而水系和林地则呈现差异化发展(见图10)。结合1983年和2015年的卫星影像图来看水系和林地的发展演变②,以南张贾村为例,1983年聚落内部有大量水系但林地极少,2015年水系面积大幅减少,但林地面积显著增加,二者总和略有增加,这一变化来自于南张贾村正在大力推行园林绿植产业,因而聚落内部开始引导大面积种植林木,因此,可以推测南张贾聚落内部自然生态系统正在经历重构阶段。
综上,基于生态环境的发展演变来看,南张贾村自然生态系统处于重构阶段,部落村即将进入快速发展阶段,岳儿寨南村和小贺屯村处于衰败极端,南沿村处于贫穷阶段。
5.3.2生态韧性小结
根据自然生态系统中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发展演变,判断出5个聚落自然生态子系统的发展演变阶段和路径,并初步判断部落村生态韧性相对较好,南张贾村生态韧性较好,岳儿寨村生态韧性相对较差,小贺屯村和南阳村生态韧性最差(见表4)。
在城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变迁的影响下,乡村聚落自然生态子系统不韧性的特征表现为土地资源的粗放利用、生态空间大量被侵占,例如南阳村就面临这样的问题。生态韧性较好的部落村,在外力干扰下,通过聚落内部调整,实现土地资源集约利用、生态空间合理调整,为人们提供维持发展的自然资源和令人满意的生态环境,从而实施自然生态系统的韧性发展。
5.4汤阴乡村聚落韧性的基本判断
乡村聚落社会生态系统中社会韧性、经济韧性和生态韧性是同等重要的[12],因此对其权重赋予相同的值,从而得到5个乡村聚落韧性的基本判断:部落村>南张贾村>岳儿寨南村>南阳村>小贺屯村(见表5)。
本研究认为,在城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干扰下部落村发展最具有韧性,能够适应外部干扰并转型发展。它通过劳动力的适度流动和社会组织的多元化发展实现社会生活系统的重构,通过丰富农业经济活动和非农经济活动的多样性实现经济生产系统的重构,通过土地资源的集约利用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重构,从而维持令人满意的生活水准,并保证整个乡村聚落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而在相同的外界干扰下小贺屯村发展韧性最差,劳动力的大量外流和社会组织的衰败反映了其社会生活系统的衰败,农业经济活动的单一和非农经济活动的缺乏反映了其经济生产系统的衰败,土地资源的浪费反映了其自然生态系统的衰败,各个子系统的衰败导致小贺屯村难以为村民提供令人满意的生活环境和工作机会,从而影响小贺屯村的可持续发展。唯有通过培育聚落内部的韧性,促进系统重构,才能实现小贺屯村的可持续发展。
6结语
乡村聚落韧性评价的目的在于更有针对性地提出培育乡村聚落的策略与方法。尤其系统衰败和重构阶段是培育系统韧性的最佳时机[8]。因此,在城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变迁的外部干扰下,应致力于提高汤阴县处于衰败或重组阶段的乡村聚落的韧性,通过重塑乡村聚落社会网络、加强乡村聚落人才培养、促进产业多元融合发展,推进乡村聚落进入新的循环,从而达到培育韧性乡村聚落的目标。
注:
①资料来源于韧性联盟官方网站:https://www. resalliance.org/resilience-assessment。
②1983年湯阴县乡村聚落卫星影像图来源于美国地质调查局(USGS)图片数据库,目前仅解密了冷战时期(1947—1991年)的卫星照片。2015年汤阴县乡村聚落卫星影像图来源于谷歌地图。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2]许家伟.乡村聚落空间结构的演变与驱动机理[D].郑州:河南大学,2013.
[3]赵民,游猎,陈晨.论农村人居空间的“精明收缩”导向和规划策略[J].城市规划,2015,39(7):9-18.
[4]赵晨.超越线性转型的乡村复兴——高淳武家嘴村和大山村的比较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4.
[5]岳俞余.基于韧性理念的汤阴县乡村聚落发展研究[D].上海:同济大学,2018.
[6] Mcintosh A, Stayner R, Carrington K, et al. Resilience in rural communities literature review[R].New England:Centre for Applied Research Insocial Science, 2008:3-6.
[7]邵亦文,徐江.城市韧性:基于国际文献综述的概念解析[J].国际城市规划,2015,30(2):48-54.
[8]沃克,索尔克.弹性思维:不断变化的世界中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9] Meerow S, Newell J P, Stults M. Defining urban resilience: A review[J]. Landscape & Urban Planning,2015(11):38-49.
[10]石翠萍.乡村社会—生态系统体制转换影响因素及稳健性[D].西安:西北大学,2015.
[11] Schouten M A H, Van d H M M, Heijman W J M. Resilience of social-ecological systems in European rural areas: theory and prospects [C]//Seminar, December, Belgrade, Serbia. European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s, 2009.
[12] Heijman.W, Hagelaar.G, Heide.M.V.D. Rural resilience as a new development concept[C]//Novi Sad, Serbia, EAAE seminar Sebian Association of Agricultural Economistys,2007:383-3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