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情的历史, 有情的文学
——关于《抒情传统与现当代文》
2019-03-15
王德威在他的著作《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序论《“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开篇中写道:1961年夏天,沈从文写下《抽象的抒情》。然后,他自然地引出了一个事实:就在沈从文默默思考“抽象的抒情”的同时,海外的汉学界已经兴起了一股抒情论述的风潮。英语世界里对抒情问题的探讨,首推陈世骧教授的系列文字,而后同在美国的高友工教授做了进一步的扩展,另外还有捷克学者普实克等人的论述和研究。在王德威看来:“沈从文、陈世骧外加唐君毅、徐复观、胡兰成、高友工等人的抒情论述其实应该视为20世纪中期中国文学史的一场重要事件。”而王德威又在他的这本著作里,专章和重点论述了《沈从文的三次启悟》,读来让人感动。王德威试图对“抽象的抒情”如何在沈从文身上逐渐衍化,并最终形成,以及它所折射出何种层面的“‘抒情’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又一面向”,做一个动情的探究。而我感兴趣的是沈从文如何从早期那种纯艺术追求的——文学写作是“情绪的体操”,从潜心探究艺术美,渐渐转化为一种“抽象的抒情”。我试图从叙事与文体层面,走进沈从文的短篇小说,走进他的《边城》《长河》,尤其是希望能够更加懂得他的《边城》——表现出“向生命的神性凝目”的抒情性的《边城》。
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也阐发了“史传”与“诗骚”传统对于“新小说”、“五四”以后的小说的影响。诗骚和抒情传统的影响,是巨大的。“五四”作家往往把散文当小说读。“五四”时代的小说杂志上常见标为小说的散文,“五四”作家的小说集更常常夹杂道道地地的散文。“五四”作家把散文混同于小说,主要来自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影响,但不能否认也有他们对于西方小说“诗趣”的自觉追求,和西方文学的影响。当然,小说和散文难以明确区分、面目接近,或者说小说散文化的情况,在郁达夫、沈从文、萧红、汪曾祺、迟子建等很多作家身上,都或多或少、或轻或重地存在着。而且每个人,都以他或她自己的个性气质和创作理念,与抒情传统分别做出不同维度和层面的对接。而其中有些作家,又几乎毫无疑问地存在着彼此师承的关系或是影响关系。废名与沈从文,沈从文与汪曾祺,都有师承关系。萧红和迟子建,都是东北边地著名的女作家,都以不失诗心和童心的笔触,对东北边地以及人生做着文学书写。中国现代抒情小说的流脉,或显或隐,一直奔涌在地表附近,一有机会,这清冽的地泉就会汩汩地流出来。不同的作家,不同的“缘情”的书写,让中国文学在20世纪以来“有情的历史”当中,留下和呈现“有情的文学”。
郁达夫小说的抒情性特征,就表现在他那“沉沦”却又不甘沉沦的孤独者的写作中。郁达夫把“凄切的孤单”,作为“我们人类从生到死味觉到的唯一的一道实味”。郁达夫小说的抒情性,受来自西方“抒情”一义的影响较多,而他所受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教育和熏陶,也同样不可忽视。郁达夫小说的叙事结构重视情绪与感觉,而不是以情节或其它来作为小说叙事结构的重心。他的作品常以主人公情感的起伏来结构成篇,形成一种饱蘸了许多感情的自然流动的抒情结构,像《茑萝行》等小说,就是典型的以人物思绪流动为线索结构而成的篇章。
沈从文,是我深为喜爱的一位作家。沈从文小说诗化、散文化,他的每一篇脍炙人口的小说,都可以当散文来读,他的小说抒情性和散文化倾向明显。沈从文擅长画境、意境和情境的营造,很多小说的书写,都达到了一种“无我之境”的生成,但背后,又有一个“有情之我”。沈从文自己有苗族血缘,和湘西特殊的人文环境——这里本就是屈原《楚辞》取材和诞生的地方。从陈世骧对于抒情传统的论述、陈平原对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的论述中,我们知道《楚辞》在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中是一个重要的源头。今处古时的源头,必然在好多事上“可以由今会古”。沈从文毫不讳言他与楚辞的地域渊源,他的写作与水的关系,他如何视写作为“情绪的体操”,并做了不少非常形象生动的文论和阐说。我们想看他是如何在“事功”和“有情”的思考中,一步一步走向“抽象的抒情”……
萧红《呼兰河传》是她最后的杰作,也是她文学和艺术上的巅峰之作。茅盾说“它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呼兰河传》散文化特征明显,故事性不强,几成共识。葛浩文虽也认为“这书严格来说,不能算是典型的小说,它大部分牵涉个人私事”,却又偏偏说它“叙述性强,但书中却有着像诗样美的辞章,以及扣人心弦的情节”。就是这样吊诡,《呼兰河传》是如何在“不能算是典型的小说”——故事性不强和散文化之外,又能兼具“叙述性强”和“扣人心弦的情节”的呢?只有求助于叙事学和文体学研究的方式方法——从隐含作者、叙事结构、情节性以及限制叙事的可能性,从童心与诗心的意向结构与非成人视角的叙事策略角度,以及如入化境的限制叙事——“我的人物比我高”的层面,方可发现《呼兰河传》的文学性以及其何以成为一部不朽小说的原因所在。而能够发现萧红的《呼兰河传》是“限知视角和限制叙事的小说范本”,其实是我用了近二十年时间的思考,和对于文学对于生活的感悟,才能够擦出的一点火花。
汪曾祺是当代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汪曾祺专擅短篇小说,其小说在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的中国小说创作中具有的重大意义,殆无疑义。他在《短篇小说的本质》当中,有段被广为征引的名言:“我们宁可一个短篇小说像诗,像散文,像戏,什么也不像也行,可是不愿意它太像个小说,那只有注定它的死灭。”我把它看作汪曾祺对于小说,尤其是短篇小说的一个文学宣言。汪曾祺无数次满怀感情地说:“我是沈从文先生的学生。”我几乎可以想象得出汪曾祺这样说时,他的感怀,他的铭记,他的缅想……汪曾祺还说:“一个短篇小说,是一种思索方式,一种情感形态,是人类智慧的一种模样。”桐城派和归有光的“文气”概念,对汪曾祺影响很深。汪曾祺在自己的文章中,曾多次细述他对归有光的喜爱,及他与归有光某些方面的文学旨趣的相投。汪曾祺自言:“有人问我受哪些作家影响比较深,我想了想:古人里是归有光,中国现代作家是鲁迅、沈从文、废名,外国作家是契诃夫和阿左林。”由汪曾祺这段话,其实串起了中国现代抒情小说史的一条线索,也显示了中国现当代抒情小说在汪曾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古今中外的艺术渊源。其实,研究汪曾祺就会发现,果如有研究者所说,中国文学史一条中断已久的“史的线索”的接续——这便是从鲁迅的《故乡》《社戏》、废名的《竹林的故事》、沈从文的《边城》、萧红的《呼兰河传》、师陀的《果园城记》等作品延续下来的现代抒情小说的线索。可以说,《受戒》和《异秉》的发表,犹如地泉涌出,使鲁迅开辟的现代小说的多种源流(写实、讽刺、抒情)之一脉,得以赓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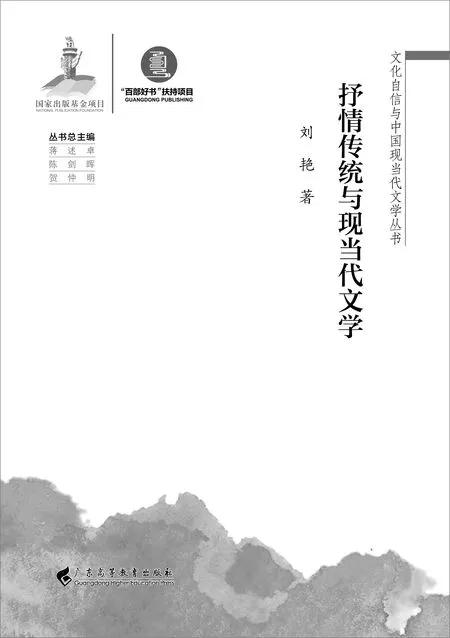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抒情传统的赓续和扩展,女作家迟子建是绕不开的。中国现当代作家小说中的散文化、抒情性因素或者倾向,在迟子建之前的作家那里,就广泛存在着。从现代白话小说伊始的鲁迅、郁达夫,到废名、沈从文、萧红等人,还有在20世纪70年代末“复出”的汪曾祺等。对百年汉语新文学,小说的散文化、抒情性,几乎可以作一连续性和谱系性的整体研究。而宗教情怀、神性因素,虽已为很多迟子建研究者所注意到,但鲜有人能够从神性书写的角度,对迟子建小说的散文化倾向作出细致梳理分析。与萧红相类,迟子建具备诗心、童心、赤子之心和“我向思维”,有着童心与诗心的文学书写方式。但与为寂寞和悒悒心境所纠缠的萧红不同的是,迟子建对于大自然、家乡物事——东北边地的文学书写,常常为一种神性灵光的东西所沐浴,沐浴着神性的自然风景,饱蕴诗性以及由诗性所衍生的抒情性;沐浴着神性的生活和人事,氤氲出人性的诗性和抒情性——这些都令诗意化、散文化成为了迟子建小说的一个典型特征。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流脉里,还有很多作家,未能述及或者细述,比如废名、师陀等等。而有研究者已经提出,“抒情的”而非“史诗的”,可以指证为是“70后”一代作家的写作特征。而限于篇幅,我还不能将这些“70后”作家引入,或者展开论述——希望这是将来可以完成的一份工作。为弥补这一大遗憾,特意在附录里,列入了谢有顺教授《“70后”写作与抒情传统的再造》一文,而他本人也欣然同意。在此谨致谢意。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里,同时也在做着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研究和写作,二者是可以兼容并互为启发的。在此,也谨以此书,作为我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世纪海外华文作家的中国叙事研究(项目批准号:17BZW171)”的一个阶段性成果奉献出来,就教于大家。同时,对一直以来,默默关心、支持和鼓励我的师友们,致以最真诚的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