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文化的思考者任继愈传(之四)
2018-04-20郭梅
郭 梅
杭州师范大学文创学院

《佛教大辞典》
由任继愈主编,众多专家学者历时13年联合撰著的《佛教大辞典》在2003年出版时引起了较大反响。
任继愈在20世纪60年代撰写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曾经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高度赞扬,并受到国内外相关学者的推崇。日本著名的老一辈佛教学家本善隆于中日建交前曾专程来华拜访任继愈,所持的欲请任继愈签名留念的《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由于多年翻阅,竟已严重磨损,可见任继愈在当时国际佛学界的影响之巨。任继愈在20世纪80年代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一、二、三卷也赢得了学术界的广泛赞誉。

任继愈主编《佛教大辞典》
《佛教大辞典》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编纂的第一部大型佛教学工具书,是佛教学工具书领域里一座新的里程碑。从任继愈几十年来所主持的《中华大藏经》《道藏提要》《中华大典》等的编撰中,我们体会到:包括《佛教大辞典》在内的这一系列文化工程,都是其“中国文化必将再度辉煌”这一文化信念的结晶和体现。
《佛教大辞典》的编撰可谓缘起已久。佛教典籍浩如烟海,佛教语、名相、义理艰涩难懂,所以一直有很多学者致力于佛家名相、义理通俗化的尝试。1921年,丁福保曾编纂《佛学大辞典》,这是我国佛教学工具书领域的开创性之作,其后还有各种佛教辞典陆续问世。1976年,任继愈在潜心研读艰涩难懂的佛教经典《大智度论》的过程中萌生了编写佛教学工具书的想法。1988年,他主编的《宗教词典》问世,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接下来,他便开始着手主持和组织《佛教大辞典》的编撰工作。由于在编写过程中编写人员、经费不稳定,所以断断续续,一直历时13年才最终完成了这部总字数达300万字的大型佛教学工具书。这是任继愈佛教研究中的集大成之成果。
任继愈认为,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可以说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当然也是一种文化形态的存在。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两千多年以来,在中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形成历史悠久、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传统,成为以儒、释、道三教合一为特点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三大支柱之一。在我们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如果忽略中国佛教文化传统,那“将是不可想象的”,中国佛教文化传统、思想资源可以成为,而且也应该成为“构建我国新文化的珍贵思想资料”。文化建设,尤其是人文学科的建设、国民人文素养的陶冶,又大不同于经济建设,不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但任继愈认为,可以预言的是,一旦我们达成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届时必会迎来新文化建设的高潮,所以他一直在为这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孜孜不倦地做着最基本却是最重要的基础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佛教大辞典》就是为未来的新文化建设高潮做准备的一项大工程。任继愈还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借鉴和继承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尤其是对外来文化的消化、吸收。中国佛教从印度传进来的蔚为大观的文化传统恰好提供了中国古人如何创造性地“洋为中用”的范例,直到现在还可以从中得到很好的启发。总结以前的历史经验总会对我们今天的文化事业大有裨益,而在这个意义上,《佛教大辞典》也可以看成是关于佛教文化的一部权威性的基本工具书。
任继愈说,《佛教大辞典》“是站在佛教学研究者的立场而非信仰者的立场,摒弃主观成见,避免狭隘偏见,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事实,客观公正地介绍佛教知识,提供可信赖的解说”。这是一个严谨的学者的学术思路。研究佛教的人常感佛教名相、术语艰涩难懂,相当枯燥乏味,《佛教大辞典》则可以帮助专业和非专业的读者顺畅地了解佛教知识的方方面面。敦煌文书、西夏佛教文献等晚近的考古发现,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以及欧美佛教的最新研究成果,在《佛教大辞典》中都得到了相应的反映。
筹建世界宗教研究所
1963年冬,周恩来总理访问非洲十四国回来后,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加强对国际问题的研究,提出成立十三个研究所。1963年12月31日,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上批示说:“这个报告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而在此之前的1959年10月13日,毛泽东曾把在北大哲学系任教的任继愈找去,见面第一句话就是,你的书我都看过。接着说,我们过去都是搞无神论,没有顾得上宗教这个问题,宗教问题很重要,要开展研究。毛泽东问,北大有没有人研究宗教?任继愈说除他搞佛教研究外,还没有其他人从事这一方面的研究。毛泽东又问,道教、福音书有没有人研究。任继愈如实回答说都没有人专门研究。毛泽东还问,你们哲学系有多少人?任继愈说师生加起来有500人。毛泽东听了,说500人一个系怎么能没有人研究宗教呢?一定要抽出个把人来研究这个问题,不能忽略,包括基督教、佛教、道教,慢慢地来,先做着。
1964年,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任继愈参与筹建了中国第一个宗教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并一直担任该所所长达二十余年。对于自己在宗教研究方面所做出的成绩,任继愈认为那是因为大环境和机遇,他个人的作用微乎其微。
主编《中国佛教史》
成立初期,世界宗教研究所主要的任务就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的理论,同时编写反映世界各国宗教现状的《世界宗教动态》。但是好景不长,不久全所成员与北京大学的师生一起上山下乡参加“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接着便是长达十年的“文革”。1976年“文革”结束后,世界宗教研究所逐渐恢复科研业务。所长任继愈决定着手主编筹划已久的《中国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世界宗教研究所教授杨曾文回忆说,《中国佛教史》开始筹划编著之初,任继愈不止一次地与他谈到此事,约他参加,并希望他在此书正式编写之前,先读原始佛教基本经典之一的《中阿含经》,然后阅读《资治通鉴》及其他史书。杨曾文按照任继愈的建议做了,通读了几部汉译《中阿含经》,分门别类地编写了有关原始佛教、部派佛教的资料汇编以及佛教传入中国的资料汇编,其间还阅读了大量中日两国的佛教研究著作。这为杨曾文以后参加《中国佛教史》的编写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那时任继愈还约请了当时在内蒙古大学任教的杜继文同志来北京一起研究过一次。很快,总体计划出来了:全书8卷,从佛教传入中国一直写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第1卷:东汉至三国佛教;第2卷:两晋及十六国佛教;第3卷:南北朝佛教;第4、5两卷:隋唐佛教;第6卷:宋元佛教;第7卷:明清佛教;第8卷:近现代佛教。这8卷是一个浩浩荡荡的大工程。
从1978年开始,《中国佛教史》正式进入撰写阶段,编写组开始只有任继愈、杜继文和杨曾文三人。杜继文于1983年从内蒙古大学调到世界宗教研究所。《中国佛教史》的第1卷完成后,经申请和评定,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
1977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成立之后,各地陆续成立省市级社会科学院或研究所,其中一些单位也设立宗教研究机构,不少高等院校也相继设立宗教系或开设宗教课。《中国佛教史》前3卷出版之后,在国内外获得好评,不仅成为各地宗教研究机构的重要参考书,而且也成为高等院校的重要教材。东邻日本近百年来在对中国佛教的研究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对《中国佛教史》也给予了高度评价。1982年,日本著名学者镰田茂雄教授给任继愈寄来在某报纸“文化往来”专栏发表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两种中国佛教史》,对中日几乎同时出版的镰田茂雄、任继愈分别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1卷及两书的编撰计划进行介绍,指出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贯彻“将中国佛教史置于思想、社会的发展中进行考察的社会科学的观点,将是新中国佛教史的决定版”。在《中国佛教史》前3卷出版之后,从1992年到1994年,由丘山新、小川隆、河野训、中条道昭等多位日本年轻学者将之翻译成日文,以《定本·中国佛教史》的书名由东京柏书房出版。应当说,这是当代中日佛教文化交流史上的一大盛事。
《中国佛教史》提出的基本观点和指导思想是:
1.以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总的指导思想,将佛教置于中国历代社会环境中进行考察和评述;
2.佛经翻译、佛教理论的传播和发展,受到历代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习俗的影响和制约;
3.源自印度的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发展进程中,经与中国儒、道等传统文化思想汇通、融合而不断充实丰富自己,逐渐实现民族化;
4.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思想支柱是“儒家及后来转化成的儒教”,佛教对中国纲常名教起着“夹辅作用”,处于以儒家为正统的“传统文化的附属地位”;
5.佛教是中国传统思想的组成部分,对中国哲学、思想和文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等文化形态产生过巨大影响;
6.编写过程中要充分依据中国自古以来丰富的文史资料和佛教文献、考古资料,并应积极参考和吸收国内外的优秀研究成果。
这六条观点和指导思想有着相当的严谨性和科学性,对于佛教文化思想的研究工作是一个极大的推进,而且对于其他宗教的研究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981年的一天,杨曾文到任继愈家里请教《中国佛教史》的撰写问题,任继愈问他有无出国考察的想法,并建议他到日本研修一个时期,借机考察一下日本学者对中国佛教史的研究情况。杨曾文回忆说:“后来经任先生联系并得到院外事局的关照,我得到日本学术振兴会的资助,在1982年1月至4月到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考察和研修三个月,收获很大,既开阔了眼界,收集了不少国内难以见到的资料,也结交了不少朋友。在回国经过东京时,还拜会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的镰田茂雄教授。他正在编撰8卷本的《中国佛教史》,听说我参加任继愈主编《中国佛教史》的撰写工作,此书也有8卷,并且结构内容与他编撰的《中国佛教史》十分相似之后,十分高兴,连续两次约我见面交谈并请我吃饭。正是这段因缘,使我与镰田成为忘年之交。后来经镰田联系和积极策划,在以本间昭之助先生为社长的中外日报社的大力支持下,并得到中国社科院和宗教所历届领导的支持,在长达18年中,每两年一次在两国共举办了10次‘中日佛教学术会议’,将两国佛教学术交流推到一个新的更高的起点。”
任继愈驾鹤西行之后,杨曾文在悼文中深情地说:
从我1964年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分配到世界宗教研究所,已度过45年,经历过了研究所筹备、“文革”下放干校、国家改革开放、研究所恢复研究业务、参加任先生主编《中国佛教史》写作……经常与任先生接触,得到亲切教诲,回想起来感念甚多。自任先生任职国家图书馆后,虽不在一起,然而每年参加学术活动和年节聚会之际,总有见面的机会,有时还能坐下来叙谈叙谈。今年正月十五日我拜访过任先生,看到他刚动过手术身体瘦弱和动作迟缓的样子,怕他劳累没敢多谈,说了一会话便赶紧告退。然而想不到这竟成了永别!6月底得悉任先生病重住院时,医院已经不许探视,只好打电话托任先生女儿任远教授代为问候。
回想自己在学术上的进步,与任先生的热情指导和提携是分不开的。1976年“文革”结束,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各研究所逐渐走上正规,开展科研工作。从1978年开始,任继愈教授着手主编《中国佛教史》,让我和杜继文一起参加编写。1982年第一卷完成后,经申报被列为中国社会科学基金“七五”规划重点项目,至上世纪90年代,前后写完四卷,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从两汉至南北朝佛教的前三卷,第四卷写隋唐前期佛教,有待出版。
编书的过程也就是我学习和研究的过程,提高了自己搜集、梳理和分析综合资料的能力、独立研究的能力。我以后能顺利完成社科基金项目《日本佛教史》《唐五代禅宗史》《宋元禅宗史》等书的撰写任务,可以说皆得益于参加编写《中国佛教史》过程所打下的坚实的学术基础。
宗教观如是说
任继愈的宗教研究从马克思主义的视角出发,以实事求是、精益求精的态度与治学精神进行,并且联系许多其他学科,比如古人类学的大量相关知识与资料——任继愈经常提到,山顶洞人生活的地区也就是北京猿人活动的地区,里面摆的殉葬物品中既有生活用品,还有一些生产用具,如钓鱼的钩子和缝衣服的针。这说明他们相信人死后有个世界,这个世界和现实世界差不多。又比如西安的半坡村遗址,是原始社会的村落,村落中出土了陶制的瓦棺,其中有一种花盆样的东西,是装死了的小孩尸体的。盆底下有一个小洞是留给死者灵魂出入的——古时候小孩的死亡率很高,小孩子离不开母亲,死后就埋在住地附近,方便他的灵魂回家找母亲。宗教起源于相信人有灵魂,正因为人类相信灵魂,所以才有了祭祀、上供等宗教活动。这是从历史客观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对宗教的认识,由此也形成了任继愈的宗教观。
又如,任继愈认为宗教本身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我们现在是文明社会,对于刮风下雨、有没有雷神一类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凡是念过中学的人都会懂得这些自然现象的科学道理。可社会上还是有很多现象解释不了,怎么办?于是宗教就站出来解释这些现象。相信“来世”的人,认为今生所没有得到的,来世可以得到加倍的补偿,所以现实世界的不合理,大可以不必计较。历史上的佛教、道教,包括基督教,培养了人们一种驯服的性格,历代帝王或当政者提倡宗教,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换言之,历代的统治者总是尽力提倡一些在他们看来适合自己统治用的宗教。像儒教也一样,儒教也讲忍的一面,比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小不忍则乱大谋”等,显然,忍让、驯顺是世界几大宗教的一致精神。
任继愈曾说:“在古代的时候,阶级社会以前的神,不具备后来赏善罚恶的性质。古代的神,如盘古、伏羲、神农都是为人类造福的,是民族英雄,为人民做好事的,所以大家怀念他,把他尊奉为神,这都反映了原始社会平等、自然的社会关系。但到出现阶级以后,出现了国家,有了法律,出现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有了监狱,神也具备了赏善、罚恶的性质,它实际上是现实社会的虚幻歪曲的反映。一个历史现象的产生不是一下子就有的,历史唯物论就告诉我们,一个东西在历史中产生也要在历史中灭亡。这一点我们和虔诚的宗教家不一样。他们认为在人类以前就有上帝,是上帝创造了人类,上帝是永恒的,没有了人类也还有上帝,地球不存在了也还有上帝。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宗教是一种社会现象、历史现象、文化现象,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才产生这个东西,再发展到一定程度,宗教也会消失。这是很长很长的过程,但现在是不会消失的,要承认它,尊重它。但是过去受极左思想的影响,认为既然把宗教看作是虚幻的不实在的,就消灭它,取消它算了,所以‘文革’时期干了一些砸庙宇、教堂、毁坏神像的蠢事。”
事实也正如任继愈所说,以这样的态度和手段对待宗教的结果,恰恰是适得其反,宗教是社会意识在人们头脑中的曲折反映,用行政干预的办法强力制止是没有效果的,在这个过程中反而破坏了很多珍贵的历史文物,造成了很多无法挽回的损失和遗憾。而且从宗教管理上来看,更是伤害了一些宗教信徒的感情,譬如在“文革”中有些造反派强迫教徒们干他们教规不允许的事,这是很不应该的,也是违背我国宪法的。
同时,任继愈还提到,宪法规定在保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同时,也保护不信仰宗教的自由。比如说,在单一宗教信仰的地区,居民都过着同一种宗教的生活,有一个人出外多年,他改变了原来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再回到自己家乡,有时就会受到歧视。可见,不信教也要有自由,才能充分保证宗教的信仰自由。任继愈对不信宗教也要有自由的解释很简洁但却很详实,使我们对此条宗教宪法有了更好的理解。这是任继愈从宗教和政治的关系中去看待宗教的观点。
道教研究
一直以来,学术界对儒教典籍研究得较多,对佛教典籍研究得较少,而对道教典籍的研究就更是微乎其微了。但是儒释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大支柱,按常理说都应该得到广泛的研究和整理才对。似乎有一个正统观点认为,只有儒家的经史子集才有资格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佛教和道教典籍则只是属于旁支而已。这应该是长期流行在中国社会的一个偏见。实际上对儒释道的研究决不能分开,因为这三者之间的联系极其密切,它们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一直是水乳交融式地一起发展的,总是互相吸收又互相争斗。
任继愈指出,道教生长在中国本土,大概与佛教同时活跃在中国古代的社会大舞台上。但是,当时道教的命运不济,让佛教给抢先了一步,失去了大好的发展机会。汉末魏晋天下大乱时期,老百姓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往往容易投靠宗教。当时黄巾起义打出的旗号是道教的,但是后来黄巾起义失败了,道教也由此受到牵连,统治者很长时间对道教不敢再予以信任。于是道教为了取得上层统治阶层的信赖和支持,便尽力想方设法去满足这些上层阶级的需要,特别是那些地主阶级,他们生活优裕,都希望能长生不老,永远享受富贵。道教为了迎合他们的需要而向他们推销养生、炼丹、房中术等内容。于是,在南北朝隋唐时期,道教的外丹教法盛行不衰。但是这也带来很多不好的问题。任继愈说,道教把道观大多建立在深山里,修身养性,但是生病了根本没办法看医生。所以很多道教大师同时又通晓医道,懂得养生、健身,以追求长寿。当然,追求长寿无可厚非,可如果由此推衍下去,要求活一百岁、二百岁、三百岁,甚至永远不死,就走到荒谬的道路上去了。任继愈常说:“道教把一些合理的、不合理的东西搅和在一起。”
20世纪80年代,任继愈在世界宗教研究所开创了对道教的正式研究。他说:“当时建立学科,宗教所招博士生、硕士生。后来重点主要转到四川去了。四川大学专门搞了一个道教研究所。”1978年,世界宗教研究所制定了《道藏提要》规划。但是《道藏》内容繁多、芜杂,其中许多典籍撰者不明,时代不详,书上表明的撰者亦真假难辨。当时研究人员很少,人力资源很缺乏,要仿照《四库全书》的体例编制《道藏》面临很大的困难。但这部道教典籍丛书是研究道教的主要资料库,对将来道教研究工作的开展有很大的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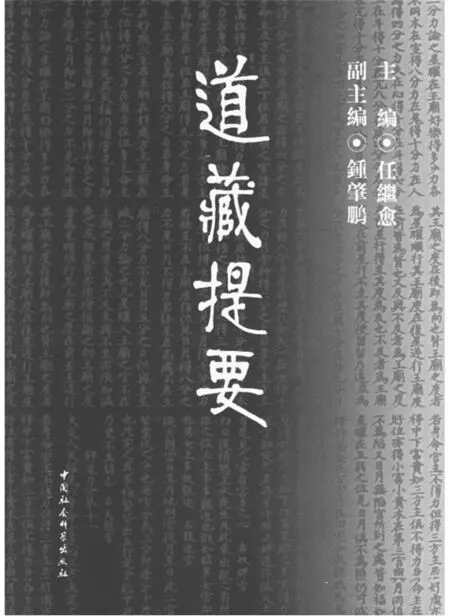
任继愈主编《道藏提要》
《道藏》中保存的思想资料库在中国思想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中国各个时代的重要哲学内容在这里都有反映。这些保存下来的珍贵资料很大程度上丰富了中国哲学史的内容。比如魏晋以后,哲学界探讨的中心问题是本体论,并以本体论取代两汉的宇宙构成论,从中可以看出中华民族理论思维能力的深入和提高。后来从本体论转到心性论,又是另一个提高。
任继愈认为道教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时期:“南北朝时,道教得到帝王贵族的支持,跻身于社会上层,这是它发展的第一个时期。唐朝皇族与老子攀亲,自称李耳后裔,大力推行道教,这是第二个发展时期。北宋真宗、徽宗先后崇奉道教,用道教麻痹人民,陶醉自己,借以遮盖北方强邻压境造成的耻辱,这是道教发展的第三个时期。明中叶帝王迷信道教,妄图长生,道士受到宠遇,出入宫禁,干预朝政,以致参加政府上层的权力斗争,这是道教发展的第四个时期。”可以说,任继愈对道教发展历史的清晰概括使得他对道教的研究思路更加明晰了。
笔耕不辍
任继愈在任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长期间,曾提出过“准备资料、培养人才”的八字方针。他看到当时的中青年学者的国学基础不够坚实,认为如果不把资料给他们整理好,将来的研究会很成问题。于是,在他的主持下,在十几年的时间里,编纂、出版了一亿余字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也已开始编纂。同时他还主编规模达150卷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并担任规模达7至8亿字的《中华大典》的总主编。为了编纂这些资料性书籍,任继愈中断了许多自己个人的研究计划。在《中华大典》的编纂中,他还亲自兼任《哲学典》和《宗教典》的主编。对此,任继愈说得很朴实:“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古的东西我熟悉,多做一些资料积累,后人用起来方便。”毫无疑问,这些伟大的文化工程给后人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正如在任继愈去世之后,时年80岁的北京大学教授、任继愈的弟子白化文所言:“我认为从某种程度来讲,任老是牺牲了他个人的学术,而把全部的时间、精力和才能用在了主持国家级国学研究项目上。当然,这些浸透了任老辛勤付出的典籍也终将流传千古,这对于任老来说是值得的。”
在回忆当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气魄敢于设想编纂一部多达107卷的《中华大藏经》时,任继愈曾说:“中国文化有三个支撑点,即三个系统:儒教、道教和佛教。儒教的影响面很广,佛教次一点,道教就更少一些。但它们都对人们的生活,甚至是家庭有着很深的影响。佛教虽然占的分量不很大,但它却是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少这部分,我们的新文化建设就少了一条腿。多年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没有一部完整的、有权威性的佛教全集,迄今世界上还以日本《大正大藏经》为权威版本,我国学者每当在使用《大正大藏经》时,心中总有说不出的沉重。因此,为了维护民族的荣誉,更好地利用我们的文化遗产,有必要编纂一部完善的汉文大藏经。当时我主持编纂《中华大藏经》这部书,并不是想马上就能用,我认为将来建设新文化离不了它,趁着我现在还能做,也有这个条件做,就想把它做出来。《中华大藏经》成书后我们也没有特别地做宣传,能对读者有帮助这是最重要的。做学问也要有这种态度才好,不要怕坐冷板凳。”

工作中的任继愈
总之,任继愈在宗教学研究方面成就卓著,组建了世界宗教研究所,陆续创设了佛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科学无神论、儒教等研究室,并创办了《宗教学研究》杂志。宗教所为我国宗教学研究界贡献了一系列基础性学术成果,为各地宗教研究机构培养了大量的学术骨干。任继愈亲自主编了多卷本的《中国佛教史》和两卷本的《中国道教史》,还有《宗教词典》《道藏提要》《宗教大词典》《佛教大词典》,还有包括《佛教史》《伊斯兰教史》《基督教史》等在内的宗教史丛书,并且培养了几十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为中国宗教研究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佛教传入中国已经有两千年的历史,不过我国佛教研究的步伐相当缓慢,在任继愈步入中国哲学研究领域的时代,佛教研究和中国哲学研究基本上是两个不相干的领域。然而他认为,佛教本身早已经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整理中国传统文化,应该包括对佛教思想的整理与探究。在1955年至1962年间,他陆续发表《汉唐时期佛教哲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等论文,汇总为《汉唐佛教思想论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论集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分析中国佛教思想,其视界的广阔、分析的深入,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不仅开创了中国佛教研究的新方向,也开辟了中国一般宗教学研究的新方向,而任继愈也因此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奠基者。
笔耕不辍的任继愈先生虽然成绩卓著不凡,但他却始终不卑不亢,平静淡然,用客观的眼光看待这些业已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当初编《中国哲学史》、《中华大藏经》时,是领导把任务交给了我,如果交给别人也能编出来,最多也就是细枝末节的不同。因此首先是因为那时国家有财力了,才有可能把这件事做成,如果是放在多少年前就根本不可能做成,旧社会就更搞不成了,这是大气候决定的。又如唐玄奘翻译佛经,大机遇是国家支持,要人有人、要钱有钱,人力、财力、物力都由国家支持,唐玄奘只管一心一意翻译就行了,他就很顺利,那一千多卷很自然地就出来了。总之个人能够做出点成绩,主要是大环境、大气候、大趋势决定了事物的成败,个人的作用微乎其微,根本的还是大环境所提供的机会。当然,机遇总是给有准备之人的,个人努力也是必须的。”
更让人惊讶的是,在任继愈先生已经八十高龄的时候,他居然说最重要的东西还没有写出来:“我手头还有几本书没有写完。等写完后,我想把这个重要的东西写出来。”这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任继愈先生坦言:“从认识论上讲,我觉得今后要提出群体的认识论这个问题。就是主客观、认识这个东西,要群体才起作用,它才有效,仅仅是我个人认识某个东西,孤明先发,不解决问题。因为好多的个人悲剧就在这个地方。把个人的东西、个人的认识强加给群体,这不行。这得有个过程,它到了一定时候,群体承认了接受了,那就大不一样。不到这个时候,操之过急,对的也行不通,还要碰壁。历史就是这样。”
任继愈先生的女儿任远教授曾说过:“父亲作为一个终生致力于哲学研究的学者,他一直有个愿望,就是重新写作中国哲学史,把自己后半生的许多重要新观点都放到书里,但为了编纂的《中华大藏经》和《中华大典》,至今也没有时间去写,成为了永远的遗憾。”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