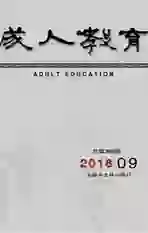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历程、问题与展望
2018-01-11徐宝良
【摘要】不同的国家对社区教育内涵的界定不同,我国社区教育有其自身的内涵特征。我国社区教育在发展过程中,本土化特色逐渐形成。但在现实中,社区教育发展还存在着诸多的问题。因此,在未来社区教育发展中,需要从内涵认知、发展理念、法律建设、师资队伍、资源利用共享等方面加以改善与推进。
【关键词】社区教育;发展历程;内涵界定
【中图分类号】G7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794(2018)09005505
【收稿日期】20180105
【基金项目】广东省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学前教育项目,项目编号为0003015095
【作者简介】徐宝良(1970—),男,浙江诸暨人,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教师教育、学前教育。2016年6月,教育部、民政部、科技部、文化部、团中央等9个部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实施意见》,在该文件中明确提出到2020年在我国建成完善的社区教育治理体系。社区教育在我国经历了30余年的发展历程,对于推进社区发展及公民素质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社区教育作为一种服务于社区民众的教育形式,其理论及实践也在不断拓展与更新,不同的历史时期社区教育的内容、功能有所不同,这也是影响社区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梳理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历程,指明其在当前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我们把握社区教育发展的正确方向。
一、我国社区教育的兴起及其内涵的界定1我国社区教育的兴起
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从时间上看,起步并不算晚,但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之前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处于空白状态。从历史上追溯,我国社区教育的前身是发端于清末民初的社会教育。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期,费孝通将英文中的“community”翻译成“社区”并引入中国,社会教育的发展才开始逐步依托于社区而进行。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教育部的社会教育管理机构——社会教育司依然保留,此时社区教育在部分领域、部分地区零散开展。1953年,教育部的社会教育司被撤销,改成工农教育司,社会教育在中国大地就此消失。1986年,上海市真如中学率先与附近的工厂联合成立了“社会教育发展委员会”,成为我国社区教育实践兴起的主要标志,由此正式标志着我国社区教育的开始。在真如中学成功探索的基础上,1988年,上海市闸北区部分街道开始成立社区教育发展促进委员会。1989年,这种旨在促进社区教育发展的自治组织开始在整个闸北区普及,推动了社区教育实践在闸北区的发展。[2]同年,闸北区教委也成立了社区教育管理科,社区教育正式进入了政府部门的关注视野,社区教育在上海地区呈现出燎原发展之势。进入1990年代,社区教育开始由上海地区波及全國。
2社区教育的内涵
社区教育作为一种教育形式,在不同的国家经历过不同的发展阶段与历程,其呈现的内核与特征也各不相同。从对其概念界定来看,也会呈现出不同的认知。国外对社区教育内涵的界定,整体上有三种主要观点:第一,将社区教育视为是一种民众启蒙教育。如丹麦的社区教育创始人柯隆威就认为,社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改善社区民众生活,是用人文精神与态度来启蒙民众,弥补民众受教育少的基本缺陷。由此,社区教育就是一种启蒙教育,而不是技能教育。[3]第二,将社区教育视为是一种社会教育。日本的学者及日本政府均认为,社区教育就是社会教育。日本在1950年颁布的《社会教育法》中就明确指出,所谓的社会教育就是面向全体社会成员的一种学校外教育。日本学者认为,教育体系由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共同组成,但两者并不能截然分开。在学校教育中可以加入社会生活、社区发展的相关内容,提升学生对社会、社区的认知;同时,学校作为一个教育机构与载体可以成为社区教育的中心,社会教育应该充分利用各类学校的资源,面向所有社会个体开放,进而提升社会教育的效果。[4]第三,将社区教育视为是一种非正规教育。美国学者就持这一观点,认为社区教育是一种非正规的技术、技能及人文精神培训教育,其立足点是为了社区发展,也是为了社区个体发展。
社区教育实践的不同模式也决定了在不同的国家对社区教育的内涵有不同的理解。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由于观察视角不同,对社区教育内涵的理解也会有差异。在我国,不同的学者对社区教育内涵的理解各不相同。如有学者认为,社区教育是立足于社区,以所有社区成员为教育对象,开展旨在提升所有社区成员素质、技能以及促进社区发展的各类教育活动的统称。[5]还有的学者认为,社区教育仅限于社区学校教育,社区教育也是一种组织化、体系化的教育形式。[6]就社区教育的发展目标而言,不同的学者也有不同的认知。有的认为社区教育应以促进社区全体成员的终身发展为目标,也有的认为社区教育的发展目标应是促进社会发展。[7]对于社区教育的运行方式,学者们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对我国社区教育的运行方式,部分学者赞同通过社区学院、社区文化中心等机构来组织社区教育的实施。[8]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社区教育的载体不仅包括学校,也应该包括科技馆、图书馆、展览馆、博物馆、剧院等公共文化实施。[9]此外,对于社区教育的发展模式,学者们的看法也不同相同。部分学者认为我国当前社区教育的发展存在四种发展模式:一是街道办主导模式;二是中小学主导模式;三是社区学院主导模式,但仅限于大城市;四是社区自治机构主导模式,如居委会。[10]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社区教育发展只能是一种模式,即必须以社区文化建设为基础来实施,其他发展模式会混淆社区教育的特性,与其他教育形式多有重合。[11]
鉴于上述学者的研究,本文认为,所谓的社区教育就是以社区为基础,充分利用社区内外一切教育资源,开展旨在提高社区全体成员的文化、精神素质及生活质量,促进社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教育形态。
二、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基本历程
11980年代中期到1990年代初:社区支援学校教育阶段
这一时期的社区教育尽管也有学校与企业联合办学的个例,但大部分的社区教育均是作为学校教育的第二课堂而存在的。换言之,就是通过社区教育这种校外形式来帮助青少年儿童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与道德品行。可以说,这一时段的社区教育对象主要是社区内的青少年儿童,发展目标也是以辅助学校教育为主。
21990年代初期到2000年:学校教育回报社区时期
这一时期,社区教育发展依托的资源依然是学校。学校的教育资源开始向社区成员开放,为社区教育的发展提供载体、资源、师资等服务。这一时期,上海地区很多街道及乡镇除了充分利用各个中小学的资源、载体优势之外,还兴办了属于社区教育的学校机构。如真如镇成立真如社区学校,普陀区东信街道成立了东信社區教育中心等等。而此时学校中的教师以及一些专业的社区教育工作者也开始走出学校,主动融入到社区,将学校资源拓展到社区,将学校教育对象从中小学生扩展到全体社区民众。
32001年至今:学校与社区双向互动时期
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国家教育改革力度的不断加大,终身教育体系构建成为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主导方向。因此,这一时期的社区教育发展在终身教育体系构建的大背景下,实现了学校教育与社区教育的双向互动,建立了互利共赢的合作机制。学校通过扩展服务社区的方式,开拓学生的课外教育资源。而社区则充分利用各级各类学校的资源与载体,不断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深度与广度,进而促进了学习型社区的建设,构建了面向社区的终身教育模式。这一时期,社区教育发展无论是在目标、方式,还是在载体、资源等方面均实现了全面的深化,其功能不断完善,形式日渐丰富,承担了大量的与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教育活动,如闲暇教育、老年教育、下岗再就业培训、公民素质及生活教育等等。社区教育作为正规教育的一种补充,其地位得到了较大的提升,逐渐成为终身教育体系发展的“立交桥”。
三、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本土特色
我国社区教育的发展历史与发达国家相比较短,但也形成了自己的本土特色。由于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各国的社区教育发展特色因此也各不相同。日本的社区教育是一种社会教育,科技馆、博物馆、公民馆、图书馆等公共文化设施成为其社区教育的主要载体,能够为不同社区个体提供不同形式的学习服务,能够满足不同年龄、不同学历的学习者需求。[12]在美国,社区学院是社区教育的主要载体,社区内的青少年可以参加社区学院的专科课程学习,但毕业后必须履行服务社区的承诺。可见,不同国家社区教育发展的特色不同,有着各自的传统与特征,但各国的社区教育均较好地契合了本国的国情,符合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因此,推进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本土化,成为提升社区教育效果的重要环节。
就社区教育的本土化问题,我国不少学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部分学者认为社区教育发展必须符合四种特性,即社区教育必须要突出其教育性、社区性、群众性、灵活性;另有部分学者认为社区教育发展需要注重社区性、开放性、补偿性等方向。[13]当然,这些观点有一定的实际价值,但笔者以为,我国社区教育发展需要突出的是自下而上性、自发性与自主性特色。自下而上性体现了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基本动力是由民众推动的,是在民众推动过程中自发形成的,社区教育的真正主体是社区民众,而不是其他主体,政府部门、社区组织在这个过程中只能起支持、协助作用,而不能扮演主导者角色。而自发性、自主性则充分体现了社区教育的主体是社区全体成员,因此,其教育活动的内容、形式、方式等应该由社区全体成员来决定,这是终身学习理念背景下民众获得自主学习权的一种保障。但就当前的实践看,我国社区教育的本土化特色尚不能达到这种理想状态。我国社区教育依然是政府主导的教育体系,行政色彩较为浓厚,民主参与性不足,推进我国社区教育的自主性、自发性发展还有较长的路要走。
2016年3月,教育部正式出台了《教育中长期规划——继续教育发展专题(2020—2030年)》。在这一政策文件中,社区教育被正式纳入到继续教育的范畴中,继续教育将成为与学校教育并列的教育体系。换言之,继续教育与学校教育将成为终身教育体系的两大领域。而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社区教育全部属于继续教育的范畴。如此,就较好地实现了社区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的对接,也促进了社区教育与继续教育中的成人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等类型的对接,这对于不同教育类型的横向及纵向联系起到了较好的作用,能够在社区教育与其他教育类型之间构建一个沟通的桥梁。
四、我国社区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对社区教育内涵认知存在偏差
尽管社区教育在我国已有30余年的发展历史,但至今学界对社区教育的概念、内涵特征的界定及办学定位依然存在较大的分歧。在国家政策导向中,社区教育并未取得单独的地位,即便是在《教育中长期规划——继续教育发展专题(2020—2030年)》这一文件中,尽管社区教育取得了独立地位,但对于社区教育教师依然没有统一的称呼,而是泛用“社会工作人员”来替代。如此,对社区教育的教育主体缺乏明确的界定,不仅导致了实践过程中社区教育发展方向的偏离,也导致了社区教育中各个概念之间的内涵、边界不明,给社区教育实践发展带来了困扰。
就社区教育内涵特点来看,我国部分地方政府对其理解有所偏差,过于注重社区教育发展的功能性特征,甚至用功利性的数据指标来审视社区教育的发展成效。社区教育并不同于其他教育类型,很难用具体的功利数据来衡量。政府部门对其理解存在偏差,导致了社区民众对社区教育存在误解。如果社区民众对社区教育发展参与程度不够,社区教育就很难获得自下而上的推动力。
2社区教育资源共享机制尚未建立
社区教育的参与主体极为广泛,教育内容也较为多元,各类教育主体的教育资源均可以被社区教育所利用,需要构建不同教育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机制,才能推动社区教育的发展。但实际上,我国社区教育资源利用的共享性不足,共享机制尚未建立。第一,社区教育资源利用不仅仅是传统的人、财、物力的投入,还包括社会设施、机构中存在的各类教育或是具有教育性质的资源(如图书馆、博物馆、展览馆、影剧院等存在的教育资源),也包括人文景观、自然风光、历史古迹中存在的教育资源。但现实中,我国社区教育资源仅限于学校教育机构的资源,对于文化机构、文化设施、旅游景区、自然资源中的教育资源未能充分挖掘,这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这些主体之间的资源共享,限制了其教育功能的发挥。[14]第二,在教育资源的合作上,仅限于中小学资源,对于高校、科研机构等教育资源开发不足,没有建立合作机制。第三,对于流动性的教育资源未能建立共享机制。尽管社区教育立足于社区,但与其他社区、其他区域的教育资源可以在流动中实现共享。我国幅员辽阔,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发展极不平衡,各个区域、社区的教育资源应该通过信息化、数字化建设,推进其共享,特别是在课程资源、学习资源等方面。建立这种共享资源体系,也是促进公民学习权平等的基本要求,尤其是发达地区要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城市要加大对农村的支持。但当前实践中,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社区教育资源未能实现合理双向流动,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社区教育区域、城乡之间的平衡发展。
3社区教育发展缺少法律支持
当前,发达国家在推进社区教育发展时,无不是立法先行,如日本在1950年就制定了“社会教育法”,韩国也在1977年出台了“平生学习法”,欧美发达国家更是制定了诸多的社区教育发展方面的法律,由此也就确保了社区教育发展能够有法可依,法律为其发展提供制度保障。反观我国,目前依然没有国家层面上的社区教育立法,甚至连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也没有。而地方立法同样欠缺,只有上海市出台了社区教育发展的相关条例。正是因为立法的缺失,导致了我国社区教育在发展中经常处于无章可循的状态。而社区教育发展本身会涉及众多部门,如教育、农业、民政、卫生等等,如果没有法律予以规范,部门之间的各自为政、互相推诿等现象就无法遏制。简而言之,法律法规的缺失导致了我国社区教育法律地位不明,也导致了社区教育实践发展的无序。
4社区教育发展师资匮乏
任何一种教育形式要想获得稳定的发展,师资始终是首要的支持要素。社区教育本身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其对师资的要求也比较高,要求教师具备专业化的素养及技能。但就我国现实情况看,社区教育教师专业化程度较低,与理想要求有较大的差距。上海市是我国社区教育的发源地,其社区教育发展水平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即便如此,上海市社区教育的专业人员在数量上也明显不足。2015年,上海市仅有1 278名专业教师,却需要服务于2 000万人口。如此悬殊的比例难以使得社区教育取得应有的发展成效。此外,目前社区教育教师年龄老化问题也日渐突出,上海市70%的社区教育教师平均年龄超过50岁,且学历程度偏低,大部分教师属于其他职业转岗而来,没有受过专门的社区教育训练。因此,对我国社区教育发展而言,专业师资的匮乏是个严重的问题。由于立法的缺失及政策上的偏差,使得社区教师教育没有统一的聘任、晋升途径,也限制了部分人从事社区教育工作的积极性,进而影响了社区教育的发展。
五、我国社区教育发展的未来展望
1需要进一步明确社区教育的内涵认知及发展目的
社区教育在未来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首先要对社区教育的概念及内涵有明确的认知,在正确理解其内涵特征的基础上,明确其发展的目标。就社区教育的内涵而言,其应该归属于继续教育体系,与学校教育处于并列地位,均是终身教育体系的组成部分。从社区教育的发展主体看,其应该服务于社区内的所有成员,为不同层次、年龄的社区成员提供多样化的教育产品服务。社区教育属于教育体系,其发展的目标是提升社区民众的技能,完善其人格与培养其人文精神。当前,我国整体经济水平还比较落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极不平衡,普通社会个体还为生计与生活奔波。因此,就目前社区教育的发展目标看,自然还带有一定的功利主义倾向。但是,社区教育的发展始终是要超越功利主义目标的,一旦社区教育发展目标过于功利,其自然无法与其他的教育形式竞争。因此,社区教育的发展不能脱离其本质,即以提升社区民众的精神素养与生活品质为目的。换言之,社区教育的发展必须不断超越功利主义目标,才能够真正走上健康发展之路,才能够在终身教育体系中获得合理的位置,才能够真正实现其自身的价值。
2需要进一步扩大社区教育的多元化、自主化与个性化的结合
社区民众对教育的需求本身是多元的,其参与社区教育的形式自然也是多样的。为了提升社区教育服务的实际效果,必须确保社区民众参与的主体性,提升其参与的自主度。因此,在社区教育发展中,需求的多元化、参与的自主化与服务的个性化必须进行有效的结合。第一,在社区教育服务内容及服务形式的设计上,必须充分尊重社区民众的意愿,在实地考察及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确立多元化的教育内容及灵活化的教育形式。第二,在保障社区成员全员参与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扩大社区教育的服务面向。同时,也需要根据个别民众的实际需要,开展针对性及个性化的教育服务,确保社区教育的实效。如上海部分街道社区教育机构在开展社区教育服务时,将外来务工人员纳入到社区教育的服务范畴,按照这些务工人员的实际需求,开设针对性的内容及产品。实际上,多元化的需求、多样化的组织与个性化的服务并不冲突,只有在个性化、多元化相互结合的基础上,才能够提升社区教育对社区的融入程度,进而提升其实际成效。第三,社区教育实践在中国还处于探索阶段,还没有固定的模式与程序,因此需要各地大胆探索,不断创新服务形式与教学方法,在探索中总结相关经验。
3需要加快社区教育的法律法规建设
立法活动并不是简单的法律规范出台的过程,也不是单纯的法律文本生产的过程。当前,加快社区教育的立法工作,并不是给社区教育发展设定条条框框,而是要將社区教育发展纳入到法律规范的范畴当中,通过立法明确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各个参与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关系,避免过多的政府干预,给社区教育发展明确其方向与定位。[15]故此,加快社区教育立法可以为社区教育发展提供生存空间,并能够明确社区教育发展过程中政府部门、社区居民、教育机构等主体各自的定位。从这个意义上看,我国可以先行推进社区教育的地方立法工作,扩大社区教育的立法试点区域,待时机成熟之后,再进行全国性的立法,进一步规范社区教育的发展方向。
4需要提升社区教育师资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从整体看,我国目前对于学校教育的师资专业化发展较为重视,对于学校外教育的师资建设不够重视,没有相关的聘任、晋升等方面的标准。我国社区教育的师资基本上来自于其他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尽管学校教育与学校外教育同属于教育范畴,但两者在教育对象、方法、方式、内容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的不同。社区教育作为学校外教育的一种类型,其专业化程度较高,因此,推进其师资队伍的专业化建设是极为重要的。第一,可以借鉴发达国家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相关经验,在大学中设立社区教育教师专业,为社区教育培养专门师资。第二,对于目前在岗的社区教育教师要继续进行岗位培训,提升其专业化水平。第三,构建社区教育内部的教师交流机制。在终身学习时代,要贯彻终身教育理念,社区教育的教师自身要先树立终身学习意识,相互之间开展交流学习,促进自身的自主学习,构建社区教育教师共同体,进而在整体上提升社区教育教师队伍的专业化水平。
5需要进一步完善社区教育资源的利用共享机制
我国目前社区教育资源的利用还存在着严重的条块分割,共享机制尚未完全建立。针对当前社区教育资源利用的基本现状,要进一步扩大其共享体系。第一,进一步提升社会公共文化设施与机构的教育服务功能,积极引导公共图书馆、科技馆、博物馆、展览馆、文化馆、影剧院等公共机构参与社区教育,扩大这些资源体系对社区民众的开放度,提升社会公共文化资源的公益性程度。第二,社区教育机构要进一步联系社区周边的中小学、大学、科研机构、文化研究机构,实现大社区范围内的资源共享。第三,鼓励各个社区利用社区特色,构建本土化的教育项目,实现不同社区之间不同特色项目的交流,进而提升这些特色教育项目资源的共享程度。
【参考文献】
[1]吴遵民.我国当代社区教育的历史回顾与展望[J].远程教育杂志,2011(3):9—13.
[2]叶忠海.社区教育基础[M].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00:24.
[3]王晓娟.丹麦民众教育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1.
[4]李慧洁.日本社区教育及其借鉴[J].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8):8—10.
[5]岳杰勇.中国社区教育未来发展模式探索[J].成人教育,2006(9):43—44.
[6]邵泽斌.当代中国社区教育问题与政策建议[J].职业技术教育,2006(22):55—59.
[7]邵晓枫,罗志强.社区教育数字化学习资源共享:理论基础、内在逻辑与动力因素[J].职教论坛,2017(12):51—55.
[8]刘彦.“互联网+”时代网络社区教育发展策略研究[J].成人教育,2017(1):39—42.
[9]沈光辉.转型发展中的社区教育问题研究[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2016.
[10]庞庆举.社会治理视野中的社区教育力及其提升研究[J].教育发展研究,2016(7):23—30.
[11]蒋健民.终身教育视角下创建特色社区教育的探讨[J].继续教育研究,2011(1):81—83.
[12]陈爱香.日本社区教育设施分析[J].成人教育,2006(8):93—94.
[13]刘增辉.社区教育新实践:社区教育创出中国特色[J].中国远程教育,2008(10):34—37.
[14]唐克,侯嘉茵.社区教育政策执行多元主体利益博弈及其均衡调整[J].现代远距离教育,2017(1):29—35.
[15]陈思.城市社区教育立法研究[J].成人教育,2017(7):29—32.
The Course, Problems and Prospects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XU Baoliang
(School of Education, Lingnan Teachers College, Zhanjiang 524048, China)
【Abstract】Different countries define the connotation of community education differently. Our countrys community education has its own connotatio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ours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localization characteristic is gradually formed. However, in reality,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Therefore,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and promote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concept, legal construction, faculty, and resource sharing.
【Key words】commun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history; connotation definition
(編辑/乔瑞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