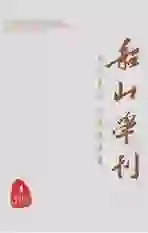夷夏之辨的两个逻辑在近代中国
2017-08-10章舜粤
章舜粤
摘 要:在中国思想史上,夷夏之辨的观念主要形成了两种逻辑。第一种逻辑认为文化先进的是华夏,而中国(大清)的文化先进,所以中国(大清)是华夏;第二种逻辑是因为华夏是文化先进的地方,而中国(大清)是华夏,所以中国(大清)的文化先进。由于中国长期在各方面领先,中国有文化既是前提也是结论,两种逻辑面目不清。而晚清之际,中国文化是先进文化已不再是必然。抱残守缺之士以第二种逻辑而抗拒西方文明,一些进步人士则以第一种逻辑主张学习西方文明。此外,清朝统治者以异族身份入主中原,使得弥平华夷和强调华夷两种思想共存,均成为晚清士人的思想资源。我们回顾这段思想史,应还原其多重面相,而不应采用辉格史式的叙述方式。
关键词:夷夏之辨;华夷观;晚清;西学中源;辉格史学
长期以来,这样一种历史叙述占领着我们的思想市场:中国的近代史开启之际,老大帝国愚昧颟顸,执迷于“夷夏之辨”,以“天朝上国”自居,在西方先進的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面前仍然自以为是,造成了“天朝的崩溃”。这种因过度文化自信导致的“华夏中心主义”大大地阻碍了中国向先进的西方学习,造成了落后挨打的屈辱的百年近代史。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过程,某种意义上便是抛弃原有的以“天下”“夷夏之辨”为核心的传统天下观,融入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现代世界体系(无论对这一过程持积极或消极评价)。
然而,这种历史叙述略有过于简单化之嫌,它没有很好地解释“天下”“夷夏之辨”“天朝”“华夏中心主义”这些概念之间的张力与界限何在。在冷战结束后,由世界局势的动荡引发的文明冲突论的讨论热潮中,一些中西学者试图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念中汲取资源,为对外超越民族国家和文明冲突,对内弭平民族、族群冲突和分离寻找可能道路,提出了“天下主义”“新天下主义”“天下体系”“王道政治”等一系列设想。这种努力一方面扩宽了大家的思路,一方面也引发新的争议。而争议的很大一部分便是来源于对上述概念的简单化解读。
其实,这些概念有着丰富的内涵,它们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不同的面相。本文将试图揭开“夷夏之辨”等被传统的历史叙述所遮蔽的另一种解释及它们对错综复杂的近代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
一、古代中国的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或者说华夷观,是传统中国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之一,它与“天下观”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天下观”滥觞于殷商时期,在周人那里已经形成比较系统的思想。它将世界由内而外地划为几个层级:《国语》里写到“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国语·周语》)目前,历史学家对商周时期具体的服事制度是什么样子尚有较大争议,然而普遍认为当时已形成了一种“以中央为核心,众星拱北辰,四方环中国的‘天地差序格局”的“价值本原”①。王居于天下中心实行统治,周围是臣服于王的四方诸侯,再外则是四方夷狄,这种状况未必是历史真实的描写,而是殷周人对天下秩序的一种想象和认同。因而,“中心——边缘”的层级安排无疑是“天下观”的核心内涵之一。那么,谁在或者应该在中心,而谁又在或者应该在边缘?“华夷观”便是在“天下观”下对此问题的回答与阐发。
“华夷观”产生于西周后期与春秋之际,它将天下划为“华夏”诸邦与“夷”“戎”“蛮”“狄”等部落。②然而它一产生,便有依文化与血统区分的两重含义在内。《左传》中记载:“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左传·僖公二十二年》)“披发而祭于野”显然有悖于周人的礼乐文明,所以此地不算华夏,而属于夷狄了。但这些“披发而祭于野”的人并不一定是华夏子民失去了文明,而是他们本来就是西戎。到底是因为他们是夷狄所以不文明,还是因为他们不文明所以成了夷狄,在这里是模糊不清的。
《左传》又记载,“十一月,杞成公卒。书曰‘子,杞,夷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杞人本是夏朝的后裔:“有夏虽衰,杞、鄫犹在”(《国语·周语》);“夫杞,明王之后也”(《管子·大匡》)。孔子也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论语·八佾》)杞人本是最正统的“夏”,然而这里却将其视为夷,是因为它已使用夷礼。可见血统、地域并不是成为“华”的决定性因素,关键还在于是否文明。
《礼记》中有一段话非常有名:“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髪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髪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王制》)唐初大儒孔颖达曾注到:“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春秋左传正义》)从中可以看出华夷之别在于“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等文化上的区别,文化先进的为中国、华夏,落后的则为夷狄。
应该说,不再以血缘的亲疏而以文明程度的差异作为区别华夷的标准,是一种被广为接受的观念。韩愈指出,“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原道》)可以说是这种观点最明确的表达之一。它表达了两种观念:首先,华和夷是可以辨别的,而辨别的标准正在于文明的程度;其次,华夷固然有别,是有界限的,但这界限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华夷是可以互相转换的。也就是说夷入华则华之,华入夷则夷之,华夏不文明了就变成夷了,夷文明了就变成华夏了。并不是说中国一定是华夏,外国人一定是夷狄。
日本学者檀上宽指出,“一方面,如果夷狄被中华礼义同化,就会成为中华子民;另一方面,即便是中华子民,如果丧失了中华礼义,则与夷狄无异。”③受中国文化的影响,朝鲜、越南和日本等汉字文化圈内的东亚国家往往也这样看待华夷问题。在传统中国看来,朝鲜、越南和日本等当然是夷,而它们也长期仰慕中华文化。当它们认为中国已经丧失了中华礼义时,例如明清易代之际,便纷纷秉持这样的华夷观念,自认为因传承了中华文化正统而成为华夏,而中国大地以华入夷,“华变于夷之态”了。④
从以上论述可以发现,华夷观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观念,它有历史地发展过程,有诸多不同的面相,既有血统、地域上的意义,更有文化上的意义。今天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切忌简单地用其中的一部分代替整体,而应历史地剖析它的不同意蕴,才能避免对历史的误解。
二、“两个逻辑”与晚清的夷夏之辨
正如宫崎市定所说的,“‘武的有无,不能决定。但‘文的有无,却可确定华与夷的区别。换句话说,‘文只存在于‘华之中,同时,正是由于有‘文,‘华才得以成为‘华。”⑤这说明夷夏之辨其实是这样的逻辑:因为有文化的人和地方才是华夏,而中国有文化,所以中国是华夏。由于这里讲的“中国”是一个较为混乱的概念,我们处于近代民族国家早以建成的时代,难免不自觉地把“中国”视为一个民族国家概念。但在历史上,“中国”事实上和“中华”“华夏”的概念近似。因为我们即将要讨论的是晚清时期的夷夏之辨,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妨用“大清”代替“中国”,(在讨论夷夏之辨的问题时,这个“大清”也可以是历朝历代,或匈奴、鲜卑、朝鲜、越南等政权和国家,)尽管这样仍有一定的问题,但它使得我们更容易看清这个逻辑的推理过程。
在采用“大清”代替中国后,我们不妨将上述逻辑叙述为这样一个三段论:
大前提:文化先进的是华夏,
小前提:大清的文化先进;
结论:大清是华夏。
为了叙述的方便,我们将其称之为夷夏之辨的逻辑I。
然而除此之外,事实上长久留在人们心目中的还有另一个逻辑:
大前提:华夏是文化先进的地方,
小前提:大清是华夏;
结论:大清的文化先进。
在这里,我们将其称之为夷夏之辨的逻辑II。
可以看到,两个逻辑的三个命题是相同的,区别在于大清的文化先进是前提还是结论。然而历史事实是,中国(汉、唐、宋、元、明、清……)长期以来在东亚处于文化、政治、经济领先的地位,中国有文化既是前提也是结论,逻辑I和逻辑II长期以来面目含混不清,难以分辨。可以说,因为中国文化在东亚世界历史上的先进性,一直以来这两个逻辑都是成立的,即难以区分,也无须区分。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尽管从理论上是以文化的高低论夷夏,但实际上长久以来关于夷夏之辨的讨论往往仍然立足于是否是中原政权(中国)⑥。
然而当时间走到晚清之际,这两种逻辑便难以再混为一谈了。当清王朝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大清仍否是文化最为先进的国家,就成了一个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在面临晚清变局之际,根据逻辑II,如果相信大清仍然是华夏,那么大清便还是文化先进之国,因此就没有必要向西方的蛮夷学习。即便要学习,最多也是也是学习他们器物上一些优点,即“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这便是传统历史叙述中,华夷观念对中国走向现代化所起到的阻碍作用。
然而如果秉持逻辑I的思维方式,情况便不同了。一些士人慢慢注意到西方列强不仅有极为发达的物质文明,在精神文明上也不遑多让,甚至超过了中国。如果是这样的话,则意味着逻辑I的小前提,即大清文化领先不再成立,取而代之的是西方文化更为先进。那么,根据逻辑I,因为有文化的地方是华夏,西方是有文化的地方;所以西方才是现今的华夏。大清隐隐约约反而成为了文化落后的地方,有变成蛮夷的危险了!
这样的结论,让沐浴在几千年文化领先的岁月中的中国士人难以接受。尽管如此,还是有人勇敢地表达出了自己的观点。
清王朝向西方国家派驻的首任公使郭嵩焘便是其中之一。他在光绪四年二月初二日的日记中感慨:“盖西洋言政教修明之国曰色维来意斯得(注:Civilized),欧洲诸国皆名之。其余中国及土耳其及波斯,曰哈甫色维来意斯得(注:Half Civilized)。哈甫者,译言得半边,意谓一半有教化,一半无之。其名阿非利加诸回国曰巴尔比里安(注:barbarian),犹中国夷狄之称也,西洋谓之无教化。三代以前,独中国有教化耳,故有要服、荒服之名,一皆远之于中国而名曰夷狄。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其视中国亦犹三代盛时之视夷狄也。中国士大夫知其义者尚无其人,伤哉!”⑦
在郭嵩焘看来,当时的西方礼义教化盛行,而中国已然沦为夷狄的境地了。当友人来信表示西方是夷狄时,他指出华夷是变化的,中国版图内很多地域历史上也是夷狄:“ 三代盛时,圣人政教所及,中土一隅而已,湖南、江浙,皆蛮夷也。至汉而南达交阯, 东经乐浪,皆为郡县,而匈奴、乌桓、西羌为戎狄。历元至本朝, 匈奴、西羌故地尽隶版图,而朝鲜、安南又为要荒属国。是所谓戎狄者,但据礼乐政教所及言之。其不服中国礼乐政教而以寇抄为事,谓之夷狄,为其倏盛倏衰,环起以立国者,宜以中国为宗也,非谓尽地球纵横九万里即为夷狄,独中土一隅,不问政教风俗何若,可以凌驾而出其上也……阁下据此为俯顺人心之证,蒙不敢谓然。”⑧而西方国家之“西洋君德,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即伊周之相业,亦未有闻焉;而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⑨
无独有偶,王韬也批驳了中国自以为华夏的观念,他指出华夏和夷狄的区分标准是文化而非地域或种族,并再三强调了夷夏身份的可逆转性,“《春秋》之法,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之进于中国者则中国之, 夷狄虽大曰子。故吴、楚之地皆声名文物之所,而《春秋》统谓之夷。然则华夷之辨,其不在内外,而系于礼之有无也明矣。苟有礼也,夷可进为华;苟无礼也,华则变为夷,岂可沾沾自喜,厚己薄人哉?”⑩
谭嗣同作为维新派,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他批评国人“好以夷狄诋人,《春秋》之所谓夷狄中国,实非以地言,故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流于夷狄则夷狄之。惟视教化文明之进退如何耳。若以地言,则我湘、楚固春秋之夷狄,而今何如也? 且我国之骄又不止此,动辄诋西人无伦常,此大不可。夫无伦常矣,安得有国?使无伦常而犹能至今日之治平强盛,则治国者又何必要伦常乎?惟其万不能少,是以西人最讲究伦常,且更精而更实。即如民主、君民共主,豈非伦常中之大公者乎?”B11
梁启超则更为激烈,他说:“《春秋》之记号也,有礼义者谓之中国,无礼义者谓之夷狄。礼者何?公理而已。以理释礼,乃汉儒训诂。本朝焦里堂、凌次仲大阐此说。义者何?权限而已。番禺韩孔庵先生有义说专明此理。今吾中国聚四万万不明公理不讲权限之人,以与西国相处,即使高城深池,坚革多粟,亦不过如猛虎之遇猎人,犹无幸焉矣。乃以如此之国势,如此之政体,如此之人心风俗,犹嚣嚣然自居中国而夷狄人,无怪乎西人以我为三等野番之国。谓天地间不容有此等人也。故今日非发明法律之学,不足以自存矣。抑又闻之,世界之进无穷极也,以今日之中国视泰西,中国固为野蛮矣。”B12在他看来,中国的国势、政体、人心风俗、法治远远落后于西方,已是夷狄、野蛮了。
可以看出,这些有识之士的论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他们均认为以地域定夷夏是不符合夷夏之辨的本意的;夷夏是可以转换的;西方的政教风俗、伦常礼义并不逊于中国,甚至胜于中国,郭嵩焘、梁启超等甚至直言西方列强俨然已是华夏,而中国是夷狄了。而夷狄必须向华夏学习,也就是大清必须向西方学习,这是由逻辑I得出的结论。对于长期秉持逻辑II的人,即便认同“师夷长技”,也实在难以接受,这是因为虽然他们都同意西方技术较为先进,但背后的逻辑是不同的。无怪乎郭嵩焘被目为禽兽,其出使英国的日记《使西纪程》刊刻印行后不久就被清廷下诏毁版,禁止流传。
三、“古已有之”“西学中源”
“逆向天下主义”与“两个逻辑”
正如前文所说,孔颖达将华夏解释为“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服章之美本身就是华夏的标志。戊戌变法时,康有为上了一道《请断发易服改元折》,提出“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 衣长后衽,乃孔子三统之一, 大冠似箕, 为汉士夫之遗, 革舄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B13
表面上看,这似乎也把西方视为华夏,但其实它与上述的夷夏之辨的逻辑I有着重要的区别。他将西服、礼帽和皮鞋与上古衣冠服制相比附,是为了说明西方文化并不悖于中国文化。这样的观点在当时非常盛行,王尔敏先生概括为“西学得中国古意”和“西学源出中国”兩种说法。B14早在道光二十二年,大理寺卿金应麟就认为西方的军舰“乃中国之绪余耳……夷人特稍变其法。而牛革蒙船,亦参用艨艟之法,无足异也。”B151865年,李鸿章在谈西方学术时也说过,“无论中国制度文章,事事非海外所能望见,即彼机器一事,亦以算术为主,而西术之借根方,本于中术之天元,彼西土目为东来法,亦不能昧其所自来。B16
“古已有之”和“西学中源”与逻辑I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它认为西方文化之所以有可取的地方,是因为它来源于中国或与之相似。言外之意,在它看来,中国文化仍然是先进文化,并未沦落至夷狄的地位,而中国看起来落后,只是因为它背离了“真正的中国文化”。因此,这实际上是逻辑II的推演,最多承认西方不再是夷狄而已,而先进文化仍以中国为标准。
因此,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便浮现出来,即两个逻辑共享的大前提中的“文化先进”指的是什么?在采用逻辑II的人看来,无疑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由于其一直以来在东亚的优势地位,导致他们在面对西方文化时,保有强烈的信心。
而认同逻辑I者,在见识了西方的社会进步之后,则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即西方社会的文化究竟有何优于中国?郭嵩焘给出的答案是“自汉以来,中国教化日益微灭;而政教风俗,欧洲各国乃独擅其胜”。B17除了政教风俗外,西方的君主宪政在他看来甚至超过了三代,“视中国三代令主,无有能庶几者”,俨然有天下为公的味道了。这是在传统观念下给出的回答。B18
谭嗣同、梁启超等人也从君主立宪、民主、法治等角度论证西方的文化先进。许纪霖先生指出这是由传统的华夷观念向近代文明论的转变,以西方作为文明(即郭嵩焘所谓的“色维来意斯得”)的尺度,则中国自然成为未开化的半野蛮之地。许先生将之称为“逆向天下主义”,即以西洋为价值尺度的近代文明论。B19
如果以逻辑II为夷夏之辨的真正意涵,则以西方文化为衡量尺度的近代文明论无疑是“逆向”的。但如果从逻辑I出发,我们发现近代夷夏的易位本身并不违背夷夏之辨的固有含义,从夷夏之辨的本意中本来就能推出中国(大清)有可能因为文化的落后而成为夷狄。既然中国并不天然是“华夏”,那就没有什么“逆向”可言。郭嵩焘等人提出的“教化”“政教”“风俗”“伦常之大公”等,本来也是一定程度上契合对“华夏”的要求的,这无疑是文明论能被广泛接受的重要文化基础。
中国传统的“天命”思想,也给逻辑I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天命”观念起源于西周或者更早,天子奉天承运,统治天下。而天子必须要修身养德,教化天下,泽被四海。如果天子失德,就会丧失天下,另有有德者取而代之。那么,当中国面临内忧外患之际,不由得让人拷问自己,是否中国已经沦为无道之国,即将丧失天命?
郭嵩焘在英国时,在议会旁听是否介入俄土战争的争论,他专门记下反对党议员阿尔该尔的发言:“土国无政事,无教化,无能自立,……往册所载,国家有道,得以兼并无道之国,自古皆然。如英人兼并印度,人多言其过,吾意不然。印度无道,英人以道御之,而土地民人被其泽者多矣,此亦天地自然之理也。B20郭嵩焘并没有直接表明他的想法,但从其记录下来的言论来看,他似乎将先进文明征服落后文明的情况理解为“国家有道,得以兼并无道之国”,而一国“有道”与否则看它的政事是否清明,是否为害人民,教化如何等等。既然有道之国得以兼并无道之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咄咄逼人,郭嵩焘认为,“三代以前,皆以中国之有道制夷狄之无道。秦汉而后,专以强弱相制。中国强则兼并夷狄,夷狄强则侵凌中国,相与为无道而已。自西洋通商三十余年,乃似以其有道攻中国之无道,故可危矣。”B21中国无道,难道不是沦为夷狄之国吗?
因此,我们发现,郭嵩焘的思想并不是简单的反对夷夏之辨,他恰恰是从夷夏之辨的逻辑I推论出中国的危险,继而要求已经成为夷狄的中国以夷入夏,学习西方的先进文化。从这个角度而言,夷夏之辨并不一定完全阻碍中国向西方学习,它同时也给向西方学习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思想资源。
四、晚清夷夏之辨的两个传统
与我们的历史叙述
在讨论晚清的夷夏之辨问题时,不能脱离清王朝是由少数民族入关统治的王朝这一重要背景。至清末之际,种族论甚嚣尘上,不惟革命党喊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非革命党人往往也接受种族作为竞争单位的观念。种族论在中国的流行,一方面与西方观念的传入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与传统中国的夷夏之辨有关。章太炎、刘师培、谭嗣同、邹容等人,往往从明末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处汲取思想资源,将满汉视为对立的两个种族,以煽动种族革命,颠覆清朝政权。朱希祖曾记载章太炎的回忆他的革命思想来源时说,“余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授余读经。偶讲蒋氏《东华录》曾静案。外祖谓:‘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余问前人有谈此语否?外祖曰:‘王船山、顾亭林已言之,尤以王氏之言为甚。谓历代亡国,无足轻重,惟南宋之亡,则衣冠文物亦与之俱亡。” 章太炎总结道:“余之革命思想即伏根于此。依外祖之言观之,可见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B22可见,种族观念在近代中国的流行,夷夏之辨的观念是内在深刻的历史记忆,特别是明末清初时知识分子留下的种种言论,例如《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纪略》《明季稗史汇编》等记录满汉民族矛盾的文献,更是为种族革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
清末官吏刘声木在其《苌楚斋续笔》卷五中《明王洙宋史质》一条里,曾分析了种族革命的两条来源,“自光绪末造,种族革命之说兴,一人倡之,千百人和之,遂至酿成宣统辛亥之变,而清社易屋。论者遂谓种族之见创自泰西,流被东瀛,四十年内,其说盛行于时。不知此种心理,其渊源早发见于三四百年以前,是当时之人,早已有此心理。其与近世相应者,盖亦有故。我朝入关之后,禁忌各书,检查毁灭尤甚严,难保无流入东瀛者。东瀛得以因之鼓荡中国人心,助成其事。”B23刘声木认为明末清初之际的种族观念传入日本再返回中国,窥见了晚明遗献的一条流传通道,但并不全面。据王汎森先生考察,道、咸之后,除了日本回流的渠道之外,各种明季遗献以口传、传抄、考证等方式复活,大大地刺激了思想界,也引发了社会激荡。B24
然而之所以将这些文献称之为“遗献”,将它们的出现称之为“复活”,正是因为他们在清朝的大部分时期处于“死去”的状态。换言之,在有清一朝,清末这些激起民族情绪的关于夷夏之辨的言说,基本处于被禁绝的状态。
清曾大兴文字狱,除了直接禁绝任何提到满汉之间的战争、种族差异等强调夷夏之辨的文献之外,往往对古代文献中提及夷夏之防的地方做偷梁换柱式的修改。除了官方的强力压制之外,在“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下,作者、刻书者、编者、出版者、后代子孙、藏书家以及读者纷纷自我禁制、自我删窜、自我压抑,使得整个清朝社会大部分时间难以直接阅读有关夷夏之辨的文字,而这对人民的历史记忆和认知的影响是巨大的。B25
例如出生于清末的钱穆,在他十岁出头时,并不知道清朝皇帝不是“中国人”:“伯圭师随又告余,汝知今天我们的皇帝不是中国人吗?余骤闻,大惊讶,云不知。归,询之先父。先父云,师言是也。今天我们的皇帝是满洲人,我们则是汉人,你看街上店铺有满汉云云字眼,即指此。”B26前文所述章太炎之“种族革命思想原在汉人心中,惟隐而不显耳”,亦可说明这种以种族为标准划分夷夏的思想在清朝可能并不是主流。
事实上,正是因为以夷夏之辨的逻辑II,作为统治者的满洲贵族难逃夷狄的指责,因此清朝的官方意识形态是弥平种族、血缘区别的“华夷一家”。B27在轰动天下的曾静案中,雍正皇帝虽然承认自己是夷狄,但他指出只要有德,便可成为华夏之主。而之后的乾隆皇帝则更是强调“中外一家”,弥平华夷的区别。王汎森先生指出,清朝忌讳夷夏之辨的文字狱,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由于这种不以汉族为中心的历史观,而是对各种族采取比较平等的观点,会不会使得清朝能够摆脱旧的华夷观来处理周边种族的问题,而且也比以前更成功地处理这些问题。”B28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对于晚清士人而言,夷夏之辨也有两个传统、两个思想资源:(一)清朝官方主流的弥平种族、血统的华夷观;(二)道、咸年间之后明季遗献的重新发现引发的强调种族、血统的华夷观。
然而由于力主种族革命的章太炎、邹容、陈天华等人,在辛亥革命之后成为民国先烈或元老,而辛亥以来革命在中国社会取得了神圣的、主流的地位,他们对夷夏之辨的理解与演说自然成為我们历史记忆和叙述的主要来源。
巴特菲尔德曾提出“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the whig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的术语,或者称之为“辉格史观”,用来描述历史学家的一种“站在新教徒与辉格党的立场上写作”的倾向性,“只要是成功的革命就去赞扬,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以及编造出一个修正当今的叙述。”B29这种史观站在“我们的视角”去审视和评判哪些历史事件是重要的,换言之,是“为了现在而研究过去”,以当下为准绳。这些历史学家因此抄近道越过了历史的复杂性。B30
从这个意义上讲,忘却晚清的知识分子实际上拥有两种夷夏之辨的思想传统,而是依据后来取得了历史地位的革命党人对夷夏之辨的阐述和理解来认知和解释晚清的夷夏之辨,也是一种“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这种历史阐释使历史学家“把复杂事物中最棘手的成分排除出去。通过利用观点与我们自己更为相似的那些历史人物及党派, 把这一切同历史的其它内容作对比,他就找到了现成的历史结构及历史节选,找到了穿越复杂的平坦大道。”B31因为长期以来的社会观念认同革命,而革命先驱章太炎、邹容等人又将夷夏之辨更多地阐释为满汉对立的种族思想。因此,我们记忆中晚清的夷夏之辨,便通过革命党人们的言说,再通过认同革命的历史学家的书写,深深地植入我们的历史记忆之中,而长期以来在清朝占社会主流地位的“华夷一家”“中外一家”便似乎被我们遗忘了。
而章太炎等人对夷夏之辨的论述,本身也是一种“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他们在解读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的言论时,有其从儒学自身“内部批判”的一面,但往往也将之比附西方观念,剪裁、挑选符合现代西方观念的部分,并按现代理论加以阐释,某种程度上亦是曲解了明末先贤的原意。B32
这也提醒我们,当现今为了解决文明冲突而向过去挖掘资源之时,切忌陷入辉格史观,“想象自己已经发现了20世纪的一个‘根源(‘root)或一种‘预示(‘anticipation)”,事实上我们“处于一个内涵完全不同的世界”“只是偶然碰到了一个可以说具有误导性的类似”B33。当我们在重释“天下主义”和“夷夏之辨”的积极意义时,必须警惕这种简单地以当下的视角和观念去阐释古人的思想的辉格史观,从而避免抹杀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同样的,尽管本文试图指出在晚清时,还存在通过夷夏之辨的逻辑I而提出向西方学习的声音,但必须承认的是这并非社会思潮的主流,它既没有引起特别多的注意,发挥重要的影响,更没有成为国人的历史记忆。近年来,学界已经有很多人注意到夷夏之辨的复杂多重性及其对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积极促进的一面。晚清的夷夏之辨既有两套逻辑,和近代史上的种族论、文明论和西学中源论、中体西用论等思想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又面目模糊;在晚清这个特定的历史时空,它还有来自清朝长期强调的“华夷一家”和复活的明末清初之际的“夷夏之防”两个传统。本文并不认为逻辑I才是夷夏之辨的真正意涵,也不认为近代中国走过了由逻辑II向逻辑I转变的演化过程,或者先由种族论而走向文明论,或抑是由“华夷一家”重新走向“夷夏之防”,更不是批判何者更为进步或者更适应现代的价值观。历史进化观或辉格史观往往引导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历史的不同面相想象成一个由落后到进步的演化或者斗争过程。但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解释,其实都是“夷夏之辨”复杂面相的一部分,都为一部分人(尽管有的是一大部分人,有的是一小部分人)在一定的时间内所认同。因此,我们在回望历史之际,一定要勇敢地直面这些复杂的面相,并努力将自己放回当时的时空去理解历史情景。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地理解过去,面对未来。
【 注 释 】
①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30页。
②陈尚胜:《中国传统对外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11页。
③檀上宽、王晓峰译:《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页。
④林恕:《华夷变态》,东方书店1981年版,第1页。
⑤宫崎市定,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翻译组编译: 《中国文化的本质》,《宫崎市定论文选集》下卷,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304页。
⑥事实上,这里的“中国”,更多的是“正统”的概念。哪个王朝、政权取得了“正统”的地位,往往就被视为是“中国”“中华”。关于“正统论”的讨论,参见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中华书局2015年版。
⑦⑨B17B18B20B21
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491、434、491、434、430—431、626—627页。
⑧郭嵩焘:《复姚彦嘉》,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00頁。
⑩王韬:《华夷辨》,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245页。
B11谭嗣同:《谭嗣同全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01页。
B12梁启超:《论中国宜讲求法律之学》,见《梁启超全集》第1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60页。
B13康有为:《康有为全集》第4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32—433页。
B14王尔敏:《晚清政治思想史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5—40页。
B1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6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06页。
B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海防档(丙)机器局》卷一,台湾艺文印书馆1957年版,第14页。
B19参见许纪霖:《天下主义:夷夏之辨及其在近代的变异》,《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B22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笔记》,《制言》1936年第25期。
B23刘声木:《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上册,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9—350页。
B24B25B28参见王汎森:《道、咸以降思想界的新现象——禁书复出及其意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34—571、410—411、432页。
B26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46页。
B27日本学者檀上宽指出,最早用“华夷一家”代替“天下一家”的是明朝永乐皇帝。这与永乐帝面临之前统合华夷的多民族政权元朝有密切关系。如此看来,即便是明朝人心中,应该也受过“华夷一家”的影响,只不过在明清易代之际强烈的刺激下,重新激起了夷夏之辨的热潮。参见檀上宽,王晓峰译:《永乐帝——华夷秩序的完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
B29B30B31B33巴特菲尔德著,李普译:《辉格党式的历史阐释》,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18—19、21、12页。
B32关于晚清思想家因西方观念的冲击而产生的“外部批判”和源于儒学内部的“内部批判”,余英时先生在《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从明清思想基调的转换看儒学的现代发展》中做了精要的论述。参见余英时:《现代儒学的回顾与展望》,三联书店2004年版。
(编校:龙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