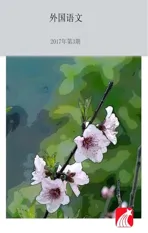沙博理《新儿女英雄传》英译本译者主体性探析
2017-03-11徐婷婷
徐婷婷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沙博理《新儿女英雄传》英译本译者主体性探析
徐婷婷
(四川外国语大学 英语学院,重庆 400031)
译者主体性的研究与译者受动性及其译者、读者、文本之间的主体间性密切相关,本文以《中国文学》创刊号刊载的《新儿女英雄传》沙博理英译本为例进行探讨。在翻译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下,通过分析该译作中的回目、译序、标题、熟语、歌谣等的翻译,让我们了解在受制因素突出的情况下,译者如何平衡、协调制约因素与主体能动性及其主体间性关系,从而确保译介效果。这在当今“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形势下,对于翻译研究而言,不能不说是一个有效的借鉴。
《新儿女英雄传》;译者主体性;主体间性;受制性
0 引言
《新儿女英雄传》是由袁静和孔厥合著的长篇小说。小说讲述了抗日战争初期冀中白洋淀农民在共产党员带领下,与日本及伪军反动势力斗争的故事。此主题贯彻实践了毛泽东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是当时的政治需要,获得主流意识形态的青睐,也广受当时读者欢迎。小说最初在报纸上连载,1949年由上海海燕出版社首次印成单行本,后经多次再版。1951年被选入《中国文学》创刊号。《中国文学》是当时对外宣传中国革命的重要刊物。在创刊初期,该杂志以懂英语的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汉学家和文艺爱好者为读者对象,向他们介绍我国的革命和斗争,以博得这类读者的了解和同情 (骆忠武,2013: 83)。
《新儿女英雄传》由著名翻译家沙博理翻译的英译本在北美发行过,是美国发行的第一部反映“红色”中国的小说。沙博理生于美国,曾在康奈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进修过中文。1947年来到中国,1948年定居北京,并继续学习中文,后与著名戏剧演员、作家凤子结为夫妻;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指示外文出版社安排他在《中国文学》杂志社担任翻译;1963年经周总理特批加入中国国籍。《新儿女英雄传》是沙博理的首部译作,在长达50多年的翻译生涯中,他还翻译过《林海雪原》《水浒传》《创业史》《春蚕》《家》《我的父亲邓小平》等,包括短篇小说在内译著达一千万字,并荣获“彩虹翻译奖” “国际传播终身荣誉奖”“中国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和“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对于他的生平和译作,曾有学者在翻译史著作或翻译论著中略有涉及 (马祖毅,等,2003;林煌天,2005;马祖毅,2006;方梦之,2011;张经浩,等,2005)。报纸也曾登载过对沙博理的采访、记录性文章 (廖旭和,1992:1; 武际良,1998:35-39;何琳,赵新宇,2011;张中江,2011);还有大量学位论文或学术论文研究沙译版《水浒传》,或分析对比其与赛珍珠版的差异。此外,李振(2009: 120-128)和邹丽(2008: 120-123) 研究过沙译“茅盾农村三部曲”及《家》的翻译策略;任东升和张静(2012: 105-109) 以《我的父亲邓小平》为例研究沙的文学翻译观;欧晓南和贾德江(2012: 115-117) 对比《水浒传》两种英译本的谶言翻译探讨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
1 译者的主体性
关于译者主体性,国内研究侧重译者作为中心主体的作用,有学者把原作者和读者作为制约中心主体的边缘中心 (屠国元,等,2003:8-14;2009:97-99); 也有学者将主体性表述为译者在尊重翻译对象的前提下,为实现翻译目的而在翻译活动中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 (查明建,等,2003:19-24)。这些研究对于翻译过程中所牵扯的译者与原文及其译文和译文读者等主体之间的间性关系有所涉及,但研究中单向侧重比较明显,对问题的探讨还需深入和明确,需要总体性的宏观视野。
译者主体性首先需要明确译者的主观能动性,正如本雅明 (2000:197) 和Jacques Derrida (1985:176) 在其翻译著述中注重译者的主体阐释作用及其创造性再现,并表示译者可以赋予原作以“来世的生命”。劳伦斯·韦努蒂(2004:344) 在《译者的隐形》一书中,明确表达了译者需要采取阻抗式的翻译策略,其地位从“隐形”上升到“显形”,进一步弘扬了译者主体的作用。
诚然,译者主体的能动性阐释确认了译者主体的介入不可避免,然而翻译毕竟不是创作,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独立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并非唯一因素,还需要关注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受到的制约。原文是译者实际操作的对象,由于其在内容、语言文化规范、审美情趣等方面的特性,实际约束着译者的翻译,其创造过程局限于原文、原作者所限定的范围。学者罗宾逊将其表述为译者向自身理性意愿之外的各种力量,尤其是原作者及/或原文本屈服、妥协的过程(Robinson,2001: 193)。此外,赞助人、意识形态等机制的制约也牵制了译者主体创造性的发挥。在主动与受制之间,译者需要协调、平衡,取舍有据,在最大限度内达到翻译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并非翻译中的唯一主体,译者主体的研究还需要规避片面的单一主体的研究,从主体间性的高度重新审视译者主体性。伽达默尔 (2005)从胡塞尔现象学中借用了“主体间性”这一术语,拓宽了翻译主体研究的理论视域,认为意义生成于主体与主体间的对话,主体间的对话、沟通和交往成为理解的关键。文学是一种主体间性的交流活动。文学翻译,就其本质来说,也是主体间(译者、原作者、读者)通过对象(文本)互相沟通、对话的形式。 毕竟翻译是涉及原文、译者、原作者、读者等因素的复杂活动,译者作为有自主意识的主体,在与原作者、原文、译文读者的对话关系中寻求主体性的存在。曾有学者建议利用人的总体性维度,将主体性与主体间性置于更广阔的空间中,从而突破理论阀限(胡牧,2006:66-72)。
总体而言,译者主体性是在赞助人、时代背景、意识形态等客观因素的施动牵制下,译者在翻译实践中所表现出的选择、认知、评价、审美、情感、翻译策略等主观能动的翻译取向和趋向,是译者与原作者、原文、译文读者等主体对象共存并平等对话的关系,表现为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能动性与受动性的统一。
如何将理论结合到实践中来,这需要对作品进行研读,落到实处,从而全面、客观、辩证地解读主体性的含义。本文选取的小说《新儿女英雄传》及著名翻译家沙博理先生登载在《中国文学》上对其的译作发表在建国17年文学时期(1949—1966)。当时文学翻译的主要目的“落实在捍卫、建设新型的社会主义民族国家这个中国社会主义现代性工程上”,其主要特征是以反帝、反封建、反资产阶级为主题(刘彬,2010:93-97)。由于译介有助于对意识形态与民族国家话语的建构,翻译直接为政府组织、宏观政策、专项制度服务。译者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在某些细节上对原文“亦步亦趋”,对那个时期的译作进行分析可谓别有意义,即使译者受制于历史情境、政治意识形态、文化与价值观迥异等因素。通过文本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该译作仍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了译者对原文理解消化后的选择性的主观能动再现,以及译者对读者的把握程度和读者对译作的认同程度所决定的主体间性关系和对话质量,说明翻译为了实现文化宣传之效应和意义,译者需要兼顾译文读者的接受能力和理解能力,准确地运用目标语言创造性地表现原作的意义,实现其应有的文学、文化效应,这其中没有哪个因素能占据绝对优势,它必然是多个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2 译者主体性在小说文本中的分析
沙博理凭借其对中、英文的流利掌握,灵活运用翻译策略,形成了译者独特的译风。通过对原文及其英译本的文本分析,本文将尝试探讨译者在主体能动性、受制性及主体间性等方面的权衡与建构。
2.1主体能动性
《新儿女英雄传》是一部章回体小说,每一章都有回目,包括民谣、民谚、民歌、成语、一句话或者诗的节选等,以此导出正文。作者以此作为情节介绍,吸引读者的注意。这些内容呼应了章节的主题,其中大多鲜明地表达了敌我对立,政治色彩浓烈。但既然章节内容有详尽阐述,回目的翻译与否不会影响到读者对作品的理解,译者对这些回目无一例外做了省略。类似的处理方法译者也曾在别的译作中运用过,“那些旨在介绍每章内容的所谓‘诗歌’仅仅是些打油诗而已,而且破坏了随后内容的悬念节奏,因此将其与其他一些冗长而累赘的细节内容统统删掉”(孙建成,2008:107)。这种翻译策略表明译者在不影响译文读者理解的前提下,对于原文所做的主观能动处理,尽管回目的内容政治意义很大,但是译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了作用,避免了文字重复,从而确保了译文流畅,增加了可读性。
此外,在小说译文的正文前面,译者增添了译序(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首先介绍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日本大举入侵中国,而伪军政府腐败无能,任由百姓遭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接着译序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组织武装保家卫国。 译序归纳了小说的主要内容是讴歌一群英雄儿女在北方平原抗击日本帝国主义及伪军的斗争。最后,译者说明了小说作者的背景及身份,他们曾亲历这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斗争。
这部分从内容及语言处理方式看较之汉语原文中郭沫若的序言有显著差异。汉语序言政治色彩浓烈,尤其突出要忠实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指示:“应该多谢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指示,给予文艺界一把宏大的火把,照明了创作的前途 …… 本书的作者也是忠实于毛主席的指示而获得了成功”(袁静,等,1978:1)。对于小说故事发生的背景、内容并未直接涉及,只是倡导向先进人物事迹学习,“男的难道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样吗?女的难道不能做到杨小梅那样吗?不怕你平凡、落后,甚至是文盲无知,只要你自觉,求进步,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忠实实践毛主席的思想,谁也可以成为新社会的柱石”。
对于写作技巧则一笔带过:“人物的刻画,事件的叙述,都很踏实自然,而运用人民大众的语言也非常纯熟。” (袁静,等,1978:1)
相比而言,英文译序对于小说背景、内容及其作者信息客观简要的介绍表现出译者主观能动的处理方式。这种主观能动性并未影响译者明确其政治立场和态度,毕竟这时的中国文学是向世界推介中国的革命战争,树立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的形象,译者只是避免了政治词汇的大肆渲染。沙博理从来都不掩饰他的政治立场,毕竟译者的价值观与他所处的社会时代密不可分,通过翻译的文学作品,最终表现在译语文本中,“做文学翻译也要有立场、有观点、有世界观。知道自己爱什么、恨什么,才能选择自己最想要外国受众知道的东西,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中国”(张贺,2010)。
英文译本的译序为读者奠定了阅读的基础,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作品。这样做无疑是考虑到译文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将主体间性关系纳入翻译过程之中。由此,英文译序将译者主体能动性、译者受制于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及译文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交流等特点综合了起来,并未因政治背景的束缚而忽略翻译所要传达的以及让读者接受的意图,明确体现译者主体性的多重意义。
2.2 受制性
文学作品是政治宣传的重要工具,译者主体性受到意识规范的严格制约。符合主流文化意识,并且与社会主流文化意识相契合的,译者需要在译文中凸显。这部小说除章节回目外,章节正文中还有12处歌谣、民谚、民歌、歌曲等,除了3处有关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以及一处童谣外,剩余8处均是老百姓中流传的抗日歌谣或革命歌曲,除去重复的因素,译者选择保留了这8处中的4处。其中一处较为突出的是第15回对于《东方红》的翻译。大伙解决了分地的问题,兴高采烈地唱着歌,歌颂着毛主席的领导。《东方红》是讴歌毛泽东在人们心目中的领袖形象,此处译者进行了翻译,虽然不是逐字逐句的完全翻译,但明确了毛主席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其他包括第1回中的《大刀进行曲》,译者选择了部分翻译。文中2处《新中华进行曲》,译者翻译了第147页的歌曲。这部分译者并没有逐字逐句地直译,而是说明了大意,但在句型结构上尽量贴近原文。此外,第14回是关于杨小梅带领百姓唱歌说服岗楼上的伪军投降,鼓励伪军弃暗投明,不做亡国奴的故事。此处译者采取的是逐字逐句地直译(Sidney Shapiro,1951)。对于这几处歌曲的保留和处理译者受制于意识形态的特点显露无遗。沙博理也曾明确表达过这种制约,“我们当时翻译主要看政治的效果。我们是对外宣传,要保留最重要的东西,要有的放矢”(洪捷,2012:62-64)。
第15回讲述杨小梅带领农民同申家庄的地主申宗耀谈减租的事情。译者添加了一大段文字说明,向读者详细解释:在日本人占领的地区,地主趁乱敛收赋税,有些农民竟然被迫缴纳收成的70%给地主抵税,生活异常艰难。当共产党重新夺回政权后,着手调整农村的土地政策,组织减租政策,同地主协商将税收降低到农民可以承受的范围以内,并且退回敌人占领时期强加的赋税(Sidney Shapiro,1951:155)。这段背景介绍清楚地交代了当时中国的国情和政策,说明为什么农民可以要求地主减少地租,为什么这个政策的实施关系到农民的生计。
沙博理的处理明确了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导向,这样做可以说是受制于译者身处的政治环境,同时向西方读者介绍了中国社会的本来面目。那个年代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是不为广大西方读者所知的,原文中涉及特定的异质社会文化信息内容,如果不加以阐释,势必影响读者对译文的理解和鉴赏,不利于外国读者了解真正的中国。当然这要基于译者的熟悉了解,正如沙博理自己所言,“一篇小说,我们总得先对内容理解透了才能翻译。我们必须知道那个社会在那个时期有什么情况,政治上经济上有什么主要的矛盾,社会和文化的状况又如何,敌对的势力有哪些,各自有什么特点,什么风俗习惯……换句话说, 我们得熟悉故事的历史环境”(洪捷,2012:62-64)。诚然,当时的历史背景限制了译者的翻译,然而译者对于原文的理解仍不可避免地包含着他的主观思考和个人审美,添加译序和文化相关信息的阐释便是译者主动性的积极表现,并且为译文读者的阅读和理解扫清了障碍。因此,受制因素并没能完全抹杀译者发挥主动性调整译文内容以确保译介效果。
2.3主体间性
《新儿女英雄传》原作者大量运用了熟语及方言土语的表达。熟语用词固定、语义结合紧密、语音和谐,它包括成语、谚语、歇后语和惯用语等。熟语一般具有两个特征:结构上的稳固性、意义上的整体性。熟语言简意赅,形象生动,极富艺术表现力。但由于其具有整体意义,切忌望文生义。此外,熟语中包含部分方言土语,富有区域性文化色彩,是表明说话者身份和文化背景的参照物,赋予了民族归属性和文化指涉性,从而增加了翻译的难度,考验了译者在原文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取舍与驾驭程度。
译者对于原文中的熟语采取了比较灵活的处理方式。有的熟语译者选择不译,尤其是下文有明确语言说明之处,比如在第2回牛大水跟杨小梅到县里训练班受训,两人都是农民,目不识丁,刚开始学习很吃力,牛大水发出感叹说他俩一般笨,用了一句歇后语, “咱俩可是高粱地里耩(jiang)耠(huo),一道苗儿”(袁静,等,1978:28)。耩是一种古老农具,用来灌溉和施肥,耠也是一种古老农具,用于翻土。此处译者没有翻译,牛大水紧跟着说的“两个傻蛋”以及杨小梅回应的“两个笨鸭子”已经把上句歇后语的意思表明了,就是两人半斤八两,都差不多笨。译者在英文中表述为:“We’re a couple of stupid hicks” (Sidney Shapiro,1951:39)。此处直接把两种农具和歇后语直译未必合适,且不说英文中能否找到这两种农具对应的英文单词,这样做避免了英文读者因为不懂两种农具及歇后语的含义可能出现的理解障碍。
对于有些熟语译者选择了直译处理。在第8回,面对敌人围剿的艰难局势,老蔡他们将县大队据点安插在敌人鼻子底下,他鼓励小梅说很多干部和群众都还坚持着,人民群众的支持是抗日最坚强的后盾,“别说冀中没有山,人山比石山还保险!” (袁静,等,1978:121) 英译为“There may be few mountains in Hopei province, but we’ll make a mountain of people that’ll be harder than rock!” (Sidney Shapiro:103) 英译保留了“人山”和“石山”的原文比喻,在贴近原文的基础上,尽量兼顾了英语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能力。
对于另外一些熟语,译者选取了意译的方式进行翻译。比如,在第13回,牛大水到地主申宗耀家去说服他积极配合八路军的抗日斗争,申宗耀急忙回应道,“我可是人在曹营心在汉”,(袁静,等,1978:176) 表明自己虽然同日本人有联系,但他的心是向着中国的。沙博理翻译成“I have always been a Chinese at heart”(Sidney Shapiro,1951:139)。译者没有选择直译,英语读者对于这个成语的典故未必清楚,毕竟英语读者对于《三国演义》的故事未必了解,如果选择直译,还需要做出说明,解释这个典故的来历和含义。所以,译者选择将成语的意思表达出来,读者完全能够理解并接受译文,不会妨碍他们对于情节的理解,同时,英语的译文也没有破坏语言整体的流畅感。但美中不足的是译文没能把典故中所蕴含的中国文化信息完全展露出来,这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不能不说是个损失。
译者选择的另一种处理方式为直译加内涵。比如,在第3回,牛大水初次带队去捉便衣汉奸,结果人没逮到,还误伤了自己人,这事大伙都很懊恼。黑老蔡鼓励大家要经得起挫折的磨炼,“人在世上炼,刀在石上磨”(袁静,等,1978:43)。英译为“Men are sharpened by their experiences like a knife on a whet-stone”(Sidney Shapiro,1951:50)。译文基本保留了原文的主要结构,但是补充了两个重要信息:将经验对于人的磨练这一信息补充完整;同时,将人与经验、刀与石头的对等对象关系进行了类比,用直接和易于理解的方式进行表达。在第13回,大水跟申宗耀谈话后希望他帮忙把那些被日本人和伪军扣押的保长放出来,申宗耀虽然口头答应了,可心里一直在盘算,“他肚子里大大小小几杆秤,正在称斤约两的活动着”(袁静,等,1978:177),英译为“In his mind, big and little scales were weighing all the pros and cons of his future action”(Sidney Shapiro,1951:140)。译文将申宗耀心里掂量的内容直接补充出来,这种补充说明清晰明了地表述了人物丰富的内心活动,更符合英语读者的思维习惯。
翻译离不开语言处理,尤其是含有显著的地方特色和民族风格的语言。如果只顾及译文的流畅,就会剥夺读者接触、体会中国丰富的地方语言及中国文化的机会;而过于忠实原文,又会让译文读起来别扭,无法满足读者舒畅的阅读感。译者灵活的处理方式,尽量保持了汉语语言特色和风貌,让读者领略到汉语熟语的韵味,毕竟人物原型是中国人,他们的语言必须与人物在作品中的身份相吻合。而作为母语是英文的译者,沙博理清楚了解何种程度的语言更适合英语读者,更能让读者感到自然。因此,在贴近原文的同时,又做了适度的调整、叛逆,以确保译文流畅,这满足了英语读者的心理期待,生长在美国的译者本能、自觉考虑到了英语读者的思维习惯从而保留了英语读者的审美期待。沙博理曾总结过好的文学翻译需要同时表达内容和文风,“译者除了要透彻了解作品历史和文化背景,人物的个性和特征、人物生存的自然环境,得同样透彻地熟悉外国的对等词语——或不如说外国最接近原意的近似词语。英语要近似中文原文的风采,或文或俗,或庄或谐,切不可二者混为一体”(沙博理,1991:3-4)。译者超越作者,不仅抓住了翻译时需要补充的地方,而且把它上升为自觉的内容,充分体现了译者在主体间性中为寻求平衡和译介效果而做的审美再创造。
而对于章节标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译者在标题后面添加了年代,将小说内容的时间分段记录清楚,毕竟在翻译章节标题时译者选择了贴近原文的处理方式,而作为英语读者仅凭这些标题未必能十分明了故事的发展过程和步骤,用时间进行记录和提示或许更便于读者的理解。章节标题的英译策略呈现出“直译”为主、以“源语”取向为主的特点;全文总共20回的标题中,除了8、9、18等章节以外,其余的章节均是汉语原文的直译,而其中第8章的翻译颇值得探讨。
第8章的标题“大扫荡”译为“Iron Heel”,这一章讲述了1942年日军发动的“五一大扫荡”期间异常残酷、野蛮的行径,译者的译文与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小说同名,该小说反映的是劳动人民对抗财阀阶级的斗争史,这个主题与中文小说章节中所要表达的主旨是吻合的,而且,“iron”与“heel”这两个词给人的意向本身就是铁腕、高压,这两个词的翻译在译文语境的关照下,正好与原文语境中的大扫荡的残酷在深层意义上构成对应,英语读者看到译者的这种处理应该比直接翻译成“大扫荡”更能产生共鸣,该标题的翻译正是译者为了更好的阅读效果而创造译文意义的个性风格体现。
除了语言的灵活处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大量运用了删节、省略、改编等策略,比如上文所提到的回目的处理,正文中歌谣、歌曲等的处理等。男女主人公爱情故事的歌谣主要有3处,译者也多采取了节译、省略等方法。沙博理对此的考虑是: “向国外读者译介中国作品要考虑受众对象。若有些作品的内容外国读者看了没有什么兴趣,或与作品最重要的主题脱离,可以翻译也可以不翻译。” (沙博理,1991:3-4) 另外,这些删节、省略、改编之处的内容完全没有影响读者对内容的理解,这样的处理方式于读者而言不会有任何信息的流失。译者的处理还避免了过多过长的注释、说明,虽说个别之处会有一定程度的遗憾,但总体而言并没有背离原文的初衷,并且译文阅读起来流畅自然、小说化,增加了译本的可接受性。正如沙博理(1991:3-4)自己总结的: “如果原文重复太多,啰里啰唆,我以为可以允许压缩。这些做法对形式会稍有改动,不致改动根本的内容,有助于外国读者更加清楚地理解原意。”
翻译强调语言表述的忠实,但是忠实不应该是对原作的复制性的刻板忠实。译者能够识别原作文体中的拖沓、冗长、重复以及语言表达上的特点,并且有意识地在译作中改进、润色、提高。译者有意识的删节、节译、改编正是译者对于原文创造性的叛逆,构成了翻译过程中的主观向度,当然这种再创造受译者对原文本内容的理解的引导,同时又兼顾读者阅读期待的一种能动性的驾驭,正所谓尽可能地忠实,必不可少的自由。在力求忠实信度的前提下,译者始终面临选择,务必充分考虑译文与原文以及与译文读者之间的关系。这是原文对译者或者说译文读者对文本的接受程度制约了译者所运用的策略,更是译者在可控范围内最大限度地协调主体间的关系,确保翻译效果的一种翻译意识体现。
3 结语
曾有学者这样评价沙博理的翻译,“信而不死、活而不乱”。所谓“信”,是指译文在内容和风格上最大限度地忠实于原作,所谓“不死”,是指译文在具体表达上不拘一格,只要能达到翻译的目的,译者皆能视具体情况灵活运笔,大胆操控。“活而不乱”是指方法虽各有巧妙,但翻译的宗旨和目的却未有随意的变更(张经浩,等, 2005:322-323)。这部作品是沙博理翻译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译文难免还有不尽完美之处,在此就不一一列举。沙博理的翻译观念在日后的翻译过程中日臻成熟和完善,但是作为译者的第一个译本,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之中,为了保证译文的政治正确性,译者必需发挥主体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可以体会译者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情感、审美情趣等都介入到文本解读的过程,体会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运筹帷幄和所能掌握的空间,体会到译者主观能动性、受制性、主体间性之中的平衡与调整,从而把握译者主体性的完整意义。本文正是以此为核心指导,在这三者中挖掘译者的主体价值,避免出现顾此失彼,有失偏颇的解读。
随着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语言、文学、文化日益受到世界关注。如何通过翻译将我们的文学和文化推介给那些感兴趣的外国读者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话题。如果翻译的作品符合译入语国家读者的期待,它当受到读者的欢迎,译介效果就好。这并非要一味地迎合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学的看法和审美。但是,在翻译过程中,译者灵活平衡翻译过程中牵扯的各种因素,争取让中国文学走出国门,为广大海外读者所阅读和接受,这就要求译者不仅有扎实的语言基础,积累丰富的文学、文化修养,还要熟知国外读者的思维方式和阅读特点,避免“以我为主”,如此才能起到良好的译介效果。当今“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应当更加注重译者的培养和翻译质量的提升,建构可行的英译作品的翻译思路,将中国文学、文化、思想传播介绍到海外。
Derrida, Jacques. 1985. Des Rours de Babel [G]∥ by trans. Joseph F. Graham.DifferenceinTranslation. Joseph F. Graham Ithaca and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Lawrence, Venuti. 2004.TheTranslator’sInvisibility[M].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Robinson, D. 2001.WhoTranslates?TranslatorSubjectivitiesbeyondReason[M]. New York: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Press.
Shapiro, Sidney. 1951. Daughters and Sons[J].ChineseLiterature(1): 19-22.
本雅明. 2000. 译者的任务[G]∥陈德鸿,张南峰.西方翻译理论精选.香港: 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方梦之.2011. 中国译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何琳,赵新宇. 2011. 沙博理与《中国文学》[J].文史杂志(6): 35-38.
洪捷. 2012. 五十年心血译中国——翻译大家沙博理先生访谈录[J]. 中国翻译 (4): 62-64.
胡牧. 2006. 主体性、主体间性抑或总体性——对现阶段翻译主体性研究的思考[J]. 外国语(6):66-72.
伽达默尔. 2005. 哲学解释学[M]. 夏镇平,宋建平,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李振. 2009. 关联理论视角下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以沙博理译“茅盾农村三部曲”为例[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 120-128.
廖旭和. 1992. 美国专家沙博理 [J]. 国际人才交流 (9):1.
林煌天.2005. 中国翻译词典[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刘彬. 2010. 勒菲弗尔操控论视野下的十七年文学翻译[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7): 93-97.
骆忠武. 2013. 中国外宣书刊翻译及传播史料研究(1949—1976)[D]. 上海:上海外国语大学.
马兴丽. 2015. 意识形态及翻译行为视角下沙博理翻译行为研究——以沙译本《新儿女英雄传》为个案 [D]. 重庆:四川外国语大学.
马祖毅,任荣珍. 2003. 汉籍外译史 [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马祖毅.2006. 中国翻译通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欧晓南,贾德江. 2012. 译者主体性在文学翻译中的体现——以《水浒传》两英译本的谶言翻译为例[J]. 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 (4): 115-117.
任东升,张静. 2012. 试析沙博理的文化翻译观——以《我的父亲邓小平》英译本为例[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1): 105-109.
沙博理. 1991. 中国文学的英文翻译[J]. 中国翻译 (2): 3-4.
孙建成. 2008. 水浒传英译的语言与文化[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屠国元, 朱献珑. 2003. 译者主体性:阐释学的阐释[J]. 中国翻译 (11): 8-14.
王晓燕. 2013. 新中国1949—1966“红色”小说英译研究——以沙博理《新儿女英雄传》英译为例[D].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
武际良. 1998. 沙博理的中国情[J]. 纵横 (8): 35-39.
袁静,孔厥. 1978. 新儿女英雄传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查明建, 田雨. 2003. 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J]. 中国翻译 (1): 19-24.
张贺. 2010. 带着理想去翻译[N]. 人民日报,2010-12-03.
张经浩,陈可培. 2005. 名家名论名译[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张中江. 2011. 著名翻译家沙博理:我的根儿在中国[EB/OL]. [2011-03-30]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1/03-30/2940435.shtml.
邹丽. 2008. 鱼和熊掌可以兼得——浅译沙译本Family的翻译策略[J]. 成都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1): 120-123.
朱献珑, 屠国元. 2009. 译者主体的缺失与回归——现代阐释学“对话模式”的启示[J]. 外语教学 (9): 97-99.
责任编校:蒋勇军
A Study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Based on Sidney Shapiro’s Translation ofSonsandDaughters
XU Tingting
The study of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is interrelated to the study of theo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and the inter-subjectivity among the translator, the reader and the tex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SonsandDaughtersby Sidney Shapiro, which was published when translation and publication are under the strict control of political ideology. Through the in-depth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the titles, the foreword of each chapter, the idioms, and the folk songs, the translator is found to minimize the restriction of the political ideology and plays a positive and flexible part in building up subjectivity and inter-subjectivity in the process of translation so a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ranslation, which is exemplary for the study of translation in the context of expanding Chinese literature through translation.
SonsandDaughters;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translator; objectivity; inter-subjectivity
H059
A
1674-6414(2017)03-0104-07
2017-01-16
四川外国语大学科研项目“美国学‘中层理论’之于中国美国学研究的启示 ”(sisu2015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徐婷婷,女,四川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翻译和美国社会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