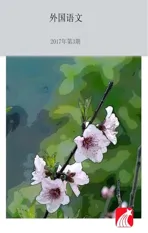《讲故事?听故事!》的叙事移情策略分析
2017-03-11钟秀妍
钟秀妍
(惠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讲故事?听故事!》的叙事移情策略分析
钟秀妍
(惠州学院 外国语学院,广东 惠州 516007)
依据苏珊·金的“策略性叙事移情” 理论解读海地裔美国后殖民小说家艾薇菊·丹提卡(Edwidge Danticat)的短篇小说集《讲故事?听故事!》*小说名《讲故事?听故事!》(Krik?Krak!)是笔者自译。在海地,krik?是请求别人讲故事,听故事的人要礼貌性地回复krak.(Krik?Krak!),可以发现后殖民小说家如何成功地运用多重策略性叙事移情手法,使文本产生移情功效,激发多元读者群的情感共鸣。这一研究同时揭示了认知理论可以为理解移情提供新的方法,达到对文本更深的理解。
认知后殖民理论;叙事移情;情感;文化
0 引言
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尤其是计算机科学的迅速发展,认知科学作为一门学科开始萌生并在70年代末宣告诞生,使“认知革命”引发了许多学科的“认知转向”,也就是将自身的研究与认知科学结合起来,从认知科学中吸取灵感、方法和研究范式。这种影响遍及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哲学、宗教、教育、伦理、文化学、政治学等领域(熊沐清, 2015)。然而,在20世纪末,一些后殖民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认为,文学文本中的维恩图解关系(Venn diagram of relationships)、移情技巧和效果以及文学认知主义所提供的理论框架并不适用于后殖民文学研究(Zunshine, 2015: 348) ,甚至认为后殖民文学批评理论应该抵制认知主义。他们的理由是:长期以来,认知主义使用实验手段,对人类心智和身体工作机制的普遍性解释,关注人类的心智普遍性,而忽视了各种各样真实的人类行为、身体经验、情感和心理体验。相反,后殖民文学批评理论认为人类行为具有语境特异性,关注人类差异性,不承认人类情感、行为具有普遍性。而且,后殖民理论家认为认知主义缺乏跨文化对比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为了更好地理解认知和情感,很多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开始关注认知科学,并逐渐以此替代了精神分析和后结构主义。一些学者开始审视和批判后殖民理论,一些认知学家也在考察主流后殖民理论产生的一些主要问题,而且着手从人类认知与情感方面解决这些问题。帕特里克·霍根(Patrick Colm Hogan)教授则更关注认知情感。尤其是认知后殖民理论强调呈现和情景化人类认知和情感共性,更是为深刻理解叙事移情提供了方法。
1 基于认知的“策略性叙事移情”
叙事移情是读者与文本世界及故事人物的情感共鸣(融合),包括“由阅读、查看、听力或想象故事的另一个的情况和条件引起的共享感觉和换位思考。叙事移情在作者创作审美作品时能够体验到并发挥作用。当读者阅读作品时它是一种心理模拟,读者接受作品时也能体验到;此外,它在文本的叙事诗学中作为正式策略使用”(Keen, 2012)。目前,认知文学研究已经将叙事移情作为文学认知的一个方面来研究。认知科学领域内对叙事移情的研究已经有相当的进展,研究者们探讨了作者和叙事艺术家把移情用在人物创造和其他可能世界创造方面以及不同读者方面的反应,例如莫妮卡·弗卢德尼克(Monika Fludernik)的 《“自然”叙事学》(Towardsa“Natural”Narratology,1996)涉及了体验,玛丽·赖安(Marie Laure Ryan)的《作为虚拟现实的叙事》(NarrativeasVirtualReality,2001)谈到了沉浸(immersion),认知科学家丹·约翰逊(Dan R. Johnson)的《个性和个体差异》(PersonalityandIndividualDifferences,2011)讨论心智意象和利他行为(altruism)等等。因而,理解叙事移情涉及心理学、对语境的敏感性、对认知普遍性和情感普遍性的认识以及当代认知主义的多个方面。
许多后殖民作品采用一系列的表现技巧来创造移情效应,所以叙事移情一直是后殖民小说研究的核心要素,对叙事移情研究也是认知后殖民文学研究的一部分。叙事移情关注的焦点是人类普遍性的心理、认知、情感研究,人类情感的跨文化研究;后殖民对人类共性的批评。基于叙事移情的认知后殖民研究更加关注文化语境,同时重新确立了后殖民理论与认知文学研究之间的关系。
美国学者苏珊·金将叙事理论、认知、情感和文学研究结合在一起。她基于认知和情感科学家的研究对移情展开分析,具体概括了作者和评论家对移情的态度,注重移情的价值和缺陷。在对待移情的问题上,考虑作品的目标受众十分关键。因而,金根据作品读者归属进行了分类,提出了3种策略性叙事移情(Strategic narrative empathy),分别是限定性策略叙事移情(bounded strategic narrative empathy)、代表性策略叙事移情(ambassadorial strategic narrative empathy)、普遍性策略叙事移情(broadcast strategic narrative empathy)。目标对象和作者的内外群体相关,目标对象不同,使用的策略也就不同。如果把目标受众孤立起来,叙事移情策略就难以理解。
限定性策略叙事移情的目标受众是内部成员(in-groups),他们与文本世界及人物没有时间、空间差异,也不受种族、国别、信仰等因素的干扰,这些读者最容易激发移情效应(Keen,2008)。代表性策略叙事移情的目标受众则是指与文本世界和人物在时空上相隔甚远、文化上差别很大的读者群。作者通过这种策略试图将情感传递给本区域外的读者群,改变他们对这一地区的态度,诱导他们在现实中提供帮助。最典型的是,作者通过代表性策略叙事移情与选定的目标读者群对话,借以引起他们的共鸣,至少带有一种呼吁正义、寻求援助和认同的含义(Keen,2008)。普遍性策略叙事移情的目标对象是所有的读者,通常是基于人类普遍经验和对特定情境的共同反映来激起读者的情感共鸣(Keen,2008)。无论读者是否与作者和故事人物共享同一个时空,都使所有读者感觉是一个整体,因而这种策略在历久不衰的经典作品中最常见。它强调我们人类的共同经验、情感,克服了巨大的地理差异、历史差异、文化身份差异和日常生活差异。
后殖民写作中似乎普遍性策略叙事移情不太常见,但这并不意味着后殖民作品的受众局限在群体内成员或群体外成员。相反,意味着作品面对所有受众,只是对受众进行某种程度上的区别。作者可能将作品的某部分的受众定位在群体内成员,或将某部分的受众定位在群体外成员,又或是同一部分意在群体内外成员,只是采用不同的处理方式而已。苏珊·金认为这3种策略性叙事移情都是作者为了影响、甚至操纵潜在的目标受众的思想情感、态度、行为所采用的叙述策略和技巧,也就是说大部分作者试图在读者身上开发出一种策略移情。
2 《讲故事?听故事!》的叙事移情策略
虽然没有一本小说或故事能够使所有读者都产生移情,但是有一些文本却被认为能够激发许多读者的共鸣。《讲故事?听故事!》就是其中之一。继处女作《息· 望· 忆》(Breath,Eyes,Memory)于1994年出版后,海地裔美国作家艾薇菊·丹提卡于1995年出版了她的短篇小说集《讲故事?听故事!》。这部小说集入围国家图书奖最终提名,并且被翻译为克里奥尔语在海地电台播放。2015年,为了庆祝小说集出版20周年,丹提卡又在原版本的尾声后加入另外一篇短篇小说,共10篇。小说的人物来自作者虚构的Ville Rose小镇,展现了生活在这里的不同年龄、各行各业的海地人尤其是海地妇女及儿童的生存状况以及海地裔美国移民的异国感受,探索了人们内在欲望与残酷现实的距离。
10篇短篇小说看似独立,但依据故事情节可看出由3条主线贯穿。第一条主线是通过“BetweenthePoolandGardenias”小说中叙述者I(我)的描述,将其中几篇小说贯穿起来。“ChildrenoftheSea”讲述的是I(我)的曾祖母Eveline的故事,“NineteenThirty-Seven”讲述的是I(我)的母亲和祖母Defile的故事。“AWallofFireRising”则是I(我)的教母一家人的生活。“TheMissingPeace”讲述的是I(我)的阿姨Marie的女儿Lamort的生活。第二条主线贯穿着“NightWoman”和“Seeing Things Simply”,主要讲述普通海地人的生活状况。第三条主线贯穿着“NewYorkDayWoman”“Caroline’sWedding”和“IntheOldDays”,讲述了海地裔美国移民的生存状况。笔者依据3条主线和3种“策略性叙事移情”从10部短篇小说选取6篇,并分为3部分具体分析,看作者是如何成功运用多重策略性叙事移情激发读者的情感共鸣。当然叙事移情理论认为叙事小说都有潜在的多元读者群,通常一个单一的作品中都可以运用多种不同的策略来面对多元读者群,所以笔者在此讨论的是面对一部作品可能产生移情效果最强烈的读者群。
2.1 “群体内”的情感融合
“ChildrenoftheSea”和“AWallofFireRising”以多米尼加共和国对海地的战争为背景,讲述战争中的海地人的生活,孩子对爱情、自由和读书的憧憬,妇女对家人团聚和幸福生活的期盼。作者采用了限定性策略叙事移情,将文本的可能受众锁定在内部成员,也就是海地人民。因为只有经历过这段岁月的海地人读到文中人物遭遇时才能唤起往事的记忆,才能深刻体会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自然也就比其他读者投入更多的情感,使移情的效果更加显著。
“ChildrenoftheSea”中的主要人物是一对刚刚通过大学入学考试的情侣。文中各小节分别由男孩和女孩以第一人称I的口吻自述,一一对应。使读者感觉好像天各一方的恋人穿越时空,面对面互诉衷肠。女孩讲述了一家人由首都太子港逃往Ville Rose小镇一路上所见所为。女孩对邻居罗杰的遭遇深感痛心,但又无能为力。罗杰因为儿子的死备受打击,还要忍受士兵们对她时不时地骚扰和恐吓。罗杰对士兵吼道:“你们已经杀死他了!还想杀了我么?尽管来吧。我不在乎,我已经死了。你们做了最残暴的事情,杀死了我的灵魂。”*文中引文均为笔者自译。(Danticat, 2015:13-14)罗杰的歇斯底里的叫喊(screaming)证明了她对士兵暴行的忍无可忍,对失去儿子的痛心疾首,自己生无可恋。经历过战争并失去亲人的海地人民,读到此处,对罗杰的内心痛苦会深有触动。
在战争的笼罩下,有些人为了生存铤而走险去美国,其实又是踏上了另一条死亡之路。男孩Konpe因参加斗争被士兵追杀逃亡到美国,记录了在船上的所见所闻: “船底传来一声破裂,看起来是破了个洞。如果洞口越来越大,就能把船扯成两半。船长让我们躲到一边,并用柏油把洞糊起来……我们要把额外的一些东西扔到海里,因为海水已经开始慢慢地渗透到船里……我昨天听到船长对被别人说他们可能要把那些久病不愈的人扔到海里”。(Danticat, 2015:17) 在海上偷渡有很大的危险,既要面临恶劣天气、触礁、疾病、缺水等,也要时刻警惕海岸警备队的巡查。这些危险时刻危及生命,只有亲身经历过并且生还的海地人才能真正明白其中的苦难。
“AWallofFireRising”展现的是海地人民对和平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女主人公莉莉是一位勤劳、聪明、勇敢的家庭主妇。男主人公盖伊是甘蔗厂的厕所清洁人员。盖伊好不容易得来的那份工作其实还只是排在78名,所以他想把儿子的名字放上去,等儿子长大就可以做这份工作。但是莉莉不同意,她认为这样做会断送儿子的前途。莉莉十分重视儿子的教育,在家教儿子背诵海地废奴领导者Boukman关于自由的演讲:“记住,你是一位伟大的反抗压迫统治的领导者。记住,这是一场革命……在你脑海里唯一的一件事是什么?……‘自由!’……‘大声点!’ ‘自由在我心中!”(Danticat, 2015:47) 莉莉一次又一次的向儿子强调,儿子一遍一遍地由心底喊出(shouted, yelled)自由。无论是在大人眼中还是孩子心里,自由是唯一活在他们心中的希望。然而,生活在和平民主国家的读者们,对反抗剥削和压迫是没有概念的,更无法想象自由对他们意味着什么。
虽然在千禧年之后,SUV的概念已经逐渐向公路行驶倾斜,但第三代路虎发现仍旧配备了和揽胜几乎没有差别的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这套可以根据路况进行选择,通过电子控制技术调整几乎全车设备以保持最佳行驶性能的系统让第三代路虎发现拥有了最为全面的性能表现,与此同时也彻底解放了驾驶者。驾驶者只需要了解自己所身处的环境,正确选择全地形反馈适应系统所提供的选项,剩下的就全部交由第三代发现来完成就好。
盖伊对自由更加渴望。他用最简单的文字“a really nice place、 something new 、my own house、my own garden ”(Danticat, 2015:61)来展现他心目中的自由就是远离这里开始新的生活,过最平淡的日子。但他最终为自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他偷偷地坐上老板的热气球,升上天,从空中跳下身亡。面对家庭的突变,莉莉和孩子十分镇定。孩子知道父亲这样做的原因,所以他跑到在父亲身旁开始背诵演讲,“用一个男人悲伤的声音咆哮”(Danticat, 2015:67)。孩子的动作(yank、race)和行为让读者看到他的勇敢和坚强。与此同时,莉莉最后一次仔细地端详了死不瞑目的丈夫,对身边的人说他喜欢看着天空。妻子明白丈夫是多么渴望走向自由的天空,这种追求自由的方式再一次证明海地人生活的无奈和艰辛,并且愿意为自由付出生命代价也在所不惜。
这两篇小说将受众锁定在海地人民尤其是经历过这场战争的海地人,最能引起移情反应。读到这些小说时他们的思绪会回到那个年代,尤其是人物和自己有着共同经历的时候,伤痛和苦难会再次撞击他们的心灵深处,那么对作品的理解自然比其他读者将更深入。
2.2 “群体外”的情感共鸣
“NightWoman”和“SeeingThingsSimply”这两篇小说讲述了普通的海地妇女和女孩的生活。作者采用代表性策略叙事移情,将文本可能受众锁定在外部成员,希望与文本世界相隔甚远尤其是文化上差别大的读者能够关注到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群。也正是通过对微小人物生活的刻画,作者才能抓住普通读者的内心,将受众扩展到买书的人、世界范围内所有受到人道主义帮助的地方和人群等,不仅只限于海地人。
“NightWoman”是一篇关于一位海地妓女的内心独白。小说开篇写到她畏惧夜晚的灯光,好像能把脸上的皮肤刺激得皮开肉绽,但是又害怕自己青春不再,只要活着就要依靠这张脸在夜晚“工作”,内心中无奈和痛苦一目了然。不仅自己要生活还要养活儿子,每个夜晚都要为儿子讲故事、唱歌,哄他睡觉。但是随着儿子年龄增长,她怕儿子知道自己的“工作”,想着儿子看到她时会有什么样的对白“他说‘妈妈’ ,我说, ‘亲爱的’”(Danticat, 2015:90),用Mommy和Darling两个单词完成对话,但是读者明白这里 “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儿子或许是疑惑或许是震惊抑或是感到羞耻,母亲或许是害怕或许是痛苦抑或是无奈,所以留给读者很多空白去填补,也再一次证明了作者希望“妓女群体外”的读者理解她们生活的艰难和无奈,希望大众能够正确看待妓女尤其是生活在海地这个特殊地方的特殊职业人群,尽管对她们的身份不予认同,也期望能够改变对她们的态度,毕竟她们也有着自己的辛酸无奈。
“SeeingThingsSimply”开篇讲述16岁的海地女孩Princesse路过斗鸡的地方,碰到醉酒的学校老师唯恐避之不及。之后她来到小镇上外国人聚居的地方,为巴黎画家凯瑟琳做裸模。Princesse知道自己的身体和别人一样,然而除了她没人愿意这么做。但是她内心又是矛盾的,既害怕别人会看到,又安慰自己死后什么也就无法在乎了,也只有凯瑟琳和上帝知道。她这样做唯一的目的就是希望学到一些画画的技巧,但是凯瑟琳却只与她闲聊。尽管如此,聪明的Princess每次都能学习到很多不同的东西。通过凯瑟琳的潜移默化,Princesse的水平不断提高“她想画声音……她想画感觉……她想画自己……”(Danticat, 2015:119)。她有了画家的敏感性和观察力,都得益于凯瑟琳的“闲聊指导”。凯瑟琳离开小镇后,她拿起画笔,画的是醉酒的老师和他妻子。凯瑟琳和Princesse本是不可能有任何交集的两类人,和那些战地记者或是支持和平的人们一样,他们与海地人素不相识,却给予了力所能及的帮助,正如凯瑟琳所说也许越是渺小的事物,比如人类,越是能改变并影响着宇宙中的大事物。正是这些看似普通却并不普通的人们对海地人民的关注和帮助,才能使更多的人去帮助海地人民改变生活现状。
这两篇小说中作者克服文化等方面的差异,让“群体外读者”了解到他们可能并不关心和在意的人和事,同时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能够引起读者移情的不一定是悲剧性人物,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些“有血有肉”的人物,让读者切实感受到即使不在同一时空,也仿佛是发生在自己身边,这样才使得移情叙事所激发的不单单是一种情感反应,更重要的是对海地人民、对世界范围内需要帮助的弱势群体给予人道主义救助。
2.3 “群体内外”的情感共享
“NewYorkDayWoman”和“Caroline’sWedding”展示的是海地移民背井离乡、定居美国的历程。和其他移民一样,他们带着本土的传统文化和知识经验来到美国,经历着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所以,无论读者是否是移民,又或是本土人士抑或是其他民族的人民,是否与作者和故事人物共享同一个时空或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读者都能克服地理的、历史的和文化身份的差异,寻找到我们人类的共同经验、情感等,所以作者在这两篇小说中采用了普遍性策略叙事移情,目标对象是所有的读者。
“NewYorkDayWoman”中的母亲难以融合进美国文化,是海地文化和美国文化结合产生的矛盾体。叙述者I(我)的母亲从来不去布鲁克林之外的街区购物,也不去我的公司,而且害怕乘地铁,因为可能会碰到抗议黑人女性的游行活动。母亲的这种恐惧的根源是美国社会和海地社会对黑人女性的歧视。对于海地,母亲的记忆充斥着暴力和血腥:“在海地,如果你被车撞了,车主会对你拳打脚踢。”(Danticat, 2015:128)也有对同胞的怜悯和帮助 “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予那些回乡的人们一些衣服呢?在海地,我们还为亲戚们省下些衣物” (Danticat, 2015:131),以及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的思念。所以她对海地的依恋造成了自己难以融入美国文化。但是,我却惊讶地发现母亲喜欢吃街边的热狗和法兰克福香肠。由于血压和心脏问题,我曾试图劝说母亲少吃,但是她回答:“我不能只吃盐啊。盐比羞耻还要沉重。”(Danticat, 2015:132) 相反,对我的事情,母亲却十分谨慎。她从来不去参加我的家长会,因为 “不想你为我感到羞耻。羞耻比盐要沉重” (Danticat, 2015:135),母亲不想因为她的缘故让我也难以融入这个社会。同样的一句话,母亲将Salt和Shame换了位置,这样矛盾的比喻恰恰体现了她矛盾的内心。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母亲只是生活在美国的海地人。所以,即使她的穿着像美国人,但她始终不能像美国人那样自由的穿梭在美国的大街小巷。和其他民族的移民一样,在多元文化的美国生存,必然会产生两种文化传统的组合体式人物。
“Caroline’sWedding”是围绕着叙述者I(我)的妹妹卡洛琳的婚礼展开的故事。25年前我跟随着怀孕三个月的母亲从海地来到美国,25年后在文章的开篇,我拿到了美国入籍证明,在母亲的要求下马上去办理护照,因为母亲认为只有护照才能证明你是美国人。对于移民,身份是他们一生中最看中的事情。然而,生长在美国,卡洛琳就与我和母亲不同。在这个家庭中,母亲是海地人,我是美国的海地人,卡洛琳是美国人。小时候,每当姐妹俩不接受海地文化特色的时候,母亲都会很尴尬地对别人解释说她们是美国人。但是,我还是会陪着母亲去教堂悼念每周在海上遇难的海地难民,而卡洛琳却为母亲煮了她喝腻的牛骨汤喋喋不休,母亲此时就会很不满意地说你以为自己是美国人,你都不知道什么对你好。其实最让母亲难过的是卡洛琳的婚礼,她希望卡洛琳的丈夫是海地人,更希望他们能够按照传统举办海地人婚礼仪式。但是一切都不和她的心意: “很美国化……一切都是机械化”(Danticat, 2015:172)。所以对于母亲这个海地人来讲,美国的一切都不美好。
而我虽然理解母亲孤独悲伤的内心,但是也不能阻止妹妹的婚礼,只能劝慰母亲。在妹妹婚礼后,母亲说:“为什么当你失去一些东西,总是要到最后才会去寻找……因为,你记着,就一定是不会去找寻。” (Danticat, 2015:188)母亲觉得姐妹俩失去了海地人的文化,更觉得自己失去了姐妹俩。所以她停在原地不断地寻找原因,其实也只是她坚守海地文化的表现。我作为生活在美国的海地人,既能理解母亲,也能接受妹妹的行为,也一直在母亲和妹妹之间寻找着内心的平衡。
在这两篇小说中,作者的写作视角转移到美国本土,同时读者的范围也随之扩大。首先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或是美国移民,或多或少都会有相似的经历,例如华裔移民也同样感受着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其次扩展到世界范围内,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永远是大众关注的焦点之一。因而,面对人们共同的情感和文化,多数的读者都会产生一定程度的移情。
3 叙事移情的功效和产生的问题
作品的叙事移情功效是一个作品进入其他文化读者群的通道。丹提卡使用了许多策略和技巧,增强了虚构叙事的移情效果,引起多元读者的情感共鸣。首先,她选取儿童、青少年、妇女这类社会弱势群体作为中心人物。其中大部分人物是受过教育并富有创造力的,比如Princesse。其次,她集中表现人类个体在毫无希望的状况下所表现出的创造性,例如莉莉和盖伊。最后,她讲述了受害者遭受迫害和剥削的故事,例如Konpe和罗杰。这些策略的运用使读者能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小说人物的艰难与困苦,从而引起大众对特定群体的关注,并呼吁对他们给予无私的援助和支持,这就是叙事移情的社会效应。例如,丹提卡的儿童读物EightDays的献词是“谨以此书献给海地儿童”,但是这本书不仅仅是献给海地儿童而且是献给所有海地人的。据出版社和学术机构的统计,作者仅以此书的收入已经向人道主义援助机构累计捐赠了10万美金,用于帮助全世界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叙事移情通过拉近读者与故事人物之间的情感关系,促使读者沉浸在故事世界之中,这就是它的沉浸效应。目前尚不能确定这两种功效是共存还是互斥关系,但是可以做出假设:沉浸越深,移情效果越强烈,对现实回应就越大,比如捐款、游行示威等。相反的情况也可能发生:沉浸越深,与现实情境的联系就越微弱,因为有些读者可能沉浸在故事内而不能自拔,只是一味地对人物的遭遇表示同情。所以,叙事学家的这些论断正在进一步被心理学家证实。但是实验已经证明,至少在短期内,读者对故事世界及人物的沉浸能够提高移情效应和助人行为。不过,叙事移情对读者行为的长期效应还有待研究证实(Nell, 1988)。
通过移情的功效可以看出,无论文学作品是否能引发移情,主要看其对现实社会产生的作用。成功的叙事移情能够跨越国界、超越种族差异,并在异国他乡产生积极的社会效应。
那么叙事移情在引导人的现实行为方面如果没有起作用,就是失败的移情(Failed empathy)。失败的移情是指在诱发行动中,无效的共享情感的问题(Keen,2007:159)。批评家对失败移情的批判着眼于人权,直率地指出失败移情是由于过分痛苦而造成同情心丧失。麦克法兰(McFarland)的研究表明心灵上的移情与对人权的支持态度密切相关,但是态度不是行动。他进一步说个体对人类共性的认同与其对人权信仰的积极践行密切相关。如果在读者在心灵上移情了但却不愿意付出行为,就是失败的移情。这种冲突就产生于行为和态度之间(McFarland,2010)。例如,有些读者对丹提卡作品中描写的海地流离失所的儿童产生移情,看到儿童的悲惨遭遇而为他们痛苦不已,那么他们为海地儿童募捐了吗?或者到海地参与人道主义援助了吗?又或是他们只是与虚构人物的感情融合,感同身吗?对于海地读者来说可能最能引起移情反应,但是进入世界范围后,尤其是不了解杜瓦利埃政权统治时期海地人民生存状况的读者来说,有些可能会显示出一种冷漠的、毫无情感的反应,甚至会对那些残害事件产生厌恶、呕吐的感觉。虽然叙事伦理避免这种可能性,关注美德的培养,但是不人道的描述促使读者的厌恶甚至促使暴行的实施和对人权的侵犯(T. Harris & T. Fiske, 2011)。
第二种可能产生的问题是虚假的移情(False empathy),读者错误地认为他们能从不同的文化、性别、种族或阶级等方面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Keen,2007:159)。虚假的移情批评者认为有的读者读完作品之后,与故事人物的情感共鸣只是自欺欺人。这种情况下读者感觉自己非常了解作品中人物的遭遇,进而认为自己是心地善良、品格高尚的人。所以,虚假的移情关注的是移情者本人的感情。读者过度关注本人的感情,这样所产生的移情效果其实不是发自内心的真正关心,而是被个人感觉驱使。正如叙事移情可能引发读者回报社会的行为,也都有可能使读者陷入这样一种错觉。例如,丹提卡小说中描述到忍饥挨饿的儿童,看到他们饥肠辘辘,难道有些读者此时就有饥饿的感觉吗?如果有,也是一种错觉。当读者看到战争作品时都会用残酷来形容它,是否内心真正理解战争究竟残酷到什么程度。其实很多时候对于未经历过的事情是永远无法深刻体会其中的内涵和深意。
叙述移情通过深化读者与叙事虚构人物的感觉联系,可能使读者沉浸在一个虚构世界的假象中,但是读者是否会产生真正的移情,并在现实世界中采取行动就要根据读者自身的情况而决定。一些殖民地作家希望读者产生移情,也希望与他们相关的一些政治政策得以改善,这就取决于作家写作的侧重点和移情策略的使用。
4 结语
丹提卡的作品将叙事移情体验与真实世界的利他行为结合起来,和许多作家一样认为叙述移情与公民道德行为有一定关系,完全符合认知主义模型。所以,对后殖民作品的策略性叙事移情的研究重点转移到读者选择什么样的阅读经验,读者如何共享作品,以及作品如何鼓励读者本人和他人对情感反应做出行动,使得认知文学研究和后殖民文学得以有力结合。
Danticat, Edwidge. 2015.Krik?Krak! [M].New York: Soho Press Inc.
Keen, Suzanne. 2007.EmpathyandtheNovel[M].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een, Suzanne. 2012. Narrative Empathy[G]∥TheLivingHandbookofNarratology, ed. Peter Hühn et al. Hamburg: Hamburg University Press.
Keen, Suzanne. 2008.StrategicEmpathizing:TechniquesofBounded,Ambassadorial,andBroadcastNarrativeEmpathy[J]. Deutsche Vierteljahrs Schrift (4):77-93.
McFarland, Sam. 2010.PersonalityandSupportforUniversalHumanRights:AReviewandTestofaStructuralMethod[J].Journal of Personality (17):35-63.
Nell, Victor. 1988.LostinaBook:ThePsychologyofReadingforPleasure[M].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T. Harris, Lasana﹠T. Fiske, Susan. 2011.DehumanizedPerception:APsychologicalMeanstoFacilitateAtrocities,Torture,andGenocide[J].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1):75-81.
Zunshine, Lisa. 2015.TheOxfordHandbookofCognitiveLiteraryStudie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熊沐清.2015. 文学批评的认知转向——认知文学研究系列之一 [J].外国语文 (6): 1-9.
责任编校:肖 谊
An Analysis ofKrik?Krak!’sNarrative Empathy Strategies
ZHONG Xiouyan
This paper adopts the short stories collectionKrik?Krak! as the study object to analyze Suzanne Keen’s theory of strategic narrative empathizing with a view of considering the multiple audiences a postcolonial fiction writer Edwidge Danticat who seeks to reach and move. It reveals that the cognitive theory provides a more profound way for empathy and more understanding for text.
cognitive postcolonial theory; narrative empathy; emotion; culture.
I712.074
A
1674-6414(2017)03-0036-06
2017-03-20
广东省教研教改项目“基于PBL的英语阅读教学改革与实践”(粤教高函[2016]236号)、惠州学院精品资源共享课“英语阅读”(JPZY2014005)研究成果之一
钟秀妍,女,惠州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应用语言学、认知诗学、跨文化交际研究。